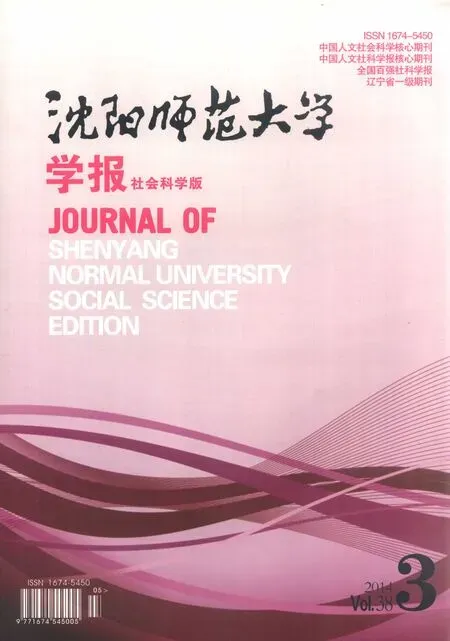1922年潮汕“八·二风灾”之各方救助
——民初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个侧面
2014-04-10孙钦梅
孙钦梅
(中国人民大学 历史学院,北京 100872)
1922年潮汕“八·二风灾”之各方救助
——民初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个侧面
孙钦梅
(中国人民大学 历史学院,北京 100872)
民国十一年(1922年),粤省潮汕地区经历了一场特大台风暴潮灾,因发生于是年8月2日,史称“八·二风灾”。本文通过对1922年潮汕“八·二风灾”及中央政府、地方官府和社会对风灾所采取的救灾活动的勾沉,分析了这次救灾活动的过程、特点及其所体现的近代特征。从中也能看出北洋政府时期在官方职能弱化的背景下,民间社会如何展现力量承担公共责任的事实。
潮汕;“八·二风灾”;救助;国家与社会
民国十一年(1922年),粤省潮汕地区经历了一场特大台风暴潮灾,因发生于是年8月2日,史称“八·二风灾”。据史料记载,这是20世纪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风潮灾,总计约有8万人丧身其中[1]17。面对突袭而来的灾难,当时的北洋政府、地方官府和社会各方都投入到这场救灾活动,从中可以窥探民国初年救灾机制的概貌,以及国家和社会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
一、灾后官方与民间救助活动的开展
1922年潮汕地区发生的这场灾难由台风引起,并引发海潮向内陆倒灌,使沿海一大片地区陷于汪洋之中。据《潮州志》记载,“灾区奄及澄海、饶平、潮阳、揭阳、南澳、惠来、汕头等县市”[2]5,灾害强度之大为广东省有风记录所仅见。
风灾发生后,北京政府由总统黎元洪拨出5万银元“以示助赈”,并于当年10月间派遣特使赖禧国抵汕视察慰问[3]26。北京“赈务处”亦决定“将所有汕头海关常关进出口货物一律附加一成,以一年为限”[4]31。但北京政府的救灾措施仅此而已。而此时的粤省政府正处于军阀混战中,再加上灾荒连年,对于各县市的灾荒已经力不从心。风灾发生后,省政务厅几乎未采取有效措施赈灾,只有盘踞潮汕的陈炯明将借款项下提抹6万元作为施赈[5]25。
从政府这一体系看,救灾的重任更多地落到潮汕地方政府的身上。风灾发生后,汕头市政厅、潮梅善后处会同汕头市总商会即成立“汕头赈灾善后办事处”(以下简称“赈灾处”),专门办理救灾事务。据《申报》报道,“当风灾之后,汕头市长、商会会长,及其余重要商人七人,即组一委员会,以料理处置死亡灾民、扫除毁伤对象、以及筹备救灾等事”[6]568。“赈灾处”不仅处理汕头善后事务,对潮汕其它灾区亦一同办理,实际上起了潮汕地区救灾总领导组织的作用。受灾各县也相继成立了赈灾公所、分所等专门性救灾机构。如澄海县县长李鉴渊即在澄海县设立救灾善后公所,又“分函各区各设分所一所,以为辅助机关,庶通力合作,易于成功而免漏滥。”[7]3普宁、潮阳等县镇也相继设立了赈灾公所和救灾分所。各级赈灾机构相继成立后,潮汕地方政府的赈灾工作随即迅速展开,具体包括:1.灾情调查。由“赈灾处”专设的“调查股”将汕头市划为八区,围绕死亡人数、房屋倒塌、堤围崩决、田园损失和财产损失等内容,分别进行考察。2.筹募捐助。“赈灾处”向社会广泛进行募捐,包括赈款、赈米和药品等。3.灾后清理。政府动员大量人力进行收埋死畜、清理垃圾和救济伤员等相关工作。
总体而言,就官方的救助活动而言,北京政府的应对无疑是疲弱无力的,潮汕地方政府尚能积极实行紧急应对措施,其力量依然有限。
相对官方而言,在此次救灾活动中,民间力量扮演了最为重要的角色。民间的救助活动主要体现在以下一些方面:
其一,传统民间义赈组织的救灾活动。清末以来,传统民间社会普遍存在一些义赈组织,包括会馆、公所和善堂等。灾情发生后,各地潮汕会馆迅速发起救灾。如上海潮州会馆,该会馆在接到乞赈灾函电后,当即决定成立“旅沪广东潮汕风灾筹赈处”,组织上海潮商捐助家乡风灾。善堂在救灾中也发挥着独特作用。历史上的善堂多以收尸殓葬为日常工作,到民国时期已经发展成为综合性民间救助的慈善机构,除收尸殓葬外,还包括施医赠药、救死扶伤、赈灾恤难等等。汕头存心善堂即是其中的典型代表。灾发后“存心善堂已派多人,沿向各处施救,死者殓之,伤者医之。”
存心善堂的行动感动了当地人,很多幸存者自愿请求加入到该善堂协助掩埋尸体,“至该善堂报名请往收埋者,亦达千数百号。”[8]268
其二,新兴慈善机构的救灾活动。中国近代化的慈善组织以中国红十字会为标志。“八·二风灾”发生后,中国红十字会总办事处立即作出反应,先后两次派医队前往灾区助赈:8月12日第一次组成医队,携带多箱药品,乘太古公司苏州轮船前往灾区救人;26日又加派救护队,携带药品数大箱,驶往灾区增援[9]47。中国红十字会南海分会、汕头分会、澄海分会、番禺分会也积极参与赈灾。如澄海分会在全埠电灯灭光,救护方法极难下手的情况下仍冒险展开救护行动,对附近的伤民极力救护[10]82。中国红十字会和各分会的救护工作使“各区灾民渐次平复”,最终取得了“八·二风灾”救护工作的圆满成功。
其三,新闻界和商界等新兴社会势力参与救灾。新闻界对此次风灾进行了广泛报道,号召社会各界支援救灾,并对各级政府救灾不力进行批评。商界则成为募捐的主要对象,以汕头为例,据第一期《汕头赈灾善后办事处报告书》记载,捐款主体为汕头各公司、银行、商号等,仅汕头一地,商人团体捐款就有四、五百家。其他如上海、广州等地的商人捐助也十分积极。
其四,海外力量的救灾活动。香港殖民当局“拨万元助赈”[11]15。港内团体“旅港潮州八邑商会”“中华商总会”“东华医院”以及“越南赈灾团”四团体,亦组设专门“筹赈潮汕风灾办事处”,并推举商会董事王少瑜为总代表率领赈灾团前往灾区救灾[12]56-57。海外潮侨也纷纷参与家乡救灾,以泰国、新加坡的潮侨表现最为突出。泰侨方面,在“泰国中华总商会”的组织下,国内潮侨迅速成立“暹罗(泰国)潮州台风海潮赈灾会”,并公推许少锋驻汕创办“暹罗赈灾团,帮助灾区襄理各项赈灾事宜。“暹罗潮州台风海潮赈灾会”创办人廖葆珊①原籍澄海区上华镇横陇村,清朝末年旅居泰国。因经商有道,为泰国洛坤王所信任。事业有成后,为服务侨商,于1910年与旅泰华侨高学修等人发起成立泰国华侨华人业缘性的最高领导机构——泰国中华总商会。之后长期在该会担任要职,并在第9届时当选为商会主席,成为当时泰国著名侨领之一。与高学修、郑子彬等人,并向泰六世皇奏陈潮汕灾,获得六世皇同情,特御赐泰币5千株助赈[13]180。在新加坡,由潮侨参与领导的新加坡商会在接到报灾电报后,即迅速成立“筹赈潮灾办事处”商议救助飓风灾事宜。该处决定先拨汇汕银1万元助赈,然后陆续筹备赈款。此外,华侨个人也为此次风灾的筹赈活动纷纷解囊,自动向廖正兴(祖籍潮安)、李伟南(祖籍澄海)等主持的四海通银行汇寄赈灾款,为数总共不下20万元[14]55。
二、“八·二风灾”的救灾特色及其近代化特征
以上分析了灾后的各方救助情形,从中不难看出此次救灾活动具有如下几个特色:
其一,民间力量起到了明显的主导作用。乾隆以前,官赈在灾荒赈济中占据绝对统治地位,民间的救灾组织是零散的。光绪年后,以民间力量为主导的义赈形式悄然兴起。至民国初年,民间慈善力量已经遍地开花,并超越政府力量在救灾机制中占居了主导地位。从潮汕“八·二风灾”的赈灾中可以看出,北京政府所产生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潮汕当地政府与中央相比明显是积极的,但限于自身的财政能力仍无力单独承担救灾职责(如“樟林救灾分所”,灾后该分所来自澄海县署的捐款占全部费用尚达不到百分之五),不得不拉拢当地一些有威望的绅商参与。与疲软的政府相比,民间救灾主体的阵容庞大,善堂、会馆、公所等传统慈善组织在此次救灾活动中仍显示出顽强的生命力,仅上海潮州会馆集募赈款即达20余万之多。红十字会、商会、报界等新兴力量则充分利用自身优势,在救灾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应该说,此次赈灾与传统相比,无论是在民间团体的阵容势力方面,还是民间团体的性质方面在很大程度上都已经产生了“质”的飞跃,民间力量表现出强烈的自主姿态,成为赈灾活动中的主导力量。
其二,海外潮侨扮演了重要角色。可以断言,近代侨乡发生灾荒,赈灾必有华侨参与。据“澄海80年前赈灾纪念碑”记载,风灾发生后“……海内外各同乡会和慈善团体纷纷捐款,捐物或派员救助,海外捐款二三百万。”[]每当家乡发生灾难,海外华侨始终与患难与共,这是“八·二风灾”赈灾中所展现出来的最鲜明的特点。但潮侨的捐助活动绝不仅限于潮汕家乡地域范围之内,如在清末“丁戊奇荒”的赈济活动中,我们同样看到了潮侨这种乐善好施的举动。这与传统社会多协助乡里的狭隘思想相比有了很大的进步,从某种程度上看已经上升到了“爱国”的理念。但笔者仍以为,排除国家遭遇外患诸如民族主义方面的内容,清末民初华侨的“爱国”仍是建立在“爱家”基础之上的,“爱家”始终是“爱国”之基点。所以,潮侨对家乡的救助是一种发自内心本能的自我反应,而对其他地域的灾变,则更多地出于一种浅层次上的怜悯抑或是道德意义上的援助。
其三,重视善后事宜。从本质上说,真正意义上的灾荒救助分为“临时救济”与“善后”两个层次。“八·二风灾”的救灾活动,一开始即依照救急与善后两个方面进行。以教育来说,传统赈灾“重养轻教”,通常极少顾及灾后教育事业的发展。“八·二风灾”的赈灾活动突破了这一点,可谓是“养”“教”兼施。据史料记载,灾后之教育,“已陷于不幸中矣”,故此次受灾“物质之破产已可怜,精神之破产,更可哀也。”[]66韩山师院也未免于此难,尽管困难重重,该校校长方乃斌以及海外华侨仍热心救助,灾区的教育并没有因此次风灾而中断。又如灾区溃决堤围的修建,各赈灾团体都给予了极大的重视,上海筹赈风灾善后即拨款5万1千元用于各地善后修堤[]66;又如为使轮船免受红罗线之风险,香港八邑商会联合各慈善团体开凿珠池肚避风港,避免“八·二风灾”中“轮船多覆灭”的惨剧再次发生[6]58-59;再如防风楼的建造。为减轻家乡台风灾害的袭击,海外潮人筹资在澄海县之外砂捐款建造“风台楼”4座,“俾有灾时,得所躲避,不致坐而待毙”,“平时以该屋为校舍,办公益之事业,有事时,则任人入内躲避,冀保安全。”[6]58-59
在“八·二”风灾的赈灾活动中,新兴的慈善机构和社会力量在救灾中展现了巨大力量,使这次赈灾活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传统荒政的救灾模式,具有明显的近代化特征。历史学者杨鹏程曾指出,中国荒政的近代化包括器物与人事两个层面。所谓器物层面,主要是指救灾信息、交通、新闻传媒等的时效性方面体现近代化的特色;而人事层面荒政的近代化则表现为专司赈济的近代化机构的出现 (包括常设性的和临时性的)、外国慈善机构和慈善家的介入(如红十字会、华洋义赈会等)以及“近代化的人”(如担任过民国总理的湘绅熊希龄)[13]。参照杨氏的荒政近代化理论,不难看出,1922年潮汕“八·二”风灾的救灾活动在器物与人事上都已实现了近代化转换。其中所展现出来的比较严密的救灾组织机构以及国内外新兴力量的大规模介入,标志着近代救灾机制体制的初步确立,客观上推动了中国近代新型赈灾机制的建立和完善。具体而言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专司赈济的近代化机构的出现。在中央,北洋政府时期已经出现了专司救灾的组织机构——“赈务处”。“赈务处”为临时之救灾组织机构,当各地灾情比较严重时一般由内务部附设“赈务处”负责处理,事毕撤销。1920年,“直北五省旱灾”严重时,即设置“赈务处”。1921年,由于各地灾情较重,中央政府复设“赈务处”,至1922年仍然存在。“八·二风灾”发生后,“赈务处”提议将“所有汕头海关常关进口进出口货物一律附加一成,以一年为限”,并“拟在上海关税加余款项下筹拨十万元,交赈务委员会组织华洋放赈团体前往施放”,发挥了一定作用。在地方上,灾后由官员与商人合办的“汕头赈灾善后办事处”可作为典型代表,该处制定了自己的12条章程,并有一套严密、行之有效的救灾组织体系和明确的救灾方法与措施,在很大程度上凸显了救灾机构的近代性。
(二)新兴力量的积极参与。同乡团体、善堂和公所等传统的救灾主体在此次赈灾活动中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这说明传统的人际、地缘关系仍受重视,传统的救灾力量仍然很活跃。但新兴社会力量在此次赈灾中的作用非常明显。国内、国际红十字会以及遍布于全国各地的商会组织,包括海外华侨商会组织等新兴社会团体在内,均在救灾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且其救灾方法与传统相比具有无法比拟的优势,反映出新生力量、新式救灾机构的优越性。
(三)近代化的交通通讯手段。首先是信息。民国初年的电报等通讯设备已经异军突起,使报灾-审灾-赈灾的过程时间缩短了一半以上,发自灾区的求助信息“在几天甚至几小时内,便可传遍世界”,“电线之所通,其消息之流传,顷刻可知”[]501。《申报》《大公报》《益世报》《东方杂志》等众多近代新闻媒体的日趋发展,又使灾讯的传播速度和准确度得到了根本性转变。其次是交通。历代救灾方式多为移粟就民,而交通不便给赈粮的运输造成了诸多困难。民国初年,近代汽车、轮船、铁路等新式交通工具已陆续出现,且速度快、数量大,使远距离迅速移粟成为可能。潮汕一带自开辟汕头通商口岸后,汕头与中国沿海各地及南洋地区的近代交通也日趋发达。灾发后,汕头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和近代交通工具,大大缩短了各地赈粮、药品甚至医护人员等运往潮汕灾区的时间,保障了整个救灾工作的顺利进行。
“八·二风灾”在海内外各界力量的倾力协助下,尽管困难重重,但仍取得了明显成效。巨灾过后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饥荒局面,也没有引发大规模的瘟疫,灾民也能得到妥善安置而没有发生“民变”。更重要的是,潮汕地区的近代化进程并没有因为风灾而中断。在当时军阀混战的局面下取得这些成绩是十分不易的。
三、余论:民初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个侧面
在传统中国社会,“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中央与地方是主从隶属关系。而在战乱、分裂的民初时期,这种稳定控制关系受到很大程度的冲击。随着辛亥革命、二次革命和护国与护法运动等多次以省为板块宣告独立革命运动形式的爆发,中央政府的权威大大削弱,地方可以发出与中央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声音。在“八·二风灾”发生后的救灾活动中,让我们从一个侧面看到了地方与中央权力的博弈。
中央政府职能的疲弱为民间势力的扩张提供了空间。随着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转型,民初民间的灾荒救助活动不再是一乡一族的事情,它已经变成了整个民间社会的责任。在民间社会,商会以及其它一些新兴社会团体(如中国红十字会)变得日益强大,这类团体越来越多地谋求将自身的利益,认同于更广泛的当地社会共同体的利益,并且利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去实现社会共同体的目标。在“八·二风灾”的救助活动中我们的确看到,救灾已经远远超出了宗法乡族的观念,救灾力量来自五湖四海,且社会组织的救灾活动并未受到四分五裂的国家政治格局的影响。
在民初的中国,由于全国性的社会整合难以出现,潮汕地区的赈灾活动主要是在地方官府与社会力量的共同参与下进行的,并呈现出合作与协调的态势。1922年,潮汕受灾区与县、乡与村的救灾活动正是依托着地方政府、商会、善团等慈善组织以及社会自治团体等等的密切协作这一新的救灾制度形式。这种新制度形式的出现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做出合理解释:从地方政府这边看,它没有独自从事这种大的救灾活动所必需的资源,因而市县政府官员通常会向地区绅商、善团求助,吸纳当地的社会资源;另一方面,民间势力虽然自19世纪中叶以后出现明显的扩张趋势,但他们却没有能实施大规模公共活动的体制组织,从而地方政府的领导与介入就是必不可少的。与此同时,在“八·二”风灾社会各界的救济活动中我们发现了一个现象:某种程度上一种事实上的乡村自治相应地出现了。潮汕当地的救灾善后活动,使我们见到了民国初年中央和粤省政府力量相对减弱的情况下,潮汕当地社会内部力量是如何有效地利用各种传统和现代的资源,应付突发事件,维持社会的稳定和生活的延续的。
但应当同时指出的是,民间组织公共功能的扩展并非意味着已经威胁到了政府权威。通过对1922年潮汕地区“八·二风灾”救灾活动的分析研究,笔者以为,中央政府职能的软弱确是一种事实,但国家与社会并未因此而出现紧张对立局面,相反,在“弱国家”的局势下,社会力量充分发挥自身的活力与地方政府密切协作,展现出二者之间的良性互动。
[1]汕头市史志编写委员会编辑部.汕头市三灾纪略(初稿)[Z].汕头.1961-323.
[2]潮州市地方志办公室,饶宗颐.潮州志·大事志[Z].2004.
[3]潮州市委员会文史编辑组.潮州文史资料[Z].第8辑.
[4]苏州大学社会学院,苏州市红十字会.中国红十字会历史编年(1904-2004)[M].合肥:安微人民出版社,2005.
[5]汕头赈灾善后办事处.汕头赈灾善后办事处报告书:第一期[Z].1922.
[6]香港潮州商会八十周年纪念特刊编辑委员会.香港潮州商会成立四十周年暨潮商学校新校舍落成纪念特刊[Z].1961.
[7]吴继岳.六十年海外见闻录[M].香港:南奥出版社,1983.
[8]申报[N].1922-183.
[9]中国红十字会总办事处.慈善近录[Z].1924.
[10]林济.潮商[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1.
[11]十大之首——“8·2”风灾,1922年汕头大台风回顾[EB/OL]. http://bbs.yphoon.gov.cn/read.php?tid=10555.
[12]东方杂志[N].63-66.
[13]杨鹏程.灾荒史研究的若干问题[J].湘潭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5):61-64.
[14]中国史学会.洋务运动[M].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
【责任编辑 李 菁】
K249
A
1674-5450(2014)03-0033-04
2014-01-15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2013年度科研基金项目
孙钦梅,女,山东临沂人,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近现代史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