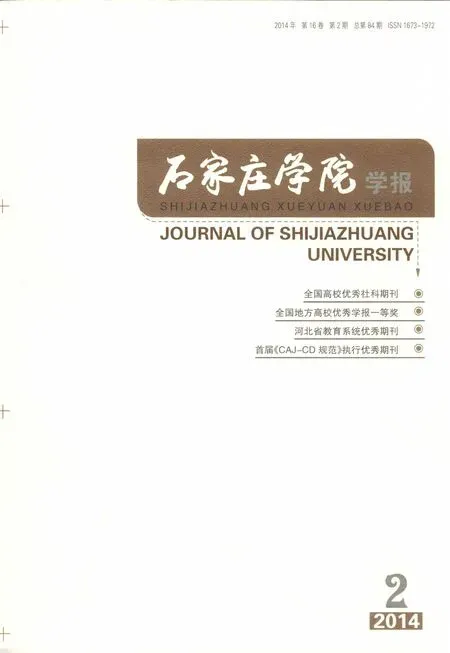自由教育的哲学基础
2014-04-10张桂
张桂
(丽水学院 教育学院,浙江 丽水 323000)
自由教育的哲学基础
张桂
(丽水学院 教育学院,浙江 丽水 323000)
自由人格具有一种反身性的伦理特征,它来源于自我对他者的超越关系,即在自我认同之中植入为他人责任的优先性,就此而言,自由人格的实质是把自我的自由奠基在为他人的自由之中。这种理解构成了自由教育的哲学基础,这意味着教育关系是一种不对称的伦理关系,在这种关系之中,受教育者的自由人格的塑造具有一种逻辑的优先性,教育者的自由以责任的实现作为自己的界限。就内容而言,这种自由教育包括三个方面的教育:自然自由、社会自由和道德自由。
主奴关系;反身性;自由人格;自由教育
一、教育中的主奴关系
主奴关系作为概念由黑格尔(Hegel)在《精神现象学》中首次提出并进行运用。黑格尔认为,自我意识具有欲望的本性,欲望是指自我对他者的统摄以及在作为中介的他者中寻回自身的过程,因此,自我意识只有在与另一个自我意识的遭遇之中,在与另一个自我意识的相互承认之中才能真正成全自身。承认的真理是自我意识对另一个自我意识的相互否定和相互肯定的双重过程,在这个历史性质的逻辑过程中,主奴关系作为承认的首要环节而出现。主奴关系即主人在否定奴隶的过程之中,得到了奴隶的肯定,主人意志即是奴隶本人的意志,奴隶本人的意志只有在主人意志之中才能得到肯定。主奴关系的必然性在于,自我意识与另一个自我意识的遭遇是以一场生死搏斗式的相互否定发生的,这种相互否定的逻辑结果就是要么在另一方死去之后自我获得空虚的肯定,要么以主奴关系的形式出现。简要地说,主奴关系是一方意志对另一方意志的支配与被支配、控制与被控制、统治与被统治、奴役与被奴役的关系。 [1]120-127
然而早在黑格尔从政法逻辑的角度对主奴关系作出概念界定之前,卢梭(Rousseau)在《爱弥儿》之中已经从教育逻辑的角度对主奴关系作过分析和论述。这种描述具有黑格尔逻辑不具备的某种新颖特点,值得我们重视。它的新颖性在于,它从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交往出发来描绘主奴关系,把这种关系界定为相互支配、相互控制、相互统治、相互奴役的关系。 [2]25,55-56,58,80,109,140-142
与寻求承认的自我意识不同,教育者寻求的是按照自己的意图、欲望与观念来塑造受教育者,而受教育者寻求的则是依赖。然而这种寻求在扭曲的教育交往之中,改变了自身的性质与特征。具有关键作用的事件是,在塑造与依赖之中常常起决定作用的是双方的任性的自由意志,因此在非自由的交往之中变成奴役双方的锁链。一方面,受教育者的弱小、无知、无力使其必须依赖教育者,然而他的自由在于运用自己的任性来影响教育者,以此来满足自己的欲望。另一方面,教育者由于在天性上对受教育者具有情感与责任,在力量、知识与能力上又拥有优势,则常常试图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塑造受教育者,以温和或者冷漠的态度,采用诸如训诫、指导、命令、说教、指责、辱骂、惩罚的教育方式。因此,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意志在交叉、碰撞的过程之中,发生了相互的影响与变形。由于受教育者追逐的是自身的欲望与利益,而追逐同时要得到教育者认可、赞许,他就必须接受教育者的统治;由于教育者在进行塑造的时候,要受到受教育者欲望倾向与任性的支配与约束,他就无可避免地受到了受教育者的统治。
事实上,卢梭批评当时教育的关键和实质在于,教育如果忽视了自然与文明的张力,忽视了儿童天性与理性之间的距离,忽视了儿童与成人、学生与教师之间的不对称关系,那么必定会陷入教育的主奴关系之中,造成受教育者和教育者同时既是主人又是奴隶的荒谬局面。儿童天生具有自爱、趋乐避苦以及自由的本性,而儿童的体能以及行动的能力、情感和理性则是不完善的,因此,当教育以成人的情感与理智来约束甚至压制儿童的自然需要,并且灌输不为儿童理解的观念与知识时,它只是在引发两种意志之间一种权力的争斗。这种争斗的实质在于它是由任性来构成的。儿童的任性出于自爱的天性,它的实质就是,如果自爱的天性无法在教育关系之中合理的实现与发展,它就会以一种非理性的方式表现出来。它不是康德(Kant)所说的不受规范约束的野蛮性,[3]4而是一种通过支配他人来满足自己私念的隐秘狡计,比如暴躁、骄纵、肤浅的自私,甚至是以损伤自己为代价以引起关注的歇斯底里。而成人的任性则是仅以自身狭隘的经验与认识,以浅薄、鄙俗的情感来对待儿童,以不恰当的教育观念与方法来指导儿童,却在活动之中试图保持自己的威权与支配力量。因此,由于这种教育缺乏沟通儿童天性与成人理性的中介,缺乏作为教育法则的根据与规范,它必将导致一种奴性的非自由的人格。非自由的人格有许多不同的心理类型与表征,抛开时代的背景因素,阿德勒(Alfred Adler)关于“自卑”的人格特征的描述,以及弗洛姆(Erich Fromm)对虐待狂、受虐狂的分析和对逃向权威怀抱的人格形象的论述,都可以作为这种非自由人格的佐证。
在具体的教育场景之中,有以下几种交往实践范围会影响非自由人格的形成。
第一,自然需要转变成心理层面的一种欲望。儿童的心理与体能的发展应该是一致的,体能只要能够满足前者的需要,就是自然的。即自然需求是一种主体与自然客体之间存在的客观联系,不涉及社会关系。而一旦超过这种客观的需求关系,儿童随心所欲的喜好、任性就会试图支配成人,就会导致儿童不是按照自己的自然需求,而是按照欲求来实施自己对事物的掌控。这种掌控归根结底是一种权力意志,通过支配成人达到对事物的支配,所以并不是一种人对世界的客观支配。而且由于这种掌控只是一种心理上的主观想像,它就变成束缚自己的幻觉和魔障。在情感的心理基础得以进一步发展与丰富之后,这种幻觉和魔障在情感的表现领域,还将会造成情感的扭曲,使人成为情感的奴隶。
第二,品德习惯方面的道德规训与说教。儿童品德的发展有一定的顺序与阶段,它受制于儿童感受能力、经验以及判断力,特别是受制于社会情感意识的发展程度。过早地或者不适当地对儿童进行道德关系层面的规训与说教,仅仅是成人对儿童心理的误解、幻象与偏见,不仅达不到促使儿童品格发展的良好效果,反而会使其养成撒谎、虚伪、支配的坏习惯。儿童要么不能理解成人世界的道德秩序,而他假装接受,并表现为一种暗地里的反抗;要么把它理解成是一种服从关系,归因于成人的强力和支配的欲望。因此,在教育者用偏见统治儿童时,儿童也在利用教育者的偏见来支配教育者。
第三,各种意见和专业权威的灌输,导致受教育者丧失了良好的判断力。个人自主的感受、建立自身经验基础上的独立判断以及自由的思想,这些是自由人格的理智基石。一种仅仅遵从逻辑,遵从秩序所提出来的专业知识、意见,在教育者的眼里代表着明白的权威,在受教育者眼里则是不能透彻理解却需要盲目遵从的权威。在哪里心理逻辑的知识与方法没有受到重视,在哪里就会存在知识所导致的理智专制。从黑格尔之后,现代哲学的一个重要观念就是真理是过程与结果的综合。对教育来说,作为目标的知识与作为过程的方法是同等重要的,只有两者的结合才能培养学生自由的思维以及良好的、准确的判断力。
以上的分析表明,儿童与成人的关系,或者说学生与教师的关系是教育关系的奠基性因素。换句话说,儿童的相互交往是以儿童与成人的交往为中介的。各种学习活动的安排、游戏、团体活动、仪式所具有的教育性质以及所采取的相应方法,取决于教育者对师生关系的觉悟与认识。在儿童的自爱和自由本性受到了抑制的地方,通达共同生活的情感、道德和理智发展的可能性也就会受到同等程度的抑制,自由人格的产生就会无比困难。
二、反身性(reflexivity)和自由人格
什么是自由人格?它是如何形成的?教育在其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这是思考自由与教育之间关系的一些基本问题。
在历史上,现代自由主义的伟大贡献就是确立了有关自由的一个根本观念,自由存在于法律和规则存在的地方。这种观念的实质就是把自由规定为公民所享有的基本权利。但是对这种权利的来源政治学家有不同的看法。早期的契约论者洛克(Locke)、卢梭都认为,这种权利来自人所结成的合法契约。虽然两者对契约的起源与内涵的解释有着相当的差异,然而他们在一个重要思想上保持一致,那就是承认权利起源的个人性。他们假设在政治社会之前,存在一个为自然法所规定的自然状态,每个人都享有为自然法所规定的个人权利。这种权利在通过契约构成政治社会之后,则转化成法定权利。[4]3-10,59-76[5]4-5,17-22这种观点在理论上的后果是很难解释社会的起源,造成个人权利与社会的分裂,在实践上的后果是把法律和国家当做是任性的产物、个人的工具,只具有出于利害关系的威慑力,而缺乏一种内在的价值与权威。
这种个人权利的先天性与后天社会性之间所存在的裂缝,在康德的自由哲学那里被推向极致。这种裂缝被康德处理成自由和自然之间的对立关系。这种对立有两个方面的特点。其一,与康德对现象与物自体的划分相对应。自由被规定为一种以人自身为对象的行动能力,它以物自体作为自己的本体论基础,不同于被知性加工为因果关系的现象。因此,自由是开始,是创生,而不是因果链条中的一个环节,它具有打破因果链条的能力。其二,与康德对经验与先验的划分相对应,与质料与形式的划分相对应。经验来自现象对感觉的刺激作用,并且为知性范畴规则化的一种知识,现象提供质料,范畴提供形式。而先验则是一种先天的知识,本身只具有形式的必然性。一方面,康德把自由作为一种先验自我的对象,强调了为自然立法,为自身立法的主动性;另一方面,康德既然把自由摆放在不受经验与质料 (即自然)影响的领域,又要使自由在这个领域发挥作用,那么他就必须强调形式规则的重要性。只要理性遵照形式规则,才能摈除自爱、欲念、情绪等质料的影响,在必然性之中获得自由。[6]106-119
这种自由哲学的实质是要在感受的被动性与理性规则的主动性之间,确立一条严格的、不可跨越的界限。当康德在变动不居的感性世界里寻找人类的自由时,他确立了一个理智想象中的自由王国。然而,当自我以理智王国作为行动的参照,以抽象的形式规则来作为行动的标准时,就会发现无法有效地确立指导行动的规则。其中的原因在于,一旦把感受性从自由王国里排除出去,我们就无法找到现实的他人,一旦无法找到他人,我们就无法确立对待他人的行动规则。康德形式主义的问题是,它解释了动机的根源,也明确了普遍化的要求,然而却远离了现实之中的他者。康德哲学中的自由看起来是普遍的自由,其实质则是自我的自由,是对他者的压制。自我的普遍化,并不就能构成社会,也不能说明社会性的起源。
自由只能来源于社会。这要求我们在考虑自由时需要从社会性的角度来分析与解释自由的根源与本质。人都有自我,然而自我的同一性(identity)只有在他者的作用下才能形成。所以,黑格尔讲述了自我意识与另一个自我意识之间的辩证法。自我意识的真实性在于,它在另一个独立的自我意识之中发现了自己(self)。“我就是我们,而我们就是我。”[1]121这是自我意识的承认欲望,是从他者回归自身的一种运动。它说明了自我作为意识的本质特点,就是把一切都统摄在意识的确定性之中。然而问题是,这并没有说明自我同一性持续不安的特性,也很难解释他者为何是独立的。一旦我在我们的家中找到了自己,找到了同一性,欲望得到了满足,我就丧失了欲望。这将是一个由意义系统组建而成的家,我和他都会成为意义系统之中的环节,自由是构成系统的基本元素,然而却由此失去了自由得以建立的脚手架。在黑格尔的逻辑之中,自我的自由依赖于他者的自由,自由的普遍化是自我与他者相互作用过程中产生的。一旦这种运动丧失了动力,那么自由也就终止于自身,他者也就谈不上独立了。
因此,一种合理的逻辑是需要在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中寻找一种无限的欲望,即对无限的欲望。按照列维纳斯(Levinas)的描述与分析,无限是一种超越于意识内在性的对象,用现象学语言来说,即意向对象超出了意向行为的观念化能力,而不能在语言逻辑的内在化之中得以构成。无限进入意识与观念的内在性,在留下自身的痕迹时,又抹去了自己的痕迹。这是自我所遭受的一种极端的被动性、敏感的易受伤性、不能被遮掩的暴露,意谓自我对他者的接近,自我对他者不可逃避、不可被另一个人替代的回应与责任。在自我对他者的回应与责任里,形成了自我的同一性。因此,同一性在起源与本质上具有伦理的意义。换句话说,这是一种外在性对内在性的入侵,但是这种入侵并不是奴役或殖民,而是作为无限的外在性撼动了自我意识的同一性,使我的存在发生转向,转向以他人为己、以他心为己心的伦理姿态。这里不存在回归、循环,因此也不存在终结。自我始终被动地遭受、被动地保持一种开放,一种由他者而来的倒转的开放,此即超越的自我,一种伦理超越。[7]26-29,75[8]93-94[9]62-65
所以,反身性即由他者而来的自我认同(self-identity)的规定性。在自我与他者的互动关系之中,反身性保护了一种关系的不对称性,即自我始终具有一种向着他者的超越,这种超越不可能被互动的逻辑所吸收而内化,我对他者的责任不能还原成他者对我的责任。自由是普遍的、对称的,是在法律与规则面前的平等,然而反身性则要求一种自由的伦理起源。维护自由的方式,固守自我自由的方式,并不是退缩到自我的安全与堡垒之内,而是对他人的自由保持一种开放与同情的姿态。所以,自由人格的实质是把自我的自由奠基在他人的自由之中。只有如此,一切维护自由的法律、规则、程序,一切团结在这些逻辑秩序周围的机构与个人,一切发挥与继承自由精神的文化传统,才会具有持续不断的生命活力。因此,自由虽然具有一种个体性,但是它不是单子式的自由,而是社会交往中的共同自由。这就是为何自由被当成一种基本权利。这正指明了一个事实:权利作为一种价值标准,在实质上涉及的是对社会交往正当性的评价。权利指涉了在社会交往之中自我应该对他者所承当的回应与责任。即权利虽然是一种个体性的权利,但是它来源于社会交往的反身性,具有一种伦理的规定性。在这个意义上,自由和权利的存在有赖于两种基本的伦理技艺——承诺和宽容。它们都具有反身性的伦理起源,前者可以使社会生活成为一种共同生活,后者能平缓、中止共同生活之中由于个体性所产生的冲突与矛盾,使共同生活具有重新开始的可能性。
三、教育实践的自由逻辑
自由人格“奠基”在反身性之上,它的理智就是遵循法律与规则平等地生活,同时依赖承诺与宽容来处理具体社会情境之中的交往与冲突。那么,如何从教育的角度来理解自由人格的形成?教育起了什么样的作用?教育所需遵循的基本原则又有那些呢?教育关系是社会关系里的一种,同样具有来自反身性的规定性。教师同等具备一些基本的权利与自由,而教育机构在面对其他社会机构时,也享有自身的权利与自由。但是在教师与学生的关系之间,反身性具有特殊的性质,教师与学生的不对称性不同于自由人之间的不对称性,前者要更为极端。对教育主奴关系的分析与描述告诉我们,教师如果不想违背自己的人格追求,陷入非自由的境地,就必须在与学生的关系中发展一种自由与创造的辩证关系。无论在自然生理条件还是社会心理属性上,学生都是不成熟的儿童,教师对学生的责任就是给予他全面的培育、训练、教导,使他能够成为一个具有自由人格的成人。在这个意义上,教育是一种孕育与奉献。自由孕育了自由,在想像中以此时的努力创造明天的现实,这种特殊的时间性类似于亲子关系。孩子是父母所孕育的,是父母自我中的他者,是父母自我向着未来的一种超越。作为孩子的他者深植于自我之中,以自我的血肉和智慧为土壤,才能获得完善的成长。然而这并不能表明,父母自我有着占有孩子的权利,孩子的超越性赋予了孩子一种权利,以柔弱来感动父母,以责任来命令父母去实现孩子的未来。[10]267-269
在教育的奉献与孕育之中,学生的自由人格得以逐渐形成。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所理解的教师身份的核心是由伦理智慧所规定的。一方面,教师与学生交往的不对称性要求教师必须限制自己的自由。在与同事、其他人的社会交往之中,教师是自由的,然而教师要爱学生,并且对其进行教导。对其他人,教师需要关心他们的自由,然而教师却要对学生的全部生活内容与发展的可能性负责。另一方面,自由人格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它的形成取决于教师对儿童自我发展规律的洞察。儿童只有经过享用自我、承认自我、超越自我三个层次,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享用自我是指自我在愉悦之中的持存,自我惬意于需要的满足、体能的发展、生命活力的展现,它是卢梭意义上的自爱,是黑格尔意义上向着自身回归的生命。承认自我是指自我与他者交往过程之中,个体要求获得社会评价平等对待的自尊。这种自尊有三个发展阶段:儿童游戏与学习活动之中由于角色扮演获得的平等尊重的需要;儿童在与成人交往之中试图获得平等尊重的需要;最终获得一种普遍的社会制度与法律意义上的平等尊重的需要。超越自我是指自我以经验获得的感受的被动性为前提,并且从理智上接受自我受反身性规定而来的自我认同。他者并不仅仅是独立的个体,而且还是我的邻居与兄弟,我是他的看护者,对他负有不可逃避的责任。简要地说,自我走向自由的过程,就是自我向着他者运动,并且使他者内在化的过程。这一过程需要我们关注两方面的要素,其一即自我的生理心理条件,其二接受相应的恰当经验的刺激。自我的被动性使自我能够感受外界的刺激,而自我的主动性则能够内化这种外界的刺激,转变成自身的经验。主动性与被动性的恰当交融,才使自我能够得到良好的发展,并且获得自由。
三种自我只有在师生关系之中才能得到呵护与发展,前一种自我是后一种自我的基础,后一自我则是前一自我的质变与发展。[11]60-73任何一个阶段与环节出现关键性的故障,就会导致自我发展受到挫折,就会出现主奴关系之中所讲述的自我各种扭曲的状况。在当今中国,我们的很多学生身体孱弱、活力衰落、情感狭隘、感受与想象贫乏、平等意识和独立思考能力缺失。其中没有一个要素不是与自由人格相关的,而且每一个要素在三种自我之中都有自己的质地与元素。因此,要实现自由人格,就不仅要提出合理的教育原则,全面彻底地把握自我发展的教育内容,而且要对教师角色的规定、对课程与教育方法的实践、对制度的构建提出具体要求。我以为自由教育需要把握以下三种基本的教育原则。
第一,活动与经验的原则。人格的造就一方面是出于自然的禀赋,另一方面出于教育的引导。教育就是把自然的质料发挥出来,并赋予一定的形式,或者可以说是潜能转化成现实的过程。自然的一个特点就是要生长,发挥自己的能动性,所以活动的原则是教育的基本原则。活动并不就是针对身体、意志、感觉,针对人的言谈与交际,更是针对人的意识与灵魂。无论是人的理性、审美,还是道德能力,都要基于这种活动能力的发展。凡是长期地压制这种天然的活动本性,必然就会造成人的颓废与死沉。西方人把这种活动的本性称之为自由的倾向,是对世界历史起着重大影响的一大发现。中国教育的特点是消沉的,而不是生机勃勃的,这是中国文化一直在走下坡路的根源所在。其二,注重活动与自由,也就必定会注重经验的生成和创造。人格的造就不是教条地接受外在教育的过程,而是在各种经验内容与形式之中去获得符合教育理念的经验,所以教育提供合适的环境与有意识的引导,就是必要的。经验的原则表示了一种平衡的技艺,一方面教育是外在的规范与引导,另一方面这种引导又必须符合内在的活动需求。
第二,塑造性格的原则。自我发展涉及到心理与行为的实质与形式,在具体生活之中则表现为一个人的性格特点,在自我发展的过程之中则表现为性格的塑造与养成。由于人格的造就涉及到心理的整体,并对行为有正确性的要求;由于心理与行为正确性的造就涉及到从婴儿到自由人的性格塑造,所以教育应该研究人需要哪些主要的性格以及这些性格的实质与特点。并且由于养成好的性格都是与避免坏的性格在生活中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教育就要知道从何处入手能避免坏的性格,从何处入手能养成好的性格。而且由于性格发展是一个过程,我们就有必要清楚地了解这一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与避免的方法、它的阶段及各个不同阶段的特点。简要地说,要根据自我发展的规律来研究性格发展的规律。
第三,民主与公正的原则。民主和公正涉及教师的德性、课程与方法的实践以及制度的性质,但它们的实质和核心指涉的是师生关系的反身性所规定的民主与公正。因此,民主是指以爱和宽容为基础的,对学生主体、对学生自我发展规律的尊重。学生的成长是一个不断生长、开放的过程,而这种成长与开放则依赖于与他人保持一种互动的交往关系,从不断的活动经验中获得生活的一切习惯、品性、知识。所以,确切地说,师生关系的民主包括教师与学生以及在教师引导下的学生与学生之间的民主。教师的重要性在于,以自身的民主态度与民主技巧,通过这种生长、开放的经历让学生懂得自身认识的有限性,使其理解对话和合作,理解他者和传统经验的重要性。只有如此,学生自我才能得以发展,教师才能获得学生的尊重,才能拥有权威,才能被学生以民主的方式对待。民主是一种相互生活的方式,却只有通过教育才能获得与拥有。同样如此,就公正而言,只有在公正之中,学生自我才能得以正常发展,才能反过来公正地对待他者。公正是指根据学生个体的同一性与相异性来平等地对待学生,以普遍的规范与法则来约束与引导学生。自由教育是一种学生平等享有的权利,而学生个体根据自己的天赋,在个人才能与职业成就上却是具有差异的。
四、自由教育的三重要义
自由教育是培养自由人格的教育,它包括三个方面的教育:自然自由、社会自由、道德自由。每一个方面都是自由人格必要的组成部分,就其中的关系而言,在层次上三者呈现一种金字塔的结构,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前者的提升与超越;在结构上,三者形成共同支撑自由人格的三脚架,缺一不可。
自然自由是自爱意义上的自由,卢梭在《论不平等》之中有过诗意的想象与描绘,在《爱弥儿》之中则有更为准确与合理的论述。自爱是自我持存的根本欲念,是对自己的爱,是需求的满足,是对个人幸福的追求。因为疾病、生存的艰难、欲望和想象的双重煎熬,人的命运是时时刻刻要遭到痛苦的。痛苦的根源产生于我们的欲望和能力的不相称。这种痛苦直接从自然基础上威胁着人的存在,所以自然自由可以理解为存在的自由。那么如何实现这种自然自由呢?其一,要获得生存的能力。在现代社会为了应付紧张的竞争压力,人们需要具备必要的身体生理与心理条件,有丰富与多面的个性,具备学习能力,掌握全面、合适的知识与技能。只有能力扩大了,才能满足各种需要与欲望。只有在没有条件扩大能力的前提下,居心叵测的人才会宣传禁欲主义,极度削弱生命的欲望,保持生命的平衡。其二,要进行心灵上的修养与节制。精神痛苦的一个重要原因产生于欲望与想象的双重作用,由于不正确的观念想像诱导欲望,导致了造成痛苦的偏见。另外一个原因的心理基础则相对比较简单,痛苦产生于扭曲的欲望,形成一种对自身有伤害作用的嗜好。想像和偏见造成的欲望是无止境的,嗜好则是很难根除的,这些必须在教育过程之中及时加以防止。总的来说,自然自由是一种与他人无涉的私人自由,是一种孤独的、干净的幸福。它不仅是对自然的享用,无论这种享用是食物、锻炼,还是散步、观赏,同时是对自身心灵的消遣,无论是游历、阅读、游戏,还是对音乐的聆听。[2]75-80
社会自由是在社会秩序之中个体的行动自由,这种自由免受他人的强制与干涉。[12]3-6用孟德斯鸠(Montesquieu)对自由的定义来说,就是一个人可以去做他应该做的事情,或不去做事情的权利。因此,与自然自由不同,社会自由处理的是个体之间的权力关系。按照霍布斯(ThomasHobbs)以来对人性的解释,人天生具有一种控制与支配他人的欲望。在历史上,强权与霸权给人类社会打下了深刻的印记。如果这种欲望不能得到节制与引导,结果要么是导致极权主义,要么引发人与人之间的战争。所以,社会自由是对文明与和平的向往,它利用法权制度的普遍性来限制、约束这种欲望,来保障文明与和平。因此,对规则系统的遵守是社会自由的基本要求,自由与任性是相对立的,任性只会导致非自由,而强力的存在,就是为了制止危险自由的这种任性。除此之外,规则的存在既然为自由提供了游戏的空间,它就不是根除了权力,而是以法权制度为中介使个体权力之间保持一种张力,为繁荣与文明发挥自己的创造性。社会自由作为一种行动性的自由,它包括言说与行为两个方面的自由,涉及人类交往的一切领域,诸如发表言论、表达意愿、结成社团,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选择、创造发明、表演活动,等等。不过,我们也要在一般的社会自由之中,区别政治自由的特殊性。政治自由的特点,就在于它涉及到的是国家的普遍秩序,而不像社会自由可能仅仅表现在个别的、特殊的范围与领域。只有政治自由的存在,才能保证国家制度的有序运行,才能为个别的社会自由提供制度性的保障。就社会自由与自然自由的联系而言,社会自由为自然自由提供了可能性,反过来,如果自然自由无法在借用社会自由之中得到原则性的实现,那么就会撼动社会自由。
道德自由面对的是由反身性而来的对个体道德性的要求,在自我与他者的交往的伦理规定之中,自我与他者之间始终保持着一种不对称的回应关系,我对他人负有责任。由于道德感受的极端被动性,对他人所负的这种责任具有无限的性质。而这种责任的极端特点,更在于我以他人的痛苦为痛苦,甚至是以他人为我的痛苦而痛苦,以我不能回报他人而痛苦。所以,道德责任容易造成三种沉重的负担:其一,对他者负有亏欠,而且一旦这种亏欠植入体内,长久地停留,就会形成存在的焦虑与危机,我还有什么存在的理由呢?其二,世界上痛苦的人很多,而我却不能帮助他们,因此同样负有亏欠。其三,道德的亏欠往往会成为牺牲自我,成为某种他者意志的“道德”奴仆。应该从这种负担的意义上理解尼采(Nietzsche)对良心、对罪、对奴隶道德的批判,这种道德让人限制在一种强迫的病症之中,让人逐渐衰落、颓废、无力。所以,道德自由是指道德负担的一种解放,是伦理超越基础上的一种自由。一方面,自我只有通过超越才能获得终极的自我认同,自我与他者虽然是一种不对称的道德关系,却不是为了让自己成为某种亏欠感的奴隶,失去自我的同一性;另一方面,自我与他者的交往存在一种社会的互动,在某种意义上,甚至亏欠也是交互的,虽然亏欠不能还原为交互。因此,无限的道德要受到理智自我的限制,道德在效果上只能做到力能所及的程度。这种程度要根据社会交互关系的性质来公正的计算。一般来说,唯一的出路就是帮助他人获得自由的能力,实现自由,使其为自己负责,而对那些人无能为力的悲伤和亏欠,则承认自己的脆弱。理智帮助与承认就是坚强的理由,以此个体获得了自己在道德上的自由。所以实质上,道德自由只能在无限与有限的责任之中行走。从逻辑上来说,道德自由使自由上升到了最高的层次,由反身性而来,并且为自然自由与社会自由奠定了更为深层次的基础。
[1][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2][法]卢梭.爱弥尔:上[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3][德]康德.论教育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4][法]洛克.政府论:下[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5][法]卢梭.社会契约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6][德]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7]Emmanuel Levinas.Alterity and Transcendence[M].London:theAthlonePress,1999.
[8]Emmanuel Levinas.Otherwise Than Being or Beyond Essence[M].Dordrecht:KluwerAcademicPublishers,1994.
[9]Emmanuel Levinas.Humanism of the Other[M].Urbana and Chicago:UniversityofIllinoisPress,2003.
[10]Emmanuel Levinas.Totality and Infinity:An Essay On Exteriority[M].TheHague:MarnitusNijhoffPublishers,1979.
[11]张桂.教育的超越:走向他者的自我 [D].南京师范大学,2011.
[12][英]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上[M].北京:三联书店,1997.
(责任编辑 苏 肖)
The Philosophical Basis of Free Education
ZHANG Gui
(School of Education,Lishui University,Lishui,Zhejiang 323000,China)
The free personality has reflexively an ethic feature,and it comes from the surpassing of self over others,that is,giving priority of self-identification to others’responsibility.The free personality,in essence,based self-freedom on others’.This interpretation makes up philosophical basis of free education,signifying that relationship of education is asymmetric ethic relationship.In such a relationship,the building of the free personality of the educated has a logic priority;the freedom of the educator takes the realization of responsibility as the limit.As to the content,the free education includes natural freedom,social freedom and ethic freedom.
lordship and bondage;reflexitivity;free personality;free education
G40-06
:A
:1673-1972(2014)02-0112-07
2013-09-05
张桂(1982-),男,浙江温州人,讲师,博士,主要从事教育哲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