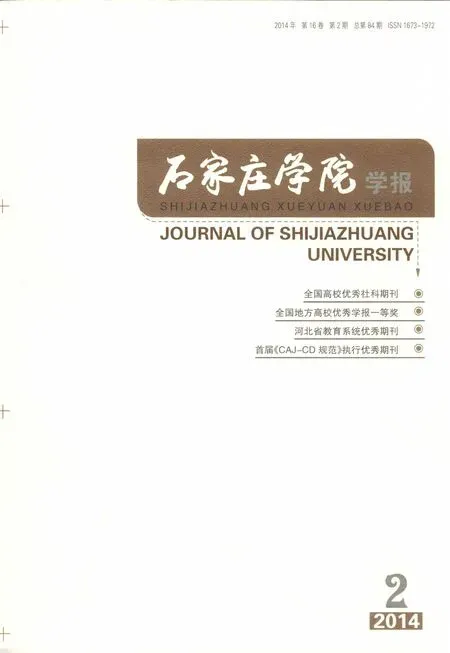多隆阿生平交游与《毛诗多识》成书之关系考
2014-04-10蔺文龙
蔺文龙
(山西大学 文学院,山西 太原 030006)
多隆阿生平交游与《毛诗多识》成书之关系考
蔺文龙
(山西大学 文学院,山西 太原 030006)
由于传记材料的简略,传世文集的缺乏,当下对《毛诗多识》成书过程及多隆阿生平交游的认识都存在误区。多隆阿生性平淡,不慕荣利。他在以萃升书院为中心的学术团体中获得了从事经学研究的基本条件,为《毛诗多识》的写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客居何维墀幕府和家居辽沈期间,多氏完成《毛诗多识》初稿;在主持平阳书院时,《毛诗多识》经多氏再次订正和王筠校对最终成书。后遗稿散佚,经程棫林、刘承干两度订正,厘定为六卷。书虽不完,其保存之功可嘉。《毛诗多识》对清代乾嘉学术在辽沈地区的传播与拓展有着重要意义。
《毛诗多识》;师友;清代学术
多隆阿,姓舒穆禄氏,一名廷鼐,字文希,号雯溪,满洲正白旗籍。正史无传。《岫岩志略》《易原又序》《例封文林郎乙酉科拔贡生多公墓志铭》可大致勾勒出其生平轮廓。幼年聪颖,读书岫岩。成童后,就学辽沈。年十九,补博士弟子员。乙酉(1825年)与何维墀举拔萃科。此后仕途不顺,专心著书,有《毛诗多识》十二卷等而下之。多隆阿出身高门,世袭经学,于天文数术,星经地志,凡百家言,无不备览。他常言“闭门学书兼学剑”,希冀有所作为,然“于帖括不甚措意,以是试京兆,辄荐而不售,有劝之揣摩时式者,夷然不屑也”[1]3461。究其原因,一是仕途险恶,人情不暖,文人惟恐避之不及。多隆阿身处“乾嘉盛世”之末,官场渐趋黑暗,“世道幻如鬼,人情薄如纸”(《拟古》)①下文中所引多隆阿诗皆出自《慧珠阁诗钞》,辽海丛书本,辽沈书社1985版。,“人心叵测善逃形,再莫轻言出户庭”(《海城县》)。尽管他有进取之意,现实与理想的矛盾使他“此生未敢貌荣名”(《独吟》)。直至晚年,他还不断反思自己的一生,“勉向时途尝学步,难将古调遇知音。当年自恃年华富,那想蹉跎直到今”(《寒夜偶成》)。二是性情使然。《岫岩志略》说他“性情耿介,不趋荣势”[2]960。多隆阿一生大部分时间过着“等闲溪畔坐,懒去问迷津”,“顿觉林泉好,闲游异俗尘”(《秋游》)的读书与隐逸生活。平淡的生活状态使其很难进入正史家的法眼,这就造成其生平及《毛识多识》的成书异常复杂。
一、书院教育与《毛诗多识》的写作
多隆阿生性平淡,不慕荣利。与人交往,皆以学问相尚。平生与其游者不多,然皆一时名士。“一卷经书读未尽,车声门外又粼粼。”(《庚寅元日》)真实再现了他与朋友交往的情形。缪润绂在《梦鹤轩楳澥诗钞·跋》中详细描述了缪立孙与多隆阿、金銮坡、尚铁峰、王义门、沈得余、福介五、符象芝彼此倡和的情形。缪云:“助教公(缪立孙),性冲淡,喜游佳山水。……行年五十考补盛京官学助教。官学接萃升书院近,一时名士若锦县金銮坡、铁岭尚铁峰、辽阳王义门、吉林沈得余,咸举为骚坛牛耳,继之者福介五、符寿潜、多雯溪倡和,无虚日也。”[3]3234这些人或为诗坛翘首,或是天资聪颖,或出身经学世家,彼此交往唱和,互相影响,学习氛围相当浓厚,对多隆阿影响很深。缪立孙,当时补盛京官学助教,又不喜帖括之学,肆力于古,成为许多文士追捧的对象,“以至沈阳有不识缪兰皋先生者,至引为阙憾”[3]3234。 金銮坡肆业沈阳书院,天资颖迈,雄视文坛。符象芝在沈阳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人物。他擅诗名,学博雅,清谈干云,更主要的是他出身读书世家,藏书甚丰,盖不啻邺侯万架。图书资料缺乏是当时北方地区的普遍现象,东北尤其如此。张玉纶、多隆阿不惜重金求购南方当时常见书籍的事例也说明了这一情况。清代学者桂馥谈到北方学术不发达的原因时,一针见血地指出:“北方学者,目不见书,又鲜师承,是以无成功。 ”[4]264对于那些渴求知识的文人而言,符象芝就成为辽东学者人人期盼交往的对象。张玉纶与符象芝友善,经常过访其家,终日不厌,“予每一过从,辄翻阅竟日,不能去也”[5]206。以致分别多年后,张氏依然流露出对符象芝学问的无比敬仰,对往昔共同研墨切蹉时光的无限留恋。道:“别后光阴水逝波,讯君佳况近如何。悬知灶上炊烟少,定拟门前债主多。诗价自然连日长,轩车可复有人过。魏公安否无劳问,依旧余生墨共磨。”(《岁暮柬符象芝》)①下文中所引张玉纶诗皆出自《梦月轩诗钞》,辽海丛书本,辽沈书社1985年版。多隆阿称赞符象芝“不藏泉货只藏书,满架牙签啸一庐”(《柬符象芝》)。
在众多友朋之中,张玉纶与多隆阿的关系最亲密,也是对其影响最大的一位。张玉纶,号绣江,辽阳人,以文学知名。《辽阳县志》云:“(张玉纶)与拔贡多隆阿、进士陈克让、附贡生特普、杭州岁贡生符象芝诸名士,以道义相切蹉……乃专力经史,锐意著述,不屑于帖括。”[6]551张氏一生“好学穷理,至老不倦”,于书籍更是痴狂,甚至倾尽家财购之,经常遭到别人讥笑。为此他写诗来自解:“夏葛冬裘典质频,案头青史快横陈。此生肯使有长物,到眼从兹多古人。学祇通经终是陋,衣犹遮体未为贫。含章定比章身好,讥笑何劳竞破唇。”(《〈廿一史〉解嘲》)他这种穷且益坚的学习态度感染了家人,全家形成了学诗作文的氛围。《漫兴》云:“南亩归来饭罢时,一灯儿女坐谈诗。”同代友人对他也十分推崇。多隆阿不屑作三代以下人物,其性格不合于流俗,然对张玉纶却非常佩服,“其能使多某诚服者,惟张绣江一人耳”[7]3352。张绣江与多隆阿一见倾心,彼此佩服对方才学和品德,同时认定对方就是能终身相交的知己。“得友如君见恨迟”(《赠及门张绣江》),“记从见面两心倾,此谊真堪托死生”(《己卯冬雪夜怀人》)。那些与张玉纶交游者,如符象芝、王补楼、刘余台、徐菊坡、恩凤丹、得承斋、德翼文、刘敬亭、广福门、广特夫、特百溪等也因佩服多隆阿的学识和人品而与之交往。许文运在《浒东诗抄》中表达了对多隆阿之才华的仰慕之情:
曾向沈阳一面逢,知君磊落出凡踪。
好书不惜挥金买,爱树常教绕屋封。
性纵云山人是鹤,文翻江海笔犹龙。
何时的宿高贤榻,话到寒山报晓钟。②此诗出自许文运《浒东诗抄》,手稿本,藏辽宁省图书馆。
许文运与多隆阿仅有一面之交,竟被其光明磊落的气质、平淡如水的性格、不惜重金购书的举动以及妙笔生花的文章所吸引,迫不急待地希望能与其再次相逢,促膝长谈。
这些人以萃升书院为依托,形成一个声势浩大的学术团体。尽管书院的职能主要是训练时文帖括,缺乏自由度和学术特色,但大多有才之士都会首先经过书院的教育,许多优秀的学者也会主动选择在书院中讲学。另一方面,书院藏书丰富,有利于学者从事研究。丰富的图书资料吸引了众多学者在书院学习、从教,使书院成为所在地区学术文化交流的中心。以多隆阿为代表的一批学者,专治经学,不屑帖括,他们相互唱和,经常彼此切蹉,互为标榜,在自身学问的增长的同时,无形中也影响了他们的兴趣和学术思想。应该说,多隆阿在以萃升书院为中心的学术团体中获得了从事经学研究的基本条件,为 《诗经》研究准备了大量基础资料,为《毛诗多识》最后成书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客居何维墀幕府:《毛诗多识》的初创期
关于多隆阿写作《毛诗多识》的过程,目前文献材料很少,难以有清晰的脉络。不过,通过对《自序》《再序》的考察,我们还是发现了一些蛛丝马迹。他在《自序》中云:“余自童年读诗,亦祇随俗立解,间有会心,亦多骑墙,鲜有依据。迨至壮岁,得读汉唐注疏,参以师友讲论。偶得义理,则用片楮记之,积之既多,恐有散失,因录成卷帙,名曰多识。”[8]3239仔细研究这则材料,我们不难发现,《毛诗多识》的写作主要分为两个阶段:一是书院教育。多氏在童年时就对《诗经》情有独衷,成年后,随着读书视野的扩展和学识的增长,加之师长朋友的影响,对《诗经》的兴趣更浓,并以片楮记之。这是《毛诗多识》的准备阶段。二是从业幕僚。壮年后,得读汉唐注疏,经过长期积累,最后完成了《毛诗多识》。这一阶段又分为三个时期:一是客居何维墀幕府时期,二是家居辽沈时期,三是主持平阳书院时期。
多隆阿一生与何维墀息息相关,多氏何时进入何晓枫幕府,是值得关注的问题。《多公墓志铭》云:“同年何晓枫维墀为礼部郎,雅重公,延公教子,兼佐幕事。”[1]3461何维墀任职京师,多隆阿并未马上成为其幕僚,兼其子教师。乙酉年拔贡后,多隆阿去南京金山书院讲学,后来回到盛京,任莲宗寺书院山长,与张玉纶相唱和。道光九年秋(1829年),道光皇帝幸临莲宗寺书院时,多隆阿还任山长。所以,多氏成为何维墀幕僚最早当在1830年以后。多隆阿入京,成为他一生当中最为重要的时期,也是最为关键的时期。清人虽没有像宋人那样聚众讲学,幕府却给他们提供了许多相互学习交流的机会。一般幕主都有自己的藏书,可以供幕僚使用。幕僚与幕主之间往往是一种师友关系,能够很便利地翻阅、使用主人的藏书,这对于他们的学术研究和撰著活动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如孙星衍阅毕沅藏书,则竟其学;赵翼得汪由敦藏书,见闻日扩,益肆力于古学;李详遍发谢元福藏书,而学识大进。[5]206何晓枫出身经学世家,父亲在朝为官,家藏图书颇丰。京师,自乾嘉以来,逐渐成为汉学的大本营,许多著名学者聚集于此,切磋学术,书籍流通便捷。多隆阿在此有机会接触到一些在辽沈无法见到的图书资料,他在教授之余,可以广泛阅读古代典籍,天文数术、星经地志,凡百家言,无不备览。同时,他还有机会与来自各地的学者进行学术交流。据《易原·自序》云,他为了完成《易原》曾广征博引汉魏诸儒的有关著述,兼取唐宋以后名家的言象之作,相互参照,辨其优劣。《毛诗多识》博引众家之说,尤其是清代许多汉学家著作,皆得益于此时的涉猎。另一方面,游幕又是增长阅历、消除悬疑的一条重要途径。这一时期,随着阅历增加和学友之间交流的频繁,多隆阿逐渐意识到先前所著《易原》草稿的不足,于是集中精力删润《易原》。《易原·又序》云:“成童后,就学辽沈,得见学校藏书,参以师友讲论,不揣固陋,僭为折衷,辑成篇帙,私藏于箧已十数年,草凡五易,釐为十六卷。 ”[8]3239-3240又《易原序》末附写于“强圉大渊献相月初吉日”[8]3239。 这两则材料提醒我们,多隆阿“僭为折衷,辑成篇帙”的初稿应写定于“强圉大渊献”即丁亥年(1827年),而“草凡五易,釐为十六卷”则当在道光丁酉年(1837年)。从丁亥年到丁酉年,整整十年,多氏的主要精力都集中在《易原》的删改润色上。从“草凡五易”的情形看,由于稿件一改再改,劳神费力,他根本无暇旁及他书。此时,《毛诗多识》还处在“每得一义,辄驰书与其共学之友相商榷”[9]64的阶段,没有成型。《毛诗多识》的写作真正被多氏提上日程应该在1837年以后。这时,《易原》已经刊刻,多氏有大量的时间投身《毛诗多识》的写作,直至何维墀道光乙巳年(1844年)知府赣州才被迫中止。多氏不去江南有多种原因,而《毛诗多识》正处于写作的关键期恐怕应是主要原因。
三、家居辽沈时期:《毛识多识》的完成期
何氏南行官仕,多氏北归著书。据《多公墓志铭》记载“会何出守江西,公辞归。既而何守平阳,聘公为山长,掌书院事。”[1]3461多隆阿在离开何晓枫幕府,主持平阳书院之前,曾一度呆在沈阳或其家中。《毛诗多识》草稿当写成于此时。《毛诗多识·又序》云:“《毛诗多识》十二卷,此为十数年前读汉唐注疏之所著也。草甫毕,即缮写成帙,寄于同年周华甫先生处求订正,其后先生殁而此本遂失。辛亥春,余自燕晋游归,日长多暇,偶阅旧书,见原草尚存,因重加删润。”[10]3361这段话,有几个重要信息:一是十数年前,多隆阿已开始着手《毛诗多识》写作;二是《毛诗多识》已缮写成帙,并经周华甫订正,然其稿已失;三是辛亥春(1851年),自燕晋回归,偶阅旧书,原草尚存;四是多氏《序》写于“岁次重光大渊献相月望前三日”即1851年七月。综合分析以上信息,我们可知《毛诗多识》经过很长时间的写作过程,并且在多氏任平阳书院山长之前业已完成草稿,否则,辛亥年由晋返回后,“偶阅旧书,原草尚存”,“因重加删润”之说就不合乎情理。再从《后序》写于辛亥年看,又与“此为十数年前读汉唐注疏之所著也”暗合。《毛诗多识》写成后,曾寄于周华甫处订正,未毕,多氏就离开沈阳入晋,周华甫先生亦因病而殁,订稿遂失。这个版本幸赖辽阳袁氏所藏得以保存。此书共十二卷,前有多隆阿《序》,无《又序》,且“文词烦冗,伪夺最甚”[11]3459,是草稿本无疑。这样看来,多氏何时去平阳就成为解决《毛诗多识》何时成草的关键。多隆阿应何晓枫之邀来到晋阳应为何时呢?据《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载:“何维墀,奉天府金州厅人,由拔贡朝考一等分礼部,道光三十年十月初二奉旨补授山西太原府遗缺知府。”又云:“延志,二十四年正月奉旨补授山西平阳府知府,三十年七月调署太原府知府。”[11]191由此可知,道光三十年(1850年)何维墀去平阳补因延志升迁而遗留的空缺。这一事件,在《临汾县志》也可证实。《何太守传》云:“平阳太守讳维墀,号晓枫,奉天金州人。乙酉拔贡,甲午举人,由礼部外郞授江西赣南知府。道光三十年擢守平阳。”[12]50何维墀道光三十年十月到达平阳后,很快邀请多隆阿同年来相约。《毛诗多识》最迟不晚于道光三十年定成稿。
四、主持平阳书院时期:《毛识多识》的修订期
何维墀擢守平阳后,多氏再三推辞不成,也很快来到平阳,但并未立即就任平阳书院山长。从时间上看,何氏于道光三十年(1850年)十月任平阳知府,书信往返,加之多氏从辽沈来平阳,最早也应在当年年底。而《又序》言“辛亥春,余自燕晋游归”,年底而来,开春就归,于情于理,都难讲通,所以最合理的解释就是多氏此来,一则是探望老友,二则更主要的是酬谢知己。《多公墓志铭》:“初至,诸生寥寥,次年学舍至为之满。值岁试,县令某聘公阅卷。……哈公芬来抚晋,莅任日,接控呈八十纸。哈公在部时,素耳何清干名,悉以委之,何以为难。 ”[1]3461仔细分析这段话,我们隐隐发现,“诸生寥寥”是何维墀力邀多氏入主平阳书院的主要原因。学校教育是封建社会考核地方官员是否合格的一个重要条件,作为一位刚刚到任的一府之长,面对如此窘迫的教育状况,必然是心急如焚,于是力“聘公为山长,掌书院事”。“何屡遣人促之”和多氏“不得已乃西”,都说明书院之事直接关系到何之仕途,作为至交的多隆阿,即使不情愿,碍于情面也不得不就任平阳书院山长。多氏也不负所托,仅此一年,书院由“诸生寥寥”到“学舍至为之满”。我们再把“初至”“次年”“哈公芬来抚晋”三者联系起来考察:哈公芬“莅任日”就接到“控呈八十纸”,悉委何维墀全权处理。据文献记载:“哈公芬,咸丰二年(1852年)十二月署山西巡抚。”[13]25这样,整个事件的脉络就十分清晰了:1851年秋,多隆阿初至平阳,次年书院就人满为患,这年冬天,哈公芬来抚晋,多氏得以再次显示其干练之才。多氏答应何维墀主持平阳书院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他找到了遗失多年且正在修改的《毛诗多识》草稿,他想利用书院藏书和相对比较宽裕的时间来完成此书的修订工作。道光三十一年(1851年),多氏将尚在删润的稿本带到平阳,并“岁次大渊献相月望前三日”写完《后序》。至此,《毛诗多识》正式完成。初,请训诂大家王筠为之订正。王筠,为官十年,皆在平阳周围,《乡宁县志》说他为道光丙午年在任,《补修徐沟县志》称其道光二十七年在任,《新修曲沃县志》称他“咸丰元年属”县令。多隆阿去平阳之时,正是王筠知县曲沃之日。王筠游历京师三十余年,博涉经史,手不释书。多氏与王筠何时认识,史无记载,但二人相交很深,常“邮书商榷,部析疑义,殆无虚月”[14]331-332。《毛诗多识》修订完成后,可能缮录成二册:一册寄于沈阳张玉纶,就是后来的辽阳张氏排印本。此书共为十二卷,《曹风》以下皆完备。题曰辽阳张氏绣江著,乃张绣江后裔所刊印。有《自序》,有张氏玉纶《再序》。卷首原《序》云“或曰此多氏之所识者”[8]3239,则书出于多隆阿之手无疑。伦明称“后《序》之题张玉纶者,乃郭象盗庄之类也”[15]401,实为不妥。 《辽海丛书总目提要》云:“及读何绍墀《阳宅拾遗序》称多氏有《毛诗多识》十二卷,又辽阳袁氏藏旧钞本有多氏再序亦称雯氏自识,乃知张刻之识,或疑氏有意让美,然张氏为多氏《志墓》亦称有《毛诗多识》十二卷,得此乃知张氏决非攘美,证以袁氏藏本,始知为张氏后裔误署。”[16]3645乃为公允之论。另一册则请王筠订校。“公以所著此书相质,先大人手校一过,爱其博赅,使小胥写副本,仍原稿归之。”[14]331王筠校订时,曾亲自赴平阳,极力劝说雕版刻印《毛诗多识》,但多氏以书未至精为由,认为不可。别后,王筠在《致多雯溪先生书》又再三重申其义,云:
“前在平阳所言大著《毛识多识》刻版后须卖之,而兄以为不可。当时弟颇悔芒浪。别后,反复思之,恐弟之说未为不可。而大兄所妨,过于狷介。则请申前说,惟大兄裁焉。……盖当其著书也,是为独善之事。及其成书也,则无论圣经贤传及诸子百家,下而一技一能。有益于人者,皆当目为兼善之事。既云兼善,则当公之天下,而不可私之一家也。彰彰明矣。……况大兄之书,弟已见之。虽以鄙陋之胸,犹窥见其可以信今而传后,使有识者见之,不知其倾倒更当如何?而欲秘之枕中,不肯悬之市上,则弟于所识之读书人,尽告以雯溪先生之书,使之为弟分不见王氏书之心病,而不甘独受此病也。 ”[17]433-434
王筠认为无论是圣经贤传、诸子百家以及私著之书,只要有益于人,都当悬之市上,兼善他人,不可秘藏枕中,亦不可因此而成为读书人的一大遗憾。何况王筠认为《毛诗多识》“可以信今而传后”,“使有识者见之,不知其倾倒更当如何?”以王筠之才学,对此书如此推崇,此书价值不言而喻。尽管王筠字字珠玑,言出肺腑,《毛诗多识》终究未刊行于世。
一年后,平阳府乱兵渐起,多氏、王筠相继亡没,多氏《毛诗多识》遗稿散落,王氏所订《毛诗多识》残缺不全。据王筠之子王彦侗在《毛诗多识》阙本后云:“扶柩归里,葬后,发箧庋书于格。后因曝书,检视此书,忽少后二册,寻问迄不可得”,后盛昱“闻此书于尹伯园,索观之”[14]331-332,因“稿本丛杂”,属程棫林校订,因盛昱不幸旋卒,未及刊刻,遗稿又散落。杨钟义于坊肆间偶见《毛诗多识》本与紫幢居士手钞本并杂所售书目中,默然伤神,于是购回。乙丑中秋,刘承干将程棫林二卷本厘定为六卷,并由嘉业堂刊印。此本校雠极审,文字经王筠、程棫林、刘承干修订,惜止六卷,未为完书。
这样,《毛诗多识》的成书过程就十分清晰了:多隆阿在以萃升书院为中心的学术团体中获得了从事经学研究的基本条件,为《诗经》研究准备了大量基础资料,为《毛诗多识》最后成书打下坚实的基础。客居何维墀幕府时期(1830-1844年),以1837年《易原》刊刻为界分为两个阶段:前期,《毛诗多识》写作还处于片言只语的积累阶段;后期,多氏有大量的时间从事《毛诗多识》的写作。家居辽沈时期,《毛诗多识》成草,并寄于周学甫订正,然周病殁,稿件遗失。主持平阳书院之前,多隆阿发现《毛诗多识》旧草,携之回平阳删润,并寄于王筠校订。因乱兵渐起,多氏、王氏相继而殁,《毛诗多识》遗失二册。后再历经程棫林、刘承干校订,厘定为六卷。虽非完书,有功于学林非浅。
[1]张玉绣.例封文林郎乙酉科拔贡生多公墓志铭[M]//慧珠阁诗钞.沈阳:辽沈书社,1985.
[2]李翰颖.文学志·多隆阿传[M]//岫岩志略:卷八.沈阳:辽沈书社,1985.
[3]缪立孙.梦鹤轩楳澥诗钞[M].沈阳:辽沈书社,1985.
[4]钱仪吉.周先生永年传 [M]//碑传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5]尚小明.学人游幕与清代学术[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6]裴焕星.张玉纶传[M]//辽阳县志.沈阳:辽沈书社,1985.
[7]张玉纶.己卯冬雪夜怀人诗·符象芝 [M]//梦月轩诗钞.沈阳:辽沈书社,1985.
[8]多隆阿.易原[M].沈阳:辽沈书社,1985.
[9]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10]多隆阿.毛诗多识[M].沈阳:辽沈书社,1985.
[11]秦国经.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第3卷[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12]刘玉玑,关世熙.何太守传[M]//临汾县志.民国二十二年铅印本.
[13]徐继畲.候选道春湖沈公八十寿序 [O]//退密斋文集.光绪石印本.
[14]屈万里.清诒堂文集[M].济南:齐鲁出版社,1987.
[15]伦明.续修四库全书提要[M].北京:中华书局,1965.
[16]金毓黼.辽海丛书总目提要[M].沈阳:辽沈书社,1985.
[17]王筠.箓友蛾术编[M]//徐德明,吴平.清代学术笔记丛刊.北京:学苑出版社,2005.
(责任编辑 周亚红)
A Probe in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oronga’s Life and the Writing of Maoshi Duoshi
LIN Wen-long
(School of Arts,Shanxi University,Taiyuan,Shanxi 030006,China)
The process of the writing of Maoshi Duoshi and recognition of Doronga’s life friend-making are misunderstood because of brief biography and lacked anthology.Doronga was contented and indifferent to worldly gains.His basic conditions for classic studies acquired from academic groups centered by Cuisheng Academy of Classical Learning provided a solid foundation for writing Maoshi Duoshi.This book is of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spreading and extension of academics of the Qing Dynasty in Liaoning regions.
Maoshi Duoshi;teacher and friend;academic study of the Qing Dynasty
I207
:A
:1673-1972(2014)02-0056-05
2013-10-21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日韩《诗经》百家汇注”(10&ZD101)
蔺文龙(1976-),男,山西洪洞人,讲师,博士,主要从事清代经学与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