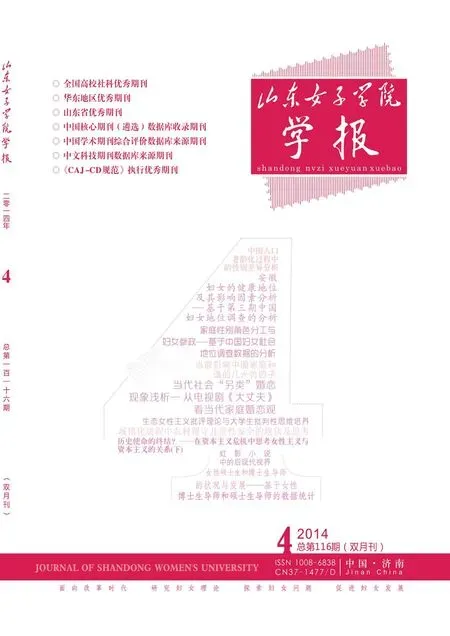虹影小说中的后现代视界
2014-04-10张守华
张守华
(山东女子学院,山东 济南 250300)
虹影是当代女性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就她的小说而言,在国内能见到的除《鹤止步》是写男同性恋外,其他皆以有着不同的职业和婚姻状况的中国女性为主角。她运用反本质主义和多维视角的叙述方式讲述了一个又一个不同于男性作家宏大历史文本中的“历史”,向男权话语统治提出质疑,向读者揭示出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二元对立”[1](P58)的复杂世界,体现出历史背景的非深度性、叙述视角的非中心性和对权力话语的解构等后现代主义特征。
一、历史背景的非深度性
在虹影看来,任何隐秘的历史都会被面向大众的历史所掩盖,翻过历史的非正式记录才能看见历史的原貌。这种对传统叙事的不信任导致了虹影小说文本对历史的模糊化,从而达到解构传统历史的目的。但是解构并不是销毁,历史也无法销毁,解构的目的在于重建,重构在“大历史”中消失的底层人物、边缘人物、女性的历史。
小说《上海王》描写大革命时期的上海,主人公——申曲名角筱月桂由一个乡下插秧女成长为上海滩名副其实的“上海王”的不凡经历。作者通过中国传统的“命相说”将筱月桂与上海洪门的兴衰联系在一起,而洪门的兴衰荣辱又与近代中国政治的风云变幻息息相关。在这个文本中明显地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筱月桂奋斗的1925年的上海的风物人情。那些大事件只是几个在任何历史教科书中都可以查到的名词。同样,在《上海之死》中,著名演员、美国情报人员于堇也是一边回忆自己的人生路一边执行一个后来改变二战战争局面的任务:窃取日本的军事情报。她的身上凝结着上海的军阀之争、国际大战盟国和协约国之争。在她纵身跃下高楼的刹那,我们看见的是一个美丽生命的终结,她的人生之所以感动我们不仅因为她挽救了中国,更因为她是一个女人,一个渴望爱却无爱的传统意义上的弱女人。正是这个弱者,这个处于战争边缘的女人改变了历史。作者将历史名词的内容巧妙地演绎成为一位民族女英雄的传记。我们可以相信,历史不只是男人创造的,可是在正史中我们却看不到女人的记录,虹影在她的小说中做到了对女性历史的重建。
关注小人物的生死情爱挣扎是虹影书写视角与男性宏大历史叙事塑造英雄的正义血性的最大不同。玛格丽特·尤瑟纳尔说:“她们把战争作为背景,个体的感情和生存遭遇才是她们关注的焦点。在我看来,这是她们共同的女性立场使然。历来战争都是男性的,女性从未真正置身其中,她们被驱逐于战争历史外,要么成为男性的欲望对象,要么等待男性的启蒙和拯救,如果个别女性想要走上战场,她们得‘通过忘却,抹煞性别’”[2]。所以,历史背景的模糊化也是作者人文关怀的需要。在小说文本故事中的人物表现出后现代文学理论所说的“零散化的共时性存在”[1](P47),因为历史本来就不是一个人的,这些小人物,没有在历史中留下足迹,他们是历史的过客。我们无法为小人物一一作传,这是文字的无力,历史的苍白。可是我们可以不再沉默,我们可以重建历史的另一半——女人的历史。虹影的小说“穿透了宏大的历史迷雾,用个人想象和经验返回到历史情境,又在对历史的书写中走进个人的情感世界。”[3]
二、叙事视角的非中心性
虹影以一种平和的心态看待人类文化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其所秉持的态度也更加宽容,视野也更加开阔。在虹影的文本中,我们看不到非友即敌、非男即女、非好即坏的“二元对立”的叙事模式,也没有把事物都归纳说出现象背后的本质的深度。因为在作者看来,人类生活在这个非单向度的历史空间中,思维不应该是一种思路,历史的本质在不同的人那里也有不同的表达。所以,她只是一个叙述者,一个享受文本欢乐的作家,那些关于历史的定义应该交由历史去评论,她只给读者提供一种现象或者自己的创作感受,甚至作者的思想都是读者产生评价的参考。
在重写笔记小说系列中,她将明清的笔记体小说框架拿到现代,用当代的人情世故重新演绎,将多视角的思考融入一个个生动的故事。《白色的蓝鸟》中,女大夫盛年年通过自己的报复惩罚了背叛者沈立,也拯救了被痛苦折磨的逻辑学家。对背叛的惩罚不是传统的两败俱伤,而是让自己扳回一点损失又同时重重打击叛逃者。她将作品中的主体选作日常生活中的凡夫俗子,通过文本对这个属于人的世界做出自己独特的陈述。在她的战争描写中我们看见不是很坏的“敌人”,如《垂榴之夏》中的缘子眼中的日本军医并不是传说中的那么坏,日本军医的“声音不凶,反而温暖人”。《鹤止步》中写白色恐怖时期特务大本营上海极斯菲尔路76号中发生的两个小混混男人间的感情。尽管我们对汪伪特务机构的凶残早有耳闻,但是在这里我们没有看见特务如何残害“正义人士”,而是通过作者细腻的心理描写看见非正常感情的挣扎,甚至这种挣扎到最后都会感动我们,就像小说的名字所表达的:“鹤欲飞,升起的腿却突然静止不动”的凄美。消解了二元对立,故事叙述变得丰富和悲悯,这也是虹影超乎寻常的人文关怀之处。
后现代主义反主体性观认为:非神圣主体的个体将那种集体性的乌托邦还原为个体性的自我存在。他只是自然地、宽容地看待事物标准和争端,没有超越历史的观点。任何标准都不可能具有先验绝对性,任何结论都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获得,而需要人这一存在主体自身不断地去发掘和把握[5](P51)。虹影在她的作品中对这一点进行了很好的探索。筱月桂成为名副其实的“上海王”以后仍是孤独的,她不是神圣的王者,她只是一个渴望亲情爱情的女人,甚至甘心做小妾。她是一个报复心很强的人,甚至想法杀掉自己的舅父母,但是对表弟并没有一起憎恨,因为父母的仇与表弟无关。同时,她又是一个全心爱自己孩子的母亲,为了成全女儿,她舍弃自己的爱人。她站在最高的上海国际饭店楼顶,内心涌动着没有亲人的悲凉。
虹影小说文本中的多种文化状态的表述瓦解了传统叙述的权威性。“她以一种中国作家普遍缺乏的全球化意识,即在全球化的历史场景中表现人类面临的生存困境。”[4]《女子有行》写一个在未来时间里穿行上海、纽约、布拉格的中国女人的生动冒险。在这三部曲里,我们看见这三个国际移民城市里纷扰的民族宗教种族纠纷。作为一个海外华人,深知离散人群的艰辛生存状态,不仅要对抗基本的生存问题还要面对排外者的歧视甚至敌对目光。作者以一种全球化的视野审视这些行为,肯定这种行为的原因是出于生存的恐慌:“每一个人的出现都是在消解另一个人的存在”,然而,这种趋势能阻挡得住吗?宗教能救赎人迷途的心灵吗?显然不能。作者透过女主人公的冒险向读者说明:国际移民势不可挡,任何阻挡都会造成伤害,看看我们是要建立一个丰富多彩的生存空间还是要建立一个国际难民营,和平共处是在经历了这一系列灾难后唯一处理民族、种族、宗教纠纷的做法。
三、叙述话语的解构性
历史的模糊化和多元叙述是作家解构权力话语的文本需要,这种解构体现在文本中就是女性话语的重建。后现代主义理论认为,话语即权力,文本写作的目的不单单是为了讲述一个有趣的故事,文本的目的是要表达一种声音。后现代主义文学理论就是虹影小说中所要表达的后现代女性主义世界观的有力工具,虹影的小说无论从写作背景还是文本结构的安排都体现着作者渴望发出声音的需要。
在虹影看来:“男权社会几千年,把女人的社会角色固定在闺帏、卧房、产房、厨房里,而女人也把自己的角色固定化了,认为外面的世界本来就是男人的世界。一句话,被男人奴役惯了,就甘于自我奴役。因此,女人的苦恼男人要负很大的责任。”[5]虹影从传统的女性形象入手,讲明女性的深重痛苦:大多数女性在最初都对男人抱有幻想,因此她们也承受着传统的不公和男人的伤害。在《上海王》和自传体小说《饥饿的女儿》中,每个女人都有一段隐痛,这种隐痛来自男人,来自男人控制的社会。筱月桂在乡下田里插秧,蚂蟥吸在腿上,怎么也打不掉,她希望有人来帮她对付那个吸血的家伙,可是没有人。六六不明白为什么别人都不理她,家里人也不喜欢她,她孤独的童年希望有人陪伴,可是没有,她懵懂的青春需要别人指点,可是没有人,只是因为她是个为人和社会所不耻的私生女。所以在得知自己身世的真相时她痛苦地选择逃离,流浪在寻找一个能容纳她的家和爱她的人的路上。这些女性,在最初都是寄希望于这个社会和这个社会的当权者——男人,她们承受着这种希望破灭后的无助和痛苦。
与一些女性作家写女性对男性的反叛流于极端女权主义或者通过自我放纵挣脱压抑不同,虹影在让我们认识到女性经历的重重伤害和磨难的原因后,她迈过“宝贝们”的肤浅身体反抗,从女性的话语权入手重构女性独立的道路。她笔下的女性有着后现代女性主义的特点:女性是自由的、独立的,女性应该自己拿主意,自己来塑造自己的角色,而不是等待男人的安排。《孔雀的呼喊》中的后现代女性柳璀在美国读书期间,有朋友质疑她不找情人,而柳璀自己的看法是:她看不起男女之间这种随便的关系,倒不是讲究道德,而是这种关系把堂堂正正的人弄得卑贱龌龊。柳璀既没有“新”到只顾一己快活,也没有“旧”到一切无所适从,丧失思考判断能力。在《我们互相消失》中,女教师尹修竹同时爱上两个男人, 这抉择对女性来说是那么困难,因为男人可以三妻四妾,女人却没有这种特权。修竹偏不做“白马与黑马”的选择,因为二者舍去哪一个都会心痛,她把选择权放给同样爱她的男人,她勇敢地说:“别害怕!我已经听够了你们俩人间来回倒账,谁欠谁的?——别以为我是你们可以切开,可以分的财产,错了,我早就明白我应该成为自己!——爱情不应该被绑架,不管以什么理由”。女性重新定义生存的这个社会,自己的感情和身体应该忠于自己的利益,而不是成为谁的附属物。她否定了女性身心内外的神话——男人的救赎和宗教的救赎,在她看来女性的自我救赎才是有效的,才是及时脱离苦海的“捷径”,这无疑是对男性创造的神话的有力还击。
掩卷沉思,虹影的小说给我们带来文本阅读快乐的同时,也以她独特的后现代叙述视角和叙述方式给我们展示了观察世界、理解世界尤其是女性世界的宽阔思维方式。她的小说正像“孔雀的叫喊”,立足于小人物,书写草民的历史,发出女性的声音,深沉而悲凉,震撼而颇具启示意义。
参考文献:
[1] 张广利,杨明光.后现代女权理论与女性发展[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
[2] 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136.
[3] 李凤青.试论虹影小说的女性历史叙事[J].批评与阐释·当代文坛,2007,(1):102.
[4] 虹影.女子有行:序言[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
[5] 虹影.我与卡夫卡的爱情[M].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6.2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