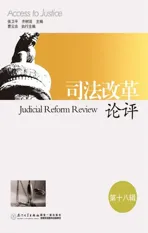人民监督员制度之完善
——兼论公诉程序之民众参与*
2014-04-09王星译
王星译
人民监督员制度之完善
——兼论公诉程序之民众参与*
王星译**
引 言
人民监督员制度是最高人民检察院首先在多个地区试点,之后正式推行的一项制度,被认为是扩大公诉程序民众参与、制约起诉裁量权的一项新举措。自2003年始试行7年之后,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10年颁布了《关于实行人民监督员制度的规定》。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人民监督员制度一直在褒赞和质疑之中步履维艰。自娩生之时,该制度就存在先天不足:受制于检察机关的内部管理,缺乏一定的独立性;监督员过于精英化,且任期过长;作出的决定对检察机关而言并不具有实际的约束力等。加之其在司法实践中的积极受益极为有限,检察机关一度的热情也渐趋冷却下来,对人民监督员制度作出进一步的改革似乎信心和动力均有不足。作为提倡民众参与、扩大司法民主的一项新举措,人民监督员的正当性以及积极意义自不待言,许多学术研究也多有涉及,本文不再展开论证。如欲实现其创设之初的目标和功用,必须对现行人民监督员制度进行几近全面的改革。
一、民众参与公诉程序之代表模式
刑事司法体系的运作从来都不是仅靠自身独立运作的,否则这种自我指涉注定会让人对其正当性产生怀疑,因此,民众参与司法甚为必要。在全球化法律背景下,民众参与司法也被各国司法实践发展出适于本国发展的模式。公诉程序作为刑事程序中衔接侦查和审判的中间环节,一方面将终结侦查权的运作,另一方面又可能触发审判权的启动。检察机关作为公诉权的垄断享有主体,对公诉与否享有一定程度的裁量权也就十分必要。同时,如何对起诉裁量权进行有限制约,以免滥用侵害个人权利,有损正当程序原则,也是各国刑事司法予以重视之处。
论及民众对公诉程序的参与,两个域外模式不可避而不谈,即美国的大陪审团以及日本的检察审查会。学者也常对二者予以介绍、比较研究,并将其与人民监督员制度进行比较研究。本文从写作主体出发,仅论争二者对于我国人民监督员制度的改革和完善的有益之处。
(一)美国大陪审团式微及可借鉴之处
大陪审团即起诉陪审团,根据美国宪法修正案,承担重罪及死刑案件的起诉职权,①U.S.Const.amend.V.该宪法性权利只适用于联邦案件,并不适用于各州。②Hurtado v.California,110 U.S.516,538(1884).其核心作用是遏制检察官起诉裁量权,③United States v.Cotton,535 U.S.625,634(2002).保护民权,使公民免遭不合理追诉或滥诉。④United States v.Dionisio,410 U.S.1,17(1973);United States v.Smith,27 F.Cas. 1186,1188(C.C.D.N.Y.1806)(No.16341A).其服务的目标在于:调查犯罪行为,听取与犯罪行为相关的证言,作出起诉犯罪行为人的指控书。⑤Jeffery T.Wennar,Gang Prosecution:the Grand Jury Investigation,43-DEC Prosecutor 27,2009,p.27.
但不可否认的事实在于,经历几百年的历史发展,到现今,美国大陪审团程序已经基本失去了创设之初的功能,其被学者所赞誉的有效控制检察官起诉裁量权的机制名存实亡,甚至也未实现保护个人权利,尤其是被告人权利的功能。⑥Andrew.D.Leipold,Why Grand Juries Do Not(and Cannot)Protect the Accused, 80 Cornell.L.Rev.260,1995,p.323.大陪审团制度在美国同样正面临亟须改革的局面。
第一,大陪审团调查程序并未体现控辩双方的对抗制,而仅听取公诉方的证据,不听取辩护方的意见,难免会被检察官“操控”,“偏听则暗”。此即大陪审团被誉为受检察官控制的“橡皮图章”的症结所在。⑦George H.Dession,From Indictment to Information—Implications of the Shift,42 YALE L.J.163,1932,p.163.
第二,大陪审团享有秘密传讯有关人员和要求被传讯者在宣誓的情况下进行陈述等特殊权力,而且拒绝向大陪审团陈述证言可以被判处藐视法庭罪,所以检察官往往能借助大陪审团获取有罪证据,⑧FEDERAL GRAND JURY PRACTICE,at 31~32.以致大陪审团一度被用作政治派系争斗的工具。①何家弘:《陪审制度纵横论》,载《法学家》1999年第3期。
第三,根据联邦最高法院的判例,大陪审团程序并不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②Calandra,414 U.S.at 344~45.即证据获得方式并不影响起诉与否决定的作出,亦不适用传闻规则等排除规则,③Costello,350 U.S.at 363.加之检察官被允许向嫌疑人问诱导性问题,④U.S.Dep’t of justice,federal grand jury practice32,1993,p.66~67.极易导致大陪审团据以作出的起诉与否之决定是建立在根本不具有可采性的证据之基础上。
最后,大陪审团信息来源几乎完全只依靠检察官,甚至对相关法律、专门知识的了解也来源于检察官。本应被监督的检察官却几乎扮演了法律咨询专家的角色。⑤Susan W.Brenner,The Voice of The Community:A Case For Grand Jury Independence,3 Va.J.Soc.Pol’y&L.67,1995,p.124.
虽然大陪审团在实际运作中存在诸多不足,然而不变的是,重罪案件必须经大陪审团起诉仍然被规定在美国宪法修正案之中。(包括大陪审团在内的)陪审制所蕴含的民主、自由等精神以及对个人权利的珍视,应成为美国人的基本信仰之一,这种信仰充分体现在刑事司法体制之中。正如《法律之门》中所言:“由普通民众组成的陪审团利用自己的良知对案件评判,让‘街上的普通人’卷入或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这是最重要的民主原则之一。”⑥[美]博西格诺等:《法律之门》,邓子滨译,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516~517页。这种对民主的信仰是当下我国刑事司法体制改革所欠缺的。当然,民主意识的培养和提升也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依靠制度在实践中的具体运作来助力,人民监督员制度正是一个绝佳契机。此其一。
其二,虽然在司法实践中,所谓大陪审团独立只是一种“法律虚拟”(Legal Fiction),近似一种假象,⑦Niki Kuckes,The Useful,Dangerous Fiction of Grand Jury Independence,41 Am Crim.L.Rev.1,2004,p.2.但其在组织上是独立的,既独立于法院,⑧联邦最高法院在United States v.Williams,504 U.S.36(1992)判例中认为联邦大陪审团并不隶属于法院,但有些州的判例则认为州大陪审团属于法院内部的机构,如N.Y. Crim.Proc.Law§190.05(Mc Kinney 1993)。也独立于检察官,并不因人员选任、经费支持等依附于检察机关。大陪审团成员的人格独立也至关重要。⑨United States v.Watkins,28 F.Cas.419,451(C.C.D.C.1829)(No.16,649).这种独立排除了大陪审团的政治和党派倾向,从而成为民众和法律的纽带。①Peter Megaree Brown,Ten Reasons Why The Grand Jury In New York Should Be Retained and Strengthened,22 Rec.Bar Ass’n N.Y.471,472(1967).
其三,大陪审团与检察官同为控诉权主体,其作出的起诉或不起诉的决定当然具有强制执行力,检察官亦不得违抗。
(二)日本检察审查会之借鉴
日本的检察审查会制度被学者认为是与我国人民监督员制度最为接近的制度,或者是人民监督员制度创设的源起。如对检察审查会作一番考察,再与人民监督员制度两相比较,会发现二者之间存在颇多差异,甚至可以认为除了目的之一为体现司法民主这一相同点之外,似乎别无其他所谓的相同之处。
日本检察审查会立法之初,对美国大陪审团制度做过考察,但鉴于日本由检察官垄断的国家追诉主义的历史背景,与美国起诉制度有所差别,加之美国大陪审团有调查案件的权力,而日本则由检察官享有。如果效仿大陪审团制度,则必然罔顾日本国情,改变现行的刑事司法权力配置,成本较高,且收益不可预见。所以日本相关立法机构将检察审查会的立法目标确定为促进“检察民主化”,并将其审查范围确定为检察权的不起诉决定。②片山直之:《検察審査会の議決に対する法的拘束力について》,载《法学研究》第8期。而检察审查会也成为公诉垄断的例外之一(另一个例外是准起诉制度)。
2004年修改并于2009年生效的日本《检察审查会法》对检察审查会制度做了进一步的完善,主要体现在审查程序的设置,参与审查人员的增设,检察审查会作出的决议的效力等。这些改革可以作为我国人民监督员制度完善的参照。
首先,有关组织设置和审查员的选任。检察审查会设立在地方法院及其支部,独立于检察机构,目的在于保障履行公诉权的过程中反映民意、正确适用法律。审查员的选任也较为“大众化”,为具有众议院选举权的公民,通过抽签的方式确定,且任期较短。
其次,检察审查会的审查对象包括:对检察官作出不起诉处理的案件是否适当进行审查的相关事项;与改善检察事务的建议或者劝告相关的事项等。
再者,设置审查辅助员,③有关“审査辅助员制度”参见http://www.courts.go.jp/kensin/seido_hojyo/index. html,下载日期:2013年11月5日。其义务是:对所审查案件涉及的法令及其解释进行说明;对该案事实和法律上的问题进行整理,并对所涉证据进行梳理;从法律的角度对该案件的审查提出必要的建议等。
最后,2004年修法的最大改革在于承认了检察审查会的决议对提起公诉的效果。对该效果的程序保障是两个阶段的审查过程。第一阶段的审查:检察审查会经审查后作出“应当起诉”的决议,检察官再次作出不起诉处分或者在一定期间内不提起公诉时即开始第二阶段的审查,审查后如仍作出应当起诉的决议,该起诉决议具有提起公诉的效果,由法院指定律师提起公诉并出庭支持公诉(即“起诉决议制度”①有关“起诉议決制度”参见http://www.courts.go.jp/kensin/seido_kiso/index. html,下载日期:2013年11月5日。)。其中,如有必要,检察审查会可以在第一阶段嘱托审查辅助员进行具有专门法律知识的审查,而在第二阶段的审查中,则必须嘱托审查辅助员。
新检察审查会法赋予审查决议强制性的起诉效力,是对贯彻民众参与公诉程序最有利的保障,新创设的起诉决议制度是一种市民与法律专家良性互动、共同协作的体制。当然该制度也面临新的挑战,比如该制度对检察官的不起诉是一种实质上的制约,可能影响到检察官的起诉标准。如果检察官考虑到其不起诉决定可能受到该制度的审查,为避免延长诉讼时间、降低诉讼效率,以及不起诉决定被拒绝等可能,会降低起诉的标准,这样又将使法律的平等统一适用、刑事诉讼对真相追求目标的妥协等成为不可回避的话题。况且,一些案件也难免会受到民意的影响,引发对公正的质疑等。为促进我国人民监督员制度完善之故,有必要关注2009年之后日本检察审查会在司法实践中的运作状况,以资借鉴。
大陪审团制度和检察审查会制度两相比较,并不存在谁对谁错、孰优孰劣的问题,二者在其产生和运作的法律环境下,均有其合理性,也有着共同的价值导向,如实际上分担一部分检察权、监督检察裁量权(尤其是公诉权)的运作、增强公诉程序的民主性等等。但是,二者之间存在的差异除了程序设置之外,还有一些值得注意,这也是为我国学者所常常忽略的,试列举几例说明:第一,内容上,前者针对起诉与否,后者则针对检察官的不起诉决定等。第二,由于前者的功能在于决定起诉与否,所以从起诉之前即参与,而后者在程序的加入上较为滞后、被动,即在如检察官作出不起诉决定之后等。第三,较之后者,前者更容易受到检察官的操控,而且程序运作之公开性不如后者,比如,检察审查会中的审查辅助员给审查员提供法律等方面的帮助,而大陪审团获悉诸如法律等问题基本上依赖检察官等等。诸如以上不同之处,实际上反而是处于两个不同法律背景的国家在刑事司法理念上的基本差异:普通法国家对国家权力有着天然的不信任,尤其对代表国家公诉的检察官,更是如此,因此,司法决断的作出更倾向于依靠常人的普通判断力。而具有职权主义倾向的日本(严格讲,日本刑事诉讼法先后继受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传统,从而成就具有“独树一帜”的混合体制,当然,这并不否认日本刑事司法中的职权主义色彩)虽然倡导诉讼之对抗性,但其司法理念却仍保有欧陆传统的理性主义,表现在刑事诉讼中就是对公权力的信任。而为了提高所谓的司法民主,增强公权力行使的透明性以及司法裁判的可接受性,方提出所谓“民众参与司法”的理念。相较之下,美国的大陪审团产生之初却并不是为了所谓“民众参与司法”的倡导,而这种历史性因素在美国刑事司法中的重要性地位也并不是日本检察审查会所能类比和企及的。
二、现行人民监督员制度之检讨
人民监督员制度自2003年适用到2010年被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法律文件确立并推行以来,已经经过七年之痒,其后三年的正式运作定会有一些经验教训,值得总结吸取。然制度建构自身如有缺陷,则往往是致命的,如继续推行,只会离制度创设之初欲达之目的渐行渐远。为此,有必要重新审视现行人民监督员制度,以寻觅相应的改革路径。
(一)独立性之匮乏
人民监督员制度最遭诟病之处即欠缺独立性,主要表现在:首先,人民监督员制度设置在人民检察院内部,运作的经费由检察院承担,组织上不具有独立性,不符合民主监督的原则。其次,人民监督员人选由检察院确定,并由检察院决定选任并颁发证书。虽具体执行的机构是上级检察院或省市级检察院,但考虑到检察院上下级的领导关系,这种人员选任的独立性、公正性不由得让人质疑。最后,人民监督员每届任期五年,较之检察审查会的六个月,大陪审团的临时性、随机性过长。过长的任期不利于人员流动性、更新性,缩小了司法民主的实现范围。甚至有学者担心人民监督员“和被监督的检察机关因日益熟悉而难以保持必要的距离,使得监督流于形式”①陈松林:《从司法民主看人民监督员制度的正当性》,载《法学杂志》2010年第1期。。
这种依附于或者受制于检察院的监督机制遭到的最多质疑在于,检察院的自我监督使得再完善的程序设置都虚置化。归根结底,独立性的匮乏正是检察院“体制内监督的必然结果”②陈卫东:《人民监督员制度的困境与出路》,载《政法论坛》2012年第4期;彭辅顺、陈忠:《人民监督员制度之检讨与改进》,载《河北法学》2010年第2期。。详言之,检察院作为法律监督机关,本来就存在“谁来监督监督者”的循环问题。作为监督检察院权力行使的人民监督员制度在法律和实践层面又被架空,从而成为检察院宣传扩大检察民主的摆设。“谁来监督监督者”③夏邦:《关于检察院体制存废的讨论》,载《法学》1999年第7期。的循环问题仍然存在。当然,究其个中缘由,有对权力必然会滥用的天然性的不信任,加之检察权兼具行政性和司法性的双重属性,很难摆脱权力集中运作的现实。更有甚者,检察权在我国当下语境下有行政化和地方化的倾向,现行人民监督员的组织设置遭到质疑并不令人讶异。
(二)监督程序未能“兼听”
现行的所谓人民监督员监督程序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程序”:程序具有交互的参与性,而人民监督员的监督程序则没有——基本上由检察院主导,缺乏辩护方的参与,“对抗性”不足,未能“兼听”。
一方面,监督程序事实上由检察院主导。检察院事先提供将拟处理决定、主要证据目录、相关法律规定等材料。在随后的具体程序中,由案件承办检察官介绍案情,说明理由和依据,并回答问题,随后即由人民监督员制度进行评议和表决。可见,人民监督员对案件的了解局限于检察机关提交的材料,相关法律适用亦由承办检察官介绍——缺乏开放性认知。这点与美国检察官控制大陪审团所了解的信息相比,倒有些许形似之处,同样面临“独立性”和“公正性”的质疑。对此,日本检察审查会审查程序中设置的审查辅助员可供参考。
另一方面,同样也是2010年的规定较之2004年的试行规定倒退之处:监督程序缺乏辩护方因素。2004年的试行规定中明确人民监督员必要时可以旁听案件承办人讯问犯罪嫌疑人、询问证人、听取有关人员陈述、听取本案律师的意见。且不说该规定是否适当,但规定背后的考量是可取的:为了有助于人民监督员作出更为妥当、公正的决议,应当听“两造陈情”。尤其当审查的事项是检察机关拟作出不起诉决定之时,更应当保障嫌疑人及其律师的意见被倾听。
(三)监督效力之弱化
人民监督员受到质疑之处还在于其行使监督权作出的决议(下称“决议”)并不具有实质上的强制力,对检察机关也未形成充分有效的制约,案件最终处理的决定权还在检察长或检察委员会手中。
现行制度下,决议并不具有强制约束力的根源在于权利和权力意识的错位。在我国的法律背景下,人民监督员制度创设的基础在于人民群众对国家司法机关管理活动享有所谓的知情权、批评权和监督权,而非司法权。①周永年:《关于人民监督员制度法律定位的思考》,载《法学》2006年第6期。同时,依据我国的宪法话语表达,这些权利自然是法律赋予的,而不是“天赋”的,这种弱意义上的权利自然也不能与国家权力相抗衡。法律理应通过对国家权力的制约来保护公民个人权利的世界性通识在我国当下语境下尚未被完全接受、贯彻。司法权威反而在这个意义上得以高度体现,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据此,认为“监督员通过评议案件形成的表决建议,仅是供检察机关在办案过程中参考,对案件行使捕与不捕、诉与不诉、撤与不撤的刑事诉讼终结性权力仍然由检察机关统一依法行使。人民监督员享有的是通过有关案件的评议行使程序上的监督权,并不享有实体上的决定权”①周永年:《关于人民监督员制度法律定位的思考》,载《法学》2006年第6期。自然不令人诧异。
如果人民监督最后的决议对检察机关并没有起到实质的约束力,那么人民监督员制度必定形同虚设,只能成为检察机关为歌颂扩大民众参与范围和程度、贯彻司法民主而放置的摆设。与其自行创设制度之后,将其架空,倒不如完全放弃,倒还能节约司法资源,以平衡刑事诉讼程序在其他领域的不足。
与2004年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的、现已失效的《关于实行人民监督员制度的规定(试行)》一个可取之处在于:人民监督员多数决定与检察委员会决定不一致的,可以要求提请上一级人民监督员复核。虽然这只是一种表达异议的形式性权利,却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即应当设置对异议的二次处理程序,如检察审查会第二阶段审查。2010年同样由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的《关于实行人民监督员制度的规定》删除了该复核申请,无疑是个倒退。
三、人监督员制度之改革
如果要实现人民监督员制度创设时的目标,即司法民主。人民监督员制度目前所能实现的也只是立法层面的“字面”上的形式上的民主,立法既没有规定实质上的民主,司法实践中连字面上的民主似乎都未实现。人民监督员制度虽然能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囿于其自身制度娩出之时的畸形,并未真正实现所谓的司法民主,或检察民主的功能。因此,必须对现行的人民监督员制度进行整体重构。
人民监督员制度的改革和完善,学界也多有探讨,且形成了一些颇为中肯的共识性意见,如人民监督员的选任及任期、组织设置、财政保障等规定亟须修改。②李卫东、维英:《人民监督员制度实行状况实证分析》,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11年第2期;阳继宁:《不起诉裁量权的扩张与制约》,载《法学评论》(双月刊)2010年第1期;罗永红:《日本检察审查会的启示——兼论我国人民监督员制度的完善》,载《河南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秦前红等:《人民监督员制度的立法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丁玮:《人民监督员制度的法理基础——司法民主与正当程序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10年版;等。本文拟提出其他问题以供评判和探讨。
第一,监督的案件范围之“拟作不起诉决定的”延伸至非自侦案件,并限于对检察官裁量不起诉的监督。③人民监督员监督的案件范围问题,囿于文中主题和篇幅不展开论证。针对目前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三种不起诉而言,法定不起诉实属不构成犯罪或者不应承担刑事责任的事项,具有终结程序的效力,不应当再经人民监督员的监督。而对于存疑不起诉,即证据不足不起诉,实际上属于对嫌疑人有利的决定,为了保持这种有利状态的稳定性,不宜经人民监督员监督。存疑不起诉的“程序补救”即如发现新事实、新证据则可以再行起诉。裁量不起诉作出的前提是嫌疑人行为构成犯罪,由检察机关行使起诉裁量权决定不予起诉,为了防止这种起诉裁量权的滥用方有必要进行监督。
第二,监督程序可采听证形式,应当给被害人、嫌疑人表达意见的机会。必要时,可以向法院申请要求被害人、证人到场,并对其进行询问;可以要求检察院告知嫌疑人或其辩护律师提供陈述意见。
第三,监督程序设置人民监督辅助员,为人民监督员就法律知识或其他专业性知识提供咨询。一来可以弥补人民监督员自身知识的不足,二来可以使其对知识的掌握不依附于检察机关,从而助力于作出更妥当的决议。
第四,人民监督员制度的核心问题即决议的约束力。对于不起诉决定,决议的形式可以包括以下两种:(1)不起诉决定不当,应当起诉;(2)不起诉适当,维持不予起诉。
对于第二种决议,自然没有异议。而对于第一种异议,如果检察院审查之后,检察长不同意,认为应当不起诉,则应提交检察审查委员会。检察委员会: (1)如果同意检察长的意见,即应当不起诉,则应将该意见告知人民监督员,继而启动人民监督员再监督程序。再监督程序后,人民监督员仍认为应当起诉的,应当将决议提交给上级检察院,由上级检察院指定其他检察院提起公诉。(2)如果不同意检察长的意见,即认为应当起诉,此时考虑到检察长和检察委员会的关系,检察长可以坚持自己的意见并对该决定负责,并将其决定告知人民监督员,后继程序则顺接前(1)。据此,可以认为,在人民监督员行使监督职权这一问题上,检察长作为检察院的首长,检察委员会作为集体决策机构,均是监督的对象,二者在个案处理上可能态度不同,但应当保持同一立场。
四、结论
现行人民监督员制度经过近十年的运作,法律层面和实践层面出现诸多弊端,亟须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否则只在未触动既得利益者的前提下,通过披挂一件司法民主的外衣,对外显示检察机关誓言贯彻检察民主的决心,对内则行“你监督你的,我决策我的”。无疑只是给检察工作徒增工作手续而已:司法资源已然匮乏,再浪费一点点亦无不可。然而,这种所谓“民众参与司法”并不是真正的司法民主。据此,人民监督员制度的改革应当通过正式的立法予以确立。首先,应当保障人民监督员的独立性。其次,细化监督程序,体现当事人的参与性;配置监督辅助员,为人民监督员提供法律或其他专业知识的咨询。最后,确定决议对检察机关的约束力:一是再监督程序的双重保障;二是经过再监督程序,人民
监督员仍与检察长或检察委员会意见不一致,仍认为应当起诉的,有权提交上级检察院,由其指定其他检察院提起公诉。
*本文系怀柔区人民检察院课题组“检察院组织法修改有关问题研究”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系清华大学刑事诉讼法学专业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