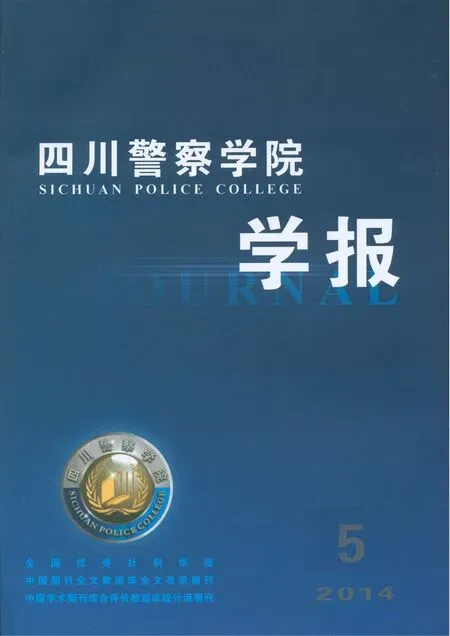论民事、行政有效性与违法性判断的分离
——兼谈法秩序的统一性与刑法判断的独立性
2014-04-09陈雨禾
陈雨禾
(华东政法大学 上海 200042)
论民事、行政有效性与违法性判断的分离
——兼谈法秩序的统一性与刑法判断的独立性
陈雨禾
(华东政法大学 上海 200042)
具有违法性的行为,在民事与行政上的效力一般被予以否定,即违法则不可能有效。但是在一些情况下,肯定这些行为的效力,更有利于法益保护和立法目的的实现,故在民法上出现了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与管理性规定的区分。这体现了有效性与违法性判断一定程度上的分离,而这在行政法上也有体现。这种分离既体现了法秩序的统一性,又体现了各部门法不同的利益导向及法的利益权衡本质,也决定了各部门法判断的相对独立性,即使具有保障法地位的刑法也是如此。“一般违法性”的存在,与刑法判断的独立性不相冲突,而民事、行政法有效性与犯罪的成立也并不完全排斥。
有效性;违法性;法秩序统一性;独立判断
一、问题的引出
《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1年第11期上刊登了“吴国军诉陈晓富、王克祥及德清县中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民间借贷、担保合同纠纷案”一案,并在其网站上作为指导案例予以公布。该案主要是关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中民间借贷合同及其担保合同的效力认定问题。
该案一审法院认为,被告涉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但这与被告和出借人之间的合同纠纷属于两个法律关系,并最终判定该借款合同有效,从而担保合同亦有效。二审法院维持了一审判决,并进一步指出,根据我国《合同法》第52条第五项的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但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正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14条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2条第五项规定“强制性规定”解释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原审被告陈晓富触犯刑律的犯罪行为,并不必然导致借款合同无效,因为借款合同的订立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效力性的强制性规定。法院认为效力上采取从宽认定,是该司法解释的本意,也可在最大程度上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
虽然上述一审法院已经指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刑事法律事实是数个“向不特定人借款”行为的总和,单个借款行为并不构成犯罪。但是不能否认的是,每个“向不特定人借款”都是非法吸收存款罪的组成部分,而且从公平的角度看,作为组成部分的其他民间借贷合同,也同样应该认定为有效。所以遵照上述判决,吸收公众存款行为的行政违法性、刑事违法性并不必然否定其在民事上的效力。
这就引出了本文的问题,那就是一个行为可能是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也即具有违法性,甚至可能构成犯罪,但其在民事上的效力并不必然被否定,也即民事有效性的判断与违法性的判断存在分离。更为重要的是,本案并不只是个别法院在个别罪名下对合同效力的肯定,而是提出了一个更具一般意义的命题:如果合同并非违反法律、行政法规中的效力性强制规定,而只是违反管理性强制规定(也称取缔性强制规定),那么合同并不必然无效。由此,一些违法行为(包括犯罪)如果并不违反效力性强制规定,合同本身仍然可能是有效的。
这就引发了刑法评价与民法评价是否存在冲突的争议。此前认为借贷合同无效的一个强有力的观点就称,借款人已构成了犯罪,合同就不可能还有效,否则刑法与民法就存在冲突,两者应该是非此即彼的关系,有效就不构成犯罪,犯罪就不能有效[1]。也即违法性与民事有效性的判断是一个同一的判断,即违法不可能有效,犯罪更不可能有效。
本文认为,这种有效性判断与违法性判断的分离并不意味着民法与刑法在评价上存在冲突,即这种分离并不违背法秩序的统一性。另外在司法实践中,这种分离不但体现在民事领域,还同样存在于行政法领域。本文认为,这种分离事实上体现的是在法秩序的统一性前提下,各部门法出于立法目的的不同以及法益保护的需要,在各自法律后果的判断上具有相对独立性。民法、行政法如此,而即使是作为保障法地位的刑法,亦是如此。
二、效力性、管理性、强制性规定的区分、依据与意义
在民事领域,违法性和民事有效性判断的分离,是由将强制性规定区分为效力性规定和管理性规定这一途径实现的,所以有必要对这一区分的发展背景进行梳理分析,由此发现其背后的法理依据,以说明违法性与民事有效性一定程度上的分离背后的正当化依据。
上述合同法司法解释将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与管理性强制性规定进行了区分,而违反管理性强制性规定的并不影响合同的效力,这事实上是为了限制国家强制对私法的干预,最大限度地保障私法的意思自治。这里的国家强制主要就体现在法律、行政法规等的规制作用上,落实到司法实践中则表现在对违法性的判断上。
诚然,民事有效性与违法性的判断多数时候是同一的,也即违法即无效。因为意思自治应该有个限度,在侵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或其他公民的合法权益的情况下,这样的意思自治就是一种权利的滥用,并不应该得到法律的保护。这也是大多数国家将违反法律或是善良风俗的民事法律行为定为无效的原因。但是在某些时候,在利益权衡的结果下,认定合同有效更有利于对法益的保护,甚至更有利于实现强制性规定的立法目的,在这种情况下就不能一刀切地否定合同效力。特别是,民法强调的是意思自治和对利益的最大化保护。
对此,其他国家立法一般都规定了除外情况。比如《德国民法典》第134条规定:“法律行为违反法律上的禁止时,无效。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至于具体如何判断违反禁止性规定的合同效力,德国理论界提出了“规范目的说”。该说认为,“法律行为是否有效应视禁止性规定的目的而定。如果认定该法律行为有效,就会同禁止性规定的目的相冲突时,就应否定其效力”[2]。我国台湾地区亦采取这样的除外规定,其《民法》第71条规定:“法律行为,违反强制或禁止之规定者,无效。但其规定并不以之为无效者,不在此限。”司法实践中将强行性规定分为效力性规定和取缔性规定。效力性规定着重于违法行为之法律行为价值,以否认其法律效力为目的,而取缔性规定着重违法行为之事实行为价值,以禁止其行为为目的[3]。也即影响法律行为效力的强行性规定仅仅为效力性规定。至于如何判断何为效力性规定何为取缔性规定,王泽鉴教授认为,“应综合法规的规范意旨,权衡相冲突的利益(法益的种类、交易安全、其所禁止者究系针对双方当事人或仅一方当事人等)加以认定”[4]。
我国《合同法》司法解释将强制性规定分为效力性规定和管理性规定的做法,事实上是借鉴了台湾地区的做法,试图通过效力性规定来实现利益权衡,更好地实现法的目的。对于违反管理性强制规定的合同,虽然并不因为违反规定而影响合同效力,但是也不会排除其承担行政上或刑事上的法律责任,从而并不会产生放纵违法(包括犯罪)的危险。这里将民法上的有效性与违法性的判断相分离,使得民法上的效力与其他法律责任相分离,可以在保护利益的宗旨下,更好地平衡私法自治和国家强制。当然,效力性强制规定不能过于限缩,否则会出现私法自治侵犯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影响其他诸如行政法或刑法等的适用效果。
当然,只有确定如何区分效力性规定和管理性规定的标准,这样的区分才有意义——在最大程度保障司法自治的前提下实现对利益的最大化保护。对此,我国学者提出了以下标准:第一,法律、法规规定违反禁止性规定将导致合同无效或不成立的,该规定属于效力规范。第二,法律、法规虽没有明确规定违反禁止性规定将导致合同无效或不成立,但违反该规定以后若使合同继续有效将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也应当认为该规范属于效力规范。第三,法律、法规虽没有明确规定违反禁止性规定将导致合同无效或不成立的,违反该规定以后若使合同继续有效并不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而只是损害当事人利益,在此情况下该规范就不应属于效力规范[5]。其后,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奚晓明在2007年5月的全国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上也提出了上述的标准[6]。这就为在司法实践中如何判断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合同效力提供了基本的标准,从而使这种将民事有效性与违法性判断适当分离的做法有了实践上的可操作性。
回到文章开头的案例。首先,虽然被告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违反了《商业银行法》和《刑法》的规定。但是《刑法》及行政前置性法规《商业银行法》仅仅规定了非法吸收存款行为的刑事和行政责任,没有对其下的借贷合同的民事效力予以否定;其次,使合同有效并不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只是涉及当事人继续履约,相较于认定无效更有力于保护善意合同相对人(民间出借人)的利益。故应该将《商业银行法》和《刑法》的相关规定认定为管理性强制性规定。
其实从这里可以看出将其认定为管理性强制性规定,并不是一种先验性的判断,而是结合具体案情、综合法益保护和立法目的,进行的实质性判断,同时这也并不会影响刑法打击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的法律效果。
首先,从法益保护的角度考虑,认定吸收公众存款罪下的合同有效,更有利于保护善意的合同相对人。因为一旦认定合同无效,根据合同无效的后果,出借人只能被返还财产,应此受到的利息损失只能由有过错的一方得以赔偿。也就是说认定合同无效,出借人一般只能得到返还的本金和银行同期同类贷款的利率确定的利息。这就使得借款人可能因为被认定为犯罪反而获利,这明显有违公平。更为关键的是,借款人在此情况下一般资不抵债,很少有能力偿付本金和利息,而如果认定借款合同无效,作为从合同的担保合同亦无效,这就使得出借人无法通过担保人获得自己债权的实现,即使担保人有过错,根据《担保法》,其承担的份额也不会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三分之一。这使得出借人的债权往往因为借款人受刑事追诉反而得不到实现,不利于法律对他们的保护。也使得这种情况下的担保毫无意义,其保障交易安全的功能被消解于无形。而且认定合同有效,也不会使得出借人得到不合理的高额利益,根据有关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超出此限度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综上,认定合同更有利于对民间出借人合法利益的保护。
其次,认定合同有效也更符合《商业银行法》和《刑法》规制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的立法目的。规制此行为本就是出于国家管理、维护金融秩序的需要,而此需要从根本目的上来说,是为了控制民间借贷的风险,保护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民间出借人的利益,这才是此强制性规定真正的立法目的,如果以牺牲民间出借人的利益来打击此类犯罪,有本末倒置之嫌。
最后,认定合同有效,并不会影响刑法的适用效果。一方面,认定民事借贷合同有效并不影响当事人承担刑事法律责任。而在判断合同效力上的利益权衡,也并不会影响将罪刑法定原则作为基本原则的刑法的尊严,因为这只是涉及合同效力的判断。刑法和民法本就有各自调整的领域,对合同效力的判断属于民事法律规范调整的范围,因此判断的标准也应该根据民事法律规范的规定,结合具体案情进行利益权衡,最终做出判断。另一方面,如上所述,认定合同有效,将使被告人承担起本该承担的债务,在一定程度上更有利于打击此类犯罪,而认定合同无效则反而会使被告人逃避部分责任。
当然,上述情形并非个别特殊情况,除了本文案例外,又如,如果认定企业非法雇用童工的合同已履行部分有效,那么将更有利于保护童工的权益保护,否则如果一律认定为无效,童工无法请求获得未支付的工资,只能基于企业的不当得利获,请求获得一定程度的劳务补偿。这显然并不合理。类似情形在民事领域还有很多。在这种情况下,将合同认定为管理性强制规定并由此认定合同有效,将有效性判断与违法性判断相分离,是有意义的。这同时也体现了民法注重调节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的部门法特点。
三、有瑕疵、未撤销的行政许可的有效性与其出罪功能
与上述民事行为效力的判断相类似,在行政法领域,也存在行为具有违法性但是其在行政法上却是有效的情形。也即违法性判断与有效性判断的分离,在行政法领域,同样存在。本文拟从有瑕疵的行政许可为例,进行阐述。
我国《行政许可法》第69条第2款规定,被许可人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行政许可的,应当予以撤销。这款规定的可撤销的行政许可,事实上指的就是被许可人因为违法或者其他不当的原因而得到的行政许可。比如被许可人通过欺骗或贿赂等手段取得了种植罂粟的许可。这种不正当获取行政许可的行为是具有行政法上的违法性的。《行政许可法》第79条规定,被许可人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行政许可的,行政机关应当依法给予行政处罚。进一步讲,这种行为也完全有可能具有刑事违法性,但在被有权机关撤销前,这样的有瑕疵的行政许可仍是有效的,其行政法上的效果与通过合法手段获得的行政许可是一样的。
而且这种有瑕疵的行政许可,也并不一定会被撤销,与上述合同法将强制性规定进行效力性规定与管理性规定的区分相类似,这里的撤销与否也要进行利益权衡。《行政许可法》第69条第3款规定,依照前两款的规定撤销行政许可,可能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害的,不予撤销。也即,可以为了更大的利益,而维持一个具有违法性的行政许可的效力。这也体现了行政法的立法目的与部门法特点。正如有学者所说,行政法规的目的在于促进行政职能的履行,而行政权具有主动性,价值取向具有效率优先性,因而更注重权力结果的实质性[7]。
这种行政许可的有效性除了并不排除其在行政法上的违法性,更进一步来讲,其在刑法上的本来应该具有的出罪机能也会受到影响。行政有效性并不能当然否定根据这种有瑕疵的行政许可而实施的行为的刑事违法性。我们知道,刑法中的行政犯具有行政附属性,在这些犯罪中,行政许可是比较典型的阻却犯罪的事由。但是上述有瑕疵的行政许可虽然有效,却并不一定能成为出罪理由。
对于这种有瑕疵的行政许可,德国刑法理论的多数意见基于一种“权力滥用”的思想来否定这种有瑕疵许可的出罪功能[8]。而我国有学者提出应该根据控制性许可和特别许可的区分来认定这种有瑕疵的行政许可的出罪功能,如果属于控制性许可,可出罪,属于特别许可,不可出罪。但是如何区分何为控制性许可,何为特别许可,事实上也没有一个事前的明确区分。这正如上述效力性规定与管理性规定的区分一样,需要结合具体案情、综合法益保护和立法目的,进行实质性判断。在这里也即需要根据刑事法律规范和其法益保护目的来进行独立的判断。如果根据有瑕疵的行政许可做出的行为除了违反行政管理的秩序外,本身侵害了刑法保护的其它具体法益或具有侵害的危险,则行政许可属于特别许可,在这里不具有出罪功能。比如上述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得种植罂粟许可的行为人,仍构成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罪,因为大量种植罂粟本身就具有危害公民健康的危险,侵害了除管理秩序外刑法保护的法益。而这就充分体现了行政有效性并不必然排斥犯罪的成立。
四、法秩序的统一性与刑法的独立判断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民事、行政有效性与违法性判断一定程度上的分离,一方面,维护了法秩序的统一性——即具有一个“一般违法性”的存在;另一方面,它又反映了各个部门法在利益权衡和对立法目的考虑的基础上,进行的对各自法律效果的相对独立的判断。前者体现了各部门法在价值评价上的一致性,后者体现了各部门法调整手段、对象及利益导向的不同。
上述法秩序的统一性即是指,不同法领域之间的规范不应发生矛盾,即一个行为不能在一个法领域合法而在另外一个法领域则违法[9]。这就要求在法秩序中对违法性应该作统一的理解,无论是宪法、民法、行政法还是刑法,在违法性的判断上不应该存在矛盾和冲突,存在“一般违法性”的价值判断打通各部门法。这为大陆法系法学理论所坚持,同时也具有应然层面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因为对同一行为的“合法或是违法”的价值判断,如果不同部门法之间存在不一致,那么会使身处其中的人们无所适从,不知以何为标准,不知如何行为才适法。各个部门法的调整对象可以不同,对同一行为调整的法律效果也可不同,但是在对行为的价值判断上不应该出现冲突,这是法秩序保持协调、共同维护社会秩序的前提。
而坚持法秩序的统一性,在刑法上具有更进一步的意义。由于刑法制裁手段的严厉性决定了其在法律体系中的保障法地位,也即通过其他部门法的手段即能达到规制目的的,就不需要动用刑罚这一最后的手段,这也是刑法谦抑精神的内涵。也就是说,某个行为要成为犯罪,首先要在法律上一般规范性地评价为违法,其次需要在刑法上进一步判断为可罚的[10]。如果某一个行为在民法或行政法上是合法的,那么其也不可能被认定为犯罪。
不过,虽然对一个行为“适法与否”的价值评价方向应该是一致的,但是各部门法调整行为的法律效果是不一样的。违法性和有效性不是同一个问题。各个部门法的目的与评价的具体侧面不同,造成了司法实践中具体适用不同部门法时,需要基于各自的规范进行相对独立的判断。即使是作为保障法地位的刑法,在具体判断构成犯罪与否时,也仍然需要进行相对独立的判断:同样具有一般违法性,民法、行政法可能通过利益的权衡将其例外地认定为有效,但这并不妨碍刑法在这“一般违法性”的基础上,将符合犯罪构成的行为予以定罪。也就是民法、行政法有效性并不能必然排斥一行为在刑法上构成犯罪,构成犯罪也并不意味着相关行为在民法、行政法上的一定是无效的。
对刑事违法性应该根据刑事法律规范进行独立的判断。原因如下:
首先,民事、行政有效与否的认定无法为刑事违法性的判断提供参照。虽然有效与否在民法、行政法上是一个明确的法律效果,分别由法院民事判决和相关行政机关根据法律规范并且进行利益权衡予以确定,但是它却不能成为刑法判断违法性的前置性步骤。一方面,这是因为刑法不同于民法和行政法,其最重要的原则是罪刑法定,其具有保护法益和保障人权的双重功能。这些部门法特点决定了其更加注重对形式的坚守,从而在适用中的利益权衡受到更为严格的限制。民法、行政法对一违法行为可以基于利益权衡认定为有效,而刑法却不能由此而放弃对犯罪行为的规制。另一方面,民事、行政有效性本身就是依赖于违法性的判断而做出的一种“二次性判断”,如果将民事、行政上的效力判断作为刑法判断违法性的依据,那么将存在循环判断的怪圈,在实践中也会出现因为刑事案件受理和民事、行政案件受理顺序的不同而得出完全不同结论的可能,这是令人无法接受的。
其次,刑事违法性的判断也不能依赖于对民事违法性与行政违法性的判断,不能将前者作为后者的前置性程序。虽然由于“一般违法性”的存在以及刑法的保障法地位,这在应然的价值层面是可以成立的,但是这种“二次性判断”更多的是体现在立法阶段,即刑法在立法时只能将具有严重危害法益的民事违法、行政违法行为规定为犯罪。但在司法实践中,却并不能将民事违法性与行政违法性判断作为刑法违法性判断的前置性程序。原因不单在于刑事规范具有一些不同与其他法规的概念(比如民法上的“占有”与刑法上的“占有”即使用语相同,内涵也不同),更为重要的是根据刑事法律规范进行违法性判断时,其实已经内化了这种民事违法性、行政违法性的判断,并不需要进行单独的民事、行政认定。比如关于行政犯的认定,我国刑法主要采用了空白罪状的形式,如“违反……法规”、“违反……管理法规”。这就意味着根据刑事法律规范进行违法性判断时,本身就需要进行行政违法性的判断,而无需单独的行政认定。而行为的民事违法性比如侵权性质,也已内涵在刑法法条的罪状描述中,并不需要再进行单独的民事违法性的判断。事实上其也很难成为刑事违法性判断的前置性依据。正如有学者提出,民法中的违法性概念及地位本身就存在争议,违法性判断弱化,模糊不清。民法违法性判断暧昧不清使其难以为刑法所参照,因为刑法的违法性判断丝毫不能含糊[11]。综上,即使在刑法仅仅是以其刑罚对其他法律给予支持时,规定宣告与适用制裁之条件的,仍然是刑法,并且只有刑法唯一决定这些条件[12]。所以刑事违法性判断仍然应该由法院根据刑事法律规范、结合法益保护的目的进行独立的判断,正如上述判断有瑕疵的行政许可的出罪功能那样。
最后,刑法判断的独立性除了由于实体上刑事违法性判断已内含民事违法性与行政违法性判断外,还存在程序上的原因。比如,行政认定如果作为行政犯认定的前置程序,不但影响了法官对于案件的整体的判断,排除了被告对部分证据的质证可能性,而且行政机关由于与司法机关的价值导向不同,更注重效率,也会导致对被告权益的保护不周,从而影响司法公正。行政认定不是判断刑事违法性的前置程序也得到了司法解释的肯定。今年3月两高一部颁布的《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条就指出了行政部门对于非法集资的性质认定,不是非法集资刑事案件进入刑事诉讼程序的必经程序,行政认定只具有参考意义。
回到本文开头的案例,判断行为人是否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应该根据刑法的相关规定进行独立判断,而不能以民间借贷合同及担保合同的效力来否定行为的违法性。在认定行为人构成犯罪后,也并不能因此一律否定民间借贷合同及担保合同的效力。民事、行政法有效性与犯罪的成立并不完全排斥。
总之,根据刑事法律规范、结合刑法保护法益的目的对刑事违法性进行相对独立的判断,并不意味着民事违法性与行政违法性判断的缺位,刑法的独立判断与法秩序的统一性并不矛盾,不违背其在法律体系中的保障法地位。在坚持法秩序的统一性的原则下,民事、行政有效性与违法性判断一定程度上的分离,也体现了各部门法具体适用时的不同利益导向及其利益权衡本质。
[参考文献]:
[1]崔永峰,李 红.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中民间借贷合同效力之认定[J].中国检察官,2012,(1):55.
[2]耿 林.强制规范与合同效力[M].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9:28.
[3]史尚宽.民法总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330.
[4]王泽鉴.民法总则[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225.
[5]王利明.合同法新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321-322.
[6]奚晓明.当前民商事审判中的几个法律适用问题[J].人民司法,2007,(13):6-10.
[7]孙笑侠.司法权的本质是判断权—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十大区别[J].法学,1998,(8):34.
[8]Wessels/Hettinger,Strafrecht BT1,2003,Rn.1061;Lackner/Kuehl,Strafgesetzbuch,2001,§324,Rn.转引自:车浩.行政许可的出罪功能[J].人民检察,2008,(15):13.
[9][日]曾根威彦.违法的统一性与相对性[M].成文堂,1996:121.转引自郑泽善.法秩序的统一性与违法的相对性[J].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11,(7):60.
[10][日]大塚仁.犯罪论的基本问题[M]。冯军,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121.
[11]王 骏.违法性判断必须一元吗?—以刑民实体关系为视角[J].法学家,2013,(5):135-139.
[12][法]卡斯东·斯特法尼,等.法国刑法总论精义[M].罗结珍,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39.转引自刘伟.经济刑法规范适用的独立性判断问题[J].刑法论丛,2013,(2):45.
On the Separation of Illegality Judgment and Validity Judgment in Civil Law and Administrative Law
CHEN Yu-he
An illegal behavior is usually invalid in civil law and administrative law.In another word,an illegal behavior can not have validity.But sometimes it is better to protect benefits and realize the legislative purpose when we confirm that the behavior is valid.So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effect mandatory provisions and the management mandatory provisions is appear in the civil law,which means,to some extent,the separation of illegality judgment and validity judgment.And it is also manifested in the administrative law. This separation reflects the unity of law order,and reflects the different Interest guides of different department laws and their nature of benefits balancing.And it determines the judgments of different department laws are relatively independent,including criminal law,which is called law of guarantees in the legal system.The existence of"general illegality"does not conflict with of the independence of the criminal law’s judgment.This separation also contributes to the situation that validity in civil law or administrative law does not completely exclude the crime.
Validity;Illegality;Effect Mandatory Provision;Unity of Law Order;Independent Judgment
DF0
A
1674-5612(2014)05-0123-07
(责任编辑:禹竹蕊)
2014-06-03
陈雨禾,(1990- ),女,浙江宁波人,华东政法大学刑法学硕士生,研究方向:刑法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