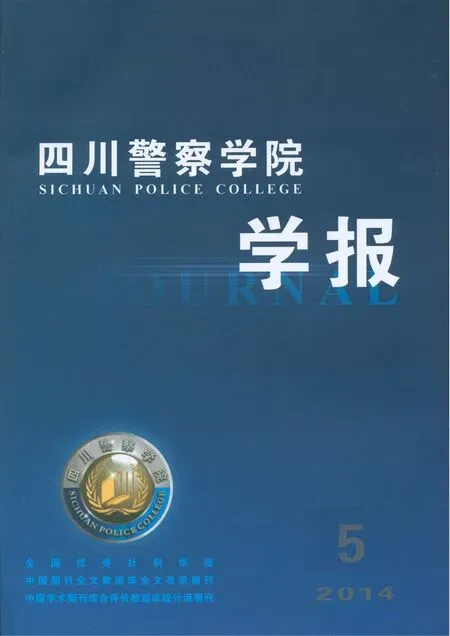论刑法对网络造谣行为的规制
——以对“公共秩序”法益的理解为切入点
2014-04-09侯帅
侯帅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 100875)
论刑法对网络造谣行为的规制
——以对“公共秩序”法益的理解为切入点
侯帅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 100875)
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使得虚假信息的传播速度加快,影响范围急剧扩大,特别是一些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网络造谣行为,具有相当程度的社会危害性。《刑法》对这类网络造谣行为的规制,应当充分运用法益分析的方法,对侵犯不同类型法益的网络造谣行为对症下药。与其冒违背罪刑法定基本原则的风险,而用寻衅滋事罪来规制网络造谣行为,不如利用其他更有针对性的罪名。对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进行扩大解释或者立法将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的犯罪对象进行扩张都不失为一种更符合刑法基本原则的方法。
网络造谣;司法解释;寻衅滋事罪
网络是现代社会中最能诠释“双刃剑”含义的科技产物。网络给刑法带来的最大难题,除了传统犯罪同网络手段相结合而产生更强的隐蔽性与破坏力,更表现为法益保护因网络而变得复杂:一方面,网络产生了一些前所未有的新生法益,需要刑法及时严密法网去加以保护。比如《刑法修正案(七)》增加了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和提供用于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的程序、工具罪,加强了对计算机信息系统运行安全的保护。另一方面,因为网络对现实生活的深刻影响,使得刑法对诸如财产、人格和社会秩序等传统法益的保护也变得更加复杂。以虚拟货币“比特币”为例,从网络的虚拟性来看,网络空间中的货币与现实生活中的货币有很大不同:比特币不依靠特定货币机构发行,它依据特定算法,通过大量的计算产生;而从网络与现实社会之间相互影响日趋加剧层面来看,虚拟货币可以通过交易、兑换,而具有一定的现实价值,体现出与现实货币相类似的某些属性。刑法如何在虚、实两层空间中游刃有余地保护法益,是刑法学界应当关心的问题。另外,应当重视法益分析方法在对网络犯罪立法、司法过程中的重要的作用。在对网络违法行为的规制中,一定要区分下列两种不同情况:如果是网络发展中新生的法益,以往刑法规范无力调整,则需考虑设立新的规范来严密法网;如果网络只是作为传统犯罪的工具,而侵犯的实际上是传统法益,则应当通过对刑法的解释和灵活运用而解决难题。
一、网络空间中的“公共秩序”法益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13年9月5日通过了《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简称为《解释》)。该解释对规范人们的网络行为,避免利用网络实施诽谤等犯罪行为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关于该司法解释的争议久未平息,特别是《解释》第5条第2款 的规定,引起了学界争鸣,其中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对寻衅滋事罪中“公共场所秩序”概念的理解,是否能扩大解释为包括“网络虚拟空间”在内?
关于这个问题,大致可分为肯定司法解释说和否定司法解释说两种观点。肯定司法解释的一方认为,《刑法》第293条第(四)项规定,“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的构成寻衅滋事罪”中的“公共秩序”包括网络虚拟空间的秩序。尽管第293条第(四)项规定是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混乱,但该条前面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扰乱“社会秩序的”,这里的扰乱社会秩序是一个抽象的评价概念,因此在网络信息空间发布虚假信息,即使没有造成公共场所混乱,但是造成了社会秩序严重混乱,或者说公共秩序严重混乱,因此司法解释的规定依然是《刑法》第293条所能够包含的[1]。
多数学者指出了《解释》在理论上的问题。有学者指出,《解释》将公共场所秩序换成了公共秩序。从概念外延上说,公共场所秩序是公共秩序的一部分,将“公共场所秩序”扩展为“公共秩序”,虽然对于实践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仍不免有“以解释之名,行立法之实”的嫌疑[2]。有学者阐述到:“网络空间”概念属于现实社会的“公共场所”尚能理解,“网络公共秩序”也应当和“现实公共秩序”一样受到保护,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寻衅滋事罪惩罚的应该是造成网络全间中的“秩序混乱”的行为,还是造成现实社会的“公共秩序”混乱的行为?什么情况下才能评价为造成了网络空间中公共秩序的混乱?这恰恰是《网络诽诱解释》模糊之处[3]。还有学者认为,“将公共场所提升为公共空间,将公共场所秩序提升为公共秩序。如同将刑法条文中规定的“妇女”提升为“人”的概念一样,属于典型的类推解释”[4]。
要得出上述争议问题的合理结论,首先当明晰社会秩序、公共秩序和公共场所秩序这四个相关概念的含义。“公共秩序”在词典中被解释为:“大家应共同遵守的社会秩序”[5]。“公共秩序”出现在我国《刑法》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第一节的类罪“扰乱公共秩序罪”中,以及一些个罪的具体罪状里,比如,第298条破坏集会、游行、示威罪规定,扰乱、冲击或者以其他方法破坏依法举行的集会、游行、示威,造成公共秩序混乱的……。“社会秩序”概念则出现在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聚众斗殴罪和寻衅滋事罪等个罪罪状中。《刑法》第290条规定:聚众扰乱社会秩序,情节严重,致使工作、生产、营业和数学、科研无法进行,造成严重损失的,对首要分子,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对积极参加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剥夺政治权利。第292条规定,在公共场所和交通要道聚众斗殴的,造成社会秩序严重混乱的……;第293条规定,有下列寻衅滋事行为之一,破坏社会秩序的……。“公共场所秩序”出现在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和寻衅滋事罪的规定中。
从“社会秩序”、“公共秩序”和“公共场所秩序”三个词语在刑法中具体运用情况可以得出:前两者的区别不大,更偏向一种广义上的概念。正如有学者认为,公共秩序是指社会公共生活依据共同生活规则而有条不紊进行的状态,既包括公共场所的秩序,也包括非公共场所人们遵守公共生活规则所形成的秩序[6]。笔者认为,公共秩序是社会作为一个整体,人们在其间正常生活、工作或者从事科教等活动的一种状态。而破坏这种秩序的表现是,人们不能正常地在通常的时间和地点从事上述活动。而“公共场所秩序”具有其含义上的特殊性,从刑法设置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在客体和法定刑等方面的区别可以看出,后者保护的是“车站、码头、民用航空站、公园、影剧院、展览会、运动场或者其他公共场所”的秩序。后罪还设置了比前罪更高的起刑点。立法者之所以将本可以归入“公共秩序”的“公共场所秩序”单独列出进行特殊保护,正是看到了“公共场所秩序”的特殊性(可能这些场所可能聚集更多公众,因此对其秩序的破坏行为可能具有更大危害性),因此,面对出现在寻衅滋事罪罪状中的“公共场所秩序”,以刑法条文整体为基础,兼顾体系性不失为一种稳妥的解释方法。
从法律文本应当对社会发展有一定的灵活性和适应性的立场来看,即使将“公共秩序”勉强解释为包括虚拟网络空间秩序,“公共场所秩序”也不能通过扩大解释容纳“信息网络空间秩序”这个概念。寻衅滋事罪的刑法条文用的是“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这样的表述方法,而《解释》将原来的“公共场所秩序”转换成了“公共秩序”,这明显有悖于《刑法》原文的精神。并且,上文已经论述了刑法中“公共场所秩序”有别于“公共秩序”的特殊性,这样随意置换,就连类推解释都不能解释这种解释方法了。
网络空间当然也有“秩序”的概念,比如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罪、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等以计算机、信息网络为犯罪对象的犯罪,就可以看做是刑法对网络空间的“秩序”的维护,这种“秩序”是计算机信息系统和网络正常运行一种理想状态。这个“秩序”的概念显然和《刑法》第293条中包含的“公共场所秩序”不同。前者是虚拟空间的秩序,后者是现实空间的秩序,后者中“场所”这样的用词,明显是为了强调有体性。
二、用寻衅滋事罪规制虚拟空间中扰乱公共秩序行为之驳论
司法解释通常针对司法实践的迫切需要而制定。现实中最需要刑法加以规制的网络造谣行为是那些在网络信息空间中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的行为,进而引发现实社会秩序混乱的情形(因造谣行为引起虚拟空间本身秩序混乱的情形几乎没有)。而刑法中与此相关的罪名只有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该罪对象是“虚假恐怖信息”,外延十分有限。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网络造谣行为确有刑法规制的必要性,但是否应以寻衅滋事罪加以规制,则有待商榷。立法者和司法者都应当在刑法灵活性和明确性中寻找更好的平衡点。
对寻衅滋事罪的争议和批评由来已久,其在立法上缺乏正当性、合理性,在司法上缺乏可操作性。这个罪名因为各种弊端被形象的称为“口袋罪”而遭到很多学者的批判。有学者就提出,“该罪的设立缺乏立法上的必要性和正当性,其犯罪构成要件并不具有独特性,在司法实务中也缺乏可操作性,应当予以废除”[7]。有的学者指出,寻衅滋事罪的司法困境表征为三个方面:第一,客观归罪化倾向太强;第二,主观目的和动机是判断寻衅滋事罪成立的构成要件要素之一,但判断主观目的和动机在司法实践中比较困难。第三,寻衅滋事罪罪状中具有很多情节要求,表述过于模糊,缺乏可操作性[8]。有的学者认为,寻衅滋事罪旨在保护公共秩序或社会秩序,而公共秩序与社会秩序这两个概念都是高度抽象化的,法益的抽象化必然带来对犯罪构成要件的解释缺乏实质层面的限制,从而使构成要件丧失本来的功能,无法应对复杂的司法实践[9]。还有论者以司法实践的视角,指出了该罪适用中的问题:寻衅滋事罪之所以频繁适用,原因在于:一方面,一些常发的违法行为为司法办案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办案素材,公安机关也特别愿意处理暴力类的案件,而不论暴力是否严重。另一方面,这类寻衅滋事案件的取证难度小,而涉案人数多,在讲求案件数量与人员数量的考核机制下,就深受办案机关的青睐[10]。
笔者认为,不宜用寻衅滋事罪来规制在网络上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行为的主要原因有三个方面。(1)寻衅滋事罪本身在立法和司法上存在很多问题。最大的问题在于:犯罪构成应当是对现实中各种犯罪行为类型化而得出的理论抽象结论。而像寻衅滋事罪这样的“口袋罪”,其犯罪构成就不能称之为“类型化”的产物。一方面,条文所规定的各种寻衅滋事罪的行为方式并非一“类”,有对侵害公民人身法益的行为,有侵害财产法益的行为,虽然被归纳进“社会秩序”法益中,但社会秩序的概念过于抽象,甚至所有的犯罪所侵犯的法益都可以归入这一概念中去,因此对司法实践几乎没有指导作用;另一方面,该罪的犯罪成立条件带有“情节恶劣”、“情节严重”这样的表述,因此,犯罪构成对犯罪行为“型”的描述也不甚清晰。“口袋罪”对罪刑法定基本原则最大的威胁来源于:对具有一定社会危害性(特别是扰乱社会秩序)的违法行为,本可以用行政法规进行处罚,但因为刑法规定缺乏明确性而处于罪与非罪“灰色地带”上,这就为该类违法行为方便入罪提供了“绿色通道”。(2)正如上文所述,网络虚拟空间是否能解释进寻衅滋事罪中“公共场所”的范畴有待商榷。在网络中编造、传播虚假信息的行为实质是一种言论,这种言论可能直接造成对网络参与者(也是虚假信息接收者)思想的扰乱,这种扰乱是否达到了我国刑法应当加以规制的严重程度(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是否达到了“一定程度的社会危害”)。(3)网络中编造、传播虚假信息的行为确实可能越出虚拟空间而间接导致现实社会秩序的混乱,然而这种间接因果关系中参杂了太多的介入因素,通常是一个连锁反应。而以刑法来惩罚距离“结果”太远的“原因”的合理性有待商榷。
一些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网络谣言行为,看似刑法中没有可以对其进行规制的罪名。这类行为是否可以用寻衅滋事罪进行规制呢?在网络空间中编造、故意传播以地震等灾害或者恶性犯罪的犯罪分子流窜至某地为内容的虚假信息都可能引发社会秩序混乱的严重后果。下文通过对网络谣言合理分类,进而论证对不同类型网络谣言行为应当采用不同的刑法规制手段。对“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中”“虚假恐怖信息”进行合理扩张,可以实现对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网络谣言行为的刑法规制。寻衅滋事罪本身弊端重重,不适宜担当此,刑法通过其他途径规制网络造谣行为,同样可以达到保护法益的目的。
三、用其他相关罪名规制虚拟空间中扰乱公共秩序行为之立论
根据对侵害法益性质的不同,网络中的虚假信息大致可分为几类:其一,诽谤、侮辱个人的虚假信息;其二,贬损公司企业的虚假信息;其三,贬损政府机关;其四,扰乱社会秩序的虚假信息。编造和在网络中故意传播侮辱、诽谤个人的虚假信息,构成犯罪的,可以诽谤罪和侮辱罪进行惩处,这种情形下,网络充当了传统的侮辱、诽谤罪新的犯罪“工具”,因此犯罪行为性质并未发生实质变化。贬损公司、企业的虚假信息,可能构成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罪,因此可以说,也有相关的刑法规范加以规制。而贬损政府机关的虚假信息的情况比较特殊,一方面,政府机关并不具有同个人那样的人格权与名誉权;另一方面,虽然这类虚假信息可能间接引起扰乱社会秩序的严重后果,但因为和公民监督权和知情权紧密相关,建议法律在规制该类违法行为时,要更加谨慎。
编造、故意传播网络虚假信息,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行为,又可以分为几种情况。刑法应当根据不同情况,做出相应的处理。其一,如果编造并在网络中传播虚假信息,并具有教唆他人实施扰乱公共秩序类罪的,可以根据具体情况,按照扰乱公共秩序罪中相应个罪进行处罚。例如,甲编造并在当地网络论坛传播关于当地法院裁判不公的虚假消息,并煽动群众冲击该法院聚集并造成严重损失的行为,可以认定甲是聚众冲击国家机关行为的教唆犯进行惩处;如若甲不但实施了上述编造、散布虚假信息的行为,还直接参与了对聚众冲击行为的组织、策划和指挥,或者积极参加,也可以直接依照聚众冲击国家机关罪进行定罪处罚。而只实施网络造谣行为,没有上述教唆和直接参加行为的,依照现关的行政法规 处罚即可。其二,可以考虑将编造、故意传播恐怖信息罪的犯罪对象进行扩充。具体来说,扩充该罪的犯罪对象又有两种途径。一种是对“恐怖虚假信息”进行扩大解释;另一种是直接将该罪的犯罪对象修改为“可能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虚假信息”。
事实上,司法解释早就开始了对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犯罪对象的扩大解释。该罪罪状对犯罪对象的表述为:“爆炸威胁、生化威胁、放射威胁等恐怖信息”,其中的“等”就为扩大解释预留了空间。2003年5月14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妨害预防、控制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就将“与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有关的虚假恐怖信息”解释为“虚假恐怖信息”的一种 。2013年9月16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条将“虚假恐怖信息”界定为:“以发生爆炸威胁、生化威胁、放射威胁、劫持航空器威胁、重大灾情、重大疫情等严重威胁公共安全的事件为内容,可能引起社会恐慌或者公共安全危机的不真实信息。”这实际也是对虚假恐怖信息概念作了扩大解释。认定“虚假恐怖信息”,关键在于对“恐怖性”的界定。恐怖性是指该信息的内容能够引起公众心理的恐惧,这种恐惧具有一定的广度和程度上的要求:广度是指,可能引起的是社会中一定数量的民众的恐惧心理,而不是特定的个人和有限的群体;程度是指,这种恐惧感并不是一时的担心和忧虑,而是足以影响人们正常生活、工作秩序的恐慌心理。因此,能引起公众心理恐惧,并潜藏严重扰乱社会秩序危险的信息,一般都和公众的生命、健康法益紧密相关。另外,“虚假恐怖信息”还必须是可能引起的恐慌的程度和范围要和爆炸威胁、生化威胁和放射威胁三类恐怖信息相似,至少不能明显弱于这三类信息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笔者认为,虚假的传染病疫情、虚假的地震信息都可以列入虚假恐怖信息的范畴。而以严重犯罪的犯罪分子脱逃或流窜为内容的虚假信息,因为可能引起的公众恐慌情绪的范围和程度有限,和爆炸、生化和放射威胁、地震等灾害、疫情的影响不可同日而语,宜以行政法规进行处罚。
如果这种对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的扩大解释仍然满足不了对网路造谣进而严重扰乱社会秩序行为规制的需要,还可以考虑将“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修改为“编造、故意传播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虚假信息罪”。但对修改后罪名的犯罪对象要进行严格限制。甚至可以考虑在立法或者司法解释中直接列举出不能包含在上述概念下的信息类型。比如,对政府工作进行质疑和监督的信息,即使其依据的事实基础可能有瑕疵,也不能将其作为可能:“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虚假信息”。
如上所述,通过对发生在网络空间的不同类型编造、散布虚假信息行为进行分析,可以看出:针对网络虚假信息所侵犯具体法益的不同,分流适用诸如侮辱罪、诽谤罪、损害商业信誉罪和聚众扰乱公共秩序罪等个罪,或者通过立法修改来扩充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的犯罪对象,都可以达到规制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网络造谣行为。对寻衅滋事罪的“变通适用”看似简单,却潜藏巨大的刑法基本原则方面的危机。还应当明确的一点是:针对网络谣言的治理,对公众进行基本知识的普及,政府工作信息的及时公开与政府公信力的培养等社会综合治理手段恐怕要比过度依赖刑法力量要有效得多。
[注释]:
①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条第2款规定:“编造虚假信息,或者明知是编造的虚假信息,在信息网络上散布,或者组织、指使人员在信息网络上散布,起哄闹事,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的,依照刑法第293条第1款第(四)项的规定,以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
②《刑法》第291条规定,聚众扰乱车站、码头、民用航空站、公园、影剧院、展览会、运动场或者其他公共场所秩序……;第293条: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
③ 《德州男子散布虚假信息被拘5天 “越狱犯”纯属谣言》,载http://news.iqilu.com/shandong/yuanchuang/2013/ 0829/1648231.shtml,2014年6月10日访问。
④《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5条规定:第二十五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5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500元以下罚款:(一)散布谣言,谎报险情、疫情、警情或者以其他方法故意扰乱公共秩序的;(二)投放虚假的爆炸性、毒害性、放射性、腐蚀性物质或者传染病病原体等危险物质扰乱公共秩序的;(三)扬言实施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扰乱公共秩序的。
⑤《关于办理妨害预防、控制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1条第1款:编造与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有关的恐怖信息,或者明知是编造的此类恐怖信息而故意传播,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九十一条之一的规定,以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定罪处罚。
[1]曲新久.刑法解释的若干问题[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4,(1):163-164.
[2]孙万怀,卢恒飞.刑法应当理性应对网络谣言——对网络造谣司法解释的实证评估[J].法学,2013,(11):14.
[3]于志刚.“双层社会”中传统刑法的适用空间——以“两高”《网络诽谤解释》的发布为背景[J].法学,2013,(10):104.
[4]张明楷.简评近年来的刑事司法解释[J].清华法学,2014,(1):17.
[5]阮智富,郭忠新.现代汉语大词典.上册[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403.
[6]高铭暄.新编中国刑法学(下册)[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板社,1998:808.
[7]王良顺.寻衅滋事罪废止论[J].法商研究,2005,(4):111.
[8]张 维,黄佳宇.寻衅滋事罪司法困境之评析[J].法学杂志,2011,(5):95.
[9]张明楷.寻衅滋事罪探究(上篇)[J].政治与法律,2008,(1):92.
[10]樊华中.寻衅滋事罪规范内的追问与规范外的反思——以随意殴打型切入分析[J].中国刑事法杂志,2011,(8):58.
On the Criminal legislations about Fabricating and Spreading False Message in Network
HOU Shuai
With the improving of network science and technology,the false message spreads fast;its influence scope expands dramatically.Especially it seriously disturbs the social order and lead serious social chaos.The method of legal interest analysis must be used sufficiently in criminal legislation about fabricating and spreading false message in cyber space.We should use different accusations to protect different legal interests.However,the crime of creating disturbances is not the best choice in controlling the crime about network false message,because the accusation itself contains the potential danger of destroying the basic principle of legality.
False Message;Judicial Interpretation;Creating Disturbance
DF6
A
1674-5612(2014)05-0101-06
(责任编辑:李宗侯)
2014-09-23
侯 帅,(1988- ),女,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2012级博士生,研究方向:刑法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