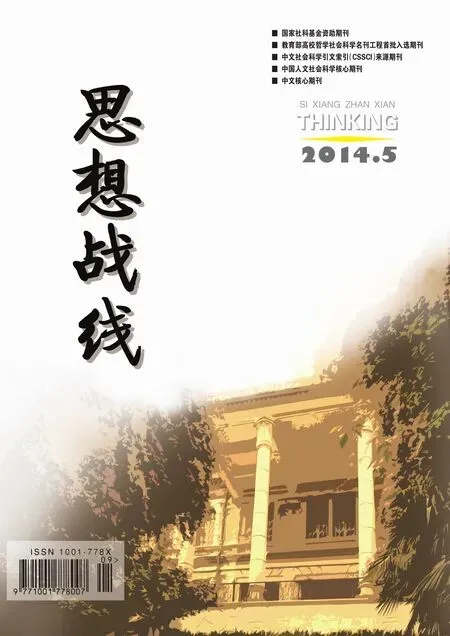零符号理论:少数民族研究中的新维度
2014-04-09聂丽君
聂丽君,李 兵
一切符号皆有零符号的性质,不存在的“零”正是零符号的所在,而任何符号要有意义必须脱离自身而存在。零符号广泛存在于符号系统里,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本文将零符号理论与少数民族研究相结合,拟作一次符号学理论与民族学田野的嫁接尝试。
一、零符号界说
在西方,零符号在自然科学中的研究和使用要早于符号学的研究。零符号(zero sign)与数学的“0”有很深的渊源,表示“空空如也”或“空洞无物”。卡普兰认为,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古巴比伦人发明了表示“这一列什么也没有”的符号形式:两个倾斜的楔形文字,表示位置上的“零”。[注][美]罗伯特·卡普兰:《零的历史》,冯振杰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5年,第10页。零符号一词最早出现在语言学中,1939年,雅柯布森(Roman Jakobson)用零符号来表示词格形式中的零词尾现象。[注]参见[美]罗曼·雅柯布森 《雅柯布森文集》,钱 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之后,罗兰·巴尔特(Roland Barthes)在《符号学原理》中把能指欠缺但本身起能指作用的符号称为零记号,但他没有对零记号的意义和作用展开系统讨论。[注]参见[法]罗兰·巴尔特《符号学原理》,李幼蒸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符号学家诺特曼认为,数字0是典型的零符号,并详细讨论了数字0对数学物理、焦点对艺术、纸币对经济的关键性影响,指出现代性完全依赖于零符号。[注]参见Brian Rotman, Signifying Nothing: The Semiotics of Zero,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对于接受美学、解构主义而言,零符号是其理论的逻辑起点。随着文化研究的兴起和对空间、货币、符号交换等领域的探索与拓展,符号学家对零符号也多有借重,使得零符号的研究更加深入。零符号的研究可分为三个阶段: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在前现代,即零符号传入之前,零符号曾引起希腊人的恐惧和不安,亚里士多德拒绝使用零符号。一直到中世纪时西方人才接受并使用零符号,并引爆了物理学和数学的革命,极大地推动了西方文明的进程。现代时期,对零符号的研究多局限于自然科学领域,进入20世纪,符号学家索绪尔才把人们的视线拉回到人文科学的领域,他在历时语音中分析了“零符号”,并指出对观念的表达不一定需要物质性符号:“物质的符号对表达的观念来说并不是必不可少的;语言可以满足于有无的对立。”[注][瑞士]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126页。这一时期,零符号的研究局限于语言学领域。在后现代时期,自然科学领域出现了一些零符号的研究,如席夫对零符号在科学、哲学和宗教中的作用进行了概要性阐述;[注]参见[美]查尔斯·席夫《零的故事:动摇哲学、科学、数学及宗教的概念》,吴蔓玲译,台北:商周出版社,2001年。哈佛大学卡普兰教授对零的历史的描述虽和席夫的著作多有重复,但对零符号的隐喻和象征意义的分析却独树一帜。[注]参见Robert Kaplan, The Nothing That is: A Natural History of Zero, Oxford,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2000.
在中国,零符号的使用和研究比西方更为久远,如《易经》中太极的思想,老庄哲学对有无关系的探讨等等。“零”字的本义专指下雨(许慎《说文解字》),直到元朝,数字“0”传入中国,才把“零”与“0”相对应,但“零”字的运用比数字“0”更灵活、广泛,这也是本文取“零符号”这一称谓的原因。王希杰教授第一次从符号学的角度提出了“空符号”的概念,[注]参见王希杰《说话的情理法》,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倪梁康教授从现象学的角度分析了零符号与形而上学的关系,认为形而上学的本质就是零,[注]参见倪梁康《零与形而上学——从数学、佛学、道学到现象学的有无之思》,《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周宪教授关于两种视觉范式的讨论为我们揭示了零符号在现代和后现代的命运。[注]参见周 宪《视觉文化的转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此外,赵毅衡教授对符号的分类与潜在符号及其意义的论述,[注]参见赵毅衡《符号学:原理与推演》,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韦世林教授对空符号在口语、书面语和建筑中之广泛运用的探讨,[注]参见韦世林《空符号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都对零符号的研究具有启示意义。
从零符号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看,黑格尔强调主体性与现代性自我确证的关系,马克斯·韦伯认为现代性始于合理化,并导致了价值领域的分化,这些理论都和启蒙运动、宏大叙事相关。但符号学家诺特曼、列斐伏尔、齐美尔等人却另辟蹊径,从零符号的角度分析现代性和零符号的关系。作为零符号的纸币,催生了现代货币经济体系,带给人们极大的自由,同时也占据着现代生活的中心,夷平了一切有差别事物的性质。作为无价值的价值符号,零符号也给人的心理注入了空虚与寂寞,这也是希腊人对零符号充满恐惧的原因。而在后现代性中,赛博空间(Cyberspace,即网络—零符号)正在威胁纸币—零符号这个绝对的中心,人们思考现实的方法趋于多样化,同时也更加虚拟化。
从修辞学的角度看,零符号可以成为一种新颖的辞格,现代主义文学如意识流大量采用标点符号的零形式,从而获得特殊的艺术效果。零符号在文本中可能具有的隐喻、象征或反讽,使其在不同的语场中彰显不同的意义和语力。
从零符号与建筑空间的关系角度看,空间分为三类:第一空间——物理空间;第二空间——心理空间;第三空间——前二者的混合,既是现实的又是想象的。空间—零符号属于第三空间,如园林艺术中的花窗借景。如果把城市看成一个话语,道路、围墙、小区等就是组合段上的语义单位,其中布满了空间—零符号。
从零符号在文学艺术中的运用角度看,文学文本中的空白和艺术文本中的“留白”都是典型的零符号,蕴含着美学的诸多特征。零符号在文学符号系统中易被忽视,却又无可替代,使用的目的不同,意义和价值也不一样。如诗歌中被节省掉的符码就成为了零符号,仍然具有能指作用。在绘画中,透视画法的没影点其实就是零符号,观者必须处于静止状态才能从最佳位置观看,零符号把人的视线拉入一个有深度的空间,没影点是可及的又是不可及的,在有限的范围内表现出无限手法,正是现代性的主要特征,而后现代的绘画则打破了这个有深度的空间,中心透视消失。在书法艺术中,章法又称布白,章法之妙在于字行点画之间相互有笔有势,富于动感和平衡,从符号学的角度看,就是划分空间,在白纸上书写零符号和字形符号,使之各自成美。在解构主义那里,原来作为附饰结构的艺术边框等零符号,成为德里达解构形而上学中心的利器。在拉康的精神分析学说中,零符号是其理论的奠基点。零符号还被运用于罗兰·巴尔特的零度批评中,成为其理论的逻辑起点。所以,艺术之美在于形式,而形式之美跟零符号的运用有关,要么借助零符号使艺术变得有意味,要么利用零符号获得美的结构与布局。零符号的使用,使得艺术与非艺术区别开来,非艺术注重认知,而艺术乐在感知,零符号使得感知的过程延长。
综上所述,对零符号的研究要么局限于科学领域,重点是探讨数字0;要么囿于语言学或哲学领域,而且其定义暗中排除了数字0,不能涵盖文化符号中的大量能指。因此,本文把空符号、数字0以及符号空统称为零符号,从符号学的角度看,所谓零符号,就是以空白、无、空间间隔及数字0等为符号形式,其能指(如文学艺术中的空白、建筑中的空间间隔等)或基本所指(如幽灵、上帝、零余人、数字0等)都是空无,在符号系统中起着重要作用。在汉语中,零符号的能指形式为:零、无、没有、空等;在英文里,零符号的能指形式为“nothing”、“null”、“naught”等。零符号可以是实在的空间及事物,也可以是人造的代码。在哲学领域中,零符号具有“无、不在场、不存在”等意味。零符号作为符号必然具有意义,但其意义指向却是属于形而上学的,我们可以无限靠近这个意义,却永远在路的中途。
二、零符号与田野的知识生产
纵观零符号的历史,其创造和使用与多种思想相连——最初是指没有数字的空位,后来就与生死轮回(印度)、“变量”、随时可以被充满物体的“容器”和“空间”(柏拉图)、上帝、道(中国)、清除异己、重新开始、死亡或终止(玛雅人、美国的印第安人)、中心(结构主义思想)、虚无(存在主义等)密切相关。[注][美]罗伯特·卡普兰:《零的历史》,冯振杰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5年,第50~230页。零符号表示的是“那些不可见的东西”,一种中心事物的隐身。[注][美]罗伯特·卡普兰:《零的历史》,冯振杰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5年,第230页。——科技的日新月异和经济的全球化加速了人类社会演化的进程,人们既摆脱不了传统的惯性,又远不能实现天下大同。文化传统的支配力在现实的发展诱惑面前日渐减退,实际的发展落差又刺激着人们回归族群的身份认同与传统再造。而某一民族的文化传统总是植根或“隐身”于其民族性格、民族精神和地方性知识当中,并贯穿于族人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的日常生活细节之点滴而延续至今,且将继续“存在”[注]参见肖伟胜《从观看到观察:图像意识的存在论阐明》,《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并影响着人们迈向明天。
作为“社会文化人类学家所磨砺出来的学术利器,后来也被民族学界、社会学界、民俗学界广泛采用,并且与从业规模比较大的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结合”的民族志,“既是社会科学的经验研究的一种文本,也是一种方法,即一种所谓的定性研究或‘质的研究’”,[注][美]詹姆斯·克利福德,乔治·E.马库斯:《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高丙中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2页。它是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田野作业后的智力成果及其知识生产的主要形式,往往成为被研究民族(特别是文化欠发达的民族)借以认知自己的新途径和其他学者进行相关研究的借鉴文本。但是,在田野实践中,众多基本的文化事象往往会因为不同场景或不同受访者的讲述而不同,因为研究者的解读和整体谋篇布局而异质。隔离感、间离效果、双方交往的关系渐进、亲疏变化等让观察者的“客观冷静”显得十分有限。同时,当地人对本民族文化、历史、现状的认识也存在差异,当他们被研究者作为“整体”进行观察和研究时,其片面性不容忽视。于是,在文本中给予观察对象更多的话语空间而非“权威概括”成为要务——基于民族志基础的更为开放的文本呈现,不再标榜或刻意强调“真实”且以“把握真理”自居,而是着力维护田野及写作过程中的“真诚”,给予被观察者更多的话语权力和主体性空间;重视叙事和修辞,承认文本的建构会因为解释者本人及其所依赖的价值和假设而生成不可避免的局限性,故得出的结论亦见仁见智;田野及文本的完成是一种成果,而观察与被观察、发现与被发现的互动与转化过程则更值得寻味。这就涉及到“主位”、“客位”方法的现实运用,也即民族志学者核心方法论——参与观察(participant observation)的具体落实:“研究者在观察的同时(尽可能)参与他们所意图记录的社会活动。其基本原理是:借助‘在那里’(being there)以及积极参与身边的互动,研究者能够更为切近地体验和理解‘局内人’的观点。”[注][澳大利亚]林恩·休谟,简·穆拉克:《人类学家在田野——参与观察中的案例分析》,龙 菲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第1页。这意味着民族志学者必须能够同时运用局外人和局内人的眼光观察(尽管这两种视角都会有所偏颇),能够抽离出足够的距离,以便对他们所研究对象中的一些想当然或离奇的规则和现象加以确认和反思。于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出现了:田野的知识生产存在着研究者与其对象之间的边界,或曰研究对象自己的“地方性知识”与研究者建构的“学术性知识”之间的边界。“前一种知识久已成为人类学研究的焦点,但后一种知识似乎仍然是研究的盲点。”[注]李 立:《在学者与村民之间的文化遗产:村落知识生产的经验研究、话语分析与反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26页。具体而言,我们用理性来认知和解释世界,形成各类学术体系中浩繁的知识成果,代表着人类智慧的进步与权威的表达,然历史和现实之真相与本质却只能无限被接近,我们自身进行知识生产的合理性、客观性、公正性等尚有待于追问和思考。即使某个民族的学者研究本民族的文化,虽然有着先天的优势可以对本族文化进行“局内人”的观察与深描,却也必须借助“局外人”的视角与方法来规避一些主位的盲区和局限,同样面临如何记录、阐释地方性知识,并经由前者而提炼、延展或曰建构出学术性知识的问题。因此,在“局外人”和“局内人”之间频繁转换甚至多个时候是处于兼而有之的过渡状态,常常将学者们抛入一个巨大无形的“零”的空间:“什么东西可以在这一秒的时候是‘没有东西’而下一秒的时候就是‘某物’,又在代替任何事物的时候出现?”[注][美]罗伯特·卡普兰:《零的历史》,冯振杰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5年,第75页。零符号背后所隐身或缺位的“存在”也会在此时突显出来,诸如依照深植的个人价值观行事的愿望、作为研究者试图保持的专业的和相对主义的立场,或前两者相互作用却难以兼顾而导致的尴尬、焦虑与疲惫。
通过对具体文化事象的分析而剥离出象征物并加以阐释形成某种文化符号,是民族学研究的惯常之法。象征物或文化符号的所指和能指意义即是零符号特有的强大生成性、繁衍力及变化性的体现,正如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中所指出的那样,零体现了“奇妙的抽象能力”和“高超的创造能力”。[注][德]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第1卷,吴 琼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第64页。云南红河一带的哈尼族流传着独特的鱼化生神话:洪水泛滥之后,人们无衣无食,正发愁之际,鸟儿告诉他们,鱼腹中藏有万物的籽种,人们受蜘蛛结网的启发,结大网捉住了巨鱼,获得了籽种,从而得救。另一神话则有着更为奇特的表达:
祖先鱼嫌咸水湖太单调,就来生万物。第一天生天,所以天是老大;第二天生地,所以地是老二;接着生了“有”、“无”、“黄”、“红”、“绿”、“黑”、“生”、“死”、“大”、“小”……,一共77个,最后一个是“半”。[注]李子贤,胡之耘:《西南少数民族的稻作文化与稻作神话》,《楚雄师专学报》2000年第1期。
在神话中,不仅具体可视之物为神奇的祖先鱼所生,就连抽象之概念也出自祖先鱼。梯田养鱼是哈尼族文化的一大特征,族人捕鱼时捉到的第一条鱼,不论大小均要放生。此外,哈尼族少女喜用金属打制的鱼装饰腰胸、挎包;女子出嫁时要用许多金属鱼装饰帽子,作为吉祥的象征;在孩童的裹背上,丰满稚拙的大鱼也被刺绣在较明显的位置,成为其避邪的灵物。鱼是稻作区的常见之物,是稻作文化的标志之一,在哈尼族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他们养鱼、食鱼、敬鱼、饰鱼,源于其生产生活的境遇以及从中孕育出的信仰与习俗,因为“共时性层面上的事件登录也有其历时性层面的对应物。事件也根据其社会重要性的逻辑被记忆。和文化叙述一样,过去的故事也是事件真实结果的选择性记述,但这种选择并非毫无章法”。[注][丹麦]克斯汀·海斯翠普:《他者的历史——社会人类学与历史制作》,贾世蘅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0页。值得注意的是,这两则鱼化生神话有着明显的生殖崇拜印记,故事中的鱼与现实里的鱼和合共生并逐渐演化成为一种寓意富足、吉祥、平安的象征物。闻一多先生在《说鱼》一文中,援引《诗经》、《周易》、《楚辞》、古诗、民谣以及其他资料,指出中国人从上古起就以鱼象征女性、配偶或情侣。[注]参见闻一多《神话与诗》之《说鱼》一文,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年。从考古学的角度,中国多处母系氏族社会遗址出土的陶器上绘着或刻着的鱼纹符号,也系女性生殖器的象征,鱼纹体现着女阴崇拜的内涵。[注]赵国华:《生殖崇拜文化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167~169页。然而,哈尼族所用的鱼饰、鱼纹相较于其他地方的不同民族具备怎样的特征?如何体现出女阴崇拜,抑或象征配偶或情侣?该如何论证?是借用现成的理论还是立足于当地的文化生境去再发现、再诠释?……无论如何,人们对世界和自我的探寻不会停歇,作为理性结晶过程的知识生产不会止步,我们还将在广阔的田野里继续前行,如同行走在“零”的荒原——“并不是虚无,而是一种有意义的空缺”,“显示的是一切符号都具有在‘无’的状态下表达意义的能力”。[注]Roland Barthes, Elements of Semiology, translated by Annette Lavers and Colin Smith, New York: Hill & Wang,1973, p.76.
三、零符号理论在少数民族研究中的具体运用:以傈僳族史诗《创世纪》为例
傈僳族是我国西南古老的少数民族之一,与彝族、纳西族等民族共源于古氐羌民族。唐朝初年,傈僳族先民就已沿着雅砻江南下,广泛分布于今云南、四川金沙江两岸河谷地带。明朝特别是清朝中后期,又从金沙江迁往澜沧江、怒江,随后南下缅甸、泰国、越南等地。国内傈僳族目前主要分布于云南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以及迪庆、丽江、楚雄、大理、保山、德宏等州市,少量仍定居于四川的西昌和攀枝花。
在傈僳族的文化发展史上,诞生了一部规模宏大、内容浩繁的民间史诗——《创世纪》,成为其民族创世神话、迁徙经历、生产劳作、习俗礼仪、宗教禁忌等的沉淀和凝聚。《创世纪》中有“峨绿瓦”(玉龙山)、“娜依墨博”(金沙江)、“蒙罕滴理”(青海湖)等地名,熔铸着该民族漫长而曲折的迁徙历史;“哪里来的哪里去”,体现着傈僳族祖先崇拜的观念和叶落归根的愿望。傈僳族认为:人死灵魂存,在弥留之际,灵魂即将离开躯体,回到祖先居住的地方。但灵魂不知道重返祖地的路线,就会留在躯体周围逗留并扰乱亲属,所以在装棺和下葬时,需由必扒(祭师)吟唱《创世纪》,为死者的灵魂指路。此仪式就是“麻札么”,汉语之意为“做道场”。指路道场是傈僳族最庄严肃穆的宗教仪式,其吟唱具有与众不同的独特魅力。必扒的音调和曲调在不同的章节有局部的变化,如前半部分主要讲述宇宙混沌和与人为善的道理,稍显轻松;到最后的《指路经》部分就显得苍凉悲怆,远古气息扑面而来,往往让人长泣不已,哀婉叹息:
这家人死了/死了魂要到/先祖居住地/他不知道路/回不到那方/死魂不出家/时时扰亲人/主人请我来/给死人指路/尔萨山神鬼/天下各路神/请让一条路……。[注]傈僳族《创世纪》的歌词来源于云南省丽江市华坪县傈僳族研究会成员杨世祥的整理和翻译,未公开出版。
人死了,若找不到寻祖的归路,亡人和存世的亲人都将会陷入到巨大的“无”的虚空当中,需要必扒指引方得解脱。这是一种隐喻,折射出人们对于死亡的恐惧和失去亲人的不舍。傈僳族相信长辈死后其灵魂不灭,可以造福家人,故设神龛供奉祖先,男祖的安置于正屋面门之墙的左上方,女祖的安置于右上方,神龛不能随意搬动。除专门的祭祖节日外,逢年过节都要对神龛敬献酒肉。“所有关系的聚合点,也是所有关系的发出点,但它本身却不具有任何可规定的内容。这是零的本质,也是所有形而上学的本质。它是空的(它以空的方式存在),但它是(它存在)(It is empty, but it is);它是无(它作为无存在),但它是(它存在)(It is nothing, but it is)。”[注]倪梁康:《零与形而上学——从数学、佛学、道学到现象学的有无之思》,《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 亡灵、神鬼、祖先,这些“缺位”的“在者”,既是人们抵挡哀思与无助的堤坝,又是人们寻求慰藉和归属的寄托。此外,在《创世纪》的吟唱禁忌中,我们可以寻到某种零符号的隐性结构,即一方面是符号形式,另一方面是符号形式所要表现的那个“缺场”和“无”:第一,女人不能吟唱,必扒使用的法器女人也不能触碰。第二,平时(没有人去世的时候)不能吟唱,否则即被认为会触犯神灵而遭受厄运。第三,必扒吟唱时,旁边的人不能说其他民族的语言,不能嬉笑打闹,否则视为对死者、祖宗、神灵及必扒的不尊重。第四,不能在别人家哼唱,这种行为相当于诅咒对方死,这是傈僳族家庭最为忌讳的。第五,只有必扒和其所收的徒弟才能吟唱,且要学就要学完,不能只学其中的片段,否则会受到神灵的惩罚,使其疯掉而无药可治。
“符号是携带意义的感知:意义必须用符号才能表达,符号的用途是表达意义。”[注]赵毅衡:《符号学:原理与推演》,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页。《创世纪》里铺陈着各类奇特想象和大胆夸张的符号,其中不乏零符号的运用,如:
昼暑夜寒的恶劣天气变化源于天上出现的九个太阳和七个月亮;洪水泛滥是因为老妇人咒天而引发了大雨,滚滚浊流将本来离得很近的天地分开;兄妹俩躲进葫芦避过洪水灾难,又顺由天意经历各种磨难和考验后结为夫妻繁衍后代……。[注]杨春茂:《傈僳族民间文学概论》,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15~316页。
“九”和“七”在傈僳族文化中占据着重要地位,“首先,数字‘七’和‘九’是两个在傈僳族日常生活中频繁出现的数字,表示概数的概念,意思是多、大、经常、频繁等等,同时它们也频繁出现于氐羌后裔如怒、彝和纳西等民族的日常生活中;其次,数字‘七’的出现大概与女性的某些生理现象有密切的关系,而男‘九’女‘七’的习俗还可能蕴含了氐羌族群古代社会中男尊女卑这样一个文化因素”。[注]侯兴华,张国儒:《从数字“七”和“九”探索傈僳族文化点滴》,《出国与就业》2011年第8期。洪水泛滥已是一个世界性的神话母题,《创世纪》中的相关表述可以成为一份佐证,其原因“老妇咒天”值得寻味,反映了人与自然共生过程里出现的某种矛盾。兄妹成亲繁衍后代也广见于很多民族的神话中,但傈僳族的《创世纪》却有着特殊的描述:
黄水淹了天/除了一兄妹/全部都淹死/兄妹一起逃/找到一芦葫/划开半边后/坐在上边漂/黄水退完后/只剩这兄妹/要传地上人/只有兄妹合/违反人伦理/只有看天意/兄妹两山头/各烧一堆火/火烟上半空/两股合一股/这还在不行/找来一副磨/兄拿了磨盖/妹拿了磨心/兄妹两山头/一起往下放/滚到山谷底/两边合一起/这还在不行/找来针和线/兄拿了线头/妹拿了颗针/兄妹两山头/兄把线头下/穿过妹针孔/儿子生三个/老大去犁地/老二当毕扒/老三去当兵/女儿生三个/老大去种地/老二去织麻/老三舅儿媳/从此繁人类。[注]傈僳族《创世纪》的歌词来源于云南省丽江市华坪县傈僳族研究会成员杨世祥的整理和翻译,未公开出版。
其中,“葫芦”、“磨盖”、“磨心”、“针孔”等均为典型的零符号,虽是现实的物品,却成为达成“天意”的途径;而“天意”本身正是零符号神秘性、象征性、无可替代性的最好诠释。
零符号一旦被实践性、技术性地引入,便会产生心灵思想上的震荡,“它本身会迫使我们进行某些思考”。[注][日]柄谷行人:《作为隐喻的建筑》,应 杰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第34~35页。在《创世纪》的研究过程里,就涉及到一些需要加以甄别和分析的实际问题:其一,《创世纪》中出现“江西”、“湖广”等地名,常常被认为就是今天之江西、湖南、广东,这将导致傈僳族先民曾在这些地方生活过的误读,而这是找不到历史依据的。其实,《创世纪》中提到的“江西”是指江的西面,有可能是怒江的西面,也有可能是金沙江的西面,还有可能是澜沧江的西面。至于“湖广”,是因为明朝以来到云南屯兵的汉族兵勇与当地傈僳族通婚后,其父系籍贯依旧保留了江西、湖南、广东地区的说法。其二,必扒吟唱《创世纪》凭借的往往是记忆和个人对史诗的理解,一般不具备质疑、考证的能力,在一代又一代的耳闻口传中,其部分史诗内容难免有以讹传讹的成分,给研究者的田野作业带来更多困难。其三,由于傈僳族居住地域的分散和宽广,造成语言、习俗、服装、宗教等方面的差异,加上没有文字的确凿记录,《创世纪》在漫长的岁月中逐渐形成了不同的版本,如:云南怒江地区的《创世纪》,由“生与死”、“采吃野菜”、“生火”、“下雪下霜”、“祖先去世”、“人类繁衍”、“语言和文字”、“葬尸”、“洪水滔天”、“葫芦里面留人种”等24个部分组成;而在云南丽江永胜、仁和、华坪,四川攀枝花、盐边、德昌、米易等傈僳族地区的《创世纪》,则分为“开天辟地”、“黄水淹天”、“兄妹造人”、“人生哲理”、“生产调”、“英雄射日”等22个章节,但其主体内容和民族精神却保持了一致性,故不能狭隘、简单地以正宗与否来加以评判。
四、余论:以跨学科理论运用拓展少数民族研究视域
《道德经》曰“有生于无”,其中的“无”不同于“空”、“色”、“感性”、“存在者”,是一种真正的“空洞无物”和发生意义上的“零”,用数学来解说,这里的“无”静居于正负两极的中间,是万物的中心。亦如倪梁康先生所概括的那样,中国文化是建基于本原/生衍两分之基础上的发生论形而上学,与“在正负数之间的零”相关,它关注的范畴是虚实相生、正负变化、动态运行的封闭体系,这是中国古代艺术文化始终停留在相生相克、辩证对立变化的“空”范畴里运行的根源,而最终在科学技术上落后于以认识论形而上为基础的西方。[注]倪梁康:《零与形而上学——从数学、佛学、道学到现象学的有无之思》,《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中国文化特别是道家文化充盈着有无关系的探讨,却缺少西方人对零的追问,即知识是什么?知识从何而来?如何获得知识?因此,中华文化关于“无”的探讨往往局限在人伦关系的框架内,而西方文化则获得了知识理性,并进一步促生了科学理性。
其实,无论地方性知识还是学术性知识,都是一种从零开始的生产。零是知识生产的坐标点,是零把人和动物区分开来,我们越过了零,超越了动物性而获得了理性,同时也创造了文化。在少数民族文化中,存在大量零符号,比如傈僳族的“尼”,其指向是现实里不存在的鬼神;还有一些能指符号指向了某种特别的象征意义,有如哈尼族文化中的“鱼”。这些地方性知识对局外人来说,恰恰就是“nothing”,即什么都不是。而作为研究者进入田野时,我们又“化身”局内人,这些文化好像又是什么。由此,零符号在少数民族文化中不仅作为一种形象存在,而且表征着少数民族文化一定程度上被边缘化、零余化的处境;在质性研究中,零符号还作为一种视角暗含于民族志的文本,表征着少数民族文化研究者的尴尬处境。零符号理论的介入,让我们把对“对象的研究”转化为研究对象,得以叩问研究者的权威性,并反思其学术文本的局限性;零符号理论的介入,为少数民族研究提供了多维阐释与解读的可能,于确定之处发现盲点和边界,由文化事象之“有”(符号的能指及所指的某些层面)而探究其“无”(符号之所指的来源或引申)。“我们必须尽最大的努力,在情感与理性之间、同情与戒慎之间以及行动与认识之间寻求平衡。不管在这‘一切都被允许’的虚无主义年代里,人类的理性能力受到多么激烈的质疑,理性毕竟是卑微、善变和激情的人类最后的凭借。”[注][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7页。——如何消除盲点?怎样打破边界?我们尚在途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