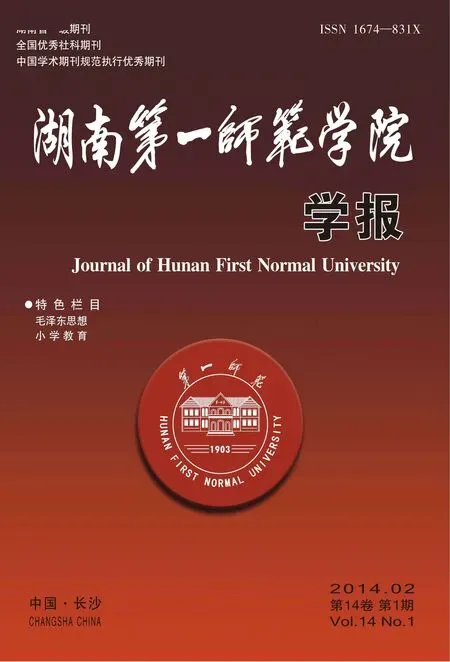论《生日》的心理空间与华裔的族裔性
2014-04-08方何荣许锬
方何荣,许锬
(1.合肥学院基础教学与实验中心,合肥230022 2.安徽财贸职业学院,合肥230601)
论《生日》的心理空间与华裔的族裔性
方何荣1,许锬2
(1.合肥学院基础教学与实验中心,合肥230022 2.安徽财贸职业学院,合肥230601)
短篇小说《生日》在叙事手法上别具一格,它将华裔主人公的回忆与现实交织在一起,通过一个个片段勾勒出华裔男青年与白人女性之间多舛的跨种族恋情。小说重点突出了华裔主人公的心理活动,折射出华裔在美国社会的边缘化处境以及他们主体性的建构。
《生日》;心理空间;华裔
《生日》(Birthday)是雷祖威(David Wong Louie)的短篇小说集《爱的痛苦》(Pangs of Love, 1991)中的一篇。小说本身并不复杂:华裔青年华莱士·王(Wallace Wong)爱上了离异的白人妇女西尔维亚(Sylvie),二人相处的过程中,王与女友的儿子韦尔比(Welby)相当投缘,允诺孩子在生日当天带他去打垒球,看比赛。后因法院将小孩的监护权判给了其父弗兰克(Frank),西尔维亚伤心出走,她与王的恋情也暂告一段落。但是,华莱士·王仍在韦尔比生日当天准时出现,兑现他与孩子之间的生日约定,却遭到了弗兰克的种种阻挠。情急之中,王将自己反锁于韦尔比的儿童房内,画孩子最喜欢的图画,提醒韦尔比自己的准时赴约。最后,见到女友回到前夫家中的华莱士·王选择了黯然离去。在《生日》中,作家没有按照传统的小说叙事逻辑,从开端﹑发展﹑高潮到结局来依次展开故事,而是采用倒叙与插叙的方式将主人公的回忆与现实交织在一起,由华裔男青年华莱士·王(Wallace Wong)看似杂乱无章却相互照应的回忆与想象联结起整部作品。在华莱士·王不停转换的思绪片段中,不同时间发生的事件被并列在同一个时空里,构成一幅幅完整的画面,切实地反应了其生存的现状及“深厚浓烈的情感世界”[1],凸显出华裔男性青年居于主流社会之外却又与家庭和本民族传统不断发生冲突的尴尬处境,以及他们既敏感又充满焦虑的内心世界。
一、小说的意识流手法
显然,小说的成功得益于作家采用的独特的叙事手法。小说一开篇便呈现出一幅奇怪的场景:一个男人在外面将门捶得山响;另一个男人则将自己反锁于屋内,毫不理会屋外的事情[2]。“门外有个人。他攥紧拳头砰砰砰地捶门,捶得房间的这一面墙都震动了。他能捶到房屋倒塌。可我才不在乎呢,那是他的房子,他尽可以随心所欲。”[3]22突兀的情节立刻吸引了读者的注意力。之后,与故事相关的一切人和事都由将自己反锁于屋内的男人华莱士·王陈述。于是,在王的回忆与触景生情般的联想中,整篇小说的情节得以逐步地展开。而所有的叙述都集中在华莱士·王将自己反锁于韦尔比房间内的几个小时之中。因而,是王内心深处的记忆碎片及其对外部世界的瞬间感受将生日事件的来龙去脉、个人的生活体验及其对未来的幻想交织起来。在这里,作家雷祖威利用人物思绪的起伏和内心意识的流动,在有限的篇幅中勾勒出一幅鲜活的画面,将华裔青年华莱士·王的现实生活空间展现给读者。也就是说,小说是根据人物的意识活动的逻辑、意识的流程来安排小说的篇章和先后次序,将散落于人物内心的情绪与思绪串联起来,形成了一个连贯的故事。即,“小说是一幅书写的画面,是流动的意识、流动的时间、流动的空间。客观景物和流动的意识共同建构了小说的立体空间。”[4]这种做法打破了文本的线性与故事的时序性,作家既不需要遵循时事件的因果关系,也不需循时间的先后顺序。而主要是运用人物的意识流动从作品内部整合全部的叙事。关于“意识流”,最初由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提出,他既强调思维的不间断性,即没有空﹑白始终在流动,也强调其超时间性和超时空性,即不受时间和空间的束缚,那么,在《生日》中,通过华莱士·王的意识,我们应能够看到华裔青年与白人女性的情感纠葛中各个事件发生的地点与场景,而它们又组成了一些摆脱客观时间限制的相对独立的空间,在不断地变化中展现这生日事件的始末。
二、孤独的情感世界
在将自己反锁于韦尔比的儿童房里的短短几个小时中,华莱士·王的回忆与联想描绘出他生命中几个重要的生活空间,它们无一例外地折射出一个华裔青年在个人婚恋问题上的尴尬处境。首先,华莱士·王触景生情地忆起了他与女友之间的恋情﹑女友前夫弗兰克在监护权诉讼中的傲慢,他更想到了年迈的父母对自己婚恋问题关切与不理解。给韦尔比画小猫时,几个用来当做猫牙的黄色小方块便让笨手笨脚的华莱士·王想起了自己的父亲。连他本人都不得不承认,此种想象过于奇特;因为除了他,“再也没有其他人会产生这种联想了”[3]23。随后,王很自然地由父亲想到了他的家。刹那间,在这个由华人移民父母和几乎完全美国化的儿子组成的三口之家中发生的种种往事纷至沓来,一齐涌上王的心头。在他的记忆中,与父母共同生活的家庭空间里一直充满着隔阂与矛盾,但核心的问题只有一个,即家中独子华莱士·王的婚恋问题。父母期盼儿子能找个合适的中国媳妇,最差也得是一位会说汉语的华裔姑娘;王却偏偏钟情于白人妇女西尔维亚,哪怕她刚刚离异又带着一个年幼的孩子。双方的巨大分歧在西尔维亚与前夫进行孩子监护权诉讼时达到顶点。父母为西尔维亚的离开而暗自庆幸,王却为躲避父母的电话而搬家,栖身于餐馆的储藏室中。女友的不告而别、恋情的无疾而终,令华莱士·王觉得自己如同濒临灭绝的加利福尼亚兀鹫3[23],在应当寻偶交配时却找不到自己想要的雌鹰,只能孤独终老。此刻,王又想起父亲有关婚恋的建议:去中国找媳妇,可是,心中对中国姑娘的轻蔑与排斥表明了他对这一看似切实可行的方案与自己父亲的彻底拒绝。在这一部分的文字中,雷祖威讲述了华莱士·王的家庭环境及其在婚恋问题上遇到的问题。整个的叙述是由主人公华莱士·王的内心一个个的思想片段组合而成,这些片段之间并没有必要的连续性,呈现给读者一种跳跃的、变动不停的物象与画面:如黄色小方块与父亲,濒临灭绝的兀鹫与找不到心仪女友的华莱士·王。在小说中,华莱士·王由几个黄色小方块想起父亲,想到父亲所代表着的家庭然后由家想到自己的婚恋问题和父子两代人之间的矛盾,再想到个人恋情的失败,最后想起父母给自己的忠告,不断转换的思绪串联起所有的相关叙事。而父子二人在不同场景中的言谈举止生动地再现了华裔家庭内部的生活现实。
在小说快结尾处,韦尔比玩具架上的众多小玩意儿令华莱士·王睹物生情,整个的思绪都随着孩子的新换的玩具而不停地来回穿梭,心中不禁忆起了往日里与韦尔比交往的情形。当读者将这些往昔不同时间的情景串联起来时,一幅关于华莱士·王与韦尔比二人之间真实的生活图景便呈现出来。玩具架上那些制作精巧的小玩具令王想起了孩子以前十分喜爱的小兔子标本。这标本代表着韦尔比曾经对他的依赖,可早已不见踪影的动物标本不禁使王联想到韦尔比的成长并由此猜测孩子对他的遗忘。由于弗兰克将韦尔比寄宿在朋友家以防华莱士·王将他接走,所以,韦尔比生日当天,华莱士·王并没有见到孩子。韦尔比的缺席使得二人之间并没有任何接触,也没有什么实际的事件发生,所有的描述都是由主人公华莱士·王当时的感受、时刻萦绕其脑海中的有关韦尔比的印象与其丰富的联想触动。在那一瞬间,出现于不同时间、地点的事件被并列、组合起来,彼此之间相互照应;读者则需根据华莱士·王的思路在不同的时空中来回移动,找出貌似随意拼凑在一起的各事件的内在联系,以适当的方式衔接起各个部分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结构。此时,华莱士·王与韦尔比之前共渡的时光、韦尔比随父生活后的转变,乃至及华莱士·王父亲对儿子的了解均与韦尔比生日当天华莱士·王的经历集中出现于同一个时空层面,从而使作家的叙述获得了一种立体、共时的效果,形成了一个空间。
与西尔维亚母子共渡的日子,愉快的也好,痛苦的也罢,都深深地印在他心中,成为其生命不可或缺的部分。因而,与维尔比的生日约定就成了华莱士·王当下生活中一件极其重要的的事情。维尔比曾经表现出对华莱士·王的喜欢与依赖一度使后者欢心鼓舞,这个男人认为二者之间已建立了一种十分融洽、近似父子的关系,而他也准备充当维尔比的父亲。但是,孩子玩具架上发生的变化,早前心仪玩具的失踪使华莱士·王突然意识到自己与维尔比之间的关系:自己不过是遭遇父母离异变故的维尔比心灵孤独无依靠时的临时玩伴,为年幼的孩子提供了一时的庇护;而非父子间的情感依赖。待到风波之后,渐渐长大的孩子便不会再需要这样的温暖。看清现实的华莱士·王终于意识到自己可能只是维尔比生活中的玩具,就如同“一个活的、会透气的电子游戏”[3]24,在孩子失去兴趣之后便遭到遗弃,无法像一个真正的父亲那样,与孩子之间形成心灵上的沟通,作孩子成长道路上的伴侣。仅仅是短暂的分离,韦尔比的世界就失去了曾经十分疼爱的小兔子标本,与之同时消失的还有他对小动物的爱,那是他与华莱士·王之间共同的记忆。如今的韦尔比只是关注小天使、机器人、火箭、航天发射器等塑料与镀铬的玩意儿,由于在整篇韦尔比始终处于缺席的状态,读者与华莱士·王一样都无从求证这些玩具的变化是韦尔比父亲的选择还是孩子本人在成长过程中的自然的兴趣转换所致,但是,恰恰是这种不确定性给了华莱士·王意料之外的挫折感,他一直认为韦尔比喜欢他、依赖他。即便韦尔比会慢慢地长大,他也不会丢弃华莱士·王送他的兔子标本,忘记华莱士·王给他画的各种小动物;他会和这个成年人一起分享自己的新玩具,新乐趣,给他解说火箭在外太空飞行的情况。现实却告诉华莱士·王,他不仅没有意识到孩子的成长,也没有预料到他任何可能的变化,而这些是一个父亲最基本的能力。就如同华莱士·王的父亲能准确地洞悉童年的华莱士·王对棒球棒与棒球帽的渴望一样,虽说这位华人移民对这项风靡美国的体育运动根本一窍不通[3]26。可是,华莱士·王对韦尔比的内心却无从掌握,或许,就像韦尔比父亲弗兰克所说的那样,华莱士·王只不过是韦尔比曾经感兴趣的玩具而已,注定是其生命中的过客。他的出现只会打破了韦尔比父子难得的清静的共处时光,对于这个已经破碎的家庭来说,华莱士·王依旧是个外来客,而不会成为其中的一份子。
三、边缘化的社会地位
关于华莱士·王的家,小说并没有给出任何具体的描述。虽然,雷祖威在创作的过程中努力地淡化其中的族裔性,不再强调人物的族裔身份,但是,读者依然能从小说中清晰地体会到华裔的诸多悲伤。从华莱士·王心中有关父母对话的点滴记忆来看,这个三口之家没有一般家庭中常见的温馨与亲情,亲子关系疏离且矛盾不断。这样的家庭自然不会令华莱士·王心驰神往,更谈不上眷恋。可这里是他生命的源头,也曾哺育过他的精神世界,他注定了一生要受这个家庭的影响。所以,他才会看见几个充作猫牙的黄色小方块便想起了自己的父亲,尽管他们之间存在着种种隔阂。华莱士·王爱上了离异的白人妇女西尔维亚,因为这份爱,他真心地愿意接受西尔维亚与前夫的儿子维尔比,难得的是维尔比他很钟意华莱士·王,因为,“当他母亲介绍我们时,这(笔者按:华莱士·王的名字)是他词汇中最清晰的三个音节”[3]22,如此和睦的关系令华莱士·王想结束单身生活。虽然,王的父亲也期盼儿子尽早成家,他却不能接受白人妇女作自己的儿媳,更何况儿子钟意的这位白人妇女还带着一个小孩。而华莱士的母亲得知儿子要与一位白人妇女结合时,不禁提出了自己的忠告。多年的生活经历使这位华人移民母亲对现实有着十分清楚的认识:在周围人的冷眼中,她忍受了种种的屈辱,她从不奢望改变自己生存的社会,只想以自己的方式在其中生存下去而已。[5]年迈的父母并不知道,他们所期盼的中国儿媳恰恰是儿子所排斥与拒绝的。正如开意大利餐馆的华莱士·王会有意识地避开木须肉这类型的中国菜肴。想做普通美国人的华莱士·王在婚恋问题上的选择简单而明确:他根本瞧不起来自中国的姑娘,也不愿意和康妮·程这样的完全不会汉语却长着一副中国人面孔的华裔姑娘结合;他需要的是一位黄发白肤的西方女性。所以,华莱士·王这只处于进化尽头的加利福尼亚兀鹫经过深思熟虑从同类仅存的三只雌鹰中选了那只长着金黄色尾羽的雌鹰。这在家中引起了轩然大波,父母二人甚至热切地希望西尔维亚在争夺韦尔比监护权诉讼中败下阵来,并为她的伤心出走而欢呼。父子两代至亲之间的想法南辕北辙,处于人生艰难时期的儿子无法让父辈明白自己的恋爱要求,更谈不上获得他们的支持和帮助。无奈之下,他只能搬家蜗居于餐馆的储藏室中,独自一人陪女友忍受诉讼的煎熬,继而品味失恋的伤痛。
华莱士·王与父母在婚恋问题上的分歧不过是两代人沟通上存在的巨大鸿沟的具体表现之一。家人无法理解他西方化的行为方式与对本身所具有的种族特征的轻蔑,却总是不失时机地向他儿子提醒其族裔身份特征。心烦意乱的华莱士·王无法忍受父母在自己婚恋问题上的固执与横加干涉,最终决定搬家,躲到餐馆的储藏室以避开父母的电话,从而能够全身心地陪女友度过其人生中的最艰难时刻。他希望女友能体会到他的这份真情,留在他身边,成为他人生的伴侣,使他从此不再孤单。可事与愿违,当华莱士·王将自己与女友西尔维亚的恋情视作突破内心孤独而获得人间真爱的尝试时,他所得到的不过是更深的孤独与令人心碎的凄凉。女友西尔维亚的不告而别曾给华莱士·王以不小的打击,他说:“在小孩母亲离开我的那个晚上,我甚至给收音机里的心理医生打电话”[3]24,奢望寻求某种安慰。但是,他一直坚定地相信,“一旦她心口的创伤愈合后,她会回家的”[3]22,因为女友终会明白他的这份真爱。西尔维亚音讯全无,华莱士·王只能将自己的一腔真情投注到小孩韦尔比的身上。在他看来,爱韦尔比就是爱其母亲西尔维亚,毕竟女友是因为丧失儿子韦尔比的监护权而非与前夫的婚姻破裂而失魂落魄,离家出走的,儿子才是女友西尔维亚的全部;终有一天,西尔维亚会走出情绪的低谷,她会因男友真心善待韦尔比而心生感动,进而接受两人之间的恋情。问题是,一度杳无音信的西尔维亚选择在韦尔比生日的当天回到了前夫弗兰克的家,她身着夸张的服饰,与弗兰克紧紧拥抱,却将曾经的男友华莱士·王视为不速之客,最终选择与前夫一起消失,让曾经的男友知难而退、自行消失。华莱士·王不得不承认,“这根本不是我所想象的那种感受”[3]26。也许,年迈的父母的警告是对的,西尔维亚从未,也不可能,爱上华莱士·王,后者只不过是一个婚姻失败的女性临时的情感寄托,终就无法摆脱被抛弃的命运。于是乎,在这场恋情中,华莱士·王自始至终只能是一个匆匆的过客,性格乖张的西尔维亚不曾真正地考虑过这个男人的感受,更谈不上任何激情或真心。
四、结语
当华莱士·王通过回忆与联想讲述个人的恋爱经历,读者不难从这些时间上稍显混乱的叙事碎片中拼凑出了华莱士·王独特的人生经历。其人生的各个阶段发生的事情全都被时间所定格,停滞在发生的时刻,就像一幅照片凝固的瞬间一样,一种空间感被表现出来,众多片段化的细节穿插所组成的小说叙事割裂了传统小说中情节发展的自然时间流程,从而表现出一种空间形式。对华莱士·王而言,与父母同一屋檐下生活的亲情与矛盾、与维尔比短暂相处的欢乐都给了他许多混杂着甜蜜与苦涩的记忆,这些烙在脑海中的回忆使父母所在的家、维尔比的玩具所在的儿童房成了华莱士·王心中的特殊空间。作为其生命的源头与人生未来的重心所在,这两个地方分别代表两个不同的世界,性质各不相同,承载着他人生中两种重要的情感,这二者之间既无法完全地分离却又不能和谐地统一在一起。通过主人公在其意识层面对这两个重要空间的描述,读者不难看出华莱士·王一直试图用爱情来恢复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与沟通,但结果总不能令人满意:他与白人西尔维亚母子之间始终存在着一种距离感,难以走进彼此的内心的情感世界;他又不愿与自己年迈的父母相妥协。因而,其内心的孤独可见一斑。而华裔青年华莱士·王的尴尬处境,“作为处于美国边缘社会的异类的体验”正是作家雷祖威所要表达的[6]。
[1][美]凌津奇.历史与想象:雷祖威、梁志英与伍惠明的小说艺术[J].南开大学学报:哲学社科版,2009(5):36.
[2]盛周丽,方何荣.深沉的爱与破碎的现实——评《生日》中的华裔男性形象[J].长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85.
[3][美]雷祖威.生日[J].吴宝康,译.外国文学,2005(5)22-26.
[4]张中载.小说的空间美——看《到灯塔去》[J].外国文学, 2007(4):118.
[5]盛周丽,王晓凌.无处宿归的灵魂——《生日》中三重空间的身份印记[J].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13(2):58.
[6]张子清.当代华裔美国文学中族裔性的强化与软化——雷祖威访谈录[DB/OL].[2004-02-15].http: //www.yilin.com/bbs/showtopic-955.aspx.
On the Psychological Space and Chinese American’s Ethnicity in Birthday
FANG He-rong1,XU Tan2
(1.Fundamental Teaching and Experiment Centre,Hefei University,Hefei,Anhui 230022; 2.Anhui Finance&Trade Vocational College,Hefei,Anhui 230601)
Short story Birthday,with a unique narrative feature,is a mixture of memories of Wallace Wong,a Chinese-American young man,and his real life,and those fragments have drawn the outline of his inter-racial love with a white woman.The novel highlights the Chinese-American hero’s psychological activities,which reflects the Chinese-American’s marginalization in American societ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ir subjectivity.
Birthday;psychological space;Chinese American
I712.074
:A
:1674-831X(2014)01-0102-04
[责任编辑:刘济远]
2014-11-03
2012年安徽高校省级优秀青年人才基金项目(2012SQRW133)
方何荣(1979-),男,安徽舒城人,合肥学院讲师,主要从事美国华裔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