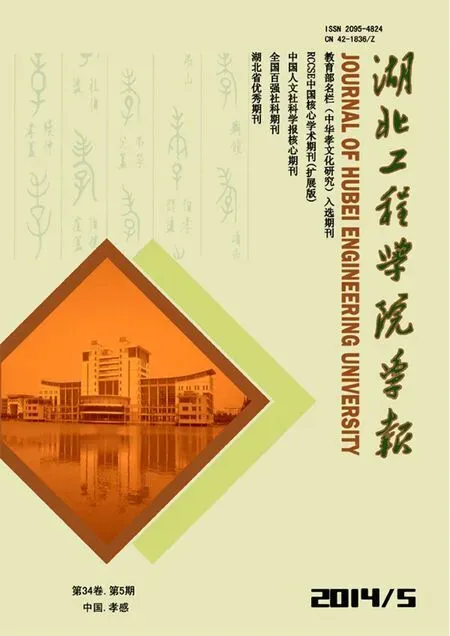遗体捐献主体决定权的行使及民法保护
2014-04-08何小锐
黎 桦,何小锐
(湖北经济学院 地方法制研究中心,湖北 武汉 430200)
遗体捐献主体决定权的行使及民法保护
黎 桦,何小锐
(湖北经济学院 地方法制研究中心,湖北 武汉 430200)
遗体捐献决定权主体的界定是开展遗体捐献活动的首要和基本问题,对捐献主体决定权予以法律保护是遗体捐献顺利开展的保障。近亲属在死者死后占有和管理死者遗体,且遗体捐献的成功必须依赖近亲属的辅助,因此,在死者没有捐献的意思表示的情况之下应该承认近亲属的捐献决定权;自我捐献决定权与亲属捐献决定权之间,国外有自我决定权优先模式和两者等同模式两种立法,我国应该坚持自我捐献决定权优先的模式;近亲属一致同意原则不利于鼓励遗体捐献,我国应该采取多数亲属同意原则;遗体捐献形式方面,有两人在场的口头遗嘱也应该作为捐献遗体的意思表示方式,鼓励捐献登记。
遗体捐献主体;捐献决定权;近亲属捐献决定权;自我捐献决定权
遗体捐献地方立法试行近十年,在我国已逐步取得认同。 实务中死者生前决定捐献遗体,但近亲属拒绝执行,使其捐献意愿落空的情况时有发生。北京青年报报道过一则案例,某地有800人就捐献遗体认捐签字,但最终只有27人得到实现,[1]其中多数都是近亲属不同意捐献,致使捐献者意愿落空。近年发生的游涵清诉其女游文杰侵犯其妻遗体捐献权案更具有代表性。原告与被告系父女关系,原告与妻子及被告签订了《家庭协议书》,其中约定原告与其妻子百年后愿捐赠其各自遗体给医学院校,被告应予以协助。但此后十余年,双方均未前往遗体捐献登记处进行登记。原告妻子去世后,被告将其遗体火化,原告遂将被告告上法庭,认为其违反了协议书,给原告造成了精神损害,要求被告赔礼道歉并赔偿损害。一审法院认为其并未进行捐献登记,遗体捐献难以执行,火化并无不当。二审法院认为被告违背原告妻子的遗愿而对遗体作出新的处分,系侵权行为。[2]此案例争议的焦点实则是被告是否享有对其近亲属(即死者)的遗体捐献与否的决定权,是否构成对死者捐献决定权的侵害?以及死者生前如果没有进行捐献登记,仅仅进行了愿意捐献的意思表示,这一意愿受不受法律保护?如果死者的捐献意愿未采书面形式,仅做了口头表达,法院如何认定?这些问题围绕着死者捐献决定权展开,对于遗体捐献的完成具有重大影响。从民法理论上看,遗体捐献是一种死因行为,即在自然人死亡之后才能发生特定效果,而自然人在死亡后遗体由其亲属占有和管理,因此会产生捐献者本人和其近亲属的意愿分歧问题。本文从遗体捐献的主体界定入手,运用民法的基本理论对这些问题作出探讨。
一、遗体捐献决定权主体的界定
遗体捐献决定权主体是指有权决定捐献或不捐献遗体的单位和个人。关涉两方面问题,其一是捐献主体资格,即是否要求其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其二是捐献主体种类,本人基于对自己身体的处分权的死后延续,当然享有遗体捐献决定权,那么,死者的亲属在其中的地位如何认定?
关于捐献决定权主体资格问题,从各地的遗体器官捐献条例地方立法来看,我国目前大致有两种做法。其一是只承认本人具有捐献决定权,其近亲属作为捐献执行人无捐献决定权。如《福建省遗体和器官捐献条例(2005年)》第四条规定:“捐献人的近亲属应当尊重捐献人的捐献意愿,支持捐献人的捐献行为。”第十一条规定:“捐献人委托并登记的捐献执行人,可以是捐献人近亲属,也可以是其他自然人,或者是捐献人的工作单位、居住地的居(村)民委员会、养老机构等组织。”《宁波市遗体捐献条例(2003)》第二条规定:“本条例所称遗体捐献,是指自然人生前自愿表示在死亡后,由其执行人将遗体的全部或者角膜捐献给医学科学事业的行为。”第十二条规定:“遗体捐献的执行人由捐献人的近亲属担任。”采这种观点的还有《重庆市遗体捐献条例(2004)》第三条、《贵阳市捐献遗体和角膜办法(2002)》第六条。这种立法模式认为遗体捐献决定权的实质是人对其身体的处分权的死后延续,除了本人之外,其他人无权处分自己的身体。近亲属作为遗体的占有者和管理者只能作为捐献执行人的身份存在,而不能违背死者的意愿决定捐献或不捐献遗体。另一种立法例则是承认近亲属也有遗体捐献决定权。如《江西省遗体捐献条例(2012)》第三条规定:“ 生前未表示捐献意愿的自然人死亡后,可以由其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近亲属共同表示捐献意愿。”第十五条规定:“生前未表示捐献意愿的自然人死亡后,其近亲属有捐献意愿的,捐献执行人由其近亲属共同指定。”《苏州市遗体捐献暂行办法(2007)》第二条规定,本办法所称遗体捐献是指:一是自然人生前自愿表示在死亡后,由其执行人将遗体全部或其部分(如可供移植的器官、角膜等)捐献给医学科学事业的行为;二是生前未表示捐献遗体意愿的自然人死亡后,由其近亲属一致同意将其遗体全部或其部分捐献给医学科学事业的行为。类似的规定还有《上海市遗体捐献条例(2001)》第二条,《山东省遗体捐献条例(2003)》第十一条。
由此引发四大问题,第一,近亲属的决定权只发生于自然人生前未做遗体捐献的意思表示之时,如果自然人生前有捐献或不捐献遗体的意思表示,那么近亲属只能依照死者生前的意愿,不能违背其意愿处分遗体。第二,学理上,死者生前未做捐献的意思表示,是否能够推定死者愿意捐献遗体?如果不能推定其愿意捐献遗体,那么近亲属的决定权就丧失了正当性。第三,何为死者生前表示同意捐献?是否要求书面遗嘱?是否需要在生前办理捐献登记?如果没有办理登记,是否如引言案例中一审法院的判决那样不予支持呢?第四,近亲属决定是指近亲属一致同意还是多数决原则。
本文认为,遗体捐献决定权的主体应该包括死者近亲属。理由是:
第一,从理论上讲,近亲属享有遗体捐献决定权确有依据。人死后,遗体由其近亲属占有。近亲属决定权来源于我国民事习惯中对遗体所有权中的有限处分权能。[3]依据我国的风俗习惯,死者死后遗体由其近亲属管理,进行悼念活动。因此,只要在不违反公序良俗和违背死者生前意愿的情况下,应该赋予近亲属有限处分权。
第二,从现实操作层面看,自然人死后遗体由死者近亲属占有和管理。而遗体捐献需要近亲属的协助。如果不赋予近亲属捐献决定权,那么近亲属未免消极处置甚至阻挠,使得遗体捐献难以实现,还会引发遗体接受机关和近亲属的矛盾。
第三,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角度,我国传统习惯认为,死者的“后事”由亲属料理,目前料理后事的依据是 《殡葬管理条例》,由亲属执行殡葬义务。遗体捐献符合社会的利益,有利于推动医学科学事业的发展,对遗体捐献行为应当鼓励。笔者认为,可以通过立法承认近亲属对死者遗体具有捐献决定权,即法律可以在亲属礼仪殡葬遗体的义务外,增加其捐献的决定权。当然需要严格限制这种权利,不得为取得财产上的利益而捐献遗体。[4]
第四,从捐献效果上看,承认近亲属的捐献决定权,利于实现死者生前捐献意思,尊重死者的人格利益。
二、遗体捐献主体决定权的行使模式
承认近亲属捐献决定权的存在,要厘清这两个捐献主体以及两种捐献方式之间的关系。
1.两种捐献主体决定模式。研究国外和我国台湾的立法探讨,死者生前捐献与近亲属捐献有如下两种模式。(1)自我决定权优先的模式。如美国、德国、我国台湾地区等。美国《统一组织捐献法》规定,死者生前表达的捐献意愿,其近亲属不得取消。1987年修改后《统一组织捐献法》规定捐献者的捐献意愿高于其直系亲属的意愿。德国《关于器官的捐献、摘取和移植的法律》第四条规定了如果死者生前反对摘取遗体器官的应当尊重;当死者未作出捐献与否的意思表示时,经过亲属允许的可以摘取。台湾地区“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实施细则”第四条规定死者本人与最近亲属意思表示不一致时,死者意思表示优先。[5](2)自我决定权与近亲属决定权效力等同模式。即死者生前意愿与近亲属意愿共同表示一致时才能进行遗体捐献,如有一方不同意则不能进行捐献,如日本、罗马尼亚、瑞典以及中国香港等地。日本《器官移植法》第六条第一款规定“医生摘取尸体器官必须有死者在生前书面同意,且家属未反对该摘除时……”1978年克罗地亚《器官移植法令》规定死者生前有书面意见表示反对的,禁止移植;如从尸体中移植器官的,需要成年的亲属同意。瑞典采同一立法模式。二者共同点是,只要死者本人生前明确表示反对,包括近亲属在内任何人都不得捐献,这是尊重与保障人权的精神要求。
中国大陆的立法中,承认近亲属捐献决定权的地区中如江西、苏州、上海等地采取的是自我决定权优先的模式。其特点是,第一,都规定死者生前的捐献意愿,近亲属应该尊重并协助其完成捐献;第二,只有在死者未作捐献的意思表示之时,近亲属的捐献决定权才产生;第三,如果死者生前明确表示反对捐献,近亲属则不得捐献遗体。
国外有些学者主张采取自我决定权与近亲属决定权等同模式。“无论是死者本人对自我捐献还是近亲属捐献,两种决定都是重要的,不能说哪一种更为优越。因为二者都有救助他人的善意,都应予以尊重。”[6]国内主要观点和理由如下,“自我决定权优先的模式”并不能很好的解决权利冲突。因为该模式的基础是:死者处理自己未来遗体的意思表示在先,优先于在其后近亲属的决定权。这一模式的实质是排斥近亲属捐献决定权,其并未能看到近亲属对遗体享有的处分权,也未能考虑到实际的效果,因为遗体大多数是死者近亲属占有,未有近亲属的同意,捐献很难顺利执行。故未来立法可以参照日本的死者决定权与近亲属决定权“等同模式”来解决权利冲突。“等同”模式的实质是死者与近亲属意思表示没有优劣之分。二者“等同”是意思表达上的效力,即二者意愿一经合法表达即发生法律效力,谁也无法取代谁,只有意思表示内容一致时,才可以或者说才能够顺利地进行遗体捐献,这样既尊重了死者的遗愿,又照顾了近亲属的意愿。[3]
2.死者自我捐献决定权优先模式更适合我国国情。死者自我决定权优先的模式有鲜明的特点。理由是:第一,从捐献决定权权力产生来说,捐献决定权是自然人生前对自己死后遗体的一种将来的处分,它来源于自然人对自己的身体的支配和处分,是第一性的权利;而近亲属的捐献决定权则是基于对遗体的占有而享有的有限的处分权,是第二性的,很显然第一性的权利应该优先于第二性的权利。第二,从遗体捐献权的构造设计来看,只有在自然人自身没有捐献意思表示的前提下近亲属才享有遗体捐献权。可见,近亲属的捐献决定权是为了弥补自我决定权没有表示的不足,是例外性的规定,具有从属性与补充性,因此难以与死者自我捐献权同等对待。第三,如果采同等对待原则显然拓宽了遗体捐献的条件,设置了更多的障碍,使得遗体捐献更难以完成。同等对待的做法是如果要进行遗体捐献必须同时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死者生前有捐献的意思表示,二是近亲属同意,这与只要死者生前有捐献意愿,近亲属只能作为捐献执行人的模式相比显然要求更加苛刻。此外,自我捐献决定权优先并非排斥近亲属决定权,因为死者有捐献意思表示时近亲属捐献权并未产生,何来排斥之说?另外无论是何种决定权优先,执行之时均需要近亲属的协助,故不能以此来论证同等对待原则的优越性。现有的地方立法及其实践证明,我国应采死者自我决定权优先的模式,江西、苏州、上海等地的做法就值得肯定。
3.近亲属如何行使决定权。在近亲属决定捐献之时,是遵循全体近亲属一致同意原则还是多数决,亦或是其他原则。江西和苏州采全体近亲属一致同意原则,上海和山东并未明确规定。国外及我国台湾有不同的做法,(1)采“全体同意”原则,该原则比较保守,即同一顺位近亲属一致同意才可以捐献,包括日本、瑞典等;(2)“一人同意”原则,即只要同一顺位之中有一个近亲属作出捐献表示即可捐献,如德国、我国台湾地区、新加坡等;(3)“多数人同意”原则,如美国。[7]细加分析,全体同意原则理论基础实际在于近亲属的决定权是一个集体性的权利,不能够由单个人或者多数人行使。我国法律规定的近亲属人数很多,近亲属之间的意见不统一是常态,因而如果采全体同意原则则近亲属遗体捐献无异于形同虚设;反之多数人同意原则更能关照社会公共利益,最大化地发挥遗体资源的效用,同时也能够兼顾大多数近亲属的意见,通过民主的方式化解近亲属之间的分歧和矛盾是一种可行的方式。而一人同意原则显得过于激进,势必会引起其他近亲属之间的矛盾,也不利于家族的和睦安定,忽视了多数亲属的意见,是不妥当的。
三、死者自我捐献决定权的民法保护
1.死者自我捐献决定权受到侵害的情形分析。根据我国现有地区遗体器官捐献模式的设计,死者生前如果没有捐献意思表示,则赋予近亲属捐献决定权,那么死者自我捐献决定权受到侵害只有两种情形,第一是,死者生前明确表示同意捐献遗体,但近亲属在其死后并未进行捐献;第二,死者生前明确表示不同意捐献遗体,但近亲属却违反其意志,进行遗体捐献活动。其实真正的问题不在于此,因为这两种情形很明显是近亲属违背死者的意志进行捐献或不捐献遗体活动的行为,按照法律法规规定显然是不合法的。问题的关键在于,何为死者生前的意思表示?是要求书面遗嘱进行表示,还是需要进行遗体捐献登记(参见引言中的案例),或者是只需要口头表示即可?这直接决定了法院的认定。第一种情形和第二种情形在口头或书面表示上具有一致性,笔者进行一体分析,在是否需要捐献登记的问题上第一种情形和第二种情形具有差别,不捐献遗体的意思表示显然不需要登记。
2.遗体捐献主体决定权行使的形式——书面遗嘱抑或口头表达。关于捐献意思表示的方式,我国地方立法均没有规定。一般而言遗体捐献意思表示的形式有如下几种:(1)订立遗嘱,在遗嘱中确定捐献意愿和最终捐献执行人之后即可成立。(2)捐献协议。捐献协议是自愿捐献人与受捐方或者相关方之间签订的以在身故后捐献其遗体为目的的书面约定。这两种捐献方式都有规范的书面文件作为日后辨别意思表示的依据。实务中的争议点一是,口头意思表示能否被认定?二是书面的协议是否需要办理公证?
关于口头意思表示,许多学者反对认定其为遗体捐献意愿的意思表示方式,理由是口头遗嘱难以辨别真伪,难以进行核实,不能准确推知死者的真实意思。然而笔者认为,这不足以成为反对的理由,第一,我国继承法承认口头遗嘱的存在。既然继承法承认口头遗嘱,那么为何同样是口头遗嘱的捐献意思表示反而不获认可?第二,口头遗嘱辨别真伪的问题是可以解决的。例如英国于1961年制定了首部人体组织法——《1961人体组织法案(第54章)》在第1条规定:任何一个自然人,任何时候以书面的形式或者是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在有两个见证人在场的情况下可以以口头的形式,做出在他死后捐献他的身体或者身体的特定部分用于医疗目的或医学教育、研究的请求。[8]借鉴英国的做法,只要有两个见证人在场作证口头遗嘱的真实性,那么认定口头遗嘱捐献有效性的方式并无不可。再者,许多死者在弥留之际方才决定要进行遗体捐献,此时他们可能已经丧失订立书面遗嘱或协议的能力,如果否认口头捐献的效力,恰恰是违背了其捐献真实意思的表示。因此,只要有两个以上的见证人在场,应该认定口头捐献的效力。
关于书面捐献文件是否必须公证。有论者认为,公证的公信力更高,近亲属也更易知晓,有利于遗体捐献的开展。办理公证的好处在于,遗嘱的订立无须其他人的意思受领。其近亲属如果无法得知这一情形,就可能在捐献人去世后反对捐献。笔者认为这一理由并不充分,捐献的意思表示能够通过一定的形式反映出来即为已足,至于公信力高低,是否为亲属知晓,其是否阻挠等都不是应该考虑的问题,不能成为应该进行公证的理由。但是,考虑到对死者捐献遗体意愿的书面文件往往由其亲属持有,而外人难以知晓死者的真实意愿,如果此时亲属违背死者意愿处理遗体,那么其他人和单位无法举证证明死者的捐献意愿,这就会使死者的意愿永远得不到尊重,故此考虑通过办理遗嘱公证,待发生纠纷之时,有关单位和个人可以到公证机关进行查询举证,以确定死者的真实意愿。因此,遗嘱和协议的公证还是值得提倡的,当然如果死者权益维护方能够获得死者意思表示的证据,则足以认定其真实意思,那么是否公证则在所不问。
3.捐献主体决定权的公示——捐献意愿是否需要登记?先看一则案例,魏某生前是军人,在弥留之际立下遗嘱,向自己的战友表示愿意死后捐献自己遗体用于医学研究。魏某死后,其战友执遗嘱前往遗体捐献接收机构申请,但接收机构以魏某未办理遗体捐献登记及公证为由拒绝了其请求。[8]此则案例同引言中的案例一样指向的问题是捐献登记问题。争议点在于进行捐献的意思表示是否需要进行登记,换言之,登记是否是遗体捐献的生效要件。关于这一问题,我国《山东省遗体捐献条例》第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办理遗体捐献应当填写捐献登记表。”而上海市和深圳经济特区并未对遗体捐献登记进行明确的规定。在法国,实践中生前同意死亡后捐献器官者可以进行捐献登记并填写捐献登记卡,但是捐献登记并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捐献登记只是有助于医院的器官获取协调小组了解死者器官捐献的可能性,只能在与家属谈判中起到促进和鼓励作用。[9]
笔者认为,捐献登记不应成为遗体捐献的生效要件,但应该鼓励遗体捐献登记。理由是,第一,从本质上讲,遗体捐献是自然人对自己身体权的处分,只要捐献者自身具有捐献的意思表示即为足够,不需要借助登记这一形式进行认定;第二,现实中登记的程序十分繁琐,且在占我国人口近三分之二的农村与乡镇却鲜有遗体捐献登记站,如果遗体捐献需要登记则会极大地挫伤捐献者的积极性。但是应该鼓励捐献登记,理由在于,第一,出于求捐献者意思的维护和保障,道理同上文的遗嘱公证;第二,遗体捐献对国家、社会以及其他利害关系人产生重大影响,立法将遗体捐献登记作为遗体捐献的成立或者生效要件,统一纳入国家管理层面,同时赋予登记行为行政行为和民事行为双重法律效力,符合我国实际情况。只有赋予捐献登记以双重法律效力,才可以对抗任何单位和个人的不正当干预,保障捐献的顺利执行。第三,遗体捐献是单方法律行为,其成立生效无须相对方(即受捐单位或个人)的同意,具有充分的自主权,因此有必要对其进行限制。
[1] 公民遗体捐献分析[EB/OL](2009-10-25)[2014-07-07].http://bjyouth.ynet.com/3.1/0508/22/1101905.html.
[2] 章建生.公民遗体捐献权的法律属性——游涵清诉游文杰其他人身权纠纷案[J].判例与研究,2008(2):23.
[3] 刘欢.遗体捐献民事法律问题研究[D].福州:福建师范大学法学院,2013.
[4] 阎锐.浅议遗体捐献行为[J].法学,2001(2).
[5] 刘长秋.台湾地区“人体器官捐献条例”评议[J].台湾法研究论坛,2004(2):75.
[6] 石原明.医疗、法与生命伦理[M].东京:日本评论社,1997:199.
[7] 刘长秋.器官移植法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198.
[8] 刘耘希.人体器官移植相关法律问题研究[D].重庆:西南大学法学院,2011.
[9] 王海燕.法国器官捐献和移植管理及规范[J].中华移植杂志(电子版),2012(6):25.
(责任编辑:胡先砚)
2014-09-03
武汉市红十字会委托项目([2014]0620)
黎 桦(1968- ),男,湖北荆州人,湖北经济学院地方法制研究中心主任,武汉大学法学博士后。
何小锐(1989- ),男,湖北十堰人,武汉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D923
A
2095-4824(2014)05-0106-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