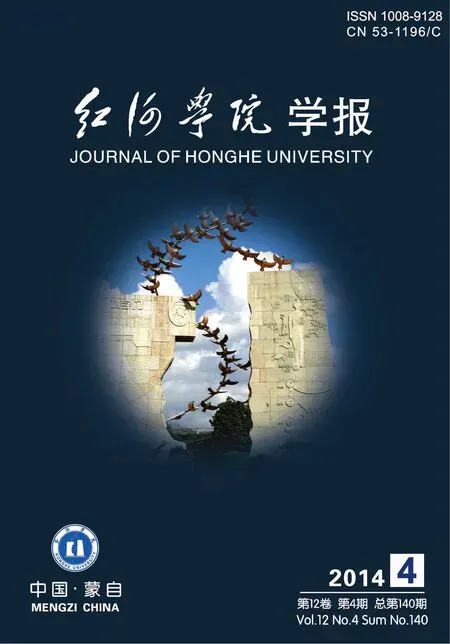试论羌语转换对地区文化安全的影响
2014-04-08叶小军
叶小军
(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四川汶川 623002)
试论羌语转换对地区文化安全的影响
叶小军
(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四川汶川 623002)
在羌语转换的大趋势下,羌族的民族身份认同焦虑越发明显,并且这种焦虑已经波及到了毗邻的藏区。从羌汉双语教育到羌语课被取缔,受到影响的不仅仅只有羌族,更让实施藏汉双语教育的毗邻藏区感到不安,敌对势力甚至借题发挥,质疑国家的民族政策,加上地方政府在语言教育问题上缺乏足够的智慧,把政治稳定作为第一要务,从而助推了这一教育上的学术问题向文化上的政治问题转变,给地区文化安全造成了威胁。
语言转换;羌族;藏族;地区文化安全
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笔者就发现羌族学生灾后异地复课期间存在严重的文化冲突问题[1],此后连续三年的田野调查中,笔者又发现羌语区语言转换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2],这不仅验证了周锡银(2004)、王明珂(2008);宝乐日(2011)、申向阳(2011)有关羌语现状的调查,也进一步证实了羌族学生在母语转换中存在语言态度(language attitudes)与身份认同(identity)的敏感与焦虑,而最新研究又发现这种焦虑还波及到了毗邻的藏区。在2012年和2013年的田野调查中笔者发现,越是靠近羌族聚居区,藏族人的语言和文化焦虑也越明显,2013年对藏汉双语学生的文化教学实证研究又进一步证明了两者之间的关联性。本文将试就羌语区语言转换给地区文化安全带来的影响展开探讨。
一 羌语现状与探因
羌族主要生活在四川省汶川县、茂县、理县和北川县,其中北川虽是全国唯一的羌族自治县,但羌语早就淡出了人们的生活[3],汶川的大部分羌语社区也基本都完成了向汉语的语言转换,只有少数偏远村落和茂县的部分地区还残存一些羌语或羌汉双语社区,并且这些村寨也只有老年人才坚持使用羌语,中年人多为羌汉双语者,而学龄儿童往往只能听懂,却不能说或者不善于说羌语,成了“被动双语”(receptive bilingualism)。羌语人群明显的老年化趋势和小学羌语课被取缔使得地区语言转换(language shift,又称语言迁移)几成定势。
我国自有文字记录以来,就有了羌人的身影,羌语历经数千年的战争、迁徙和民族大融合仍然保留至今,足见其生命力之顽强。在上世纪90年代初,羌语仍然是羌人的主要生活用语,然而仅仅二三十年的时间,羌语的境况就急转直下,到了濒临灭绝的地步,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三点:
一是国家原想帮助羌人统一标准语,创建文字,结果在标准语选点上出现了不可逆转的致命性失误。受政治观念的影响,那个时代的语言学家总认为语言没有阶级性。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社会活动,语言是没有阶级性的,但是阶级对语言确有一定的影响[4]15,语言一视同仁地为社会各个阶级服务[5]81。陈原(1980)也明确提出语言没有阶级性[6]1,但实际情况是选取茂县曲谷乡作为标准音点,直接导致城镇人口对农村土语的不屑一顾,不仅拒绝使用,而且各方言区甚至因为标准语选点问题出现了裂隙。其实,与农村方言相比,城市方言具有更大的威望[7]177,20世纪20年代乌兹别克斯坦的乌兹别克语标准语选点就已经有过前车之鉴,这也刚好可以解释为何羌语境况急转直下与羌语文字创制在时间上存在重叠。
第二个原因是国家从未将羌语或羌汉双语教育纳入正规的教育体系。在羌族文字创制前后,公立学校的羌语课一直时断时续得不到保证。政策的不连贯性和现代教育体系对羌语的排斥直接导致新生代族语能力的下降。不仅如此,无神论教育对释比(相当于汉族的端公)的生存发展还造成了沉重的打击,本来就为数不多的年轻释比为生计不得不改行务农或打工。释比的转变进一步导致羌民对本族语言和文化坚守的怀疑。
第三个原因是全世界少数民族语言都面临的两个共同问题,也就是语言的社会地位(socialstatus)和经济地位(economic status)。就前者而言,新创制的羌文字一直没有得到国家的正式认可(叶小军,2012),社会地位自然无从谈起,甚至《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总体规划》中也未直接涉及羌语的保护。就后者来说,语言生命力中的关键因素,很可能就是少数民族语言的经济地位[8]5。羌人从狩猎到农耕,几乎未曾与现代文明有过关联,羌语区内外极富悬殊的经济发展水平直接导致羌语话语力和话语权的丧失。
二 羌语转换对地区文化安全的影响
当前世界上的民族问题,大多与语言有密切关系[9]74。对于世界上大部分人而言,语言之间不平等的权利分配永远是造成语言不安感和语言压迫感的原因。[10]128当前的语言问题已经远远超过了其本身,母语问题已经与民族平等、民族独立问题紧密相连[11]73-74,更多地成了一种社会和政治问题。一个简单的现象就是,任何国家的官方通用语都会在少数民族语言区形成事实上的语言霸权。虽然从理论上来说,双方的政治地位是平等的,但官方语言享有更多的教育资源、市场平台和话语权,以及由此产生的各种发展机会,而语言人的经济地位又强化了这种事实上的社会地位落差,并进而人为地被“政治化”和极端“民族化”了。如果这些情况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少数民族对族语的正当权益要求就有可能升格为狭隘偏激的民族主义,给地区文化和意识形态安全乃至国家安全造成潜在威胁。
“语言文字”是全部文化和文明中最基本、最稳定、最持久的构成部分。改变一个民族的语言文字,对这个民族和国家的人民来说是一个比掠夺他们一些土地和粮食更为痛苦的事情,必然触及其心灵深处。[12]88-89羌族的一些有识之士曾经多次要求羌语进课堂,茂县也确实编写了一套简单的羌语教材,但小学羌语课时断时续得不到稳定的支持,而有关专家在阿坝师专筹建羌语相关专业的努力也始终未能成真,这些都让羌族的知识阶层非常受挫。与此同时,毗邻地区的藏族人把羌人的语言遭遇看作是藏语的前车之鉴,不断致力于捍卫藏语的尊严和地位。虽然藏语是学校语言,但很多公立学校不断扩大藏汉双语教育的规模和汉语的使用比例,相比全藏语的寺庙学校而言,汉语被看做是对藏语纯洁性和社会地位的公然挑战。以汶川县水磨中学为例,学校升国旗仪式上,发言的师生都被要求使用普通话,校报《萌芽》也暂不接受藏文作品,英语等科目均使用汉语授课等等。类似问题被认为是对少数民族的歧视,而一旦这种语言上的文化问题发展成文化上的政治问题,就变得非常敏感和棘手。
如果说国家是一个政治共同体,那么民族就是一个文化共同体。在国家机器的强势姿态下,各个文化共同体可能会在相互交流中产生妥协与融合,并产生新的共同的文化认同,我国的汉族就是由多个民族在数千年的妥协与融合中产生并不断发展壮大的,而且各少数民族对更高层次的“中华文化”也是持肯定态度的。当然了,各种文化共同体并不总是能够达成妥协,特别是对那些有着自己的语言文字、宗教信仰等完整文化体系的民族来说,妥协是很困难的,而对于只有语言没有文字的羌族人来说,语言上的妥协几乎同时意味着更深层次的价值观念和传统经典的消亡,如果不能尽快找到新的文化认同,其后果将会非常严重。于是毗邻藏区的羌人选择了藏语认同,毗邻成都平原的羌人选择了汉语认同。但是别人仍然称他们为羌族人,也就是说他们并没有真正被接纳为藏族或汉族,而更糟糕的是作为羌族人的民族身份归属感又不如毗邻的以汉语为母语的回族强烈,民族个性的消逝和民族身份认同的焦虑不断袭扰着敏感的神经。
羌在藏汉之间,这不仅仅是羌族文化的一大特色,而且还对汉文化向藏区的传播起到了一个缓冲乃至过滤的作用,因此历史上藏区很少直接与中央政府发生宗教、文化或者政治冲突。然而羌族聚居区的迅速“汉化”导致这个缓冲地带也迅速消退,这让毗邻藏区感觉到了本族传统文化的纯正性和传统“领地”面临的直接威胁,好事者甚至利用羌族“被汉化”的问题在毗邻藏区煽动和鼓吹民族“复国主义”情绪,他们对“被汉化”的羌族乃至回族越来越没有好感。因此越靠近羌族聚居地,藏族人的语言和文化焦虑就越明显,捍卫本族语言和文化的决心就越大,行动也越多。此外,藏族是一个全民信教的民族,羌族释比的遭遇对藏区宗教界是一个很大的刺激;而且过去中央对藏区的统治多以封王“自治”为主,新中国打破了藏区原来的利益格局,旧的统治阶级不甘失败,一直妄图追溯失去的既得利益,加上外国敌对势力从中作梗,各方面综合因素最终导致藏区局势的紧张。
文化安全问题也体现在国民教育体系安全上。对任何一个现代国家、民族而言, 本土精神的沿续和传统文化的继承主要是通过国民教育体系和媒介宣传两大渠道完成的。[13]14但是,当前少数民族地区的学校教育越来越趋向于国家文化而不是乡土文化,语言上越来越趋向于国家通用语而不是方言或者少数民族语言,媒体越来越趋向于中西方流行文化而不是传统文化,这些都对地区文化安全构成了潜在威胁。随着国内语言安全研究的深入,国家已经开始着手有关语言教育的改革,其中包括强化国语和国家传统文化的学校教育,纠正英语过分狂热的问题。但是这样的改革尚未涉及到少数民族语言的生存和发展。此外,虽然少数民族文化已经成为旅游开发的一个新热点,但相关的努力同样也不包括少数民族语言的保持(language maintance)。
小语种对于国家安全的意义远远超过人们的想象。美国二战期间曾用纳瓦霍( Navajo) 语编制了一套密码,并征召纳瓦霍人担任相关情报和通讯工作,敌人一直未能破译。我国自卫反击战期间,“兴化通讯连”也曾用晦涩难懂的莆田话作为工作语言,有效避免了前线无线通讯信号屡屡被越军识破的危险。然而,西方国家的关键语言策略和我国的汉语国际化推广工作已经让我们失去了过去的汉语语言屏障,甚至汉语已经被作为战略武器反作用于中国自身。 如果一个国家文化无险可守, 那就会变得非常危险[14]13,在此大背景之下,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的保持和作为国家语言战略屏障的作用就显得越来越重要。更何况对少数民族人民来说,学习族语还可以满足民族认同和寻根的基本需求,也是保持民族文化和增进民族团结的重要途径,同时还为国家保留了重要的语言资源。
当然了,我们在强调民族语言保持的同时并不排斥国家通用语。少数民族学习国家通用语可以共享国家资源,参与国家建设,有利于国族身份构建和国家认同的形成,同时也可以消减语言差异带来的不安,加强地缘政治意识等等,因此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国家通用语和民族语的双语教育一直都是世界各国通行的做法。但是,忽视民族语言基础上的国家通用语教育很容易被敌对势力借题发挥,他们用“驯化”、“民族同化”之类的字眼蛊惑不明真相的群众,甚至很多基层教师也接受了这种观点,这是非常危险的,会直接导致教育教学过程中的方向性错误,并在学生心目中留下民族歧视的刻板印象。事实上四川阿坝有些双语学校就曾爆发过激烈的冲突,汉族师生被赶出校园,这就证明语言问题是有可能导致政治冲突的。
文化安全的其他方面,无论是价值观念、意识形态,还是风俗习惯、生活方式,都没有像语言文字那样成为一个国家文化中最稳定的要素。[15]尽管没有自己文字的羌族对民族文化的坚守并不如其他少数民族强烈,羌语转换到目前为止也没有出现过分突出的意识形态危机或者直接相关的社会动荡,但这并不能说明语言转换及其转换速度就为大家所欣然接受,至少他们的内心世界存在着这种焦虑,并且随时都可能导致矛盾激化,更何况我们还应当观照周边其他少数民族的感受。至少,从不够健全的羌汉双语教育到羌语课完全被取缔,这件事本身就足以让其他接受民汉双语教育的少数民族感到不安,更有居心叵测者质疑国家的民族政策,从而将一个教育上的学术问题扩大为政治问题,成为地区文化安全和政治稳定的一个不确定因素。
简而言之,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是互为支撑的,国家认同往往以民族认同为前提,而且强烈民族认同基础上的国家认同才能更坚定、更持久。当前四川阿坝藏、羌、回、汉多民族杂居区的语言之争越来越激烈,而地方教育主管部门又恰恰缺少这样的学术高度和文化认识,更多的往往是从政治稳定的角度处理问题,反而帮助敌对势力把语言上的教育问题演变成了一个文化上的政治问题,让这一学术和文化问题的政治气氛越来越浓,越来越难以驾驭。笔者也曾尝试将这一问题回归到学术的范畴,并开展乡土文化进课堂的教改实验,让藏族师生共同参与带有学术性质的讨论,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成功实现了政治话题到教育话题的转变,大幅度消减了民族师生(主要是学生)的对立情绪。但是,单独一门课程的努力显然不足以完全化解如此复杂的局面,更深层次的学术探讨和教育教学改革势在必行。
结束语
通常情况下少数民族对语言权利的要求都会被认为是民族自我中心主义思想膨胀的表现,往往被打上民族主义的标签而受到各种形式的抵制,而地方政府、基层学校和教师把政治稳定作为第一要务又进一步刺激了民族主义思想的产生和膨胀。前南斯拉夫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语言的长期较量和冲突就成了国家分裂的两大元凶之一。我们并不能坐等少数民族自己主张语言权利,因为这种情况一旦发生,往往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相反,我们必须通过细化的立法确保少数民族语言的教育和传播权利,并在教育梯次结构、文化产品输出和经费保障等方面予以全面支持。一旦少数民族看到了国家在保障民族语言权利方面的努力和成效,其民族和国家认同感才会得到持续有效的巩固,而在此基础上为促进国内经济文化交往而实施的民汉双语教育也才能为大家所真心接受。
[1]叶小军.灾后复课需要理性的凸显[J].中国科教创新导刊, 2009,(29).
[2]叶小军.羌语保持的语言人类学思考[J].黑龙江民族丛刊, 2012,(6).
[3]北川羌族自治县概况编写组.北川羌族自治县概况[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
[4]陈海英,魏烨.试析英语语言中的政治意识[J].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4,(4).
[5]徐有志.语言•方言•语域[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2,32(5).
[6]陈原.语言与社会生活[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
[7]何俊芳.语言人类学教程[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5:177.
[8]Colin Baker.双语与双语教育概论[M].翁燕译.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8.
[9]王宁,孙炜.论母语与母语安全[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34(6).
[10]戴曼纯.国家语言能力、语言规划与国家安全[J].语言文字应用,2011,(4).
[11]王宁,孙炜.论母语与母语安全[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34(6).
[12]刘跃进. 解析国家文化安全的基本内容[J].北方论丛, 2004,(5).
[13]潘一禾.当前国家体系中的文化安全问题[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35(2).
[14]李克勤,朱庆葆.加强语言战略研究,确保国家文化安全[J].汉语学报,2009,(1).
[15]刘跃进.国家安全体系中的语言文字问题[J].语言教学与研究2011,(6).
[责任编辑龙倮贵]
A study of Qiang Language Shift and the Effect on Regional Cultural Security
YE Xiao-jun
(Aba Teachers College,Wenchuan623002, China)
The ethnic identity anxiety becomes more and more obvious during the language shift of Qiang, which has been spread to the neighbouring areas. From the Qiang-Han Bilingual Education to the cancellation of Qiang language course, the Qiang ethnic cannot find the future of their native language, due to which the Tibetan in the neighbouring area begin to worry about their own Tibetan-Chinese bilingual education, not mention hostile forces seize the chance to question the national policy. Meanwhile, the local governments are obviously short of wisdom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language education, but to take the political stability as the priority. When the academic issue was boosted into a cultural political one, the regional cultural security became complicated and uncertain.
Language shift;Qiang ethnic;Tibetan;regional cultural security
H2
:A
:1008-9128(2014)04-0005-03
2013-12-16
叶小军(1975—),男,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民族文化,中西方跨文化比较,英语教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