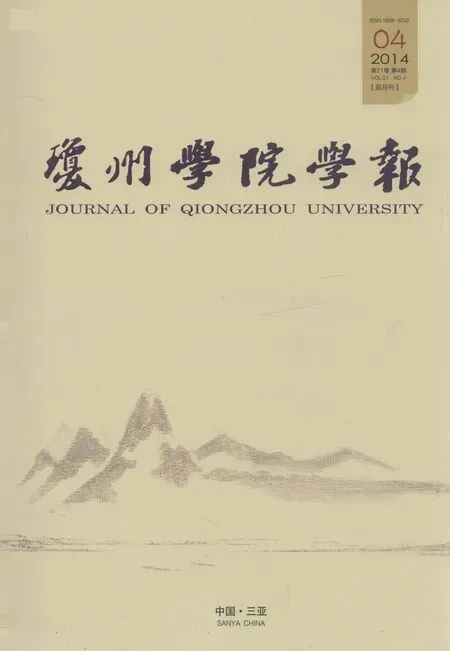清人批评沈德潜辨析
2014-04-07叶雪竹
叶雪竹
(安徽师范大学 文学院,安徽 芜湖241000)
沈德潜,字确士,号归愚,历经康、雍、乾三世,是乾隆时期执掌诗坛的盟主,在清代中期占有重要地位。纵观德潜一生,其诗歌上的贡献主要在创作和批评两个方面:创作有《归愚诗钞》五十八卷和《归愚诗钞餘集》二十卷;批评主要是其诗学专著《说诗晬语》和诗歌选本如《唐诗别裁集》《古诗源》《明诗别裁集》《清诗别裁集》《宋金三家诗选》等,归愚一生致力于诗歌创作和诗歌批评,并取得成就,受到时人好评。如郑方坤《国朝名家诗钞小传·竹啸轩诗钞小传》:“归愚积学工文,古文辞跌宕夷犹,谨守尧峰家法,无敢逸出范围。……所选有《古诗源》《唐、明诗别裁》行世,横截众流,独标心印,诚谈艺家之金丹大药也。”[1]2228徐珂《清稗类钞·文学类》盛赞归愚,诗家大宗“不能不推德潜”“大率皆唐人之是学,未尝及德潜门,而实受其影响者。”[1]2235周春《耄馀诗话》卷一叙其授业于德潜,夸赞德潜“待人和蔼,一出于诚”[1]2239。然而,清人对沈德潜的评价差异很大,也有许多批评其诗歌成就的言论,如文廷式《琴风餘谭》①这个评价主要是针对沈德潜所写“奉和”之诗导致“试帖诗”的滥觞而发的,可参看严迪昌《清诗史》(下),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628 页。:“本朝诗学,沈归愚坏之,体貌粗具,神理全无。”[1]2235汪国垣《论近代诗》:“沈则通体工整,无可读之篇,无可摘之句,勉诵一过,了无动人。”[1]2237此类批评,从着眼点看,可分为以下三个方面:“温柔敦厚”“规模特甚”“学古遗神”。
一、关于“温柔敦厚”
沈德潜倡导“温柔敦厚”的诗旨,把儒家传统诗教作为创作原则,主张人格为先,诗歌内容要言之有物,有所寄托,表现方式含蓄蕴藉,在其诗作和诗论中都有所反应。如《说诗晬语》上:“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真诗”[1]1910“凡习于歌声之道者,鲜有不和平其心者也”[1]1978。这是对诗人人格修养的重视;“陶公以名臣之后,际易代之时,欲言难言,时时寄托,不独《咏荆轲》一章也”[1]1928“讽刺之词,直诘易尽,婉道无穷”[1]1913,这是对诗歌含蓄蕴藉的重视。
针对归愚“温柔敦厚”的诗教,历来批评较多,尤以袁枚为重。他在《与沈大宗伯论诗书》中提到,沈德潜所云“诗贵温柔,不可说尽,又必关系人伦日用。此数语有褒衣大袑气象,仆口不敢非先生,而心不敢是先生。何也?孔子之言,戴经不足据也,惟《论语》为足据”,在他看来,“温柔敦厚”诗教未必是孔子的话,而《论语》中的“兴观群怨”说才是比较科学的论述,因而他主张诗歌要抒写真情,一定程度上是对沈氏诗教的反叛。不仅如此,袁枚也不赞成沈德潜把艳诗即爱情诗作为有违诗教、有伤风化的作品,他在《再与沈大宗伯书》中对“情”充分肯定:“情所最先,莫如男女。古之人屈平以美人比君,苏、李以夫妻喻友,由来尚矣。”清人中还有对沈德潜诗作“平正通达”的指斥,如谭献《复堂日记》:“横山主持诗坛,未昌其教,门下得沈文慤负朝野重望。乃横山体素储洁,而归愚多渣滓,则过求平宽之流弊耳。”[1]2233时人对“平正通达”的批判,只是被本质所隐藏的现象,而其根本则是对“温柔敦厚”的批评。沈德潜确有一些平正而乏精警之作,如应制诗和歌功颂德诗,主要集中在《矢音集》《南巡诗》中,《归愚诗钞》等也有一些,总共500 首左右,与其3200 首诗歌相比,只占六分之一的篇幅。①可参看王玉媛《沈德潜诗歌创作简论—兼论对沈德潜诗歌研究现状的感想》,载《合肥学院学报》,2013年第2 期,第63 -67 页。而与其山水诗、田园诗、怀古咏史诗相比,为数不多。
沈氏虽提倡“温厚和平”,不作奇诡语,不押险韵,导致其诗作过于平正,缺乏真气、真情,被后世诸家批评。但其持论并非完全囿于儒家传统诗教,他多次运用“情至”“至情”来品评诗歌,是其对传统诗教的突破。例如《说诗晬语》:“予最爱《东山》三章:‘我来自东,零雨其濛。鹤鸣于垤,妇叹于室。’末章:‘其新孔嘉,其旧如之何。’后人闺情殆源于此。又爱‘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依人,在水一方。’苍凉弥渺,欲转即离,名人画本,不能到也。”[1]1916归愚并非拘泥于名教,对其中的情爱描述,虽显得比较委婉,但寄托于言外的咏叹之情是显而易见的;而且归愚在其选本批评中也有类似关于“情”的言论,如《明诗别裁集》卷九评万历朝诗人徐熥:“七言犹能作情至语,在李庶子,郑都官之间。”[2]《清时别裁集》评陈恭伊《发舟寄湛用喈钟裴仙湛天石》:“如面诉友朋,婉转关情,情文并至。”[3]147评刘岩诗:“诗品发乎至情,不尚词华,世罕称述,予独珍重之。”[3]371评潘高《忆幼子》:“慈爱至情,委曲传出,无心学陶,去陶公未远”[3]154。以上观之,沈德潜论诗延续儒家诗教,要求诗作反映现实,有所寄托,但并不囿于道德伦理,而对诗歌本身的情感也给与肯定,虽然这种情感要关于人伦日用,与古今成败相关联,但不可否认,这是一种突破。
清人对沈德潜“温柔敦厚”的批评有其合理性,也有不足,因为沈氏倡“温柔敦厚”诗教是顺应历史时代的必然之举。其一,“温柔敦厚”历来是统治者维护封建秩序的道德伦理规范,但在明代中晚期却遭到要求个性解放的文学思潮前所未有的冲击。但随着明清易代之际,社会矛盾的激化,晚明文学新思潮迅速消退,正统文学思潮再度主导文坛。清中叶,德潜标榜儒家正统诗教有其现实必然性。其二,沈氏强调诗要以“温柔敦厚”为旨归,不仅要求诗歌有充实的内容,还要富于情感与美感的力量,如其用“情至”“至情”论诗,将其作为诗歌创作的重要原则,一方面是对儒家“温厚和平”中所蕴藉的现实性与艺术性的继承与开掘,另一方面也是对清代中叶,以袁枚为代表的缺少理性节制的“性灵说”的反驳与修正。其三,沈德潜确有一些歌功颂德,粉饰太平之作。但联系其遭际,一方面他并未经历明清易代,没有很沉痛的亡国之思,所以对清廷也没有仇恨心理,即使一些反映现实的诗作也不可能触及到社会制度的根本;另一方面,沈氏所处的时代,虽是太平盛世,但文字狱极其严重,所以文人也不敢畅所欲言,而且他的一些歌功颂德之作,确实是对那个时代盛世气象的描述,不应一笔抹杀。
二、关于“规模特甚”
沈德潜论诗不仅重内在思想层面,还重外在的审美形式,如《唐诗别裁集序》“既审其宗旨,复观其体裁,徐讽其音节”[1]1301;《七子诗选序》“予惟诗之为道,古今作者不一,然揽其大端,始则审宗旨,继则标风格,终则辨神韵”[1]1360;《重订唐诗别裁集序》“先审宗旨,继论体裁,继论音节,继论神韵,而一归于中正和平”[1]1997。这些体裁、规格、音节,外在形式方面的标准都是归愚所重视的,尤其在规格方面,他更是提出许多作诗的法度。
对于杜甫的诗作,他总结出“倒插法”“反接法”“透过一层法”“突接法”。[1]1938在用字方面,沈德潜认为要以平常语出新,如《说诗晬语》下:“古人不废炼字法,然以意胜,而不以字胜,故能平字见奇,常字见险,陈字见新,朴字见色。近人挟以门胜者,难字而已。”[1]1960而且并不只在新奇上下工夫,炼字要建立在“意”的基础上,不能刻意雕琢:“《鸱鸮》诗连下十‘予’字,《蓼莪》诗连下九‘我’字,《北山》诗连下十二‘或’字,情至不觉音之繁,词之复也。”[1]1916在字的运用上是主“意”也是主“情”的。用句方面,沈氏《说诗晬语》中论述较多,针对不同体裁,每一联都有其句法,如“起手贵突兀”[1]1941“入手须不平”[4]“中联以虚实对、流水对为上”[1]1941“三四贵匀称,承上斗峭而来,宜缓脉赴之;五六必耸然挺拔,别开一境。上既和平,至此必须振起也”[1]1941“收束或放开一步,或宕出远神,或本位收住”[1]1943“中二联不宜纯乎写景”,[1]1942对诗歌起句、尾句和中间有所论述,起句应给人一种出人意外之感,尾句要拓开境界,中间不宜平铺直叙,要极尽曲折变化。章法方面,沈氏主张一以贯之,注重篇章结构的完整。如“章法之妙,不见句法,句法之妙,不见字法”[1]1944;对于五言古长篇“必伦次整齐,起结完备,方为合格”[1]1924且“五言长篇,固须节次分明,一气连属。”[1]1933沈德潜比较认可的是气象浑融的上乘之作。沈氏也较欣赏有“声韵”之作,如“诗之以声为用者也,其微妙在抑扬抗坠之间。”[1]1909
沈德潜讲究诗法,不仅体现在其论诗专著中,其诗歌选本的评语也有涉及。《唐诗别裁集》评王维《观猎》:“章法、句法、字法俱臻绝顶,盛唐诗中亦不多见”[5]319;评杜甫《戏为双松图歌》:“突兀起不妨平接,如‘堂上不合生枫树,’下接‘闻君扫却赤县图’是也。平调起必须用谨语接,如‘天下几人画古松’下接‘绝笔长风起纤末’是也。学者于此求之,思过半矣”[5]215;评高适《送前卫县李采少府》:“情不深而自远,景不丽而自佳,韵使之也。”[5]442如《清诗别裁集》中评许缵曾《睢阳行》(卷三):“龙虎真人以法驱之,转受揶揄,得此一衬,接入汤公,倍觉有力,此文章烘衬法也”[3]49;评徐钟釚《十八滩》(卷十二):“极写滩声之可畏,中夹入岭猿一语,则险恶愈出,此加一倍法也。”[3]232
由于归愚论诗过分讲究规矩法度,遭致清时人“规模特甚”的批评,如余雲焕《味蔬诗话》批评德潜:“归愚论诗,专主格律,原本忠孝……规模狭小,声调短促,少变化,故词意多尽直,一览无餘。”[1]2236这是针对其讲究规格导致诗作无“言外之旨,味外之韵”所发的。尚镕《伯山诗话》以:“归愚才力之薄,又在渔洋之下,且格调太入套”[1]2232来批归愚过分讲求格调。朱庭珍《筱园诗话》:“沈归愚先生所为诗,平正而乏精警,有规格法度而少真气……绝无出奇生新,略加变化处,殊无谓也。”[1]2233“殊无谓”用词苛刻,相当严厉,在朱庭珍看来,沈氏诗作只可作为初学,诗歌选本只是学诗的入门指南,对其评价不高。
沈德潜作诗的确讲究法度,但其并非拘泥于法,他在论诗专著和选本批评中都强调“变法”。如《说诗晬语》:“若泥定此处应如何,彼处应如何,不以意运法,转以意从法,则死法矣。试看天地间水流云在、月到风来,何处著的死法”[1]1910“诗不学古,谓之野体。然泥古而不能通变,犹学书者但讲临摹,分寸不失,而己之神理不存也。”[1]1911《清诗别裁集》中赞美宋琬《狱中长至呈同系诸公》“三四是活对法”。[3]31归愚主法,但不泥法,且主张活法,同时他也对局守规格进行批评,如:《说诗晬语》:“谢茂秦古体,局于规格,绝少生气。”[1]1959不仅如此,他还把“体”“法”联系起来①参看段宗社《论沈德潜诗歌批评模式》,载《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33 卷第3 期,第378 -383 页。,在《答滑苑祥书》中,指出体法有“不变者”“至变者”,以此证明其并非守死法,而注重活法。
沈氏在其论诗专著和诗歌选本中多次提到规矩法度,不守死法,主张“变”法,可为何还会受到时人“规模特甚”的批评呢?其一,在归愚看来,体格风格在盛唐已经基本形成,只有向最高水平的汉魏、盛唐学习,才能创作出优秀的诗篇,为此他总结的指导创作的规矩法度,如《说诗晬语》《唐诗别裁集》《明诗别裁集》《清诗别裁集》《古诗源》等都是初学者入门的范本,被奉为圭臬,所以必然对沈氏的规模法度亦步亦趋,这对于主观性很强的诗歌来说,无疑扼杀其创新性,所以受到时人讥讽。其二,沈德潜虽反对“死法”,主张“活法”但在其诗作及选本中涉及较少,他仍然对有法度之作大加赞誉。如李白“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得归愚“起句高唱入云”之势,受到好评。杜甫《送重表姪王砅评事》篇:“‘上云天下乱’云云,‘次云最少年’云云,初不说出某人,而下倒补云:‘秦王时在座,真气惊户牖。’”[1]1938符合倒插法。所以后人对其在“规模特甚”方面的评价不无道理。
三、关于“学古遗神”
明清文学的复古派,发源于南宋的严羽,其《沧浪诗话·诗辨》篇:“推原汉、魏以来,而截然谓当以盛唐为法,虽获罪于世之君子,不辞也。”[5]5到明代得到全面的展开,“复古”“学古”一直是明代诗学比较突出的问题,七子派格调上学古,流于面目上相似;神韵派学习古人神韵,虽比七子派进步,但也只是从形似到神似,免不了似古人。清中期的沈德潜继承复古派的理论的同时,吸取其经验和教训,成为“传统诗学体系的再修正和总结”[7]511者。沈德潜也主张学古,“诗不学古,谓之野体”[1]1911。
清时人对沈德潜“学古”的批评较多,如洪亮吉《北江诗话·卷四》:“沈文慤之学古人也,全师其貌,而先已遗神。”[1]2230朱庭珍《筱园诗话·卷二》:“袭盛唐之面目,绝无出奇生新,略加变化处,殊无谓也。……门户依傍渔洋,而于有明前后七子之徒及卧子、竹垞诸公遗言绪论,亦多摭拾。”[1]2233在袁枚看来,七子派、王渔洋都是貌袭古人,没有自己的面目,“虽没有直接批评沈德潜貌袭古人,但他对七子派的批评可视为对沈德潜的批评”[6]。德潜一病在“袭”,历来为诗家批评较为严重。
沈氏虽学古,但反对字模句仿,如:“泥古不能通变,犹学书者但讲临摹,分寸不失,己之神理不存也。”[1]1911归愚反对模拟之同时,提出“作文作诗,必置身高处,放开眼界,源流升降之故,瞭然于中,自无随波逐浪之弊”[1]1911。不仅如此,沈德潜还对有沿袭雷同之作进行批评,如“李于鳞拟古诗,临摹已甚,尺寸不离,固足招诋諆之口。”[1]1958对于时人学宋诗,沈氏批评其并无学到宋人的学问,而仅仅学其皮毛,只求一些“字句对偶”及“曲摹里巷”之语。总之,归愚的学古言论是反对袭古仿古的。
沈德潜虽然主张学古,但在其诗论和选本中都有“学古而不泥古”的言论,那清时人对其“学古遗神”的评价缘于何?沈氏诗作中最有价值的部分应该是其反映现实的作品,这是他学习杜、白而来,在《归愚诗钞》中,这些作品大概有三十余篇,在一定程度上有对现实状况的反映,如:《食豆粥》叙写惨状:“连年山左荒,齐鲁一路哭。掘草剥树皮,形状如鸠鹄。夫妇两相弃,儿女无处鬻。”[1]123面对如此现实,沈德潜并不把矛头指向最高统治者,而歌颂“圣心遍抚绥”,批评“民愚聚鸦噪”,这不禁对其反映现实的诗作持怀疑态度,受到时人抨击。又如《宿八叉路》中,前面部分是对“四年三大水”惨况的描述,本可让人流涕,深感沈氏反映现实力度之广,但其笔锋一转,歌颂天子的圣明,“幸逢天子圣,赈贷得不死。即死已后时,感恩入骨髓”[1]139,言辞谄媚,极尽颂德之能事。再如《地震行》中记述陕西地震,使原本人民困苦的生活更加艰难,可这时沈氏又为统治者说话,“唯时宗周驰纲纪,天遣灾变相频仍。方今圣皇位九五,经济上下还清宁。”[1]168类似之作,比比皆是,这些反映现实的作品,与杜甫、白居易的力作有很大差距,根源在于其矛头不敢直指最高统治者,而杜、白指斥力度之深是其无法企及的。如杜甫《兵车行》讽刺唐玄宗好大喜功,《丽人行》讽刺杨国忠兄妹,《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又是讽刺挥霍无度的唐玄宗,导致民不聊生,生灵涂炭。白居易也和杜甫一样忠厚耿介,如其自己所说“不惧权豪怒,亦任亲朋讥”(《白氏长庆集·寄唐生诗》)他的新乐府“使权豪贵近者相目变色”(《与元九书》)而这些在沈德潜的诗作中是绝对不可能出现的,所以与其同时的洪亮吉敏锐的认识到沈德潜:“全师其貌,而先已遗神”,虽他也是学杜、白的现实主义之作,却遗失了其现实主义精神,保留了现实主义外皮。所以这种评价也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沈氏反映现实的诗作在其诗歌比重中所占甚少。而其他诗作,如写景诗,不乏清微幽远之作;咏史诗,借历史人物抒写自己坎坷经历,感喟兴亡等。因而不可把沈氏学古之作一概而论为“全师其貌,而先已遗神”。
结 语
对沈德潜的批评历来很多,不仅仅是清时人“中正和平”“规模特甚”“模拟蹈袭”的评价,近来也有不少,如“大量诗作雍容典雅,平庸无奇,为典型的台阁诗体”[7];“沈德潜的诗歌生涯空前地带有‘仰体圣意’的御用性,对诗这一运载心灵的事业损大于益,实无多可称处”。[8]
沈德潜的诗歌创作和诗学思想,是以儒家诗学的伦理价值为核心,继承七子派的“格调说”和王士祯的“神韵说”,最终确立的以人心教化为本,性情为先,兼容格调与神韵的诗学理论。沈德潜诗学思想的形成,是康乾时期平稳政治经济状况的必然反应,是知识分子从追求“内圣”到追求经世致用的主流文化选择,因而沈氏诗学观的形成具有历史必然性。但不可否认,归愚诗教说秉承儒家诗学思想,在伦理标准与审美原则的选择方面,沈氏诗学善的原则居第一义从而导致对美的原则的斫伤,表现一定的局限性。①批判者或是针对其诗作的一个方面,或是为宣扬自己的诗歌理论,但不能以偏概全,否定归愚诗歌和诗歌理论的价值和地位,应该知人论世,全面客观对待其人和诗,方公允。
[1][清]沈德潜.沈德潜诗文集[M].潘务正,李言,点校.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
[2][清]沈德潜,周准.明诗别裁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5:103.
[3][清]沈德潜.清诗别裁集[M].吴雪涛,陈旭霞,点校.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
[4][清]沈德潜.唐诗别裁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331.
[5][宋]严羽.严羽集[M].陈定玉,编.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
[6]张健.清代诗学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763.
[7]袁行霈.中国文学史:卷四[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320.
[8]严迪昌.清诗史:下[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6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