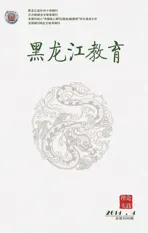《愤怒的葡萄》的生态批评探析
2014-04-07林意新
林意新,杨 悦
(哈尔滨理工大学,黑龙江哈尔滨150080)
美国著名小说家约翰·斯坦贝克的《愤怒的葡萄》讲述了以乔德一家为代表的农业工人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被迫流落到加州的故事,是对美国流动农业工人苦难生活的真实记载和社会斗争历史场面的生动再现,揭示了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表达了作家对生态危机深深地担忧和对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相处的美好愿望。它是一部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也是一部具有社会价值的重要文献,先后获得了普利策奖和诺贝尔文学奖。
一、生态批评
生态批评作为一种全新的文学和文化批评理论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文学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是其主要探讨的对象。美国生态批评主要倡导者和发起人彻丽尔·格罗特费尔蒂下的定义是:“生态批评就是研究文学和物质环境的关系,正如女性主义批评从性别意识的角度去审视语言和文学,马克思主义批评给文本阅读带来了一种生产方式和经济阶层的意识一样,生态批评对于文学研究采取的是以地球为中心的方法。”[1]
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生态环境逐渐遭到破坏,人与自然环境和谐相处成为我们关注的话题。在此情况下,生态批评彰显出强大的生命力,它用文学去重新审视人类文化并且进行文化批评,进而探索环境恶化和生态危机是如何被人类的思想、文化、社会发展模式影响甚至决定的。生态批评的理论活力和生命力是由它积极关注自然和人类的态度而凸显出来的。人类中心主义是生态批评主要关注的对象,被认为是当代生态危机的主要思想根源。生态批评不仅解构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而且构建自然生态价值观和绿色可持续的生活方式,从整个生态利益的角度出发,重建人与自然之间的新型关系。
二、《愤怒的葡萄》的生态批评解读
(一)人类中心主义
人类中心主义把人类看做地球上最核心或最重要的物种,借助人类的视角去评判现实的真实与否,即人类至上的思想。由于将自己看做最高级的存在,人类为了一己私利可以任意破坏自然环境和生态系统。作为一种价值观和尺度,它已根植于大多数人的心中,促使人们不计后果地任意掠夺和蹂躏大自然。20世纪30年代美国南部大平原的生态灾难就是在人类中心主义思想腐蚀下人们不顾后果征服和改造自然,对生态环境进行破坏所致。
《愤怒的葡萄》中有很多关于自然环境遭到破坏的描写。在小说开始部分,作家运用颜色描绘了干旱带来的持续性灾难:“地面结了壳,一层薄薄的硬壳。天空变成灰白,大地也跟着变成灰白,红色的原野变成了淡红色,灰色的原野变成了白色。”[2]斯坦贝克突出描写了俄克拉何马干旱少雨和强劲风沙的恶劣天气以及沙尘弥漫和庄家尽毁的生态状况:“风越刮越猛,在石头底下吹过,卷起稻草和枯叶,甚至还卷起小土块,在掠过田野的时候留下了它的痕迹。”[3]这些描写既表现了生态危机,也凸显了未来农民破产和流亡的悲惨命运。导致尘暴气候的原因是人类价值观的唆使,它形成于人类追求物质文明的过程中,而这种价值观归根结底就是在西方文化中长期处于统治地位的人类中心主义。美国农业工人就是秉承着这种思想对土地进行无情地掠夺和开发的。人类中心主义是一切生态危机的根源。
(二)人与自然的关系
人是自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是自然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与自然的命运是密不可分的。《愤怒的葡萄》通过揭露人与自然的矛盾来主张人与自然之间要建立和谐的关系。
美国的经济结构在20世纪30年代发生了巨大变化。大规模的现代机器被用在农业领域,逐渐使农业变得工业化。工业技术的极度发展促使了人类物欲的增长,先进的现代工业在造福人类的同时也引起了严重的生态危机。小说中俄克拉荷马平原曾是生活着几代人的沃野千里的大平原,却在人类改造下变成一片荒原。“慢慢地,土地变得梗结、贫瘠,天气持续干旱的时间越来越长,农作物很难生长,土地在铁的机器下受苦受难,在机器底下渐渐死去。”[4]农民难以继续在土地上耕作,不得不外逃去寻找新的生存地。可是当他们充满希望的来到加利福尼亚时,却失望地看到土地在那里被同样地利用和破坏。斯坦贝克在这里要表达的是,当人类对自然实施破坏,将自己的利益凌驾于自然之上的同时,必将遭受自我的毁灭。
斯坦贝克描写的大自然是充满活力和生命力的,他在辛辣谴责人类贪婪地破坏自然的同时,也向读者展示了大自然的美好。小说蕴含着对自然的歌颂和赞许,对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想之情。“阳光照射在草地上,草地暖洋洋的,草的阴影里有各种昆虫在活动……潮虫用许多细脚像许多犰狳一般慢腾腾地踱步。”“于是地面、洞穴、草丛里的生物渐渐开始活跃起来了……猎食的飞虫在头上无声地掠过。”[5]在这里,人与自然的关系覆盖着和谐与友爱,反映了作家对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向往。
(三)人与人的关系
小说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描写让读者更加充分认识斯坦贝克的生态思想。人们相互理解,相互依靠,团结一致,共同忍受困难和障碍,合作、互助、共享精神始终围绕着流离失所的人们:“由于他们又孤寂,又迷茫……他们便聚在一起,一起谈话;一起过着同样的生活,分享同样的食物,他们对于新的去处抱着共同的希望……到了晚上,奇怪的情形发生了:20家变成一家,孩子们都成了大家的孩子。丧失了老家成了大家共同的损失,西部的黄金时代成了大家共同的美梦。”[6]
斯坦贝克强调母性文化的重要性。小说中乔德的妈妈是主张整个自然世界团结和谐的母体文化的象征之一。在去加利福尼亚的途中,她的行为影响了许多人。她无私、友善、乐观、坚强,用勤劳的双手把家操持得井然有序,让家庭每个成员都能生活在和谐舒适的环境中。她用智慧和顽强帮助家人度过困难,同时也将爱心洒向所有经历苦难的人们。正如她所说的:“从前总是先照顾到自己一家人。现在不是这样了。对谁都是一样。日子过得越不顺当,越要帮别人的忙。”[7]罗撒香是小说中另一个突出的女性。她受母亲的影响,用爱心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虽然有孕在身,但她仍然帮助妈妈细心照料生病的奶奶,洗衣做饭,摘棉花,挣钱让家里宽裕一些。更令人感动的是,她承受着失去孩子的痛苦,却用自己的乳汁去挽救一个陌生的男人。
小说突出描写了破产农民的互助精神。素不相识的难民只要走在同一条路上,就会从具有相同痛苦经历的人那里得到支持和帮助。威尔逊和乔德一家结成联盟一同去西部,虽然途中遇到许多困难,但他们互相帮助,同渡难关。斯坦贝克饱含深情地赞扬了人与人之间团结、友爱、互助的精神品质,同时也讴歌了和谐的人际关系,表达他对人类和谐关系的期望和对美好未来的憧憬。
《愤怒的葡萄》无情地揭露了生态危机的根源是人类中心主义,尖锐地批评现代技术文明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同时也倡导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之间团结互助的人道主义精神,表现了他高度的生态责任感和对人类美好未来的憧憬和希翼。作为绿色生态主义作家,斯坦贝克表达了对自然生态系统受到破坏的极大愤怒、对人类命运的深切担忧和对人类未来的极大关注。在人类面对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和环境灾难的今天,斯坦贝克在《愤怒的葡萄》中体现的生态思想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1]Alexander,Charlotte. John Steinbeck's The Grape of Wrath. Beijing: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and Research Press,1996:3.
[2][3][5][6]斯坦贝克.胡仲持译.愤怒的葡萄[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1、5、15-16、221.
[4][7]斯坦贝克.刘红霞.译.愤怒的葡萄[M].天津:天津科技翻译出版社,2011:5-6、98.
[8]夏光武.美国生态文学[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9.
[9]陈凯.斯坦贝克与环境:跨学科研究结硕果[J].中国比较文学,20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