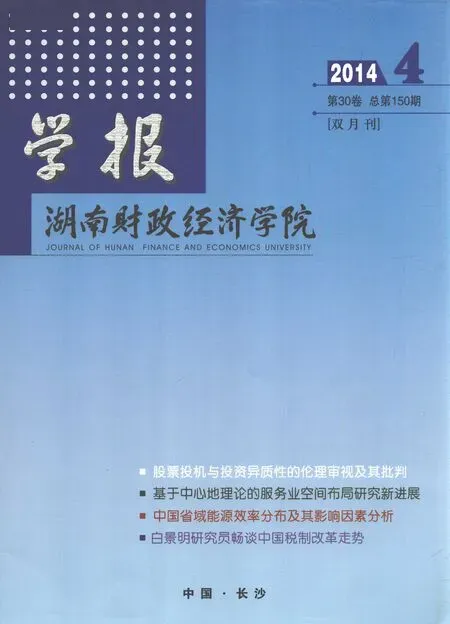遗产税与相关各税的关系研究
2014-04-07张永忠
张永忠
(江苏大学 财经学院,江苏 镇江 212013)
一、遗产税与所得税、财产税的关系
以往的理论一般笼统地把遗产税归类为财产税。但是,根据遗产税模式理论,遗产税有总遗产税、分遗产税和总分遗产税三种类别,而不同类别的遗产税属于不同的税类。
1、分遗产税
在三种不同类别的遗产税中,分遗产税是被最为广泛实行的一类,在征收遗产税的国家和地区中占比为74.5%[1]。所谓分遗产税,也称为继承税、相续税,是以继承人为课税主体,就各个继承人所分得的遗产分别征收的一种遗产税。显而易见,这种遗产税是一种所得税。因为这种遗产税是对继承人的征收,而继承人所继承的遗产是突然增富的一种,正是一种流量而不是存量,是一种纯收益,因此是一种所得而不是财产。由此可见,绝大多数征收遗产税的国家和地区虽然在观念上把遗产税视为一种财产税,但实际上实施的却是一种个人所得税。
由此要面对的质疑是,既然分遗产税是一种个人所得税,那么,为何不在个人所得税制中增设一“遗产继承所得”项目,而要单独设置遗产税,徒增人们的反感呢?这些遗产在被继承人作为所得而取得时已缴纳了个人所得税,现在又要求继承人缴纳同为个人所得税性质的分遗产税,这不是重复征税吗?同样是个人所得税,为什么分遗产税的扣除额却要远远大于一般的个人所得税?同样是个人所得税,为什么分遗产税却要区别遗产继承人与被继承人的亲疏等差,适用高低不同的差异税率征收呢?这表明,作为一种个人所得税,分遗产税制需要有特别的理由予以说明。
分遗产税,即继承税,更无法面对的质疑是:对遗产的继承应该征税吗?因为作为继承税的理论依据,边沁那种“遗产权是国家所赋予私人的,凡国家所赋予者,国家亦可随时收回之,何况抽一些遗产税”[2]的主张显然是危险的;而约翰·穆勒那种“没有人应当享受比他的相当独立生活所需要的财富还多的遗产”[3]的主张也是难以令人信服的。相反,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将自己身后的财产遗赠给后代是人所具有的正常感情和理智,是人的天性,是一种天赋人权,对其只能尊重和保护,不能灭除和剥夺;对遗产继承的征税是对成功者的惩罚,是对勤奋和节俭的打击,将抑制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削弱社会创造力[4]。事实上,这些不应该对遗产继承征税的理由,确实是无法驳倒的。由此说明,继承税,即分遗产税是不能成立的。而这又不仅意味着,需要说明分遗产税这种特别的个人所得税的理由,是根本不存在的,无论是把分遗产税归类为财产税,还是所得税,都是说不通的;而且也意味着无论总遗产税能否成立,遗产税的不同模式都是不存在的,遗产税的模式理论只是一种误识[5]。
2、总遗产税
所谓总遗产税,也被称为综合遗产税,是以被继承人为课税主体,就其遗留的全部遗产征收的一种遗产税。总遗产税的课税对象是被继承人遗留的全部财产,表面上符合一般财产税的特征,因此将总遗产税归类为财产税,似乎是有道理的,但同样要面对这样的质疑:既然总遗产税是一种财产税,那么,为何不在财产税制中增设一“遗产”项目,而要单独设置遗产税,徒增人们的反感呢?既然总遗产税是一种财产税,那么,这些遗产在被继承人生前已经被征收过财产税了,现在又要征收总遗产税这一财产税,这不是重复征税吗?同时因为总遗产税的课税主体是被继承人,必然还要面对这样的质疑:被继承人已经死亡,已经既无权利能力,也无行为能力,怎么能对死人征税呢?这表明,总遗产税的成立和税制的特别,都需要有特别的理由予以说明。遗产税的社会资源垄断论正可以提供这种特别的理由。
遗产税的社会资源垄断论认为,在一小部分国民的巨额财富中,有相当多的份额是其利用社会强势地位,对本应属于全社会的各种资源形成垄断而得到的,应该归还给全社会,不能遗赠给自己的后代,而能承担起这一归还角色的,非国家莫属,国家能据以完成这一归还任务的最佳方式,就是税收。这就是遗产税[6]。可见,遗产税的实质是“归还”,而财产税和所得税的实质,则是按两种不同的标准,对国家提供公共产品的费用进行的分配。在遗产税的征收中,国家只是巨富和社会其他公众之外的“替天(天下人)行道”者,是第三方,其身份是一般的社会管理者;而在财产税和所得税的征收中,国家则是公共产品交易两方中的一方,是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正是因为遗产税与财产税、所得税具有如此不同的逻辑基础,所以尽管被继承人的遗产在其生前已经征收过所得税和财产税,但在其死后仍要征收遗产税,而这绝不是重复征税,所以遗产税必须独立设置,而不能以增添“遗产继承所得”或“遗产”等所得税或财产税税目的方式,代替遗产税。
至于对死人征税,这正是遗产税的又一独特性。遗产税的实质是“归还”,是去世的巨富生前应承担的一种债务,同其他所有的债务一样,人死债不灭。因此,作为债务人的被继承人没有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并不是问题,并不影响遗产税这种债的索偿,更不影响其巨额遗产对这种债的偿还能力。至于由什么人完成遗产税的缴款手续,那更不是问题,反正有巨额的遗产存在,而遗产税这一债权优于继承权,不纳遗产税,不得继承遗产,自然有人急于拿到遗产税的纳税凭证。事实上,遗产税的征收恰恰以巨富的去世为前提条件,因为不要巨富在生前归还其占有的全社会的财富,而要其在死后归还,符合全社会的最大利益[6]。
综上,可做这样的推论:因为遗产税体现的只是作为巨富的被继承人与社会公众和国家的关系,与继承人无关,由此决定了总遗产税就是遗产税的唯一形式,因而不应该存在其他的形式或模式;因为国家据以征收遗产税与所得税财产税的身份根本不同,由此决定了遗产税具有独特性,其性质既不同于所得税,又不同于财产税,因而无论将其归类为所得税,还是财产税,都是不妥当的。
二、遗产税与印花税、契税的关系
有观点认为,历史上,遗产税、印花税和契税都发挥过确认产权转移的功能,遗产税曾以印花税的形式存在,契税则是中国原生的“印花税”,其中曾内含着遗产税。因此,遗产税与印花税、契税的关系密切。
遗产税原产于西方,确实曾发挥过确认产权转移的功能。比如,古代西方普遍流行土地等财产属于君王的观念,臣民占有使用的土地只及终身,要在死后归还给君王,如其后代想要继承,可以缴纳一笔资金,以行“归还”,由君王核准其继续占有和使用。这笔资金就是继承金,是较早的一种遗产税,是君王确认臣民继承土地的费用。
但是,遗产税曾以印花税的形式存在,这一说法却是不正确的。从很早开始,私有财产的不断增加,就将遗产税与遗嘱紧紧地联结在一起了。比如在古罗马,为求确保该税的征收,立法把它与遗嘱的开启挂钩,《关于1/20 的遗产税的优流斯法》规定继承人一般应于被继承人死亡后3-5日内将遗嘱代交税务处,在税务员前经半数以上的遗嘱见证人验视密封遗嘱的印章,然后启封,当众宣读遗嘱内容,并由税务员笔录遗嘱副本存档,交纳1/20 的税金,但是留给父亲和孩子的以及金额很小的遗产,免征。这招很绝,造成了不纳国税即不得继承遗产的效果[7]。而随着私有制的逐渐形成和不断深化,遗产继承中的纠纷越来越多,社会要求国家介入遗产的继承,对产权的转移发挥监督确认公证公示的重要作用。由此,遗产税与遗嘱挂钩的制度,便逐步演变成了所谓的另一种形式的遗产税——遗嘱检验税,并长期成为政府检验遗嘱合法有效,确认国民财产继承的费用。可能是从纳付不多、事关重大、民众乐于接受的早期遗嘱检验税中得到了启示,1624年荷兰人发明了印花税。这种税是对用于证明权利创设及变更的凭证征收的一种税,创立之初,由于缴税时是在凭证上用刻花滚筒推出“印花”戳记,以示完税,因此被命名为“印花税”。这种税征收普遍,负担轻微,手续简便,取轻用宏,被公认为良税。毫无疑问,这时的印花税具有确认产权转移的功能,而近代西方一些国家的遗嘱检验税便采用了印花税的形式。比如,1694年英国征收了遗嘱税,规定遗嘱中有遗产者须贴印花,方为有效,这实际上是一种印花税。由此可见,遗嘱检验税确实曾以印花税的形式存在,但遗嘱检验税却并不是一种遗产税。一是遗产税是对遗产的征收,而遗嘱检验税却是对遗嘱检验的征收;二是遗嘱检验税名为税,实为对遗嘱检验服务的收费。所以遗产税曾以印花税的形式存在,这一说法是不正确的。
不过,遗产税与印花税也不是一点关系都没有。毕竟一些国家,比如英国和美国,今天的遗产税就是从遗嘱印花税演变而来的。开征遗嘱印花税,民众更容易接受,而通过对其不断的改造,就能达到推行真正的遗产税的目的。其结果是,开征该税的目的一开始无疑是取得财政收入,但逐渐就变成了公平社会财富的分配,该税的性质则由普遍征收的遗嘱印花税,逐渐变成了只对死亡的巨富征收的遗产税,税率形式也由比例税率或定额税率变成了超额累进税率。这样,近代以来,遗产税也就与印花税渐行渐远,到如今,遗产税成为“巨富死亡税”,而印花税则是“权利凭证(理论上包括遗嘱)税”,两税各司其职,互不相干。
契税原创于我国东晋时期,是国家对民间所订的契约课征的一种税。古代契税的课税对象是奴婢、马牛、田宅等较为重大的买卖契约;其税缴纳要经过呈契、验契、纳税和盖印四个程序;纳税后要将所获契税单证粘连于契约尾部,与原契合二为一,作为原契已依法投税成立的证明,是为契尾制度,颇似西方的印花税贴花方式。古代契税同样具有使契约合法化、受国家保护和公示等确认产权转移,从而“省词讼,清税赋,有助于财计”的功能,因而确实是中国原生的印花税。更值得注意的是,南宋法律规定遗嘱继承必须投契纳税,并设有专门的机构和程序进行有效管理和征收专门的遗嘱税。《宋史》卷一四七《食货志上二·赋税》载:“绍兴三十一年……凡嫁资、遗嘱及民间葬地,皆令投契纳税,一岁得钱四百六十七万余引。”四川总领王之望曾解释这样做的目的是:“委可杜绝日后争端,若不估价立契约,虽可幸免一时税钱,而适所以启亲族兄弟日后诉讼。”[8]这就是说,在中国古代存在过遗嘱税这种所谓的遗产税,而且是专门的一种税,由专门的机构,以专门的程序,对其进行有效地管理和征收。但这种遗嘱税却仍然只是对遗嘱这种契约或权利凭证的征收,仍然只是一种契税,或今天的印花税,而不是真正的遗产税。因此,如果说契税是中国原生的印花税,无疑是正确的,但如果说中国契税中曾内含着遗产税,则是不恰当的。
另外,尽管我国现行的契税在制度设计上并不存在明显的缺陷,但我国当前税制中契税与印花税并存。契税以转移的土地、房屋权属为征税对象,向取得土地使用权、房屋产权等的产权承受人征税,税率为转让价格的3%-5%。印花税“产权转移书据”的征税范围包括财产所有权转移书据,税率为0.5‰。也就是说,契税的税基与印花税“产权转移书据”的税基重叠而税率高出100 倍[9]。显而易见,印花税是对各种权利凭证的普遍征收,而契税仅是对土地、房屋产权转移的权利凭证的征收,将契税并入印花税,势在必行,而在今天,作为对一切用于证明权利创设及变更的凭证普遍征收的税种,印花税应该对任何人,无论穷富,所立的遗嘱和继承遗产的产权凭证征收,同时,作为一种对社会公众财富的归还方式,遗产税应该对去世的巨富,就其巨额的遗产征收。由此,印花税和遗产税各自便能为社会的和谐发挥重要作用。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在今天,无论是遗产税,还是印花税,抑或是契税,既不再发挥确认产权转移的功能,也不再具有规费性质,或者说,都已经成为无条件的义务。因为,土地继承金这一形式的遗产税早已退出历史舞台。还应该能想得到,遗嘱检验税这一制度实行的长期结果,既可能使国家陷于私人家庭纠纷不能自拔,又可能使国家热衷于收费而怠于履行其职责,还可能使国家对私人遗产继承过多过深地干预。这使双方都不满意,使遗嘱检验税难以为继,而这正是征税权参与遗嘱检验的必然结果。这一法则同样适用于原初意义上的印花税和契税。事实上,奥地利政府在1854年便推行了纳税人自贴印花税票的纳税方式,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认同和效仿。这意味着,国家征收印花税不再需要提供什么特别服务。我国契税的发展史反映了同样的规律。今天的遗产税和印花税的征收不仅不需要国家提供特别的服务,而且现代一些国家还以法律规定,不纳遗产税者不得继承遗产,不贴印花税票的应税凭证不具有合法性,以此强制遗产税和印花税的缴纳。当然,我们的社会仍然需要由权威机构进行遗嘱检验。
综上分析可知,尽管遗嘱税与印花税、契税有一定的渊源关系,但不是真正的遗产税,现代的遗产税与印花税和契税均不相干。
三、遗产税与消费税、关税的关系
为了防止巨富以生前赠与的方式逃避遗产税,世界各国开征了赠与税,一些国家还开征了隔代转移税,以与遗产税相配套。但是,如果仅有这些辅助税种的配套,遗产税仍将在事实上鼓励巨富生前大肆挥霍,少留或不留遗产。而这意味着,大量属于社会公众的财富也将被浪费,不能得到归还。为此,就需要消费税、关税发挥与遗产税的协同配合作用。
一般而言,消费税是对消费征收的各种税的总称,包括消费支出税和消费品税。其中,消费支出税是对消费者的支出征收的一种税,亦称综合消费税,是个人所得税的一种转化形式[10]。消费品税是对消费者消费的货物和劳务征收的各种税,包括一般消费税和特别消费税。一般消费税是对货物和劳务普遍征收的各税种,如世界各国征收的增值税、货物税、销售税、营业税、关税等,特别消费税是在征收一般消费税的基础上,选择部分特别的货物和劳务征收的一种税,如中国现行的消费税(尚未对劳务征收)。
从理论上讲,消费支出税能以超额累进税率,较好地识别巨富的消费行为,对其消费支出,尤其是对其个人及其家庭的消费支出征收高额税收,但问题是,消费支出税只是一种理想,似乎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真正实行。而一般消费税在世界各国普遍征收,但因其普遍征收,对消费物品不加区别,无法识别巨富的消费行为,不能对其征收高额税收。因此,不论是消费支出税,还是一般消费税,对巨富生前大肆挥霍以逃避遗产税的行为,都难以有所作为。
特别消费税,是在征收一般消费税的基础上,选择一些特殊的消费品和消费行为,对其分别采用不同的税率,进行征收。在这些特殊的消费品和消费行为中,顶级的奢侈品和奢侈行为的消费对象非巨富莫属,与其他消费者无涉。因此,通过顶级的奢侈品和奢侈行为,就可以方便地识别消费者中的巨富,对其征收高额的特别消费税,从而较好地配合遗产税,解决巨富大肆挥霍的税收问题。所以这一特别消费税对遗产税的配合作用,可称为顶级的奢侈品和奢侈行为的征税问题。
对顶级的奢侈品和奢侈行为征税,之所以使特别消费税能较好地配合遗产税,解决巨富大肆挥霍的税收问题,是因为作为遗产税潜在的课税主体的巨富,一般同时是消费顶级奢侈品和从事顶级奢侈行为的巨富,对这些巨富的大肆挥霍征收高额的税收,就是对那些以少留遗产或不留遗产方式逃避遗产税的巨富的高额征税,使其在生前便归还应属于社会公众的财富。特别消费税的这一归还方式,比起遗产税来,只是更早的归还,而不是不归还。当然,对于那些极少数生活节俭,不事奢侈的巨富,特别消费税对奢侈品和奢侈行为的征税对其无能为力,但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巨富对社会公众财富的归还,有遗产税就足够了,不用特别消费税发力,而且这些巨富的节俭行为,能提高全社会的福利,因而应该是税法所鼓励的。至于巨富的慈善捐赠行为,尽管也会减少遗产,少纳遗产税,但这种行为同特别消费税对顶级的奢侈品和奢侈行为的征税一样,也是对社会公众财富更早的归还,而且这种行为不仅能解决社会急难,而且能使巨富得到社会的特别尊重,激发其更大的创造力和更高的慈善捐赠热情,因而同样应该是税法所鼓励的。
也许会有这样的疑问:经济学常识告诉我们,奢侈品的需求价格弹性大,即价格的轻微变动会引起需求量很大的变动,而对奢侈品的征税必然导致价格的提高,既然如此,特别消费税对顶级的奢侈品和奢侈行为的高额征税怎么可能?这是因为:由于财富的极大丰裕,(巨富)这一类人群对奢侈品的欲望与要求几乎完全不受其支付能力的限制和约束,因此,他们是不存在消费可能性曲线的。对他们而言,奢侈品消费已不仅仅是财富的堆积和社会地位的象征,更多的是一种生活方式和生活格调。在他们的眼中,所谓的奢侈品其实就是必需品,因而其消费极具刚性,价格已不是其关注的重点,而价格的变化对其实际财富的影响也可以忽略不计。所以,即使对奢侈品课税导致商品价格上升,顶级富豪们的消费行为也几乎不会受到任何影响。[11]也就是说,奢侈品的需求价格弹性对拥有不同财富的人是有区别的,对于一般人,价格小幅度的提高都会引起需求量很大的减少,需求价格弹性确实比较大,但对于巨富,其弹性则为零,甚至是只买贵的,越贵越买。正因如此,特别消费税对顶级的奢侈品和奢侈行为的高额征税才成为可能;同时,对顶级的奢侈品和奢侈行为征税,既影响不了价格,也影响不了巨富的行为。
顶级奢侈品的产地,只是极少数国家的屈指可数的几个地方。因此,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巨富消费的顶级奢侈品,基本都来自国外。为此,就需要关税发挥与遗产税特别消费税的协同配合作用。
关税也属于普通消费税,对进口商品普遍征收,但其区分货物品目类别分别规定的不同税率,同特别消费税一样,通过顶级的奢侈品和奢侈行为,就可以方便地识别巨富,对其征收高额的税收,较好地配合遗产税,解决巨富大肆挥霍的税收问题。因为进口商品一般均为不含税商品,即这些商品在出口环节已由出口国政府退还了前面各环节已纳的税款,关税则是进口国政府对进口商品应含税款的一次性补征。这就意味着,尽管巨富从国外购买了顶级奢侈品,但该商品应负担的税款却能够不受损失,从而也成为巨富对社会公众财富的一种更早的归还。因为巨富为顶级奢侈品花费的巨额价款毕竟为外国企业所得,巨富在国外的奢侈性消费的价和税更为外国企业和政府全得,造成了巨富未来遗产的减少,而应属于本国社会公众的财富部分并未归还,所以有必要为顶级奢侈品规定较高的关税税率,以便足额补偿。这也正是世界各国的实际做法。同时,世界各国对其进口商品应负担的一般消费税和特别消费税,都由海关利用其优势,在征收关税时一次代征,而这又意味着关税的征收能配合特别消费税的征收,保证巨富对本国社会公众财富的部分的更早归还。
四、遗产税与资源税、社会保障税的关系
遗产税自然不能被归类为商品劳务税,但前已论及,遗产税具有独特性,其性质既不同于所得税,又不同于财产税,无论将其归类为所得税,还是财产税,都是不妥当的。事实上,不仅仅是遗产税,资源税和社会保障税同样存在难以归类的问题。
也许是因为资源税是对资源的征税,即征税对象为资源,有些学者便把资源税归类为商品劳务税,但资源无疑不是劳务,而资源税是向从事资源开发和利用的人或单位的征收,此时的资源显然也不是商品,所以这种归类很难说得通。也许是因为我国现行资源税的计税依据为资源的销售收入,有些学者把资源税归类为商品劳务收入税,但看一看与其商品劳务收入税相对立的所得税、财产税,便可知销售收入作为计税依据,并不是此处划分税收类别的真正标志,而且资源税计税依据的真正特征是已开采资源的价值,而不是销售收入,所以这一归类同样是有问题的。也许是因为资源是一种自然财富,有些学者把资源税归类于财产税,但资源税的代际补偿价值和外部补偿价值显然无法涵摄于财产税的概念,可见资源税具有不同于财产税的本质,不能将其归类为财产税。也许是因为开采资源这种行为不同凡响,有些学者把资源税归类于行为税,但行为税这一概念本身就是问题。这一类税被认为是对纳税人特定行为征收的一类税,事实上,所有税种都是对特定行为征收的税,不独资源税,这意味着行为税没有分类学上的意义。正因如此,行为税的概念被越来越多的学人所抛弃。总之,资源税的归类真可谓众说纷纭,但都难以令人信服,这正说明了资源税的归类之难。
由于社会保障税的课税对象主要是工资薪金,所以一般将其归入所得税类。但是,这样的归类并不严格,因为对雇员或自营业者课征部分的课税对象是工资薪金所得或经营所得,而对雇主课征部分的课税对象并非其所得额而是其支付的工资薪金额。除了课税对象的特殊性外,社会保障税在计征标准及其管理使用制度等方面也与所得税有很大不同,因此,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税收分类中,社会保障税是作为单独的一类税。[12]
遗产税、资源税和社会保障税之所以都难以归类,是因为征收这三种税时,国家的身份都具有独特性。如上所述,遗产税的实质是“归还”。在遗产税的征收中,国家只是巨富和社会其他公众之外的“替天(天下人)行道”者,是第三方,是调节者,其身份是一般的社会管理者。而资源税的实质是平衡资源开采与生态环境补偿的利益,平衡当代人与以后各代人的资源利益,平衡资源开采企业与社会公众的利益,等等。在资源税的征收中,国家的身份则是与资源开发使用相关的各种利益的协调者,同样是第三方,同样是一般的社会管理者。社会保障税的实质则是国民为自己的健康、养老和生活中的风险而储蓄。在社会保障税的征收中,国家的身份则是庞大的全民储蓄计划的组织者,是储蓄者当前利益与未来利益的协调者,是年轻的在业者与年老的退休者利益的协调者,是出险者与未出险者利益的协调者,同样是第三方,同样是一般的社会管理者。但在一般各税的征收中,国家的身份则是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是公共产品供求双方中的一方,而不是第三方,是特殊的社会管理者。问题是,以往的税收分类,都是在国家以公共产品的提供者这一特殊的社会管理者的身份而征税这一框架中进行的,而遗产税、资源税和社会保障税却是国家以一般的社会管理者身份征收的,自然不在这一框架中。因此,尽管根据课税对象的性质进行的分类方法被认为是最能反映现代税制结构的分类方法,但仍然难以将遗产税、资源税和社会保障税归类于商品劳务税、所得税和财产税中的任何一种税类。这就如同南辕北辙的故事,搞错了行动的根本方向,马良,用多,御者善,不更使其离目的地越来越远吗?
在太多的方面,遗产税、资源税和社会保障税之间都大异其趣,很难讲相互有什么关系,但在国家据以征收的身份这一点上,三税竟然完全相同。这种同一性无疑可以充分说明国家征税身份的多重性,而这正是以往的税收理论研究所忽视的重要问题。国家以第三方、一般的社会管理者身份征收的税种具有众多相同的重要性质,比如,这类税种一般会形成基金,进行特别管理,不进入国家预算等等,很有必要深入研究。
鉴于现有的税种分类理论框架存在严重缺陷,应先根据国家征收身份的不同,将税种分为两类,一类为一般税收,另一类为特别税收。前一类为国家以公共产品的提供者、特殊的社会管理者的身份而征收的税种,后一类为国家以第三方、一般的社会管理者的身份而征收的税种。在前一类税收中,同一性质的税种较多,自然有必要进行税种的再分类,现有的分类方法在此时才能适用。在后一类税收中,税种应该不很多,但绝不止于遗产税、资源税和社会保障税,只是每一税种都应该很独特,性质相同的税种应该没有或极少,所以用不着税种的再分类。
另外,国家以第三方、一般的社会管理者身份征收遗产税、资源税和社会保障税的事实,给我们这样一个启示:在一些问题的处理中,我们通常会说某某财物或利益收归国有,这是有问题的。因为在这样的情形中,国家只是社会利益的调节者、平衡者、协调者,如果这时将其中的某某财物或利益收归国有,这无异于为两个小猴子分馅饼的那个老狐狸,故意一次次将馅饼分得不一样大,还故作公允,堂而皇之地一口又一口将别人的馅饼吃到自己的肚子里。这不是帮助别人解决问题,而是骗人自肥。如果将“收归国有”改为“收归社会公众所有”,一方面就能凸显国家作为社会利益的调节者、平衡者、协调者的单纯而公正的身份,而不再是骗人自肥者;另一方面并不改变国家对这部分利益的管理权,更重要的是能强化国家管好用好这部分利益的责任。
五、结语
遗产税与相关税种的关系是一个重要的视窗,从中不仅可以更好地认识遗产税的独特性,消除许多对遗产税的疑虑,而且还可以改变不少似是而非的税收观念,增强税收理论的科学性。因此,应该对遗产税与相关税种关系进行更深入更广泛的研究。
[1]刘 佐,石 坚.遗产税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61.
[2]李权时.遗产税问题[M].上海:上海世界书局,1930.8.
[3][英]约翰·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上卷)[M].上海:商务印书馆,1991.254.
[4]张永忠.遗产税与遗产继承无关论[J].税收经济研究,2012,(1):8.
[5]张永忠.遗产税模式理论为何是误识[J].地方财政研究,2012,(10):46.
[6]张永忠.遗产税的法理依据新论[J].兰州商学院学报,2011,(6):62.
[7]徐国栋.罗马人的税赋[J].现代法学,2010,(5):7.
[8]黄启昌,赵东明:从“名公书判清明集”看宋代的遗嘱继承[J].湘潭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3):39.
[9]饶立新.中国印花税研究[M].北京:中国税务出版社,2009.56.
[10]马国强.中国税收[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8.87.
[11]闻 媛.我国奢侈品税的政策效应分析[J].财贸研究,2007,(3):69.
[12]王国华,张京萍.外国税制[M].北京:财政经济出版社,200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