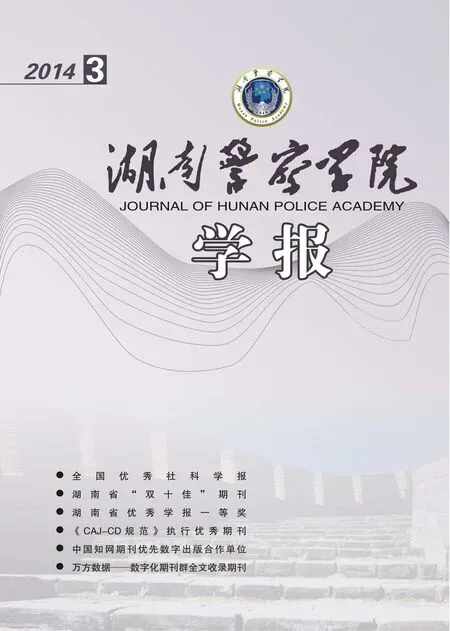网络诽谤罪的客观要件分析
2014-04-06霍俊阁
霍俊阁
(西南科技大学,四川绵阳 621000)
网络诽谤罪的客观要件分析
霍俊阁
(西南科技大学,四川绵阳 621000)
网络诽谤行为一直以来备受关注,其不仅涉及到宪法权利的保护,还涉及到刑法法益的保护。为了准确的打击犯罪,平衡刑法的法益保护机能与自由保障机能,我们首先应当对诽谤、网络诽谤的概念及其外延进行深入研究阐述,其次应对网络诽谤的罪量标准进行定位和具体认定,从而在司法实践中正确地认识和对待网络诽谤罪。
网络诽谤;客观要件;分析
随着网络的发展,我国的诽谤犯罪也延伸至网络中,特别是近期出台的关于网络诽谤的司法解释,更是把网络诽谤的热潮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对于网络诽谤的认定问题,我国刑法理论界的众多学者虽然相继发表了很多论文,但是,笔者认为,我国对网络诽谤的研究并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刑法理论研究还有待深入。理论研究的缺乏,司法实践的困境,网络的快速发展等等情况,无一不迫使我们更加深入的研究网络诽谤问题。为了不再发生诸如“韩兴昌诽谤案”、“彭水诗案”、“艾滋女案”之类的案件,我们应当对网络诽谤行为进行明确的界定,应当对网络诽谤的罪量标准进行实质性的分析。
一、网络诽谤的概念
用语具有不确定性、多义性等特征,我们在理解刑法条文时,首先应当考虑用语的常用含义,其次应当考虑用语在刑法语境中的含义[1]53。为了准确的认定犯罪,我们应当对网络诽谤的概念作出准确界定,使刑法所描述的行为既符合犯罪的形式构成要件,又保障刑法机能的发挥。认定诽谤罪时,必须明确该罪的实行行为,实行行为在认定犯罪性质、犯罪中的因果以及认定共同犯罪具有重要的意义。诽谤作为诽谤罪的实行行为,首先,我们应当明确“诽谤”的内涵和外延;其次,应当明确刑法规定中的网络诽谤的概念,这样才能保证刑法法益保护和自由保障机能的发挥。
(一)诽谤的内涵和外延
概念的内涵是指概念反映的的对象的本质属性和特征,外延则是指概念所反映对象的范围。我们要明确诽谤的概念,就必须掌握诽谤的确切内涵和具体对象的范围。
1.诽谤的内涵
网络诽谤是指借助网络等现代传播信息手段,捏造、散布虚假事实,损害他人名誉的行为。我国诽谤罪规定,“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情节严重的”构成诽谤罪,“诽谤”作为网络诽谤的实行行为无疑具有重要地位。然而,对于诽谤罪中的“诽谤”这一实行行为内涵的理解存在不同意见,具体而言,对“捏造并散布”这一行为存在不同认定。
有学者认为,“所谓散布是指采取某种形式以使第三人可能知悉此事实.....明知他人捏造的事实而故意散布,但并没有同捏造者形成共同犯罪关系的,也不应构成本罪,但可能构成侮辱罪”。[2]也有学者认为,“一般的诽谤,都有捏造和散布的行为,但有时没有捏造行为,也能构成诽谤,如道听别人谎言,明知其不实而又加以散布的,虽没有捏造,但因其散布行为同样给受害人造成名誉损失...故仍可构成诽谤罪。因此,对于捏造和散布,更应强调后者的作用”。[3]还有学者认为,“如果本人没有捏造事实,而只是有意或者无意地散布了他人捏造的事实,也不能构成诽谤罪”。[4]上述学者将诽谤罪中的“诽谤”或看作单一行为,或看作复数行为,他们理解的差异对于网络诽谤行为在理论上的认定,有着重要的影响。为了使得刑法条文的表述更能体现犯罪的实质,笔者认为应该从犯罪的本质即犯罪的法益侵害性出发,来理解“诽谤”的内涵。
笔者认为,该罪的实行行为即“诽谤”是单一行为,无论是捏造虚假事实并散布还是明知是虚假事实并散布,都是“诽谤”行为。即使刑法规定诽谤罪是“捏造并散布”虚假事实的行为,但是也不一定就说明该罪的实行行为就是复数行为。具体理由如下:第一,犯罪的本质是法益侵害性,刑法的任务和目的是保护法益;事实上没有法益侵害性的行为不能构成犯罪,当然没有法益侵害性的单纯的捏造行为并不能成为网络诽谤的实行行为[1]499。至于没有捏造而散布的,要区分故意和过失,这个是责任的讨论范畴,笔者在此不予讨论。“诽谤”作为诽谤罪的实行行为,只能是具有发生结果的一定程度以上的危险性的行为。明知是虚假事实而散布的行为,其法益侵害性并不低于捏造虚假事实并散布的行为,甚至其主观恶性要高于捏造并散布的行为,无论是从法益侵害性还是主观恶性,我们都没有理由否认明知而散布的行为不构成“诽谤”。第二,造成法益侵害具有紧迫危险性的行为是散布虚假的、损害他人人格和名誉的行为。例如,甲捡到一张纸条,上写“某高官乙于某年以抢劫罪被判刑入狱”,甲明知此事实是虚假事实,但是仍然通过网络向外散布,导致乙的名誉和人格遭受重大侵害。很难说,这一单纯的散布行为没有侵害乙的法益,对于甲的这种行为,明显应该以诽谤罪论处。这不仅说明没有捏造的散布行为同样侵害了诽谤罪所保护的法益,而且说明捏造行为只有加之于散布行为才具有刑法处罚的意义,才能称之为“诽谤”。第三,笔者认为,刑法条文中将“诽谤”解释为捏造并散布,只是为了将散布真实事实的行为排除在诽谤罪的构成要件之外,只是为了区分故意和非故意的行为。
因此,笔者认为,本罪中的“捏造并散布”并不是一个复数行为,捏造只是诽谤的前置行为,散布才是诽谤的最终实行行为,没有散布的捏造在刑法上毫无意义,但是没有捏造的散布却进入了刑法的视野。我们在认定网络诽谤行为的时候,要以法益侵害的紧迫性来判断某种行为是否属于诽谤的实行行为,在司法实践中要把网络诽谤行为与言论自由行为进行区分。
2.诽谤的外延
一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是反比关系,内涵越少,概念所包含的外延对象就越多。对于诽谤这一概念而言,我们明确了诽谤行为的内涵以后,还必须正确把握诽谤概念的外延。一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共同组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对内涵的把握离不开外延的支持,对外延的认识也需要内涵的指导。否则,我们就不免会陷入“白马非马”的争论中。
传统的诽谤在形式上可以分为书面诽谤和口头诽谤,而且在英美法系国家主要是这两种诽谤形式,即传统诽谤的外延是指书面诽谤和口头诽谤。书面诽谤是指,诽谤传播的方式是通过书定、印刷的文字,或以一些有形的或者物理的形式[5]。口头诽谤是指,诽谤以语言或者短暂的手势为传播的方式的一种诽谤形式。随着科技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诽谤的表现形式和外延已经超越了传统的诽谤分类,对于目前备受关注的网络诽谤,我们很难认定其是属于书面诽谤还是属于口头诽谤。一方面,在英美法系中,网络诽谤被归入书面诽谤一类。英国1990年的广播电视法规定:“对于书面诽谤和口头诽谤,在任何节目,包括节目服务活动中发布的信息,应当视为以永久方式发布的内容”。可见,在英国网络诽谤被定义为书面诽谤的一种。另一方面,网络诽谤的内容并非都是永久保存的,例如在论坛发带有诽谤性内容的帖子,在微博等平台发布诽谤性语言,等等这些诽谤性内容都可以被随时删除。这些富含现代元素的网络传播方式,使得网络诽谤的内容并非是以永久方式发布。因此,对于英国诽谤法的这一规定,笔者不能完全同意。
笔者认为,根据诽谤内涵的界定,网络诽谤无疑是诽谤概念的一个外延形式,网络诽谤是与书面诽谤、口头诽谤相并列的,一种新的诽谤形式。我们只有从实质上把握和理解了诽谤的内涵与外延,才能正确认定各种形式的诽谤行为,才能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丰富诽谤的外延。但是,我们也必须不断完善诽谤的内涵,以求将网络诽谤行为与网络言论自由进行严格的区分,达到平衡名誉权、人格权和言论自由权的目的。
总而言之,完善和限定内涵,是减少外延的必要途径,也是平衡刑法法益保护和自由保证机能的重要途径。我们必须对网络诽谤行为的概念进行确切的阐释和分析,必须把一般的网络诽谤行为与诽谤罪中的网络诽谤行为进行区分,必须严格坚持刑法的谦抑性和最后性。
(二)诽谤罪中的网络诽谤
由于语言的模糊性和开放性,使得同一概念在不同的语境中具有不同的含义,因此必须对刑法的网络诽谤作出符合刑法目的的解释。日常用语、民法、刑法上都有网络诽谤的概念,但是网络诽谤在不同的视野下却具有不同的解释。为了区分一般用语中的网络诽谤和刑法语境中的网络诽谤,为了区分刑法与民法语境中的网络诽谤,为了保护法益和保障自由的平衡,也为了维护刑法的正义性,笔者认为,我们应当坚持实质犯罪论的观点,即犯罪的法益侵害性,来解释刑法语境中的网络诽谤行为。
1.以法益侵害性为原则来区分网络诽谤行为
由于成文法的局限性和语言的特殊性,我们必须考虑同一用语在不同语境下的含义。刑法分则并不是完全由专业用语构成,而是大量使用了日常用语,所以,在解释刑法分则条文的概念时,必须采纳用语在日常生活中的含义。但是,有的用语在刑法上或者刑法学上具有特定的含义,可谓专业术语。在这种情况下,就不能按照用语的日常含义进行解释[1]53。同时,刑法的目的和任务是保护法益,犯罪的实质是对法益的侵害。因此,笔者认为,我们应当坚持法益侵害性原则,来区分一般用语中的网络诽谤概念与刑法诽谤罪中的网络诽谤概念。
笔者认为,刑法禁止什么样的行为,防止什么样的现象,是由刑法的目的和任务决定的。因此,对刑法中中具有违法性的犯罪行为的理解,必须以刑法的目的和任务为指导。刑法以保护法益为目的和任务,那么,刑法就只能把侵害或者威胁法益的行为规定为犯罪[1]340。对于诽谤罪中网络诽谤行为的认定也应当坚持法益侵害原则,在司法实践和理论研究中应当把刑法中与一般语境中网络诽谤的概念进行区分,只有这样才能限制刑法的处罚范围,保障言论自由和国民的预测可能性。
如果不坚持法益侵害性原则,将无法区分一般语境中的网络诽谤和诽谤罪中的网络诽谤,将会把没有法益侵害性或者自我侵害的行为认定为犯罪行为。是否坚持法益侵害性原则,决定着没有侵犯他人人格权和名誉权的网络诽谤行为是否构成诽谤罪。具体有以下三种情况:第一,对在网络上诽谤虚无人的行为如何认定,是否属于网络诽谤行为,是否构成诽谤罪。例如,甲在网络上诽谤虚无人乙,虽然事实确实充分,甲确实在网络上对虚无人乙进行了诽谤。如果根据一般语境中网络诽谤的概念,甲的行为确实属于刑法中的网络诽谤行为;如果按照法益侵害性原则,则甲的行为不属于刑法中的网络诽谤行为。第二,对在网络上诽谤自己的行为如何认定,是否属于网络诽谤行为,是否构成诽谤罪。例如,甲在某网络论坛发帖诽谤自己。根据一般语境中的概念,甲的行为属于刑法中的网络诽谤行为;根据法益侵害性原则,甲的行为并不属于刑法中的网络诽谤行为。第三,对得被害人承诺的诽谤如何认定。例如,甲经过乙的同意,在网上散布诽谤乙的言论。根据一般语境中网络诽谤的概念,则甲的行为属于刑法中的网络诽谤行为;根据法益侵害性原则,甲的行为不属于刑法中的网络诽谤行为。
我国刑法将诽谤罪编排在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一章,说明我国刑法规定诽谤罪是为了保护公民的人格权和名誉权,这也是学界的通说。因此,我们应当坚持法益侵害性原则,来理解刑法中网络诽谤的概念,将没有法益侵害性或者自我侵害的网络诽谤行为阻却在刑法的视野之外。
2.以法益的种类来区分网络诽谤行为
犯罪的实质是对法益的侵害或者威胁,但是,应当说,刑法与其他法所保护的利益都是法益[6]164。例如,公民的人格权和名誉权受到刑法的保护,在刑法中自然属于诽谤罪所保护的法益;但是,民法同样也保护公民的人格权和名誉权,其在民法上也是法益。刑法法益与其他法益的关系问题,其实就是是刑法规范和其他法律规范的关系问题。因此,民法所保护的法益,刑法可能也同样保护,但是,并不是所有民法所保护的法益,在刑法中都同样保护。可以看出,刑法法益和民法法益是有区别的,刑法中的网络诽谤行为与民法中的网络诽谤行为也是存在区别的。例如:刑法诽谤罪中并未将死者的人格权和名誉权列入保护范围,而民法将死者的人格权和名誉权作为诽谤侵权行为的保护对象。笔者认为,这是由刑法的谦抑性和最后性决定的,也是民主法治发展的结果。因此,为了限制刑法的处罚范围,为了保持刑法的正义性,我们有必要对诽谤罪中的网络诽谤行为与民法中的网络诽谤侵权行为作出区分。
网络诽谤行为只有侵害或者威胁的是诽谤罪的法益,才能是诽谤罪中的诽谤行为,否则只能是民法中的诽谤侵权行为,或者刑法中其他罪名内的行为。笔者认为,无论从刑法和民法的关系而言,还是从刑法的谦抑性而言,都不能将网络上诽谤死者的行为认定为诽谤罪中的网络诽谤行为。理由如下:第一,法益作为犯罪所侵害或者威胁的利益,必须具有可侵害性[6]164,死者的人格权和名誉权并不能受到犯罪行为的侵害。法益必须是在实际生活中能够被犯罪行为所侵害的利益,也就是说,诽谤罪所保护的人格权和名誉权必须是能够被网络诽谤行为所侵害的。笔者认为,人格权和名誉权不仅是社会对个人的评价,也是个人对自己地位的感知。名誉权和人格权是否受到侵害,应该由被害人个人作出自我评价。如果被害人客观上受到了诽谤,但是本人主观上并没有感觉到自己受到了诽谤,也没有因为诽谤而遭受损失,那么这种诽谤行为就不具有刑法中的法益侵害性。同样,死者并不能感知到自己的法益受到侵害,也不可能因被诽谤而受到人格、名誉贬损所带来的损害。第二,刑法中的人并不包括死人,死人的人格权和名誉权也并不属于刑法所保护的公民人身权、民主权利的范围。古典刑法理论的抽象刑法人理念认为,刑法中所谈论的人都是能够鉴别善恶、可以弃恶从善、有自由意志的社会一般人[7]。笔者认为,刑法中的人主要是指现实生活中的人,虽然刑法规定了盗窃、侮辱尸体罪来保护死者的利益,但是该罪的法益并非死者的人格权和名誉权,而是社会秩序。如果将通过网络诽谤死者的行为认定为刑法中的诽谤行为,不免会扩大刑法的处罚范围,违反国民的预测可能性。第三,从刑法的立法精神来看,诽谤死者的行为并不为刑法所规制。纵观刑法条文,我国刑法并没有保护死者法益的条文。一方面,即使是保护死者尸体的盗窃、侮辱尸体罪也是规定在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一章。另一方面,在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一章中,所保护的法益都是社会上真实存在的人的法益,也并没有包括死者的人格权和名誉权。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死者的人格权和名誉权并非刑法的保护对象,网络诽谤死者的行为并不是刑法中的网络诽谤行为。我们应当区分不同法规范中的网络诽谤行为,以保障刑法处罚范围的合理性和正义性。
二、网络诽谤的罪量标准——“情节严重”的地位
然而,并非所有刑法视野中的网络诽谤行为,都构成诽谤罪。我国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条规定:以暴力或者其他方法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根据刑法规定只有达到“情节严重”的网络诽谤行为才构成诽谤罪,因此,在明确了刑法中的网络诽谤行为以后,还应当对诽谤罪中网络诽谤的罪量标准进行阐述。笔者在此,首先就网络诽谤行为的罪量标准,即“情节严重”的地位作进一步阐述。
对于“情节严重”的罪量标准意义,学界和实务界都毫无疑问,但是学界对“情节严重”地位的理解却存在不同意见。在此,笔者就有关“情节严重”地位的不同观点,作以下梳理:
(一)构成要件否定说
有学者认为,诽谤罪条文中的“情节严重”并非构成要件,而是一种提示性的规定。理由如下:“第一,犯罪构成要件一般都提四个方面,还没有人把情节提作犯罪构成的第五个方面的要件;第二,就刑法规定的众多情节而言,有的属于客观方面,有的属于主观方面,还有的属于客体或者对象的,有的属于主体的。既然犯罪构成的四个方面都包含情节,我们就不应该把情节作为独立的要件;第三,刑法分则有的条款只是把情节作为区分同一犯罪中的重罪、轻罪的标准,显然不是构成要件”。[8]
笔者认为上述观点,并不具有合理性,上述否定观点对“情节严重”的理解存在偏差。理由如下:第一,笔者认为,我国的犯罪构成要件体系是认定犯罪的唯一根据,那么,犯罪构成要件所描述的违法性和有责性就必须能够达到值得科处刑罚的程度,否则,犯罪构成要件就不是认定犯罪的唯一根据。诽谤罪条文对罪状的描述并不能使行为达到值得科处刑罚的程度,一般的诽谤行为并不是刑法规制的对象。第二,我国刑法分则条文中,对于罪状的一般性描述不能使行为达到值得科处刑罚的程度时,就会增加某个要素,使客观构成要件所代表的违法性和有责性达到值得科处刑罚的程度[9]238。笔者认为,“情节严重”作为诽谤罪的整体评价要素,是为了说明行为的违法性和有责性在整体意义上达到了值得科处刑罚的程度。“情节严重”的违法性和有责性征表功能,决定了其作为构成要件要素的合理性。倘若否定“情节严重”的构成要件地位,则只能在诽谤罪的犯罪构成要件之外,寻找网络诽谤行为的违法性和有责性根据,这种做法势必将扩大诽谤罪的成立范围。第三,笔者并不赞同,否定观点中提到的“情节严重”作为独立于犯罪主客观方面以外的要件。笔者认为,“情节严重”中的具体情节也并非独立与主客观要件之外的,情节亦是主观和客观方面的情节。
(二)构成要件肯定说
也有学者认为,“情节严重”是构成要件。其理由如下:“例如,《刑法》对诽谤罪的规定,并不是任何侮辱、诽谤行为的违法性都达到了值得科处刑罚的程度。在认定行为是否构成侮辱、诽谤时,首先要考察行为人是否实施了侮辱、诽谤行为;其次,对诽谤的整体行为进行判断,得出情节是否严重的结论;……所以,情节严重这种整体的评价要素,也是一种构成要件要素”[9]240。
笔者认为,上述观点具有合理性,应当为我们所坚持。理由如下:第一,将“情节严重”作为犯罪构成要件,可以保持刑法的谦抑性和补充性,防止扩大处罚范围,能够保障公民的言论自由和国民预测可能性。第二,将“情节严重”作为构成要件,能够把行为违法性的根据限定在犯罪构成要件体系之内,更加符合刑法的正义性和罪刑法定原则。第三,上述观点把“情节严重”作为对诽谤行为的整体性评价要素,以行为的法益侵害性作为处罚根据,不仅符合刑法的主客观相统一原则,也符合社会的公平正义原则,和犯罪的实质特征。第四,将“情节严重”作为诽谤罪的构成要件,能够保持构成要件的开放性和简短性。不仅如此,“情节严重”的构成要件地位,还有利于刑法的稳定性和司法人员的认定事实的灵活性,有利于使刑法条文适应不断变化着的社会实际和生活需要。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应当将“情节严重”作为诽谤罪的构成要件,只有这样,才能使诽谤罪的认定符合刑法的基本原则和我国的立法精神,才能将并非“情节严重”的网络诽谤行为排除在诽谤罪之外,才能使言论自由权和名誉权保持平衡。
三、网络诽谤“情节严重”的认定
“情节严重”在诽谤罪中具有罪与非罪的机能,是诽谤罪重要的构成要件。因此,在明确了“情节严重”的构成要件地位以后,亟待解决的问题就是:任何认定网络诽谤犯罪行为是否属于“情节严重”?
(一)关于“情节严重”认定的分歧
“情节严重”如何认定?情节具体是指哪些情节?在理论界存在不同的观点。张明楷教授认为:“一旦采取以违法与责任为支柱的三阶层或者两阶层体系,就会认为,作为整体的评价要素的‘情节严重’中的情节,并不是任何情节,而是指客观方面的、表明法益侵害程度的情节”;[9]241陈兴良教授认为:“罪量既不同于罪体具有客观性,也不同意罪责具有主观性,就其内容而言是既有主观要素又有客观要素,因此是主、客观的统一,具有复合性。在罪量要件中仍然包含一些主观要素,例如‘情节严重’中的情节,就包括反映行为人主观恶性的情节”。[10]
笔者认为,刑法的目的和任务是保护法益,犯罪的本质是对法益的侵害或者威胁,诽谤罪中“情节严重”的情节应当是说明行为的客观法益侵害性达到值得科处刑罚程度的情节。因此,在认定“情节严重”时,应当首先从客观方面出发,坚持罪刑法定原则,如果行为的客观违法性即法益侵害性并没有达到“情节严重”,则不能认为该行为符合诽谤罪的犯罪构成。如果行为的客观法益侵害性,达到了诽谤罪中的“情节严重”,那么,要根据责任主义原则,进行进一步的判断,判断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具有非难可能性;如果没有非难可能性,则不能将该“情节严重”中的情节归责于行为人。
(二)关于“情节严重”认定的两阶层思考
笔者认为,对诽谤罪中“情节严重”的认定,应当分为两个阶层,第一阶层主要判断:网络诽谤行为在客观上是否具有严重的法益侵害性;第二阶层主要判断:能否将“情节严重”中的严重情节归责于行为人。根据罪刑法定原则,只有网络诽谤行为在客观上造成了严重的法益侵害,达到“情节严重”的程度;同时,根据责任主义原则,可以将该严重情节归责于行为人时,才能认定该网络诽谤行为构成诽谤罪。
在此,笔者对认定网络诽谤行为是否达到“情节严重”的两个阶层,具体阐述如下:
1.第一阶层:“情节严重”应当是客观法益侵害性严重
刑法客观主义犯罪论认为,刑事责任的基础是表现在外部的犯罪人的行为及其实害,或者说犯罪概念的基础、可罚性及其刑罚量的根据是客观行为及其实害[11]56。如果不坚持客观主义的犯罪论立场,将会出现刑法过度干预个人生活,造成大量的思想犯,进而侵犯个人的合法权利。在诽谤罪中,作为整体的评价要素的“情节严重”中的情节,并不是指任何情节,只能是指客观方面的表明法益侵害程度的情节[9]241。
笔者认为,我们在认定作为网络诽谤行为罪量标准的“情节严重”时,也应当坚持客观主义犯罪论,严格按照法益侵害性和法益侵害的程度来进行认定。然而,我国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在认定网络诽谤行为时,却存在不合理之处。
一方面,就刑法理论而言。笔者认为,传统刑法理论在认定“情节严重”时,存在不合理之处。根据传统的刑法理论,认为主观恶性和客观危害性是相加关系,如果主观恶性和客观危害分别没有达到情节严重,但是二者相加达到了情节严重,则构成诽谤罪。笔者认为,认定“情节严重”,应当仅仅考虑行为的客观法益侵害,而非考虑犯罪人主观恶性及主观方面的动机、目的等要素。如果行为人主观上具有诽谤他人的恶劣动机,客观上并没有造成严重后果,不具有侵害法益的严重性,则不能认定为“情节严重”。反之,如果行为人并没有主观的恶劣动机,但是客观上造成了严重的法益侵害结果,则应认定为“情节严重”,至于是否构成诽谤罪,则是责任的范畴。
另一方面,就司法实践而言。笔者认为,我国现行司法解释关于网络诽谤行为“情节严重”的认定,存在不合理之处。我国关于网络诽谤行为的司法解释规定:利用信息网络诽谤他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一)同一诽谤信息实际被点击、浏览次数达到五千次以上,或者被转发次数达到五百次以上的;(二)造成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精神失常、自残、自杀等严重后果的;(三)二年内曾因诽谤受过行政处罚,又诽谤他人的;(四)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笔者认为,对于“同一诽谤信息实际被点击、浏览次数达到五千次以上,或者被转发次数达到五百次以上的”,能否认定为情节严重,不能仅从形式意义上进行理解,应当根据客观的法益侵害性理念进行分析,否则将不能实现刑法的法益保护和自由保证机能。例如:行为人甲在网络上发布诽谤乙的信息,而且该信息被转发五百次或者被浏览五千次,但是乙被没有感觉到自己的名誉权和人格权受到损害,乙也并没有任何其他的损失。如果仅从形式上理解该司法解释关于“情节严重”的规定,则必定认定甲的行为构成网络诽谤犯罪,这不免会扩大刑法的处罚范围,而将没有法益侵害性的行为纳入到刑法规制之内。如果从实质上理解该司法解释关于“情节严重”的规定,则不会认为甲的行为构成网络诽谤犯罪,因为甲的行为并不具备客观的法益侵害性。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对“情节严重”认定的第一个阶层中,我们应当坚持客观的法益侵害性原则,将没有法益侵害或者法益侵害轻微的网络诽谤行为排除在刑法的规制之外。在适用刑法和司法解释中也应当贯彻该原则,以实现刑法的法益保护、自由保障和规制机能。
2.第二阶层:对“情节严重”中的情节具有非难可能性
虽然,客观主义犯罪论认为,刑事责任的基础是外部的犯罪人的行为及其实害。但是,同时认为,仅具有外部行为及其实害并不能成立犯罪,我国的犯罪构成体系就表现了这一点[11]57。我国的犯罪构成体系由四个方面构成,坚持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在认定犯罪时不仅考虑犯罪行为的实际侵害,而且考虑行为人的主观故意或者过失。只有坚持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才能将犯罪行为与合法行为真正的区别开来,才能将犯罪行为与正当防卫等违法阻却事由区别开来。因此,笔者认为,应当将判断行为人对行为及其结果是否具有非难可能性,作为网络诽谤行为是否达到“情节严重”的第二个阶层。以此来限制诽谤罪的处罚范围,平衡言论自由权和名誉权保护。
正如日本学者盯野塑所言:“犯罪由行为的客观要素和主观要素构成。现在,行为人对其实施的行为不具有非难可能性时,就不处罚的责任主义是妥当的;由于行为在客观上产生了犯罪事实就处罚的结果责任的观点,作为恶的客观主义受到排斥”。[11](P59)笔者认为,我们在认定行为人对严重情节是否具有故意时,应当坚持责任主义原则,判断该行为和结果是否可以归责于行为人,判断行为人是否具有期待可能性和正当化事由。刑法分则中规定诽谤罪是故意犯罪,因此,笔者认为,只有当行为人对其实施的网络诽谤行为具有故意时,才能将该行为及其结果归责于行为人;否则,将违反责任主义原则和罪刑法定原则。如果行为人对“情节严重”的结果是出于过失或者意外情况,则不能将该“情节严重”归责于行为人。例如:木马软件自动转发微博上的诽谤信息达到五百条;记录诽谤信息的笔记本被盗而意外散布等情形。针对上述对“情节严重”的行为及其结果没有故意的情况,虽然形式上达到了法律规定的“情节严重”的情形,但是实质并没有“情节严重”的故意。如果把过失或者意外事件造成的诽谤结果归责于行为人,则并将违法刑法的正义性和合目的性。刑法是一种行为规范,而不是一种处罚工具,因此,我们在认定网络诽谤行为和适用法律时,应当秉持正义、自由观念;应当坚持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和罪刑法定原则,保证刑法的良法之治;应当坚持责任主义原则,摒弃结果责任。
总而言之,笔者认为,对于网络诽谤行为是否达到“情节严重”,进行以上两个阶层的认定,不仅符合刑法的正义性和自由理念,而且符合罪刑法定原则和谦抑性原则。
[1]张明楷.刑法分则的解释原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2]陈兴良.刑法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
[3]吴大华.刑法各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4]高铭暄,马克昌,赵秉志.刑法学[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
[5]王利明.人格权法研究[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6]张明楷.法益初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
[7]赵龙.试论刑法中的“人”[DB/OL].荆楚法律网,2013-2.
[8]高铭暄.中国刑法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83.
[9]张明楷.犯罪构成要件体系与犯罪构成要件要素[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10]陈兴良.规范刑法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11]张明楷.刑法的基本立场[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
Analysis on the Problems of Internet Defamation
HUO Jun-ge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Mianyang,Sichuan,621000)
Internet defamation has received attention.It is not only related to the protection of constitutional rights,but also is related to protect the benefit of criminal law.In order to combat crime,balance the function of law protection and the function of liberty protection,we should first make a deep research and connotation on the defamation and internet defamation,and then make a specific identification of internet defamation crime, with the aim of correctly recognize the judicial practice and internet defamation.
internet defamation;object elements;analysis
D924.36
A
2095-1140(2014)03-0066-08
(责任编辑:天下溪)
2014-1-15
霍俊阁(1990-),男,河南开封人,西南科技大学法学院2012级法律硕士,主要从事网络犯罪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