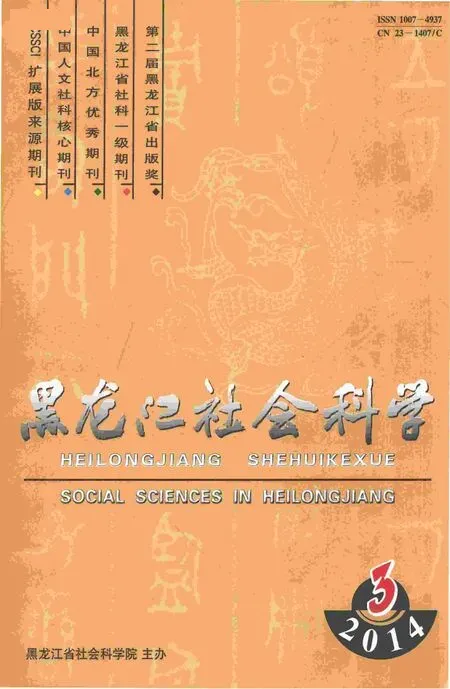明“化”而见“独”——《庄子》“独—化”论解析
2014-04-06朱小略
朱小略
(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北京100872)
“独”“化”二概念,在庄子思想中有着极为特殊的地位:自《逍遥游》《齐物论》两篇以“鲲鹏之化”与“庄周梦蝶”始,“化”字逐渐成为注庄诸家特别重视的核心范畴:以郭象、罗勉道等注家为首的后学,更将“化”字拔擢到《庄子》精要的高度。至于“独”之一字,各家虽未专章论述,但都首肯“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一句恰如其分地诠释了“真我”的风貌。但在庄学派分之中,这两词的本义都未得到合理的阐发,取而代之的是后人的郢书燕说之举。①以“化”为例,郭象以玄学解庄,时常支离文献原义,阐发己说。郭氏以为:“夫相因之功,莫若独化之至也。故人之所因者,天也;天之所生者,独化也。”在这里,他以“独化”合用,作为存在论的范畴,强调物与物之间无法转化,而只能“自化”,即自己默然变化。这一点与“物化”之说不合,实质否定了《庄子》“气化”的世界观背景。谭峭著《化书》,强调“物化”才是“化”的含义,但这一说既过分注重道教修仙腾挪变化的理论阐发,又忽视了庄子寓“独”于“化”,以“真我”应万化之世,“虽天地覆坠,亦将不与之遗”的修养论思想,而走向另一个极端。时至近世,学界为西方哲学思想所浸染,对《庄子》一书诠评,更有“汉话他说”之嫌。
庄子之所谓“化”,尤其是“物化”之意义,自胡适以来便屡遭曲篡。胡适以为“化”为“进化”之说,主张庄子自古代已提出进化论之思想。这明显有望文生义之嫌。胡氏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提道:“这些种子,得着水,便变成了一种微生物,细如断丝,故名为。到了水土交界之际,便又成了一种下等生物,叫做蛙之衣(司马彪云:‘物根在水土际,布在水中。就水上视之不见,按之可得。如张绵在水中。楚人谓之蛙之衣’)。到了陆地上,便变成了一种陆生的生物,叫做陵舄。自此以后,一层一层的进化,一直进到最高等的人类。这节文字所举的植物动物的名字,如今虽不可细考了,但是这个中坚理论,是显而易见,毫无可疑的。”[1]这就完全将《至乐》当成了自然演化的过程。这一说法是荒谬的,盖以胡氏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以西方哲学为哲学范式,而事事比附西方思想。这一做法虽然在当时有一定的理论基础,但却带上了强行比附的色彩。冯友兰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所完成的《中国哲学史》之中,虽然在“化”字义上,没有带上明显的西化色彩,但却以庄子的“化”为变动不居之义,并未在此基础上有进一步的阐发。
而建国以后,学界在过去机械的唯物唯心二分论的思想中,也对《庄子》的“化”之说误解连连。学界均以为“化”之说并非哲学观念,而是认识论上的相对主义诡辩论。譬如,任继愈先生在《中国哲学史》四卷本中认为:“《齐物论》还用了一个寓言式的故事说明这种不可知论的观点:有一次庄周梦为蝴蝶,他难于搞清楚,是庄周做梦,梦中变为蝴蝶呢,还是现在的庄周的活动是蝴蝶所做的梦?《齐物论》最后的结论是,不但一般人没有认识事物的能力,就是最高指挥的‘至人’也不能解答这个问题。”[2]这就完全取消了“化”的哲学内涵,仅以认知的变化不确定为由,认为庄子提出“化”之观念是认识论的怀疑论观念。冯友兰先生在这一时期完稿的《中国哲学史新编》中,一转其先前的观点,以为“化蝶”“物化”之说各有短处。化蝶之说,是认识论上相对主义的推衍,自然达到诡辩论:“由相对主义的推演,一面便自然会达到诡辩主义……很明白,这是一种混淆是非,颠倒黑白的诡辩论。这是庄周抛弃了老聃的辩证法,把老聃的哲学降低了。”[3]另一方面也认为,《至乐》所言之化,是由抽象的本原而至于具体的万象的形而上学的演绎过程,是“类”至“殊形”的过程。他虽然含蓄地批评了胡适之说的荒谬之处,但却将“化”的过程解释为由“道”而至于“殊相”的过程。这就是以己说而替庄子立言了。总的来说,自建国后至90年代,学者著书立说,受教条主义的影响甚深,并消解了《庄子》一书固有的范畴,取而代之的是以各种主义先行的研究方法来加以诠释。以马解中,比附盛行,这样就使自民国始的错解风进一步蔓延开来。
而时至今日,学界对“化”字的诠释,仍然是“剑走偏锋”得多。从主要倾向上看,虽然已从唯物唯心二分的传统中解脱出来,不将庄子之“化”简单斥为相对主义的诡辩。但大家多以中西对比,或古话今说,仍然走着胡适先生所开辟的老路。譬如,邱景源将“物化”思想与西方文化批判理论并列,认为庄子之“物化”有三重涵义:一是抽象的“物质”范畴,追求万物运动变化的根本规律;二是以“物”为世俗身外物,即人类文明的创造成果;三是物我一体之物,亦即西方哲学所说之“现象”,汇合人的意识之物。此说虽有新意,但却几乎完全脱离了文本的原生语境,赋予了过多的现代诠释[4]。何光顺以为,“物化”是庄子对生存的困惑,是反对人性异化的先声,是超越的途径,将庄子同海德格尔、马克思等思想家加以比较[5]。这都是在现代语境中对“物化”的过度诠释。中国古代哲学的核心范畴诠释,不能依靠西方哲学的话语“想当然耳”地加以比附。而应严格因循中国哲学范畴结构的范式,从训诂等“寻章摘句”的手段出发,先厘清字义的本意及其源流,将其在文献内部的多处引用中加以比较,再从共时和历时两个维度,在对同侪和后学的理解阐发之间指同辨异。这样,才能形成对中国哲学核心概念的正确认识。《庄子》的“独”“化”之说,只有先在解析中回归本位,才能在可靠的基础上加以阐发。否则,学界所汲汲于求的便只是“《庄子》中的哲学”,而非“《庄子》哲学”。因此,重新对《庄子》中“化——独”之说加以剖析,是非常必要的。
一、“化”之内涵
“化”之概念,为《庄子》所反复提及。后世学者尤其重视这一思想:罗勉道著《南华真经循本》,以“化”为《庄子》一书之主旨。时至当世,劳思光先生也仍认为,通人我的修养境界即是“化”[6]。这些说法都正面地肯定了“化”的理论价值。然纵观全文,“化”既有积极的一面,又有消极的意义,只有条分缕析,才能还原其本貌。梁徐宁在《庄子的〈物化〉概念解析》中指出:“物化”有四个层次,“幻化”“死亡”“自化”和“观化”。他在“物化”层面将“化”引申为“幻化”和“死亡”二义,这是很有见地的[7]。本文也依从这一基本的划分。但是,其将“物化”的本性解为“自化”,以“化”为无为而顺应自然之化,这实际上消解了“化”的宇宙论背景,而将“化”自性化了。“化”之所以突兀而不可逆,是因为人以自身之立场强分“顺逆”“成毁”的缘故,“化”自身仅是气聚散的表现,其根源在气而非性。而若“化”是由自性来决定的,那么“性”就成为世界的最终因,从而消解了庄子的“道”体之论。这是有待商榷的。徐氏之论侧重于“物化”,而“物化”之实,重在对人之心性有所影响,即所谓“心与物化”,这一节是梁氏所未点透的。“幻化”和“私生”是“物化”的核心意义而非全部意义。且除“物化”之外,“化”仍有其他意义,而这些意义又无不与“独”有着顺承关系,因而对“化”进行全盘的梳理,是很有必要的。
“化”的本义是“教化”。《说文解字》注“化”曰:“教行也。”而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也加以注解道:“教行也。教行于上,则化成于下。”国家教育百姓,移风易俗。对接受教育的庶民而言,这一学习的结果就是“化”。《应帝王》篇说道:“君人者一己出经式义度,人孰不敢听而化诸”,此处的“化”继承的就是“教化”的基本义。①在《左传》中,“化”出现过1次,《公羊传》中出现过两次。《公羊传·桓六年》说:“化我也”。注解解释说:“行过无礼谓之化,齐人语也。”这是齐方言中“化”的意思。“化”字出现稍多的经典还有《礼记》,但总计也仅出现过六次。在先秦的文献中尤为重视“化”字的哲学内涵,可见《庄子》的眼光是独到的。“化”这个词在《庄子》中出现了90次,常以单音词用法出现;在双音节词中,“物化”的搭配出现了9次,“变化”5次,“造化”3次,“自化”3次。从篇章上看,“化”首见于《逍遥游》,而在《大宗师》:中出现最频繁,共计18次。其词形以单音词居多。从整体上看,它的意义大致分为两类:首先是“教化”;其次是“天或道的运行”;再次是“变化”,譬如《大宗师》:“善妖善老,善始善终,人犹效之,而况万物之所系而一化之。”而在这三重意义中,“变化”才是最主要的含义。其哲学内涵在此又大致可以归纳为两个层次:“物化”与“心与物化”。在本文中,“化”首重的意义是物与物之间的转化。《至乐》篇说道:
种有几,得水则为继,得水土之际则为鼃蠙之衣,生于陵屯则为陵舄,陵舄得郁栖则为乌足……干余骨之沫为斯弥,斯弥为食醯。颐辂生乎食醯,黄軦生乎九猷,瞀芮生乎腐蠸。羊奚比乎不箰,久竹生青宁;青宁生程,程生马,马生人,人又反入于机。万物皆出于机,皆入于机。
这就是对“物化”最直观的描述。在“物化”中,庄周梦为蝴蝶,蝴蝶又为庄周。这不是“进化”,而是“转化”。《至乐》篇强调万物齐一及其物间的转化,其意义就在于此(胡适以《至乐》篇为庄子的进化论思想,是不甚妥贴的)。①“从这个极微细的‘几’一步步的‘以不同形相禅’,直到人类;人死了,还腐化成微细的‘几’,所以说,‘万物皆出于几,皆入于几。’这就是《寓言篇》所说‘始卒若环,莫得其伦’了。这都是天然的变化,所以叫做‘天均’。这种生物进化论,说万物进化,都是自生自化,并无主宰。”(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88页)这一义出现得很早。《逍遥游》首句即说:“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南华真经循本》说道:“篇首言鲲之化为鹏,则能高飞远徙,引喻下文;人化神为至,则能逍遥游,初出一‘化’字,乍读未觉起有意,细看始知此字不闲。”[8]这里肯定了“化”的神妙作用,即以“化”为变化和逍遥的直接因素。但实际上,“物化”是否就等同于“化神为至”呢?不尽然如此。《齐物论》说:
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尽。与物相刃相靡,其行尽如驰,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可不哀邪!人谓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与之然,可不谓大哀乎?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独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
可以看出,上述种种形体的转化也是“化”。但这里的“化”却是悲哀的。形体老去,疾病缠身。“化”的基调是沉重的。它仅是生成论中的一环,而非“化神为至”的人生修养。因此,以“化”为逍遥精要的理解,是谬误的。
应当说,在《庄子》的世界观中,物与物的区别只在外在的形态,而非内在的本质。厘清这一点对理解《庄子》之“化”而言,至关重要。《易传·系辞》说:“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9]精气凝结即是物,而物既然出于同源,它们的转化便不无可能。在此前提下,一切都是可化的。《庄子》以天地为气的思想,与此类似。②《知北游》:“臭腐复化为神奇,神奇复化为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气耳。’”物是可化的,但《庄子》之所以强调它的神妙,正是为了引申出“化”不可控的一面。冯友兰先生以“道”“德”“命”“性”为《庄子》思想的内在体系。③冯友兰:“江氏谓道者人之所共由;德者人之所自得。颇能说明道德之所以同,及其所以异。不过依庄学之意,则应云:道者物之所共由,德者物之所自得耳。物之将生,由无形至有形者,谓之命。及其成为物,则必有一定之形体。其形体与其精神,皆有一定之构造与规律,所谓‘各有仪则’;此则其性也。”(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282页)对人而言,“物化”即“命”的一种表现形式。梁氏以“幻化”与“死生”为“物化”的内涵,这一观点是精辟的。
但是,“化”的第三重含义,又鲜为人提及,这即是“心”与物化。什么是“心与物化”呢?《德充符》说:“刖者之履,无为爱之。皆无其本矣。”养生丧死是物化,而人们的态度随之变化,这就是“心与物化”:“物化”是引发心机的诱因,而主体的“心”境和情绪也随之转变。对一个先前健全而后遭刖刑的人而言,他对待鞋子的态度是不同的。显然,这种“化”决然没有化蝶时的潇洒与欣然。唯有平静地接受物化,才能使“心”保持不变。《大宗师》说:
夫大块以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今大冶铸金,金踊跃曰:“我且必为镆铘!”大冶必以为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为不祥之人。今一以天地为大炉,以造化为大冶,恶乎往而不可哉!
对子舆而言,死是无奈的。可是面对命定的祸患,人们的心还要保持安定。否则,形体的福祸与得失就带动了心机,而心机的萌发就预示了真我的沉沦:心不知生死皆是一气的道理,误以生为欢愉,死为苦痛,使内心陷入无尽的煎熬之中——这样,“物化”和“心与物化”就逻辑地连接了起来。而唯有看破这一点,人才能将“心”从“化”中拯救出来。①《至乐》:“庄子以鼓盆送妻死:‘是其始死也,我独何能无慨!然察其始而本无生;非徒无生也,而本无形;非徒无形也,而本无气。杂乎芒芴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今又变而之死。是相与为春秋冬夏四时行也。人且偃然寝于巨室,而我噭然随而哭之,自以为不通乎命,故止也。’”《大宗师》以子舆病中之论为例,展现出一副形化而心不与之然的图景:
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为鸡,予因以求时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为弹,予因以求鸮炙;浸假而化予之尻以为轮,以神为马,予因以乘之,旗更驾哉!且夫得者,时也;失者,顺也。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谓县解也,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结之。且夫物不胜天久矣,吾又何恶焉!
重病或残疾带来的恶症,不仅体现在形体中,也能影响到“心”:嫌恶、悲观、厌世、憎恶,都是真我的沦落和常我的萌发。唯有明确“化”的究竟,才能顺应物化,保持心不与物化。“物化”是自然的转化,有德之人要做的,是不使“心”也随之而“化”。领悟了这个道理,才可以达到“命物之化而守其宗”的境界,也就是《庄子》中“独”的境界。
二、“独”之内涵
在列出“幻化”“死生”“自化”等义之后,梁氏提出了“观化”之说,作为修养论的一环节。他以“物化”同“观化”对举,作为世界观至修养论的渐进,思路是值得称道的。然而,“观化”所倚重的是主体的修养之法;而“化”作为一世界观的概念,逻辑上对应的应当是人生论意义上的“境界”,亦即“我”之合理的“存在”形态,这样才能形成完整的“世界观——人生论”之体系。本文认为,正如以“化”来总领“物化”之义之法,在理论上更为直截;对举“独”之一字,以代“观化”,可以更好地还原《庄子》哲学的原貌。
“独”字,在《庄子》思想研究中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部分是“独”的贬义色彩使然:《说文解字》注“独”为“犬相得而斗也。”由犬性好胜而落单出发,“独”的含义就被引申至“单个,单独”。段玉裁注曰:“犬好斗。好斗则独而不群。引申假借之为专一之称。”应当说,“单个,独个”及“无嗣”,是“独”的主要字义。
而在儒家思想中,“独”也是屡被提及的字眼之一。《尚书·泰誓》说道:“独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仇。”“独夫”指的是商纣。“言独夫,失君道也。大作威杀无辜,乃是汝累世之仇,明不可不诛。”[10]《孟子》也说道:“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弒君也。”[11]“一夫”,就是“独夫”。而残仁残义则在儒家的观念中冒大不韪。由此可见,“独夫”是贬义色彩极重的名词。②与此相反,《论语》中“德不孤,必有邻”的说法,更加表明了儒家“失德之人孑然一身”的思想倾向。
尽管《庄子》中的“独”在某些语境下是负面的。譬如《人间世》中的卫君,在庄子看来,其刚愎自用,残贼王道,是所谓“独夫”。但《庄子》之“独”与其他各家之“独”,却有着本质的差异。在《庄子》中,“独”字出现了66次,分布于全篇的53句中,没有固定搭配,在《齐物论》(6次),《在宥》(6次)和《天地》(5次)中出现较多。“独”的贬义色彩均为褒义色彩所代替。这一意义在《齐物论》中主要以两种用法来体现,有对真人的摹描,也有对道的刻画:第一种是作形容词使用,《在宥》篇有“独有之人”一说,在该篇中,《庄子》在此以“世俗之人”同“独有之人”相对比。“世俗”的特征是“人我之辩”,这便是“常我”;而所谓独有之人,所持的是应道之心。道生自然,其可以保持自我的完整与不俗。达到这种境界的人,不以具体的物化框架禁锢一己之心,在万化的时间中作逍遥游,独来独往:“黄帝问广成,尧之见四子,皆以大物为息,欲明物物者之非物而已。吾所体者道,道外无物,是以谓之独有。夫大人之教,若形声之于影响,而不为天下先,此所以为之配也。”[12]187独有之人,明了道外无物,摆脱“心随物化”的俗人之见,最终保持的是“心”的不易与完整。相比万变的外物,独守的“心”才引领人至逍遥的境界。显然,《庄子》中“独”的地位是卓尔不群的。
“独”还有第二重用法,它在《庄子》中为“独有之人”的思想提供了形而上学的基础。《老子·二十五章》有言:“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这里的“独”即是“道”最显著的特征之一。以“独”为“道”,虽然在《庄子》66处“独”中所见最少,但其意义也最深刻。郭象以为“独”即是“道”。钟泰在《庄子发微》中也表达了相似的观点:“‘见独’,独即道矣,天也。谓之‘独’者,无与为对也。自‘朝彻’而‘见独’而‘无古今’而‘入于不死不生’,不言日数者,一彻而俱彻,更无先后渐次也。”[13]明确地表达了其自“明化”而“见独”密不可分、浑然一体的思想——这都说明“独”与“道”在内涵上有着紧密的联系。《大宗师》说道:“吾犹守而告之,三日而后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后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后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后能朝彻;朝彻而后能见独;见独而后能无古今;无古今而后能入于不死不生。”南伯子葵与女偊论道,唯有圣人之才的人才可以悟道:三日后心无家国之碍,七日后心无外物之扰,九日后人参通生死,至此,心便明化而近道,“常我”为之隐退,“真我”随之觉醒。而人也便经由大彻大悟而达到“独”的境地。什么是“圣人之才”?明达死生存亡,穷达贫富,这就是所谓才全:吕惠卿认为“独”是明化之境界。①褚伯秀:“有圣人之道者,得其大本大宗;有圣人之才者,能以是道推之天下、国家也。卜粱倚有其才而无其道,故守而告之,由粗以至精。已外天下而后外物,外物而后外生,外生而后朝彻,言况冥于有身自省,至是彻而为旦也。见独者,彼是莫得其偶。无古无今,参万岁而一成纯也。”(褚伯秀:《南华真经义海纂微》,华夏出版社2004年版,第111页)这一层“独”为“独与天地精神向往来”之说提供了形而上的基础,进而凸显了《庄子》理想的人生境界。
那么,“化”与“独”二者理应如何衔接呢?这就应看《天下》篇“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之说,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即是独有之人游心于道的写照。然而,独有之人必然超脱化外,趋近道体。这时的“独”即等同于“真我”。“真我”既然独有,那么其物质存在的载体便无所谓变与不变。正如气的聚散不过是形式的改变,其本质都是道。形全与性残,得福与得祸,都影响不到独于外物的“真我”。故此陈碧虚说:
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则离人入天,放旷八极。不傲倪于万物,不责人之是非,故处世而和光,应物而无件……信能冥心于芒昧之际,而得其所以运化者,则可与天地精神往来,无愧乎秉灵人矣。此段南华首于论化;次则自迷其所言所行;后又归结于化,明己能穷神知化,所以横说竖说,无非道也[12]534。
在此,陈碧虚特别将“独”与“化”衔接起来,以“独”应“化”,乃至于由明“化”而近“道”。这一条路可说正是《庄子》“化”“独”二论的真谛,将“世俗”与“独有”两相结合起来,即《庄子》人生论的旨趣所在。《大宗师》也在对“真我”的描述里充分体现了这一精神:“古之真人,不知说生,不知恶死。其出不欣,其入不距。翛然而往,翛然而来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终。受而喜之,忘而复之。是之谓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谓真人。”②《庄子》之中,常有“真人”之说,由此也可类推出“真我”一概念。这一说更阐发了庄子自己对“真我”观进一步的理解。
综上所述,“化”与“独”在庄子中是一对极为重要的范畴,这一点不仅体现在对范畴的数据分析上,也在其理路上有所体现:以“常我”所知的世界是多变而不恒定的。变幻的不仅是“物”,心机的萌发也带来了人的“化”。于此,“化”不是通向解脱和明达的逍遥之径,而是人不能保持本真的缘由;只有明“化”才能使人涵养自身,回复“真我”。“真我”之“独”,不是“独夫”之“独”,而是“独有”之“独”。明物之化而不扰其心,独于天地相往来。这是应道之性,也是本真的人所处的状态。庄子揭示了一条由“化”而“独”的修养进路,而在这样的进路中,人逐渐地近于逍遥应世的“真我”。
[1]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183.
[2]任继愈.中国哲学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178.
[3]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411.
[4]邱景源.庄子的物化思想的文化批判意义——与20世纪西方文化批判理论相比较[J].佳木斯教育学院学报,2004,(3).
[5]何光顺.《庄子》“物化”思想初探[J].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3).
[6]劳思光.新编中国哲学史[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196.
[7]梁徐宁.庄子的物化概念解析[J].中国哲学史,2001,(5).
[8]罗勉道.南华真经循本[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558.
[9]王弼.周易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266.
[10]何休.尚书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280.
[11]赵岐.孟子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53.
[12]褚伯秀.南华真经义海纂微[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
[13]钟泰.庄子发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1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