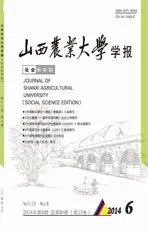权力意识操控下的翻译活动及启示
——以建国初期十七年中国翻译活动为例
2014-04-04张小玲
张小玲
(山西农业大学 文理学院,山西 太谷 030801)
权力意识操控下的翻译活动及启示
——以建国初期十七年中国翻译活动为例
张小玲
(山西农业大学 文理学院,山西 太谷 030801)
翻译活动是受意识形态及赞助人等权力操控下的一种社会活动。借助于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及勒弗菲尔的改写理论从历史实证角度探讨建国初期十七年新中国翻译活动的过程及其制约因素,旨在揭示这一阶段中国翻译活动的基本特点,为新时期翻译活动的良性发展提供一些引资借鉴。
意识形态;赞助人;改写理论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中国迎来了又一次翻译高峰。翻译活动从政治著作、文学译介以及科学著作等各方面都出现了阶段性的高度繁荣。但长期以来,译界对1949年到1966年这一阶段的探讨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普遍认为这一阶段翻译活动完全受政治影响,研究价值不高,虽有一些学者对其有所论述,但由于条件所限,仅将其视为中国现代史发展进程中的一个片断加以分析与界定,缺乏完整深入的分析与探讨。本文在对建国初期十七年翻译活动进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客观地描述其特点及成就, 并总结经验,以期为新时期翻译活动的开展及政策的制定提供一定的历史借鉴。
一、权力、意识形态与翻译
权力是一种特殊的、强制性的力量,是政治理论中的核心概念。英文中“权力”(power)一词源于拉丁文potestas 或potentia, 意指“能力”。不同理论家赋予权力不同的概念,但大多认为:“权力”指一个行为者或机构影响其他行为者或机构的态度和行为的能力。法国哲学家福柯就权力、知识与话语之间的关系提出了权利话语理论。他认为权力通过特定的社会机构掌控知识进而操控整个社会。社会的变化伴随着知识的改变,知识通过语言与话语的形式来界定我们的现实世界进而反映出不同的权力关系。语言不仅是一种话语的秩序,而且是一种权力的建构。[1]权力具有特殊的强制力和支配力,其表现形式可以是有形的也可以是无形的,其中意识形态、文化宗教等属于无形的权力,而国家政权机构、方针政策、法律条文等属于有形的权力。无论有形还是无形,其目的都在于改变被操控者的意识形态以符合统治阶级的利益与诉求。福柯的哲学思想在西方引起了极大的关注并被广泛应用到许多学科当中,致使“每一种学术性学科都能从他那里得到某种启发”,[2]翻译研究就是其中一例。
福柯在他的权力话语理论中虽没有直接谈论翻译与权力的关系,但他的理论被许多翻译理论家,比如巴斯内特、勒弗菲尔、斯皮瓦克等,所引用并进一步融入到他们的理论之中,这对翻译研究范式的转变、翻译理论的扩展都起了积极的作用,尤其是到20世纪中后期,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试图将翻译活动置于更大的社会及文化历史背景中进行探讨,翻译从最初对文本内部的研究转向文化研究,而这次文化转向中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对意识形态的关注, 其中,借助于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勒弗菲尔将其视为“在特定社会历史时期所形成的并被普遍接受的一种观念和态度,而这种观念与态度又进一步左右着译者及读者对文本的处理。”[3]在他的著作《翻译、改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操控》中提出了改写理论并认为:翻译即改写,任何翻译,无论我们是否意识到,都是对原作的改写与操控,在不同形式的改写中,翻译是最明显、最有影响力的一种改写,而这种改写并不是在“真空”中进行,他同时受意识形态、赞助人等多种因素的权力操控。[4]勒弗菲尔在其论述中将文学视为文化体系中的一部分,并认为这种体系受内外双重制约,一种是内部的“专业人士”制约,比如译者、评论家和教师等,他们往往会对原著进行改写以符合主流意识形态,另一种是“外部人士”即赞助人的制约。赞助人代表了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并通过对改写者的意识形态、经济状况以及社会地位的操控来体现他们的权力话语,反映当时翻译活动的流行趋势。[5]
继勒弗菲尔之后,与意识形态密切相关的权利关系进一步引起译界关注。聚焦翻译与权利,翻译文化转向开始转向权利。为建构某种“预期”的文化,原文受制于权力,意识形态及赞助而被操纵,以创建某种特定的体现方式。而翻译活动在权力与意识的双重操控下彰显出其独特的历史特点和阶段性优势。
二、权力意识操控下的十七年翻译活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际上,西方列强竭力遏制新生政权并阻挠其他国家与新中国建交,毛泽东提出了“一边倒”、“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三大外交方针,新中国迅速与社会主义国家结盟;从国内来看,百废待兴,新生政权急需肃清反动势力,宣传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以巩固无产阶级政权。结合国内外政治形势,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加强了思想控制,即:大力宣传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思想意识。翻译活动受此影响,从文本及翻译策略的选择乃至赞助人等方面都显现出明显的意识形态倾向。
(一)意识形态对翻译活动的权力操控
意识形态是特定社会及文化的产物,它伴随着社会,文化的产生而产生。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交际行为,涉及两种文化的交流,其实质是将“他者”文化及意识形态引入本土文化,并加以同化以融入本土的价值体系和意识形态当中。[6]
建国后十七年的翻译活动无论是汉译外还是外译汉,都出现了阶段性的翻译高峰。从汉译外来看,首先,新中国掀起了全面学习苏联的热潮,周扬在苏联杂志《旗帜》上发文指出:“‘走俄国人的路’,政治上如此,文学艺术也是如此。……文艺工作者应当更努力地学习苏联作家的创作经验和艺术技巧,特别是深刻地去研究他们作为创作基础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7]受此思想影响,在文本选择上,来自苏俄的社会主义和现实主义文学作品被大量译介,而这一高峰主要出现在建国初期的十年间,据统计,从1949年10月到1958年12月,总共有3526种苏俄文学作品被翻译出版,占整个外国文学翻译作品的2/3。[8]但从50年代末开始,中苏关系开始出现裂痕,中苏意识形态的对立严重影响了中国对苏联文学的译介活动,从1960年到1966年间,前四年公开出版的苏联文学译作单行本共11种,后三年苏联文学作品被翻译成汉语的数量为零。[8]其次,来自苏联的科技著作被大量译介。建国初期译出的科学著作,大部分原著皆来自苏联,其中,从1952年到1960年科技作品的译介最多,1954年达911种,1957年最多,总共有2557种科学著作被译介,其中2/3以上来自苏联,[9]这一阶段正好是国家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和第一个科学发展远景规划执行阶段,可见国家的政策及意识形态导向促进了这一阶段科学翻译高峰的到来,而从1960年开始苏联单方面撤走在华专家,中苏关系破裂,来自苏联的翻译作品出现低潮,尤其是1961年达到最低潮,只有126种苏联科技原著被译介。[9]最后,政治作品的译介。为进一步宣传无产阶级意识形态,1953年1月,党中央成立了中央编译局,任务是有系统有计划地翻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于是,十七年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作品由俄语被大量译为汉语并促进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政治意识在中国的传播。从1956年到1966间,中共中央编译局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翻译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前22卷(不包括第20卷);从1955年到1963年,《列宁全集》共39卷由俄语全部翻译成汉语,而《斯大林全集》13卷也于1953年到1956年全部被翻译完成。[10]马列著作的翻译与编辑在国家有计划的指导下迅速完成,这为新中国的经济,文化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治基础。
总之,建国初期外译汉翻译活动受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制约呈现出明显的特点:其一,苏联作品无论是文学还是科技都在短短的几年内迅速被译为汉语,并得到广泛传播,但同时由于受政治意识的影响,又在很短的时间内由高潮跌入低谷;其二,在国家政权及政府的支持下,政治经典作品经由俄语很快地被大量译为汉语,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翻译活动的开展和新生政权的巩固。
从外译汉来看,中国历史上,很少有汉语书被翻译成外文并在异国得到广泛传播。新中国成立后,为了让世界无产者更多的了解中国,同时与更多的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中国外文局以外文出版社的名义翻译出版了大量外文图书, 其中毛泽东著作的翻译被放在了首要位置, 尤其是《毛泽东选集》英文版第四卷的翻译与出版,外文出版社决定先出第四卷,然后再出第一、二、三卷,文化部就其出版发行工作于1961年先后发出两个书面通知,要求当地书店在请示党政领导后方可开始发行,并对其发行对象及数量加以限制。由此可见,毛泽东著作的翻译及出版被当作一项政治任务,并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据统计,从1949年到1965年间,3000多种中文图书被译成20多种外文在国外得到传播,其中毛泽东著作有536种。[11]另外,一些介绍领袖著作和中国革命经验的小册子被译成多种语言在国外发行,这些小册子在国外受到欢迎,并成为外国人了解中国、研究中国的一种有效途径。总之,这一阶段汉译外翻译活动以翻译毛泽东著作和政治文献小册子为主,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倾向性。为巩固新生的无产阶级政权,新中国通过翻译来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以争取更多的支持,而其传播对象为亚、非、拉争取民族独立的国家以及欧美发达国家的一些左派组织和进步人士,因此,这一阶段的汉译外翻译活动在关注文本自身的同时,更多地考虑其包含的政治与社会因素。
(二)赞助人对翻译活动的权力操控
赞助人的权力意识是操控翻译活动的又一重要因素,它是推动早期现代社会进步的基本力量之一,其影响力远超过文学作品对社会的影响。英文中“patron”一词来自拉丁语patronus,意指为实现特定目的而给予委托人资助的人。赞助人操纵着翻译活动的各个方面包括翻译内容,翻译选材甚至翻译策略及译作宣传等。赞助者可以是有权威的个人,也可以是出版商,政府机构等,其目的在于通过为译者或作者提供一定的经济支持、社会地位或政治庇护,使其创作与翻译与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相一致,以保证译作符合特定的社会规范或特定阶层的利益诉求。
新中国成立后, 翻译活动的赞助整体上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这一阶段出版社作为赞助人的角色在不断发生变化。 建国之初,各地出版业发展不均衡,国有出版社与私人出版社并存。据1950年3月统计,全国11个大城市中,有244家私营书店经营出版业务,出版社成为这一阶段的主要赞助人,其拥有一定独立的经济能力,并通过对译者的经济支持以实现对翻译活动的赞助。从1954年开始,国家有步骤地对私营出版社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到1956年底,基本实现了对私营出版社的社会主义改造,出版社中私营成分退出,赞助人构成也同时在发生着变化。第二阶段从1957年到1966年,这一阶段出版社作为独立赞助者的权力被弱化,翻译活动中政府机构,比如文化部、中央宣传部等及权威个人,比如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等的赞助占主导,出版社的独立性已不复存在,尽管在翻译活动中它们可以决定译什么、怎么译,但当其意识形态与政府机构或权威个人的意识形态相违背时,它们必须服从后者。比如在翻译内容上,有人主张在《人民画报》外文版上翻译介绍中国革命经验,毛主席不赞成,主张“能够真实地介绍我们的生活就很好了”。[12]再如,《毛泽东选集》第四卷英文版的翻译,党中央指定章汉夫、孟用潜负责具体的领导工作,翻译过程中,中央有关领导,如周恩来、陈毅等,均参加过译文的审定工作。赞助人对翻译活动的操控还体现在翻译策略的选择上。不同类型的文本有不同的翻译策略。政治文本翻译时力求准确完整地表达原文的内容,这类文本的编辑加工问题,应严格请示汇报;文艺作品的翻译要尽量体会原文风格,必要时做适当的文字加工,但不能随意改动原文的内容;一般报道则应更多地适应外文报道的习惯,考虑国外读者的接受能力,在翻译时可以有较大的灵活性,但有关方针,政策和重大事实不能随意改动。由此可见,建国初期的翻译活动译者的权力更多地受控于赞助人及其意识形态,正如杨宪益所言“不幸的是,我俩只是受雇的翻译匠而已,该翻译什么不由我们做主……,中选的作品又必须适合当时的政治气候和一时的口味。”[13]
三、建国十七年翻译活动的启示
建国后十七年的翻译活动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第四次翻译高潮,而促成这次高潮的关键因素在于政府对翻译活动的统一领导与规划。建国初期,国家通过召开一些全国性的会议,加强了对出版业和翻译活动的组织和计划。首先,为整治出版业的混乱状态,领导全国的出版工作,国家出版总署先后于1950年9月和1951年8月分别召开了第一届全国出版会议和第一届全国出版行政会议,会上都强调了出版物的质量问题,尤其是第二次会议,将提高出版物的质量作为出版业的首要任务,并强调了书刊的审读及开展书评的重要性。
其次,为提高翻译质量,订立计划,国家出版总署于1951年11月召开了第一届全国翻译工作会议,会上将翻译工作的计划化和制度化列为组织翻译工作的中心任务,并强调在全国学术界和出版界广泛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以改进和提高翻译工作的质量。再次,1954年8月,中国作家协会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文学翻译工作会议。会上,茅盾提出文学翻译工作必须有组织、有计划的进行,要加强文学翻译工作中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以提高文学翻译的艺术创造水平。
这几次会议之后,翻译活动,尤其是翻译批评活动,在中国被广泛开展,翻译作品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有了很大的提高。据统计,从1919到1949年,30年间中国共有6680种翻译作品出版,而从1949年10月到1958年底,全国翻译出版的外国文艺作品就达5300多种,其中译自苏联的占65.5%。[8]而这一阶段的科普作品翻译达3600多种,其中大部分作品也是来自苏联。[9]这一阶段的翻译批评也广泛开展开来,从1950年到1952年,仅发表在《翻译通报》上的文章就达74篇,许多译者不仅敢于提出批评,而且对自己译作的错误主动提出自我批评。例如汪飞白1952年5月在《翻译通报》上发表了《评蒋译“星”》对蒋路的译作进行批评,接着蒋路发表了《关于“星”译本的检讨》对其译作中的错误做自我检讨。
与建国十七年的翻译活动相比,21世纪以来中国的翻译活动更加繁荣,涉及范围也更加广泛,但同时也出现了许多问题。首先,译作质量低下。为扩大销售量,追求丰厚的利润,许多出版社争先买下国外畅销书的版权,并组织译者尽快译成中文,以获取最大利润,而这一过程导致译文的质量难以保证进而影响读者对原著的欣赏。其次,盗版活动猖獗。盗版书不仅版本众多而且价格低廉,包装精美。许多出版社为逃避盗版指控,甚至乱编译者的名字。以叶君健先生译的《安徒生童话》为例,仅他知道的盗版版本就有约40个。[14]再如人民文学出版社所有过去翻译出版的书籍几乎全被盗版过。类似例子举不胜举,盗版行为不仅影响了正规出版社的权益,也损害了读者享受精美译文的权力。
针对这些问题,从历史角度来看,首先,加强政府对翻译活动的领导与组织必不可少。目前为止,我国尚没有一个政府部门专门主管翻译活动。市场经济在推动翻译活动广泛开展的同时,其盲目性和对利润的追求导致翻译产品的精神性、文化性难以很好地体现。因此,政府相关部门对其整体规划和引导对翻译活动的有效开展起重要作用。
其次,大力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提高翻译质量的有效途径。翻译作品的质量低下在一定程度上可归咎于翻译批评的缺失。整体来看,目前我国就翻译批评类文章发表数量仍然较少且实践研究多于理论研究, 以2011年为例,翻译批评类文章共14篇,仅占总数的2.2%,[15]再从2010年82篇批评类文章来看,仅有四篇是关于翻译批评理论方面的研究。[16]从内容来看,文学批评占主导且大多属赏析类批评,尤其侧重对名家的分析,对译者的表扬大于批评,翻译批评理论建构不足,缺少真正的实质性批评。翻译批评尚且如此,来自译者的自我批评性文章更是少之又少。总之,作为翻译活动的一个重要领域,翻译批评不可或缺。
四、结论
建国初期翻译活动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点。首先,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翻译活动以译介苏联作品为主。为巩固新生政权,国家急需新的理论与模式加以借鉴,而苏联模式在当时被认为是最先进,最革命的模式,对其借鉴与学习促进了新中国政权的巩固与发展,而翻译作为借鉴苏联模式的有效途径,在中苏文化交流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其次,从意识形态方面来看,这一阶段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占主导,体现在翻译活动上,即:大量反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作品被译介;大量反映无产阶级思想的政治文献被译介。通过对这些作品的翻译及改写,我国社会主义文化事业进一步得到繁荣;再次,从赞助人角度看,来自政府机构及国家领导人对翻译活动的支持与参与,使翻译活动具有更加明显的政治倾向,但同时也使翻译活动更加规范。翻译活动的高度组织性和计划性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翻译活动的进一步开展。总之,建国初期,意识形态及赞助人对翻译活动的双重权力操控贯穿于翻译活动的始终,在翻译活动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尤其是政府的领导作用以及翻译界普遍开展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活动为新时期翻译活动的良性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历史镜鉴。
[1]许宝强,袁伟.语言与翻译的政治[C].北京: 中央编译出社, 2001:1-20.
[2]吕俊. 翻译研究:从文本理论到权利话语[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2,1(18):106-109.
[3]Bassnett, S amp; Lefevere, A. Constructing Cultures: Essay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 [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48.
[4]Munday, J. Introducing Translation Studies Theories and Applications[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10:127-129.
[5]Lefevere, A.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M]. 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10:1-70.
[6]王东风. 一只看不见的手——论意识形态对翻译实践的操纵[J].中国翻译,2003,5(24): 16-23.
[7]周扬.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中国文学前进的道路[N]. 人民日报,1953-01-11(1).
[8]文记东.1949~1966年的中苏文化交流[M].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1:101,144.
[9]马祖毅. 中国翻译通史 现当代部分(第三卷)[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6:207-225.
[10]人民出版社马列著作编辑室.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文本书目(1950~1983年)[Z].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11]周东元,亓文公. 中国外文局五十年史料选编(1)[M]. 北京:新星出版社,1999:399.
[12]新星出版社编辑部. 中国外文局五十年回忆录[M]. 北京:新星出版社,1999:37,420-421.
[13]杨献益,薛鸿时.漏船载酒译当年[M]. 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1:225.
[14]杜萌. 翻译市场滥译滥编侵权现状调查[N].法制日报,2009-03-02(8).
[15]中国翻译协会. 中国翻译年鉴:2009~2010年[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1: 241,232.
[16]中国翻译协会. 中国翻译年鉴:2011~2012年[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3:157.
TranslationManipulatedbyPowerandIdeologyanditsImplications——ACaseStudyofTranslationActivitiesinChina(1949~1966)
ZHANG Xiao-ling
(CollegeofArtsandSciences,ShanxiAgriculturalUniversity,TaiguShanxi030801,China)
Translation is a social activity manipulated by powerful ideology and patronage. The paper examines the seventeen-year translation activities after the foundation of the PRC from empirical and historical perspective under the guidance of Foucault's theory of power and discourse and Lefevere's rewriting theory. It aims at exploring the features of translation activities to make reference to the sound development of the present-day translation activities.
Ideology; Patronage; Rewriting theory
2014-02-20
张小玲(1978-),女(汉),山西临汾人,硕士,主要从事文化对比与翻译方面的研究。
H059
A
1671-816X(2014)06-0610-05
(编辑:佘小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