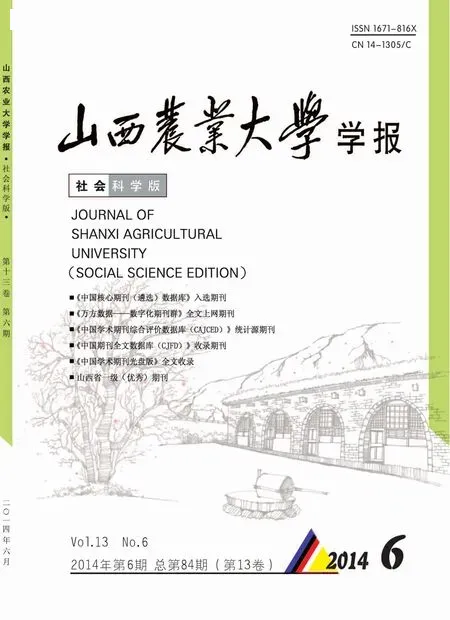基于认知视阈的“语言游戏说”探析
2014-04-04赵雁林魏屹东
赵雁林,魏屹东
(1.山西农业大学 校长办公室,山西 太谷 030801;2.山西大学 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山西 太原 030006)
基于认知视阈的“语言游戏说”探析
赵雁林1,魏屹东2
(1.山西农业大学 校长办公室,山西 太谷 030801;2.山西大学 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山西 太原 030006)
“语言游戏说”是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的核心和基础。语言在使用中才有意义,词语的意义就是它的用法。表征是连接语言和意义的认知纽带。“语言游戏说”中的语境依赖、生活体验、规则遵守和家族相似等观点反映出人类探寻语言认知路径的一些取向特点。基于认知视阈阐释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说”,从而能够更好地解释语言在现实中的运行方式。
维特根斯坦;语言游戏;认知;语境;规则
“语言游戏说”是后期维特根斯坦哲学的核心和基础,它为我们绘制了一幅语言实际使用的图景。维特根斯坦对于其它问题的理解都建立在“语言游戏说”的基础之上。
一、意义即使用:“语言游戏说”的认知基础
“语言游戏说”的提出得益于一场足球赛的启发。维特根斯坦在思考关于语言及其意义的问题时恰巧看到一场足球赛,足球的意义体现在足球赛中,他由此受到启发,我们说话正是在用语言做游戏。维特根斯坦认为,语言的意义取决于语言游戏中字词等语言符号的具体使用。这正如在现实生活中,语言技能要在使用语言的实际过程之中获得,仅研究字典和语法而不去实际使用字词等语言符号并不能获得语言技能。字词等语言符号本身是僵死的,使用才使得它有了生命活力。
维特根斯坦使用“语言游戏”这个词的主要目的在于指出语言游戏就是语言与行为的一种结合。他说:“我也将由语言和行动(指与语言交织在一起的那些行动)所组成的整体叫做语言游戏”。[1]语言体现的是心智与客观世界间的某种关联,因此,语言的意义绝不独属于客观世界,也不独属于心智世界。人类依赖于语言符号的运用,将客观事实及其作用规律表征出来形成科学知识,从而表现为人们的思想和观念。认知能力与人类的心智和人类生存的外部环境都有关系。语言必须透过认知加以解释,没有认知,就不会有现存形式的世界。脱离语言的具体使用,意义只能是空中楼阁。意义实现需要认知的直接介入。
二、表征:语言和意义的认知纽带
表征是人类最重要的认知方式,没有表征我们就不能解释认知现象。语言是一个表征系统,使用语言的过程也就是表征的过程。根据信息加工的观点,语言信息在心理活动中的表现和记载方式即为表征。表征是心智通达世界的手段或工具。当心智对语言符号这种特殊的外界信息进行输入、编码、转换、存储和提取等时,语言符号以表征的方式在头脑中呈现。人类的认知是依靠表征完成的,语言符号表征出意义使人们认知世界。认知能力是人类语言能力的根本。意义的认知源于语言的具体使用,认知先于语言、决定语言,是语言的基础;语言又可反作用于认知,可促进认知的发展和完善。[2]
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本身无所谓意义,语言和表征相结合才产生出了意义。表征一方面反映接收到的语言信息,从而代表客观事物,另一方面又是客观事物在心理活动中的内部再现,属于心理活动要进一步加工的对象和客体。语言符号经由表征生产出意义的过程是心智与环境互动的过程。对于言者,表征代表着概念化活动的实施,而对于听者,表征则引导其通过语言对所述场景重新概念化。[3]要说明认知系统如何显示意义,无论如何离不开表征。没有适当的表征,就无法呈现认知的意义。[4]通过表征在言者和听者间的实践和运作,人与人之间交际的内容得以体现,可共享的意义产生出来。
表征具有中介性,即表征是心灵把握世界的中介。[5]在当代认知心理学和认知科学中,认知被看作是心灵的表征状态和表征过程。语言的表征过程就如同我们的视觉系统在面对外界景象时,利用视网膜形成映像的过程。认知不但包括思维,而且包括语言运用、符号操作和行为控制。[6]在认知过程中,字词等语言符号的表征起了重要作用,口语借助声音语调,书面语借助文字符号,身体语言借助表情姿势等。语言游戏是语言游戏者共同参与的协商、约定和建构的认知过程。语言以特定的方式凭借字词等符号来传达意义。意义就是语言系统不同层次或类型的表征形态,它表现为语言系统和语境之间的一种结构性“产出”。[7]因此,表征介于语言符号及其所表达的意义之间,是连接语言和意义的认知纽带。
三、“语言游戏说”的认知取向特点
维特根斯坦要求我们跳出单个字词等语言符号,结合具体的表征方式和语言环境来寻求语言的意义。语言符号的意义体现于语言游戏的使用过程之中,这就像下棋时,棋子的意义取决于它在棋盘中的位置及运用。维特根斯坦用一系列语言游戏的实例表明,语言游戏无本质,语言是手段,认知才是目的。“语言游戏说”中的语境依赖、生活体验、规则遵守和家族相似等观点带有合理的认知成分,反映出人类探寻语言认知的取向特点。
(一)语境的动态性
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过程就是语言符号表征的过程,其实质是语言在广义的动态语境之下的认知活动。语言游戏就相当于语境,不同的语言游戏构成了不同的语境。[8]语境内在地包涵了一切影响和制约语言的发生、发展、存在和变化的因素。表征过程是语境敏感和语境依赖的,语言使用的语境某种程度上决定着意义的具体表征。所以,对语言和意义的研究决不能脱离语境。语言与语境密切相关,语境随着语言交流的进行持续不断地变化着,这体现了语境的动态性特点。事实上,对语言使用中相关语言特征的选择,就是对语言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心理的背景选择。而这种选择功能,只有通过语境的作用才能得以实现。[8]语境的动态性提示我们,必须关注认知过程中的特定语境,我们才能正确把握语言信息背后的真正意义。
维特根斯坦在突出强调了语言游戏中语言的具体使用之后,又指出要注重语境分析的方法,从而完成了对逻辑语义分析的僵化模式的彻底否定,凸显了语言使用中的各种语境条件的重要作用。对于认知而言,语境是必要的平台。同样的语言现象在不同的语境中出现时,会产生不同的表征效果。假设仅当某人喊出英语单词“Fire!”时,我们是无法判断究竟意为“失火啦!”还是命令“开火!”,这就是因为我们忽略了语言游戏中语境分析的作用。语言的研究与语境分析密切相关。意义在操作上可以描述为基于语境功能的语言使用。语境的存在给人类提供了理解的可能性。语境是语言和行动的整合,它是一个动态的心理建构体,是说话人对世界的一种合理假设。[9]在语言游戏过程中,基于主体、客体以及主体间的关系,语境对当前所有信息进行重新建构,是语境赐予了语言符号以意义。语境的心理建构超越了语言符号与客观事物之间的关联。从交际的角度来看,语言游戏是主体不断地选择、延伸、调整和顺应不同语境的过程。语境不同,意义自然不同,人类认知具有差异性的部分原因即在于此。意义以表征的方式在特定的语境中存在着和发展着,语境对意义有制约作用,语境发生变化,意义也随之发生改变。[10]语境构成了维特根斯坦判定语言意义的最高法庭。
(二)体验的涉身性
语言是一种社会实践或生活方式。语言的意义不限于语言内容,而来源于人与客观世界互动的认知,来源于语言使用者对世界的理解。维特根斯坦说,语言的言说,部分是一种活动,部分是一种生活方式。[11]语言游戏是生活形式的基本单位。语词在我们日常生活的细枝末节之中显现出意义。意义正是人对生活实践中语言信息处理和加工的结果,其本质是一个心理表征的建构体。语言的意义必须和具体的语言使用者的认知联系起来。表征是人类最重要的认知和学习方式。语言对现实的表征依赖于人类大脑的功能。所以,表征的能力是基于身体经验的,其物质承担者就是大脑神经系统。我们的身体以及身体同环境的互动提供了认知世界的最原始经验。凭借主体的表征能力和生活体验,人类完成了对语言游戏的各种认知操作。
维特根斯坦用“语言游戏说”把语言同人类的生活体验联系在一起,突出强调了语言游戏中人的参与作用。表征以我们涉身体验到的感觉和知觉信息为基础。语言使用者的体验在意义的表征中作用巨大。认知是涉身的活动,我们不能把语言仅仅看作孤立静止的描述符号,而要看作动态的认知体验活动。意义是通过人的身体和想象力获得的。人以自身的感觉器官直接感知客观世界,在与客观世界的互动中认知世界。语言和意义依赖于心智体验,而心智体验是基于大脑和身体的感觉、知的一种功能。它发端于人自身的机体构造、神经结构、生理特征,与人的感官和运动系统的活动方式以及当下的心理状态紧密相连。感觉和知觉给予我们关于周遭环境中事物情况如何的信念或判断,感觉和知觉具有的信息承载功能表明它们本身即是一种表征,是我们认知世界的主要方式之一。感觉和知觉的主体是身体,因而认知是身体的认知,离开身体的认知是不可能存在的。总之,对语言游戏的认知活动必须完全嵌入到人的身体活动之中。
意义出现在我们使用语言的生活体验之中,它与我们的日常生活融合在一起。心智体验的涉身性决定了我们语言表征的习惯和看待世界的方式。对语言的认知仅仅从逻辑和语法上把握是不够的,日常生活中语境化了的语言游戏参与者,使得认知过程必然带有个人的生活体验。世界多姿多彩,语言千变万化,体验的涉身性使得认知的主体和客体相融,共同组成一个完整的语境化的动态统一体。因此,要想真正认知语言符号的各种意义,生活体验是不可缺少的途径。
(三)规则的意向性
维特根斯坦把人类的语言活动比作一种游戏,不仅是为了说明字词等语言符号的使用是有意义的,而且还在于强调语言活动是一种有规则的游戏。维特根斯坦认为,语言是建立在规则基础之上的,语言要成为交际的工具就必须要有达成的契约。[1]人类的认知系统要求知觉和认识世界时有对应的一套规则。意义在本质上是公共的和约定俗成的,因而意义的表征过程必然基于一定的规则。乔姆斯基认为,说话者和听话者的能力可以很理想地用一个将符号和符号的语义解释联系起来的规则系统表达出来。[12]人类凭借自身的理性,通过实际地参与语言游戏活动,了解和掌握各种游戏规则。进行语言游戏时知道规则遵守,需要认知的过程中将这些规则内化到我们的大脑中,犹如踢足球的时候要知道怎么算越位、怎么算犯规,下象棋的时候要知道马走“日”字、象走“田”字一样。认知就意味着内化了一个规则系统。规则内化到大脑中后,形成基本的认知条件,在语言游戏时成为我们进行判断和解决问题的依据。
规则如同路标一样,为我们指明前进的方向。意义的充分表达有赖于意向性的展开,规则的指向功能说明规则内在地包含着意向性的成分。意向性是语言功能实现的基础。表征的起点是从心智的意向性选择开始的。意向性在语言活动中赋予了语言表达以意义,规则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导向作用。维特根斯坦说,“不要想,只要看(做),通过参与游戏,融入到一种已有的生活形式之中,这样个人就会理解到了这种生活形式的规则。”[11]语境论事实上包含了语言游戏及其特定的规则。[13]遵守规则蕴含了意向性的选择程序。语言是具有社会规约性的符号系统,它按照一定的规则在特定语境中使用。规则的意向性统一了我们表征时的内在知觉感受和外在语境根据,使得语言游戏成为一种符合语境化要求的人类现实活动。
(四)表征的家族相似性
维特根斯坦认为,各种语言游戏之间的家族相似是一种错综复杂、重叠交错的“相似性”关联。他说,“我想不出比家族相似性更好的表达式来刻画这种相似关系,因为一个家族的成员之间的各种各样的相似之处:体形、相貌、眼睛的颜色、步姿、性情等,也以同样方式互相重叠与交叉。所以我要说:游戏形成一个家族。”[1]表征基于相似性。[5]现实世界中,家族相似性无处不在。由于语言的表征具有开放性,有一个潜在的发展空间,家族相似带来的关联为我们认知新事物创造了条件。我们可以通过创造新概念等方法去表征新的未知对象,或使以前的对象获得新的表征形式。[14]
家族相似性的观点对认知语言学的重要理论“原型范畴”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范畴的中心是范畴的原型,范畴的边缘与原型相似性较低的成员即属于非典型成员。范畴化即是根据认知对象的特征及其与某一范畴的原型的相似性大小来判定其是否属于该范畴的过程。[15]家族相似是人类根据已有范例创造新的语言表达的一种认知过程。认知对象的整体是由各个成分构成的。家族相似性强调整体的优势效应,重视整体和各部分之间动态的联系以及创造性思维运用,其本质是一种格式塔转换。正是基于家族相似的格式塔转换,人类整合了纷繁歧异的现实事物之间的相似性,利用类比、模型、隐喻等各种思维范式,达到了辨识世间万事万物的最终目的。
四、结语
后期维特根斯坦“语言游戏说”的哲学贡献是显而易见的,它映现出20世纪中期哲学思维方式发展的一种关键性变革。维特根斯坦通过列举各种类型的语言游戏,对语言及其意义进行了合理的分析。尽管他很少使用“认知”、“语境”之类的词语,但在表述语言游戏过程中对认知、语境、甚至人类实践等问题进行了大量有意义的讨论。实质地看,维特根斯坦创造性地把语言、意义和关于语言的心理学功能地结合在了一起,他用“语言游戏说”对我们人类的认知运作规律进行了一种合理假设。认知是一种用符号来表征外部环境事件和自身感受的依规则操作的信息加工过程。心智的本质决定了认知取向必然带有语境的动态性、体验的涉身性、规则的意向性和表征的家族相似性等特点。以语境甚至实践作为切入点探讨语言游戏以及人类的认知过程,也许可以给我们更多的启示。总之,维特根斯坦对语言使用过程中认知因素的探寻将哲学研究的方向转向了社会、生活以及人的认知活动,“语言游戏说”在一定程度上诱发了当代语境论和实践观的形成。
[1]维特根斯坦著.李步楼译.陈维杭校.哲学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5,7.
[2]王寅.认知语言学之我见[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4,27(5):3.
[3]Brandt.Subjectivity in the Act of Representing: The Case for Subjective Motion and Change[J].Phenomenology and Cognitive Science,2009(4):145.
[4]魏屹东,常照强.当代认知系统研究的趋向与挑战[J].社会科学,2013(6):123.
[5]魏屹东.表征概念的起源、理论演变及本质特征[J].哲学分析,2012,3(3):118,102.
[6]魏屹东.“孪生地球”假设的哲学内涵与语境认知形式[J].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07(1):28.
[7]刘伟伟,郭贵春.英国语义学研究的历史传统与发展趋势(下)[J].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12,29(4):25.
[8]胡瑞娜.当代反实在论的语用分析走向[J].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32(4):74,78.
[9]邓小琴.我经验到因为——论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对20世纪语言学发展的影响[J].前沿,2010(24):183.
[10]魏屹东.语境论与马克思主义哲学[J].理论探索,2012(5):10.
[11]L.Wittgenstein.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M]. Trans.by Anscombe G E M. Oxford: Blackwell,1958:11,47,242,355.
[12]Searle J R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M].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1:11.
[13]郭贵春.语境的边界及其意义[J].哲学研究,2009(2):99.
[14]刘西瑞.表征的基础[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5):30.
[15]吴世雄,陈维振.范畴理论的发展及其对认知语言学的贡献[J].外国语,2004(4):38.
Viewsof"LanguageGameTheory"BasedontheCognition
ZHAO Yan-lin1,WEI Yi-dong2
(1.Headmaster'sOffice,ShanxiAgriculturalUniversity,TaiguShanxi030801,China;2.ResearchCenterforPhilosophyofScienceandTechnology,ShanxiUniversity,TaiyuanShanxi030006,China)
"Language Game Theory" is the core and basis of Wittgenstein's later philosophy. His key ideology is"Language games". Only through applying the language, can it be meaningful. The significance of words is the application. Representation connects language and meaning. Context reliability, living experience, rules observation and family resemblance in "language game Theory" reflect some features which human searched in cognition behavior. Since there are less studies on the cognitive role in this theory,the cognitive perspective is focused in this paper to explain the function of language in actual use.
Wittgenstein; Language game; Cognition; Context; Rules
2014-01-16
赵雁林(1978-),男(汉),山西太原人,硕士,主要从事思想政治教育和外国哲学方面的研究。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2BZX018)
B15
A
1671-816X(2014)06-0572-04
(编辑:佘小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