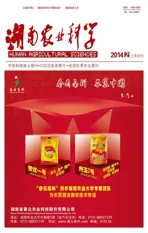非洲菊种质资源研究进展
2014-04-03李有清吕长平胡春梅
李有清,吕长平,胡春梅
(湖南农业大学,湖南 长沙 410128)
作为世界五大切花之一的非洲菊,其市场需求量非常大。据了解,国外年平均需求量在2 800万株左右,国内年均需求量则在6 000万~8 000万株之间。如此庞大的需求量,足以显示其在鲜花市场的重要地位。因此,非洲菊的栽培技术的提升对其市场供应量的提高十分重要。目前,非洲菊栽培技术方面的研究与应用技术虽然非常多,但能真正形成高质量、快速度、成规模的品种和栽培技术仍显不足。文章综述了非洲菊的种质资源的利用与研究的现状,强调非洲菊种质资源研究的重要性,以期为今后的非洲菊育种及分类鉴定工作提供相关参考。
1 非洲菊种质资源概述
非洲菊最早由雷曼1878年在南非德兰士瓦发现,同年布拉斯将其送到英国邱园。英国的林奇最早进行非洲菊杂交育种,他将非洲菊和绿叶非洲菊进行杂交,育出杂交种;其后,法国的阿德奈选育出了用于切花的非洲菊品种;1950年以后,在欧洲育成新的品种;1980年还育成矮生盆栽品种,花期几乎全年不断。日本也在重瓣非洲菊的育种上获得了成功。
非洲菊花色基因遗传丰富,且异质性非常高,其子代花型、花色差异大,因此由优良的杂交单株可借组织培养迅速大量繁殖成营养系,品种随着流行趋势更换很快,其花色以白、红、粉、橙、紫等为主,加上种间杂交融合容易,除以上固有色系外,也有许多中间色系。
近年来我国虽然加紧了非洲菊的育种工作,但是与国外相比,非洲菊栽培品种仍然不多。据农业部信息统计,在1999~2012年期间,国内非洲菊新品种虽然授权11个,但推广应用很少,且其中多数由云南省农业科学院培育,因此培育非洲菊新品种的任务仍较为艰巨[1]。
2 非洲菊种质资源遗传多样性研究进展
非洲菊种质资源研究的根本目的在于利用其进行非洲菊的新品种选育,提高育种效率。近年来,国内非洲菊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遗传育种、切花的保鲜、种质的保存,尤其是非洲菊的引种驯化以及组织培养与快繁等方面,利用分子标记技术对非洲菊种质资源遗传多样性的分析也有若干报道。
近几年随着对非洲菊种质资源研究的重视,也有若干研究报道非洲菊种质资源的主要性状的相关性分析及花色素组分。陈建等[2]分析9个非洲菊品种在花瓣试验中的特征颜色反应和紫外-可见光谱,结果表明组成不同花色品种的花色素为类黄酮、类胡萝卜素和花色素苷三大类,并对不同花色品种非洲菊的花瓣颜色构成做了初步的总结。这一研究工作为非洲菊的品种分类、色素化合物的分离和结构鉴定,以及非洲菊品种的花色改良技术研究提供了一定的依据。李云等[3]对13个非洲菊品种进行了主要园艺性状遗传相关实验及其通径分析,发现花径大、花梗粗、单株分株数多与产量的相关性达极显著水平,因此认为这3个表现性状可以作为主要选择性状对非洲菊进行遗传改良。以上两个研究从不同的一些特征元素角度对非洲菊种质资源进行了评价研究,对于非洲菊种质资源的分类整理和品种筛选在理论上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相关研究仍然不全面,需要开展更多更系统的研究工作。尽管如此,对不同品种非洲菊这些性状的特点的研究,为在分子水平上研究非洲菊种质资源遗传多样性提供了一定的基础。
国内外现有的非洲菊种质资源没有清晰的遗传谱系,而且对其遗传分化及多样性研究不多,主要是因为研究方法还不多且不成熟。通过运用AFLP技术及ISSR技术等从分子水平上进行非洲菊种质资源遗传多样性分析,有助于加快非洲菊的育种工作进程,也能为非洲菊的遗传改良和合理利用提供一定的依据。但是,国内这一方面的研究报道很少,只有文献报道了部分非洲菊品种的遗传多样性研究内容。
聂京涛等[4]利用ISSR分子标记技术对75份非洲菊材料进行了遗传多样性研究,说明了非洲菊具有丰富的遗传多样性。他们将非洲菊材料聚类结果与其花色、花型、管状花颜色、花径作比较,发现其呈现一定的相关性,认为这为非洲菊优良品种的选育奠定了一定的分子理论基础。钟海丰等[5]设计100条ISSR引物,利用ISSR分子标记技术对外引的22个非洲菊品种进行了遗传多样性及聚类分析,得出了和聂京涛等的研究一致的结论,即非洲菊具有丰富的遗传多样性,并且花瓣及花心颜色可以作为区分非洲菊品种分类及分析亲缘关系的初步依据。另外,吴莉英等[6]的研究为非洲菊AFLP分析材料的制作方法做了一个成功的示范,他们改进了CTABFREE洗涤法、CTAB法,并获得HMW基因组DNA;其中改进后的CTAB-FREE洗涤法提取的DNA纯度较高,其操作简单,并能有效地将非洲菊老叶中富含的酚类、多糖类物质去除,使得提取出的DNA的纯度、浓度都合符AFLP分析要求,取材也最方便。其研究还获得了非洲菊的清晰AFLP指纹图谱,为非洲菊的分类鉴定等相关研究提供了参考。
目前,对于非洲菊种质资源的分类研究还不够充分,缺乏广度和深度,仅仅停留在形态学方面适应市场应用的分类方法上。非洲菊的遗传多样性研究不仅能对非洲菊的遗传改良提供很好的依据,指明育种的正确方向,而且对于非洲菊种质资源分类和鉴定的研究也能提供分子水平的参考依据,对于有序化非洲菊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3 非洲菊引种研究现状
虽然国内对非洲菊的研究投入不少的人力及相关资源,但目前我国生产上应用的非洲菊优质品种仍然主要从国外引进,并且通过引种试验来观察其在国内的生长适应状况,进而评估其在国内有关地区的栽培利用价值,以筛选出适合栽培的品种推广应用,但自主培育的优良品种很少[4],且即便是培育出的新品种,能够进入生产实践的也极少。
如上所述,我国大部分的非洲菊生产品种都是从国外引进的,因而,在非洲菊的引种研究方面倾注了大量的力量,也有不少研究文献的报道。近年来,我国从国外引进试种的非洲菊品种有“Monza”、“Maria”、“Formosa”、“Nalacer”,改良种“Beatrisity”,荷兰新品种系列如“Beatrix”、“Pascal”、“Alami”、“Cathy”等多个品种,并已在上海、南京、新疆等多个地方推广应用。这些品种主要分布在上海、深圳、云南三地,进行大面积栽培[7],并且由于许多引进品种出现退化现象,有许多新的品种仍在不断地引入我国进行驯化栽培。另外,在国内培育出的新品种也有在其他不同气候地区引种驯化栽培研究的需要,且主要集中在国内品种以及利用国外引进品种培育的新品种跨地区引种驯化研究。
引种试验的方式均为大棚温室栽培中的有土及无土栽培。引种栽培评价指标主要包括生育期、植物学性状、花枝品质、产花量、抗性和切花瓶插寿命、定植成活率等[8-11]。常规的非洲菊引种试验已经有不少人做了研究,研究的目的是筛选出适合其所在地的土壤气候条件的非洲菊品种,并根据评价指标对所引种试验的非洲菊品种进行了详细的栽培表现的分级描述。如秦光义等[8]对从云南省农科院引进的10个非洲菊品种在日光温室进行3a的对比试验,根据产量、切花质量、抗病虫害和耐热、耐寒性各项指标分析了不同品种的表现差异,对10个品种在西北干旱冷凉地区的适应性进行了评价并筛选出了适应其生长条件的品种。金国林等[9]综合花色、秋冬产量及花的商品性等因素,通过对非洲菊19个品种进行栽培试验对比,筛选出适合浙北地区栽培的5个主栽品种,并结合东方人对颜色的偏好提出生产上红色品种与其他颜色品种种植的优化比例。桂敏等[10]通过25个非洲菊切花品种的试种观察,就各品种的生育期、植物学性状、切花产量、抗病性、切花瓶插寿命、商品性及主要性状各月变化的情况等方面进行了比较评价,据此推荐了11个综合性状较好的品种。姚丽娟等[11]对15个非洲菊切花品种进行引种试验,以不同品种的定植成活率、切花产量、切花品质、抗性等进行综合比较分析,筛选出6个综合性状表现优良、适合文成山区生产的品种。另外也有研究不同的栽培基质和施肥方式对不同非洲菊品种的影响。黄作喜等[12]采用不同配比的栽培基质及施肥方式研究了非洲菊7个品种在内江地区的栽培表现,并发现在基质配比中,蘑菇渣、堆土和珍珠岩的配比为1∶1∶1时,栽培的非洲菊的生长较旺盛,缺硼症比例最低。在施肥方式上,以复合肥做底肥时,非洲菊的长势超过对照,缺硼症比例低于对照。故利用传统的堆土栽培非洲菊,可施用复合肥提高基质的肥力,同时添加珍珠岩以改善基质的物理结构。
植物的引种驯化意义重大,不但能保护濒危植物,保存优良植物品种,丰富并优化当地植物物种种质资源,而且结合其他的相关技术如栽培、育种技术,能够培育出许多新的品种,如米丘林的“风土驯化学说”,在结合栽培育种技术与方法后培育了超过300个的果树品种[13]。在非洲菊的育种研究中,加大研究种质资源引种理论与方法的研究力度,是强化我国非洲菊研究工作的重要途径,并且引种成功的非洲菊品种可作为非洲菊育种工作的物质基础。
4 非洲菊种质资源保存研究进展
所谓种质,是指决定生物体遗传性状并将遗传信息从亲代传给后代的遗传物质。种质资源的调查、收集、保存和评价是科学开发利用植物的基础,对最大限度地发挥种质资源利用潜力具有决定性的作用[14]。非洲菊种质资源的收集与保存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许多有重要特性及价值的非洲菊品种逐渐在国内由于气候条件与栽培技术的限制,普遍出现品种退化的现象,导致一方面国家需要花费大量资金购买国外的优质种苗[15],另一方面,随着新品种的持续推广,会造成已有的非洲菊优质种质资源的逐渐消失。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迄今为止有关非洲菊快速繁殖的研究较多,而专门对于其品种收集与保存的研究只有少量报道。组织快繁既是一种解决非洲菊优质种苗短缺的有效途径,也是一种解决非洲菊种质资源保存的基本方法,它能快速建立一个高效率的植株再生系统,避免了非洲菊用种子繁殖极易产生变异和退化,并且其结实率低,种子寿命短,发芽率也很低的先天缺陷。目前,国内虽然有许多传统的种质资源保存方法,但是关于非洲菊种质资源保存的研究,仍集中于优化组培保存法的相关保存条件及其方式的改进。
吕长平等[15]做了将近几年流行的玻璃化法超低温保存法应用在非洲菊种质资源保存中的研究,并试图建立其再生系统。沈强等[16]则针对增殖培养基和生根培养基进行了试验,研究了不同培养基及其激素浓度对外植体存活率及变异情况的影响,结果表明:以花托作为外植体可大大降低污染率;同时用KT、6-BA搭配和添加较高浓度细胞分裂素、低浓度生长素有利于提高花托不定芽的分化率;为了利于试管苗的生根,并防止内源激素的增加引起变异,增殖培养基中6-BA的浓度应控制在1~2 mg/L,并需要结合“MET”和低温同时进行。
[1]杨 尧. 不同化学诱变剂对非洲菊离体培养的影响[D]. 杭州:浙江大学,2012.
[2]陈 建,吕长平,陈晨甜,等. 不同花色非洲菊品种花色素成分初步分析[J]. 湖南农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9,35(1):73-76.
[3]李 云,李 涛. 非洲菊主要园艺性状的遗传效应研究[J]. 湖北农业科学,2009,48(5):1176-1177,1188.
[4]聂京涛,潘俊松,何欢乐,等. 非洲菊部分品种资源遗传多样性的ISSR分析[J].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农业科学版),2011,29(3):76-82.
[5]钟海丰, 黄宇翔,钟淮钦等. 22个非洲菊品种遗传多样性ISSR分析[J]. 南方农业学报,2012,43(1):1-4.
[6]吴莉英,唐前瑞,李 达,等. 非洲菊的AFLP指纹图谱构建[J]. 湖南林业科技,2008,35(4):8-10,23.
[7]孙 强. 非洲菊育种技术及优良品系选育初步研究[D]. 南京:南京农业大学,2007.
[8]秦光义,魏兴琉,郭晓成. 不同非洲菊品种在日光温室的栽培表现[J]. 西北农业学报,2003,12(3):136-139.
[9]金国林,李红煜,童 敏. 非洲菊品种引种试验[J]. 浙江农业科学,2012,(3):344-346.
[10]桂 敏,陈 敏,龙 江,等. 非洲菊切花品种引种试种研究[J]. 北方园艺,2010,(10):93-96.
[11]姚丽娟,蒋加勇,钱仁卷,等. 山区非洲菊切花品种引种栽培试验[J]. 浙江农业科学,2013,(4):432-434.
[12]黄作喜,李 琴,周市会,等. 非洲菊的引种栽培研究[J]. 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10,25(12):56-58.
[13]杨书才,王 华. 植物引种驯化理论与实践评述[J]. 吉林农业,2011,(6):302.
[14]戴思兰. 中国菊花与世界花卉园艺[J].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学报,2004,(3):1-7.
[15]吕长平,栾爱萍,陈海霞,等. 玻璃化法超低温保存非洲菊茎尖及植株再生[C]. 中国观赏园艺研究进展,2012.
[16]沈 强,衣常红,赵 娟. 非洲菊品种的收集、繁育及保存研究[J]. 上海农业学报,2005,21(1):45-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