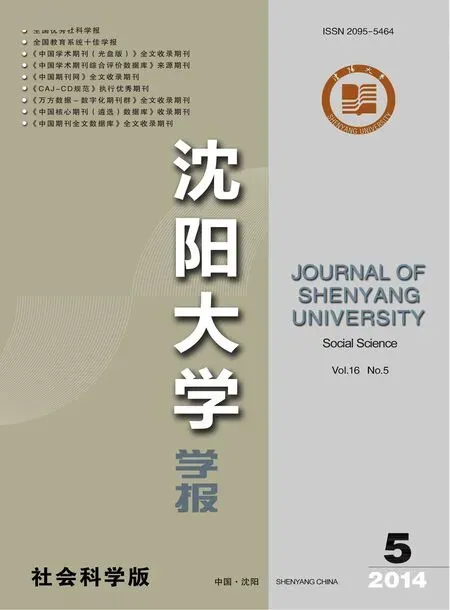全球正义:内涵、框架及限度
2014-04-03靳志强
靳 志 强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 党的建设教研部, 福建 福州 35000)
全球正义:内涵、框架及限度
靳 志 强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 党的建设教研部, 福建 福州 35000)
分析了全球正义的内涵、适用框架及其限度等问题,指出在全球化时代,全球正义不仅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还是一个重要的实践问题,相较于传统的正义观研究,全球正义问题是在跨国的层面展现的,它不仅具有一般正义问题的共性还有其内在的规定性。全球正义不仅仅是传统正义在跨国层面的延伸,在全球主权无法成立的条件下,对全球正义的呼唤也是突破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的客观诉求,更是对当下世界贫富分化日益严重的理论应答。
全球正义; 政治哲学; 内涵; 框架
我们生活的世界并非完全正义。对于这一点,在政治伦理的视域内少有争议。但问题是,如果当下的世界是作为非正义而存在的,那么什么才算是正义?如果正义真的存在的话,我们又应如何在全球化时代建构正义?如果我们真的能够建构出一套具有普遍适用的全球正义观,我们又应在什么样的平台上把它付诸实践?对上述一系列问题的追问和思考,一方面凸显正义问题的复杂性和多元性,任何一个层级的问题如果不能得到建构或得不到恰当的建构都会影响到下一层级问题的解决。另一方面,也正是因为正义之惑的存在,才使得正义问题的研究迷人而又散发光彩,当你因困惑不解而打算抽身离开时,你又能切身体会到(非)正义就在你的身边。
一、 全球正义的内涵
什么是正义呢?对于这一问题人们并不陌生,古往今来,相关著述颇丰。例如,在亚里士多德的世界里,“各取所值”[1]、得所应得就是正义;在查士丁尼的眼里,“正义是给予每个人他应得的部分的这种坚定而恒久的愿望”[2];在西塞罗看来,正义则是“使每个人获得其应得东西的人类精神意向。”[3]由此可见,对正义的理解和探讨总是围绕着利益展开的。本文不打算具体罗列关于正义的各种陈述,也不打算沿着利益分配之管道具体探讨如何分配利益以使这个社会充满正义感,而是试图在一个更为抽象的层面建构正义,并使之可普遍化。
(1) 正义是一个价值范畴,价值是主客体之间的一种效用关系,正义的价值就在于,确立或者说是评估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交互过程中的正当性、有用性。
(2) 正义的目标应是为上述各种交互过程确立一个规范性原则,并且该原则应具体化为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制度规范。
(3) 正义应关照人的现实生活,把理论上的正义转化为具体的正义实践。
从上述三个基本观点出发,可以将正义的本质概念化:正义是用于评价主客观世界活动正当性的终极价值。它立足于人的本质,为人的交往加上制度规则,并对现实的人提供终极关怀。这样,可以得出一个关于正义的公式:正义≈价值+制度+人的关怀。其中,价值、制度、人的关怀缺一不可。缺少了价值关怀的正义,就缺少了为人生活的经验世界立法的依据,缺少了制度关怀的正义,价值关怀就缺少了政治制度上的支点,其对人的关怀也就难免陷于塌陷的地位。因此,罗尔斯才会讲“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所谓主要制度,我的理解是政治结构和主要的经济和社会安排。……主要制度确定着人们的权利和义务,影响着他们的生活前景即他们可能希望达到的状态和成就。”[4]
那么,全球正义的内涵是什么呢?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正义,全球视野的正义问题涉及两个层面。
1.国与国之间的秩序问题
在全球视野内,国家之间的正义就是要确保国家与国家之间价值观上的相互包容、经济上的平等地位、文化上的相互承认、资源上的共享身份、军事实力上的平衡,等等。上述目标的达成或实现,有赖于一套公平合理的国家之间的行为准则或者说是秩序规则,比如,人们常说的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原则,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原则,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原则,等等。相反,打着主权高于人权的旗号肆意干涉别国内政的行为,或者在国际社会恃强凌弱、执行双重标准的做法,都是非正义的。因为前者损毁了平等交往的主体、后者破坏了平等交往的原则。正因如此,人们才强调要打破旧的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建立一个新的公平合理的国际秩序。
2.应该着眼于跨国的人与人之间的平等问题
无论正义还是全球正义,其终极指向都应是正义的最细小的主体——即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具体而言,全球正义应该致力于在资源、财富、健康、安全、教育、生产、发展等诸多层面赋予不同国家、不同肤色、不同民族的人以同等的权利,包括参与权、享有权等。当然,在这里要特别注意,不能把人的满足混同于权利的满足,不能把人的正义混同于当权者的正义。总之,只有从国与国和人与人的双维视角出发去理解全球正义,正义的内在规范性所要求的价值、制度、人的关怀等才不会落空,在实践中才不会因忽略正义主体的现实需要而陷入“乌托邦”境地。
二、 全球正义的框架
全球正义不仅在内涵上有别于传统的正义,在框架上与传统的正义框架也有分歧。近代以来,威斯特伐利亚框架确立了现代民族国家的主权原则,划定了主权国家的领土范围。相应的,在该框架内关于正义的讨论都是在一个假定的有边界的主权独立的民族国家内进行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带动的政治、文化以及交往的全球化,关于正义问题的讨论似乎就变得没有那么简单了。关于正义的讨论单元,早已跨越了威斯特伐利亚框架框定的有边界的主权国家的领土范围。比如,2008年的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对世界各主要经济体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是经济上的,而且是政治上的、文化上的、价值观上的。又如,环境保护的话题也早已不再是一国范围内的责任,而是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所有人共有的责任和义务,世界环保组织的成立、《京都议定书》的签订就是例证。再如,互联网的普及早已使全球“互联”,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发生的事情,都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在全球传播、形成全球性的公共话题。正如弗雷泽所言:“无论问题是全球变暖,还是移民、妇女权利,或者贸易条款、失业、反恐战争,公众舆论的当前动员很少停留在领土国家的边界上。”[5]99
此外,另有一些情况则在权力层面直接突破了威斯特伐利亚所框定的民族国家的正义框架。比如,欧盟成员国的国家法院要执行欧洲联盟法院的裁决;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的国内法院,要执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组织的法院判决。这说明,正义所要讨论的范围并不局限于一国内部,而在跨国范围的权力层面依然存在。这给人们提出了一个重要任务,不同于一般意义上主权国家内部的正义,全球正义或者说是“后威斯特伐利亚”世界中的正义问题日益凸显。所以,弗雷泽认为全球化世界中的“跨越国界的社会运动正在争论着一种国家框架,在这种国家框架中,正义的冲突已被历史性地加以了定位,并且寻求在一个更广阔的尺度上重新图绘正义的边界。”[5]1
既然全球化进程中传统探讨正义的民族国家框架已被冲破,人们又应如何在“后威斯特伐利亚”的框架中重新图绘正义呢?目前为止,有三种理论观点:
1.国内与国际二分法的正义构想
如罗尔斯通过设计一种“原初状态”,确立了公平正义两原则:第一条原则是“平等自由的原则”,该原则确定了每个人都有与他人同等的权利和自由。第二条原则是“差别原则”,该原则承认社会上存在着智力、教育、体力等方面的差别(不平等),而且还认为应给予弱者以最大的照顾和机会。但值得注意的是,第一条原则是绝对的,而第二条原则是相对的、补充的。1999年,罗尔斯在他所写的《万民法》一书中进一步将他的正义理论由国内拓展到全世界,但是正义的主体或者说是正义的适用范围仅仅限定在遵守万民法之人民,他明确反对差异原则在全球或跨国层面应用。换句话说,罗尔斯的全球正义框架是国内、国外有别的二元正义构想。
2.以人格基础作为划分正义框架的界限
不同于罗尔斯,另有一些哲学家,如玛莎·努斯鲍姆(Martha Nussbaum)等人通过诉诸人格标准来搭建正义的平台,对他们而言将一个人的集合体转变为正义的伙伴主体是有区别的人性特点的共同占有,如自治、合理性、语言、受难的能力等。这种观点是以人格基础作为划分正义框架的界限,这对传统的主权领土框架进行了批判性审查。但这种观点存在致命的缺点,“由于高傲地遗忘了实际或历史的社会关系,所以,它不加选择地将身份与涉及每件事的每个人相符合。通过采用这种以一概全的全人类框架,它阻止了这样一种可能,即不同问题需要不同的正义框架或尺度。”[5]73
3.通过诉诸相互依赖的社会关系来构建正义的理论框架
除上述两种观点外,还有一些人,如彼得·辛格(Peter Singer)通过诉诸相互依赖的社会关系来构建正义的理论框架,对他们来说,使一个人的集合体转变为正义的伙伴主体是这些主体在因果关系网中的客观叠加,换句话说,在同一个事件中所有受到影响的人构成了正义的主体范围。但弗雷泽认为这一策略“由于不能识别道德上相关的社会关系,所以,它在抵抗它试图回避的以一概全的全球主义时陷入麻烦。”[5]74
由于上述三种观点都具有难以克服的内在缺陷,弗雷泽构思了一个新的“所有人受制约原则”的竞争性框架。根据这一原则,将个人的集合体转变为正义的伙伴主体的既不是成员资格或国籍、也不是抽象的人格占有或相互影响的因果事实,而是他们共同受制于的一种治理结构。她说:“所有受制于一个给定的治理结构的人都有与之相关的作为正义的主体的道德身份。”[5]74从而将道德关怀的范围与受制约的范围相互匹配。当然,弗雷泽的逻辑能否成立完全取决于人们对“所有人受制约原则”的理解。比如一些设定全球经济、卫生或安全规则的跨国机构,如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国际原子能机构、国际刑警组织,等等,从形式上讲,这些机构的成员国都对他们参加的国际机构背负道德义务,受他们所参加的机构的制度规则的制约,所以同一个跨国机构的成员国之间背负了道德义务、构成了正义的主体。而实际上,许多国家同时属于几个不同组织的成员,如果那样,作为正义身份范围是多重的,这些跨国机构如果想真正发挥作用,还得回到成员国国家内部,也就是还得依靠民族主权国家的强制力。这样看来,无论何种原则、何种建构方式,“后威斯特伐利亚”世界中的全球正义,仍和民族国家紧密联系,甚至不可分割。
三、 全球正义的实践
如果全球正义能够成立,它应通过什么样的管道或者途径付诸实践呢?从逻辑上讲,必须考虑到四方面的问题:
1.正义与主权之间的关系问题
既然传统正义理论是在一个主权独立的民族国家内探讨的,那么,在“后威斯特伐利亚”的正义理论中是否存在全球主权呢?如果全球主权并不成立,人们又应依赖什么样的平台在“后威斯特伐利亚”框架下建构正义呢?实际上,国家主权是一国在国际法上固有的处理对内对外一切事物的权力,而无需国际法的赋予。如果全球主权真的能够成立,还应存在一个能够掌握全球主权的国际机构,且世界上的相关国家应把主权进行全面的让渡。即便是联合国能就国际和平、安全、温饱等问题达成决议,它本身并没有强制的执行力,更无法奢谈全球主权。再如,欧盟的各成员国,他们也只不过是有强大欧盟做背景的主权独立的国家,因为欧盟的存在并没影响成员国的国际法主体地位。像其他的国际性的组织,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卫生组织、世界银行等,它们的运作来自于成员国的资金支持,它们的权力范围来自于成员国的授权、受成员国的控制,它们的目标也仅仅是成员国相互妥协商定的,所以它们难以真正做到凌驾于诸多国家之上、作全球正义的裁判者。由此可见,到目前为止尚无任何迹象能够把世界上所有国家的主权收罗进同一个口袋,所以全球主权在可预见的时间内难以成立。尽管如此,像联合国和欧盟这样的国际组织,还是在跨国的层面搭建起一个可以沟通、对话甚至是做出全球或区域构想的平台,依然可以算作“后威斯特伐利亚”世界中建构正义的一个重要管道。
2.如何应对不同国家之间文化冲突和全球价值观重建的问题
根据亨廷顿的理解,未来世界国家之间的冲突,将不再是意识形态的或经济的问题,而是不同文明圈之间的冲突,也就是说文明的冲突将是未来世界最大的威胁。如果照亨廷顿的理解,全球化时代的政治格局正在以文化和文明为界重新形成,那么全球正义的实现则依赖于如何在后冷战时期、在不同的文明之间形成一种相互竞争、相互宽容、相互承认的文明秩序。当然,与文明秩序相关联的另一个重要的序列就是价值观问题。毋庸讳言,如果说文明的冲突属于未来世界的问题,而价值观的问题就是眼前世界的问题。当今世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根本性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冲突,在根本上是无法解决的,只不过他们在国家利益面前找到了暂时的一致性,也就是说各个国家的国家利益在不同程度上不是消解而是屏蔽了意识形态矛盾和价值观的冲突。特别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外扩张战略的转变,使之前直接的军事占领转向新的文化殖民或价值观的占领。由此可见,在不同社会形态的国家之间,矛盾、冲突、竞争也一刻未曾停息。那么,在这种条件下,全球正义的文化基础不能完全具备。
3.全球分配正义的问题
全球范围内的资源、财富、原材料如何被分配或者能否被公正地分配,依然关系到全球正义的实现。高收入国家以其只占世界人口15.7%的人数拥有79%的世界收入(World Bank2006: 289)。至于何以造成这样的结果,有两种鲜明对立的见解。例如,世界主义者就认为,发达国家的财富积累是通过其对其他国家的剥削和殖民获得的,其原始积累本身就是一个赤裸裸的不光彩的历史。相应的,不发达国家的贫穷和落后是由于被殖民、掠夺导致的,在他们看来,罗尔斯的分配正义的差异原则应该被延伸到国际层面。当然,共同体主义者认为,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是由于不同的文化和制度差异造成的,贫穷国家的领导精英应该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们反对发达国家承担贫穷落后国家的道德义务。在实践中,无论是全球性分配正义的诉求还是落实全球分配正义的实践都是软弱无力的。例如,世界上贫穷落后的国家在国际社会的交往中往往处于不利的地位,他们发出的声音要么不被重视,要么处于一种被失语的状态。即便依赖世界上最大的维持世界秩序的联合国组织所制定的千年发展计划,其目标的实现,除了要靠贫穷国家自己的发展之外,还仰仗发达国家真正兑现承诺、增加发展援助。
4.国家利益与全球利益的关系问题
如前所述,正义的核心是利益,全球正义的核心要义仍然与利益问题密不可分。利益本身是中性的,它不具有属人的特性,但当利益与利益主体结合起来的时候,利益就变得具有明显的倾向性。从全球的视野看,国家利益是一个难以回避的现实问题。例如,《京都议定书》是一个在跨国层面建立起来的一个气候正义的协定,日本曾经以该议定书的签署地京都命名为荣,但目前日本政府“坚定”的拒绝了《京都议定书》的第二期承诺,这实际上就等于是扼杀了世界上至今唯一有效的国际气候条约,由此看来,在国家利益与全球利益的横摆中,国家利益无形中消解了全球正义之诉求。与日本相反,还有一些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坚定的执行了《京都议定书》的各项承诺,从而把国家的利益与人类的长远利益统一起来。
通过对上述四个问题的鉴别、分析,人们可以勾勒出一个关于全球正义的可能的管道:在全球主权并不存在的情况下,不同国家可以在低烈度的文化冲突或价值观分歧的前提下,通过协议或者授权搭建起一个“所有人受制约”的正义框架并做出建设性的决策,以弥合全球贫富分化,以及国家利益与全球利益之间的冲突。
在全球化时代,全球正义不仅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还是一个重要的实践问题。相较于传统的正义观研究,全球正义问题是在跨国的层面展现的,它不仅具有一般正义问题的共性还有其内在的规定性。全球正义不仅仅是传统正义在跨国层面的延伸,在全球主权无法成立的条件下,全球正义理论和实践面临更多的争议和难点。如何在“后威斯特伐利亚”世界中构建一个普遍适用的正义框架,如何处理好不同国家价值选择上的冲突与分歧,如何平衡国家利益与世界人民的福祉等一系列问题有待更深入的理论探究。
[1] 亚里士多德. 尼各马科伦理学[M]. 苗力田,译. 北京:中国社会文献出版社, 1990:94.
[2] 查士丁尼. 法学总论[M]. 张企泰,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65:5.
[3] 西塞罗. 论共和国、论法律[M]. 王焕生,译.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7:216.
[4] 约翰·罗尔斯. 正义论[M]. 何怀宏,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8:303.
[5] 南茜·弗雷泽. 正义的尺度[M]. 欧阳英,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责任编辑王立坤】
GlobalJustice:Connotation,FrameworkandItsLimits
JinZhiqiang
(Research Departmentof Party Building, Fujian Provincial Committee Party School of CPC, Fuzhou 350001, China)
The connotation, framework and the limits of global justice are analyzed. It is pointed out that,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global justice is not only an important theoretical problem, but an important practical issue. Compared to the research on traditional concept of justice, global justice issue is in transnational level, it not only has the general common justice issues as well as its inherent determination. It benefited from the need of global justice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on one side, also an objective demands to break through unfair unreasonable old order o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economy, and a theory response to the increasingly divided between rich and poor in the current world.
global justice; political philosophy; connotation; framework
2014-02-20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青年博士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课题(11YJA710079)。
靳志强(1982-),男,山东菏泽人,中共福建省委党校讲师。
2095-5464(2014)05-0611-05
D 08
: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