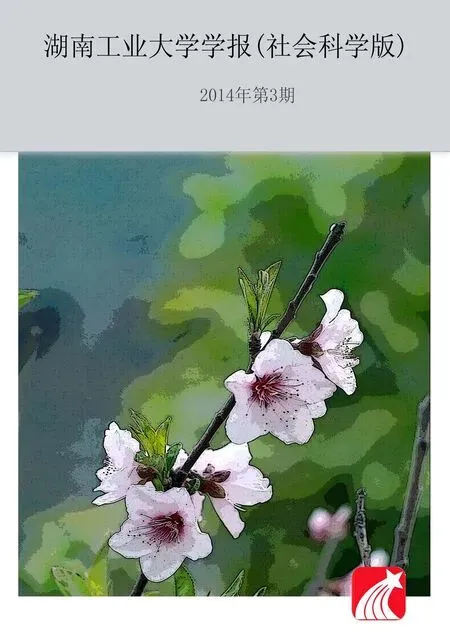卢卡奇对西美尔的态度转变历程
2014-04-01王园波
王园波
(江苏康缘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党委办公室,江苏 连云港 222047)
西美尔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他不仅是卢卡奇最早的思想启蒙者之一,也是对卢卡奇影响最深、伴随他思想发展时间最长又最为他熟悉的思想家之一。卢卡奇早在1904年就开始阅读西美尔的著作,1905至1914年与西美尔保持着密切往来,1918年为西美尔的逝世写下祭文,1955年又对西美尔的思想进行了全盘清算。谢胜义认为1910年左右的卢卡奇“在思想上似乎很难跳出席默尔的某些理论范围之外,而自行发展”。[1]弗里斯比也认为:“只要人们不着意从其政治立场的改变来看待其思想的根本变化,卢卡奇著作中一直存在的西美尔影响的痕迹就不足为奇。”[2]综览卢卡奇的一生,他对西美尔的态度经历了从着迷、疏离到批判的过程。
一 着迷于有魔力的西美尔
卢卡奇1885年生于匈牙利布达佩斯,1902年进入布达佩斯大学,由于在他看来布达佩斯大学的教授们“没有一个对我有重大影响”,[3]206于是他偏离自己社会科学的专业,而将兴趣重心放在了文学艺术之上,在大学期间就阅读了西美尔的著作。1905年卢卡奇怀揣成为文学史家的梦想前往柏林,在聆听了西美尔在柏林大学的讲课之后,瞬间就被西美尔的“魔力”[4]33所吸引了。1906年寒假,卢卡奇再次前往柏林加入了西美尔的文化沙龙,直到1910年他都在西美尔的门下学习。1910年后,卢卡奇与西美尔依然保持着书信往来。1912年,卢卡奇听从布洛赫的建议留在了海德堡,进入了韦伯的文化圈。韦伯和西美尔一样,每个星期天在家中举行讨论会时卢卡奇表现活跃,给韦伯留下深刻印象。但在韦伯的讨论会中依然可以见到西美尔的身影,韦伯夫人在回忆中曾说“有几回是格奥尔格·西美尔夫妇为整个气氛定了调子”。[5]此后,1914年西美尔前往斯特拉斯堡大学任教,而卢卡奇也在1915年至1917年多次在海德堡与布达佩斯之间穿梭。1917年卢卡奇回匈牙利,次年参加共产党,而1918年西美尔去世,西美尔与卢卡奇直接的交往到此为止,但此次相遇却为卢卡奇全面系统学习西美尔的思想提供了契机。
谈及西美尔对自己的影响,卢卡奇曾说“西美尔的《货币哲学》……是我的‘文学社会学’的榜样……我一方面依照西美尔的榜样使这种‘社会学’尽量和那些非常抽象的经济学原理分离开来,另一方面则把这种‘社会学的’分析仅仅看作是对美学的真正科学研究的初期阶段”。[3]206-211由此,卢卡奇自觉《现代戏剧发展史》本质上是“西美尔的哲学”,[4]47而《小说理论》则是青年时代阅读西美尔等人带来的“精神科学倾向的一个典型产物”。[6]1973年发现的海德堡手稿,也证实了卢卡奇早年曾研究西美尔的《面容的美学》《货币哲学》等著述来为自己的文学社会学汲取营养。[7]卢卡奇对早年迷恋西美尔自认不讳,1917年他在简历中写到在德国听西美尔的课给他的激励和帮助“具有决定意义”。[3]206西美尔对卢卡奇的这种决定性的影响在卢卡奇的《现代戏剧发展史》和《心灵与形式》中表现最为明显,尤其体现在两者对形式概念的运用以及他们的悲剧性体验上。
西美尔继承了康德的先验形式思想。在西美尔的认识论中,使认识成为可能的条件的形式和通过认识而明确的经验内容必须加以区分,正如他将社会化的形式作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加以界定,而不是将社会内容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但西美尔反对像康德那样制定一张特定的范畴表的形式对认识的先验性条件进行确定,而是提出了看似矛盾的相对先验。如果说先验形式在康德那里是绝对的,是认识的必须条件,是纯粹理性形式的话,那么西美尔则更多是借助一个对形式的假定试图达到认识社会、认识生命的目的。毕竟在西美尔的时代如何认识整体的科学知识已经不是需要加以探究的问题,相反,科学知识已经成为事实的存在为人们所普遍接受。由于西美尔的相对主义,他对形式界定有些飘忽不定,他的形式概念不仅有先验的成分也有经验的成分。社会学中,他将竞争、家庭、婚姻、游戏等都视为形式,而又认为“经验的、社会的、生活的先验是:生存并非完全是社会的;我们塑造我们的相互关系,不仅在我们的个人人格的没有进入相互关系的部分的消极的保留物中进行;这一部分不仅通过一般的心理学的联系,对心灵里的社会的进程产生影响,而且恰恰是它处于社会的进程之外这一形式上的事实,决定着这种影响的方式。”[8]同样,西美尔将艺术、技术、经济等一切人的活动都纳入到形式的考察之中,认为一切文化都是作为人的生存形式而被创造出来的,而形式又以自己的逻辑展开,有着自足的特性。
西美尔对形式的理解在卢卡奇那里得到了共鸣,卢卡奇早期的思想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对形式的关注,卢卡奇曾说“文学中真正具有社会性的东西是形式”。[4]39他模仿西美尔的做法,将艺术作品的形式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但是他并不是站在形式与内容的对立的基础上进行理解,而是将艺术的概念统一定位在形式之上,在他看来,形式同样是先验的东西,任何体验在形式上已经被体验了。同时,由于卢卡奇又受到西美尔生命哲学的影响,将西美尔的“生命与形式”概念类比到了自己的《心灵与形式》之中,西美尔接受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将生命看成持续不断的绝对延续,生命的每个瞬间都是生命的全体,生命的不间断流动就是生命所具有的唯一形式。而卢卡奇则在1908年《关于易卜生的见解》中写道“所谓形式并不是说可以随意穿上和脱下的衣服,它在本质上并不独立于穿衣服的人,因为形式、技术是从最深层的心灵的主要因素中产生出来的东西”,[4]55在此,他对生命形式的看法与西美尔如出一辙。如果说卢卡奇对形式有什么超越西美尔之处的话,可能仅是因为他将形式的概念充分运用到了对艺术作品的分析之中,《现代戏剧发展史》、《心灵与形式》等都是以形式为核心展开的著作,因此,卢卡奇的形式也是一种审美形式。比如他曾说“形式把生活的素材组织成一个独立自足的整体,规定了它的速度、节奏、起伏、密度、流动性、硬度和软度;它强调那些可感受的重要部分而排出那些不太重要的东西;它将事物或者置于前台或者置于背景之中,将它们组合成一个模式”。[9]但是艺术不过是一种文化现象,依然属于生存形式的外化。卢卡奇无论是从小而言之的艺术形式还是从大而言之的文化形式对戏剧、小说展开的研究都有着更为深刻的目的。在资本主义的异化面前,他试图打破心灵和现实的壁垒,探索出真正的形式存在的可能并建立一种新形式,创造一种新文化,以结束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悲剧。
文化悲剧是西美尔对现代性危机的精辟诊断,在他看来,文化意味着个体通过对事物的培养来达到个体的培养,而随着文化发展的日渐成熟,文化危机也愈益严重。“首先,生活的目的臣服于其手段,从而不可避免地使许多不过是手段的事物被人们认为是目的;其次,文化的客观产品独立发展,服从于纯粹的客观规则,二者都游离于主体文化之外,而且它们发展的速度已经将后者远远地甩在了后面。”[10]173客观文化的发展速度已经远超主观文化,造成了对主观文化的压制,从而文化危机在所难免,文化悲剧无所不在,除非文化发展能够得到主体文化的不断反抗或者通过社会动荡暂时挽救走向解体的文化生活,不然文化将会发展到灭亡。因此在西美尔看来:“文化的命运就是一场不断延迟的危机……面对这场以一己之力无法衡量的浩大危机,我们被深深地震撼了……不论是否意识到,这是每一个人灵魂的危机。”[10]184-185西美尔敏锐地捕捉到了现代社会文化危机的存在,然而由于文化危机的普遍存在和文化危机的根深蒂固甚至已经渗入每个人的灵魂,在不可避免的文化危机面前,他陷入了莫大的悲情之中,这种悲情也蔓延到了卢卡奇那里。卢卡奇在成为富有激情的共产党革命者之前,也深受悲剧性体验的困扰。暂且不提卢卡奇青年时期恋爱的失败以及1911年遭受申请布达佩斯大学教授资格的失败和同年初恋情人伊尔马的自杀给他带来的创伤记忆,在《现代戏剧发展史》中的一段话就足以证明卢卡奇的悲情论调。“始于18世纪的戏剧时代已经结束了吗?我们所见到的戏剧形式(以悲剧为顶点)究竟完结了吗……我们仅仅感觉到这些疑问的沉重,也只是感到惟有时间才能予以回答”。[4]49-50也许对他们而言,作为资本主义文化危机日益突显的时代中的思想家,对文化发展的思考正是基于他们的担忧和不满,而在没有找到根本解决的方法之前,所有的思考都将蒙上悲剧的色彩也是在所难免。
二 疏离过渡哲学家西美尔
卢卡奇一生的思想来源极其驳杂,思想转变也是几经曲折,里希特海姆喻其思想为“当时正处在空前大危机前夜的文明的一面镜子”,[11]正是由于认识到了其思想的庞杂性。因此,虽然卢卡奇曾痴迷于西美尔的思想,但也很快就看到了西美尔的不足,早在1910年左右就产生了疏离西美尔的念头。在1910年的信中他曾说“西美尔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对我关注(上一次我曾经被迫在他家花了两个多小时),但他能给我的东西很少;不论我能由他那里学到什么,我在很久以前早已学到了”。[12]在访谈也曾说“我……对西美尔的轻浮则作了批评,因此我们之间的关系疏远了”。[13]45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在对待战争的态度上,卢卡奇与西美尔再次表现出了明显分歧,西美尔给韦伯夫人的信中写道“如果卢卡奇不能理解这次战争伟大意义的话,那么事情就没有希望了。对这次战争只能是直观地理解,在这种情况下,同他谈论这个问题也就没有丝毫意义了。”[13]15
也许只有保持一定的距离才能更为清楚地看清事物的面目,当卢卡奇远离了对西美尔着迷的岁月之后,在1918年为西美尔去世而写的祭文中,对西美尔进行了较为客观的评价,也是迄今为止西美尔的评价中被认为是最为准确的评价之一。卢卡奇认为“西美尔无疑是整个现代哲学最重要、最有趣的过渡人物”。[14]171西美尔独特的思想风格吸引了一大批青年学子拜倒在他的门下,虽然他没有做到像李凯尔特那样形成自己的学术门派,但他却不失是一位伟大的启蒙者。很多人称赞西美尔的聪慧,而卢卡奇认为依然没有触及西美尔的本质,因为西美尔拥有的是哲学家的本色,不仅能洞察到最细微的日常现象,也能敏锐地发现不为人知的哲学事实,因此他称西美尔是“我们时代最伟大的过渡哲学家”。卢卡奇中肯的评价丝毫没有掩饰他对西美尔的称赞,这正是他对卢卡奇曾经着迷的情感体现,然而卢卡奇在疏离西美尔之时也正是敏锐地把握住了西美尔的过渡性。他称“西美尔是位伟大的启蒙者,却并非是伟大的育人者,也并非是真正的完成者”[14]171正是这个意思。在他看来,西美尔的印象主义做派本质上就是一种过渡形式,艺术上的印象主义就是生命反抗那些过于僵化、不足以塑造生命完整的形式,因此是十足的过渡现象。同时,卢卡奇称西美尔是“过渡哲学家”还由于西美尔的多元主义方法论。人们习惯将西美尔的多元性和不成体系作风视为相对主义,但卢卡奇认为西美尔虽然描述了许多哲学规定方式,但他并不相信任何一种先验的哲学把握方式可以理解生命的整体。
“过渡哲学家”的判断不仅成功地把握住了西美尔的思想底色和思想风格,而且也能够将西美尔在时代思潮中的坐标勾画出来,倘若我们能够祛除习惯上对“过渡”的贬义成见,就可以发现这是极具说服力和准确性的判断。其实早在1901年西美尔的好友约尔就曾称西美尔是一位“时代哲学家”,过渡的意味已经隐约可见。过渡不仅联系着新与旧,过去与现在,也有暂时性的含义在其中,其形成的张力关系正是西美尔的特性所在,毕竟时代“恰恰是借助于一种单单与现在相关的时代意识的瞬间特性与其他的历史时代区别开来”,[15]而西美尔的一生正是对现代社会展开了一项富有哲学意味的现代性考察。
而北川东子则从另一个层面也证实了西美尔的过渡性。西美尔在黑格尔死后(1831年)二十多年才出生,而在海德格尔发表《存在与时间》(1927年)十几年前去世,而这段时期可谓是德国哲学界“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李泽厚语)的年代。学院的哲学研究逐渐走向科学化的闭塞状态,黑格尔般以思想把握时代的声音逐渐退隐,而一心追逐哲学的西美尔则陷落在这个尴尬的时代孤独探索。“如果早些时候出生的话,在黑格尔死后,就会背负上在体系哲学中进行思考的命运……也许就会创造出形而上学的新形式……如果他更晚些出生,活到1945年,并能体验纳粹主义和大屠杀的话,他就不会写出那种不彻底的‘生的形而上学’,而会在其思想中把彻底的绝望和希望交织在一起吧。”[18]5-6北川东子惋惜的语言实际上也透露着西美尔思想的过渡性,然而正是由于西美尔在过渡中的对哲学的坚守,才使得哲学在自然科学横行的时代呈现出了另一番风景。曾对西美尔提出的思想进行过深入思考的人物不仅有卢卡奇,也有本雅明、阿多诺、布洛赫、韦伯、马尔库塞等等,就连20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海德格尔早年也曾致力于西美尔研究,而这些人如今看来都是德国乃至欧洲的思想巨擘。因此,德国现代哲学正是越过了西美尔这座桥梁才达到新的阶段,虽然西美尔没有建立一种体系性的哲学理论,但是他“从最宽泛、最常识的观点出发,从头讲述了‘哲学之为何物’”。[16]12尤其是西美尔将哲学与体验相互融合,将哲学作为体验的场所,将体验作为思考的对象,为哲学注入了强劲的生命力。因此与其说西美尔的思想肤浅,何不说西美尔的思想更富趣味?然而不应该忽略卢卡奇对西美尔的指摘,西美尔的确是一个缺乏决断性的思想家,卢卡奇曾说西美尔是“哲学的莫奈,但至今仍没有哪个塞尚接踵其后”。[14]173的确,就连西美尔自己都预料到了自己死后可能的寂寥,他曾说“我知道我将在没有学术继承人的情形中死去,但事实也应如此”,[17]但他却并没有意识到这样的结果正展现了他的个性本质,虽然没有人直接追随他的脚步,“但也没有人不透过他的观察方式,就可以或能够着手从事历史哲学本质的东西”。[14]176
由此看来,卢卡奇在疏离西美尔之后对西美尔才有了清晰的认识,虽然卢卡奇一方面对西美尔的魔力依然大加赞扬,但是也捕捉到了西美尔的印象主义本色,将其定位成过渡哲学家。过渡哲学家的判断意味无穷,时代性、矛盾性、非决断性、承前启后性等都蕴含其中,是卢卡奇对西美尔形成的既矛盾又完美印象。
三 批判寄生虫式的西美尔
1923年出版的《历史与阶级意识》是卢卡奇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的标志性著作,从此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立场成为卢卡奇思想的最主要底色。1924年出版的《列宁》标志着卢卡奇“已经完全成为一个列宁主义者”了,[18]此后卢卡奇的思想在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上与西美尔渐行渐远,逐渐走上了批判西美尔的道路。《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卢卡奇认为西美尔之流资产阶级思想家对异化的分析虽然“细节十分有趣”、“感觉敏锐”,但他们所提供的仅仅是描写这个“着了魔的、颠倒的、倒立着的世界”,始终停留在异化现象的直接性上围绕着异化最表面和最空洞的外部表现形式兜圈子。[19]卢卡奇不满又刻薄的语言已经暴露出对西美尔的高度不满,这种不满已经使他超越了此前对西美尔的相对客观公正的评价,而是在自己的思想中装满了马克思的火药。
1930年代以来,随着对法西斯主义的反思,卢卡奇对西美尔进行了更猛烈的鞭挞。《理性的毁灭》中卢卡奇斥责西美尔为“帝国主义时代依靠利息吃饭的寄生虫”。[20]403在卢卡奇看来,西美尔是个彻底的主观主义者,西美尔虽然认识到旧唯物主义的机械反映论不能彻底解决复杂的客观性问题,也继而否认可知性、否认客观现实的存在,但是西美尔比那些现代唯心主义者的对客观世界的否定上态度更为坚决。西美尔不仅否定一切客观现实,而且同时也建立了一个与人对立的虚假客观的外在世界,而仅仅承认艺术、宗教等这些与现实对立的不同的生命形式。西美尔还是个极端的相对主义者。西美尔从早期的实证主义走向形而上学的道路往往被认为是走向克服相对主义的道路,但是在卢卡奇看来,随着西美尔潜伏着的生命哲学倾向成为他思想的核心,西美尔的相对主义不是减少了反而是增加了,他埋葬了客观科学知识的同时给混乱反动的蒙昧主义以及神秘的虚无主义保存了空间。西美尔在《货币哲学》中提出的灵魂同它自己的客观化出来的产品相互对立导致的文化悲剧在卢卡奇看来是对历史唯物主义背叛,偏离了经济、社会历史等原因,这种“把帝国主义时代有关个人处境的种种环节(特别是有关与这种文化密切联系着的知识分子的处境的那些环节)夸张为一般文化的‘永恒的’悲剧”的目的就在于将知识分子的反资本主义的不满情绪强行改变为“自足、自满和自我陶醉”。[22]402-403因为在西美尔揭示出货币文化的悲剧之时,竟然认为货币文化之中也存在着值得肯定的成分。在此,西美尔只接触到了悲剧性冲突,而这种悲剧性冲突随后就转变成了一种和平共栖。西美尔在札记中曾写道:“对于比较深刻的人来说,根本只有一种把生命维持下去的可能性,那就是,保持一定程度的肤浅。因为如果他要把对立的、无法和解的冲动、义务、欲求、愿望通通像它们的本质所要求的那样深刻地那样绝对彻底地深思下去,则他就必然会神经崩溃,疯狂错乱,越出生命以外去。”[22]406同时,也由于西美尔提倡的这种肤浅,使人在相对主义的虚无中自我消溶,产生一种心安理得的舒适感,给德国哲学带来了一种自我陶醉的玩世主义,造成思想家一方面追求纯粹思想上的极端主义而另一方面却形成一种对经不起任何批评的具体环境的绝对适应,而这成为了战前德国思想界的普遍状况。由于思想家们在各自的思想逻辑中形成了对自己的社会地位的舒适和安全的感觉,从而也就否定了真实客观的东西,这种倾向最终发展成为法西斯主义。对西美尔的不满和批判在于卢卡奇看到了西美尔思想的不彻底性或非决断性,西美尔虽然能够敏锐地把握现代文化的脉搏,但是在思考中却往往陷入相对主义的漩涡,从而不能触及问题的本质。
可见,在《理性的毁灭》中卢卡奇基本上全盘否定了西美尔的思想,不仅斥之为帝国主义寄生虫,称其为极端的相对主义者、极端的主观主义者,甚至从宗教、文化哲学等多个维度对西美尔展开了猛烈的批判,最终将他扣上了法西斯主义幕后推手的历史罪名。然而在对西美尔的批判中,卢卡奇的立场也暴露无遗,他是站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将当时的一切非理性的哲学思想都斥之为反动的资产阶级哲学,并且高度结合了自己在匈牙利和俄国所接触到的革命实践经验,从他极富战斗性的语言中就可明显发现这一点。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来看,卢卡奇的批判当然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但是也有着明显的绝对化嫌疑,而从卢卡奇自身思想发展来看,此番批判则彻底颠覆了此前对西美尔的评价。然而正如卢卡奇所言,“每个思想家都要为他的哲学思想的客观价值在历史面前负责”,[22]2卢卡奇也应该为在《理性的毁灭》中对西美尔的批判担负历史的责任。
[1] 谢胜义.卢卡奇[M].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0:47.
[2] G Simmel.ThePhilosophyofMoney[M]. trans. T. Bottomore, etc. London: Routledge, 2004: 20-21.
[3] 杜章智.卢卡奇自传[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6.
[4] 初见基.卢卡奇:物象化[M].范景武,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5] 韦伯.马克斯·韦伯传[M]. 阎克文,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533.
[6] 卢卡奇.卢卡奇早期文选[M].张亮,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
[7] G Lukács.NotizenzuGeorgSimmelsVorlesungen, 1906/07,undzuráKunstsoziologieá,ca. 1909[M]. Ostfildern: Hatje Cantz, 2011: 2-3.
[8] 齐美尔.社会学[M].林荣远,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25.
[9] 刘象愚.卢卡奇早期的美学思想[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1(1):70-80.
[10] 西美尔.时尚的哲学[M].费勇,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
[11] 里希特海姆.卢卡奇[M].王少军,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51.
[12] 刘昌元.卢卡奇及其文哲思想[M].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1:24.
[13] 艾尔希.卢卡契谈话录[M].郑积耀,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
[14] K Gassen,M Landmann.BuchdesDankesanGeorgSimmel[M].Berlin: Duncker und Humbolt,1958.
[15] K Lichtblau.GeorgSimmel[M]. Frankfurt: Afra Verlag, 1997: 11.
[16] 北川东子.齐美尔:生存形式[M].赵玉婷,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17] D Frisby.GeorgSimmel[M]. London: Routledge, 2002: 137.
[18] 卢卡奇.列宁:关于列宁思想统一性的研究[M].张翼星,译.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1:3.
[19]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M].杜章智,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161.
[20] 卢卡奇.理性的毁灭[M].王玖兴,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