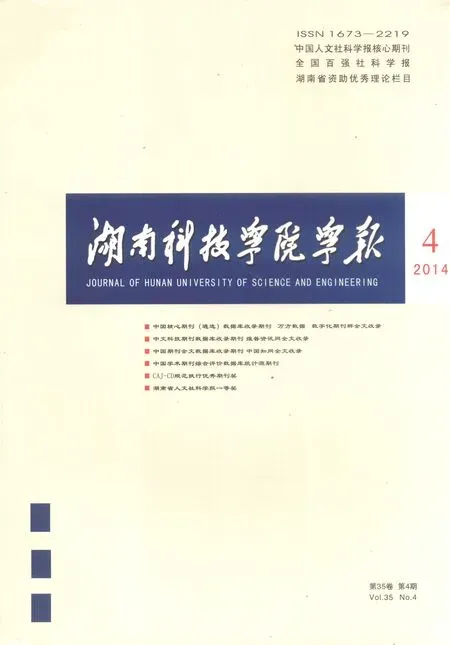史诗的仪式发生学新探——以苗族活态史诗《亚鲁王》为例
2014-04-01蔡熙
蔡 熙
(贵州省社会科学院 民族研究所,贵州 贵阳 550002)
对文艺发生学的研究由来已久。自古以来,关于文艺的起源问题众说纷纭,如“灵感说”、“模仿说”、“劳动说”、“巫术说”、“心灵表现说”等。文艺起源诸说虽然各有其道理,但在我国学界居于主导地位的是文艺起源于劳动的观点。虽然两千多年前亚里斯多德从酒神狄奥尼索斯的祭祀仪式与悲剧的发生关系入手,提出了悲剧源于对酒神祭祀仪式的模仿,“借以引起怜悯和恐惧来使这种情感得到陶冶”[1]P19。但论者只知其“模仿说”却淡忘了其影响深远的“仪式说”。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指出,中国戏剧来自宗教性的巫舞,“灵(巫)之为职,或偃蹇以象神,或婆娑以乐神,盖后世史诗之萌芽已有存焉者矣”[2]P9。但文艺起源的仪式说,在我国应者寥寥。主要原因在于,仪式往往与宗教巫术难分难舍地纠结在一起,长期以来,人们把仪式展演当作一种封建迷信。在贵州麻山地区苗族的丧葬仪式上展演的活态史诗《亚鲁王》为我们探讨史诗的仪式起源问题提供了鲜活的例证,本文以《亚鲁王》为例,对史诗的仪式发生学作一初步探讨。
一 《亚鲁王》对史诗发生学的挑战
在民间流传几千年的苗族史诗《亚鲁王》直到2009年紫云县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中才意外现身,同年成为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的重点项目,并被文化部列为2009年中国文化的重大发现之一。2011年《亚鲁王》荣列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2年2月由中华书局出版,并入选中国社会科学院六大学术事件,与中国作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等事件相提并论。这部26000余行的史诗涉及古代人物10000余人,400余个古苗语地名,至今仍以口头形态在贵州麻山苗族地区的3000多名歌师中口耳相传。《亚鲁王》的横空出世对史诗的概念、史诗的发生学以及史诗的分类都提出了挑战,这是目前史诗学界不能不回应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
史诗究竟起源于何时,引发它起源的直接诱因是什么?这就是史诗发生学。谈到史诗的发生学问题,人们一般认为,人类的史诗是从原始氏族社会解体到奴隶社会初期产生的,它代表了那个时期的文学成就。苗族史诗《亚鲁王》直到21世纪的今天才被发现,至今还是活形态的史诗,依然在民间流传。面对《亚鲁王》,认为人类的史诗产生于原始氏族社会末期到奴隶社会初期的史诗起源理论,显然不能自圆其说。《亚鲁王》主要流传于麻山地区的紫云县,分散流传于邻近的罗甸县、望谟县、平塘县,另外在贵阳、花溪、龙里、息烽、平坝、黔西、大方、织金、威宁、镇宁、关岭自治县等西部苗族地区也有少量流传。麻山地区深处高耸入云的喀斯特大山之中,地理位置偏远荒僻,外人罕至,交流不便,信息闭塞,语言独特,生活状况十分原始,这为史诗《亚鲁王》的传承不衰提供了一道天然屏障。可见,只要存在特定的文化空间,活态的民间文化遗产就会代代相传。
关于史诗的类型学问题,西方的史诗种类比较单一,史诗一般是指以英雄人物为中心的英雄史诗。就史诗的内容而言,在中国,除了英雄史诗以外,还有神话史诗、创世史诗、民族迁徙史诗。《亚鲁王》兼具创世史诗、迁徙史诗和英雄史诗三个亚类型的特征,可以说是一部“复合型史诗”,《亚鲁王》的发现丰富了世界史诗宝库,为史诗的分类提供了当代的新案例。从文明形态来看,以跨海远征作战、海上漂流冒险为主要内容的荷马史诗是海洋城邦类型的史诗,印度的史诗《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是森林史诗。我国北方著名的三大史诗《格萨尔》、《江格尔》与《玛纳斯》发端于北方草原游牧文化土壤,属于草原史诗。流传于我国南方麻山地区的史诗表征的是山地文明形态,反映了苗族先民在高原山区创世、征战、迁徙的生活历程,属于典型的山地史诗。史诗是人类社会和精神文化发展史上的普遍现象。在我国,由于史诗研究起步晚,甚至于史诗(epic)这一概念也是舶来品,再加上缺乏多民族的文学观念,引发了长时间的我国有无史诗的争论。事实上,我国不仅有史诗,而且拥有多种类型的史诗,是史诗的富国。史诗的发生学以及史诗的分类学唯有纳入“仪式”的视角才能得到很好的说明。
二 史诗在仪式中发生
史诗是最古老的文学样式。苗族活态史诗《亚鲁王》唱述了古代苗族亚鲁王国第17代国王兼军事首领亚鲁在频繁的部落征战和迁徙中创世、立国的坎坷发展历程。当历史的车轮辗转到21世纪,工业化、城市化已经高度发达的今天,《亚鲁王》作为苗族的“活态”文化大典,依然在麻山地区的民间传唱。《亚鲁王》为史诗起源于宗教祭祀仪式提供了强有力的佐证。
麻山地区苗族丧葬仪式的程序复杂多样,耗费时间长。根据田野调查的情况,由于深处山地的苗族住地分散,支系众多,各地的仪式的程序存在一定的差异,如紫云县大营乡巴茅村、宗地乡大地坝村的丧葬仪式要经过净身装棺、停棺、牵马走亲戚、隔房家族的晚辈给亡人献牲、孝子给摩公倒洗衣脚水洗脚、摩公唱念经词、牵马到砍马场的喝酒仪式、牵马到砍马场、开马路、众亲戚上祭、念唱砍马经、为亡人宣告恩怨了结、牵魂回家、请吹打班子进砍马场踩场、亡者的女儿和儿媳妇喂马、用鞭炮惊吓献牲、砍马师进入砍马场地、砍马抬杉树下塘、献牲、亡者的女儿送饭、摩公为亡人唱念开路的经词、为亡人指路、烧掉亡者的不洁之物、出殡上山、下塘、扫家和解簸箕等28道程序。虽然各地的丧葬仪式程序有一定的差异,但从根本上来看是大同小异的,即这部26000余行的史诗围绕核心人物亚鲁王而展开,唱诵史诗《亚鲁王》是葬礼的灵魂,它统领了其他所有的仪式程序。唱诵的内容,一般从亡者何时何地出生,到亡者的家庭成员,再到亡者的父辈、祖辈,一直追溯到亚鲁王乃至最远古的祖先,重点唱诵苗族先民在亚鲁王的统领下创世、征战和迁徙史的历史,历时9-10小时不等,企望通过这种反复唱诵的仪式过程,实现与祖先的对话,让死者能够回归祖先的身边。在种种仪式中,最重要的是两种仪式,即开路仪式和砍马仪式,下面分别展开探讨。
(一)开路仪式
在麻山苗族地区,亡人过世后都要请当地的摩公(即在麻山苗族的丧葬仪式中主持巫祀仪式活动的歌师)到家中主持仪式为亡人开路。开路是麻山苗族丧葬仪式最重要的部分,意为给亡人指路,即请摩公给亡者指引一条回归到祖先故地去的路。开路前,主人家要给亡人准备好五谷种、包晌午饭等。供饭时,主人家会抬来一头猪和一条狗,放在棺材的大头位置。
在开路仪式上,摩公要为亡人唱诵《开路经》,其中唱诵的亚鲁王部分在凌晨两点开始,历时大概三个小时。其内容分为四个部分:(1)唱述宇宙和人类创世的由来。以创世神话为基本内容,以天地万物、人类社会、文化起源及演进发展为叙述线索,主要神话有造天造地,造人,造山造丘陵、赶山平地、造太阳月亮、造唢呐铜鼓、箭射日月、与雷公斗争、洪水滔天、俩兄妹治人烟、蝴蝶找来谷种、萤火虫带来火、马桑树天梯等神话。(2)唱诵亚鲁王的故事,重点唱诵亚鲁王成长、创业、征战和迁徙的故事,塑造了一位勤劳智慧、能力超凡、关爱民生的苗人首领形象。(3)杀鸡开路。唱完最后一部分之后,摩公右手怀抱半大的子鸡,左手执剑,把用来给亡人开路的鸡在地上摔死,然后用竹子纵穿鸡的身体,插在饭篓上给亡人,是谓“杀鸡开路”。杀鸡给亡人指路,首先将亡人送到东南方,然后再转回到门口,接着送到西方。指路过程需要两个多小时。(4)为亡人指明本家族先人所在的地方,自己的祖先是怎么来的,祖先迁徙来此定居的路线,怎么样回到祖宗的故地。麻山苗人认为,亚鲁是他们的祖先,是亚鲁把苗人带到这个地方来定居的,亡人要走的路,就是沿着亚鲁迁徙的路线回到过去曾经生活过的东方老家。
在开路仪式中,对苗族祖先亚鲁王的唱诵贯穿了整个丧葬仪式的始终。因为苗人自古以来具有追本溯源、慎终追远、扬尚祖德的传统。他们认为,只有灵魂得到妥善的安置,才能回归到祖先的住地,与祖先的灵魂共同生活。麻山苗族浓郁的祖先崇拜意识表征了他们独特的民族信仰、坚定的民族传承性和强烈的精神回归的生命意识。
(二)砍马仪式
砍马仪式可分四个阶段。(1)砍马前,摩公把悬挂在大门上方的糯米谷穗分发给主家的各女性,大孝子肩扛长梭标去屋外牵马,从拴马的地方把马牵到大门,然后牵到拴马的地方,如此反复三次。(2)供马。到了砍马场,马的头要朝向东南方,分到糯米谷穗的女性聚集过来,一边哭泣一边把手中的稻穗敬献给马。先由主家的摩公供马,供马时要敬三碗酒,供完后直接倒在马的脖子上,摩公要喊到主家的祖先三辈。(3)念《砍马经》,唱述砍马的由来与历史,指明马如何到达祖先之地。马背上驮着一系列带领亡人灵魂回归祖先之地的物件,其中包括酒瓶、葫芦壳做成的水壶、六个竹筒(五个竹筒装水,一个竹筒装干鱼、豆腐和其他菜)、布袋(装有少许糯米饭、三个碗及打火石)、饭箩(装两斤左右蒸熟的糯米饭)。在苗族人看来,人死了之后就要回到祖先生活过的地方。因此,在亡人归家的路上生者要为之提供更多便利,其中包括为亡人供饭,给亡人开路,砍马送亡人等。虽然人已仙逝,但生者仍然要为亡人提供回归祖先途中所需的干粮,表明了苗族人灵魂不灭的伦理观念。《砍马经》详细交待了杉树的来历以及与亚鲁王的关系。“多王受优待,享福不知福。吃鲁命中树,啃鲁命中竹。”[3]P167这棵杉树是亚鲁王的生命树,这匹马是亚鲁王的战马,亚鲁王依凭这匹战马打了很多胜仗。但因为战马居功自傲,偷吃了生命树上的粮食种子,破坏了亚鲁那多年精心培育起来的物种。亚鲁王含泪把战马砍死,让它带着亡人去追寻亚鲁的足迹,回到祖先的故地。“待人死了后,才砍送亡人,亡人骑马上,哒哒寻祖先。祖先开大门,把他迎进屋,今有某某人,天上寻祖先,今日把你砍,带他上天庭,你莫怨砍者,应恨你祖先,祖先亚多王,已经许了愿。”[3]P168念完《砍马经》之后,摩公在马鬃上喷洒用树叶泡制后的酒水,然后携主家众人,围着马逆时针方向转三圈。(4)砍马。一般由两名砍马师轮流上场,每人砍一刀,并且只能在马逆时针奔跑时才能动刀砍。被砍的马在砍的过程中升华成为亚鲁王祖先的战马,与亡者一同返回亚鲁王的时代,回到远古祖先的身边。马蹄、耳朵和生殖器割下放入棺材中陪葬。显而易见的是,砍马仪式是对古代战争场面的模仿,以这匹英雄而苦难的战马所经历的残酷血腥的场面让族人刻骨铭心地见证并铭记亚鲁王当年在征战和迁徙途中所经历的死亡存亡的考验。
由此不难看出,传统的丧葬仪式才是史诗《亚鲁王》传承千年不衰的深厚社会基础,一旦离开仪式展演,史诗《亚鲁王》就失去了存在的空间和土壤。事实上,在我国的西南少数民族中还存在着不少口头流传的活态史诗,如彝族的英雄史诗《勒俄特伊》也是在丧葬祭祀仪式上由祭司庄严地唱诵的,独龙族的《创世纪》是在祭祀天鬼的仪式上由主祭的祭司唱诵的,云南大姚、姚安一带的彝族在为亡者举行的送灵仪式上由祭司毕摩唱诵创世纪史诗《梅葛》,纳西族的《创世纪》是在祭天仪式上由祭司东巴唱诵的。西方的史诗书面文本定型较早,已经成为书面的文学经典,但是《荷马史诗》的背后是一个口传文化传统,《荷马史诗》是无文字时代的歌手们口头传唱的,盲人荷马只是其中的一个歌手,作为歌手的荷马不单单是一位文艺家,他是带着古老的没有文字社会悠远的历史记忆唱诵史诗的,史诗背后是深远的文化记忆。
从亚里斯多德的《诗学》到尼采的《悲剧的诞生》,都认为仪式是西方文艺的诞生地。亚里斯多德说,悲剧“是从酒神颂的临时口占中发展出来的。[1]P14在祭祀酒神的仪式上,由巫师戴着羊的面具,唱着狄俄尼索斯死亡的哀悼之歌。“弥尔顿的《失乐园》是一个哀悼的仪式。”[4]p98歌德的《浮士德》完全是一个社会化“通过仪式”在艺术作品中的范例。[5]p110“诗歌是一种复活和再生的仪式。”[6]p174叶芝的戏剧作品“不是戏剧,而是一种丧失信念的仪式。”[7]p176北美印第安人的口传神话肇端于仪式,其仪式主要有五种:(1)烟熏祭天地用的贡品(2)洁身礼即洗一次汗浴(3)斋戒和守夜礼仪(4)召唤自然神的巫师仪式(5)公共仪式,大多数是跳舞,包括祈祷,献祭,纪念祖先和死者。
由此可见,最早的史诗是从仪式中孕育发展出来的,仪式中的程式化、表演化、性格化特征,孕育未来文艺的胚芽。仪式陶冶了人类激越的情感体验,培养了人类幻想的形象性、艺术的想像力,激发人类用象征的、隐喻的形式来表现人类的情感、渴望和理想。当神话渐渐式微,各种艺术就从仪式中脱胎出来日渐走向成熟。
三 史诗仪式发生说的当代价值
亚里斯多德对酒神祭祀仪式的经典阐释成了仪式命题的学术原点。苗族史诗《亚鲁王》在仪式中产生,又在仪式中口耳相传为史诗的仪式发生说提供了鲜活的当代案例。史诗的仪式发生说对于文艺起源的探究具有不可低估的价值和意义。
首先,从仪式中孕育了最早的史诗形式,而最早的史诗却是一种融混性的艺术,表征了艺术起源时的原生形态。在苗族丧葬仪式上由摩公唱诵的史诗《亚鲁王》与宗教祭祀、巫术、音乐、舞蹈等活动紧密结合在一起,集唱、诵、仪式表演于一体,体现了艺术起源的原生态特征。在史诗展演时,“摩公”面对死者,要随身佩戴一系列的道具,如身穿苗族传统的长衫,头戴斗笠,头帕里装上稻谷,手提一只鸡,脚穿铁鞋(铧口),肩上扛着长剑等。此外,在展演过程中,还要配以木鼓、铜鼓、牛角等神器。从仪式展演的声音类型看,有“器声”和人声。其中器声包括木鼓、铜鼓、牛角、鞭炮、鸣枪等声音类型,器声的演奏,其实质是族群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的外显。人声包括丧礼现场孝女(妇女)们的哭唱声和摩公唱诵史诗《亚鲁王》的吟唱声。摩公在演诵的时候要根据丧葬仪式的语境氛围和观众的表情来展演,他们那庄重苍茫的曲调,时而快捷、时而舒缓、时而长叹、时而手舞足蹈。史诗的表现形式灵活多变,根据史诗《亚鲁王》的内容,摩公唱诵的歌调可分为离世调、永别调、开路调、请祖调、砍马调、发丧调等等。显然在仪式上展演的史诗不是纯文学的,而是融混性的。同时,史诗在漫长的口头传承过程中,融进大量的神话、传说、民间故事、歌谣及谚语等,因此,史诗含纳了多种文类要素,既具有强烈的地方特性和民族特性,又具有人类的普适性。
但是,长期以来,“文学的”史诗观在我国的学术界占据着支配地位,从而导致现代中国学术语境中史诗定位的褊狭化和虚幻化,一般只关注史诗的历史文化内容、历史渊源、流传地域等问题,而对史诗的文类特征、史诗的传播、仪式语境、史诗歌手等方面重视不够,导致史诗研究无法延伸到文字记录以外的广阔领域。故而,对现代中国几代学人习惯已久的文学本位史诗观进行批判性反思,重新构建一种贯通文、史、哲、宗教、道德、人类学的跨学科的史诗观念十分迫切。
其次,过去的文学研究片面地偏重于汉语书面文献,不同程度地忽略了依然活在田野的口头文学;过去的史诗研究过于偏重文学维度,相当程度上忽视了其他类型史诗的存在。“一种文化从其诞生之初起,就具备一种本性,它就是一种生命形式,虽然历经变化,但其本性与生命一直贯穿了全部的发展历程之中。”[8]P2在苗族丧葬上唱诵的史诗《亚鲁王》,绝不是纯文艺作品,而是与人类的生命活动、文化活动等混沌为一体的原生态文化。仪式是一种符号和意义的复杂体系,为人们提供了一种特殊的体验。因而,史诗的仪式发生说,可以极大地丰富和深化《亚鲁王》所蕴含的文化知识资源的总储量,进而充分地展示和重塑史诗生命的整体过程,对史诗的生命过程、总体精神及整体风貌进行本质还原。对口头史诗的研究,要突破文人文学的樊篱,重视口头传统的特点,注重史诗传承人、史诗的听众和史诗展演语境三者之间的互动,大力倡导具有世界意义的比较口头诗学研究。
再次,史诗的仪式发生说可以极大地拓展《亚鲁王》的研究视野和研究空间。书面史诗的研究一般以史诗文本为依据并参考其他文献资料,研究相对来说比较单纯。以口耳相传为载体的活态史诗是一种口传文化系统的信息传播,仅仅依赖史诗文本是远远不够的。它要求我们必须将目光从史诗文本转向史诗田野,对其进行动态研究,始终坚持文学与人类学的互动。也就是说,要以田野调查为基础,以口头诗学理论、文学人类学理论、间性诗学理论为指导,通过走访一系列杰出的歌师,并作访谈录音记录,把握每一个歌师的成长经历、个人职业、习艺过程、性格特征、展演实践、当下的生活状态等;要深入考察歌师在表演过程中的眼神、表情、手势、嗓音变化、肢体语言、乐器技巧、音乐旋律等展演风格,对歌师划分类型,并进行比较研究,分类考察他们的文化传统、传承线路、史诗故事的变异和创新,揭开史诗传承人的本真性、地域文化的多样性;此外,史诗的接受者——听众研究,史诗形成、发展、流传、变异与创新的研究也是必不可少的研究对象。
[1]亚里斯多德.诗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2]石泰安.藏族格萨尔王传与演唱艺人研究[J].民族文学译丛(第l集),1983.
[3]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亚鲁王》文论集:口述史·田野报告·论文[C].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1.
[4]Wittrelch,J.A.,Jr.Visionary Poetics: Milton’s Tradition and His Legacy,San Marino[M].Calif: Huntington Library,1979.
[5]Hartman,G.H.The Fate of Reading and Other Essays[C].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5.
[6]Cope,J.I.The Theater and the Dream: From Metaphor to Form in Renaissance Drama[M].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73.
[7]Gorsky,S,R.A Rital Drama:Yeats’s Plays for dancers,see Modern Drama[M].1974.
[8]朱炳祥.何为“原生态”?为何“原生态”[J].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