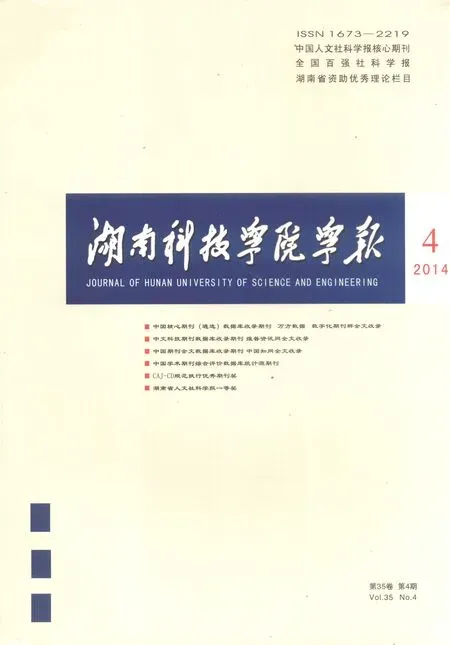试析孔子思想中的“天”
2014-04-01范玉亮
范玉亮
(上海大学 历史系,上海 200444)
一
《论语》中有关“天”的言论一共出现了17次,其中出自孔子之口的共有13次。本文试图通过《论语》的文本来简略分析孔子眼中的“天”究竟何指,有何特色,在他整个思想体系中居于什么地位。
学界以往讨论孔子的天道观或天命观的意见大致可以分为四类:一以郭沫若为代表,认为孔子是怀疑派,“天”是指自然之天;二以任继愈、侯外庐为代表,认为孔子相信天命和鬼神,“天”仍然是有意志的人格神;三以徐复观为代表,认为孔子之“天”,乃是道德性之天而非宗教性之天;四将孔子口中的“天”分解成各个层次的天,如意志之天、义理之天及道德之天等。
当代学者在这一问题上仍然是见仁见智。其中,有人将孔子的“天”理解为“主宰之天”,“是宇宙万化背后的决定力量,是一个决定着社会、自然与人生命运的至上神”;[1]也有人完全否认孔子思想中的宗教因素,认为孔子之“天”只能是自然之天、伦理之天、道德之天;[2]也有人认为孔子并不在意到底有没有主宰之天及其它鬼神,而是以神道设教与中庸思想为指导,将未知世界整合在“尽人事而知天命”的积极进取精神中了;[3]还有人认为孔子之“天”有两个维度,就外在性而言是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主宰之天,就内在性而言是带有浓厚价值意蕴的道德义理之天。[4]可以看到,近年来的学者关于孔子之“天”的观点尽管在深度上有所推进,但实际上并没有超脱前辈学人的藩篱。
认为孔子之“天”是完全的主宰性的至上神的看法尽管有其道理,但存在夸大“天”之作用的倾向。而完全否认“天”有宗教意味的观点,则无法解释何以孔子在困厄之时总会频频诉诸于一个超越的“天”。至于将孔子的“天”分解成若干层次的说法,则显然是以今人的眼光来裁剪古人的思想,盖孔子之“天”,只可能是一个独特的“天”,尽管这个“天”可能有着多重内涵,但我们只能说孔子之“天”有主宰性、义理性及道德性的内涵,而不能硬生生将之分解成意志之天、义理之天、道德之天或其它层次的天。
二
本文以为,孔子所谓的“天”明显具有超越的特点,仍然是宇宙的最高主宰者。但是这种主宰并不是全方位的了,更多的则是表现为一种制约、规定性的力量。同时,孔子虽然信仰“天”,但并没有把现世的一切事物都交给“天”来处理,而是大力倡导人的作用,以至于世间的理想状态下的政治社会秩序——即所谓“道”——之实践,就只能靠人的主动性了。
孔子所谓的“天”首先是一个宗教范畴内的至上神。这从以下内容可以明显看出:
王孙贾问曰: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何谓也?子曰:不然。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八佾》)
子见南子,子路不悦。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论语·雍也》)
子曰:天生德于予,桓 魋其如予何?(《论语·述而》)
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论语·子罕》)
以上内容表明,孔子所谓的“天”具有人格神的特点。“获罪于天,无所祷也”,以及孔子曾说过的“丘之祷久矣”(《论语·述而》)之语,足见孔子是以庄严敬畏之心来对待“天”的,还深怕获罪于它,这里的“天”只能以宗教中的人格神的观点视之。“天厌之”、“天生德于予”、“天之将丧斯文”等语,至少表明了“天”是拥有一定意志的,可以决定世间的某些事情。尤其是受困于桓魋及“畏于匡”时,孔子在危难之中无不将自己传承文明的使命与看不见、摸不着的神圣的“天”之意志联系起来,这种情怀更可见他对“天”的笃信之坚。
《论语》中还有两句,虽不是孔子所言,但是反映了同时代人对于“天”的看法:
仪封人请见。曰:君子之至于斯者,吾未尝不得见也。从者见之。出曰:二三子何患于丧乎?天下之无道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论语·八佾》)
太宰问于子贡曰: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子贡曰:故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论语·子罕》)
“天将以夫子为木铎”、“天纵之将圣”均反映了“天”作为至上神而拥有特殊意志及深不可测之能力的特点。同时代的人也作如是观,可作为孔子之“天”有超越特性这一观点的旁证。
由此可以看出,孔子所谓的“天”确实有至上神的意味,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志而决定某些人间事务的运行、发展。问题是,这个“天”的法力究竟多大,或者“天”之能够施展或愿意施展的法力究竟有多大?能不能主宰一切、决定一切呢?
殷周革命,实际上已经将“天”的权威弱化了,因为自称秉承天意的殷王朝竟然丧失了“天”的庇佑,最终使得天下归于宗周。所以,周人一方面仍然敬畏上天,但同时也知道所谓的“天”是靠不住的,于是提出了“敬德”的口号。而到了孔子所处的春秋末期,礼崩乐坏之事频发,以往的至上神“天”所主宰的世间秩序发生了大规模的动摇,这个时候“天”之权威无疑会进一步下降。孔子是殷商之后(《史记·孔子世家》载:“予始殷人也。”),同时推崇的是西周的礼乐文化(《论语·八佾》:“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他的思想自然不可能脱离传统的框架而急遽转变,以至于否定“天”之权威;但同时,他也不可能将世间一切的命运都交给至高无上的“天”,毕竟“天”已经对世间的纷乱保持了沉默而不是降威惩罚那些僭越之辈、卑劣之徒。与孔子同时而略早的郑国大夫子产的一句话大概可以表明孔子的心声:“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左传·昭公二十八年》)天道深邃幽眇,不是我们所能得知的;而人道则是我辈能够改善的。这也可能就是“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公冶长》)的原因。所以,孔子一方面保留了对于“天”的信仰和敬畏,以至于在遭遇困厄等特殊时候诉诸于这一坚实的信仰,而另一方面倡导“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卫灵公》),主张以人的能动性来致力于政治社会秩序之改善。
三
以上我们初步分析了孔子思想中的“天”在宏观层面上的特性,接下来我们看看在微观层面上孔子之“天”还有什么其它意涵。当然,这只是就其主要方面而言,完全不是全面具体的分析,这必须提前说明。
首先,“天”是世界秩序之源。
子疾病,子路使门人为臣。病间,曰:久矣哉,由之行诈也!无臣而为有臣。吾谁欺?欺天乎?且予与其死于臣之手也,无宁死于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纵不得大葬,予死于道路乎?(《论语·子罕》)
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论语·宪问》)
子曰:予欲无言。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
子贡曰:君子一言以为知,一言以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不可阶而升也。(《论语·子张》)
根据当时的礼制,孔子不是卿大夫,是没有资格拥有治丧组织(即“臣”)的,而子路却在孔子病重之际主持成立了类似组织,孔子在病情缓和之后便责备子路的违礼之举,说道:“吾谁欺?欺天乎?”孔子是最为痛恨僭越礼制之行为的,显然在这里他也是将违礼以举行大葬的做法看作是“欺天”的行为。换言之,上下有别的人间等差秩序其实也是体现在“天”身上的,打破这种秩序实际上也就意味着“欺天”。这句话是《论语》中的“天”能够代表人世之秩序的最坚实的证据。而当“孔子”在说“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之时,他显然是说自己的学识或思想已经无法被世人所了解了,能够理解的恐怕只有“天”了;子贡在说孔子之不可及“犹天不可阶而升也”之时,同样也是在表达一种参差之秩序的观念,认为孔子的思想或境界,是其他人远远不能望其项背的。“天何言哉”中的“天”,实际上还是一个有超越特性但是有所克制的人格神(当然,将这里的“天”直接视作自然之天也是说得过去的。但本文并不同意这一看法,因为按照上下文的意思,将“天”理解为人格神更合乎语境,也更适合“言”这一动作),“天”虽然不言,但仍然制约着“四时”运行、“百物”生长等自然规律,所以这里的“天”也与秩序有关。
由上分析,我们可以得知《论语》中的“天”与人世间的秩序有关联,但是分析到此尚无法断定,“天”一定便是秩序之源。然而,我们应该明白,思想史上往往有一个极为有趣的现象,那就是一种理论本来是内涵丰富的,而后人往往仅执其一端,而忽略掉一些本该更重要的理论要素。如,关于自由主义,当后人过分强调国家权力与公民社会的冲突时,往往便忘了对于强有力的国家权力的要求首先便是自由主义的题中之义。所以,当政治上早就稳定的英美的自由主义侧重于强调经济自由时,而尚处于四分五裂的德意志的自由主义却呈现出另一种形态,即特别强调现代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5]后人在回视德国这段思想进程时,可能仅仅会从国家-社会的关系入手认为德国当时的思想不能算是自由主义,主张强有力的国家怎么能算是自由主义呢?可是,现代国家本来就是自由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前提,只是我们往往忽略掉了。本文以为,这种现象完全也体现在孔子的思想被后人的解读之中。首先,如果仅仅将“仁”、“礼”等某些特定的方面概括为孔子思想的核心,便忽视了孔子本来是一个成体系的思想家这一基本事实。孔子思想的本体仍然是一个有着超越特征的“天”,只是这个“天”并不直接插手人间事务,所以孔子根本也不寄望于上天来审判僭越之徒或恢复人间秩序,而是发挥精英士人的主动性来建立一个人间的良善、有序的政治社会秩序。其次,涉及到“天”的特性时,“天”乃宇宙秩序之源恐怕也是孔子及其同时代人的一个基本认知;而这一认知相当于时人的共识,是他们所有言论的前提预设之一,自然不会特别强调。这一推论可以从《论语》中的其它内容得到旁证。前面已分析道,“天”仍然有超越的特性,而既然“天生德于予”,那么“天”为什么不能生出秩序呢?实际上,如果不把秩序产生之根源归结于“天”,那么孔子思想体系的自洽性似乎便得不到保证。所以,本文倾向于认为,“天”除了前文已强调的有着超越性之外,其第一个重要特性便是“天”乃宇宙秩序之源。
其次,“天”是道德之源。
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 其如予何?(《论语·述而》)
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论语·泰伯》)
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论语·子罕》)
孔子说“天生德于予”,集中表明了“天”作为道德之源的特点,尽管孔子也认为道德的提高也必须依赖后天的培养——《论语·述而》载:“子曰: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这说明,孔子认为道德可以通过后天的培养而改善。“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这里的“天”倒不好说一定是何种“天”,但它无疑是圣君治国所当效法的对象,而“天”之所以能被效法是因为其德广远,不可形容——“故其德之广远亦如天下之不可以言语形容也。”(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至于“天”之“将丧斯文”抑或“未丧斯文”,按诸孔子的口吻明显是“天”不会抛弃自周文王一直传承到自己身上的这一文化传统,“天”之具有德性不言自明。
然后,“天”之特性还表现在“天命”上。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
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论语·季氏》)
“五十而知天命”,至于孔子所知的“天命”到底指什么,自然莫衷一是,言人人殊;而“畏天命”中的“天命”又是何指,恐怕也不会有统一的看法。无论如何,我们大致可以断定,这里的“天命”是超乎人的力量的,是人所无法掌握的一种类似“绝对精神”或者形形色色的“历史规律”的人类发展趋势,不同之处是孔子并未将“天命”绝对化。这一“天命”也以不同的表述方式出现在“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天之历数在尔躬”及“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等《论语》的内容中。由于文言文言简意赅之特性,我们实在难以肯定“天命”及其它表现形式的词汇到底是什么意思,但是可以肯定这种“天命”是与“天”的超越性联系在一起的,因为“天命”是一种人类难以理解且超出人之掌控的东西。
综上所论,《论语》中的“天”或者说孔子眼中的“天”延续商周之观念,仍然是宇宙的最高主宰,是秩序之源、道德之源,还体现着一定的“天命”。但是,这里的“天”已不是无所不能、逞威施暴的拥有绝对权威的“天”了,而是一种体现着秩序的,散发着德性的超越性的在上之“天”。孔子真正诉诸于“天”的时候往往是困厄之际或者诉求个人的终极关怀时,这意味着“天”对于孔子来说更多地起信仰支撑作用,而不是一种需要终身奉献的绝对真理;事实上,孔子一生最所措意的是“道”之实行,也即改善现世的政治及社会秩序——这一秩序用朱子的话来说就是“治隆于上,俗美于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
四
孔子眼中的“天”的超越的特性在后世精英士人那里便不那么突出了。首先,孟子所谓的“天”向着德性的一面靠近了一步。他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也。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孟子·尽心上》)这句话无疑是在“性善论”的基础上说的,“知其性,则知天也”,知道人性本善,那么也就知道天道贵善了。后来的宋明理学便是在孟子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挥了“天”之德性的一面的意蕴。其次,荀子所谓的“天”向着自然之天转进了一大步。他所说的“天行有常”已经没有孔子口中的“天命”的意味,而是表达一种人定胜天的征服自然的意志:“大天而思之,孰与物蓄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荀子·天论》)
然而,“天”之作为超越的存在又是历朝历代所不可否认的事实,最明显的莫过于作为天子的皇帝的祭天制度。祭天是皇帝的专属权力,是一种庄严神圣的宗教仪式,只有九五之尊的皇帝才有资格隆重祭天,这里的“天”很显然是一种超越的存在。不仅如此,历代士大夫藉以压制皇权之泛滥的一个重要的因素也是抬出超越性的“天”,如史书中常见的“天降灾异”——“灾异”象征着皇帝的德行有亏——便是试图约束皇权的说法。更何况,在广阔的民间,普通民众对于“天”的敬畏之情一直不减,即便同时信奉其它宗教,他们潜意识中的最高主宰往往也还是“天”。
对于上述分析的解释是,在孔子之后,“天”在士大夫的个人超越的信仰领域的地位可能有所衰落,但是作为传统文化的一个核心要素,“天”无疑对上到皇帝下到普通百姓的极其广阔的人群仍然是具有极大权威的。
[1]赵法生.孔子的天命观与超越形态[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6).
[2]王志强,王功龙.论孔子的天道观[J].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7).
[3]张海英,张松辉.“神道设教”和“中庸”整合下的孔子天道观[J].求索,2009,(2).
[4]邱忠堂.从天人合一重释孔子之天[J].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4).
[5]李强.自由主义与现代国家[EB/OL].凤凰网读书频道,http://book.ifeng.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