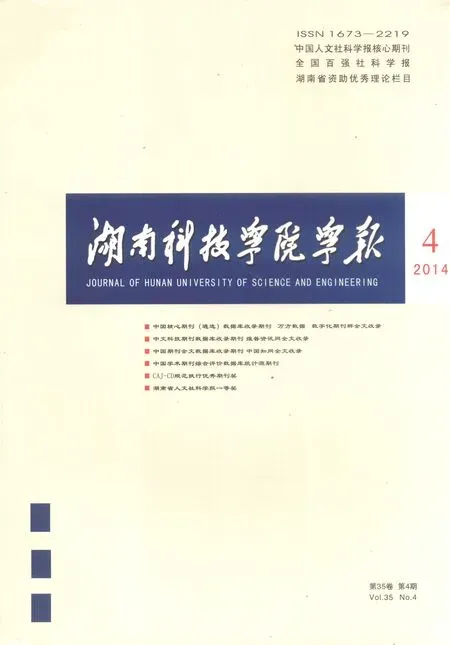文必宗经说
2014-04-01张善文
张善文
(福建师范大学 易学研究所,福建 福州 350007)
先师六庵教授①先师姓黄氏,讳寿祺,字之六,号六庵,学者称六庵先生。福建霞浦人,公元1912年生,1990年辞归道山。早岁就读北平中国大学国学系,嗣在母校任教。所从问学者有章太炎高足吴承仕先生、吴汝纶高足尚秉和先生等老师宿儒。抗战间南旋闽省,先后执教于国立海疆学校、福建师专、福建师范学院、福建师范大学等高校,曾任福建师范大学副校长。学贯群经子史,尤精于《易》。有《群经要略》、《易学群书平议》、《汉易举要》、《周易译注》、《楚辞全译》、《六庵诗选》等行世。尝以所著《群经要略》课诸生,曾谆谆诲曰:中国经学与文学关系十分重大,群经原即文学作品之最典范者,后世各体文学皆自群经出,凡欲治中国文学史或从事文学创作者,倘无经学根柢,概莫能为也。故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云:“文能宗经,体有六义。”②刘勰:《文心雕龙》卷一《宗经》篇。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谓:“夫文章者,原出五经。”③颜之推:《颜氏家训》卷上《文章》篇。二者均以为经学与文学息息相关,允属确论。
以吾之不敏,长年反复耽思师言,愈久而愈觉其寓意深邃,且颇有兢忧世人淡忘经学、疏远圣贤之微旨存焉。今谨循此课题,检讨旧籍,综而考之,以为斯事宜有四端值得当今经学界与文学界共审观之:一端,经乃千古至文,异彩光耀后世。故群经自身的文学价值应予充分认定。二端,经承文人崇奉,融入文章血脉。故群经对历代作家文学作品的内容及形式之影响应予认真品评。三端,经含文学理论,伟韵通达文心。故经学在文学思想领域的渗透作用应予深入考察。四端,经属道统根源,宗经方可为文。故今日中国文学的创作旨趣,是否仍需毋忘宗经之道,应予切心体会。兹依次窃为简述,以乞政于大雅君子。
一 经乃千古至文,异彩光耀后世
大凡能成为“经典”的作品,其自身必极富文学性,才能传诸后世而脍炙人口。孔子曰“言之无文,行而不远”④《左传·襄公二十五年》:“仲尼 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又《孔子家语·正论》所载略同:孔子“谓子贡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之不远。”)是矣。后人论群经之文学意义,除前引颜氏谓文章“原出五经”、刘氏称文宜“宗经”外,更有颇多警策之说。如唐刘知幾云:“自圣贤述作,是曰经典。句皆韶夏,言尽琳琅。秩秩徳音,洋洋盈耳。譬夫游沧海者,徒惊其浩旷;登太山者,但嗟其峻极。”⑤刘知幾:《史通》卷六《叙事》篇。白居易云:“天之文,三光首之;地之文,五材首之;人之文,六经首之。”⑥白居易:《白氏长庆集》卷四十五《与元九书》。宋陈瓘云:“五经之文,久而愈新。”⑦《宋文选》卷三十二载陈莹中( 瓘)《文辨》语。《四库全书总目》云:“《宋文选》三十二卷,不著编缉者姓氏。案张邦基《墨庄漫录》称崔伯易有《金华人记》,编入《圣宋文选后集》中。则此乃其前集,在南渡以前矣。所选皆北宋之文。”又云:“宋人选宋文者,南宋所传尚伙,北宋惟此集存耳。其赅备虽不及《文鉴》,然用意严慎,当为能文之士所编。”王质曰:“文章根本在六经。”①王应麟《困学纪闻》卷一引王景文(质)语。李涂云:“《易》、《诗》、《书》、《仪礼》、《春秋》、《论语》、《大学》、《中庸》、《孟子》,皆圣贤眀道经世之书,虽非为作文设,而千万世文章从是出焉。”②按:李涂《文章精义》,乾隆十二年撰《钦定续文献通考》云:“一卷,旧题李耆卿撰,耆卿里贯无考。”“案焦竑《经籍志》有李涂《文章精义》二卷,书名及撰人之姓均与此本合。耆卿疑即涂之字云。”又《四库全书总目》著录《文章精义》一卷(《永乐大典》本),曰:“是书世无传本,诸家书目亦皆不载。惟《永乐大典》有之,但题曰李耆卿撰,而不著时代,亦不知耆卿为何许人。考焦竑《经籍志》有李涂《文章精义》二卷,书名及李姓皆与此本相合。则耆卿或涂之字欤?载籍无征,其为一为二,盖莫之详矣。其论文多原本六经,不屑屑于声律章句,而于工拙繁简之间,源流得失之辨,皆一一如别白黑,具有鉴裁。”凡此诸论,均异口同声地揭明群经即历代文学之最高典范之旨。
既然古代经典堪称文章之极至,或将问曰:群经有何文学特色?
此问题前人实已作过完美的解答。《礼记·经解》引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又曰:“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疏通知远而不诬,则深于《书》者也;广博易良而不奢,则深于《乐》者也;洁静精微而不贼,则深于《易》者也;恭俭庄敬而不烦,则深于《礼》者也;属辞比事而不乱,则深于《春秋》者也。”③均详阮元刻《十三经注疏》本《礼记正义》。本文所引群经之文,多依此本。下仿此,不出注。此中通过“入国知教”的分析,点出六经文学内容影响于人的六大特色。刘勰更就群经的文学风格与艺术境界论曰:“夫《易》惟谈天,入神致用,故《系》称旨远辞文,言中事隐。韦编三绝,固哲人之骊渊也。《书》实记言,而诂训茫昧,通乎尔雅,则文章晓然。故子夏叹《书》,昭昭若日月之明,离离如星辰之行,言昭灼也。《诗》主言志,诂训同《书》,摛风裁兴,藻辞谲喻,温柔在诵,故最附深衷矣。《礼》以立体,据事制范,章条纤曲,执而后显,采掇片言,莫非宝也。《春秋》辨理,一字见义。五石六鹢,以详略成文;雉门两观,以先后显旨。其婉章志晦,谅以邃矣。《尚书》则览文如诡,而寻理即畅。《春秋》则观辞立晓,而访义方隐。此圣人之殊致,表里之异体者也。”④刘勰:《文心雕龙》卷一《宗经》篇。文中历陈五经的文章特质,称为“圣人之殊致”,宜其赞颂有加。唐韩愈亦曰:“《春秋》谨严,《左氏》浮夸;《易》竒而法,《诗》正而葩。”⑤魏仲举编:《五百家注昌黎文集》卷十二《进学解》。则以精约之语概括了四部经典的为文之美。明朱右又曰:“《易》以阐象,其文奥;《书》道政事,其文雅;《诗》发性情,其文婉;《礼》辨等威,其文理;《春秋》断以义,其文严。然皆言近而指远,辞约而义周,固千万世之常经,不可尚已。”⑥朱右:《白云稿》卷三《文统》。也是深刻地揭示出五经的文章妙处。
前儒不仅综言群经的文学特色,甚至评述了各经具体篇章的行文之用心与法度。宋李涂曰:“《孟子·公孙丑下》,首章起句谓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下面分三段:第一段说天时不如地利,第二段说地利不如人和,第三段却专说人和,而归之得道者多助,一节髙似一节。此是作文中大法度也。”此言《孟子·公孙丑下》的作文之法。又曰:“《诗·生民篇》如庐山瀑布泉,一气输写直下,略无回顾。自厥初生民,至以迄于今,只是一意。”⑦并见:李涂《文章精义》。此言《诗·生民篇》开句与结语首尾洞贯的行文气势。明王鏊曰:“世谓六经无文法,不知万古义理、万古文字,皆从经出也。其髙者远者,未敢遽论。即如《七月》一篇,叙农桑稼圃;《内则》,叙家人寝兴烹饪之细;《禹贡》,叙山水脉络原委,如在目前。后世有此文字乎?《论语》记夫子在乡、在朝、使摈等容,宛然画出一个圣人,非文能之乎?”⑧王鏊:《震泽长语》卷下《文章》。此言《诗经·七月》、《礼记·内则》、《尚书·禹贡》及《论语》诸篇的叙事、状物、写人的文学笔法。由此足见,群经之为前圣绝美文章,允属古代学者之共识。
今之研究经学与文学关系的学者,亦有诸多可取的见识。惟或提出“经学如何变成文学”及“经学的文学化”问题⑨龚鹏程:《六经皆文》首章,台湾学生书局有限公司2008年初版。按,龚氏所称“经学”若含群经本文在内,“文学”若含文学作品在内,则群经作品原无异于文学作品,何须“变成文学”?若其规限“经学”仅属历代学者对群经的学术研究范畴,“文学”仅属学人研讨文学作品的内在规律的范畴,则经学是经学,文学是文学,治学领域不同,角度各异,经学又岂能“变成”文学?因名责实,无论作何评析,其说似皆不甚通妥。,似可商榷。群经本即“千古至文”,又何需“变成”文学?何有“文学化”的过程?故愚意以为,群经自形成之日起,即以典范的高雅文学形式而流传后世,不仅通过精深的内容影响着中国千百年的思想意识领域,而且凭着渊粹的文华章彩光耀于后世。
二 经承文人崇奉,融入文章血脉
中国经学源远流长,在数千年的文化学术思想史上,历代文人所接受的熏陶莫大于群经、莫深于群经。毋庸置疑,自孔子删定六经之后,尤其是汉代创立群经博士之后,经学思想作为文人崇奉的最高典则,不但优化着人们的行为规范,同时在学人的文学创作中也打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甚至融入了各类优秀文学作品的血脉。略观中国文学的发展步武,可知群经作为文学典范之“榜样力量”是无穷的,其对后世(特别是两汉至清代二千多年间)文学作品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前儒以为,许多重要文体,盖皆因群经的文学模式而派生。刘勰指出:“故论说辞序,则《易》统其首;诏策章奏,则《书》发其源;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铭诔箴祝,则《礼》总其端;纪传铭檄,则《春秋》为其根。并穷髙以树表,极远以启疆,所以百家腾跃,终入环内者也。若禀经以制式,酌雅以富言,是仰山而铸铜,煮海而为盐也。”①刘勰:《文心雕龙》卷一《宗经》篇。认为所列二十种文体,分别出自五经,后人倘能禀经以创制文式、增富语言,则就像“仰山铸铜”、“煮海为盐”一样取用不竭了。颜之推也有类似之论曰:“诏命策檄,生于《书》者也;序述论议,生于《易》者也;歌咏赋颂,生于《诗》者也;祭祀哀诔,生于《礼》者也;书奏箴铭,生于《春秋》者也。”②颜之推:《颜氏家训》卷上《文章》篇。其意在于论证文章各体皆“原出五经”,与刘勰的观点如出一辙。此类理念,颇为后来学者所认同。直至近代,严可均在编纂《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时,仍明确表示:“是编于四部为总集,亦为别集,与经、史、子三部必分界限。然界限有定而无定。诏令、书檄、天文、地理、五行、食货、刑法之文,出于《书》;骚赋韵语,出于《诗》;礼仪,出于《礼记》;传,出于《春秋》。百家九流,皆六经余润。故四部别派而同源。”③严可均:《铁桥漫稿·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总例》。其言谓目录学家区分各部各类的文章体式,无不同原于六经。可见,后代诸多文体,颇因群经的浸染而日渐成型且不断发展繁富。
中国古代诞生过层出不穷的文人与名作,有一个共同的规律:一切优秀的作家作品,无不在经学的熏沐下走向文学艺术的辉煌。以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为例,其毕生“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沉浸醲郁,含英咀华,作为文章”,遂有“闳其中而肆其外”④魏仲举编:《五百家注昌黎文集》卷十二《进学解》。的鸿文伟作。知者尝寻检韩文所承六经融陶之显迹,谓其《贺册尊号表》用“之谓”字,盖取《易》之《系辞》文;《平淮西碑》叙宪宗命将遣师处,是学《书》舜命九官文法;《沂国公碑铭》朴茂典重,亦远法《尚书》气势;《元和圣德诗》云“驾龙十二,鱼鱼雅雅”,乃深于《诗》者;《画记》用“者”字,气韵条贯,可追《周礼·考工记》之文澜;《国子助教河东薛君墓志铭》述大会射节,文法盖自《仪礼》来;《柳州罗池庙碑》叙事明旨,直如《左传》文情;《原道》、《赠太傅董公行状》等篇行文之雄迈曲折,又似《孟子》文⑤此节所引论韩文者,凡有陈骙、许顗、郑瑗、沈德潜、曾国藩、吴汝纶、刘朴、张裕钊、吴恺生诸家之说。详先师黄寿祺教授《群经要略》卷十一《总论篇》,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10月初版。。明王鏊也曾就韩文概括曰:“昌黎序如《书》,铭如《诗》,学《书》与《诗》也。其它文多从《孟子》,遂为世文章家冠。”⑥王鏊:《震泽长语》卷下《文章》。不独韩愈如此,古代有成就的文学家,盖皆不能外乎经学的涵养。
尝披阅有清巨编《御定历代赋彚》,见数千篇作品中,以群经内容命题之作甚多。随意举之,如《天行健赋》、《人文化成天下赋》,取题于《易》也;《齐七政赋》、《江汉朝宗赋》,取题于《书》也;《日升月恒赋》、《湛露晞朝阳赋》,取题于《诗》也;《南风之熏赋》、《王言如丝赋》,取题于《礼》也;《获麟赋》、《曹刿请从鲁公一战赋》,取题于《春秋》也。他如命意于《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者,亦屡屡可见。至于作品内容汲取群经故实或经学思想,熔冶新意以成华章者,更是不胜枚举。岂赋之为体,最受群经寖染而多氤氲于经学气息欤?曰:不然。此仅试举一端,未及其余也。中国古代文学,凡韵文、散文、小说、戏剧诸大门类,琳琅满目的作品宝藏不计其数,一旦细加征考,吾人总将惊叹其中所焕发出的异彩纷呈的经学蕴蓄之光华。
达理明义者不难晓悟:古之文人莫不穷经崇圣,终身精研圣贤之书(纵有离经嫉世者亦未必不先读经),其学殖宏贯于中(大儒硕学者尤如是),一旦发为文章,则治经之素养,与夫禀经穷理之思维,终能不期然而然地畅抒于斯文。笔者所言经承文人崇奉,而融入文章血脉,盖实录矣。
三 经含文学理论,伟韵通达文心
群经乃圣人之千古至文、且融入后代文章血脉既明,吾人又需研探经中含藏的不可忽视之文学理论。纵览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思想(乃至美学思想),不难看出,其间往往贯穿着群经学说的内涵。
兹稍依诸经之次,略举有涉文论的若干例子为证,以概其余。《易》之《系辞传》曰“物相杂故曰文”,谓错落有致乃成文章。明王世贞激赏之云:“文须五色错综,乃成华采;须经纬就绪,乃成条理。”⑦王世贞:《弇州四部稿》卷一百四十四《艺苑 巵言》。《系辞传》又曰:“其旨远,其辞文”,谓文章形式的辞彩文饰与内容的旨义深远之完美结合。明茅坤赞云:“孔子之系《易》,曰其旨远,其辞文。斯固所以教天下后世为文之至也。”⑧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总序》。按坤编《文钞》一百六十四卷,原为举业而设,《四库提要》谓其选录“尚得烦简之中,集中评语虽所见未深,而亦足为初学之门径。”《书》之《舜典》曰:“诗言志”,表明诗歌创作当以抒发心志为尚。梁刘勰引申曰:“大舜云:诗言志,歌永言。圣谋所析,义已明矣。是以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舒文载实,其在兹乎?”①《文心雕龙》卷二《明诗》篇。《舜典》又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指出诗歌音乐以和谐为最高准则,乃能使神人共鸣。宋薛季宣云:“八音克谐,律吕斯应。动天地,感鬼神,有生之类无不获者矣。夫如是也,弦歌之事可得而略也。”②薛季宣:《浪语集》卷三十一。《周礼》之《考工记》曰:“画缋之事后素工。”言文章绘画或有以素朴为美者。北齐颜之推云:“画绘之工,亦为妙矣;自古名士,多或能之。”③颜之推:《颜氏家训》卷下《杂艺》篇。《礼记》之《乐记》曰:“正声感人,而顺气应之;顺气成象,而和乐兴焉。”言诗歌音乐需遵循正声之道。明李东阳云:“观《乐记》论乐声处,便识得诗法。”④李东阳:《怀麓堂诗话》,无锡丁福保校印《历代诗话续编》本。至若《论语》载孔子论《诗》“思无邪”说⑤《论语·为政第二》:“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君子“文质彬彬”说⑥《论语·雍也第六》:“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关雎》“乐不淫哀不伤”说⑦《论语·八佾第三》:“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以及《孟子》关于“知人论世”⑧《孟子·万章下》:“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浩然之气”⑨《孟子·公孙丑上》:“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夫志至焉,气次焉,故曰持其志无暴其气。”又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又曰:“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以意逆志」⑩《孟子·万章上》:“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的思想,亦无不对后代文学理论产生了十分重大的影响。此类例子,细探各经的内容,可谓比比皆是,不胜胪列矣。
进而思之,不独群经之本文内容往往蕴含着文学理论意义,因群经而衍发之历代经说,亦多有同类情实。如《易》学之“阴阳说”、《诗》学之“比兴说”、《春秋说》之“褒贬说”,皆其典型而特出者。今就此三者略作个案简析。
阴阳说,为《易》学思想之核心。《系辞传》称“一阴一阳之谓道”,朱熹云:“盈乎天地之间,无非一阴一阳之理。”11朱鉴编:《文公易说》卷十八,又见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六十七、清程川编《朱子五经语类》卷一。这一学说,与古代文论关系重大。文学规律,盖亦颇含阴阳刚柔之旨。古代诗文声律理论所谓“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12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以及四六文的骈排句式、近体诗的对偶形态,均与《易》学之阴阳刚柔说密相吻合。清姚鼐以阴阳论文章风格,颇具创获,其曰:“天地之道,阴阳刚柔而已。文者,天地之精英,而阴阳刚柔之发也。”并提出文章有“得于阳与刚之美者”,有“得于阴与柔之美者”,以为凡雄浑、劲健、豪放、壮丽之文皆可归入“刚美”之类,凡修洁、淡雅、高远、飘逸之文皆可归入“柔美”之类13絜姚鼐:《惜抱轩文集》卷六《复鲁 非书》,清嘉庆间刊本。,谓“苟有得乎阴阳刚柔之精,皆可以为文章之美”14姚鼐:《惜抱轩文集》卷四《海愚诗钞序》,清嘉庆间刊本。,允有见地。及观刘熙载之言:“文,经纬天地者也,其道惟阴阳刚柔可以该之。”15刘熙载:《艺概·经概》。似亦同乎姚氏之论矣。
比兴说,于《诗》学中极为突出,本于《毛诗大序》的“诗六义”之旨。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16朱熹:《诗集传》。。昔刘勰专叙“比兴”之义云:“《诗》文弘奥,包韫六义;毛公述传,独标兴体。岂不以风通而赋同,比显而兴隐哉?故比者附也,兴者起也。附理者切类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拟议。起情,故兴体以立;附理,故比例以生。比则畜愤以斥言,兴则环譬以记讽。盖随时之义不一,故诗人之志有二也。”17刘勰:《文心雕龙》卷八《比兴》篇。又曰:“虬龙以喻君子,云蜺以譬谗邪,比兴之义也。”18刘勰:《文心雕龙》卷一《辨骚》篇。唐刘知幾亦云:“昔文章既作,比兴由生。鸟兽以媲贤愚,草木以方男女。诗人骚客,言之备矣。”19刘知幾:《史通》卷六《叙事》篇。概览古今文人,凡论诗文创作,其沾洽“比兴”说之化泽者实多。
褒贬说,即世所谓“春秋笔法”,旧称以一字为褒贬的文学语言艺术。依循此法所产生的艺术效果,晋范宁言之最确:“一字之褒,宠逾华衮之赠;片言之贬,辱过市朝之挞。”20范宁:《春秋谷梁传序》,详阮元刻《十三经注疏》本《春秋谷梁传注疏》。今思其谓“笔法”、谓“褒贬”者,盖含二义:一曰简约,二曰含蓄。亦即刘勰称“《春秋》一字以褒贬”,“此简言以达旨也”21刘勰:《文心雕龙》卷一《征圣》篇。。故宋刘爚述莆田陈均撰《皇朝编年举要备要》之感触曰:“昔尝读朱文公《通鉴纲目》,叹其义例之精密。盖所谓纲者,《春秋》书事之法也;而所谓目者,《左氏》备言之体也。”“其书法,或寓褒贬于其间。”22宋刘爚:《皇朝编年举要备要序》,详所著《云庄集》卷五。清李光地亦叹曰:“圣人著语,即一虚字都一团义理,尽是春秋笔法。”23李光地:《榕村语录》卷九。历来传史叙事之名篇佳作,无论是官修史书,还是私家传记,其能成功的原因,或多收益于沿承正确的“褒贬理念”、严谨的“春秋笔法”。即便今日欲作史者,也不能忽视这种科学的创作思想。
除此三则个案之外,历代经说之影响于古代文论者尚多,如“意象论”(易学)①《系辞传》:“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王弼《周易略例·明象》云:“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又云:“象生于意而存象焉,则所存者乃非其象也;言生于象而存言焉,则所存者乃非其言也。然则,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忘言者乃得象者也。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故立象以尽意,而象可忘也;重画以尽情,而画可忘也。是故触类可为其象,合意可为其征。”其旨趣主于“得意忘象”、“得象忘言”,对后世文论家之“意象”说颇有影响。、“风化论”(诗学)②《毛诗大序》:“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此说即文学作品的“风化”论之源头。、“治乱论”(诗学)③《毛诗大序》:“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乎诗。”其中所言“治世之音”、“乱世之音”、“亡国之音”,颇为后世论诗歌音乐者所宗。、“笔削论”(春秋学)④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后人论创作文章的删润提炼过程,颇以此为式。宋李纲《雷阳与吴元中书》云:平时观书,“偶有所得,随亦忘失。唯笔削之,则说而不通必思,思而不得必考。沉思博考,心醉神开,然后得之。此训释前言,所以不为无补于学也。虽然,岂敢谓足以垂世哉?聊以自娱永日而已。”(《梁溪集》卷一百十三),以至统该群经学说的“文道论”⑤刘勰《文心雕龙》卷一《原道》篇:“文之为 徳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迭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又曰:“至夫子继圣,独秀前哲,镕钧六经,必金声而玉振;雕琢情性,组织辞令,木铎启而千里应,席珍流而万世响。写天地之辉光,晓生民之耳目矣。”其所主张,在于文以载道。至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曰:“始吾幼且少,为文章以辞为工。及长,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为炳炳 烺烺,务采色、夸声音而以为能也。”又曰:“故吾毎为文章,未尝敢以轻心掉之,惧其剽而不留也;未尝敢以怠心易之,惧其弛而不严也;未尝敢以昏气出之,惧其昧没而杂也;未尝敢以矜气作之,惧其偃蹇而骄也。抑之欲其奥,扬之欲其明,疏之欲其通,廉之欲其节,激而发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本之《书》以求其质,本之《诗》以求其恒,本之《礼》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断,本之《易》以求其动。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柳河东集》卷三十四)其说力主“学须通经”、“文以明道”的思想,对后代文学理论具有积极的启迪作用。等,均可看出经学思想与文学理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诸多契合之点。因此,群经对于中国文论的密切渗透而通达万世“文心”的学术规律,值得我们认真探索。
四 经属道统根源,宗经方可为文
中国古代正直的文人必具敦重道统的品格。何谓“道统”?曰:古之圣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曾思孟,递相授受而流布于今的优秀文化思想系统也。群经的思想本质,即是全面记载并宣扬这一道统。故古之学者读经以循道,为文以弘道,是其人生治学的最高境界。所谓“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⑥《周易》上经《贲》卦《彖传》:“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是也。居今之世,文人是否仍有宗经的必要?今日之宗经又当以何为指向?笔者以为,此问题仍需向古人求教。
先叙文人宗经之意义。刘勰说得最见深透:“三极彝训,其书言经。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又曰:“故文能宗经,体有六义∶一则情深而不诡,二则风清而不杂,三则事信而不诞,四则义直而不回,五则体约而不芜,六则文丽而不淫。”⑦刘勰:《文心雕龙》卷一《宗经》篇。这里论及文人宗经,足以使所作文章的内容和形式具备六大境界,尽获“情深”、“风清”、“事信”、“义直”、“体约”、“文丽”之妙。当然,其根本前提是通过宗经而明“至道”、识“鸿教”:只有文人自身思想升华了,才能运笔传神、言之有物,所谓“道”充于内而“文”发于外也。
历代文人多明此理,史上有作为的文学家亦颇能缘此而身体力行之。故魏张辽叔曰:“六经为太阳,不学为长夜。”⑧魏嵇康:《嵇中散集》卷七《难自然好学论》引张辽叔语。梁元帝曰:“凡读书必以五经为本,所谓非圣人之书勿读。读之百徧,其义自见。”⑨梁元帝:《金楼子》卷二《戒子篇》。唐韩愈曰:“非三代秦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⑩魏仲举编:《五百家注昌黎文集》卷十六《答李翊书》。宋王禹偁曰:“夫文,传道而明心也”,“今为文而舍六经又何法焉”11王禹偁:《小畜集》卷十八《答张扶书》。?元赵孟頫曰:“学文者当以六经为师,舍六经无师矣。”12朱彝尊:《经义考》卷二百九十六引。明林俊曰:“夫史子百家,皆文也。六经,文之至也。周程张朱皆学也。”13林俊:《见素集》卷六《小录前序》。清黄焯亦曰:“六经,文之至也,不可以拟而续也。后之为文者,舍六经奚以哉?”14朱彝尊:《经义考》卷二百九十七引。古人如此论说,盖一一本诸切身体会,展示出通过思想涵育之“内圣”,而达到文学创作之“外王”的规律,这就是前儒强调再三的先“道德”而后“文章”的立身准则。
再叙宗经为文之大道。文人宗经的必要性古人言之灼灼,而宗经为文的指向,亦即秉持宗经之本以把握文学创作、立足于淑世化俗的正确思想,也是古人所高度重视的。宋王禹偁曰:圣人文章是“不得已而为之”15王禹偁:《答张扶书》。,犹言无益于世道人心者必不作也。明邓黻曰:“文莫粹于经,圣贤以其精藴而形诸辞。辞可以已,圣贤必无事于作。作焉者,不得已也。”16朱彝尊:《经义考》卷二百九十七引。这“不得已”三字,极见义理,今之为文者尤当细心品察体味。
回思颜之推论文章原出五经之际,还曾说过:经典之文“足以尽天下之情、之辞、之政、之心,不入于虚伪,而归于有用。”17颜之推:《颜氏家训》卷上《文章》篇。谓之“有用”而“不入虚伪”,与“不得已”正相同趋,皆言往圣为文之大道,必当有补于世。故明代王志坚评颜氏之说曰:“此篇为一种无行文人针砭膏肓,大有禆益。”①王志坚编:《四六法海》卷十。斯论允称一语中的。谓为“无行文人”,盖表示对那些炮制无用文章以沽名钓誉而惑世诬民者的深恶痛绝之情。曾读《近思录》,至“伊川先生答朱长文书”条,有一节足以警醒世人之语:“圣贤之言,不得已也。盖有是言,则是理明;无是言,则天下之理有阙焉。如彼耒耜陶冶之器,一不制,则生人之道有不足矣。圣贤之言,虽欲已,得乎?然其包涵尽天下之理,亦甚约也。后之人始执卷,则以文章为先,平生所为,动多于圣人。然有之无所补,无之靡所阙,乃无用之赘言也。不止赘而已,既不得其要,则离真失正,反害于道必矣。”②朱熹,吕祖谦合编:《近思录》卷二。程子这一段短短的分析,深刻论及圣人文章“不得已”之所以然,直将古代圣贤为文之大道,与当世文人以“无用之赘言”而害道的负面现象,作了鲜明对比,其间之是非真伪判然立晓。无怪乎清代学者魏源读至此,惶惶然批诸卷端曰:“平生所为,动多于圣人,令人汗下。”③湖北省图书馆藏清陈亢《近思录补注》手稿,《续修四库全书》第九三四册影印本。像魏源之学富五车,尚且掩卷愧汗,又何况其余呢?
由是知之,宗经必在立本,为文务循其道,自古已然。遍览古今文学佳作,其能传世不衰,历久弥新,必多缘于此也。若今或有津津乎乐以文名炫世者,不务实学,其所自诩之“作品”(有文学作品亦有理论作品)不过粗制滥造之物,且问世不愈日即消弭无用,又将何补于世?吾人则将奈之何耶?论者云:“近年世道日坏,学风也愈来愈坏,论文写作渐成知识产业中批量生产的商品,讲究规格化、数量化、标准化,产品还要分级。学者则以承揽业务、包发工程鸣高。结果是 SSCI、CSSCI等唉唉不绝。期刊分级、教授分等,学校以兹为指标,国家以此投资助。看来一片欣欣向荣,漪欤盛哉,其实是每年制造若干万吨学术垃圾,许多基本问题却闲置着没人愿意去碰。大家勤于放焰火,而少人从事埋水管的工作。”④龚鹏程:《六经皆文》卷首《自序》,台湾学生书局有限公司2008年初版。其说激愤忧惕,虽不留余地,恐致小有误伤,但总归实事求是,切中时弊。彼所言者,宜属今日两岸学术论著之事,倘类推于当今文学艺术诸领域的创作现状,盖亦断断乎如是矣。称为“每年制造若干万吨学术垃圾”(尚有“文学垃圾”、“艺术垃圾”等等),绝非危言耸听。有识之士忧心如焚,学界情状依然如故。或许,世人应当认真思考“文必宗经”的问题了,应当重读程子关于圣人“不得已”而为文的谆谆教诲了。
概以言之,笔者探讨了群经自身的文学价值、古代文人对群经文格的承传、经学的文学理论内涵之后,以今人宗经庶可端正文风为归结,实亦有感而发也。今日世界,已远离了圣人经典的时代,但圣贤的思想、经学的精神,又岂能弃若敝屣呢?余甚惧前文所述,适如程子指谪的“无用之赘言”,则非“愧恧”二字所能搪塞矣。惟余心与诸多同道所共相期盼者,在于吾辈学人能效法前贤,勉力宗经以承续优秀道统,笃行征圣以涵濡千古文心,庶将不诬于述作之旨欤?昔儒称:“经禀圣裁,垂型万世。删定之旨,如日中天。”⑤详《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总序》。吾愿与诸同道共勉之。
主编识语:王晚霞博士从福州归,偕来质之先生《文必宗经说》一文,首论群经本身即具有文学价值。昔余读《大戴礼》,至“天地以合,四海以洽,日月以明,星辰以行,江河以流,万物以昌,好恶以节,喜怒以当”一节,擘画天地人文之分,涵泳宇宙生生之妙,而言语清简,文学价值莫此为甚,此即可为质之先生之说补注一例。忆昔壬午(2002)冬至,余倩质之先生为书前六句,其后十年暌违,一旦翰札在案,仍有会心。
质之先生又论群经之影响,千百年所已然者,此即昔日古文家所着力处。近余亦尝窃议经之名与经之义,略论群经之所以然,则欲追模今文家之用心焉。盖近百年来学科发展,皆以“民主自由”为基础,而文学学科之所以自立者,即以推翻“文以载道”为前提。余则谓非惟文学载道也,史学、哲学亦载道也,万物莫不皆载道也。群经言志言心言理言道,发而为文,诸子、集部虽不得不有流衍,然其会归祈向者在此,合则两成,分则两毁。分殊而理一,其此之谓乎!
质之先生此文为近年绝少之宏论,治文学者当列为第一要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