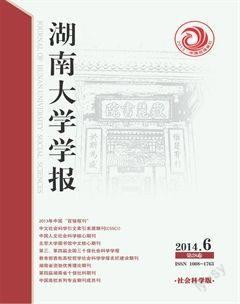再谈经学与中国哲学的关系问题*
2014-03-31邓林
邓 林
(湖南大学 岳麓书院,湖南 长沙 410082)
近些年来,中国传统文化以及所谓的“国学”日渐得到了人们的重视,这从官方到民间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传统的经学研究也随之有了逐渐复兴之势,与此相关联,反思经学与中国哲学学科的关系也成为了学术界的一个问题点。该问题最主要的一个历史背景就在于:经学原本是中国古代的一门学问,而且是中国传统知识学术的核心,也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干;与此相对,哲学则是近代随着中西文化交流而在中国逐渐建立起来的一门现代学科;然而,就在中国哲学学科建立和发展的过程中,经学是被废止的并因此也不断地走向了衰落,更为关键的是传统经学的内容和价值一直未能在中国哲学学科的相关研究中得到应有的对待和体现。于是,随着经学研究又重新受到重视,反思经学与中国哲学的关系问题便进入了学人们的视野。
一 经学进入哲学?
至今为止,学术界已经有一些文章就经学与中国哲学的关系问题进行了研究,虽然大家讨论的角度以及提出的观点都未尽一致,但是对于经学在中国传统文化和古代学术中的核心地位与重要价值基本上都是认可的。关于经学与中国哲学的关系问题,此前笔者也曾撰文发表过自己的看法。在该文中笔者曾提出,上个世纪初我们将“意识形态”层面的“经学”连同“知识学术”层面的“经学”尽皆废止原本就是一个错误,经学作为中国特有的一门知识学术在我国现行教育研究体系里面应该占有一席之地(建议设立经学学科),今天的经学与哲学等其他学科之间应该是平等的关系。①邓林、姜广辉:《也谈经学与哲学的关系》,《哲学研究》2012年第6期,第25-34页。前不久,陈壁生先生在《哲学研究》2014年第2期发表了《经学与中国哲学——对中国哲学学科建构的反思》一文(以下简称“陈文”),着重针对中国哲学学科建构过程中经学的“缺位”进行反思。这仍然可以说是围绕经学与中国哲学的关系问题而展开的讨论。
陈文的重点在于指出历史上的孔子原本具有“儒家始祖”和“经学开创者”的双重身份,而“中国哲学”学科在建构的过程中为了能够更加“哲学”而硬将孔子“经学开创者”的身份抛弃了,从而只剩下“作为诸子的孔子”,结果导致了“经学研究的大量缺失”。陈文一方面认可甚至表彰了冯友兰先生所著二卷本《中国哲学史》的典范价值以及冯氏在其中对“中国哲学”所作的理解,即用西方的“哲学”来对接中国传统的“义理之学”以成“中国哲学”;另一方面,陈文又认为正是因为冯氏以来的中国哲学史写作对“义理之学”作了“狭隘化”的理解,才导致了现如今“狭隘化”的“中国哲学”会将经学排除在“中国哲学”的范围之外。②陈壁生:《经学与中国哲学——对中国哲学学科建构的反思》,《哲学研究》2014年第2期,第43-49页。质言之,陈文主张应该扩大“中国哲学”的研究对象范围,应该将经学中的相关“义理”内容也纳入到“中国哲学”学科的研究中来。
应该指出,笔者基本上认同陈文的观点,尤其是对于经学在今天所面临的尴尬处境我们同样认为是不合理、不应该的。这主要表现在:作为中国历史上极为重要的一门学问,经学在现行教育科研体制中竟然没有“容身之处”。在这里,问题的核心就在于:作为一门知识学术,经学的位置究竟应该在哪里?经学是应该进入哲学,还是应该“单立门户”?换言之,我们应该用“经学”来扩大和完善现有的“中国哲学”学科,还是应该为“经学”独立设科?或者说,我们应该把“经学”和“哲学”融合在一块儿,还是应该让“经学的归经学,哲学的归哲学”?这些问题肯定还有进一步探讨的余地,这或许也是笔者与陈文在经学与中国哲学关系问题上最主要的一点不同。
本文认为,如果让经学进入哲学,在这里还需要弄清楚一个关键的问题:我们到底是想要在经学里面去努力寻找和建构更加“中国”的哲学,还仅只是为了在“中国哲学”里面为经学寻得一个“容身之处”?我们需要注意,这指向的是两个根本不同的问题。前者不仅牵涉到前些年曾争论不休的“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而且中心问题还在于我们能否在现有“中国哲学”的基础上通过经学构建出一种更加“中国”的“哲学”?后者则涉及如此学科设置或安排是否合理的问题,即便先不谈“中国哲学”是否能够完全“容纳”经学的问题,我们将传统经学的内容纳入到中国哲学学科的研究中来就是对经学价值应有的认可了么?问题可能还不止于此,我们还会需要面对为什么是让经学进入哲学,而不是进入历史学或文学等问难。如果让经学进入哲学,这些问题恐怕都是需要我们认真面对的。
但是不可否认,在经学还未能“独立设科”之前,我们退而求其次,让经学进入哲学,将经学研究纳入到现行“中国哲学”学科的研究中来,这未必不是一种暂时解决问题的办法。事实上,现在不仅已经有高校开始这样处理③比如,复旦大学2014年的博士招生开设了专门的“中国经学史”研究方向,就是列在哲学学院“中国哲学”学科的名下。,而且中国哲学领域内确实已经有学者就将“经学研究的全面复兴”当作近年“中国哲学研究”的“一种新的趋向”来看待。④张志强:《礼俗与文明——当前中国哲学研究的一种趋向及其思想关切》,《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6月30日第B01版。由此可见,“经学进入哲学”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理论问题了。所以,面对这样一种新的形势和现实,为进一步厘清经学与中国哲学的关系,笔者以为在这里重提并试图明确“经学与哲学的疆界”问题就是十分有必要的。因为胡适先生曾说过:“经学与哲学的疆界不分明,这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大毛病。经学家来讲哲学,哲学便不能不费许多心思日力去讨论许多无用的死问题,并且不容易脱离传统思想的束缚。哲学家来治古经,也决不会完全破除主观的成见,所以往往容易把自己的见解读到古书里去。……经学与哲学,合之则两伤,分之则两受其益。”⑤胡适:《戴东原的哲学》,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胡适卷》,陈平原编校,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353-354页。
二 经学与哲学的“疆界”
首先,从研究的对象来说,经学与中国哲学的研究对象之间确实会存在一些交叉或重叠的部分,但二者之间的差别无疑才是主要的。在陈文中曾指出,胡适、冯友兰以来的中国哲学史写作由于对“义理之学”作了“狭隘化理解”,导致经学的绝大部分内容被排除在“中国哲学”的范围之外。①陈壁生:《经学与中国哲学——对中国哲学学科建构的反思》,《哲学研究》2014年第2期,第49页。这样一种中国哲学史的写作或叙述模式无疑是值得我们反思的,但是这依然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经学与哲学之间在研究对象上所存在的差别。因为即便我们对“义理之学”采取一种更为宽广的理解,即把经学之中的相关“义理”内容也纳入到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中来,但我们依然无法使得经学的全部内容都进入到中国哲学的范围。质言之,经学并不全是“义理之学”,经学之中还有许多不是专讲“义理”的内容。更何况“义理之学”是否能够完全等同于“哲学”还是一个问题,恐怕经学之中的“义理”内容并非都可以简单地当作“中国哲学”来看。相比经学研究仅仅只是针对儒学而言,哲学的研究对象范围显然要更为宽广。总而言之,儒家经典和经学之中比较具有“义理性”的相关内容可能会是经学与中国哲学共同的研究对象,但是中国哲学的研究对象却不会只是儒学一家,而经学也不是研究儒学的全部,经学之中同样还有许多内容也不能为中国哲学所容纳。
接下来,我们再从研究的进路或方法来看,经学与哲学也有着很大的不同。
一般而言,传统经学按时间的先后大体可以分为汉唐经学、宋明经学和清代经学。②关于中国经学史的分期,请参阅姜广辉主编:《中国经学思想史》(第一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5-19页。相应地,依照研究方式或进路的不同,传统经学又大致地可以分为:“通经致用”或“经世政论”派(以西汉和清末时期的今文经学为主)、“义理阐发”派(以魏晋和宋明时期为主)和“章句训诂”或“辞章考据”派(以东汉古文经学和清代时期为主)。必须指出,这样一种划分并不是十分严格或截然无误的,因此只具有相对的意义。比如,并不是说清代经学就完全没有“义理阐发”,也不是说宋明时期的经学就没有一点“考据”和“训诂”。这样一种划分确实是“大体”而言,主要是为了我们分析和叙述上的方便。仍然是“大体”而言,“义理阐发”派大约相当于现在哲学的研究方式或进路,“章句训诂”或“辞章考据”派则类似于现在历史文献学(也有一些文字学)的研究方式或进路。而“通经致用”或“经世政论”派就很难把它归入现在具体哪一种学科的研究方式或进路,因为它的侧重点在于“术”而不在于“学”,即“喜以经术作政论”③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朱维铮导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77页。,所以更多的是对现实社会和俗世生活的一种强烈而显性的关切。④应该说,中国学术有着“经世致用”的传统,经学从来就不只是儒家的“经典”之学,更是儒者们的“经世”之学。所以,无论何种经学学派或哪一位经学家,在他们那里“通经致用”的诉求只是多与少、显与隐的差别。
今天的经学研究当然可以适当地选用传统经学的研究方式,但我们相信更多的应该会是一种综合性的方法和进路,这也是弥补现代学术分科研究的需要。⑤邓林、姜广辉:《也谈经学与哲学的关系》,《哲学研究》2012年第6期,第29页。而传统的“小学”功夫,比如文字学、音韵学和训诂学仍然会是当代经学研究的基础和门径之一。因此,以必要的“小学”功夫为根基,积极地借鉴和运用传统经学中的方式和方法,争取实现一种多学科或跨学科的综合性的研究方式,应该会成为当代经学研究的主要方向。而“义理阐发”派的方法可以说已经成为现如今哲学学科对“经典”研究的主要研究方式或进路之一。这也是我们按照一般的做法更愿意把“魏晋玄学”和“宋明理学”当作“哲学”而不是“经学”的主要原因。
恰恰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哲学的研究方式或进路与经学有着很大的不同。我们固然也可以把“魏晋玄学”和“宋明理学”纳入一种广义的“经学(思想)史”范围,因为二者的思想根底和来源毕竟主要还是儒家经典。但是,我们也要看到“魏晋玄学”和“宋明理学”却不只是“根源”于儒家经典,同时它们也融合了老庄、佛学(教)的思想在其中。更为重要的是,“玄学”和“理学”所采取的论述方式或进路与“经学”有着显著的差别,而这种差别在历史上主要体现在对“经”的“阐发”程度上,在今天则主要体现在对“经”的主观态度上。
现代新儒家熊十力先生曾将历史上的儒者分为两种:“释经之儒”与“宗经之儒”,他说:“有释经之儒,以注解经书为业。如治训诂名物等等者是。校勘亦属之。……有宗经之儒,虽宗依经旨,而实自有创发,自成一家之学。如韩非所举八儒,孟、孙二子之书尚在。此皆各有创见,各自名家,但以六经为宗主而已。宗经之儒,在今日当谓之哲学家。”⑥熊十力:《读经示要》,《熊十力全集》(第三卷),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811页。在这里,我们不妨像熊先生所说的那样,把“宗经之儒”看成是哲学研究者,比如历史上大部分的玄学家和理学家们,因为他们所采取的更多地是一种哲学的进路,“治经”对于他们而言更多地是一种“工具”或“途径”;而把熊先生所说的“释经之儒”视作真正的经学研究者,比如郑玄、孔颖达、邢昺等人,因为他们本就是“以注解经书为业”,“治经”本身就是他们的目标。这倒不是说,从一开始“宗经之儒”就没有把“治经”当作目标,而是指他们在“治经”的过程中所萌发和形成的思想已经超出了原“经”的范围。也就是说,“宗经之儒”对“经”的“阐发”已经超出了“经学”原有的系统,而“释经之儒”虽然也可对“经”有所“阐发”,但还是在“经学”原有的系统范围之中的。
在今天,经学研究者与哲学研究者对待“经”的主观态度是有所不同的,也需要有所不同。正如胡适先生早就指出的:“我们不要忘记,经学与哲学究竟不同:经学家只要寻出古经典的原来意义;哲学家却不应该限于这种历史的考据,应该独立地发都[挥]自己的见解,建立自己的系统。”①胡适:《戴东原的哲学》,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胡适卷》,陈平原编校,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353页。因此,相比而言,“经”在哲学研究者那里远没有像经学研究者所认为的那样“崇高”和“神圣”,当然也就不会具有像经学研究者那样一种对“经”的“敬”意。哲学研究者当然也需要借助“经典”(却不会只限于儒家经学之中的这些“经”),甚至也尊崇“经”,但是他们却不局限或拘泥于“经”本身。哲学研究可以对“经”提出怀疑甚至是批判,关键是能够允许“经”被超越乃至出现儒家以外的新“经典”。而对于经学而言,这些一般都是很难想象和做到的。
总的来说,“经”(尤其是看具体哪一部“经”)在哲学与经学研究的过程中所占有的地位和所具有的价值是不同的。在哲学研究者眼里,“经”就像是一条“路”,是一条经过历史证明的大多数人都会走的“常道”②刘熙的《释名》中就说:“经,径也。如径路无所不通,可常用也。”(但注定也会有不走“寻常路”的人);而且,关键是哲学研究可以说是“条条大路通罗马”,“路”绝非只有儒家这一条。在哲学研究过程中,“经”只是研究的“起点”,却不是“终点”;“经”只是研究的“工具”,却不是研究的“目的”。而经学研究却始终是以“经”为中心、以“治经”本身为目标的(虽然不一定是最终目标);“经”在经学研究者看来是至高无上的,除非有证据表明经文为伪造,一般是不能怀疑的,更不要说去批判“经”了。在经学研究过程中,“经”既是研究的“起点”,也是“终点”;既是研究的“工具”,也是“目的”。
综上可知,今天我们不论是从研究对象还是从研究方法或进路来看,经学与哲学之间可能永远都会存在一些无法消除的差异。因此,如果说“经学与哲学的疆界不分明”在还没有如此学科划分的古代是已成的事实,那么今天的学人对于这两种学问之间的差异和边界应该多少要能够有所体察和掌握。必须指出,我们在这里特意指出并强调经学与哲学之间的“疆界”,并不意味着要笼统地反对让经学进入中国哲学的研究领域,更不是要反对中国哲学研究者来从事传统的经学研究。毋宁说我们还希望更多的人一起来关注和探索新时代的经学研究应该如何开展,本文在此只是希望能够预先指出如果混淆经学与哲学将可能产生的问题。一方面,只有知晓了经学与哲学之间的“疆界”,我们才能对经学所能进入哲学的“限度”有所掌握;另一方面,今天的经学研究在方法或进路上如果完全没有理论自觉,经学即便进入了哲学,我们可能依然无法使经学走出被现代学科“肢解”的困境。这里问题的关键恐怕还在于:进入哲学之后的经学还能成其为“经学”么?
这就涉及到经学与哲学各自的精神传统是什么的问题了。
三 经学与哲学的精神传统各异
经学与哲学作为一门学问在人类历史上的传承和发展都已逾千年之久,分别有着各自独特的精神和传统。可以说,正是因为二者在根本精神传统上就存在着差异,才使得经学能够成其为“经学”,也使得哲学能够成其为“哲学”。然而,此处所说的精神传统指的是什么?经学与哲学在精神传统上又有何差异?③必须指出,就算仅就“哲学”的精神和传统而言,中西哲学之间就存在很大的区别。但是,只要我们承认历史上有“中国哲学”的存在,我们还是能够在中西哲学之间找到一些“哲学”的“共性”。事实上,这样的问题绝不是轻易就可以回答的,更为重要的是每个人的看法未尽相同,很难形成一个统一的意见。尽管如此,为了进一步明确经学与哲学的关系,尤其是为了能够掌握二者之间的根本差异,我们不得不深入谈到它们的精神传统。为此,接下来笔者就尝试谈谈自己的一些粗浅之见:
第一,经学自“敬”入,而哲学自“疑”入。
蔡元培先生曾将哲学与宗教进行对比,他提出:“哲学自疑入,而宗教自信入。”④蔡元培:《简易哲学纲要》,《蔡元培全集》(第四卷),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462页。蔡先生的这个观点即便是在今天来看依然还是很有见地的,把他这句话中的“宗教”换成“经学”似乎也能讲得通,因为经学在某些方面确实与宗教有一定的相似之处。比如,李源澄先生曾提到:“经学虽非宗教,而有宗教之尊严。”①李源澄:《经学通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5页。从某种角度来看,经学在传统的中国社会中起到了宗教在西方社会所发挥的某些作用,一般来说经学和宗教一样都很难允许有“批评的态度”等。笔者以为,除了对“经”的“信”之外,经学更有一种对“经”的“敬”。也就是说,学习和研究经学首要的是对其所研究的对象——“经”本身要有一种“敬”意。通常来说,“经”在经学研究者那里不仅是研究的对象,而且是“遵从”的对象,甚至也是少数人“信仰”的对象。我们一般只能在既定的“经”之上进行“有限”的研究,对它或注疏或解释或阐发。而所有这些似乎都不需要特别的理由,就因为它是“经”。
而学习和研究哲学最重要的却是敢于怀疑,在哲学史上往往由怀疑而提出一个哲学问题比它的解答更有意义。英国哲学家罗素曾说:“哲学之应当学习并不在于它能对于所提出的问题提供任何确定的答案,因为通常不可能知道有什么确定的答案是正确的,而是在于这些问题本身;原因是,这些问题可以扩充我们对于一切可能事物的概念,丰富我们心灵方面的想象力,并且减低教条式的自信,这些都可能禁锢心灵的思考作用。”②罗素:《哲学问题》,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133页。因此,哲学研究者要敢于怀疑和批判现有的一切权威乃至既有的经典,如果非要有所“遵从”的话,那么应该只“遵从”真理。当年力主哲学“不可不特立一科”的王国维先生就说:“余谓不研究哲学则已,苟有研究之者,则必博稽众说而唯真理之从。”③王国维:《<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徐洪兴编选:《王国维文选》,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11年,第124页。
第二,经学以“经(文)”为导向,而哲学以“问题”为导向。
如果说经学和哲学分别有一个中心或导引,那么经学的中心或导引就是“经”本身,而哲学的中心或导引则是历史上那些永恒的哲学“问题”。一般来说,经学的研究始终以“经(文)”(文本)为中心,对其进行的所有诠释和研究都离不开“经”。对于这一点,李源澄先生曾说:“治经之道,一曰释文,二曰释义。……治经又当以经为律令,以经证经,合于经者为是,不合于经者为非,于其无明文者则阙疑。”④李源澄:《经学通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6页。由此可见,“经(文)”不仅是经学研究的中心,也是经学研究的基础和最重要的根据。而且,经学依据研究中心——“经”的不同,我们又可以从中分列出若干“专经之学”,比如有“诗经学”、“尚书学”、“春秋学”、“易学”、“礼学”等。
而哲学的中心始终是历史上那些永恒的哲学性追问,所以常常会出现几千年前某个哲学家提出的问题直到今天还在讨论的情况,甚至依然没有一个完美的解答。比如,在中国哲学史上所讨论过的“有无”之辩、人性善恶的问题、“天道”与“人道”及其关系的问题等直到今天还在被不断地研究。因为真正的哲学问题总是永恒的,在哲学史上真正的哲学问题其提出往往比其解决更有价值。正如张东荪先生所说:“一部哲学史不是问题的解决,乃是问题的翻新。我尝说哲学上新问题若能层出不穷,这就是哲学的发展。至于有人以为非把问题解决不能得安慰,这便是不甚了解哲学的任务。因为哲学的功用不在于能解决问题,而在于能提出问题。”⑤张东荪:《哲学究竟是什么》,左玉河选编:《科学与哲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77页。
第三,经学重历史传承,而哲学重思想创新。
正因为经学是以“经(文)”为中心,所以经学研究一般都是围绕着经典的文本(即“经”),以历史上已有的诸家解说和确凿的史料文献等材料为基础,讲究“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因而往往非常重视经学自身的历史传承。相比而言,哲学则更为看重思想本身的价值和理论自身的圆融与逻辑上的自洽,尤其注重思想理论上的创新。必须指出,这并不是说哲学就不需要依靠历史传承,而经学就不需要创新。对于经学的这一特点,正如近代经学家皮锡瑞先生说得透彻,他说:“盖凡学皆贵求新,惟经学必专守旧。经作于大圣,传自古贤。先儒口授其文,后学心知其意,制度有一定而不可私造,义理衷一是而非能臆说。世世递嬗,师师相承,谨守训辞,毋得改易。如是,则经旨不杂而圣教易明矣。”⑥皮锡瑞:《经学历史》,周予同注释,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93页。
此外,章太炎先生在《清儒》中评论清代学术时曾说:“清世理学之言,竭而无余华;多忌,故歌诗文史梏;愚民,故经世先王之志衰。(三事皆有作者,然其弗逮宋明远甚。)家有智慧,大凑于说经,亦以纾死,而其术近工眇踔善矣。”⑦章炳麟:《訄书》,向世陵选注,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43页。应该说,章氏对“清学”的论述基本上是信实的,清儒们的“智慧”确实是大都用在了“说经”上面;而他所说的“清世理学”大体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清代哲学”,则只能说是“竭而无余华”。同样,梁启超先生在其《清代学术概论》中也认为“清学自当以经学为中坚。其最有功于经学者,则诸经殆皆有新疏也。”①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朱维铮导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49页。所以,这样相比而言,清代的经学可以算是比较发达的,但是清代的哲学思想就逊色多了,至少像章太炎先生所说的是“弗逮宋明远甚”。从清代学术里经学与哲学的这样一种对比中,我们也可以看出经学与哲学在历史传承与思想创新上的侧重点是不同的。
第四,经学具有公共性,而哲学具有个(体)性。
相比较而言,也是从根本上来说,经学是具有公共性的,而哲学是具有个(体)性的。在这里,经学的公共性是指经学需要进入公共领域被某一社会群体(最好是社会的大多数人)所认可、重视并研习才能成就自身。因为对于一个人或少数几个人而言是无所谓“经”的,“经”之所以为“经”必须要获得公共群体的认可(虽然这种“认可”可以通过历史传承或默认或约定俗成甚或是政治权力的强制来实现)。因此,中国历史上的经学从其诞生起就与政治、科举等公共事务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可以说从来就不是具有某种私人性质(甚至也不是少数人)的事情。
所谓哲学的个(体)性是指所有的“哲学”从一开始都只是某个哲学家的“哲学”,是这位哲学家以个人独特的观察、感悟、分析等并以理论的形式去把握这个我们所共同生活的世界和哲学家自己的独特人生,它强调了哲学思想应该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甚至是哲学家的个人印记。哲学既是属于哲学家“个人”的,但同时又是属于整个“人类”的。正如有的学者所说,“对于任何一个哲学家来说,他总是以人类的名义讲述个人的故事,又是以个人的名义讲述人类的故事。个人的体悟和思辨,与人类的思想和文明,与时代的特征和潮流,是水乳交融,密不可分的。就此而言,全部的哲学都是以时代性的内容、民族性的形式和个体性的风格去求索人类性问题,因而总是一种历史性的而非超历史性的思想。”②孙正聿:《“哲学就是哲学史”的涵义与意义》,《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1年第1期,第49-50页。
虽说在经学与哲学之间存在“疆界”和根本性的差异,但二者同时也还是有联系的。比如,经学与中国哲学在研究对象上会有交叉和重叠,作为一门学问来讲二者各有学术价值,它们的研究方式也各有所长,二者完全可以相辅相成等等。近代以来,经学逐渐走向衰落,哲学则渐渐兴起,这容易给人造成一种“此消彼长”的假象,更容易让人误解以为经学与哲学是不能共存的。事实上,严格地讲起来,近代以来经学的“消”与中国哲学的“长”完全是两件事情,二者之间并无多少因果联系。经学与哲学也不是不可以“共存”,尤其是从儒学的角度而言,经学与哲学未尝不可以成为现代儒学发展最主要的两种学术进路,即“作为经学的儒学”和“作为哲学的儒学”可以成为现代儒学诠释的两种基本形态。③景海峰:《经学与哲学:儒学诠释的两种形态》,《哲学动态》2014年第4期,第11-17页。
本文认为,将经学研究纳入到现在的中国哲学学科的研究中来,尤其是让经学中的相关“义理”内容也进入到中国哲学史的范围,其实这些并不是真正的问题。因为鉴于当前这样一种学科体制现状,为了经学研究的开展让其进入哲学学科可以说是一种“没有办法的办法”;而将经学之中的“义理”内容也纳入到中国哲学史研究则是为了纠正此前的某些偏失,可以说本来就理应如此。而真正的问题只在于,如果我们对于经学与哲学的关系没有一种更深入的了解,尤其是对于这二者之间的“疆界”和本质区别不清楚的话,让经学进入哲学的实质还会只是用经学去扩充了中国哲学史的“史料”范围而已。如此一来,进入哲学之后的经学依然是被“肢解”了,经学的价值依然没有得到应有的对待。而这是我们所不希望看到的,也是本文现在来讨论这些问题的原因和主要意义所在。
最后,撇开当前的“国学热”不说,仅从越来越多的学人对经学研究的日渐重视来看,经学作为一门纯粹的知识学术在此后数年内实现复兴应该是可以期待的。正因为如此,前面所有的问题其实最后都可以归结到一点:今天我们对待经学的态度如果不再是“再见”的话,那么接下来就应该认真考虑如何“再建”经学的问题了!所谓“再建”经学,不仅是指经学学科的设置和归属问题,更重要的是指我们在今天究竟应该如何来开展新时代的经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