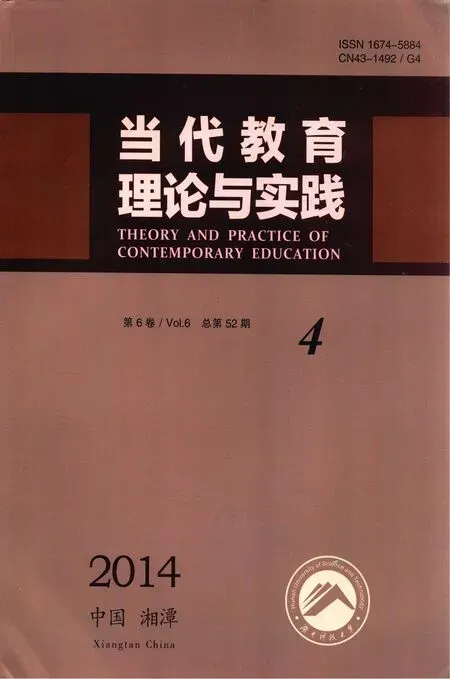不同政治局势下的中国译学史发展①
2014-03-30张奕欣曾晓芳
张奕欣,曾晓芳
(湖南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湖南湘潭411201)
谈及翻译的历史,陈富康的《中国译学史》是不可不谈的一部著作。该著作分别从四个阶段详细地描述了中国译学的发展过程,即中国古代、晚清民初、民国时期、新中国成立后[1]。这些都有利于我们了解中国译学发展的曲折历史以及推动中国译学蓬勃发展的一些重要因素,进而可以得知促进翻译发展的因素无外乎是政治、经济。本文着重分析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政治局势是如何促进翻译飞速发展的。
1 中国古代的译学发展
众所周知,佛教不是我国的本土宗教。理论上来说,作为外来宗教,它对中国的影响本应弱于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然而,这个由古印度的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境内)传来的宗教到至今为止都深深地影响着中国人民,融入于中国灿烂的五千年文化中。而道教在中国的发展却止步不前。究竟是什么造成如今这样的局面呢?
毫无疑问,翻译对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功不可没。但是,为什么古代民众愿意花费大量的时间钻研佛经,而不选择大力推行本土的道教思想呢?这得从佛教和道教的核心思想说起。佛教宣传的思想是忍耐,号召劳苦大众要顺从,来世就可以富贵,这恰好符合统治者的思想要求。因此相较于道教倡导的无为而治,统治者更乐于举国推行佛教。于是就有了佛教现今的遍地开花。前有苻坚邀请鸠摩罗来什来华宣讲,后有玄奘远赴西天取经,无一不反映当时统治者对佛教的热衷程度。
由于统治者想维护自身利益,加强政权统治,佛教如竹笋般飞速发展。与此同时,佛经翻译也得到了良好的发展。然而,有关佛经的译著虽然比较多,但是与之相关的译论却十分罕见。并且,如果要叙述我国古代译学理论,需追溯到六朝以后的佛经译论,而中国早在秦始皇时期就有佛教了。
纵观我国古代的佛经译论,可以发现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译经理论大多都是零星的、片断的译论,但合而观之,所涉及的方面较广,仍具有研究价值。例如:在关于专名的音译问题上,玄奘提出了“五种不翻”理论,即神秘语,多义词,中国没有的无名,久已通行的音译,以及为宣扬佛教需要的场合,凡遇此类名词,皆宜不翻。“释迦牟尼”如果意译为“能仁”,则其地位便似乎不及孔子与周公,“般若”一词显得庄重,意译为“智慧”就显得轻浅了;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其中“五失本”抓住了涉及翻译的直译与意译、质直与文丽、质与量的矛盾和统一;“三不易”涉及了翻译活动的主体性问题,是系统的、辩证的、先进的中国传统译论。“五失本,三不易”涵盖了翻译学本体和主体问题,具有全面、系统性。而且,其中的许多观点非常先进,与现代翻译理论和语言学观点有相通之处,对中国传统译论进行现代的诠释具有深远的意义,是构筑中国当代翻译学的一块基石。
二是译经理论在服务于外来宗教的同时,借鉴了本土文化,并扎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使之易于中国人民接受。例如,译经理伦中常常将佛经中的经典故事与中国传统经典著作《诗经》、《尚书》等。例如支娄迦谶把“真如”译作“本无”,安世高译《阴持入经》把“色、受、想、行、识”五类构成人的因素译作“五阴”,再如支谦译《般若波罗密经》为《大明度无极经》,把“般入”(智慧)译作“大明”、“波罗密”(到彼岸)译作“度无极”,均取自《老子》的“知常曰明”和“复归于无极”。佛经以翻译为媒介进行的传播促进了中国语言、文学、民间艺术、本土信仰、宗教组织、社会风尚等诸多方面的新发展;此外源于本土的哲学思想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升华,这是佛经翻译所产生的正面影响,而这些思想的传播逐渐为封建统治者所用,成为长期桎梏人民思想的束缚,佛教的适时而进,佛教的传入即是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也是一种关于社会和经济发展的人类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当时中国的劳动人民的精神诉求。
佛经翻译到北宋时期基本结束。此后,由于动荡不安的局面和统治者闭关锁国的政策等原因,除了少数民族进行了少许翻译活动外,翻译活动趋近于无。直至17世纪,西方天主教开始打开中国市场,翻译活动才开始复苏[2]。但与佛经翻译相比,未能产生比较重要的翻译理论。此外,由于罗马教廷干涉中国内政,不少传教士不只能动中国文化礼仪和习俗,18世纪初遭天主教到统治者的驱逐,直接影响到中外交流和翻译的发展,标志着我国古代第二次翻译活动又一次停止[3]。
2 晚清民初的译论
由于清王朝的闭关政策,中国盲目自大,没有赶上“蒸汽时代”。随后,在1840的鸦片战争中,帝国主义列强凭借火力十足的枪炮打开了中国尘封已久的大门,再加上清政府自身的腐败,中国沦为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此时,在帝国主义如狼似虎似地瓜分中国领土时,各种西方思想文化也大量涌入中国。另一方面,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为了救国复兴,也开始学习西方先进的文化知识,以寻找强国之路。
在这样一个复杂的政治背景下,翻译活动也开始复苏,日益频繁,并在中国近代史上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此时,有关翻译的理论也随之增多,也更加丰富了。翻译活动也不再局限于宗教翻译,而涉足于科技翻译。例如,以严复,张之洞为代表的官僚洋务派就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在一定程度上刺激翻译活动的蓬勃发展,体现了统治者开始意识到翻译活动的价值,注重培养翻译人才、组织译者工会等。但是由于自身的封建思想的桎梏,在翻译外国著作中,会反对翻译国外有关“男女平等”等内容的书。
虽然洋务派寻求翻译内容的突破,但在中国近代对翻译理论作出最大贡献的当维新派莫属。例如,马建忠、梁启超、凤谦等人,最早提倡广译,便突破了洋务派及教会人士专译格致类书的狭隘格局,随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又提倡快译和译日文书。
这一时期,涌现了大批翻译家,他们各自都提出了自己的译论。如严复提出了翻译的“信、达、雅”标准,是翻译界的金科玉律;林纾强调发展翻译事业,才能“开民智”,才能让国人了解列强的凶恶和阴谋,才能抵抗欧洲列强,此外,他认为救国应当靠“实业”,所以他在翻译过程中注重实业发展;以及鲁迅和周作人这对兄弟强调翻译对于“改良思想,补助文明”,引导国人进步意义重大,注重“异域文术新宗”的艺术性,强调翻译文学作品的怡情和涵养深思作用。并且周氏兄弟不像梁启超那样,简单地以翻译直接作为改良社会的武器或论证的工具。他们在强调翻译的社会功利目的之外,同时不忘记文学本身作为艺术的特点和功能。
3 民国时期的译论
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民国时期主要提倡民主与科学,批判中国文化,并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虽然只有短短三十几年,但在这一时期,文坛上和译坛上能人辈出。但此时与晚清时候相比,人数虽多,更多不是靠思想、政见来划分,而是依据社团与流派角度来区分。其中,建树比较大的社团是文学研究会、创造社、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新月派和论语派等。
其中,文学研究会的朱自清虽然有关翻译的论述不多,但是其对译界的影响程度不可小觑。例如,他将历来译名的方法概括为五种:一是音译分译,即一般音译,一半意译;二是音译兼译;三是造译;四是音译,五是意译。他对这五种方法逐一作了分析,他认为,“音译分译”历来少用,原是一种尝试,并不作为正法,其缺点是既不像音,又不像义。“音译兼译”则极难,“如要两全,必然两失”,吃力不讨好。“造译”除了译化学书常用外,也很少用,而且这种新词令人音义茫然。
此外,以郭沫若为首的创造社是民国时期另外一个有重大影响的新文学社团。郭沫若在文化学术很多领域都做出了十分重大的贡献,精通日、德、英等国文字,一生翻译了大量作品。他在翻译上理论上也有其独到的见解。他的译论也影响到了郁达夫、成仿吾等人。同时,无可讳言,当时他的文艺思想带有宗派主义和唯心主义色彩,这也影响到他的翻译理论。他不赞成矛盾、郑振铎主张的翻译介绍“应该审时度势,分个缓急”的意见,认为这是“阻遏人自由意志”,“是专擅君主的态度”。并且,他强烈翻译文艺的“功力主义”,认为这是“文艺的堕落”。他还自创了“风韵译”,强调“诗的生命,全在它那种不可把捉之风韵,所以我想译诗的手腕于直译意译之外,当得有种‘风韵译’”。
民国时期译论史上的批评、讨论和争辩是很火热的,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翻译理论的发展。例如,新文化运动者,一开始便以林纾,甚至严复为批评的靶子。虽然,这些批评未能充分肯定严、林两位对翻译事业的贡献,但对于端正新文化运动中的翻译事业的方向确实起了重要的作用。此外,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就涉及翻译的“外部研究”也在潜移默化的丰富译论,为我国译学史上增添了夺目一笔[4]。
4 新中国成立后的译论
新中国成立后,百业待兴,翻译工作自然是其中之一。但是由于十年文化大革命,新中国翻译理论史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文革前,翻译工作随着新中国的发展而取得了较大的成绩,翻译理论工作也随之得到了重视。在此阶段,就有《世界知识》社创刊了《翻译》月刊,其代表编辑有董秋斯、林淡秋、胡仲持等翻译工作者。除此之外,中央人民政府出版创刊了《翻译通报》月刊,该刊适应了新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要求,并把加强翻译工作者之间的联系,交流翻译经验,展开翻译界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提高翻译标准为宗旨。当时,由于我国与苏联关系密切,大力宣扬共产主义,中共中央宣传部还设立了斯大林著作翻译室,全面、系统地开展了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编译工作。
第二个阶段是文革期间,由于当时对知识分子的打压以及闭关锁国政策,中国文化停滞不前,翻译研究工作基本停滞。但港台地区以及旅居海外的翻译研究者仍在继续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如香港的翻译工作者自发组织了“香港翻译学会”,经常组织各种学术活动,并出版会刊《译讯》。学会几乎每年都举办一次较高水平的翻译研讨会,并将这些研讨会上的论文编为《翻译丛论》出版。此外,香港还出版了许多翻译大家的译学著作,是当时不可多得的翻译材料。台湾地区的翻译活动也非常活跃,出版了许多翻译著作,有关翻译理论的书和论文也出了一些。但是,在当时虽然台湾地区的翻译人才众多,翻译作品丰富,但却没有一个全省的翻译工作者的统一组织。与香港相比,就落后了一大截。
纵览中国译学历程,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翻译研究,尤其是翻译理论研究正在不断的自我完善、日趋成熟。然而翻译活动要得到健康发展,则需要国家政局稳定的支撑、国家明朗政策的引导,以及对翻译活动者的开拓创新精神的大力支持与鼓励。
[1]陈福康.中国译学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2]廖七一.当代英国翻译理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
[3]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4]许 钧.翻译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