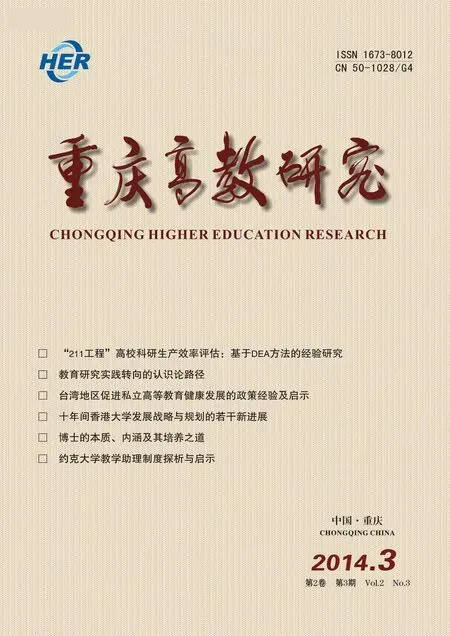跨文化教育:文化融通的智慧
2014-03-29刘徐湘
刘徐湘
(云南大学 高等教育研究院, 云南 昆明 650091)
跨文化教育是当今世界一种新的教育思潮。经济全球化进程一方面加强了世界各国各民族相互交流与沟通,另一方面也使得文化冲突日渐突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跨文化教育就是为了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努力增进世界各国交流与融通,其中蕴含的文化融通智慧值得我们探究。
一、跨文化教育之目的在于文化融通
跨文化教育作为一种世界教育新思潮始于20世纪80年代,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倡导下,它经历了一个从理念到实践的过程。1980年联合国开始倡导跨文化教育,并在“世界文化政策大会”后进行了“世界文化十年”活动。199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教育对文化发展的贡献》的文件, 在该文件中明确系统地提出跨文化教育的理念,尔后,教科文组织开展了跨文化教育实践活动,探究了许多跨文化教育实践方法。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跨文化教育目的十分明确,那就是“促进对文化多样性的尊重、相互理解和丰富”,“促进尊重文化的多样性及增强理解可以确认的不同团体的文化”,“增进国际理解, 并使同各种排斥现象作斗争成为可能”, “其目的应是从理解自己人民的文化发展到鉴赏邻国人民的文化, 并最终鉴赏世界性文化。”[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跨文化教育目的的提出与当今世界文化冲突与融合的背景有关。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各国与各民族之间的交流逐渐深入。但与此相随的是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文化冲突与融通。
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萨缪尔·亨廷顿率先提出“文化冲突论”,认为世界冷战后主宰全球的不再是意识形态的冲突而是“文明的冲突”[2]372。纵观当今世界发展,文明冲突的确存在,一方面存在强权的意识形态以世界警察或拯救者身份干涉他国内政,另一方面存在极端的宗教势力或组织以恐怖主义方式破坏世界安宁。它们所具有的共性即是跨文化影响导致人们对异质文化的排斥甚至仇视,即便是一个国家或民族被屈服于另外某种文化,也必将导致人们的心灵创伤。
与“文化冲突”相反的是文化融合与融通。人们在不同文化的交流与交往中获得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并且不断地完善自身文化体系,得到良性的发展,这就是文化融通。
当不同文化相遇时会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境况,一种是文化的冲突,一种是文化的融通,是冲突还是融通取决于人们面对异质文化的态度。由此,跨文化教育走上了前台,基于人们对不同文化的理解,为了世界和平与发展,我们需要跨文化教育。正是在此背景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倡跨文化教育,其目的就在于文化融通。
人们很早就认识到教育之于人类社会文化传承与交流的作用,因而,跨文化教育对人类文化变迁与交流表现出举足轻重的作用。历史上跨文化变迁与交流有两种形式:一种为强制形式,如战争与文化侵略。美洲印第安民族文化就在战争与文化侵略中逐渐消失,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希特勒更是想用种族灭绝方式消灭犹太民族文明,这样的变迁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因为,一方面是战争的残酷导致人类的灾难,另一方面是一种文化的消失或灭亡对于人类本身而言也是一场灾难。另一种是非强制的形式,比如旅游、通商与教育。中国古代丝绸之路就在中西方搭建了一座美好的沟通之桥,马可波罗中国之行也为西方了解中国开启了一扇天窗。但教育与旅游或通商不同,教育有着明显的目的性与计划性,并且可以向着未来做筹划。
教育富有目的性与计划性也不是天然的。当他没有理性思考,没有对文化与传承的认同和责任时,也会放任自流。萨缪尔·亨廷顿敏锐地感受到冷战后世界形势是文化和文明冲突。他重申莱斯特·皮尔逊的警告,人类正进入“一个不同文明必须学会在和平交往中共同生活的时代,相互学习,研究彼此的历史、理想、艺术和文化,丰富彼此的生活。否则,在这个拥挤不堪的狭小世界里,便会出现误解、紧张、冲突和灾难”[2]197。他以理性思考给教育的提示是:如果我们要在未来世界中保持和平发展的良性态势,就要提倡避免文化冲突的教育,而这种教育就是跨文化教育,就是文化融通的教育,它主张不同文化之间要相互理解、认同、交流和学习,主张培养学生优良的文化融通素养与素质。跨文化教育体现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与发展委员会报告中,《文化多样性与人类全面发展——世界文化与发展委员会报告》中专门论述了跨文化教育问题[3]。
199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其专题研究报告《国际理解教育: 一个富有根基的理念》中,分别介绍了世界各地跨文化教育的一些实践案例[4],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教育目标很明确,就是要在各种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氛围中形成学生文化融通的素质。
只有在当今的教育中提倡文化融通的目的,才能造就出理解本国异质文化,理解他国异质文化,最终理解世界性文化的一代新人,从而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宁。当今时代文化冲突的确存在,如果我们放任文化冲突并让它不断放大,如果我们听任强权意识形态的文化侵略,听任极端文化势力的恐怖威胁,文化对抗将无处不在。那样,人类将陷入仇恨与战争中而难以安宁。如果我们坚持文化融合的理念,并以此为目的提供跨文化教育,促进异质文化之间的交流与理解,那么,人类就会拥有博大胸怀,世界和平值得期待。让我们充满信心的是:我们从事着教育,教育影响将是稳定而长期的。教育通过培养人而实现外在目的,通过文化融通理念的倡导,通过以文化融通为目的的课程与教学,通过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良好结合,我们一定能够培养出具有文化融通素养的人,从而实现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二、跨文化教育需要文化融通的智慧
跨文化教育要实现文化融通并非易事,它需要文化融通的智慧。所谓智慧是人们对宇宙人生博大圆融的理解和素养,表现为融合理智、道德、审美在内的整体心理结构和精神力量。从跨文化教育的目的要素来看,从跨文化教育培养人才的基本素养来看,我们需要的正是文化融通之智慧。
(一)跨越不同文化需要文化融通的智慧
所谓跨文化教育需要解决不同文化之间理念与观念的冲突,在不同文化之间搭建沟通之桥,他的关键词是“跨文化”。由于环境和历史的不同,世界各国的文化存在明显的差异,即使同一个国家也有不同文化的存在。从宗教信仰到衣食住行,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很大甚至有矛盾与冲突。怎样在不同文化之间实现跨越,怎样让不同文化能和谐共处,需要一种异中求同的智慧。中国文化有着“和而不同”的思想,这是承认差异和谐共处的智慧,是一种文化融通的智慧。然而不是所有文化都能有如此包容之智慧,因而,跨文化教育需要从世界上所有文化中吸取文化融通的智慧,以实现不同文化之间的跨越,以真诚之心搭建不同文化之间理解之桥。
(二)达成不同文化之间相互理解需要文化融通的智慧
现象学家在面对实事时,往往采取“悬置”[5]的态度,“悬置”是存而不论,经验事实依然存在着。如果借用这个态度来对待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那就是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存在着,但我们可以把它“悬置”起来不加讨论。有明显文化冲突的人们要达到相互谅解,这种态度十分必要。但是,我们除了“悬置”争议,还要追求相互理解,进一步的文化融通就是要消解争议,让不同文化之间的人们能相互理解。中国文化中就有此智慧,老子的“道”蕴含着无中生有、有中生无的过程,世间万物在生生不息中转化着。佛学传入中国,也与中国文化结合起来,佛学的无差别对待就是一种圆通之境,“圆觉”“圆观”就是对佛法的真正领悟。“一摄一切,一入一切”[6],了悟事事融通,心无挂碍,方得涅槃之境。佛学理论是文化融通之高智慧高境界,它是人生哲理,也是我们实现不同文化之间相互理解融通的智慧。我们需要从世界文化宝库中吸收文化融通的智慧,使自己成为有着文化融通智慧的人。
(三)使人们形成世界性文化素养需要文化融通的智慧
康德在展望未来社会时预见了公民社会的到来[7]210,世界性公民有着世界性文化修养。马克思则从哲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角度论证未来将是“每一个人都自由发展”[8]的时代。
能够欣赏世界性文化的人本身就是充满文化融通智慧的人,自古以来,这样的文化精英引领着社会发展,中国的玄奘、意大利的马可波罗曾经给世界带来文化大融合。但是,当今世界需要一大批有着文化融通智慧的人,因为经济全球化使各种文化不断交汇与融合,文化融通智慧将成为每个人的基本素养,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在世界大融合中减少文化冲突和对抗,各民族与文化的理解与包容将成为基本的国际文化氛围。由此我们看到,跨文化教育需要面向未来,以文化融通的智慧为指引,努力造就一代能创造和欣赏世界性文化的人。
世界性文化修养需要培养个人“世界历史性”[7]18观念,需要国际理解教育,可持续发展教育,和平教育,多元文化教育的整体价值理念[9]。但是,理念付诸实践需要文化融通的智慧,需要包容各种不同文化理念,并选择最为合适的理念作为未来教育实践方向。世界性文化素养不会轻易降临,他需要不同文化之间的融通,需要一种大智慧,那是值守自身文化又超越自身文化局限性的智慧。
可以说世界性文化修养有一个文化融通小智慧到大智慧的升华过程。所谓文化融通小智慧是理解不同文化,达到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而文化融通大智慧则是坚守自身文化的本性,又能超越自身文化局限性,是自身文化主动融入世界整体文化的过程。
世界性文化修养首先要理解不同,理解不同文化的差异性。睁眼看世界,我们知道世界是多么的不同,它依然是认知过程,就像知识能够使我们聪明而不一定会带来智慧一样,理解的智慧阶段由于其认知特性依然是初级的。它只能是小智慧。
而大智慧则是我们理解文化的差异,更加感悟到自身文化的本真与可贵,也知道自身文化的弱点与不足,从而在值守自身文化本性的同时超越自身文化,使自身文化主动地融入世界整体文化中。它是文化的自我觉悟,表现为“文化自觉”[10],因此,“全面地了解和掌握世界脉搏和各民族文化发展变化的信息,吸取世界各民族文化中的精华,在相互学习、共生中共同努力克服全球化给世界带来的风险,为争取一个更为和谐的世界早日到来而贡献力量,就成为今天坚持文化自觉性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方面。”[11]它超越了认知束缚达到了知情意的结合,它是对世界性整体文化的认知,蕴含着对世界性整体文化的情感和价值认同,并通过主动行为使自身与世界性整体文化融合。 它是文化融通的大智慧。
三、跨文化教育的文化融通智慧策略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尝试了各种跨文化教育改革实践,这些改革行之有效,它也给我们提示出文化融通的智慧策略问题。从国家民族文化自身发展与完善的角度来看,跨文化教育需要文化融通智慧的策略。这些策略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理解
文化融通首先强调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文化异质性是文化发展的本然状态。由于地域和历史不同,文化发展有其自身发展脉络,各地文化表现出不同的精神与物质追求,从宗教信仰到饮食习惯沉淀为不同发展状态。
正像生物多样性一样,人类世界的文化也表现出多样性特征。从科学原理中我们知道,恰恰是生物多样性维系着我们生命发展与完善,人类从生物多样性中获益匪浅,仿生学与遗传工程为人类创造了无尽财富,而我们人类自身也正是在生物多样性选择中脱颖而出的,可以说没有生物多样性选择背景,就没有我们人类。从社会学原理中我们可以明确,不同社会结构,不同社会生产方式导致不同文化存在,结合语言学与历史学考察,我们更加明确,人类文明差异是多么自然。这些理性态度需要我们跨文化教育获得,跨文化教育就是要使受教育者成为能够理解不同文化及其生存方式的人。
理解扩展着理解者的精神世界,理解一方面在于意义生成,我们知道不同文化对于人类文化本身的价值;理解另一方面就在于它对于理解者精神世界的不断完善。对于每一个体,“自我的构成与意义的构成是同时的”[12],在理解的意义构成中,人成为有着理解素养的人。
(二)认同
如果对于异质文化仅仅停留在理解水平,还不会与本民族文化发生积极内化作用。若要对不同文化有进一步融通还需要认同的作用,认同是在理解基础上展开的,只有理解了才会有建立在理解基础上的认同。
认同与理解最大不同就在于理解可以停留在认知层面而认同则要在认知基础上达到情感与价值诉求。人们对于事物的理解可以停留在认知层面,停留在认知层面的理解承认事实或法则,但不一定会认同它,认为这些事实合理合法,但是不一定合情,这样的事实是不会唤起认知者情感认同的。相反,人们认同的事实或法则能引起认同者强烈的情感体验。因而,跨文化教育需要使受教育者认同一些异质文化,跨文化教育实践首选艺术交流与学习,因为艺术建立在人们共通的情感诉求基础上,这些交流往往能很快唤起不同文化人们之间的认同感。
认同伴随着认知与情感的互动,并会上升为认同者的行为习惯。人们在认知与情感长期互动中形成认同。与此相应,跨文化教育也要强调认知与情感互动,以达到对异质文化的认同,这就像中国的书法和武术在一些国家广为流传一样,那些喜爱中国书法和武术的人们有一个认识与情感长期互动过程,他们研习书法和武术原理,又在不断练习中养成好的行为习惯,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爱上了书法,爱上了武术,这就是文化认同。
(三)相互学习与完善
不同文化都有自身并不完善的地方,文化融通就是要从其他文化营养中吸收精华,以进一步完善自身文化。
跨文化教育要达到如此目的需要倡导开放心态。随着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剧,全球化时代的来临,文化交流无处不在。在全球化背景下,多元文化的独立与交流将成为常态,文化霸权的时代已经结束,沃勒斯坦认为,产生于16世纪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本来是一种文明,但随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建立,这种文明以社会科学和意识形态的扩张形成为一种普适化的文明,逐渐异化为一种霸权模式[13],这种模式在多元文化与文明背景下需要不断地改进。每一种文化都有其自身的独立性,但是独立性并不排斥其他文化,要想自身文化得到保护需要在与其他文化交流中获得新的力量。中国云南少数民族文化在与外界不断交流中反而扩大了自身影响与感染力,以杨丽萍舞蹈为例,在结合了芭蕾与现代舞功底以后,她的“雀之灵”反而更显出本土民族的艺术魅力。
另外,需要我们具有文化吸收的能力。文化在交流中获得完善,但是,如果在吸收过程中我们完全丧失了自己,就会失去吸收其他文化的能力,这就是为什么有的文化会在不断交流中消失的原因。因此跨文化教育并不是要我们放弃本国本民族文化,反而是要我们珍惜本国和本民族的文化,让这些文化继续发扬光大。对其他文化的吸收能力来自对本国文化和本民族文化自身特性与独特性的坚守,我们要在文化交流中不断完善自身文化体系而不是要削弱它。
文化吸收能力还在于对其他文化的选择,并不是所有外来文化都利于在本国或本民族传播,如何选择可在本国或本民族传播之文化需要我们的智慧。有些文化也有传播途径与交流方式等问题,这也需要我们做出明智的选择。
文化吸收能力还需要我们对其他文化优势的敏感性,我们需要学习其他文化的心态,从精神到语言,从文学到艺术,都需要我们认真地学习。
参考文献:
[1] 赵中建. 全球教育发展的历史轨迹: 国际教育大会60 年建议书[R].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1999:498-507.
[2] 萨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 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
[3]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多样性与人类全面发展——世界文化与发展委员会报告[M].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
[4] 赵中建. 全球教育发展的研究热点: 90 年代来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报告[R].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1999:367-374.
[5] 胡塞尔.纯粹现象学通论[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97.
[6] 太虚.佛学概论[M].新加坡:南洋佛学书局,1993:57.
[7] 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8]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86.
[9] 冯建军.当代主体教育论[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174-178.
[10] 费孝通.“美美与共”和人类文明(上)[J].群言,2005(1):17-20.
[11] 苏国勋.全球化:文化冲突与共生[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115-116.
[12] 伽达默尔.效果历史原则[J].世界哲学,1986(3):55-58.
[13] 王正毅.世界体系论与中国[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