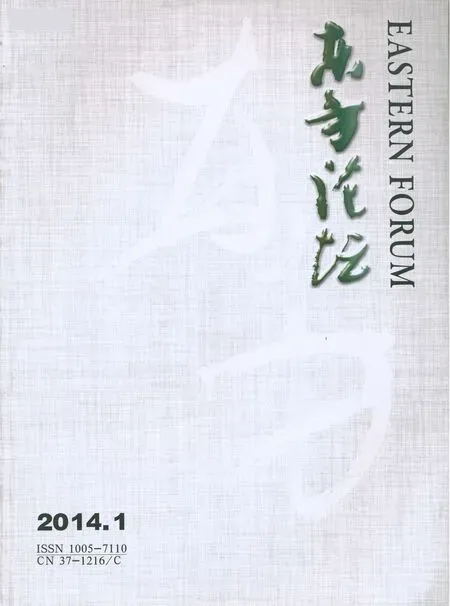自我身份探索的途径
——《同名人》异族婚恋主题分析
2014-03-29张玮
张 玮
(安庆师范学院 外国语学院,安徽 安庆 246201)
自我身份探索的途径
——《同名人》异族婚恋主题分析
张 玮
(安庆师范学院 外国语学院,安徽 安庆 246201)
流散文学中,对自我身份的探索和文化身份认同是重要的表现内容,印裔美籍流散作家裘帕·拉希莉的《同名人》描写了两代印度移民自我身份探索时的困境、文化融合等问题。异族婚恋是《同名人》中,第二代印度移民面对印度文化与异质文化之间冲突与抉择时,进行自我身份探索的途径,也是身份认同的中介及桥梁。
流散文学;裘帕·拉希莉; 《同名人》;文化身份
印裔美籍女作家裘帕·拉希莉以短篇小说集《疾病解说者》获得2000年度普利策小说奖,她的首部长篇小说《同名人》出版后也获得了各界好评,小说讲述了两代印度移民在美国建立新生活的过程,展现了他们在异域文化环境中的心灵历程。对裘帕·拉希莉这样的流散作家来说,自我身份探索和文化身份的认同是其作品中很重要的表现因素,本文分析《同名人》中在美国出生的果戈理﹑毛舒米﹑索妮娅等年轻一代印度移民面对印度文化与异质文化之间冲突与抉择时,通过与异族青年婚恋这种途径,进行自身身份的探索,从而获得身份认同和文化归属感。
一、自我身份探索的困境
“身份认同的依据乃是文化,在多种文化并存的环境中,人们不但觉得新奇有趣,更是常常深感迷茫。”[1](P4)对于出生﹑成长在美国的果戈理等第二代印度移民来说,在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里,他们不得不在两个(或多个)文化——家庭内的原文化和家庭之外的异质文化——之间变换模式,他们的文化归属感是模糊的﹑双重的。
年轻一代的印度移民从小就生活在家庭中原文化的影响下,从每日的饮食起居到和其它印度家庭的定期聚会,再到跟随父母回印度省亲等等,他们在父母所沿循的印度传统文化中长大。尽管果戈理出生在美国,在他六个月大的时候,父母尽可能地邀请了所认识的印度人来给他办米庆仪式。小果戈理被打扮成典型的印度儿童,按照传统的方式被喂食米饭﹑抓选能预测他未来之路的各种象征物品,宾客们也穿着传统服装,吃着用美国原料做出来的印度风味的食物。这些同样可能出现在其他印度流散者家庭里的食物﹑穿着和仪式,以直观的方式向周围的印度人(大人和孩子)演绎着印度文化,以具象的形式展现着印度文化,“社会的和象征性的民族环境交往有助于提高群体认同感”[2](P627),久而久之,这些形式不知不觉地都会被内化为流散印度人的文化特性。
然而,“果戈理”们同时还要面对家庭外/异质文化圈的影响,这种影响有时候也会渗入到家庭所统辖的印度文化范围内。年轻一代的移民在学校里所接受的正式西方教育,给他们印度文化背景贴上了异质文化的标签。如果戈理“已经爱上了校园里的哥特式建筑,总是为环绕在他周围具形的美而深深惊叹”[1](P122),他理解并沉迷于这种不同于印度文化的东西。并且,异质文化的多样载体以时尚潮流的元素吸引着他们,外化在他们言行﹑穿着和工作﹑交友等方面,如毛舒米的英国口音,索菲亚耳朵上多的几个洞,果戈理的朋克摇滚乐专辑和甲壳虫的海报等。他们每日面对印度文化和异质文化之间的差异,在两种文化圈内出入,随时进行文化心态调整,这些难免会行成自我身份探索的困境。“身份(认同)问题永远是一个困难的问题,尤其是对于那些文化上挪移的人,如移民……他们同时在两个世界中成长。”[3]他们在两种文化间摇摆,内心无法安宁,更加希望能早日确定自己的文化归属。对于年轻人来说,较为直接和明确的文化身份认同表现是获得异族/美国异性在情感上的接受,因此,果戈理等年轻一代选择了与非印度裔人谈恋爱这种途径。
二、异族婚恋:自我身份探索的途径
《同名人》中的主人公果戈理﹑毛舒米等都有着若干次与异族青年的恋爱经历,尽管这些恋爱关系都以分手告终,但恋爱过程中的情感体验和情感失败的原因,在他们所进行的自我身份探索过程中可以帮助他们认识自我﹑定位自己的文化归属。
1.果戈理:回归印度文化
大学二年级时,果戈理在火车上遇到了美国姑娘露丝,两个人兴趣爱好相仿,对艺术作品有着相同的欣赏品味,两人在一起无话不谈。果戈理把露丝带回家,向她介绍自己父母和他成长的生活环境。潜意识里,果戈理希望这位异族女子能进入到自己家庭里的印度文化氛围中。然而,受英国文化吸引,露丝去了英国读书,失去了两者的交集文化/美国文化后,露丝渐渐走出了果戈理的生活,果戈理通过异族恋爱的方式获得异质文化认同的尝试没有成功。果戈理与他的第二位美国女朋友麦可欣交往时,“从一开始,他就觉得已经毫不费力地融入了他们的生活”。[1](P153)果戈理住在她家里,和她父母一起出去度假,“在如此离尘出世的荒凉之地,他是完全自由的”。[1](P129)在自然界这个没有文化差异的环境里,人的文化背景被弱化至最小值的时候,果戈理才能感受到真正的自由。这也就不难理解,果戈理的精神世界在父亲突然去世后的转变和清晰化。父亲去世后,果戈理遵循印度传统的服丧方式,并计划全家回印度将父亲的骨灰撒在恒河里(这个计划并没有把麦可欣包括进去)。同时,果戈理花更多的时间陪母亲和妹妹而疏远了麦可欣,当被质问这些时,果戈理说:“我不想离开。”[1](P207)最终,果戈理走出了麦可欣的生活。从小到大,果戈理都希望成为一个真正的美国人,内心深处拒绝承认自己的印度文化背景,父亲的突然去世,绷紧了他所维系的印度文化之线,这线也拉起了内化在果戈理骨子里的印度文化特性,使他最终在内心倾向于认同印度文化,把自己定位到印度文化中,归属于印度文化中,并用同印度后裔毛舒米的婚姻,从形式上宣布对印度文化的回归。
2.毛舒米:在第三方文化中寻求平衡
毛舒米在英国出生,美国长大,又去巴黎学习,她身上所体现出的多国文化杂糅性更强更明显。十二岁的时候,她就“在纸上写下誓词,发誓永远不找孟加拉男子”,[1](P241)她在美国男人和法国男人间周旋,最终她向一位美国男子求了婚。那位美国男子和她一起去了加尔各答,并答应在美国举行印度式的婚礼。但是,婚礼前几个星期,毛舒米听到未婚夫在大庭广众之下抱怨印度之行,大吵一架之后,取消了婚礼。毛舒米觉得美国未婚夫“拒绝她的过去,挑剔她家的门风”[1](P246),他能接受非常西方化的毛舒米这个个体的人,无法理解或接受她身上所属的印度文化背景。毛舒米拒绝这个异族婚姻,是维护自己家庭/文化的尊严,也是对自身身份﹑地位﹑精神独立的维护。
与果戈理结婚后,一个偶然的机会,毛舒米和少女时代暗恋的美国人德米特利重新取得联系。毛舒米中学毕业时就认识了德米特利,这个美国男人成熟﹑自由﹑随性和不羁,他的个性对青春叛逆期﹑自我身份探寻期的毛舒米充满吸引力。德米特利会定时给她寄他读过的﹑认为她会喜欢的书,他还会在夜半时分给她打电话,连着说上好几个小时,可以说,德米特利是毛舒米文化性格形成时期的引路人和塑造者。尽管有十年没有联系,再见面时,两个人仍然能毫无隔离感地﹑自然地进入到之前的交往状态中。和果戈理结婚后,毛舒米还认为“他恰巧就是她心里想着要避开的那种人”[1](P241)。德米特利的再次出现,对结婚后还在选择文化归属的毛舒米来说,是一个选择加速器。她和德米特利的婚外情,是对丈夫的背叛,也是对自己妥协归属印度文化的不满表现,更是对印度传统文化的背叛。这种背叛,也是自我身份探索中对异质文化的倾斜和归属,她最终选择了第三方文化,“她沉湎在第三国语言﹑第三种文化里,那成了她的避难所;她接近了法兰西,一种与美国和印度不同的文化。”[1](P243)就像三角形具有稳定性一样,在印度﹑美国和法国文化所组成的三角结构中,毛舒米达到了自身身份探索的目的和文化身份的归属划分。
3.索妮娅:混合文化身份
裘帕·拉希莉并没有花很多笔墨来描写果戈理的妹妹索妮娅的恋爱经历,但从她之前一些非常“美国化”的穿着﹑喜爱等行为来看,索妮娅对自身身份的探索不比果戈理他们轻松。索妮娅在父亲去世后,搬回家和母亲一起住并且担负起每日做饭的责任(印式食物),看起来,她似乎回归了印度文化。然而,她选择了和一位身上有一半犹太血统一半华裔血统的美国青年本杰明在一起。本杰明的成长环境中,一定也有过或者正在进行着文化归属的选择,犹太文化﹑中国文化和美国文化这三种文化也组成了一个三角形般的文化环境,保持了他在家庭内的多样文化圈和家庭外的美国文化圈里找到文化归属的平衡。本杰明和索妮娅同样有自我身体探索的困境和焦虑,他们之间更容易获得理解和认同,和谐相处。
“从流散文学作品中可以看出,流散者反对固化身份,提倡混合身份。”[4]索妮娅的选择,既接受美国/异质文化对自己教育和塑造,也在自己的文化性格和文化身份上继承和保有印度文化的传统,她认识到身为流散者面对的文化变迁,她以一种混合文化身份的方式在文化交流中获得平衡。正如刘洪一所说:“在这种文化变迁中,文化的本原传统和基本精神得到保持和延续,同时,流散文化又能与时俱进,通过对异质文化优质要素的吸纳,对本土文化的扬弃,在文化的适度变迁中使得文化传统一以贯之地得到延续。”[5]
三、异族婚恋:身份认同的中介和桥梁
异族婚恋主题也是裘帕·拉希莉其它作品中经常出现的主题。裘帕用种种印度人的异族婚恋感受来表述这种自我身份探索中的体会,身份选择的结果和选择后的心理状态。如短篇小说《不适之地》中,女主人公嫁给一位美国人,生活平淡而不失幸福,但她的内心永远有一种不安感,这不安是对非印度裔丈夫能否值得依赖的犹疑,也是自己在异质文化中生活的不安。“生活在跨国空间的‘印度人’构造中的那些微妙的变化,至今没有得到认真的研究”,[6](P42)裘帕·拉希莉用自己的作品表现了移民的惶惑﹑思乡,以及对抛在身后的味道﹑气味和习俗的向往,记录流散者在寻找自我的过程中的探索和努力。
“对自我的失而复得——不是由主导的全球意识,而是由文化和社群来定义的自我——可能会在下半个世纪最初的几十年,成为社会批判和政治行动的首要任务。”[7](P90)在全球化的语境下,流散作家创作出的流散文学中,自我身份探索和文化身份认同等问题是其中一个重要表现主题,作家们试图在作品中解决流散者所面临的抉择困境问题。在自我身份的探索过程中,异族婚恋可以作为寻求身份认同的中介和桥梁,这种方式能帮助流散者在异质文化氛围中认清自我身份,不管是选择原文化还是异质文化,或者在两者间获得一种生存和内心的平衡感,流散者完成文化归属的选择。
[1] 裘帕·拉希莉.同名人[M].吴冰清,卢肖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2] A.班杜拉.自我效能:控制的实施[M].缪小春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3] 梅晓云.名字的背后是什么——评裘帕·拉希莉的小说《同名人》[J].西北大学学报.2008.(1).
[4] 陈春霞.流散文学的文化研究[D].苏州大学,2007,(4).
[5] 刘洪一.流散文学与比较文学:机理与联结[J].中国比较文化,2006,(2).
[6] 特贾斯维莉·尼南贾纳.特贾斯维莉·尼南贾纳读本[M].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2010.
[7] 阿希斯·南迪.民族主义,真诚与欺骗[M].卢隽婷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责任编辑:冯济平
Ways of Questing Self-identify in The Namesake by Jhumpa Lahiri
ZHANG Wei
(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Anqing Normal University, Anqing 246201, China )
The quest for self-identity and cultural identity are most important things represented in diaspora literature. The Namesake, written by the Indian-American diasporic writer Jhumpa Lahiri, describes the problems of the second-generation Indian immigrants in their quest for self-identity and cultural collision. When they face the confl icts and choices between different cultures, the second-generation Indian immigrants seek their self-identity and cultural identity by means of intermarriage.
diaspora literature; Jhumpa Lahiri; The Namesake; cultural identity
I109
A
1005-7110(2014)01-0116-04
2013-09-30
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民族与文化认同——印度英语小说研究(1947-2010)”(项目编号:13YJC75029)、英语国家级特色专业(项目编号:TS12154)阶段性成果。
张玮(1971-),女,安徽灵璧人,安庆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东方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