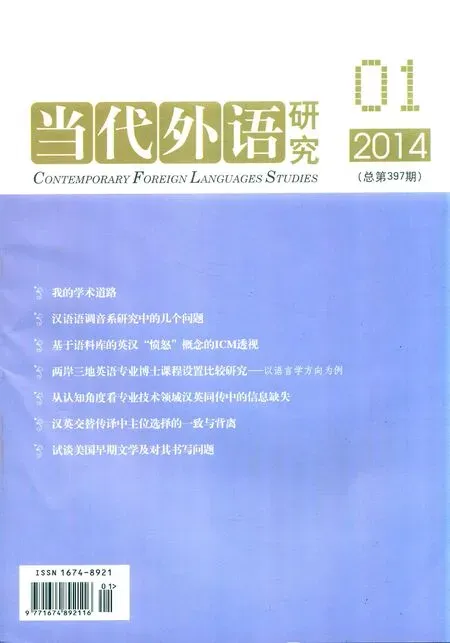解读《红字》和《磨砺》中的重复与差异
2014-03-29黄青青
黄青青
(福建农林大学,福州,350028)
《红字》(1850)自出版以来,就广受关注。国外对这部小说的评论真可谓包罗万象:D·H·劳伦斯认为这部小说彰显了清教徒式的道德(参见Elbert 1990:223);弗德里克·坎贝尔·克鲁斯(Frederick Campbell Crews)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角度观察认为《红字》展示出了人们对性欲的渴望和自我压抑,以及这种欲望被隐藏或得以升华的种种方式(参见Murfin 1991:217);伊弗特·奥古斯特斯·杜伊金柯(Evert Augustus Duyckinck)高度赞扬《红字》,认为它是奉献给世界的最正宗的美国本土作品(Duyckinck 1910:270);艾尔墨·肯尼迪·安德鲁斯(Elmer Kennedy Andrews)提出《红字》标志着美国文化的独立,代表了美国独特的文学传统(Andrews 1999:5)。
国内的评论亦五彩缤纷,不一而足。彭石玉(2005)基于诺斯普·弗莱的原型理论,探讨了《红字》中人物在《圣经》中的原型及情节原型。刘林(2008)关注到《红字》的长篇序言“海关”的叙述者“我”和小说正文的主人公有着相似的心路历程,因此认为“海关”与《红字》间存在同构关系。毛凌莹(2011)对《红字》的镜子意象进行分析,认为其承担重要的叙事功能。总之,纵观国内外评论,对《红字》的解读从精神分析到女权主义批评,可谓流派纷呈,目不暇接。
《磨砺》是英国20世纪著名女作家玛格丽特·德拉布尔(Margaret Drabble,1939~)于1965年出版的作品。小说问世便受到读者喜爱,获得约翰·卢埃林·里斯纪念奖(John Lewelyn Rhys Memorial Award),并在BBC女性节目中广播,因此甚受评论界关注。评论开始多集中于探讨小说的主题思想,如盖勒·维提尔(Gayle Whittier)认为,和德拉布尔的其他作品一样,《磨砺》的主题是关于母性和性爱、母性和职业之间的矛盾,但德拉布尔并不因此感觉惘然不知所从,而是认为母性和职业之间的二元对立是可调和的(Whittier 1980:197)。随着女权运动的波澜起伏,研究视角自然转向女性主义,比如,艾琳·克罗南·罗斯(Ellen Cronan Rose)提到,包括《磨砺》在内的早期作品中女主人公徘徊在“渴望长大而同时又幻想永远长不大”的尴尬中(Rose 1980:8)。随着研究视角的不断扩展,关于《磨砺》的评论亦呈现多样化趋势。威尔瑞·格若斯维纳·迈尔(Valerie Grosvenor Myer)认为德拉布尔塑造的所有主角都体现了清教主义的负罪与焦虑感(Myer 1974:15)。其他评论还涉及到小说中的宿命论倾向等问题。国内的研究亦伴随着国外研究动向亦步亦趋,近年来较具代表性的研究包括如杨跃华(2011)和刘巧(2012)等。前者把《磨砺》、《瀑布》和《金色世界》看作是一个三部曲系列的整体,反射出当代知识女性在人生不同阶段的求索历程。后者指出《磨砺》中存在大量的含混因素足以解构小说的主题意义。
综上所述,以往的评论从未把处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两部经典《红字》和《磨砺》并置研究。本研究将从一个新的视角解读文本,拟以《磨砺》文本为主,《红字》为辅,用解构主义文学理论家J·希利斯·米勒的重复理论解读作品中呈现的重复与差异,以期彰显女性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的生命轨迹。《红字》中的海斯特实质上依旧是男性权威的代言人,《磨砺》中的罗莎蒙德则带着内心的矛盾刻意地反抗男权至上的传统社会对女性的规范。很明显,霍桑在小说中构建了一个男性权威为主导的社会,而德拉布尔则想通过探索追求独立的现代女性面对的生存困惑力图重构一个摆脱男权控制的世界。
1.人物和情节设置的重复
依据米勒的重复理论,小说中出现的重复现象分为三大类:一、细小处的重复,如语词,修辞格等;二、作品中事件和场景的重复;三、一部作品与其他作品在主题、动机、人物、事件上的重复(Miller 2004:6),第三类重复是一种典型的互文现象,暗合了法国当代文艺理论家茱丽亚·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的观点:“任何文本都是对另一文本的吸收和改编”(Kristeva 1986:37)。
不管是《磨砺》还是《红字》都是讲述一个女人的故事,这两个女人都有私生子,并且都因此遭遇磨难,但她们都以积极的心态融入社会进行自我救赎。《红字》主人公海斯特生活在17世纪末的波士顿,那是清教文化盛行的时代。当时清教徒们在新英格兰成功地压制了所有的公共娱乐活动和几乎所有的私人消遣,包括音乐、舞蹈、戏剧、公众游戏和游乐性集会(Mill 2001:80)。在个人道德方面更是苛求备至,因此,海斯特和丁梅斯代尔的私通行为难逃清教戒律的严厉惩罚。《磨砾》中的罗莎蒙德虽然生活在两性关系日益开放的20世纪60年代,但身为高级知识分子的她还是有意识地用维多利亚时期的传统道德规约自己。偶然的一次约会使她怀孕生子,开始面对种种生活挑战。
这两个女人虽然生活在不同时代并拥有各自不同的故事,但她们身上有很多相似之处。首先,女主人公海斯特和罗莎蒙德都本性善良,年轻漂亮,即使生育完孩子还能保持优美体型,但她们的家庭却总有些不尽如人意。海斯特出身于没落贵族家庭,有过不幸的毫无爱情可言的婚姻,但是她勤俭,乐于助人,积极向上。罗莎蒙德从小温厚宽容,虽来自于有教养的学者家庭,但对父母的所思所行并不十分认同,甚至还觉得“荒谬”(德拉布尔1997:27)①。其次,罗莎蒙德和海斯特触犯道德戒律的诱因颇有几分相似,都是源自对心中恋人纯真热烈的爱情。海斯特与原来的丈夫老医生齐灵沃斯之间根本没有爱情,到了波士顿和年轻牧师丁梅斯代尔相恋后生下了女儿珠儿,为了保护牧师不受伤害,海斯特自己勇敢地接受惩罚,抚育女儿,内心出于对恋人无私的爱促使海斯特坚强地面对惩罚和苦难。19世纪的欧洲受到英国维多利亚女王时代严厉的宗教性禁锢影响深刻,对女性的贞洁要求非常苛刻(罗素2009:1),而罗莎蒙德深受维多利亚时代道德影响,对两性性行为保持高度戒备,起先为了逃避与男性朋友上床,自己独创了“双重防护系统”,即同时与两个男友交往,并巧妙地使每一方产生错觉,以为她已与另一个上过床,通过这一方式小心翼翼地维持自己的贞洁。而当她正洋洋得意地在乔和罗杰之间纵横捭阖之时,乔治的陡然出现使这个运转地极好的“防护系统”瞬间崩溃瓦解。对乔治的爱是如此之强烈,以至于她情不自禁地献身于乔治并怀上了孩子。出于谨慎,罗莎蒙德向乔治隐瞒了私生子的情况并有意地避开他,她不想让乔治陷入由自己造成的不必要的烦恼中,同时也不敢确定乔治是否真地爱自己,她已然考虑到“性交与生育之间关联于生理,不关联于精神,这如同性交与爱之间没有必然的关联一样”(别尔嘉耶夫1994:197)。她唯一确定的是她自己深爱着乔治,深爱着他们的女儿。
此外,罗莎蒙德和海斯特都富有牺牲精神。海斯特为了恋人不被暴露而甘受惩罚。刑满之后,她本可以带着孩子远离是非之地,但为了守候恋人,她又甘愿忍受周遭市井小民的欺负压迫,毅然选择留在波士顿,期望有朝一日能和丁梅斯代尔远走他乡,去开创幸福美满的生活。罗莎蒙德在知晓了女儿的严重病情后,几番犹豫终究没有告知乔治真相,而是在自己博士即将毕业之际,独自照顾女儿,联系医生,在承受内心痛苦之余,还“为乔治从未分担过这不必要的忧伤而感到高兴”(143)。二人展现母爱的方式也很是深沉一致。海斯特在珠儿的抚养权要被强制剥夺时表现出以死相拼的坚定和决绝;罗莎蒙德根本不顾家人朋友的强力反对,克服客观存在的重重困难,坚决地生下了孩子;在孩子患病住院期间,由于被禁止探望孩子,焦灼不安的她顾不上自己作为一个高级知识分子的体面和尊严,不惜在护士们面前装疯卖傻地闹腾,终于如愿以偿获准留在病房照顾幼儿。在照顾女儿上,她们也有颇多相似之处,她们都有一双灵巧的手,善于做手工,在多少个不眠之夜,倾心为女儿缝制亮丽的新衣裳,这也足以说明她们对于恋人的爱是执着真挚的。
最有意思的是,两位女主人公都有一位才貌双全、出类拔萃、近在咫尺却又可望而不可及的恋人。海斯特的恋人丁梅斯代尔牧师年轻英俊,“曾就读于英国的一所名牌大学”(霍桑1996:56)②,因“雄辩的口才和宗教的热情”(57)而受人敬重,他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对于自己所犯的罪过负疚不已,一直“一副忧心忡忡,诚惶诚恐的神色”,“好像自感到在人生的道路上偏离了方向,惘然不知所从”(57)。因为内心受到宗教信仰的规约,年轻的牧师在上帝和海斯特间徘徊,最终选择了上帝,在向上帝的无限虔诚的忏悔中逝去,临死前告诫海斯特要继续完成上帝的旨意,因为他们犯了罪。罗莎蒙德的心中所爱乔治是BBC广播电台的播音员,“清瘦而富于美感的脸庞,发出BBC播音员那种令人愉快的声音”(21),此外,乔治的魅力还在于能够巧妙地回避罗莎蒙德追问的娴熟技巧,对于罗莎蒙德而言,这个像迷一样神秘的男人是那么不可捉摸,他的矜持多少让罗莎蒙德怀疑自己只是一厢情愿。罗莎蒙德为了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不再陷入传统女性角色的桎梏,在小说结尾时并未向乔治透露真相,虽然内心矛盾重重。海斯特和罗莎蒙德各自若即若离的爱情都没有理想中的完美结局,海斯特终究没能盼到和丁梅斯代尔长相厮守的美好日子,他们的爱情成了宗教教义的牺牲品;罗莎蒙德则因为主观因素和乔治的爱情也戛然而止。尽管如此,两位女主人公都是痴情的女人,海斯特在丁梅斯代尔过世多年后又回到给她带来无尽耻辱的波士顿,继续行善助人,完成恋人所交代的上帝的旨意;而罗莎蒙德除了乔治,“好像再也不会深深地喜爱任何人了”,“我怀着温情想念的唯一的人,就是乔治”(137)。
生活在不同历史空间的两个女主人公有着如此惊人的相似经历,并非出于偶然,这似乎已经很鲜明地暗示,爱情具有普泛性,不管时代如何变迁,“那种爱而不能得其所爱,亦不能忘其所爱的巨大的心理遗憾,以及对于天长地久永无绝期的坚贞美好的爱情的向往,却是一致的”(王耀辉2012:167)。
2.重复中的差异
《磨砺》和《红字》之间的重复不是单纯的“柏拉图式重复”。当代法国学者德鲁兹在《意义逻辑》中阐释了“柏拉图式重复”与“尼采式重复”的区别。“柏拉图式重复”突出的是具有重复关系的两部作品中相似的成分,而“尼采式重复”则更彰显双方重复基础上的差异性,前者的理论植根于一个纯粹的原型模式,强调模仿的真实性,后者则假定世界是建立于差异的基础上,万事万物皆有别于他物,所谓的“相似”只是表面的幻象,其本质皆是独一无二的(参见Miller 2004:6)。《磨砺》与《红字》之间虽然存在上述多处重复相似之处,但其各自的文本内涵则各有千秋,体现了重复的差异性。两部小说的差异性主要体现在两个女主人公对两性关系的态度在本质上是截然不同的。
《红字》女主人公海斯特终其一生都在为心中的神圣爱情牺牲自己,她的所有活动都是以恋人丁梅斯代尔牧师为轴心。勇敢坚强的海斯特内心并不认同清教戒律,但为了能与恋人一起,刑满释放后并没有选择回欧洲,而是继续戴着“A”字带着孩子在人们的蔑视羞辱中度日。表面上,她在继续为自己赎罪,实则在等候适当时机说服丁梅斯代尔带着自己和孩子秘密逃离。她心中期待的是与恋人远赴他乡重建爱和温馨的家园,但令人扼腕的是丁梅斯代尔并没有以同样的热情回应海斯特的召唤,对于宗教的虔诚使他拼命地压制对海斯特的感情,因为他的内心充满着对自己所犯下的“罪恶”的忏悔,自认为“是个外表受人敬重,内心堕落的罪人”(Smith &Wright 2011:41)。根据基督教精神,与上帝和快乐隔绝的,第一是自私,第二即是肉体之欲,这些是黑暗及死亡之路,隔断了与上帝的联系(詹姆士2002:321)。丁梅斯代尔临终时还不忘告诫海斯特,要“完成他的意旨”(233),“宗教使人与自身的本性发生隔离”(史密斯、瑞珀尔2000:171),丁梅斯代尔在基督教道德教化和清教禁欲主义的双重围攻下完全丧失追求自由爱情的勇气和对生命的激情,犹如行尸走肉般游弋于宗教理想和海斯特之间。最后耗尽了自己年轻的生命,他还诚恳地要求海斯特要继续忠诚于上帝的仁慈,继续赎罪。
痴情的海斯特执着地投入自己的一生精力和感情守候恋人,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在丁梅斯代尔过世多年、珠儿长大成人远嫁欧洲后,海斯特又毅然地回到充满悲伤记忆的波士顿并又重新戴上“A”字生活。与其说是回来继续行善赎罪,倒不如说是为了与埋葬在这里的恋人能长相厮守,丁梅斯代尔无疑成了海斯特心中永恒的上帝,真正的精神主宰。“她的人生浪费在了这个绝望的牧师身上”(Colacurcio 2006:106),丝毫没有自己的生活空间,丁梅斯代尔成了她生命中唯一的主宰。她的坚忍和勇敢也是建立在对这份遥不可及的虚幻爱情的守候上。她自始自终都忠诚于丁梅斯代尔,而后者则义无反顾地忠诚于上帝。因此,“她对清教权威的反抗不能说是完全成功的”(同上:105)。
海斯特的结局反映了她潜意识里对父权制文化的认同,从这个意义上说,她从来没有独立过,海斯特在两性关系上呈现出完全一边倒的趋势,是菲勒斯中心主义男性权威控制女性意志的二元对立的典型体现,而《磨砺》中的罗莎蒙德则正相反,作为亲历60年代欧洲女权运动的知识女性,已经形成属于自己的女性意识,不再迷惑于男性权威对“完美女性”的道德设置。罗莎蒙德不甘心“仅仅根据各种关系——性关系、母子关系、家庭关系——都是和男人的关系,来界定女人的身份”(弗里丹2007:1),她要“用自己的社会行为定义自己的身份”(同上)。
同样在男权社会中经历困惑与挣扎,同样陷入爱情的艰难抉择,同样面临独自养育孩子的辛酸,罗莎蒙德却凭借内心强大的女性意识,度过了重重精神危机,勇敢地面对生活的挑战。
罗莎蒙德强烈的女性意识使她拒绝成为像姐姐比阿特丽丝那样的传统女性,她深知“大多数的婚姻注定要形成精神上的失望和肉体上的疲惫”(转引自埃利斯2004:213)。惧怕因为爱情而深陷父权制文化的控制,成为“房中的天使”和男性的奴仆,对个体自主权的牢牢把握体现了罗莎蒙德鲜明的个人主义,虽然她深知自己可能走向另一个极端,即强烈的女性意识可能使她陷入一种孤独的精神流放,因为“为爱情而牺牲了整个的事业,虽然有时也许是一种悲壮之举,然而总的来说是愚蠢的;为事业而完全牺牲爱情,同样也是愚蠢的,而且丝毫没有悲剧意义上的英雄气概”(罗素2009:128)。而小说结尾也再次重复她对乔治的内心渴望和表面刻意否拒的矛盾,矛盾心态表露出女主人公潜意识中深埋着对传统男女二元对立关系中男性高居统治地位的排斥和不满,更体现她深怕一旦和乔治结合,会成为婚姻和家庭牺牲品的恐惧,因此,即便“只要她稍稍地给乔治哪怕只是一点点机会,乔治都有可能接受她和孩子”,“向乔治隐瞒孩子的真相是对乔治极大的不公”(Myer 1991:42),罗莎蒙德还是选择疏远乔治,她的内心“想要像个男人一样”(同上:44),独立自由地生活,她在潜意识里已把男性贬为“他者”,从而自然而然地剥夺了乔治的“知情权”。也正因为想要成为男人,罗莎蒙德怀有“阴茎妒羡”情结,而Susan Spitzer认为女性婴儿可以当作“阴茎替代品”(同上),因此,正如班扬通过基督重获新生,罗莎蒙德凭借女儿奥克塔维亚构建一个全新的自我(Sadler 1986:33)。
其次,两部小说对“A”字的隐含之意刚好相互对立,在《红字》中,海斯特胸前绣着鲜明的红“A”字代表着“放荡,通奸”,时时提醒她犯有罪过。耐人寻味的是,《磨砺》中亦提到了红“A”字,罗莎蒙德感觉自己“穿着胸前绣有醒目红A字的衣服东奔西走,不过我这个‘A’作为第一个字母,代表的是禁欲而不是放荡”(17)。她认为因为自己不能像同时代的其他姑娘们那样,不管不顾地慷慨“参与性活动”,而是自觉地用维多利亚时代的严谨道德约束自己,因此,偶然的一次性行为就怀了孕,她自认为是“受到了维多利亚式的惩罚”(17)。得知女儿奥克塔维亚生病后,罗莎蒙德的负罪感再次油然而生,“如果奥克塔维亚死了,这就是对我的罪过的报应,—无辜的将为有罪的而遭难”(152)。即使她内心深处还涌动着一股反抗的力量质疑她和乔治之间是否犯有罪过。虽然《磨砺》重新提到了《红字》中的“A”字,以及它带给女主人公的负罪感,但不同的是,《磨砺》对《红字》中“A”字意象进行巧妙地解构和重构,颠覆其原有的喻指意义,即淫荡,给予了“A”相反的含义,即禁欲,这也暗示了罗莎蒙德在反抗男权社会的压制,追求自身独立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把爱情与事业当作不可调和的二元对立的矛盾,虽然内心渴望乔治的爱情,但还是选择“事业型女人”和“母亲”的角色,而刻意逃避“情人”和“妻子”的角色。
再次,两部小说的差异性还体现在两位作者对男主人公的塑造手法上,《红字》中的男主人公丁梅斯代尔是作者霍桑着力着墨的中心人物,亦是小说情节发展不可或缺的支柱性人物,即使是配角奇灵沃斯,作者也是不惜笔墨大书其险恶用心。而《磨砺》中的男主人公乔治从头至尾都被作者德拉布尔“边缘化”,只寥寥数笔带过,而且皆是从女主人公罗莎蒙德所感所思的角度描述,根本没有给予他粉墨登场的独立舞台。跟其他男性配角一样,乔治并没有从德拉布尔的笔墨中多分到一杯羹,而只能屈当“闪过”的跑龙套式角色,男性角色的心理感受以及他们的言行统统被作者“雪藏”,他们仅仅只在女主人公的眼皮子底下和思维活动中方才“露面”。对比之下,很显然,从两个女主人公对两性关系的态度以及男主人公的塑造手法上的差异性可看出两位作者创作意图的差异,即霍桑以维护男性绝对权威的立场塑造了一个获得男权社会认可的“完美”女性海斯特,那么德拉布尔刚好反其道行之,《磨砺》挑战了男性话语体系,解构了男权至上的传统社会定义的“理想”女性的原型,颠覆了在男性话语霸权中把女性贬抑为隶属于男性意识的弱者。
3.结语
霍桑在《红字》中构建的是属于父权制基础上的菲勒斯中心主义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海斯特没有婚姻自由,她无奈地与一个毫无爱情基础的畸形老医生结婚;她没有恋爱的自由,与丁梅斯代尔的爱情被视为亵渎神灵,罪大恶极。《红字》暗示了作者霍桑潜意识里对男性话语体系的支持。女性在这个体系里,不管被描绘地多么勇敢、纯洁、美丽、高尚,她都缺乏自我意识,在这个世界里,女性没有属于自己的意识形态,父权制社会总是适时地向女性灌输男权中心体系的道德意识。海斯特对恋人无比忠贞,对上帝的旨意执着坚守,对鄙视侮辱她的人始终以德报怨,这些都是男权中心的社会赋予女性的标准美德,她的实践经历最终符合了男权社会对女性的道德规范,从而得以善终。这种善终可以看作是作者霍桑或者男权中心的社会体系对她表现良好的“嘉奖”。很明显,海斯特对于自身命运的反抗从未逃离过菲勒斯中心主义的牢笼,她无形中守护了宗教权威统摄下的男性中心主义的社会体系,默认了自己作为“女性他者”的地位。在《红字》里,宗教(上帝)的力量高高凌驾于人的意志,人在全能的上帝面前显得渺小无力(Maclean 1955:13),上帝可以轻易地给海斯特的爱情判处死刑,不管她内心有多么强大的意志力,最终还是成为宗教和男性权威的牺牲品,因此,《红字》展示的是一个由宗教力量统治男性意志,而男性意志又控制女性意志的菲勒斯中心主义的世界。
罗莎蒙德摆脱了父权制社会赋予女性的道德枷锁,但又不得不面对新的生存困惑,这正暗合了小说题目millstone磨石源自《圣经》的寓意。罗莎蒙德的人生选择构成了她生命中的沉重的“大磨石”(Spitzer 1985:87)。即使如此,作幽默诙谐的笔调还是为作品营造出积极向上的基调。罗莎蒙德虽然投入巨大的精力照顾生病的孩子,但她还是非常顺利地完成毕业论文并找到满意的职位。小说中男性权威的不在场使罗莎蒙德的女性意识有了用武之地。虽然她因此饱尝痛苦折磨,但其积极融世的心态足可证明她的顽强意志和反抗世俗束缚的勇气。面对生存的困惑和挑战,罗莎蒙德不再随意盲从男权社会的规则,而是多了几分审慎的执着,这也暗示了当代知识女性的走向。《磨砺》还彰显了德拉布尔对男性与女性,中心与边缘,权力与身份的颠覆和重构意识,暗示了作者对在男权制度下女性生存状态的忧虑和不满。德拉布尔之所以乐于展示知识女性面对的种种挑战,因为她本身就曾陷入这样的困惑:“是嫁个学究还是当个学究?”(Singh 2007:37),每个成年女性几乎都面临类似的困境,作为庞大的弱势群体的一员,德拉布尔绝不是一个头脑简单的女权主义者,而是以一名“谨慎的女权主义者”(Cooper-Clark 1986:47)的身份探索当代女性的精神世界。从她的作品中,不难体察到作者对于追求独立的现代女性面对生存困惑能否寻找到突破口的关切。
附注
①下引此作仅注页码。
②下引此作仅注页码。
Andrews,E.K.(ed.).1999.Nathaniel Hawthorne:The Scarlet Letter[M].Cambridge:Icon Books.
Colacurcio,M.J.2006.Woman’s heart,Woman’s choice:The“history”of The Scarlet Letter[J].Poe Studies(1-2):104-14.
Cooper-Clark,D.1986.Interview with Contemporary Novelists[M].New York:St.Martin’s Press.
Duyckinck,E.A.1910.Encyclopedia of American Literature[M].New York:Henry Holt.
Elbert,M.1990.Encoding the Letter“A”:Gender and Authority in Hawthorne’s Early Fiction[M].Frankfurt:Haag &Herchen.
Kristeva,J.1986.Word,dialogue and novel[A].In Toril Moi(ed.).The Kristeva Reader[C].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34-61.
MacLean,H.N.1955.Hawthorne’s SCARLET LETTER:The dark problem of this life[J].American Literature(1):12-24.
Mill,J.S.2001.On Liberty[M].Ontario:Batoche Books.Miller,J.H.2004.Fiction and Repetition:Seven English Novels[M].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Murfin,R.C.1991.Case Studies in Contemporary Criticism[M].New York:St.Martin’s Press.
Myer,V.G.1974.Margaret Drabble:Puritanism and Permissiveness[M].New York:Barnes &Noble.
Myer,V.G.1991.Margaret Drabble:A Reader’s Guide[M].London:Vision Press./New York:St.Martin’s Press.
Rose,E.C.1980.The Novels of Margaret Drabble:Equivocal Figures[M].London:Macmillan.
Sadler,L.V.1986.Margaret Drabble[M].Boston:Twayne.Smith,A.M.&E.J.Wright.2011.Hawthorne[J].American Literary Scholarship(1):31-43.
Singh,A.2007.Margaret Drabble’s Novels:The Narrative Of Identity[M].Delhi:Academic Excellence.
Spitzer,S.1985.Fantasy and femaleness in Margaret Drabble’s The Millstone[A].In E.C.Rose(ed.).Critical Essays on Margaret Drabble[C].Boston:G.K.Hall.87-105.
Whittier,G.1980.Mistresses and Madonnas in the novels of Margaret Drabble[A].In J.Todd(ed.).Gender and Literary Voice[C].New York:Holmers &Meier.197-213.
贝蒂·弗里丹.2007.第二阶段(小意译)[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伯特兰·罗素.2009.性爱与婚姻(文良文化译)[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哈夫洛克·埃利斯.2004.性心理学(陈维政、王作虹、周邦宪、袁德成、龙葵译)[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琳达·史密斯、威廉·瑞珀尔.2000.智慧之门:宗教与哲学的过去和现在(张念群译)[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刘林.2008.“海关”与《红字》的同构关系[J].外国文学研究(1):61-69.
刘巧.2012.含混——《磨砺》的解构主义解读[D].成都:四川外国语学院.
玛格丽特·德拉布尔.1997.磨砺——一个未婚母亲的自述(程遒欣、吕文镜译)[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毛凌莹.2011.《红字》中的镜子意象及其叙事意蕴[J].外国文学研究(3):81-88.
纳撒尼尔·霍桑.1996.红字(姚乃强译)[M].南京:译林出版社.
尼古拉·别尔嘉耶夫.1994.人的奴役与自由(徐黎明译)[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彭石玉.2005.霍桑小说与《圣经》原型[J].外国文学(4):64-69.
王耀辉.2012.文学文本解读[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威廉·詹姆士.2002.宗教经验之种种——人性之研究(唐钺译)[M].北京:商务印书馆.
杨跃华.2011.知识女性的愿景——玛格丽特·德拉布尔小说研究[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