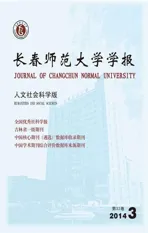忘不掉的身份:索尔·贝娄创作的“犹太性”
——以《洪堡的礼物》为例
2014-03-29黄筱莉
黄筱莉
(天津外国语大学 比较文学研究所,天津 300204)
忘不掉的身份:索尔·贝娄创作的“犹太性”
——以《洪堡的礼物》为例
黄筱莉
(天津外国语大学 比较文学研究所,天津 300204)
美国当代作家贝娄虽从不承认自己是“犹裔美国作家”,但这并不妨碍其创作的犹太性,《洪堡的礼物》颇为典型。小说深刻地揭露了犹裔美国作家的身份焦虑以及对美好“家园”的渴望。犹太人“负罪—受难—救赎”的生命历程构成了小说的内在结构,以灵魂不朽解脱死亡重负的核心观念被设定为小说的旨归。在同犹太思想的呼应中,不仅突出了犹太性,更赋予了小说感慨沉郁、荡气回肠的悲剧意蕴和深厚的历史感。
流散;身份焦虑;受难;死亡;犹太性
当代犹裔美国作家、197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尔·贝娄“在所有犹裔美国作家中,最丰富地吸收了犹太文化”[1],但他“一直拒绝承认自己是‘犹裔美国作家’”[2]。然而恰恰是这种颇为纠结的身份感赋予了贝娄作品以巨大的张力和强烈的犹太性,这在其普利策奖获奖作品、自传式长篇小说《洪堡的礼物》中体现得尤其明显。小说描写了两代美国犹太作家洪堡和西特林的悲惨遭际及他们在苦难中前赴后继追寻“故国旧土”的心路历程,揭示了特定历史时期犹太人的身份焦虑和试图建立超地域、民族的“神圣家园”的美好愿望。本文意在运用流散理论,深入分析这部犹裔美国文学经典作品所体现出来的犹太性,揭示其独特的艺术魅力。
一、流散中的身份焦虑
《洪堡的礼物》带有强烈的自传色彩,事实上小说记录的正是贝娄同诗人德尔谟·施瓦兹之间的友谊,“正如作者所公开宣称的一样,德尔谟·施瓦兹是一个原型,在他构思《洪堡的礼物》的早期,对诗人德尔莫·施瓦兹的回忆占据了他笔下主人公所有的特点。”[3]施瓦兹就是洪堡的原型,至于西特林,无论从家庭背景、获奖情况,还是生活态度等方面看,都取材于作者本人。而且,小说不时地提到两位主角的犹太身份,对身份定位与回归的隐喻随处可见,这无疑决定了小说的犹太视角,“贝娄的视角无疑是犹太式的。贝娄以一种《旧约》先知的方式写作,他本质上是个宗教中人,文学对他而言是‘走近上帝的方式’”[2]小说中,作者的观念很好地投射在了人物角色洪堡身上——他对“故国旧土”的信念、对生活的预见性,他那神经质的性格、疯癫乃至惨死的结局,就是犹太历代先知的形象缩影。
按照犹太人的思想,“走近上帝”必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流散”因而是注定的命运,“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指示你的地去。”犹太人两千多年的历史就是一部流散史。“‘流散’一词植根于‘七十士译本’——圣经最原始的希腊文译本之一。而在它最初的语境中,意指犹太人按照神意,从圣地即以色列之家分散到世界各地,在末世来临时由先知弥赛亚召集在一起。”[4]流散的终端是上帝应许的美好“家园”,“流散概念的核心是在时间和空间上都保持着一定距离的记忆中故园的形象。”[5]小说中,洪堡对“故国旧土”的执着追求正是家园情结的体现,“洪堡的主题之一就是一种永恒的人类感觉,认为有一种失去了的故国旧土。有时候,他把诗比做仁慈的埃利斯岛,在那儿一群异邦人开始改变国籍。洪堡把今天的世界看成是昔日故国旧土的一种令人激动的缺乏人性的摹仿。他把我们人类说成乘船遇难的旅客。”[6]43像先知一样,洪堡决心肩负起责任,让人们重归故园。只不过,犹太先知用的是淬火的言辞,“我就要用杖责罚他们的过犯,用鞭责罚他们的罪孽。”(《诗篇》89:32)而洪堡选择的却是基督爱的诗句,“你本来也可以认为,那些维护基督新教和‘斯文传统’的评头品足的非犹太评论家一定是不能接受他的措词造句的。……这位洪堡·弗莱谢尔却捧着爱的礼物出现了。”[6] 25洪堡指责美国当代诗人缺乏“坚定而清醒的理想化精神”,“当基督徒不用说是不可能的,当异教徒也不行。”[6] 25可是他自己又何尝当得了基督徒?
身份的转换绝非易事。犹太人在漫长的流散过程中,为了保存自身的纯洁性,严禁族外通婚,顽强地坚守着自己的种族身份,这也是犹太人虽历经两千多年多灾多难的流徙仍能生存下来的重要原因之一。种族身份是犹太人同“异族”之间最基本的区别特征,是刻在集体无意识深处的烙印。“身份问题”也正是现代流散理论的核心问题。1990年,关于“流散”,斯图亚特·霍尔写道:“我是在隐喻的而非字面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对于我们来说,流散指的不是那些分散的部落——他们的身份只有在同某些神圣土地联系在一起时才能得以实现,他们会不惜一切代价回到圣地,哪怕那意味着把其他的人都赶进大海。这是古老的、帝国主义的、霸权式的‘种族’形式,……这儿,我打算提出的流散经验不是由本质或纯洁性来定义的,而是由对一种必要的异质性和多样性的认识、在差异性生活中形成的‘身份’概念以及混杂性来定义的。”[7]洪堡显然已经超越了“古老的、帝国主义的、霸权式的‘种族’形式”,他积极投向基督教怀抱,一心要成为真正的美国人。他创作充满基督之爱的诗歌,同反犹主义教授塞威尔称兄道弟,积极参与美国大选活动,还冲破重重阻力“占有了”基督徒凯丝琳。
然而,洪堡终究是个犹太人,身份的焦虑让他极度敏感,哪怕对凯丝琳也不放心,西特林回忆到:“在乡下,他却感到犹太人的深切的恐怖。他是个东方人,而她是个基督徒,他因此感到害怕。当他躺在卡斯特罗式沙发上读普鲁斯特或者杜撰什么丑闻的时候,他预计三K党会把十字架烧在他院子里,或者隔着窗子向他射击。凯丝琳对我说,他还在别克车的车篷下搜索,看是否有人设下机关暗算他。洪堡不只一次地硬要我承认,我对黛米怀有同样恐惧的心情。”[6] 46洪堡曾得到德国柏林自由大学的邀请,却因害怕纳粹党徒的迫害而拒绝了。身份的焦虑感最终一发不可收拾,他怀疑塞威尔要把他清除出学校,怀疑妻子凯丝琳通奸,怀疑自己的“门徒”西特林背叛了自己。最终,他非但没能拯救失去了乐园的人们,自己还发了疯,被警察关进了疯人院。
洪堡身上显然有着贝娄的影子。贝娄虽然拒不接受“犹裔美国作家”的标签,却从不否认自己的犹太身份。并不顾一切地捍卫它。与此同时,贝娄对自己的“美国身份”也一直持积极认同态度,甚至超过了犹太身份。“我首先是个美国人,其次才是个犹太人,”贝娄写道,“我把自己看做是一个出身在犹太人的人——是美国人,有犹太血统——有一定的生活经验,其中一部分具有犹太特点。”[8]然而,“美国人”却一度不买“犹太人”的帐。上世纪30年代的反犹浪潮一直延续到40年代,并在大学知识分子中蔓延开来。贝娄置身其中,显然很难处理两种身份在特定时代的矛盾。“‘美籍犹太人’这一身份,是贝娄心底深处难以‘理顺’的一个最为基本的既存状况。”[9]而这个“状况”在“洪堡”这个角色身上终于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达,“在洪堡身上体现的受迫害的感觉以及由之而来的恐惧感,实际上真正地反映了20世纪40年代普遍存在于美国常春藤大学英文系中对犹太人的憎恶和歧视。”[10]小说中,洪堡曾痛斥西特林:“我想让你和我一样感到羞辱,不要把什么都兜到我的头上。你为什么不感到愤慨呢?你不是个真正的美国人。你对此反而感恩戴德。你是个外国人。你像那些刚到美国来的犹太移民,老是低三下四,卑躬屈膝。你也是经济萧条的产儿。你大约万万没有想到自己会有一个职业,还配备上办公室、办公桌和私人专用橱柜。你是受宠若惊了。你不过是这些基督徒大宅子里的犹太小耗子,而却又妄自尊大,目中无人。”[6] 168这段话无异于作家对不平等的社会现实的深切控诉。
然而,“诗人不幸,诗家幸,”身份焦虑对作者贝娄来说肯定是很难熬的事,但于他的艺术创作有莫大的益处。小说中,洪堡和西特林的犹太身份感贯穿始终,并在同美国身份的对立中形成了巨大的张力,既推动着情节的发展,又构成了扣人心弦的悬念。当然,小说中,贝娄对犹太人身份问题的探索并未止步于此,如何走出这种焦虑感才是贝娄真正要解决的问题。
二、受难中的信仰启示
“受难”是犹太人在通达应许之地的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仪式。在犹太人的思想中,人因其自由意志,离开了上帝之道,犯了原罪,必须受罚。“你们的儿女必须在旷野漂流四十年,但当你们淫行罪,直到你们的尸首在旷野消灭。”“罪人”只有历经苦难才能坚定信仰,获得终极救赎。“负罪—受难—救赎”就是犹太人的典型的生命历程,而“受难”则是必经的环节。《洪堡的礼物》中,西特林的一生就是对犹太人受难观最好的诠释。
小说以西特林对洪堡的回忆开始,核心主题则是洪堡之死。洪堡最终穷愁潦倒,流落街头。而此时西特林则凭着以洪堡为原型创作出来的剧本《冯·特伦克》一鸣惊人,成了举世闻名的作家,戴高乐封他为“荣誉军团”骑士,肯尼迪总统邀请他去白宫做客,达官贵人争相延请他为座上宾。与此同时,西特林也获得了百万家财,可谓名利双收。飞黄腾达的西特林完全离弃了落魄的恩师洪堡。他曾在街头偶见一名不文的洪堡,然而非但没有救对方于水火之中,反而囿于世俗的虚荣,躲在汽车后面连面都不见。两个月后,洪堡惨死下等公寓。西特林为此内疚不已,“我还是应该走过去跟他谈谈。我本该和他靠近些,而不应该躲在汽车后面。”[6] 80这种负罪感成了回忆的主旋律,而作为叙述者的西特林则通过不断的回忆把自己钉在了十字架上,成了忏悔的罪人。西特林背叛了自己的“导师”,一如犹太人背离了上帝,等待他的只能是受难。
同洪堡一样,西特林也是犹太移民。只是作为故事的叙述者兼主人公,西特林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犹太意识。但与贝娄笔下的其他主人公一样,即使他自己并没有完全意识到,而“犹太性”已融入到他的行为举止和性格中,并在他的回忆中展现出来。西特林的情人黛米是虔诚的基督徒,总是半夜被噩梦惊醒,因害怕下地狱而呜咽哭泣,而西特林都会安慰她“世界上只有天堂,没有地狱”,这正体现了西特林的犹太教的宗教观——地狱主要是基督教的观念,犹太人对地狱从来都缺少明晰的意识。事实上,西特林的犹太身份已经成了他和妻子丹妮丝之间不可逾越的障碍。丹妮丝是典型的美国贵妇人,热衷于同社会名流交往。她高傲,自以为是,尽管靠西特林挣钱才过上了奢侈的生活,却总是一副居高临下的姿态,尤其瞧不起犹太人。西特林曾自嘲地对朋友乔治说:“她还以为她赐给我美国婚姻的福祉呢。……像我这样一个移民的孩子就该知足了;对一个犹太人来说,更可以说是一步登天了。”[6] 66对于西特林的犹太人朋友,丹妮丝更是动辄破口大骂:“你周围全是些狗屁不通的犹太佬,都是流氓无赖。”[6] 67丹妮丝对西特林形成了巨大的精神压力。如果说西特林同丹妮丝结婚象征着他试图融入美国上层社会的努力的话,那么两人之间从头到尾无休无止的争斗则象征了两种身份之间难以调和的对立冲突。
面对内心的矛盾冲突,洪堡试图以诗和艺术来拯救堕落的美国文明,而西特林却选择了独自寻找家园之路。如日中天的西特林于是带着妻子儿女离开了繁华的大都市纽约,退隐到破败落后的芝加哥,开始了受难之途。对此,丹妮丝责骂说:“你一不去伦敦,二不去巴黎,三不去纽约,却非要来到这里——这个倒霉的、丑恶的、下贱的、危险的地方不可。因为归根结底你毕竟是从贫民窟出来的穷小子,你的心仍在老西区的臭水沟里。”[6] 64丹妮丝进而一针见血地指出西特林有“低级的怀乡病”,“有时我这样想,是不是因为你的祖先埋在那里?那里的黄土下埋着我的犹太父老?”[6] 67这些话尽管充满着对犹太人的鄙夷侮辱,但西特林也不得不承认“有不少道破了事情的真相”。只不过丹妮丝口中的“贫民窟”、“臭水沟”于西特林而言正是久违了的“故园”,其初恋情人卢茨就是鲜活的象征。西特林一生中经历了很多女人,但只有跟卢茨在一起才能感受到真正的快乐,“当我爱着内奥米·卢茨的时候,我感到坦然,快乐,生活充实而有意义,就是死了也心甘情愿。”[6] 107西特林来到芝加哥就去寻访初恋之地,查看卢茨住过的茅屋,小说中的回忆更是一次次回到真诚、朴实的卢茨,所有这些都反映了他对故园执着的追寻。高傲的丹妮丝不可能理解他这种犹太情怀,最终离他而去。回归的道路充满着苦难,丹妮丝就是最大的考验,作为妻子,她给西特林造成了巨大的精神压力;离婚后,她把西特林告上法庭,纠缠不放,不仅让他精神上受尽了折磨,还剥夺了他全部的财产。
然而,西特林的受难远不止于此。地痞流氓坎特拜尔像个真正的撒旦一样缠上了他。就因为牌桌上欠了几百元钱,坎特拜尔就把西特林的梅赛迪斯高级轿车砸得稀巴烂,还侮辱、折磨了他一整天。到了晚上,又把他带上了建筑工地五六十楼层高的脚手架,把他的魂都吓掉了。可是,虽说已经“赎了整整一天的罪”,西特林的苦难到此仍不是尽头——他视为终生伴侣、最后依靠的情人莱娜达也抛弃了他。至此,西特林真正是一无所有了,他只能寄宿在西班牙一个下等的膳宿公寓里,一身黑色丧服,满面愁容,心怀怨愤,就像遭重重灾难打击后的约伯。苦难中的约伯不断地向上帝倾诉,悲痛的西特林则把自己完全交给了洪堡的魂灵,“我真想知道我为什么对死者如此忠诚不渝。听到他们的死讯,我常常对自己说,我必须继承他们的未竟之业,做他们的工作,完成他们的任务。当然,我是没有能力这样做的,但是,我却发现他们的某种特性逐渐依附到了我的身上。”[6] 145西特林开始同洪堡合体,意味着他将回归由先知指引的道路。
西特林通过洪堡重新确立了信仰,回归犹太身份。当此之时,宽恕与救赎如期而至。正是因为出于对洪堡的坚定信念,西特林才不顾莱娜达的激烈反对,坚持要远赴荒僻的科尼岛,看望疗养院中洪堡那孤苦无依的老叔叔,而正是在科尼岛之行后西特林才收到了“洪堡的礼物”——洪堡遗留下来的一卷文稿。洪堡的礼物中有封写给西特林的信,信中洪堡宽恕了西特林。除此之外,礼物还包括两个剧本纲要,一个是两人合作的,另一个是洪堡的独创。就在西特林落难膳宿公寓、山穷水尽之际,两人合作的剧本纲要被好莱坞采用,拍成了电影,热映一时。而洪堡像所有犹太先知一样,具有准确的预见性,早就保存好了关于纲要所有权的证据。西特林从这部电影以及洪堡留下的其他材料中获得了大量财富,一如约伯重新恢复了他的财产。
西特林的“负罪—受难—救赎”构成了小说的内在结构,不仅浓缩了西特林的心路历程,也深刻地揭示了犹太人宿命式的信仰回归之路。这种看不见的内在结构也赋予了小说感慨沉郁、荡气回肠的悲剧意蕴。
三、死亡中的灵魂皈依
在西特林信仰回归的过程中,始终伴随着对“死亡”这个“问题中的问题”的思考。死亡本身在犹太文化中极富象征意义。犹太人的始祖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死了,“亚伯拉罕为她哀恸哭号。后来亚伯拉罕从死人面前起来,对赫人说:‘我在你们中间是外人,是寄居的。求你们在这里给我一块地,我好埋葬我的死人,使她不在我眼前。’”赫人卖了块田地给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就把撒拉埋在田地中的麦拉比洞里。麦拉比洞也成了犹太人的祖墓。后来,“亚伯拉罕寿高年迈,气绝而死,归到他列祖那里。他两个儿子以撒,以实玛利把他埋葬在麦比拉洞里。”这之后,早期那些伟大的族长们死了都要“归到他列祖那里”。当年亚伯拉罕带着族人离开“迦勒底的吾珥”,北上哈兰,再南下迦南,后又去了埃及,在大地上四处流散,对“应许之地”实无明晰的概念,直到撒拉死了,亚伯拉罕从迦南赫族人那买了麦拉比地。这是亚伯拉罕和他的族人在大地上明确拥有的第一块土地,尽管面积小得可怜,但终究可以自由支配,可以“埋葬我的死人”,这种确定性正是家园感的基础。“称一个地方为家是一种权力的叙述。说某地是家园,犹太人表达的意思是定居、控制和熟识。家园是这样一种地方,那儿人们可以实现自己的身份,建立亲密的关系,那儿他们可以宣称谁属于或不属于某个团体。”[4]麦拉比成了犹太人最早的家园,也是后来一切家园的原型,从此“应许之地”才算有了真正的所在。然而,这最早的家园却是埋葬死人的墓地。家园本该是“生”的所在,现在只能由“死”来定位,由坟墓做了标识。死亡观由是成了犹太人的家园观念中不可分割的部分。由此,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什么《洪堡的礼物》中,一心追寻“故国旧土”的洪堡、特别是西特林总也摆脱不了死亡问题的困扰。
洪堡之死成了西特林人生的重要转折点。“洪堡之死对我来说意味深远。”西特林追忆道,“我花了过多的实践对死者沉思,跟死者谈心。我和他的名字原是联系在一起的。”[6] 23事实上,正是《时报》讣告栏上洪堡那消沉颓唐、满面黑灰的遗容,以及“他从死亡领地上”投来的阴森可怖的目光,警醒了正如日中天以至于忘乎所以的西特林,使他得以回归自己的本性,开始人生的反省。死亡一如死后的洪堡,时刻困扰着西特林。一方面,他对死亡显然充满着恐惧,“死亡将是多么令人厌烦啊!躺在墓穴里,躺在一个地方,那是多么可怕呀!”[6] 262正因此,洪堡之死带给他的第一反应是锻炼身体,并为成功逃脱了一次暴徒的袭击而沾沾自喜;另一方面,他又似乎只有同初恋情人内奥米在一起才能真正克服对死亡的恐惧,“我情不自禁地想到,如果我同内奥米生活在一起,那该是多么幸福啊!如果我搂着内奥米度过一万五千个夜晚,那么,即使面临坟墓的凄清和烦恼,我也会一笑了之。”[6] 108这句话以不同的方式在小说中不断地重复,象征着犹太思想的呼唤。与此同时,莱娜达无视死后世界、及时行乐的思想也对西特林产生极大的诱惑,“我倒认为当我生机勃勃地走在莱娜达后面时,我才改变了我对死亡的态度。我已经开始准备考虑其他可供选择的对象。”[6] 415西特林纠结于不同的死亡观,从灵魂到肉体都不得安宁,直到收到“洪堡的礼物”。
洪堡的礼物让西特林意识到“正是对死的无知在毁灭着我们”[6] 443,而关于死亡的最重要的知识就是灵魂不朽。犹太圣典《旧约全书》则成了西特林知识的源泉,“《旧约全书》要我们不要同死者打交道。教义说,这是因为,在死后的最初阶段,灵魂进入了一种感情的炽烈状态,进入了某种类似血与神经的状态,低级的冲动就会因这种最初阶段跟死者的联系激发起来。”但经书并不反对“沟通”,“经典上说,跟一个已经死去的人求得实际上的沟通,虽为不易,但还是有可能的,只不过需要训练、机警和一种敏锐的意识。也许最低级的冲动会突然爆发,同你纠缠一番,那就必须用一种纯净的意念去约束情欲。”[6]550循着犹太教义,一无所有的西特林在西班牙一个破落的膳食公寓里坚持探索着灵魂的秘密,他在那一呆就是两个月,思想“变得更坚定了”。
在西特林“坚定思想”的过程中,始终面临着选择的考验。西特林本已计划好同莱娜达去意大利旅行,就在出发前他收到唯一的哥哥将要做心脏手术、面临死亡危险的消息。他于是决定先去探望哥哥,但遭到莱娜达的坚决反对。后者历数西特林哥哥的斑斑劣迹和对西特林的无情无义,试图说服西特林。西特林虽深知莱娜达所说有理,但还是选择先去看望面临死亡危险的哥哥。“一旦他们在那里——无可辩驳——就拿他们没有办法。他们的现实比我的实惠更重要。超越了生动的某一点,我就变得热情地依恋。”[6] 449亲人最终战胜了情人,体现了犹太文化强大的凝聚力。莱娜达独自去了意大利,并同敛尸人佛朗萨里结了婚。西特林没有陪莱娜达去意大利,抵制住了美国文化最后的诱惑,实现了完全的回归。失去莱娜达的西特林更加积极地沉浸于对死亡的探索,最终把自己提升为“一个未来的先知”。洪堡曾指责他汲汲于俗世的浮华,如今在参透了死亡的秘密后,财富、荣誉等再也不能让他动心,真正实现了在世的超脱,同时也变得无比强大——暴徒坎特拜尔从此再也不能伤害他。
小说的结尾,西特林同洪堡唯一的舅舅沃尔德玛、曾经的老房客孟纳沙一起,为洪堡和他的母亲举行了一个“完满而得体”的葬礼。葬礼过程中,孟纳沙唱了“一首古老的美国黑人的圣歌‘回家’”:“回家,回家,我要回家。”[6] 605对于长期流浪的犹太人来说,死亡并不可怕,重要的是灵魂能“回家”。正因此,犹太人死了总要想尽一切办法“回到列祖列宗那里”。亚伯拉罕之后的第四代族长约瑟尽管在埃及享尽了荣耀,但临死前还是要子孙后代起誓,一定要把他的骸骨带回迦南同列祖合葬,“约瑟对他弟兄们说:‘我要死了,但神必定看顾你们,领你们从这地上去,到他起誓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地。’约瑟叫以色列的子孙起誓说:‘神必定看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搬上去。’”四百年后,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时没忘他们的誓言,“摩西把约瑟的骸骨一同带去。”西特林迁葬洪堡,一如摩西迁葬约瑟——都内在于伟大的犹太文化传统。而这种呼应无疑也赋予了小说以厚重的历史感。
[1][美]欧文·豪.父辈的世界[M].王海良,赵立行,译.上海:三联书店,1995:83.
[2]Goldman, L.H. Saul Bellow and the philosophy of Judaism[J].Studies in the Literary Imagination, 1984,17(2):87, 95.
[3]Zipperstein, Steven J. Isaac Rosenfeld. Saul Bellow, Friendship and Fate[J].New England Review, 2009,30(1):10-20.
[4]Shneer, David and Aviv, Caryn. Jews as rooted cosmopolitans: the end of diaspora Diasporas: Concepts, intersections, identities, Kim Knott and Sean Mcloughlin, ed.[M].London: Zed Books Ltd., 2010:263.
[5] Stock, Femke. Home and memory, Diasporas: Concepts, intersections, identities, Kim Knott and Sean Mcloughlin, ed.[M].London: Zed Books Ltd., 2010:24.
[6][美]索尔·贝娄.洪堡的礼物[M]∥索尔·贝娄全集:第6卷.蒲隆,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7]Hall, Stuart. Cultural Identity and Diaspora, in Identity: Community, Culture, Difference, ed. Jonathan Rutherford[M].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1990:235.
[8]Miller, Ruth. Saul Bellow: A Biography of the Imagination[M].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1:163.
[9]武跃速.无处置放的乡愁——论索尔贝娄的《耶路撒冷去来》[J].外国文学评论,2012(4).
[10]Atlas, James and Schwartz, DelmoreThe life of American Poet[M].New York: Farrar, Straus Giroux, 1977:162.
Unforgotten Identity: Jewishness in Saul Bellow’s Creation ——Illustrated byHumboldt’sGift
HUANG Xiao-li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stitution of Tianjin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Tianjin, 300204, China)
Though Saul Bellow’, a famous contemporary American author never declares admits himself as a “Jewish American author”, his creation is full of jewishness, especially in theHumboldt’sGift, which revealed profoundly the identity anxiety and yearning for a homeland of the Jewish American writer. The inner structure of the novel is the life course of Jew, that is “Guilty—Suffering——Redemption”; and the axis of the novel is the core notion of the inmortality and liberation from the burden of death. In the retrospect of Jewish, it is not only extruded the Jewish, but also enriched novel of gloomy tragic connotation and deep-seated sense of history.
Diaspora; indentity anxiety; suffering; death; jewishness
2013-11-29
天津市社科规划课题(TJWW13-011)。
黄筱莉(1990- ),女,湖北宜昌人,天津外国语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硕士研究生,从事美国文学研究。
I712.074
A
2095-7602(2014)03-0106-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