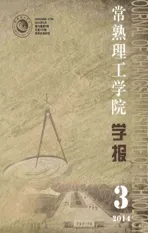刘毓盘与民国词坛
2014-03-29李剑亮
李剑亮
(浙江工业大学 人文学院,杭州 310023)
1933年12月出版的《词学季刊》第一卷第三号,刊登了查猛济的《刘子庚先生的词学》一文。文章第一段写道:“公元一九二八年的夏天,北大词学教授刘子庚先生暴死在北平西四牌楼胡同内的一所破陋不堪的屋子里面,不但中国的词坛上,顿时失去了一位忠实的导师,就是一切山水、星辰、森林、花草,也该都变了颜色,悼惜他们管领的主人。最可纪念的:北大中国文学系里‘词史’这门功课从此再没有人敢继续他讲下去。这一点,也可证明近代词学的消沉和先生在词坛上的地位了。”[1]43这里所说的中国词坛,指的是民国词坛。那么,这位刘子庚先生在民国词坛上到底拥有怎样的地位呢?
刘子庚(1867-1928),名毓盘,字子庚,号噙椒,浙江江山人。生活在晚清民初的刘毓盘,既是一位大学教授,又是一位词人。1919年9月,刘毓盘至北京,任北京大学教授,所教课程便是词学、词史等,又撰写了《词史》一书。同时,他又创作了不少诗词作品,流传至今的有词集《噙椒词》[2]等。
一、刘毓盘的词创作
考察刘毓盘写词的经历,可从其学词说起。刘毓盘对自己的学词经历,曾有过这样的叙述:
九岁学诗,先人授以作诗法。十二,请学词。先人曰:“小词学唐,慢词学宋,朱竹垞之言也。浙派主协律,常州派主立意,沟而通之,斯得矣”。[3]
在这段自序中,刘毓盘不仅介绍了自己学词的过程,更重要的是交代了学词的路径,即兼学唐宋,沟通协律与立意。所谓兼顾,即既重视音律,又注重意境。不过,相对而言,刘毓盘对音律似乎更关注。这既体现在他对自己作品的评价上,他曾对人说:“凡载在这册集子里的词,没有一首不能按之管弦的”[1]43;也表现在他对清人戈载论词观点的推崇:“戈氏精音律,于白石旁谱多所发明,以正万氏之失,其《词林正韵》,亦足以正仲恒、吴烺之失也。”[4]206
当然,无论是重视音律,还是强调意境,这首先是刘毓盘创作上的一种追求,而不表示他的作品都已达到这样的境界。正如李清照在《词论》中所标榜的论词标准,并不都在其作品中能体现一样。不过,刘毓盘词对音律与意境的追求,还是达到了较高的水准。尤其在作词造句上,力求自创,如“花约夕阳迟,一齐红几时”(《菩萨蛮》)[2]、“月不负人人负月,先放下水精帘”(《唐多令》)[2]、“蝴蝶赶春忙,飞来总一双”(《菩萨蛮》)[2]等。这些词句,将汉语的古今特点融为一体,通俗而又不乏内涵,有唐五代小令之神韵,却没有简单袭用前人词句。
刘毓盘词的这种自创性,与他自身的经历有关。他少遭家难,屡踬文场,而又“行年四十,三遣悲怀”(《哨遍》小引)[2],因此其作品融入了他的身世之感,哀婉动人。如《鬲溪梅令》云:“春棠开作断肠花,会心差。况是阴阴梦雨湿窗纱,风枝摇倦鸦。 翠帏朱幄又谁家,早凉些。未必新人还比旧人佳,所思天一涯。”[2]“未必新人还比旧人佳,所思天一涯”两句,其“新人”、“旧人”的比较写法,虽唐代诗人如杜甫等已有表现,但其抒情的角度还是有相当的创新性的。
又如《浣溪沙》云:“旧恨空中记不全,一窗花落又今年,玉珰缄札诉缠绵。 未必有情成眷属,明知无路访神仙,芳尘如梦梦如烟。”[2]与上首词相同,这首词也表现了一段已经失去却又难以忘怀的情感遭遇。特别是下阕三句,更是表现了词人对那段感情难以自拔的心境。有学者认为这些作品是悼亡之作[5],结合刘毓盘的生活经历来看,这样的结论亦可信。
刘毓盘的词集有《濯绛宦词》,木刻一册,无刻印年月。扉页有己酉(1909)六月吴俊卿篆书《濯绛宦词》四字。据此可知,此集最早当刻于1909年。正文第一行题《濯绛宦存稿》,第二行低一格题《噙椒词》。卷首有光绪辛丑(1901)彭世襄序,又有作者自记云:“五季北宋,津逮风骚。二窗中仙,开闢门户。华年选梦,锦字缄愁。律据音先,意写言外。美人香草,无憀极矣。”其下不署年月。这个集子共有两种版本,初版收词68阕,补刻本增11阕,共79阕。前者刻于吴中,后者则是晚年的手定本。林辰先生在《刘毓盘和他的〈濯绛宦词〉》一文中说:“这两种本子我都有,初刻本钤有‘子韶’方印,系南社词人陈虑尊旧藏;补刻本有‘贵旧赵氏寿华轩藏’长方印,系乡人赵氏旧藏”。[5]
据《鲁迅日记》1925年3月20日记载:“午后往北大讲;刘子庚赠自刻之《濯绛宦词》一本。”[6]538可见,刘毓盘的词集也曾在自己的同事中流传。
二、刘毓盘的词学教学
1919年秋天,刘毓盘到北京大学任教,讲授的课程有词史、词家专集、中国诗文名著选等。据周作人《知堂回想录》记载,在一本1922年北大中国文学系课程指导书里列着:“词史,二小时,刘毓盘。戏曲史,二小时,吴梅。小说史,二小时,周树人。”[7]541可见,在北大时,刘毓盘与鲁迅、吴梅为同事。周作人所记的这些课程,与刘毓盘的学生钱南扬的回忆相一致:“(北大)四年正科是选科制,我先后选了刘子庚(毓盘)先生的词选、词史,许守白(之衡)先生的曲选、曲史,鲁迅(周树人)先生的小说史。”[8]12
刘毓盘在大学中开设词史等课程,开展词学教学,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民国大学教育与民国词坛的一种新气象。中华民国成立后,传统的书院制度被现代教育制度所取代,那种以经学为学问主轴的思想有了变化,原本不登大雅之堂的辞章之学,如诗、文、词、小说、戏曲,作为一种学科门类渐渐地进入大学讲坛。这也使得民国词坛出现了更加多元的格局,一部分大学教授既开设词学课程,又从事词创作。
有关刘毓盘词学教学的情景,其学生徐铸成有如下回忆:“教词曲学的刘毓盘先生,那时年已近古稀,但教授也非常认真,他对这一门造诣之深,大家认为是超迈前人的。”[9]86另一位学生陆宗达也回忆说:“北大的课分三个专业,文学专业、语言专业和文献学专业,我选的课是以语言专业为主……同时也选一部分文学课,印象最深的有两门,一是刘毓盘先生的词学,分词律、词选和专家词三部分,还要求选课的人每两周交一篇自填的词,刘先生对我的词很赏识,1927年,我去了东北,听说刘先生还问起我。”[10]可见,刘毓盘在大学课堂上,不仅讲授词学理论、词的发展史,还指导学生填词,体现了理论与实践并重的教学理念。
三、撰写《词史》
刘毓盘的《词史》一书,便是他在北京大学讲授“词史”的讲义。该讲义起先在《东北大学周刊》连载,然后经其弟子查猛济、曹聚仁整理,由上海群众图书公司1931年出版。该书前有作者“壬戌(1922)仲秋”自序,可知该书完稿时间当在1922年;后有曹聚仁民国十九年《跋》,介绍该书的出版过程。
《词史》凡十一章,依次为第一章“论词之初起由诗与乐府之分”,第二章“论隋唐人词以温庭筠为宗”,第三章“论五代人词以西蜀南唐为盛”,第四章“论慢词兴于北宋”,第五章“论南宋词人之多”,第六章“论宋七大家词”,第七章“论辽金人词以汉人为多”,第八章“论元人词至张翥而衰”,第九章“论明人词之不振”,第十章“论清人词至嘉道而复盛”,第十一章“结论”。
此书名曰《词史》,自然要对中国词史进行梳理与描述。如何来梳理与描述中国词史,这首先取决于作者对词这一文学样式的认识。
《词史·自序》曰:“《说文》:词,意内言外也。明乎我所欲言,必有司我言者,而后可以尽我之词,故隶司部。意者,司我言者也,故曰内。意与志不同,故词与诗不同。诗,志也。《说文》从言,寺声。古文从言,之声。心之所之为志。善于诗者由衷而出,一意孤行,随其心之所之,以求合于六义之府。其至者,可以感天地,通神明,惊风雨,泣鬼神,以成一家之言。……词则源出于诗,而以意为经,以言为饰。意内言外,交相为用。意为无定之意,言亦为无定之言。且也意不必一定,言不必由衷。美人香草,十九寓言。其旨隐,其辞微。言之不足故长言之,长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后人作词之法,即古人言乐之法也。盖忠臣义士,有郁于胸而不能宣者,则托为旁人思妇之言。隐喻以抒其情,繁称以晦其旨。进不与诗合,退不与典合。其取径也狭,其陈义也高,其至者则东西南北,惝恍无凭。虽博考其生平,亦莫测其真意之所在。而又拘以格律,谐以阴阳,毫厘杪忽之微。不得自我而作古,必有司我言者,不能随我心之所之也。故与诗相成而适相反。”[4]2
若将刘毓盘此序与清代张惠言的《词选序》作一比较的话,不难发现,两者之间有不少的相似之处。刘毓盘认为,词“源出于诗”;张惠言则认为“词者,盖出于唐之诗人,采乐府之音,以制新律,因系其词,故曰词。《传》曰:‘意内而言外,谓之词。’”[11]1
当然,两者也都认为,词在随后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不同于诗歌的一些特点,这不同之处,在张惠言看来,词“莫不恻隐盱愉,感物而发,触类条畅,各有所归,非苟为雕琢曼辞而已。”[11]1在刘毓盘看来,词“其取径也狭,其陈义也高”。可见,刘毓盘对词体的认识,受清代常州词派的影响是比较明显的。
正因为如此,刘毓盘在对一些词人的评价上,也与张惠言的观点相近。如对于温庭筠的评价,张惠言指出:“自唐之词人,李白为首,其后韦应物、王建、韩翃、白居易、刘禹锡、皇甫松、司空图、韩偓,并有述造,而温庭筠最高,其言深美闳约。”[11]1而刘毓盘在《词史》中,也充分肯定了温庭筠在唐代词史上的地位,该书第二章,专立标题为“论隋唐人词以温庭筠为宗”。在刘毓盘看来,温庭筠在隋唐词人中具有相当高的地位。刘毓盘推崇温庭筠,大致基于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认为温庭筠词具有意内言外的特点。在分析温庭筠的《菩萨蛮》(南园满地堆轻絮)时,刘毓盘指出:“张惠言茗柯《词选》曰:温氏《菩萨蛮》,皆感士不遇之作,细味之良然。”[4]当然,张惠言此论,实际上也有南宋张炎词论的影子。对此,刘毓盘也引《词源》之语曰:“《词源》尝谓词之难于令曲,如诗之难于绝句。不过十数句,一字一句闲不得。末句最当留意,有有余不尽之意始佳。”[4]在引了《词源》此语后,刘毓盘与张炎一样,也以温庭筠为例证,曰:“温氏其首出也。”[4]张炎的表述为:“当以唐《花间集》中韦庄、温飞卿为则。”[12]34
当然,刘毓盘对温庭筠在词史上的地位的考察,也有超越张惠言视野的地方,那就是,更多的是从词律角度,而不仅仅是从词意角度,来评价温庭筠的词史地位。这也是刘毓盘推崇温庭筠的另一个原因。刘毓盘称“隋唐人词以温庭筠为宗”,在一定意义上,正是从词律这个角度来立论的。他在这一章中指出:“其所创各体,如《南歌子》、《荷叶杯》、《蕃女怨》、《遐方怨》、《诉衷情》、《定西蕃》、《酒泉子》、《玉蝴蝶》、《女冠子》、《归自谣》、《河渎神》等,虽自五七言诗句法出。而渐与五七言诗句法离。所谓解其声,故能制其调也。宜后人奉以为法矣。”[4]认为后人奉温庭筠为法的原因,就在于他具有“解其声”、“制其调”的才能。为此,刘毓盘还引《词苑》之言来说明后人是如何奉之以为法的。其曰:“右司空图《酒泉子》词。按《词苑》,此调始于温庭筠。有四十字、四十一字二体。司空图始改作四十五字体。毛文锡仿之,首句曰‘绿树春深’。‘春’字改平声。宋人遂通用此体矣。”[4]
可见,刘毓盘对温词的推崇,是从温词的词意和词律两个层面来确立的。这也传达了刘毓盘对词史的一个基本态度,那就是词意与词律并重。
刘毓盘之前,词坛上交织的是常州词派与浙西词派两种词学观。常州派主立意,浙西派主协律。与此相对应的是,常州派推崇唐五代和北宋词,浙西派则看重南宋词。对此,刘毓盘在第四章开头有这样的论述:“言词者必曰词至北宋而大,至南宋而深,固也。常州派言词则耑主北宋,以为北宋之词与诗合,南宋之词与诗分;北宋犹争气骨,南宋则专精声律,是南宋词虽益工,以风尚而论,则有黍离降而诗亡之叹矣。不知南宋词即出于北宋,特时代之有先后耳。北宋国势较强,政府诸公,以及在野之士,方以雍容揄扬,润色鸿业为乐事,其上者见朝政之弊,则借词以格君心之非。若夫先之厄于辽,后之厄于金,我能为献纳一字之争,已可告无罪于天下。初无人作深虑之论也。南宋局守一隅,议和议战,叫嚣不已。自命爱国者,方挟君父之仇不共戴天之说,以博舆论之归,又知兵力之不足以胜人也,则口诛之,笔伐之,不遗余力,虽权奸亦未知之何。文网愈严,则词意愈晦。蚕室之僇,不能加诸其身。盖解人固不易索焉。故曰北宋之词大,南宋之词深。时为之,亦势为之尔。”[4]
文中,刘毓盘陈述了前人对两宋词的不同认识。简言之,北宋词大,南宋词深;北宋词与诗合,南宋词与诗分;北宋词重气骨,南宋词精声律。在对这些差异的原因进行分析后,刘毓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即“南宋词即出于北宋,特时代之有先后耳”。这种南北融合的词史观,相比于此前或只重北宋、或只重南宋的词学取向,显得更为客观。
对于刘毓盘《词史》在词学研究史上的地位,学者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予以肯定。杨世骧从词史撰写史的角度作出评价,其曰:“词的产生虽有一千年的历史,而向无一部系统地评述的专著,有之,则以他的这部《词史》为嚆矢,其价值殆无异王国维《宋元戏曲史》在曲一方面的地位。”[13]
王易《词曲史》在评述晚近词学著述时,将刘毓盘的《词史》与朱彊村的《宋词三百首》、陶湘的《影宋金元人词》等并称,曰:“晚近词学著述,除前述外,选集尚有彊村翁之《宋词三百首》,去取特严,或病其偏取涩体,然其用意原以针流滑粗犷之病,不违雅正之音。汇集则又武进陶湘《影宋金元人词》,参入《吴氏双照楼刻》,皆精本……评论考证之作,则又刘毓盘之《词史》,辨析源委,约而能赅。”[14]321王易将刘毓盘《词史》认定为“评论考证之作”,并称其“辨析源委,约而能赅”,肯定了其在词史文献考证上的成就。
陈水云也认为:“《词史》的意义不仅仅因为它第一次系统地勾勒出千年词史的发展变化,而且还因为它从考镜源流、辨章学术的立场对中国词史进行综合的考察。它不同于传统词话和词选,或用作初学者的创作指南,或为宣扬编者的审美观念,它的目标重在培养学生的审美感悟力和理论思辨力,是‘使学者知各代文学变迁及派别’。因而他也就从晚清常州派词学观念里超越出来,而主张兼融浙西、常州两派的思想,并初步注意到对词史发展变化规律的揭示。”[15]187
可见,刘毓盘的《词史》,无论是在词史的撰写史方面,还是在词作评论、以及考镜源流、辨章学术方面,均具有重要的意义。
四、词籍辑佚
刘毓盘在民国时期另一项重要的词学活动,就是辑录《唐五代宋辽金元名家词集六十种辑》。全书收唐词二种三家,五代词四种五家,宋词四十四种六十四家,辽金词四种十家,元词五种五家,高丽词一种一家,共计六十种九十家,多为辑本。“每一种成,则仿《提要》法,或论其人,或旁证其间,新知旧说,唯意欲言。词太少,则以类相从者附焉”(《自序》)[3]。
刘毓盘辑录词籍的工作,一定程度上是受其父亲刘履芬的影响,同时也与晚清民初词坛词籍校勘风气有关。刘履芬曾为宋翔凤刊刻《乐府余论》,为孙麟趾刊刻《词迳》。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对刘履芬喜好收藏古籍的情景,有这样的描述:“刘泖生刺史,性嗜书,遇善本必倾囊购之,其不能者,手自抄录,日课书十纸,终日伏案矻矻,未尝见其释卷以自嬉。”[16]
晚清民初词坛,词籍校勘风气颇盛。影响深远者有朱孝臧的《彊村丛书》、王国维的《唐五代二十一家词辑》等,朱、王的词籍辑录与校勘成果,自然会对刘毓盘产生积极的影响。而且,相对于朱、王两家而言,刘毓盘还有开拓之处。举例来说,刘毓盘对金、元、高丽词的辑录(辽金词四种十家、元词五种五家、高丽词一种一家),便是朱、王等前人未涉及的领域。因此,朱彊村在《致夏承焘书》中盛赞此书:“子庚先生辑本,诚有功词苑。”[17]不过,这部辑本也存在较多的问题。赵万里在《校辑宋金元人词》中曾指出:“其弊不仅在所见材料之少,而在真伪不分,校勘不精,出处不明,使人读之如坠五里雾中。”[18]172
除了《唐五代宋辽金元名家词集六十种辑》外,还有一册《词家专集》也被林辰先生收藏。据林辰先生叙述,《词家专集》内收《李太白词》、《温飞卿词》、《南唐二主词》、《三衢人词》、《小山词钞》、《宝月集》、《大声集》、《顺庵乐府》、《东山乐府》、《涵虚子词》等,自唐至元,凡十种。每种词集后都有刘氏所作校记和跋文。刘毓盘在目录后的识语曰:“凡词十种,共十四家,太白词、飞卿词已见《全唐诗》,二主词、小山词已见汇刻本,惜其未全。其余各家佚之久矣,故从各本辑出,字句之别,各附校记一通,原有集名者从之。续有所得,当补录焉。甲子暮春,江山刘毓盘识。”[5]14林辰先生因此推断:“这一校辑工作,是在癸亥(1923)、甲子(1924)年间进行的。我因没有见过《唐五代宋辽金元词辑》,所以不知道这十种是否即是该书的一部分。这一册《词家专集》,线装铅印,大概也是北大的讲义。”[5]14
五、结 语
综合上述内容,不难发现,刘毓盘在民国词坛上所从事的词学活动是比较全面的,取得的成就也是明显的。尤其是《词史》一书,更让我们看到了他对此前词坛上各种词学观的调和与融合。
晚清民初词坛,是一个传统与现代的交汇期。此时,既有传统词学思想的延续,这种思想主要以晚清四家及民初词学家为主,他们推崇唐代北宋之作,强调比兴寄托的观念;同时又有近代词学观念的形成,如王国维提出“一代有一代之文学”[19]1,把词作为有宋一代的文学,且推崇五代北宋。其后,胡适等学者则表现出轻宋词尤其是南宋词的倾向。
身处这样一个新旧交汇的词坛,刘毓盘论词则力求折中于新旧之间,即以守律与意境(情性)合而论之。对此,查猛济有这样的分析:“近代词学,大概可以分做两派,一派主张侧重音律方面的,像朱古微、况夔笙诸先生是;一派主张侧重意境方面的,像王静安、胡适之诸先生是。只有《词史》的作者刘先生,能兼顾这两方面的长处。”[1]46查猛济为刘毓盘的学生,故文中对刘毓盘的评价难免带有个人情感色彩。但总体来说,还是比较客观地揭示了刘毓盘在民国词坛的作用与地位,即以意境与词律并重的原则来论词。虽然,持此原则的并不只有刘毓盘一人,但通过《词史》这样的著作来阐释这一原则的,则只有刘毓盘。
[1]查猛济.刘子庚先生的词学[J].词学季刊,1933,1(3):43-48.
[2]刘毓盘.噙椒词[O].清宣统二年(1910)刻本.
[3]刘毓盘.唐五代宋辽金元名家词集六十种辑·自序[M].排印本.北京:北京大学,1925.
[4]刘毓盘.词史[M].影印本.上海:上海书店,1985.
[5]林辰.刘毓盘和他的《濯绛宦词》[J].鲁迅研究动态,1987(8):12-14.
[6]鲁迅.鲁迅全集第十四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7]周作人.知堂回想录[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8]钱南扬.回忆吴梅先生[M]//赵景深.戏曲论丛:第1辑.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6.
[9]徐铸成.旧闻杂忆[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
[10]陆宗达.我的学、教和研究工作生涯[M]//陆宗达语言学论文集.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664-672.
[11]张惠言.词选[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
[12]张炎.词源[M]北京:中华书局,1991.
[13]杨世骧.文苑谈往[J].新中华(复刊),1943,1(6):136-138.
[14]王易.词曲史[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
[15]陈水云.浙江江山刘氏与清末民初词学[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4).
[16]叶裕仁.刘泖生莎厅课经第二图后序[M]//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北京:燕山出版社,1999.
[17]朱彊村.致夏承焘书[J].词学季刊,1933,1(1).
[18]赵万里.唐五代宋辽金元名家词辑题纪[M]//校辑宋金元人词.排印本.南京: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1.
[19]王国维.宋元戏曲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