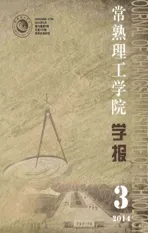宋季词史作品探讨
2014-03-29刘华民
刘华民
(常熟理工学院,江苏 常熟 215500)
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第六条曰:“感慨所寄,不过盛衰;或绸缪未雨,或太息厝薪,或己溺己饥,或独清独醒,随其人之性情、学问、境地,莫不有由衷之言。见事多,识理透,可为后人论世之资。诗有史,词亦有史,庶乎自树一帜矣”[1]。周济可能是最早提出词史概念、指出词史现象的词学专家。
一、诗史界定
诗史、词史是特定的概念,有着特定的内涵。而要界定“词史”,就必须先讲清“诗史”。
古今都有学者将诗史观念的产生追溯到先秦、孔孟,但是我们必须承认,诗史概念的正式提出在晚唐。唐末孟棨的《本事诗·高逸》以“当时号为诗史”赞誉杜甫诗[2],给人这样的印象:似乎把杜诗看作诗史在唐代已成共识,其实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当时”资料,却仅此一家之言。入宋以后,诗史之说才蔚然成风,这主要表现在对杜甫诗歌的阐释上,由于主客观条件的种种限制,还没有被运用于诗歌创作中。直至宋末元初,一批爱国诗人才既具有强烈的诗史意识、明确的诗史主张,又写出了大量的诗史作品。也就是说,宋末元初的诗史之作,是诗史理论与诗歌创作实践第一次自觉结合的成果。它们是明清两代学者、诗人继续研究诗史理论的典型材料和效法诗史创作的光辉榜样。明末清初的诗史作者与其说是继承杜诗传统,不如说是受宋季诗史的深刻影响。
研究宋季诗史现象,首先应该重视当事人(作者)和当时人(读者)的观点。这不仅因为当事人是诗史的“血心流注”的自觉创作者,当时人是诗史的感同身受的现场评论者;也不仅因为当事人和当时人的观点是我们今天研究的第一手资料,并且本身就是宋季诗史现象的组成部分;更重要的是,诗史的产生除了作者的主观因素外,还有其必要的客观条件。我国古代的诗史总是产生在周边少数民族侵略中原、江山易主、社稷倾覆之际,也就是顾炎武所谓“亡天下”的特定历史时期。宋季诗史的作者和当时的读者身经目击民族劫难的沧桑巨变,他们直接的切肤之痛,他们对诗史的深刻理解和把握,自有后人“不可同日而语”之处。我们今天可以也应该在古人、前人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究竟什么是诗史、怎样的作品才是诗史,我们可以也应该提出我们的诗史观;但是,首先要把握宋季诗史作者和论者的观点,否则,就可能远离了诗史的原生状态,模糊了诗史的本来面目。
文天祥是宋季诗史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作者。他的《集杜诗·自序》集中体现了他的诗史观:“昔人评杜诗为诗史,盖其以咏歌之辞,寓纪载之实,而抑扬褒贬之意,灿然于其中,虽谓之史,可也。予所集杜诗,自余颠沛以来,世变人事,概见于此矣,是非有意于为诗者也。后之良史,尚庶几有考焉。”[3]分析这一自序,可知文天祥所认为的“诗史”,包括这样几个要素:一是诗歌的语言,二是纪实的笔法,三是“世变人事”的内容,四是抑扬褒贬的批评态度,五是良史可考的创作动机。这是关于诗史问题的简明扼要又完整全面的表述。
仔细研读宋季诗史作者和当时读者对诗史的论说,他们的共同认识是:
(1)正史亡,诗史出——诗史是特定时代的产物。文天祥在《指南录》和《集杜诗》的序言中都交代了“患难”之中、“颠沛”以来的写作背景,并一再强调“使来者读之,悲予志焉”、“使天下见之,识其为人”;他还说过“亡国大夫谁为传?只饶野史与人看”(《己卯十月一日至燕,越五日,罹狴犴,有感而赋·其五》)[3]。“世变”、“亡国”这样异乎寻常的危急时刻,才需要也只能够以诗存史,昭示后人。周方《书汪水云诗后》云:“余读水云诗,至丙子以后,为之骨立。再嫁妇人,望故夫之陇,神销意在,而不敢出声哭也……千载之下,人间得不传之史。”[4]周方以亡夫之遗孀比亡国之遗民,以“人间得不传之史”,说明汪元量诗是朝廷正史不传情况下的民间之史。同样的,李钰、刘辰翁等都称汪元量诗为宋亡之“野史”。汪元量《答林石田》诗曰:“我更伤心成野史,人看野史更伤心。”[4]也把自己的诗看作野史。这一点,郑思肖说得更加明确、透彻:“天下治,史在朝廷;天下乱,史寄匹夫……史而匹夫,天下事大不幸矣。我罹大变,心疢骨寒,力未昭于事功,笔已断其忠逆。所谓诗,所谓文,实国事、世事、家事、身事、心事系焉。”[5]国史是由朝廷编修的,国家亡而正史亡,正史亡而野史出,诗史则是野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重要表现形式。宋季诗史作者就是以这样的诗史意识自觉担当起以诗存史、通过诗歌创作保存民族历史、弘扬民族文化的神圣使命的。国家灭亡之际的“野史”,诗史的这一本质属性,决定了诗史的内容是“世变人事”,即社稷沦亡过程中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诗史的主题是反侵略、反投降,是亡国之痛、故国之思,而诗史作者无疑是爱国诗人。
(2)重纪实,也抒情——诗史是两种属性的结合。古今学者对诗史的理解,有的侧重于诗,有的侧重于史,罗时进先生归纳为“纪实论”、“知世论”、“感时论”三种主要观点,并且认为宋代占主导地位的是“纪实论”。[2]宋代其他诗史论者的观点我们暂不涉及,只看宋季诗史作者和当时读者的观点。诚然,他们是重纪实的,但他们在强调“史”这一面的同时,并没有忽略“诗”的另一面。文天祥在“以咏歌之辞,寓纪载之实”后,有“抑扬褒贬之意,灿然于其中”,这“抑扬褒贬之意”不就包含着爱憎喜怒之情吗?这“灿然于其中”不就是强烈显著的抒情吗?更何况,在此之前,他还点明“子美于吾隔数百年,而其言语为吾用,非性情同哉”。他的《集杜诗》是既纪史实又抒性情的。再看汪元量,他有一句名言:“走笔成诗聊纪实。”(《凤州》)他的《妾薄命呈文山道人》亦云:“君当立高节,杀身以为忠。岂无春秋笔,为君纪其功。”[4]“纪实”似乎就是他的诗史创作原则。汪元量诗史作品不少,诗史论述却不多,上引诗句未必全面反映他的诗史观。而他的同时人,都注意到并且指出了他的诗史作品的抒情性。李钰《〈湖山类稿〉跋》云:“汪水云出示《类稿》,纪其亡国之戚,去国之苦,艰关愁叹之状,备见于诗,微而显,隐而彰,哀而不怨,欷歔而悲,甚于痛哭。”[4]悲哀愁苦甚于痛哭,感情之强烈可想而知。刘辰翁《湖山类稿序》云:“杭汪水云……凡可喜、可诧、可惊、可痛哭而流涕者,皆收拾于诗。解其囊,南吟北啸,如赋史传。”[4]惊诧悲喜之吟啸与史传之叙述铺陈是“皆收拾于诗”的。周方《书汪水云诗后》也以“闻见其事,奋笔直情”,即叙事抒情相结合来评论汪元量的诗史之作。还有郑思肖,他强调自己的诗实“事所系焉”,又一再表明“敬以诗识之,储为史官补”(《辛已夏七月》),“为痛英雄并消没,托诗为史笔传闻”(《哀刘将军》);而其诗所系,除国事、世事、家事、身事外,还有“心事”,其“井中奇书”名曰《心史》,根据他“发明《心史》之义”的《总后叙》可知,[5]“心”与“史”在这里不是偏正结构,而是并行关系,是亡国之史与复宋之心的统一。林景熙《书陆放翁诗卷后》开头两句先评杜甫诗:“天宝诗人诗有史,杜鹃再拜泪如水。”《郑中隐诗集序》云:“花泪鸟惊,诗中有史,千载犹有考焉。”《宋景元诗集序》云:“仆端读尽卷,毛骨起立,而知翁方寸之耿耿者亡恙。然则诗中有史,固不使《石壕吏》、《庐子关》等作得以独雄千古也。”[6]“杜鹃再拜泪如水”,是故国先帝之思,“花泪鸟惊”是感时伤世之情,“方寸之耿耿者”是忠君爱国之心,林景熙无论评杜甫之诗史还是评时人之诗史,都是兼顾史实与诗情的。林景熙本人的诗史作品体现了他的诗史观,清鲍正言《霁山先生集跋》就是以“屈子《离骚》、杜陵诗史”[6]评价林景熙诗的。纪实是史的本质属性、主要特点,抒情是诗的本质属性、主要特点,宋季诗史作者和论者,是纪实与抒情并重,是诗与史相统一相结合的。
综上所述,在民族危亡、社稷倾覆之际,以诗存史,以诗补史,记丧乱之由,发黍离之悲,纪实与抒情并重,叙事与伤时兼备,这就是宋季诗史作者和论者共同的诗史观。诗史应该这样来定位,诗史的内涵应该这样来理解;那么,作为诗史精神在词坛的移植,词史也应作如是观。
二、词史作品
宋元交替之际的词史作品,虽数量远不如诗史作品,但也卓然可观。主要包括:
(一)文天祥后期词
同仕至宰辅、力行革新的范仲淹、王安石一样,文天祥也是能词而少作。他现存8首词,其中6首写于起兵抗元之后。
先看《沁园春·题潮阳张许二公庙》:
为子死孝,为臣死忠,死又何妨。自光岳气分,士无全节,君臣义缺,谁负刚肠。骂贼睢阳,爱君许远,留取声名万古香。后来者,无二公之操,百炼之钢。 人生翕歘云亡。好烈烈轰轰做一场。使当时卖国,甘心降虏,受人唾骂,安得流芳。古庙幽沉,仪容俨雅,枯木寒鸦几夕阳。邮亭下,有奸雄过此,仔细思量。
这首词原误题“至元间留燕山作”,中华书局新版《全宋词》据永乐大典改。[7]
潮州双忠庙在广东潮阳县城郊东山上,据《隆庆潮阳县志》,元代潮州路总管王用文有《刻文丞相谒张许庙词跋》;又清代诗人丘逢甲《岭云海日楼诗钞》有七律二首,题为《潮阳东山张许二公祠为文丞相题〈沁园春〉词处,旁即丞相祠也。秋日过谒,敬赋二律》,其一首联云:“夜半元旌出岭东,文山曾此拜双忠”。
南宋端宗景炎元年(1276)五月,文天祥任枢密使、同都督诸路军马,七月开府南剑(今福建南平),而后崎岖岭海,转战闽、粤、赣,于祥兴元年(1278)十一月率行府进屯潮阳,不久,元将张弘范即大驱入潮阳,文天祥移趋海丰,12月20日在五坡岭兵败被执。文天祥是在千钧一发的危急之际,拜谒潮阳张许庙的,所写《沁园春》词,对张巡、许远作了十分热烈的赞颂,而给“降虏”、“卖国”的“奸雄”以当头棒喝、无情鞭挞,这首词吊古喻今,反映了南宋爱国志士既要同外部侵略者、又要同内部投降派作斗争的史实,并表示了自己尽忠死节的决心。毫无疑问,这首《沁园春·题潮阳张许二公庙》是堪称词史的。
再看《南康军和东坡酹江月》:
庐山依旧,凄凉处,无限江南风物。空翠晴岚浮汗漫,还障天东半壁。雁过孤峰,猿归老嶂,风急波翻雪。乾坤未歇,地灵尚有人杰。 堪嗟飘泊孤舟,河倾斗落,客梦催明发。南浦间云连草树,回首旌旗明灭。三十年来,十年一过,空有星星发。夜深愁听,胡笳吹彻寒月。
南康军是宋代一行政区域,辖境相当于今江西省星子、永修、都昌等县地。祥兴二年(1279)二月,厓山兵溃,帝昺沉海,南宋彻底灭亡,文天祥自广东被押往燕京,舟行途经南康军时作此词。词上片描写峰峦巍峨的庐山、波澜壮阔的长江,风物依旧,而江山易主,作者一方面心境凄凉,另一方面又满怀希望:“乾坤未歇,地灵尚有人杰”,爱国志士将再度奋起,光复河山。江西是文天祥的故乡,他是在这里起兵勤王的,词下片由眼前的“漂泊孤舟”回想自己参与和领导抗元的情景,乃至状元及第、步入仕途、救亡图存三十年的历程,无奈回天乏力,“空有星星发”。全词饱含着国破家亡的深恨巨痛。这首《念奴娇》虽以写景抒情为主,但从其背景、内容看,肯定可资后来史传取材、考证。
和文天祥一起被押解北上的是邓剡。邓剡在南宋厓山行朝任礼部侍郎、学士院权直,厓山溃败时,邓剡跳海自尽,被元兵钩起,遂与文天祥同行。祥兴二年六月十二日,两人到达建康(今南京),八月二十四日渡江继续北行,邓剡因病留建康,文天祥作《酹江月·驿中言别友人》、《酹江月·和》两词与邓剡诀别。
《酹江月·驿中言别友人》的著作权争论已久,至今未决,我们认为不是邓剡而是文天祥写的。词的上片抒写兵败国亡的遗恨:“水天空阔,恨东风不借世间英物”,“此恨凭谁雪”;下片追述起兵抗元的经历,从出使元营、脱逃南归、再举战旗,到兵败被俘,结尾“伴人无寐,秦淮应是孤月”点“言别”之题。综合考察、辩别版本、唱和、内容理解三个问题,可以说这首《酹江月》是文天祥所写几不容置疑(详见拙著《文天祥诗研究》第十一章“作品考辨”,巴蜀书社1999年版)。
停留建康期间,文天祥还写了两首《满江红》。德祐二年(1276)春,元军破临安,宋恭帝、全太后、福王及南宋宗室、宫人,被掳北上大都。南宋度宗昭仪(皇宫女官)王清惠随三宫入燕,在汴京夷山驿壁题《满江红》一首,中原传诵。文天祥在建康也读到了这首词,认为末句“若嫦娥于我肯相容,从圆缺”“欠商量”,便和韵一首,代言一首。和韵词的小序点明“以庶几后山《妾薄命》之意”。后山是北宋陈师道的字,陈师从曾巩,受曾巩特殊恩遇,曾死后,陈作《妾薄命》二首,表示决不改从他师。文天祥此词用以表明自己绝不变节事敌,南宋虽亡,义不帝元。“代王夫人作”之词,结尾云“算妾身,不愿似天家,金瓯缺”,也表明虽山河残破国家灭亡,自己仍要保全名节。
总之,文天祥在建康写的四首词,从作品的“本事”看,从作者的身份看,都称得上是“词史”。文天祥作为南宋重臣、抗元领袖,其重要经历、言行作品乃正史所必载。
(二)汪元量北行词[7]
汪元量是南宋宫廷琴师,供奉禁中。在宋恭帝、全太后被掳北上不久,太皇太后谢道清也被迫北上大都,汪元量等随行。赴燕途中,汪元量作《洞仙歌》,小序云:“毗陵赵府,兵后僧多占作佛屋”,反映了元蒙统治集团尊崇佛教、番僧多骄横不法的史实。又作《莺啼序·重过金陵》,从城郭、街巷写到历史、人物,表现古今兴亡的主题,寄寓南宋覆灭的沉痛教训。《六州歌头·江都》是他过扬州所作,主旨与“重过金陵”同。
我们再来看他的《水龙吟·淮河舟中夜闻宫人琴声》:
鼓鼙惊破霓裳,海棠亭北多风雨。歌阑酒罢,玉啼金泣,此行良苦。驼背模糊,马头匼匝,朝朝暮暮。自都门燕别,龙艘锦缆,空载得、春归去。 目断东南半壁,怅长淮、已非吾土。受降城下,草如霜白,凄凉酸楚。粉阵红围,夜深人静,谁宾谁主?对渔灯一点,羁愁一搦,谱琴中语。
首二句用唐玄宗、杨贵妃的典故,谓元军兵临城下,宫内人心惶惶;“歌阑”三句写帝后、嫔妃、宫女哭哭啼啼,被迫踏上北去的路途;“驼背”三句借用杜甫诗句形容元兵军容整齐、戒备森严,每天夹持押解在左右;接下来点明此行乃乘船前往。元蒙入临安、掳三宫押赴大都后,文天祥、张世杰、陆秀夫等在温州拥立益王赵罡再举战旗继续抗元,而手握重兵的南宋淮西统帅夏贵却以所辖全境降元,汪元量他们过“长淮”时,“已非吾土”,眼前“草如霜白”,心中“凄凉酸楚”;本来,皇帝、太后,与嫔妃、宫女,等级分明,一旦沦为俘虏,便都是臣妾,夜里相依而眠,不分宾主贵贱,这是北上情景的真实写照;结尾处照应标题“淮河舟中夜闻宫人琴声”,蕴含不尽之意。
赴燕途中,汪元量还写了《婆罗门引·四月八日谢太后庆七十》词。谢道清乃宋理宗之后,宋恭帝年幼,谢以太皇太后身份垂帘听政,恭帝德祐二年二月,谢道清下诏书向元蒙投降,接着身不由己地以病余之躯北上大都,她的七十岁生日是在“冷泪交流”、“梦破”、“离愁”中度过的,聊可自我宽慰者只是尚能“把酒”、“听箜篌”。孔凡礼先生评点云:“此词之特点即为实写,其历史价值亦在此。”
抵达大都之后,汪元量又有《玉楼春·度宗愍忌长春宫斋醮》词:
咸淳十载聪明帝。不见宋家陵寝废。暂离绛阙九重天,飞过黄河千丈水。 长春宫殿仙璈沸。嘉会今辰为愍忌。小儒百拜酹霞觞,寡妇孤儿流血泪。
长春宫即白云观,在北京广安门外。愍忌,死者生日。斋醮,设坛祭祀。咸淳,度宗年号,度宗在位凡十年,1274年7月死,仅隔一年半临安陷落,恭帝北狩。璈,一种古乐器。寡妇,指全太后,孤儿,指宋恭帝。这首词记载了南宋皇室沦落塞外,在异国他乡祭奠度宗的史实。度宗的亡灵不得安宁,要“飞过黄河”才能受祭,虽然现场鼓乐依旧,皇室成员的处境却是悲惨之至。
汪元量的集句组词《忆王孙》9首和组词《忆秦娥》7首,虽然比较委婉含蓄,却是真切地描述了被掳到北地的宫女和士子的生活、心绪,应该视作词史。孔凡礼先生云:“《忆秦娥》组词七首,代被俘至北之宫人士人立言”,并逐首一一指明内容,如评组词第二首:“此词写宫人长期流落蓟门之凄凉处境”;评组词第三首:“此写宫人穷冬往边塞之哀愁。宫人留边塞,史籍未载,此可补其遗”,等等。[8]
汪元量的身份、地位本不如文天祥那样重要,但他随南宋皇室北上,又留北12年侍奉左右,他是这段史实的亲历者、见证人,又以诗词纪事存史,在我们讨论诗史词史问题上,他是一个重量级人物,就词史而言,他的作品比之文天祥,数量多,叙事性强。
(三)刘辰翁入元词[9]
刘辰翁是宋末元初最重要的词人。他曾自称“老来诗,句句皆成史”,他的《须溪词》中确有多首“词史”之作。
先看他的《兰陵王·丁丑感怀和彭明叔韵》:
雁归北。渺渺茫茫似客。春湖里,曾见去帆,谁遣江头絮风息。千年记当日。难得。宽闲抱膝。兴亡事,马上飞花,看取残阳照亭驿。
哀拍。愿归骨。怅毡帐何匹。湩酪何食。相思青冢头应白。想荒坟酹酒,过车回首,香魂携手抱相泣。但青草无色。 语绝。更愁极。漫一番青青,一番陈迹。瑶池黄竹哀离席。约八骏犹到,露桃重摘。金铜知道,忍去国,忍去国!
丁丑是南宋端宗景炎二年(1277),此前一年是丙子,宋恭帝(赵显)德祐二年,五月改端宗(赵昰)景炎元年。是年二月初五日,宋恭帝率百官上表降元,三月,元丞相伯颜派人逼迫宋恭帝、全太后、福王赵与芮、沂王赵乃猷、度宗生母隆国夫人等“入觐”,从临安到大都(今北京)拜谢元世祖“不杀之恩”,部分臣僚、嫔妃、宫女、士子随行。刘辰翁这首《兰陵王·丁丑感怀》就是追忆这一史实的。词分三叠,一叠写临安百姓亲眼目睹南宋帝后君臣走马挂帆被押北上的情景,亡国之恨千年铭记;二叠用蔡文姬和王昭君的典故,写太后途中的哀愁及归骨的意愿;三叠用周穆王会西王母的典故,写恭帝离宫去国而哀民的悲恸,结尾处用金铜仙人辞汉的典故及重复的修辞,强调不胜拳拳去国之情。另一首《兰陵王·丙子送春》,则通篇采用比兴手法,通过春末特有的意象,借喻南宋亡国和君臣去国的史实,两首《兰陵王》可谓姊妹篇。再看他的《柳梢青·春感》:
铁马蒙毡,银花洒泪,春入愁城。笛里番腔,街头戏鼓,不是歌声。 那堪独坐青灯!想故
国、高台月明。辇下风光,山中岁月,海上心情。
吴企明先生《须溪词校注》认为“本词约作于祥兴元年(1278)或二年”,我们认为是正确的。从词所描写的景物看,应该是元宵节。一个本该热闹喜庆的日子,因为蒙古铁骑的侵入,使临安变为愁城,街上的花灯流淌着伤心的烛泪,街头的鼓吹杂戏,演奏的是胡音番腔,作者面对如豆青灯,由故都高台宫殿的荒芜凄惨,想到当年的美丽繁华,想到自己避难山中的经历,更想到仍在闽粤沿海一带坚持抗元斗争的爱国志士。骑哨巡逻,戒备森严;初闻番笛,感觉刺耳;闽粤沿海的抗元斗争寄托着南宋民众的一线希望,祥兴年间的特定情景在词里表现得十分鲜明。
刘辰翁《永遇乐·余自乙亥上元诵李易安〈永遇乐〉,为之涕下。今三年矣,每闻此词,辄不自堪。遂依其声,又托之易安自喻。虽辞情不及,而悲苦过之》和《永遇乐·余方痛海上元夕之习,邓中甫适和易安词至,遂以其事吊之》两词,前一首作于丁丑岁端宗景炎二年(1277)或三年。作者把开封、临安的变迁,李清照和自己的遭遇,糅合起来,表达故国之思、亡国之痛,又反映了当时临安上元节居然禁火戒严,元军如临大敌,反映了江南沦陷,多少人包括作者妻离子散、颠沛流离的现实;后一首作于己卯岁帝昺祥兴二年(1279),直接点明宋元厓山决战,陆秀夫负帝昺蹈海殉国,南宋彻底败亡的史实。
刘辰翁是江万里的门生,江万里号古心公,官至参知政事,宋末赴水殉国,刘辰翁的《行香子·次草窗忆古心公韵》和《行香子·叠韵》两首以“魏阙心,磻石魄,汩罗身”等词句记载、歌颂了江万里的功德和气节。刘辰翁曾短期参与文天祥的勤王幕府,他的《莺啼序·感怀》“匆匆何须惊觉”和《莺啼序》“闷如愁红著雨”两词,为悼念文天祥而作,将“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文天祥比作三国时期的诸葛亮,歌颂他“至死而已”的精神和“垂名青史”的业绩。庐陵教官贾昌忠,号节庵,其弟贾纯孝追随南宋小朝廷至厓山,元军破厓山,贾纯孝抱二女和妻子一起蹈海赴死。刘辰翁《齐天乐》用屈原、《离骚》的事典、语典,纪念和赞颂了贾纯孝的壮举:
节庵和示中斋端午〈齐天乐〉词,有怀其弟海山之梦。昨亦尝和中斋此韵,感节庵此意,复不能自己,倘见中斋及之。
海枯泣尽天吴泪。又涨经天河水。万古鱼龙,雷收电卷,宇宙刹那间戏。沈兰坠芷。想重整荷衣,顿惊腰细。尚有干将,冲牛射斗定何似。 成都桥动万里。叹何时重见,鹃啼人起。孤竹双清,紫荆半落,到此吟枯神瘁。对床永已。但梦绕青神,尘昏白帝。重反离骚,众醒吾独醉。
刘辰翁还有许多题咏“送春”的篇章、忆念临安的作品和大量的节令词、咏物词,叙写天地翻覆、社稷沦亡的巨变,抒发深切的故国之思、亡国之痛、黍离麦秀之悲,准确表现特定的时代和遗民的心理,整体上富于词史的价值,但因为不像前面列举几首那样维系具体的重要史实,为避免“词史”的泛化,我们就不一一指实了。
(四)《乐府补题》37首[10]
《乐府补题》是一本奇书,至今未能断定是何人编辑,又因寄慨遥深,主旨隐晦,其背景、本事各有所见。可以确认的是,它是宋末遗民词人(王沂孙、周密、张炎、陈恕可、仇远、唐珏等)的咏物词专集,运用寄托手法,饱含故国之思。宋亡以后,周密、张炎、王沂孙、王易简、冯应瑞、唐艺孙、吕同老、李彭老、李居仁、陈恕可、唐珏、赵汝钠、仇远等14位遗民词人,先后结社唱和,以《天香》、《水龙吟》、《摸鱼儿》、《齐天乐》、《桂枝香》5个词牌分吟龙涎香、白莲、莼、蝉、蟹5种生物,最终结集成书,共辑录37首词。清人厉鹗以为《乐府补题》与宋帝陵墓盗发之事有关,今人夏承焘又申此说。
元世祖至元二十二年(1285),元朝江南释教总统杨琏真伽发掘会稽南宋六帝陵墓,劫取陪葬的金银财宝,而将陵中骨骼抛散草莽间,这是民族歧视的暴行逆举,是南宋遗民的奇耻大辱。林景熙、唐珏、郑朴翁、谢翱等人或扮为乞丐,或扮为采药者,潜往拾取陵骨,或者招募少年趁夜收殓。他们把高宗、孝宗等的遗骸装为两函,托言佛经,秘密移葬于兰亭,并种植冬青树于土坟上以资识别。这在当时是一重大事件。林景熙有《梦中作》、《冬青花》、《酬谢皋父》,唐珏有《冬青引》,谢翱有《冬青树引》,皆以诗暗记此事。明末清初黄宗羲列举历代诗史之作时说:“非石田(林景熙)、晞发(谢翱),何由知竺国之双经”,视为诗史。
暗记南宋帝陵被盗掘的诗是诗史,那么,借喻同一事件的词应该就是词史。本事相同,手法相同,体裁不同而已,两者的本质属性应该是一致的。我们来看《乐府补题》中的一首,王沂孙的《齐天乐·余闲书院拟赋蝉》:
一襟余恨宫魂断,年年翠阴庭树。乍咽凉柯,还移暗叶,重把离愁深诉。西窗过雨。怪瑶珮流空,玉筝调柱。镜暗妆残,为谁娇鬓尚如许。 铜仙铅泪似洗,叹携盘去远,难贮零露。病翼惊秋,枯形阅世,消得斜阳几度。余音更苦。甚独抱清高,顿成凄楚。谩想薰风,柳丝千万缕。
题中的“余闲书院”是当时遗民词人结社唱和的地方之一。这首词从字面看,通篇咏蝉。上片起二句用齐女化蝉典故,总写蝉年年栖身于翠阴庭树,孤寂清苦。接着“乍咽”三句写蝉鸣,她一会儿在寒枝高处哽咽,一会儿在密叶深处悲泣,诉说自己的离愁余恨。以上5句是从正面咏蝉,接下来5句是从反面衬托。“西窗过雨”,秋天来临,雨后,蝉声格外清脆,蝉翼格外透亮,这是蝉在生命结束前的回光返照。下片写进入秋季的蝉,本以饮露为生,现露盘去远,何以卒岁?病羽残翼,何以御寒?势必当不得几度斜阳,时日无多了。因此而“余音更苦”,垂死前的蝉鸣,倍觉凄楚。薰风吹暖,柳丝轻飏的盛夏景象,一去不复返,昔日的回忆,徒增现实的悲痛。
从深层看,这首词借咏蝉而写人。一襟余恨,宫魂离愁,瑶珮玉筝,青镜蝉鬓,非人而何?通篇在寒蝉的背后,晃动、飘舞着一个女子的倩影。此女子是哪一位、哪一类?怨忿而死,尸变为蝉的齐女,乃齐王之后,故作者用“宫魂”一词。魏明帝拆迁西汉建章宫的金铜仙人到洛阳,这个大家熟悉的典故主要表达的是忆昔怀旧的兴亡感触和离别心情,金铜仙人“潸然流下”的乃是亡国之泪。“娇鬓”一词也有出典,魏文帝时宫女发式制如蝉翼,称为“蝉鬓”。总之,作者使事用典,都与宫廷、王室、后妃有关。南宋覆灭之际,一群忠君爱国的遗民特地结社唱和,包括本非词人的唐珏等也积极参与,按照约定的统一方式,咏物赋词,极沉痛,极隐晦,必有所指。咏物重寄托,是南宋词人继承《诗经》比兴、楚辞香草美人传统而采用的惯常手法;而联系绍兴帝后陵墓遭盗掘一事,托物寄意,影射暗示,是完全可能的。研读王沂孙这首《齐天乐》,说是为发陵而作,应该不算牵强。细检《乐府补题》诸词,大率如此。因此,本文将其列入词史之作。
南宋遗民词中,有不少真实反映遗民悲惨遭遇、艰辛生活和痛苦心情的作品。比如徐君宝妻的《满庭芳》:
汉上繁华,江南人物,尚遗宣政风流。绿窗朱户,十里烂银钩。一旦刀兵齐举,旌旗拥、百万貔貅。长驱入,歌台舞榭,风卷落花愁。 清平三百载,典章人物,扫地俱休。幸此身未北,犹客南州。破鉴徐郎何在,空惆怅、相见无由。从今后,梦魂千里,夜夜岳阳楼。[7]
元军南侵,岳州城破,徐君宝妻与丈夫离散而被俘虏,始终不肯屈从,最后投水以死,殉国殉节。这首《满庭芳》是她的绝命词,是以鲜血和生命写就的杰作。再看蒋捷的《贺新郎·兵后寓吴》:
深阁帘垂绣。记家人、软语灯边,笑祸红透。万叠城头哀怨角,吹落霜花满袖。影厮伴、东奔西走。望断乡关知何处,羡寒鸦、到着黄昏后。一点点,归杨柳。 相看只有山如旧。叹浮云、本是无心,也成苍狗。明日枯荷包冷饭,又过前头小阜。趁未发、且尝村酒。醉探枵囊毛锥
在,问邻翁、要写牛经否。翁不应,但摇手。[7]
这首词写元军灭宋、改朝换代之际,南宋遗民的流离失所和衣食无着。上片用往日家庭生活、用寒鸦尚可归巢作为对比,突显作者的东奔西走、颠沛流离。下片用枯荷包冷饭、探枵囊、问邻翁等细节,写谋生艰难,生活困穷。作者的漂泊之苦又是与亡国之痛紧相融合的,这是一篇现实主义的佳作。
以笔者看来,根据本文对诗史、词史的界定,徐君宝妻的《满庭芳》是真有其人、确有其事,虽一普通女子,其人其事其词均惊天地、泣鬼神,永垂不朽,应属词史。蒋捷的《贺新郎》当然也是真实的,但未系具体的史事,不属词史作品。这样区别,丝毫不是降低蒋捷词和其他同类词的价值,这些词同样有认识价值,只是非词史而已。
三、词史、诗史之比较
宋末元初,天翻地覆,巨大的民族劫难催生了一批诗史、词史作品。词史之作同诗史之作两相比较,差异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诗史完整,词史零散
文天祥的《集杜诗》200首,从《社稷第一》到《陆枢密秀夫第五十二》,写南宋败亡的过程,起自元蒙南侵之初,依次写景定元年泸州叛,咸淳九年襄阳陷,咸淳十年荆湖诸戍接连投降,德祐元年鲁港、镇江先后败遁,以及临安失守,三山拥立,行朝浮海,景炎宾天,祥兴登极,厓山覆灭等重大事件。从《勤王第五十三》到《入狱第一百四》,写自己后期抗元的经历,起自应诏勤王,依次写孤军赴阙,守吴门,戍余杭,使虏营,被扣押,发京师,去京口,行淮东,归浙江,至福安,而后转战闽粤赣,到空坑败绩,潮阳被俘,跋涉万余里,就囚燕狱。从《怀旧第一百五》到《次妹第一百五十五》,是纪念部将、战友和亲人的。最后部分,抒发“思故乡怀故山之情”和以身许国的夙愿、杀身殉国的决心。《集杜诗》以“史有考”为主旨,完整地反映了作者“颠沛以来”的“世变人事”。文天祥的《集杜诗》是以诗史自许的,并且得到社会承认,《集杜诗》在明代印行时,后人即题为《文山诗史》。文天祥还有《指南录》、《指南后录》,可与《集杜诗》互为补充,互相辉映。《集杜诗》对宋季历史的记载更完整,《指南录》对亲身经历的叙述更详细;《指南录》是“即时实录”、“现场直播”,《集杜诗》是事后痛定思痛的追叙,两者都是规模宏大、相对完整的诗史,既有各自存在的价值,合起来又倍增其价值!
汪元量的《醉歌》、《越州歌》、《湖州歌》,以及《亡宋宫人分嫁北匠》、《全太后为尼》、《瀛国公入西域为僧号木波讲师》等,从襄樊失守,临安陷落,三宫北上,一直写到抵燕之后,也是反映宋亡经过的规模宏大、相对完整的诗史。
比较起来,词史则缺少反映宋亡历史过程的宏构巨制,只是载录宋元之际的某一重要事件或某一重要人物。
文天祥后期备位将相,不但参加而且领导了抗元斗争,是贯串南宋末年始终的重要人物;汪元量虽身份卑微,作为宫廷琴师,却是南宋帝后侍臣,国亡北徙后他仍供奉左右。文天祥和汪元量两人的身份、经历,使他们能够以当事人、见证人来完整地反映宋元交替的历史。两人都是诗史、词史的主要作者,又都主要是以诗存史的,对他们来说,词乃“诗余”,词史亦是诗史之余。而其他词史作者不具备文天祥、汪元量那样的条件,更不可能写出完整反映宋亡过程的词史。这是词史不如诗史完整的原因。
(二)诗史具体,词史概括
宋季诗史追求的是实录,是生活的真实,是史实的完整具体的记述,所叙之事无论主干还是枝节,都是生活中实际发生的;与此相应,许多诗史采用了诗文结合的方式、大型组诗的体制和赋笔直书的手法。文天祥的《指南录》和《集杜诗》严格地说都不只是诗集,而是诗文合集。《指南录》有《自序》、《后序》两个总序,此外,全集91题诗,有64题附小序,共有122段小序,有几段小序长达四五百字,《出真州十三首》的序文加起来达1500多字。所有这些序,绝大多数是记事,叙述细致具体,文字简洁明了,保留了许多珍贵的史料。《集杜诗》除庚辰年写的序、壬午年写的跋以外,还附诗前小序105段。《指南录》、《集杜诗》中的序既有独立存在的价值,又与诗紧密结合,序为纪实之笔,诗为咏歌之辞,诗文互相补充生发,而以叙事纪实为宗旨。以“少陵诗史”自许的南宋遗民舒岳祥,则广泛运用了以序代题的方式,即以长行纪实性诗题来发挥丰富、补充、印证诗歌内容的作用,这是又一种类型的诗文结合。
宋季诗史大量运用组诗形式,体制宏大,组诗内各诗之间的衔接十分紧密。文天祥《指南录》里有22题组诗,共计111首诗,占全集诗歌的62%,这些组诗绝大多数是一脉相承的叙事诗。包括诗篇最多的是《至扬州二十首》,是写“至扬州城下,进退维谷,其彷徨狼狈之状”的,写了一天两夜发生的事情:露宿破庙,候启城门;鼓角悲鸣,进退不可;两种意见,从违难定;随行四人,携金逃走;跟一向导,暂避土围;元军数千,隔墙而过;两仆被捕,解金获免;饥寒交迫,乞食他人;樵夫引路,前往高沙。逃到扬州,李庭芝闭门不纳,这是文天祥虎口脱险南归途中的一件大事,这件大事又由若干小事构成,《至扬州二十首》一诗一事,既清楚明白,又显示出事情本身的错综复杂、曲折惊险。《集杜诗》200首,更是连篇接续,体大思精,完全可以看作是一个大型组诗。汪元量的《醉歌》10首、《越州歌》20首、《浮丘道人招魂歌》9首、《杭州杂诗和林石田》23首,也都是联篇吟咏的诗史长卷,特别是《湖州歌》98首,尤为叙事精详内容丰富的大制作。
在我国,诗歌历来是抒情的艺术,以每句字数相等、通篇整齐划一的诗体来叙事,特别是叙述复杂、曲折的情节,是比较困难的。利用诗前附序这一形式,实际上使诗歌与散文结合起来,困难就迎刃而解了。短诗篇幅有限,长诗构思费时,复杂的情节、完整的过程需要较长的篇幅,战乱的年代、危险的处境不允许从容地谋篇布局,而把单篇短诗连接起来,困难就迎刃而解了。文天祥、汪元量、郑思肖、舒岳祥等宋季诗史作者正是这样做的,从而得以及时地“以诗记所遭”,写下大量的叙事性诗史。特别是文天祥,把诗文结合加上联篇吟咏(尤其是七绝组诗加大段序文)以叙事,这是其诗史最富特色的艺术形式。
从本文第二部分所列举的词史作品可以见得,宋季词史也有不少附小序,只是序文简短,记事简略;也有几组联章词,只是架构过小。汪元量的《忆王孙》集句9首和《忆秦娥》7首,初具规模,却全无序文,又淡化情节,叙事性明显不及诗史作品。
宋季诗史是赋笔直书的,是“敷陈其事直言之”的;而宋季词史则多用比兴手法,以典故、借喻、寄托等隐约委婉叙写,本事往往退在“幕后”,不注重事件的完整、情节的具体。因而可以说,词史之记事存史主要是一种艺术概括。
(三)诗史侧重在史,词史侧重在词
我们先来看张炎的一首词《解连环·孤雁》:
楚江空晚。怅离群万里,恍然惊散。自顾影、欲下寒塘,正沙净草枯,水平天远。写不成书,只寄得、相思一点。料因循误了,残毡拥雪,故人心眼。 谁怜旅愁荏苒?谩长门夜悄,锦筝弹怨。想伴侣、犹宿芦花,也曾念春前,去程应转。暮雨相呼,怕蓦地、玉关重见。未羞他、双燕归来,画帘半卷。[7]
这首词反映了三个重要史实。一是南宋贵族国破家亡,流离失所。张炎是南宋初期功臣循王张俊的后裔,祖父张濡镇守独松关时,部下误杀元蒙使者、礼部尚书廉希贤,临安陷落时惨遭元兵报复,祖父被凌迟处死,家人多被杀被掳,家财全部抄没,张炎侥幸独存而只身漂泊,寄食于人。词以“离群万里,恍然惊散”写灾祸突至,以“自顾影、欲下寒塘,正沙净草枯,水平天远”写无处安身。二是爱国志士囚禁于北方,忠贞不屈。文天祥在大都监狱关押四年,元朝统治者威逼利诱,软硬兼施,文天祥始终不改殉国死节之志。“残毡拥雪”用苏武牧羊的典故,暗喻文天祥,其“故人心眼”——对故国家乡的思念之情,虽因“孤雁”“写不成书”而“误了”,但还是“寄得”“一点”,山长水阔毕竟阻绝不了故国之思。三是部分叛臣降将,卖国求荣。词以半卷画帘之上的“双燕”借喻那些投靠侵略者而得到高官厚禄的败类,表达了对卖国者的鄙视和自己虽历尽艰辛也要保持操守的态度。
从蕴含在字面背后的“本事”看,这首《解连环·孤雁》应属词史之作,但作者采用的是咏物寄托的方式。全词明写孤雁,暗写自己,既状雁精细,形神兼备,不仅写出雁的习性、环境,而且写出了它的特征、精神;同时又以雁喻人,托物言志,反映国破家亡的巨大变故和志士仁人的崇高气节。这是一首艺术性、思想性很强的咏物之作、词史之作。
《乐府补题》37首与张炎《解连环·孤雁》属同一类型的词史作品,咏物而别有寄托,蕴含着重要历史事件,只是更加隐晦曲折。
我们再来看刘辰翁的《兰陵王·丙子送春》:
送春去,春去人间无路。秋千外,芳草连天,谁遣风沙暗南浦。依依甚意绪。谩忆海门飞絮。乱鸦过,斗转城荒,不见来时试灯处。 春去,最谁苦。但箭雁沉边,梁燕无主。杜鹃声里长门暮。想玉树凋土,泪盘如露。咸阳送客屡回顾,斜日未能度。 春去,尚来否。正江令恨别,庾信愁赋。苏堤尽日风和雨。叹神游故国,花记前度。人生流落,顾孺子,共夜语。
这首词正如陈廷焯《白雨斋词话》所云:“题是送春,词是悲宋,曲折说来,有多少眼泪”。作者整体采用比兴手法,通过一系列春末特有的景象和大量相关的典故,借喻南宋的沦亡和君臣北去的史实。丙子,宋恭帝德祐二年(1276),是年二月,元兵入临安,南宋朝廷投降,三月,南宋帝后皇室等被押解去燕京。这首词在“江令恨别,庾信愁赋”之后,原有自注:“二人皆北去”,作者“丙子送春”的醉翁之意由此可见。
上述两词都将本事隐去,而以比兴寄托出之,这是词史之作有代表性的写法。与此迥然有别,文天祥、汪元量等人的诗史之作,则是明言直说,纪实写真,不假外物,不尚雕饰,曲尽其事,足资考证。总体而言,宋季诗史侧重在史,宋季词史侧重在词。
[1]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2]罗时进.唐诗演进论[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
[3]文天祥.文天祥全集[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
[4]汪元量,撰.增订湖山类稿[M].孔凡礼,辑校.北京:中华书局,1984.
[5]陈福康.井中奇书考[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
[6]陈增杰,校注.林景熙诗集校注[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5.
[7]唐圭璋,编纂.全宋词[M].简体增订本.王仲闻,参订.孔凡礼,补辑.北京:中华书局,1999.
[8]周笃文,马兴荣,主编.全宋词评注[M].北京:学苑出版社,2011.
[9]刘辰翁,撰.须溪词[M].吴企明,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10]四库全书:第一四九○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