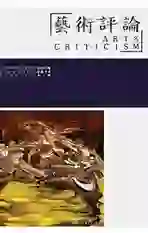陇南白马藏傩舞面具的设计宗源
2014-03-28邓亚楠夏航
邓亚楠 夏航


身处我国“藏彝走廊”上的陇南白马藏族,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特殊、饱含独特民俗风情的族群。而在白马人精神生活中占有极其重要地位的藏傩舞,更是白马藏人千年文化的凝固和传承,藏傩舞表演所需之面具,又从另一维度上诠释了白马人的艺术灵感、文化意蕴与精神崇拜。经过时间的洗礼、岁月的流逝,藏傩舞面具已然成为一种文化符号,值得我们去细考其中的艺术特色、文化喻指,并得出其设计宗源及艺术表现形式,为我国珍贵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发展做出一点奉献。
一、陇南白马藏傩舞面具的基本类型及其文化源考
在万物有灵的信仰时代,白马人在藏傩舞表演中使用面具是基于某种图腾崇拜的表现,据对白马人在宗教信仰活动中采用傩面具的考证来看,主要包括“池哥昼”、“麻昼”以及“甘昼”三种基本类型,不同类型代表着别样的文化源考。
(一) “池哥昼 ”傩舞面具及其文化源考
“池哥昼”是陇南白马人最具象征性、代表性的藏傩舞形式,从戏服、装饰、面具、宗教等各个方面展现了白马人文化的典型性、稀有性及原始性。“池哥昼”也被称为“仇池舞”或“鬼面子”。“池哥昼”藏傩舞的产生与传说有着较大的关系,传说白马人的祖先“叶西纳蒙”为了躲避战火而将自己打扮成身着怪异服饰的彪形大汉,后人为了纪念他而编排了“池哥昼”藏傩舞,而“池哥昼”的面具设计则与“三眼神”(二郎神)存在着极其重要的关联。对于这一点,从面具的“纵目”、“立目”、“凸目 ”等特征中就能反映出来。
“池哥昼”藏傩舞表演包含着九个人物形象,具体是四位“池哥”、两位“池母”、猴夫妻“池玛”及猴娃“鄢拜”。在九位人物形象塑造中,“池哥”与“池母”均需带面具出场,而“池玛”及“鄢拜”则脸抹锅灰、涂黑墨扮。“池哥”面具为青面獠牙的木雕彩绘面具,彩绘主要以暖色调为主,表现为红、黄、绿、白、黑五色的搭配,以色彩的不同搭配来展现威武、勇猛、夸张、变形的人物特征,以展示色彩强烈的“天神”形象。“池母”面具则类似于菩萨的形象,表现得慈眉善目、端庄秀丽,展现了女性的温柔、慈爱的一面。
(二)“麻昼”傩舞面具及其文化源考
陇南白马“麻昼”傩舞面具也称为“十二相”,是由十二种生肖属相所构成,表现为在藏傩舞表演过程中,头戴动物面具而舞。“十二相”的来源凸显了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的因素,同时也表达了白马人在民族融合过程中与汉文化之“十二生肖 ”的交融与 “层累”。
随着历史的推移,今天陇南白马“麻昼”傩舞面具“十二生相”的具体构成包括:两个池哥面具、两个池母面具、两个笑面鬼面具以及狮子、龙、牛、虎、鸡、猪等动物面具。这一具体构成并非古而有之,而是文化“层累”的结果,据史料记载,“麻昼”藏傩舞面具原先是完全按照“十二生相”来进行表演的,后来发现“齐上阵”的表演对村寨不吉利,慢慢就演化成今天的“样式”。
(三)“甘昼”傩舞面具及其文化源考
除“池哥昼”、“麻昼”两种藏傩舞需戴面具之外,“甘昼”藏傩舞进行表演时也必须戴上傩面具,与“池哥昼”、“麻昼”不同的是,“甘昼”以白马人具体的生活场景为表演素材,尤其是本地区女性的生活状态,如哺育孩童、烹煮做菜、擀面做饭、裁剪制衣等等,以歌颂女性的魅力与伟大。从“甘昼”之头戴笑脸面具来看,“甘昼”藏傩舞表演传达的无疑是一种欢快、祥和的气氛。因此,“甘昼”面具在制作时必须呈现人物性格中诙谐、幽默的特征。
“甘昼”表演是藏傩舞与戏剧相结合的结晶。通过以戏曲的方式来表达白马女性的生活场景,在具体的表演过程中,将生活场景的动作与伴唱相结合,无疑突破了原来藏傩舞只舞不唱的缺陷,并成为我国今后戏曲发展的重要源头质材。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具有了古代傩舞戏的“活化石”价值。
二、陇南白马藏傩舞面具的设计宗源
藏傩舞面具作为白马人祭祀活动中的重要道具,其设计宗源并非“灵光一闪”,而是具有浓墨重彩的原始宗教“动物图腾崇拜”的性质,并表达了“祖先崇拜”所激活的强化民族认同感“集体意识”的精神呼唤。
(一)原始宗教“动物图腾崇拜”彰显
在陇南白马藏傩舞表演中,存在着非常明显的原始宗教“动物图腾崇拜”的痕迹。“十二生相”面具最终得以呈现,与远古时代氏族部落时期羌戎民族群体的动物图腾崇拜是遥相呼应的。然而动物图腾崇拜的起因,则是基于原始人类对未知世界(包括自然界)种种错误的认识,并直接导致了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观念,进而衍生出最为原始的宗教。在原始宗教支配下,一切人类未能征服之物都有可能成为“神”,并为原始人类供奉,而其中也不可避免地包括了动物,在动物崇拜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之后,动物图腾崇拜便成为历史发展之必然。也正是基于此,才有了《后汉书 ·礼仪志》中关于甲作、腆胃、雄伯、腾简、伯奇、强梁、祖明、委随、错断、穷奇、腾根等动物的别称,其实就是为了彰显“神兽”驱邪、“食疫”的强大威力。
(二)“祖先崇拜”激活民族认同感“集体意识”的精神呼唤
在“池哥昼”藏傩舞表演中,最为突出的形象是四位“池哥”的“二郎三目神”和白马老爷的造型。无论是“二郎爷”或“白马老爷”,都是万物有灵时代白马人为了驱魔除妖而涂抹出的极具“祖先崇拜”宗教色彩的象征物。此外,在“池母”、“麻昼”等藏傩舞面具的设计上所表达的特殊内蕴与意指,同样是原始“祖先”的彰显,具有特殊的历史图腾崇拜渊源与符号意义。基于“祖先崇拜”的内涵,在傩面具的设计中彰显“祖先崇拜”的符号,无疑是为了激活民族认同感“集体意识”,以实现白马人不屈不挠的精神呼唤。
三、陇南白马藏傩舞面具的艺术表现形式
陇南白马藏傩舞面具不仅是白马人民族风情活动中的重要道具,承载了白马人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以及文化遗产的传承。更有甚者,傩面具在诸多学者的研究推广之后,赋予了独特的文化价值,并挖掘出傩面具的别样艺术表现形式。
(一)傩面具造型设计的宗教化、符号化
傩面具源于白马人在万物有灵时代对未知世界敬畏而产生的图腾崇拜,天生被赋予了某种神祗的象征,而在“池哥昼”、“麻昼 ”、“甘昼 ”等表演中被表演者所戴,喻指表演者成为神祗代言人及载体的角色。正是基于傩面具如此神秘的宗教符号,在傩面具造型设计上则不得不呈现其宗教化、符号化的典型特征。
无论是“池哥”面具的“二郎三目神”造型,还是“池母”面具的“菩萨”造型,或“十二生相”的动物造型,都无一例外地表达了白马人沿袭下来的宗教信仰,并通过对各种类型面具神性、宗教化、符号化的赋予,刻画出了各种类型面具的造型。以不同的造型来表现不同的面具性格,“池哥”则怒目圆睁;“池母”则眉慈目善;“十二生相”则变形夸张。然而无论是何种面具都凸显了“眼睛”之“开光”、“灵性”的特效,用以凸显面具造型的独特性、宗教性,带有极其浓厚的宗教意味。此外,白马人在制作傩面具之时也同样体现了宗教性,制作前需择良辰吉日,并向神祗请示,以获应允。制作完成之后还需举行招神仪式,以获神祗庇护。
(二)傩面具制作技法的精刻化、协调化
要达到藏傩舞表演情境的效果,傩面具精雕细刻以表现每一个面具背后的神祗物象性格特征,则显得尤为重要。傩面具的制作基本程序为一锯、二砍、三加工,所谓的“一锯”则是用锯子锯出面具长 30cm、宽 20cm的基本尺码;“二砍”则是用平斧砍出面具的基本造型;“三加工”则是用凿子、手刀、刮刨等对面具进行精细化的加工,以还原神祗物象的个性化特征,“池哥”、“池母”、“十二生相”等在造型上或凶悍、或勇猛、或逼真、或慈祥、或狂傲,无一不是精雕细刻的杰作。
在傩面具的制作中,对眼睛、眉毛、鼻子等部位的技法要求极高,尤其是眼睛刻画。如池哥一般是豹眼圆睁,这就要求艺术家必须做到 “凸目”,才能表达凶悍的性格;而池母则是凤眼微闭,这就要求艺术家做好“收目”,以衬托善正慈祥的特点。此外,眉毛也是表现不同神祗物象特征的重要标尺,四位“池哥”的眉毛各异,分别为卧蚕眉、长毛眉、剑眉、浓眉,这都是艺术家对“池哥”性格定型之后精雕细刻之上乘之作。当然,神祗物象的性格实现并非某一部位的精刻化之功,还需要通过面具各部分的协调化来表达,做好五官的整体一致,才能彰显傩面具的气派、自由、堂皇、清新的艺术气息。
(三)傩面具色彩搭配的程式化、工艺化
傩面具除了造型奇特、雕刻精细之外,其在色彩的搭配上也显示了极为高超的艺术表现力。现代傩面具一般表现为多种色彩的搭配、融合,以展现惟肖惟妙、精妙绝伦的傩面具特色,然而今日傩面具之色彩风格并非古而有之,经历了一个由感性到理性,由稚嫩到娴熟的过程,早期的池哥面具主要以黑色为主,池母则表现为白色,而“十二生相”则多保留木材本色,颇具汉朝“人面木牌”之风格。而早期白马人对于色彩不讲究之缘由,主要在于保持傩面具的自然本色。
随着时间的推移,色彩搭配在傩面具制作过程中被逐渐重视,以表现神祗物象不同的艺术效果。傩面具的色彩搭配主要通过红、黄、绿、白、黑等五种颜色来完成,以色彩的不同搭配,来诠释强烈的色彩跳跃,以凸显神祗物象的鲜明形象。如池哥老大的鼻子、下巴、脸颊一般采用红色,主要是基于红色所表达的血性、血气、忠勇的性格;池母的脸部则采用黄色,主要是基于黄色所享有的沉着、历练的性格特征。色彩在傩面具不同部位的运用,可以造就出一种实感性极强且使观众感动神秘而富于宗教色彩的效果,再辅之以特殊的场面,更是衬托了一种质朴、天然、原始的艺术美感。
陇南白马人藏傩舞面具的设计宗源及其艺术表现形式并不能一语概之,然在对其进行具体论证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明显感受到傩面具中所彰显的文化历史深远性和文化内涵丰富性,傩面具的发展正是基于如此的意旨,不断进行着文化的层累,并成为今日傩面具研究的重要素材和源泉。
邓亚楠:北京联合大学文化创意研究所副所
长、副教授夏 航:北京联合大学广告学院艺术设计系
副主任、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