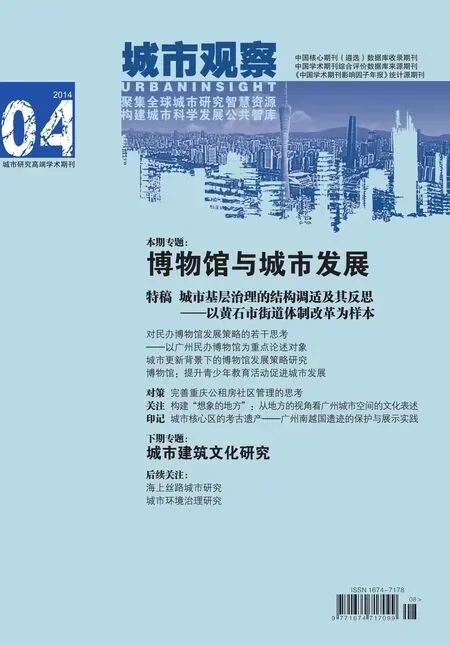构建“想象的地方”:从地方的视角看广州城市空间的文化表述
2014-03-28◎李燕
◎ 李 燕
构建“想象的地方”:从地方的视角看广州城市空间的文化表述
◎ 李 燕
在世界同质化加剧的今天,地方的独特性和差异性成为城市提升吸引力的重要手段。从地方的视角体察城市的演进和变化,进而构建“想象的地方”,或者可以成为地方参与城市规划与建设的一种方式。不过,地方本身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地方根著于历史,但地方又是一个“未完成的过程”,因而地方处于流变之中。根据地方的社会建构理论,广州的作为地方的独特性和差异性首先可以集中表现为由千年古港的经济活动所建构的商贸文化传统。以千年古港和商贸之都为核心,构建“想象的地方”,就是将这种商贸文化传统融入多种表现形式的城市叙事,通过地方记忆的再现,获得地方认同。
地方 独特性 城市空间 广州
一、引言
现代工业文明对都市空间的改造,带来城市面貌的趋同化,即所谓“无地方性(placelessness)的扩散”。[1]大众传播、增强的移动力以及消费社会等全球化因素进一步加剧了这一倾向。与此相适应,城市的本土化进程作为对抗或消解全球化效应的手段受到普遍的关注。本土化的实质,就是在趋同的全球背景下,彰显城市作为“地方(place)”的独特性和差异性。Hospers等(2003)的研究认为:要解决“全球化-地方化的矛盾”,在全球化过程中城市必须更加依靠自身独特的个性[2]。全球化意味着全球财富和资本的再分配,独特性和差异性则有助于城市提升辨识度和吸引力以竞逐全球范围内流动的资本。正如Harvey(1996)所说,在全球经济重新配置时空的状况下,由于时空压缩,物理区位变得不那么重要,地方品质对资本移动的区位选择则变得更加关键。“那些居住在地方的人,更加敏锐地意识到他们正在与其他地方竞逐高度移动的资本……因此,地方上的人试图区别他们的地方与其他地方,并且变得更加有竞争力,以便获得或保住资本投资。在推销地方的过程里,运用各种能够集结的广告如影像建构的巧妙手法,已经是至关紧要的事”。[3]从更深层的精神意义上,Lippard(1997)主张,“即使地方力量减小而且往往沦丧消失,地方(作为缺席者)还是界定了文化和认同。地方(作为现身者)也继续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4]西方许多城市开始创建“安全而富有吸引力的地方”,诸如都市文艺复兴等努力,都是为了使城市富有鲜明个性和迥异于“他地”的文化意象,突出城市能见度,进一步提升城市对外认知度、吸引力和竞争力,从而在全球化资本竞争中获得更好的生存和发展机会。
正因如此,“地方”这个原本小众的概念,近年来反而变得比以前更加重要。“这并不意味着地方的意义在社会生活中已经改变,而且在某些方面,这种影响的作用使得地方更显重要,而非无足轻重。这可能说明了过去十年左右,以‘地方’为标题的研究大量涌现体现的原因”。[3]
二、关于地方的理论
作为地理学的核心概念之一[5],地方的内涵实际上极为复杂且无所不包。早期区域地理学专注于地方差异性的描述,如文化区、文化景观等。地方(place)常常与区域(region)、地域(local)混同。这一对地方的理解直到现在仍然具有广泛的影响力。事实上,由于世界同质化的加剧,地方的差异性和独特性在全球化浪潮下的现代信息社会,较之从前更趋重要。不过,自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现代“地方”研究已经不满足于各个地方的特殊性的描述,而是透过地方差异性和独特性的表象,追求和探索其内在的经验和意义。譬如人本主义地理学开始关注地方作为一种概念、观念,在世存有(being)的方式,以及地方何以为地方的本质(essence),因而具有明显的哲学转向。其他诸如地方与实践的关系,地方的社会建构,资本、权力、政治等因素对地方的控制和改造,以及地方作为一种“边界”,如何影响各类细分人群(如年龄、性别、族群、社会阶层、生活方式等)的身份建构等,这些也都是现代“地方”研究比较关心的议题。正因如此,地方的概念,在差异性和独特性的表象之下,不仅关涉了哲学上的本体论和认识论,也深入联结社会理论和文化研究领域。
何谓地方?鉴于地方涵义的复杂性,这个定义并不容易界定。Tuan(1977)和Relph(1976)都试图透过与抽象空间的对比,来阐述地方的概念[1][6]。“空间似乎为地方提供了脉络,却从特殊地方来引申其意义”。也就是说,地方与空间的区别,在于地方赋予了空间以意义(meaning)。作为“有意义的空间”,Agnew(1987)提出地方的三个面向:区位;场所(社会关系的物质环境);地方感(情感依附)[7]。空间强调经济理性的抽象考察,地方则更偏重于主体性和经验。Tuan(1974)指出,人与地方之间的情感联系,即地方之爱(Tophilia),是地方作为“关照场域”(field of care)的基点[8]。透过人类的感知和经验,我们得以透过地方来认识世界。因而地方不仅是“权力脉络中被赋予空间意义的过程”,也是我们“观看、认识和经验世界的方式”之一[9]。Heidegger(1966)的地方哲学强调地方作为“充满意义的根基”对人类存在的意义,他用诗意的语言表述地方的重要性,“必须具有源自大地的根,才能在天空中开花结果”[10]。然则这种聚焦于乡村意象的理想化地方亦被认为是对全球化的一种退避。
以Harvey(1996)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女性主义者以及后结构主义者阐述了地方的社会建构理论,即地方是由(多重的)社会过程建构的,人类活动不仅建构了地方的物质性(materiality),也建构了地方的意义[3][11][12]。其中,Harvey尤为重视地方的权力政治和全球资本流动对地方形构过程的影响。在他的论述中,大量分析的是移动的资本与固著的地方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他认为,“时空压缩”和高度的移动性对地方的侵蚀,形成了一种来自地方的反抗,即所谓“战斗性的特殊主义”(寻求真实的地方感),地方因而被视为“集体记忆的所在”。不过,Harvey也承认地方的变动性,在他看来,地方是时空之流中依条件而定的“恒常”方式。无论多么坚实,始终都会“臣服于一直消逝中的时间”,并“随着创造、维持和崩解的过程而变化”[3]。
与Harvey的研究异曲同工,Seamon(1980)放弃了根基与真实性,从“身体的移动性”(bodily mobility)入手,通过观察“空间的日常移动”如何经由“时空惯例”(time-space routine)形成
所谓“地方芭蕾”(地方经验的隐喻),探讨地方是如何透过日常生活日复一日的操演出来[13]。Pred(1984)、de Certeau(1984)、Thrift(1996)等进一步发展了这种地方与实践的关系理论,指出地方实际上是一个“未完成的过程”,总是处于流变(becoming)之中[14][15][16]。因而,地方透过反复而持续的社会实践和操演,不断地被建造和重造。在这种意义下,地方不再是人本主义地理学所倡导的“根著于真实性观念的稳固存有论事物”[9],而是更为开放和变化的概念。正如Escobar(2001)所主张,“地方是以特殊的构造聚集了事物、思想和记忆”[17]。地方不仅在时间上处于未完成的过程,在空间上也并非是孤立的事物。地方关涉了联结[4]。地方与外界的联系亦是地方得以建构的因素之一。这种开放和流动为特征的地方观念,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获得进一步发挥。过去地方被视为“马赛克”式的各不相同的点,现在地方更被认可为“全球体系中的切换点或是跨越地方的网络中的节点”[18]。地方之间的联系与差异并存。Massey(1993)强调“与时俱进的地方感”[19],与Harvey聚焦于地方在“资本主义下的政治经济学”考量不同,Massey认为“正是地方的互动界定了地方的独特性”。所谓的“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20]或许正是传统地方与现代移动世界之间复杂关系的重新思考和再认识。
三、广州的地方性及其流变
城市的独特性和差异性,究其本质,离不开城市的历史积累以及长期演化所形成的文化性格。一座城市特有的文化是难以复制的,因为它与“地方”相伴相生,需要“天时地利人和”,故而,“地方”的文化特质才会构成城市的独特性和差异性。然而,地方是一个“未完成的过程”,始终处于流变之中,城市文化因此也并非一成不变,传承与创新必然相辅相成,历史的传统的文化唯有与时代的生活融为一体,才能代表城市文化的精神。
作为与中原文化大相径庭的岭南文化中心,广州拥有独具一格的城市发展史,地方的特质十分鲜明;作为经济发达的珠三角城市群的引领城市,长期的现代化进程和全球化的浸润,也使得广州的城市景观与国内其他大都市一样,表现出强烈的同质化和无地方性。近年来,广州提出建设世界文化名城的战略目标。然而,世界文化名城都有一个清晰的城市形象或者代表性的文化符号。如伦敦、巴黎等公认的世界文化名城,除了完备的公共文化服务和发达的文化产业等城市文化资本之外,其城市吸引力最重要的一环,是具有鲜明的个性和城市意象,而这恰恰来自于地方赋予城市空间的内涵和意义。由此,广州建设世界文化名城,也应回归地方的视角,构建(再建)属于本土和地方的独特性和差异性。在都市规划与建设中,以地方的眼光体察城市的演进和变化,藉由地方叙事的理解重新回归独特性和差异性的体验和关注,以此或许才能从根本上消解或摆脱“无地方性”对城市个性的侵蚀;并进而通过寻找、确立以及主动的培育最具有地方代表性的那些文化特质,逐步建立广州的城市文化性格和城市意象的能见度,拓展广州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和知名度,这样才有助于广州在未来的全球化竞争中获取更好的生存和发展。
具体而言,广州在两千多年的建城史中,一直保持着中西融合、兼容并蓄的文化心态,形成以高度的外生性和开放性为特色的商贸文化传统。这种历经两千年的地方形构所生成的商贸文化认同,尽管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存在种种变异,但就其内涵和意义仍然保持了历时而不衰的连续性、稳定性和传承性。以千年古港和商贸之都作为广州的地方独特性和差异性,创建“想象的地方”,重塑城市的共同记忆,以召唤城市应有的地方感和地方认同,或者可以成为广州建设世界文化名城的途径之一。
(一)地方根著于历史
地方是充满人类历史和记忆的特定空间。所以,地方的形成非一朝一夕之功。由此,找寻广州的地方性,应当回到城市的历史链条中进行分析。按照前述地方的社会建构理论,地方是由(多重的)社会进程所建构的。广州在两千年的发展史中,推动城市演进、影响地方形构的的因素可能有多个,但最重要的社会建构力量无疑是与经济活动紧密相关。偏处岭南一隅,远离中原政治文化中心,特殊的地理位置造成广州在历史上一直是一个政治力量薄弱,受中原正统文化影响较小,而本土文化自成一体的特殊区域。两千年长盛不衰的对外贸易港口功能,又使得广州不仅长期以来商贸经济发达,而且城市功能也呈现出集中和单一的特征。近代以前,广州是典型的以港兴市,几乎整个城市的运转都是围绕着港口贸易进行服务。
1.千年不衰的对外贸易大港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番禺(广州)就与山东半岛的转附(今芝罘)、琅琊,长江口的吴(今苏州)、会稽(今绍兴)、句章(今宁波),以及福建的冶(今福州)等并列为我国最早的港口。秦平百越后,赵佗在此建立南越国,是为广州建城之始,而这一城址历经千年至今仍为广州旧城中心。随后,汉武帝南征,将南越等割据小国纳入大汉版图,广州在《汉书地理志》的记载中,已经是“多犀角、象、毒冒(玳瑁)、珠玑、银、铜、果、布之凑”的全国九大都会之一。三国以后,交广分治,番禺(广州)成为岭南行政中心。汉代开辟的海上丝绸之路原本以合浦、徐闻为始发港,三国以后由于航海技术和造船技术的进步,南海航路有所变更,广州遂占据各种天时地利之便,一跃成为南海市舶贸易的中心和枢纽港。唐宋时期,广州作为全国第一大港的地位更加稳固。号称“雄蕃商之宝货,冠吴越之繁华”,据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中的考证,唐代的广州每年大约有八十万人进出参加贸易活动。又据毕仲衍《中书备对》的记录,宋神宗熙宁十年(1077年),明、杭、广州市舶司共收购乳香三十五万四千四十九斤,其中所收惟四千七百三十九斤,杭州所收惟六百三十七斤,而广州所收则有三十四万八千六百七十三斤,约占全国总额的98%以上。《宋会要辑稿·职官》记载,南宋高宗绍兴二年(1132年),广州提举市舶司表示,“广州自祖宗以来兴置市舶,收课入倍于他路”。元代的航海贸易更加开放和繁荣。尽管有泉州港异军突起,但广州港依然保持兴盛的态势。广州和泉州并列为当时最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泉州港在明代以后逐渐衰落,后为厦门港所取代;而广州即使在明代全国性的海禁和贸易萧条之时,仍然是全国唯一保持繁荣的对外贸易大港。康熙开海之后,全国成立粤、闽、浙、江四大海关,但唯有广州所在的粤海关才以对外贸易为主。早在17世纪初,外国商船就自发地集中于广州,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实行一口通商之后,广州名正言顺垄断全国对外贸易长达八十多年。1850年在世界城市经济十强中,广州名列第四,是当时世界级的大城市之一。作为两千年屹立不倒的东方大港,广州在我国的航海贸易史上堪称唯一。然而在现今的媒体宣传和城市意象的设计推广之中,广州作为港口和对外贸易的成就似乎只有清代十三行的历史片断得到了充分渲染,这一点与广州港在中国航海贸易史上的实际地位并不相称。
2.高度开放性和外生性的商贸文化
如前所述,地方的社会建构理论认为,社会进程不仅建构了地方的物质形态,也建构了地方的意义。对于广州来说,以港口为核心的商贸经济活动,是城市形态历史演进的主要推动力。由于港口贸易的繁荣,广州城在历史上的形态拓展主要是沿珠江一带作东西向延伸。尤其是清代以后广州西部十三行和外国商馆区的繁荣,导致原本为农田和池塘为主的西关地区迅速发展起来,并在晚清时期一跃成为广州经济、文化和人口分布的重心。这是地方景观形态受社会活动的力量所塑造的结果。从地方的内涵和意义上来说,广州作为千年不衰的对外贸易大港,也深刻影响了地方文化特质的生成,即直接塑造了广州特有的与开放多元的海洋文明息息相关的商贸文化特色。
借助于港口的“东风之便”,广州很早就与南洋诸国互有贸易往来。来自海外的舶来品经广州集散、中转进而运销全国各地。所以,早在秦汉时期,广州就是全国著名的商业都会。唐代时,航海贸易进入大繁荣大发展的阶段,广州作为第一大港,在此建立了全国也是历史上第一个市舶司,并在港口附近形成第一个外国商人聚居生活的“蕃坊”。所以说,广州的商贸文化不仅拥有悠久的传统,而且受港口对外贸易的影响,也表现出极为强烈的开放性和多元性。这尤其可以表现为广州对外来人口和外来文化的兼容并蓄。至少自唐代开始,广州就是十分国际化的商业港口城市,大量的阿拉伯商人、东南亚诸国的商人前来定居或从事进出口贸易。宋代广州的蕃坊成立了自己的蕃学、蕃市等附属设施,规模之庞大可推想而知。而在清中期以后,以十三行为中心的西关地区,表现出强烈的中西文化交融的特征,同时促生了各种新生事物并引领全国风潮。广州作为对外贸易的唯一窗口,也曾经一度成为全国商品的垄断性的集散地,商品种类极大丰富,商贸文化的繁荣也达到鼎盛。
总的来说,广州的商贸文化主要表现出两个特点。
第一,是商贸业的传统和发达程度。自秦汉至今,商贸业一直是广州城市经济活动的主要支撑点,历史堪称悠久;凭借对外贸易大港的优势,广州历史上商贸活动的繁荣也足以匹配“千年商都”的称号。千年古港和商贸之都共同构成一种对商贸文化的传承和认同。
第二,广州的商贸文化与外界的联系十分密切。可以说,正是与外界的互动奠定了广州的城市发展和进步,也催生了广州与中原正统文化差异明显的地方性。大批的广州人远渡重洋,大量的海外人士留居广州,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商旅客人在广州集散。与历史上大多数地方的封闭性和孤立性相比,广州作为地方特色的商贸文化具有高度的开放性和外生性。与中原的正统文化相比较,广州的地方文化在学术、思想等方面似乎优势不显,但以商业交换为准则、平等、包容、开放以及具有强烈外生性的商贸文化则体现得淋漓尽致。广州特有的人文风情、城市景观等,也都表现出平等、杂糅、散漫无序等与中原秩序井然的正统文化迥然不同的特点。这一点,恰恰也是广州在长期的港口发展中所形成的迥异于其他地方的城市独特性和差异性的最突出表现。
(二)地方处于流变之中
基于广州两千年的港口发展史,广州的地方性可以概括为千年古港和商贸之都两大特色,进而也可以将两者合并归结为一种对商贸文化的传承和认同。文化本身具有稳定性的特点。广州的商贸文化历经千年,随着港口和商贸经济活动的发展不断地被实践再实践,因而这种传统几乎可以说是根深蒂固。另一方面,地方并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概念,而是一个“未完成的过程”,始终处于流变之中。随着社会经济活动的变迁,地方的物质特征和内涵意义也都会不断的发生变化。这也是地方与空间最明显的差别,即空间是客观存在的,而地方因为充满了经验和意义,所以是一个动态的变量。由此可知,商贸文化作为广州地方性的体现,它也会随着城市政治、经济活动的变化,而在形式或方式上发生一定程度的改变。譬如,近代以后,随着上海和香港的异军突起,广州港的功能受到抑制,因而在全国对外贸易格局中的地位有所降低。因此,广州以港口贸易为主要特色的商贸文化虽然仍然保持了对外来文化尤其是西方新思想、新技术的引入和吸收,但在商业业态等方面就变得更加多样性和差异性。除了传统因贸易而衍生的各种商贸服务业,新的零售百货业、饮食娱乐业、报刊业等开始蓬勃发展。改革开放以后,大型购物中心、中心商务区(CBD)、总部经济、文化创意产业园、现代化影城、酒吧一条街等等属于现代化进程的产物,尽管与传统的商贸文化形态大为不同,但究其本质,这些都是广州商贸文化传统的延续。以开放、平等和包容为特色的商业文化精神依然支配着现代和当代广州的主要经济活动,并且深刻影响着广州的城市文化性格。只是这种地方性,在现代化和全球化力量的显性推动下,变得更加隐蔽和含蓄。
四、构建“想象的地方”
广州的商贸文化无疑具有深厚的历史基础和地方特色。只是在城市的现代化进程和全球化力量的强势推动下,这种地方性应如何得以更好的发挥和保留,以对抗世界同质化的侵蚀,展示广州的独特性和差异性,进而提升广州外在的城市魅力和城市吸引力,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MacCanell(1976)指出,现代性的最终胜利并非是非现代世界的消失,而是它的人为保存和重构[21]。从地方的经验来说,地方不可能重构,但是可以“再现”地方的记忆。由于大规模生产、大众传播和全球移动,地方正被破坏,变得“不真实”(Relph,1976)[1]。因此,地方的建构主要表现为一种“想象的地方”的建构,即主动地自觉地努力召唤地方感和往昔感。简单来说,就是基于地方的想象,再现那些可以展示“想象的历史”的事或物,从而构建有明确目的指向性的城市集体记忆,令本地居民从中找到地方归属感和情感依附,外来的游客则可以体验并进而欣赏、喜爱甚至流连于这种独特的地方感。这或者是建立地方差异性和独特性的有效方式之一。
从广州的案例来说,广州在港口贸易发展史上的辉煌成就,堪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然而在城市文化形象的宣传和推广中,广州的贸易大港形象仅仅局限于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地或津津乐道于近代的十三行,未免令人有“一叶障目不见森林”之感。作为千年不衰的对外贸易大港,广州的价值在于其连续性和传承性。从春秋战国最早的港口之一,到大唐盛世与阿拉伯帝国的远洋贸易,到宋元时代与世界140多个国家的通商往来,再到明清长期垄断全国对外贸易的一枝独秀,其历史之源远流长,文化积淀之深厚,远非扬州、泉州、上海、天津等某一断代时期的著名港口所能比拟。千年古港造就广州商贸的繁荣,也深刻影响了城市文化特质的生成,即直接塑造了广州特有的与开放多元的海洋文明息息相关的商贸文化特色。无论是历史还是现状,商贸文化都是广州最突出的文化特征。与其他商贸城市不同的是,广州的商贸文化背后,还隐藏着一段千年古港的辉煌故事,在这个故事中,长盛不衰的广州港具有全国的唯一性,并且长时间的与大海、风浪、冒险、传奇、异国情调等遥远而又新鲜的体验紧密联系,这些都与中原内地平稳的生活节奏大相径庭,因而都可以包装成为富有想象力和吸引力的文化要素。
因此,如何构建以千年古港和商贸之都为核心的地方想象,可以有两个方面的考量:
第一,依靠政府的力量建构“想象的地方”,建构具有共同记忆的城市文化空间。在具体的城市规划实践中可以体现为对于历史的“再现”,即以商贸文化认同为核心,围绕“港”和“商”字,整合现存的历史文化碎片,重构城市历史链条,通过多种多样的文化符号的表述再现记忆中“想象的地方”。譬如建立各种以港口和商贸文化为主题的博物馆、体验区,重点保护那些可以反映广州商贸文化特色的商业步行街、历史街区等。在传统的保护与开发并举的规划思路中,加入地方感的考量,包括如何在地方记忆中塑造城市整体的(而非零散的)商贸历史和文化脉络,并将其铭刻于适当的地景之中。凡是拥有悠久历史的世界文化名城,其城市风貌包括街道、建筑,甚至一草一木都可以蕴含历史的凝重和艺术的美感。广州也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但在城市空间上的文化表述仍显得模糊不清。除了重点的历史街区和文物保护单位,其他城市空间的利用显得杂乱无章。城市文化意象缺乏整体性和连续性,而且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也与现代的城市生活脱离开来,难免会有刻意和割裂之感。那些著名的历史古城如伦敦,巴黎,城市的历史叙事往往与平淡的城市日常生活交织在一起,所以显得更加随意、从容,具有真实感。所以广州构建一个“想象的地方”,首先就是要想方设法在商贸文化的核心理念之下,建立城市文化空间表述的连续性和整体性。林奇(Kevin Lynch,1960)在他的经典之作《城市意象》中提出城市意象五要素:道路、边界、区域、节点和标识,认为这五大要素的组合共同构成城市的形态和意义。城市意象应具有两层递进的含义,其一是指人们的潜意识中对城市的感觉和印象,此时的城市意象类似于城市的空间形态或视觉景观。其二则是指公众普遍认同的具有城市自身发展脉络痕迹的特征和特色。所以说,城市空间要素的组合,除了构建视觉景观,还应通过各种文化符号的表达来叙说历史,讲述那些“昔日的光荣与骄傲”,从而构建城市的共同记忆,强化地方认同。同时借助大众传播手段,以政府为主导,通过各种形式的宣传和诱导,保存和深化“场所精神”,即在一个不断更新的历史语境中如何将地方的本质更加具体化。重点塑造广州作为千年古港和商贸之都的城市意象,通过各种推销手段如广告片、宣传品、移动新媒体、网络平台等,深化和强化这种城市意象,形成公众耳熟能详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第二,在现代商业业态以及城市景观规划与设计中召唤地方感,进一步深化商贸文化认同。地方根著于历史,但不等同于历史。正如前面一再所强调的,地方是一个“未完成的过程”,它是一个不断处于动态变化的概念。正因如此,在旧城改造中政府应考虑的是如何保存和恢复地方的历史记忆,在现代城市新景观设计中更应强调的是如何在现代建筑景观中融入和谐一致的地方感,将新的商业业态与广州传统的商贸文化传统紧密融合在一起,从而创造具有新时代特征的独特性和差异性。如天河城、农林下、北京路、上下九等大型商业区或商业地带,其实已经形成了各自不同的购物特征和消费人群,所以其地方性的展现,不应是盲目的复古,而是需要进一步丰富其地方内涵和意义,加入地方情感的吸引。从城市的整体格局来说,广州是千年商贸之都,人流稠密,商业文化氛围浓厚,商业业态类型丰富,北京路、上下九、农林下以及天河城一带分布了从传统到现代,各种类型的商业街区和大型购物中心。从西到东,从旧城区到新城区,从传统文化的体验到现代文化的感知,广州的几大商业中心恰好可以与城市文化景观按历史序列(古代-近现代-当代)的展示相重叠。因此,现代商业、消费文化与历史商贸文化资源的混合开发,从千年历史到现代时尚,是广州先天具有的得天独厚的优势。以千年古港和商贸之都作为发展重点,充分彰显广州的商业文化特色,既延续了历史和传统,也符合时代发展的特征,从而也可以构成广州在新时代商贸文化发展的一种新的地方性,或者可以说是传统的“地方”的延续。故此,这同样也是建构“想象的地方”的方式之一。
[1]Relph E.Place and placelessness[M].London: Pion Limited, 1976.
[2]Hospers G-J.Creative Cities: Breeding Places in the Knowledge Economy[J].Knowledge, Technology, and policy, 2003,16(3), 143- 162.
[3]Harvey D.Justice, nature and the geography of difference [M].Cambridge, MA: Blacewell Publishers, 1996.
[4]Lippard L.The lure of the local: Senses of place in a multicultural society [M].New York: The New Press, 1997.
[5]Cresswell T.‘Place’.In P.Cloke et al.(eds) Introducing Human Geographies [M].London: Arnold, 1999.
[6]Tuan Yi-Fu.Space and place: The perspective of Experience [M].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77.
[7]Agnew J.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world economy [M].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8]TuanYi-Fu.Topophilia: A Study of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 attitudes, and values [M].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1974.
[9]Cressell T.Place: a short introduction [M].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2004.
[10]Heidegger M.Discourse on thinking [M].New York: HarperCollins, 1966.
[11]Clayton D.W.Islands of truth: the imperial fashioning of Vancouver Island [M].Vancouver: UBC Press, 2000.
[12]Till K.Neotraditional towns and urban villages: the cultural production of a geography of ‘otherness’ [J].Environmental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1993, 11(6): 709-732.
[13]Seamon D.Body-Subject, time-space routines, and place-ballets in Buttimer, A.and Seamon D.eds.The Human experience of space and place [M].London: Croom Helm, 1980.
[14]Pred A.R.Place as historically contingent process: Structuration and the time-geography of becoming places [J].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1984, 74(2):279-297.
[15]de Certeau M.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 [M].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16]Thrift N.J.Spatial formations [M].London: Sage, 1996.
[17]Escobar A.Culture sits in places: Reflections on globalism and Subaltern strategies of localization [J].Political Geography, 2001, 20(2): I39-174.
[18]Crang P.‘local-global’.In P.Cloke et al.(eds) Introducing Human Geographies [M].London: Arnold, 1999.
[19]Massey D.power geometry and a progressive sense of place.In J.Bird et al.(eds) Mapping the futures [M].London: Routledge, 1993.
[20]Swyngedouw E.The heart of a place [J].Geografisak Annaler, 1989, B71: 31-42.
[21]MacCannell D.The tourist: A new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 [M].New York: Schocken Books, 1976.
Constructing “An Imaginative Place”: Cultural Representation for Urban Spa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lace
Li Yan
With the world being increasingly homogenized, it is more important for a city today to think highly of the uniqueness and distinctness as a place in order to gain more attraction.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lace, how to construct “an imaginative place” based on urban development is a good way to participate in urban planning and urban construction.However, place is not a simple and distinct concept.It is very difficult to explain clearly what a place is.Generally it is acknowledged that place is rooted in history and it is not unchangeable.According to the social constructivist theory for place, the uniqueness and distinctness of place in the case of Guangzhou, is primarily shown as a sort of commercial culture constructed by economic activities of Guangzhou port during the past 2000 years.So constructing “an imaginative place” can be considered as a process to reflect this kind of commercial cultural tradition by many means of narrations on urban life and then arouse public memories and gain place identity.
place; uniqueness; urban space; Guangzhou
TU984
10.3969/j.issn.1674-7178.2014.04.021
李燕,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博士,研究方向:历史地理和文化地理。
(责任编辑:卢小文)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271164)“城市新文化空间的建构与消费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