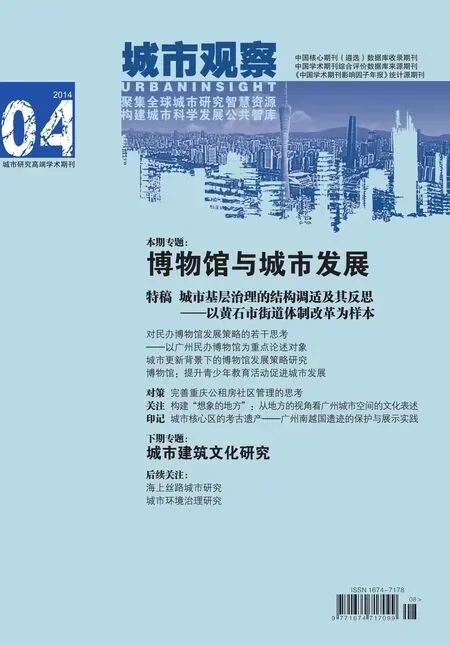探析“隧道效应”在社会治理中的应用
2014-03-28杜静元
◎ 杜静元
目前,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一直存在着“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状况,各社会阶层和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日趋明显,全国刑事犯罪、社会治安事件发生率居高不下,群体性事件频发易发,可以预期我国社会治理将长期面临新的形势和新的挑战。在这些挑战和问题面前,我们必须通过对我国社会治理状况的深入分析,深化对社会治理规律和特点的认识,从当前中国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深刻变革的背景出发,立足我国的历史传统和现实国情,找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治理体系应遵循的基本原则,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治理体制机制,提高社会治理的能力和水平。本文将“隧道效应”这一经济学的概念引入到社会治理的研究中来,分析“隧道效应”发生背后的文化逻辑,并从社会的角度来分析这种正的隧道效应是否可以持续,从一个较新的视角思考如何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得出妥善处理各种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的一些原则,进而从源头上防范社会风险。
一、何为“隧道效应”
1973年美国经济学家赫希曼和罗思奇尔德发表了一篇名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对收入不平等的不同忍耐力”的文章,首先提出了“隧道效应”[1](Tunnel Effect)的说法, 它是指由于其他人的经济条件改善而导致个人效用增加(或者说由于预期的影响个人对更大的、更高的不平等程度的忍耐)。这个提法源于他们俩看到的一个生活中的小经验,假如你开车进入一个双车道的隧道,而且都向同一个方向行驶,这时遇到交通阻塞的情况,两条车道上的车都无法行驶。但是,过了一会儿,你发现右车道上的车开始缓缓移动,而你是在左车道上,这时你的感觉是更好还是更坏呢?赫希曼和罗思奇尔德认为这取决于右车道上的车会移动多久。开始时你会想,前方的交通阻塞情况已经结束了,要轮到你可以开始移动了。所以即使你现在还没有开始移动,你的心情也会好很多。但是,如果右车道的车一直往前走,但左车道的车一直没有要移动的迹象,那么你很快就会变得沮丧,甚至会想办法插入右车道。如果有很多人用这种方法的话,堵车情况将会变得越来越糟糕。
根据这个经验,赫希曼和罗思奇尔德解释了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人们对于收入不平等的忍耐问题,他们认为个人的福利不仅取决于他现在的满意程度,而且取决于它预期的未来的满意程度。如果在他周围的一些人的经济或社会地位得到了显著的改善,他对于这些改善的反应将取决于这些改善对于他自己未来前景的预期。如果他相信,其他人的好运也意味着将来自己的前景会更好,那么其他的人相对收入增加不会是这个人感到更糟糕,赫希曼和罗思奇尔德就把由于其他人的经济地位改善而导致的个人效用增加称为隧道效应。
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如果这种隧道效应能发生或持续,对于社会的稳定将是一件好事。根据赫希曼和罗思奇尔德所描述的隧道效应,我们用中文来理解的话可以表示为一种正的隧道效应,即在一条车道上处于堵车的人看到另一条车道上的车开始移动后的第一阶段,在行驶较慢或没有移动的车道人的心态是乐观的。而到了第二阶段,如果在左车道的人一直不动,而在右车道的车一直往前走,那么左车道的人就会沮丧甚至要想办法插入右车道。我们将这种由于其他人境况的改善而导致个人效用减少的情况称为负的隧道效应。这样作为同在隧道中的车,正的隧道效应和负的隧道效应都会存在。下面过渡到人类学所关注的问题,与发展经济学所不同的是,经济学家仅将这种隧道效应应用到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如何影响经济发展的问题,即如果该国的社会隧道效应是呈现负的趋势(也就是对不平等程度的忍耐力低),那么“先增长后分配”的战略就不可能成功。“即使最开始阶段的隧道效应很强,如果统治集团和政策制定者对于随时间变化而不断减小的这种效应不敏感的话,也可能阻碍经济发展的过程。”[2]而笔者所要关注的是这种隧道效应为什么能在一个社会中产生,其背后的文化逻辑在哪,研究了这一点我们就能体会到在不同的文化中隧道效应是不同的。对于社会而言,这种正的隧道效应是否可以持续,通过举例我们来评价在社会组织中这种效应产生后对社会组织所造成的影响问题。首先我们来谈在中国社会中隧道效应背后隐藏的文化逻辑是什么。
二、隧道效应背后的文化逻辑
用隧道效应来比喻人们对于不平等程度的忍耐力的差异几乎完全是经验主义的,而这种提法对于我们认识社会中对于收入分配不平等以及社会制度的不对等所造成的差异和矛盾是有意义的。社会发展作为一个动态的过程,这种忍耐力的变化是需要社会学者密切关注的,而这种忍耐力与这个国家或社会的文化密切相关。
传统社会中,中国人的自我是受中国传统文化深深影响的自我,其内涵与西方的自我具有很大的差异性。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儒、释、道三家对自我人格的影响最为深远。
(一)儒家文化中包含的隧道效应背后的文化逻辑
儒家从关系本位的自我出发, 强调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相处,而达到和谐的方法在于“克己复礼”, 克己是为了确立道德主体,复礼是为了维护社会秩序。从个人角度讲,在德行和品格上要实现“克己”,在事业和行为上要实现“复礼”。 透过这样克己的功夫, 将社会的规范通过“礼”内化在“自己”之中,这也就是所谓的“克己复礼为仁”。“礼的主要目的在于约制人的私欲, 使之合乎情境的要求, 个体不能按照自己的情感、愿望来做事, 而要按照社会伦理道德,依当时的情境, 按道德和情境所指定的合理合宜的行为来做事。”[3]这其中就包含着对不平等现象的忍耐力。
另外,从中国人的集体观念的角度讲,儒家文化中蕴含的“推己及人”和家、国、天下之心也是包含着对不平等现象的忍耐力,因为儒家的终极关怀在于建立和谐的社会秩序。儒家的不同之处在于求在人之心性中完成我,“人有两大限:人我之限,生死之限。人生所有痛苦皆从这两大限生。释迦牟尼曰无我涅槃,耶稣曰上帝天堂,大旨意在逃避此生之有限,为儒家主张在此有限人生中觅出路,求解脱。怎样做到的呢?曰:“身量有限,而心量则无限”,人当从自然生命转入心灵生命,即获超出此有限,解脱痛苦。对于生死之限,中国人不想涅槃,不想天堂,也不想在生前尽量发展个人自由与现世快乐。而是想死后留名,活在别人心中。对于人我之限,孔子提倡心走向心以求解脱,此便也是孔子所谓的仁的一部分。中国的五伦人生观中,全体从个体上可以看见。我为父而慈,即表现了全体为人父之慈。孝慈对我而言,似乎是一个其他人的心,但是从人同此心的类心性而言,是个全体心,孔子曰心之仁,孟子曰性之善,皆由个别心来发现总体心,人必成伦作对,在此中将心比心,融成一心。从心走向心会感到她是自己的同类,是自己的相知,因此他是自己的乐土。这样一人之心,化成了一家之心,一家之心化成了一国之心,一国之心化成了天下之心。心和宇宙和合为一,也和万物和合为一了。”[4]怀着这样的集体主义胸襟自然能在不平等的社会现象中处于正的隧道效应的阶段。相信别人的境况和整体的境况改善后自己的境况也会改善。
(二)佛教中包含的隧道效应背后的文化逻辑
佛教传入中国以后,曾与中国原有的传统思想发生激烈的碰撞和争论, 后来经过融合之后产生了理论上的修正,开始沿着中国文化轨迹演变、适应及发展。 从而形成了中国本土的佛教理论和宗派,禅宗融合儒、道两家学说, 强调“梵我合一”的世界观, “明心见性”的当下顿悟, 及“以心传心” 的直观认识,这对中国人的性格有着深远的影响。[5]佛家认为众生要从有限存在的凡夫众生变为无限存在的大解脱者。众生的忧悲苦恼和生老病死, 均由于对人世幻景的贪求、嗔拒和无智慧, 人们被幻景所左右, 以至于身陷于幻景的有限之中, 因此要遵循一定的方法让众生从幻景之中走出来。于是,佛家认为在修身过程中强调通过“苦、集、灭、道”的四圣谛法灭除贪欲、无知和妄念, 以证得真理, 使自己具有智慧, 并觉悟本性。这种悟禅的方法虽然不是民众普遍所用,但是其思想广为传播,对于增加人们对不平等的忍耐力亦有帮助。
(三)道家文化中包含的隧道效应背后的文化逻辑
老子说:“夫唯不争, 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在民间便有了“吃亏就是占便宜”的说法,这种视弱为强、视输为赢的认知思考模式成为苦难或不平等的社会中求生存的处世智慧。明恩溥(Arthur H.Smith,1894)所写的《中国人的气质》中所描述的:“中国人的忍耐力在于毫不抱怨、泰然若素地忍受痛苦的能力。”[6]此外,他更深刻的看到这种忍耐力源于中国历史上所积累下来的保守观念,他说:“中国社会的保守观念也渗入全体民众,源远流长,任何对命运不满的实际表现都会受到压制。因此,他们自然感到不幸,但他们认为不幸是不可避免的……中国人的忍耐和勤劳都是面对不幸必须的选择,如果能赋予一种知足的气质,就会维护和平安定的社会秩序。”[6]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其实也经常听到“吃亏是福”、“知足常乐”的句子,显然这种认知方式在今天仍然起着调节生活中的不平等的作用,使得中国人“忍”的能力大大地增加,使这种正的隧道效应得以持续。由此可见,邓小平同志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的战略眼光不仅考虑了经济政治的因素也同时考虑到了文化上人民的承受力。
(四)隧道效应背后的中西方文化机制的对比
隧道效应所反映的这种心理现象,并不为中国人所独有,而是人类所共有的一种心理现象。但是西方价值体系强调“个人主义”,每个人皆可以依凭自我的自由意志追寻幸福,所以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忍”即他们所谓的“自我控制”是与中国的忍截然不同的。在西方心理学界第一个谈到自我控制理论的是弗洛伊德(S.Freud),他的自我控制理论认为,自我(ego)根据现实原则调和本我(id)和超我(superego)之间的冲突。西方另一较有代表性的自我控制理论是由社会认知心理学家克莱尔·考普(Claire Kopp)提出的,他认为自我控制是个体自我意识发展到一定程度所体现的功能,是个体一种内在能力,外在表现为一组相关行为,是个体自主调节自己行为使其与个人价值和社会期望相适应的能力。自我控制引发或制止特定的行为,主要包括五个方面:即抑制冲动行为、抵制诱惑、延缓满足、制定和完成行为计划、采取适应于社会情景的行为方式。他从社会认知角度,侧重于研究个体对外部行为的控制。[7]
但是,中国与西方心理学所讨论的心理控制却有几点不同:首先,西方的心理控制更强调个人利益的满足,属于个人主义的。而中国人所表现出的忍的心理历程却不仅是为了个人的利益着想,更是为他人、为公众,属于一种社会取向的表现。其次,中国的“忍”的心理状态不仅包含克制,还包括坚韧、容受和退让等成分,在忍的过程中,个体不仅仅要延缓个人需要,还可能会放弃个人需要来让予他人,要做到这些必须要靠改变自己的认知和情性来容受外部的压力和挫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忍不仅是中国人应对外部压力的策略,也是中国人自我修养和社会化的一种手段。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隧道效应所反映的是一个国家或社会的文化,中国人对别人状况改善的忍耐力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体系中对人的设计及强调人伦、讲究关系的社会结构,中国传统文化中表现出的隧道效应里坚信在别人状况好转后自己状况也会好转的心态既有具有儒家自我修养和自我超越的色彩,同时也具有道家和佛家出世和超脱的色彩,强调的是无我和天人合一的境界。
三、在从传统到现代的社会过渡中正的隧道效应何以持续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对中国的影响日渐加深,西方强调自由民主和个人主义的文化也使得传统文化下对有利于隧道效应发生的心理状态开始变得不被推崇,如安·兰德的《源泉》里所言,成功和功成名就没什么关系,成功就是一个人捍卫自己的完整性,道德只能建立在个体理性的基础上,它的基础不应该是任何宗教、情感、社会、国家、阶级以及任何形式的集体。这不是一个在“传统”和“现代”之间的审美选择,这甚至不仅仅是一个在勇气和懦弱之间的人格考验,这是在人的存在与虚无之间作出的选择。[8]尽管受西方个人主义的影响,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文化传统已经深植在每个人的心中,中国人而言隧道效应的发生更多的是中国人自我修养和社会化的一种手段,而不是否认自我的明证。“忍”的文化逻辑也依然被人们无形地化于行动之中。然而,诚如开始时所提到的,这种正的隧道效应在中国社会中是否可以持续呢?
首先,中国人知足的气质对于维护和平安定的社会秩序是一种很有用的长效心理机制,有利于维持这种正的隧道效应,刚才我们讨论这种隧道效应背后的文化机制也在起作用。
其次,随着互联网等新媒体的发展,人们的交往方式和国家治理方式的转变,使得隧道效应的发生成为可能。其实,不论是能否接受新媒体的人还是整天面对新媒体的人,对于所有中国人而言有一个很好的发泄方式,明恩溥早以他在中国40多年生活的经验告诉我们,中国最主要的享乐之一是同别人聊天,这种在谈话中对人类社会的品评,大大减轻了中国人所遭受的许多痛苦。[6]中国人对于戏剧的钟爱也反映出对这种发泄的需要。在现实无法改变的情况下,人们在戏剧中寻找放松和理想,或是找到同情和同病相怜之感,所以戏剧在中国流行至今。通过新媒体时代中网络电视、电影的流行就可以看到人们对于新的交流方式的喜爱。此外,今天在中国,博客、微博、空间、微信等网络聊天工具的盛行都可以反映出这种聊天方式的扩展和需求的增大。与此同时,网络问政的流行也代表了政府让人民群众参与国家治理的决心。从单向管理向党委、政府、社会组织、人民群众多元共治转变,是现代国家治理的重要特征。网络问政作为一种便捷有效的沟通方式和协作方式,为政府和群众搭建了桥梁,为群众有序参与国家治理提供了渠道。以上这些都有助于正的隧道效应的发生。
再次,正的隧道效应表现出的是一种社会宽容,它不仅仅表现在个人的道德和精神层面,更重要的是表现在社会结构、社会秩序和社会控制等方面。保持社会结构和社会秩序的适当弹性是正的隧道效应参与社会运行的一个重要应用,通过正的隧道效应我们可以减少社会矛盾、减少人们对现行社会秩序的抵制,这并非是对“侵害者”的纵容,而是在社会平等的语境下,拓展社会结构和社会秩序的一种有效方式,他并不是将社会矛盾搁置以来,而是在彼此竞争中宽容,强调平等主体之间彼此的给予性。
莱博若(Takie Sugiyama Lebra)指出:“每个文化都提供一种机制,这个机制能将由均衡与不均衡间相互制约而产生的社会紧张限制在一个界限内。”比如对于中国的腐败问题,对于送礼者和受礼者的忍受就超出了我们的想象,这是因为存在着传统文化中某些机制使人们对这些社会不公平变得可以理解和接受。比如,送礼者在等级背景中的不利位置被中国文化中的主导观念平衡过来,即对于这种送礼现象在中国文化背景中被认为是可以接受的,如道家的“柔弱不争”和儒家提倡的“礼”以及传统社会特征中的关系取向、特殊主义,都是对这种不均衡现象的自我平衡方法。而且传统社会中,中国人是产出取向对政策和制度是接受的态度,不像西方社会是自我取向和投入取向,积极参与政治。所以这种文化机制可以提高人们对社会的忍耐度。
但是,在看到传统文化对隧道效应起作用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这种隧道效应的动态发展过程,在文化机制作用的一定界限外,隧道效应将表现出负的方向,如何在正负效应临界点之前调整好社会矛盾是我们所应该进一步研究的课题。
此外,除了对于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忍受,我们往往还忽略了制度的不平等或者说不对等的问题。对于中国这个多民族且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国家来说,我们应该注意到在不同的社会组织中这种隧道效应产生后对社会组织所造成的影响问题。下面就举一个关于现代环境保护制度在喜马拉雅山村如何实施的例子,来说明在这种隧道效应的影响下必须将强加的体制变为当地人自我调试之后的体制才能被当地社会所接受的事实。
四、隧道效应在村落改造中的一个应用
前面我们提到除了收入的不平等,还包括了制度的不对等也会带来隧道效应。在这样的情况下,制度不对等带来的隧道效应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样简单,这是因为走在慢车道的人有时并不会觉得自己想进入快车道,反而,在快车道的人想让慢车道的人进入快车道。因此,我们说这种隧道效应是反向的。对于存在进化论思想的人来说,存在着先进的和落后的制度的概念,因此,当先进制度下的人看到落后制度下的社区的生活时,会有一种改造的心态。我们说这类似在快车道行驶的人对于慢车道行驶的人有一种反向的隧道效应,他们愿意去给慢车道的人强加他们的先进制度,而慢车道的人是如何反应的呢?我们来看看下面这个例子。
在位于喜马拉雅山的半山腰的舍帕族人村庄,名为纳姆切巴扎鲁,这个美丽的村庄因首次登上珠穆朗玛峰的埃德蒙·希拉里而闻名。为了报答那些帮助他登上珠峰的舍帕族人,他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为他们铺设了用水系统、建造桥梁、修建学校和医院。除此之外,为了运送建筑材料,还在村旁兴修了机场。而这一切的村落开发带来的结果可想而知,随着交通的便利,登山客的激增,燃料需求不断增加,周边的森林就成为天然的燃料,无一幸免。这样的乱砍滥伐,将有可能导致舍帕族人社会的崩溃和全人类最宝贵的自然资源的消失。于是,希拉里向新西兰政府寻求帮助,1976年,在新西兰政府的财政援助下,尼泊尔政府在此成立了地方国家公园。从此,村民们像过去那样自由砍树和放牧都不被允许了。地方社会管理森林资源的智慧在被开发后变得很难让外地人识别,而取而代之的是外地人认为的科学管理体系。这种看似“正确”的观念和制度在纳帕人中得到贯彻了吗?其实,很容易想到,并没有那么容易。就像我们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改变自己的任何习惯一样,纳帕人用他们的智慧来曲线地抵制这种所谓的科学管理。比如,根据国家公园规定,限定每个村民一生可以砍伐的树木为三棵,在此之上是被严格禁止的。但是这连每日基本的燃料供给都不能满足。这项规定在保护人类共同财产的名义下“强加”给当地村民。这种以前再合理不过的砍伐现在变成了违法,村民们为了生计也难以接受,所以“聪明”的人们想出了各种规则外的方法来实现自己的目的。例如他们利用准许采集枯木的规定,先将树木劈开,等其自然枯萎后就可以按规定采伐了。如果想要三棵以上的树木,可以找外来人帮忙砍伐丢掉,再去让他们捡来。由此可见,对于所谓“科学制度”的迷信该到此为止了,应该看到制度的制定者是人,制度的破坏者也是人,所以对于谙熟于当地生活环境的村民来说,外来人无论怎样制定规章制度,他们依然可以有办法去规避。而这种环境保护的目的反而在强迫的状态下很难实现。如果不能在村民自发的接受和学习状态下让他们接受新的制度,那制度的作用其实不会真正体现。
在一个地方社会中,那些没有逻辑化、体系化的“非科学”事物,不能证明其不合理。如希拉里对喜马拉雅山的小山村所进行的先开发后保护的过程中,他逐渐发现地方性知识中已经包含的对保护地方环境的力量。而且在这种地方性知识中也包含了保护地方社会的力量。这恰能弥补单纯的自然生态学所不能顾及的,即人作为环境的一部分在自然生态系统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自然生态学认为,人类不加以干涉的自然是最理想的状态,因此出现了希拉里要推行地方国家森林公园的计划。而此计划并没有将人在自然系统中所起到的作用予以足够的重视。他们对于这个地方的管理体系并不是一个有效的融于社会的环境保护机制。他们所推行的管理思想和在此思想指导下的条例和管理办法对于当地居民是一种“强加”的灌输。于是出现了我们在上面看到的当地人对于这些规章制度的种种对策。但是我们且看看他们是怎样保护当地环境的,虽然他们违背了这些规定但是他们并没有乱砍乱伐,而是早已在当地社会形成了一种看管体系,来维持地方生活的同时达到保护水、森林和耕地等资源的目的。
在经济学领域,由于有了“交易成本”和产权的概念,新制度经济学把经济学引向了更社会化的方向。正如科斯所说:“现代制度经济学应该研究现实中的人,即将人置于真实制度的约束之内。”[9]制度是“非正式约束”(风俗、文化、禁忌等)和“正式约束”(法律、产权等)的总和。人类学就为人们对这种“非正式约束”的了解和理解提供了一种途径和方法。他并不像一些社会调查一样,只把一个问题从整个生活中剥离出来,再加以逻辑性整理,而是从一个整体的调查中得出一个直观的看法,然后再加以分析。
如果能结合人类学的调查方法,对于社区或者社会组织的历史和实际需要进行调查,通过经验式的体验来推动社区或组织中的成员的学习,那么将必然减少由于将“这种自有的制约机制无保留地转换成一元化的高效体系所产生的问题。”[10]这也是属于本文所提出的“隧道效应”产生的问题之一。
这种经验式的体验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人类行为的结果及将来行为的可能性,其行动的根源在于以往积累的经验,我们要以此为依据进行分析。保罗·康纳顿(Paul Connerton)在《社会如何记忆》中写到:“我们对现在的体验,大多取决于我们对过去的了解;我们有关过去的形象,通常服务于现存社会秩序的合法化。”[11]这句话有两层含义,其一是强调对过去的了解的重要性,即我们所说的经验的重要性,其二是强调过去的经验如何服务于现存社会秩序,即强调过去经验在当代社会的适应性问题。我们应当看到对于社区或社会组织的“强加”制度,明白这种“强加”源于调查者往往只看到这个社区的表面的选择,却看不到其背后的其他选择,因为我们没有深入他们的生活世界,比如当取得了社区成员的信任之后围绕一个社会问题,像水利工程、祭祀或者特殊的经历,让他们讲述自己的故事,体会他们生活中蕴含的选择的智慧,这样制度和价值这一类问题才能在这样有包容性的回忆性的话题中显现出来。
因此,我们可以总结出以下的结论,在一个社区中,无论是开发还是保护,都是外来的或施加给他们的产物。对于这种来自外部的强制力,村民们有时无视他们,依然遵循着自己的生活方式。他们根据长年以来构筑的自我环保体系,缓冲行之过甚的开发路线,智慧地在法律规则中游走,同时修正保护路线对生活的忽视。由此我们看到是一个从“强加”体制到自我调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虽然我们意识到现代制度的进入已成为不可逆的历史进程,但是,我们应该在进入的方法上进行调试,对于当地社会的运行逻辑予以重视、对民间的社会治理智慧予以理解,这样才能在制度不对等的情况下完成对于隧道效应的把握,从而获得对于由此产生的社会问题的解决途径。
[1]Hirschman, Albert O. and Michael Rothschild. 1973. “The Changing Tolerance for Income Inequality in the Cours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87.4: 544-566.
[2][美国]德布拉吉·瑞.发展经济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3]杨国枢,陆洛.中国人的自我:心理学的分析[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9.
[4]钱穆.人生十论[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
[5]葛鲁嘉.本土心性心理学对人格心理的独特探索[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43(6).
[6]Arthur H. Smith.1894. Chinese characteristics[M]. New York: Fleming H. Revell Company Press.
[7]陈萍.中国人尚忍心态的心理学研究[D].南京师范大学,2006.
[8]刘瑜.送你一颗子弹[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0.
[9]科斯.企业、市场与法律[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0.
[10]古川彰.向地方性知识学习的方法[A].王静爱,[日]小长谷有纪,色音主编.地理环境与民俗文化遗产[C].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
[11]保罗·康纳顿著;纳日碧力戈译.社会如何记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