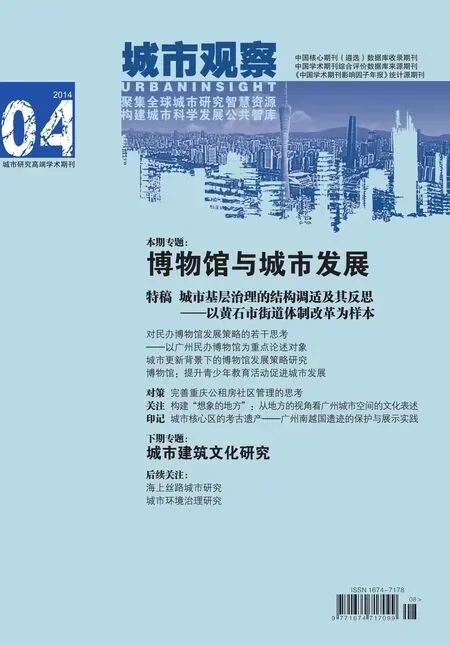伦敦都市圈及其管理体制的发展演变及特点
2014-03-28◎王涛
◎ 王 涛
伦敦都市圈是当今四大都市圈之一,其含义大致可以分为三种标准,即行政建成区,功能区和城市聚集区。本文所讨论的伦敦都市圈指的是麦特绿带以内的区域,面积约为1600平方公里,人口约800万。该都市圈表现为三层圈层结构,核心为伦敦金融城,内圈为伦敦城外的12个自治市,其余20个自治市构成伦敦都市圈的外圈。对伦敦都市圈及其管理体制发展与演化的研究将有助于加深对都市圈本质及其治理的理解。
一、伦敦都市圈的形成与演变
伦敦最早来自于古罗马建立的伦敦城。公元43年罗马人登陆英国以后最初的统治中心在科尔切斯特。直到公元49年,罗马人为方便自己的统治,在泰晤士河畔距离出海口很近的地方建立了一座新城即伦敦作为自己的统治中心,便捷的交通使伦敦自建立之初便是连接欧洲大陆与英伦三岛的桥梁,为其以后成为贸易与工业中心奠定了良好基础。公元2世纪“罗马和平”结束之后,不列颠陷入了混乱的局面,迫使罗马人在伦敦建起了长约3.2公里的城墙保护自己,这座城墙便成为了伦敦城的边界,直到今天,这座城墙依然是伦敦城的边界。
伦敦城在罗马人统治时期就已经超过科尔切斯特成为英国最大的城市并在此后一直维持着这一地位直到今天。但是随着古罗马陷入混乱和帝国的崩溃,整个欧洲陷入了动荡的局面,城市的扩张受到了限制。伦敦也是如此,伦敦墙建立后一千余年,伦敦只是固守在伦敦墙内没有向外扩展。但随着欧洲新的经济扩张来临,英伦三岛与欧洲大陆的经济联系变得更加密切,这使14世纪初以后,伦敦开始了自己的扩张。这种扩张与商人取得伦敦的统治地位是密切相关。在英国与法国,王权为了削弱与之对抗的封建贵族的挑战,中央权力与地方权力形成了暂时性的联合,城市自治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产生的。[1],P271在12世纪时,通过一系列的特许状,伦敦获得了包括市民人身自由、司法权、包税权、独立贸易权以及管理自身事务的一系列权力,成为自治城市。[2],P5-7凭借国王的权力与优越的地理位置,伦敦的商人不但控制了国内贸易,而且垄断了国际贸易。16、17世纪英格兰最主要的出口商品是呢绒,伦敦的出口量一般占到全英国输出量的60%~85%,1568-1569年甚至达到了93%。[3],P39此后,随着呢绒贸易地位的日益降低,伦敦商人也日益将其重点转向新兴贸易,维持了其在英格兰进出口贸易中的垄断地位,1699-1701年,伦敦控制了62.5%的本国产品出口以及84%的转口贸易和80%的进口。[4],P202由于看到从海外贸易中可以获得的巨大利益,伦敦商人成为英国海外扩张过程中最重要的力量,伦敦商人资助了很多冒险家的探险,其它地区的商人希望探险时,也往往寻找伦敦的商人作为投资者。1694年,英格兰银行的建立是一个具有标志意义的历史事件,它不仅标示着现代金融体系的建立,政府与私人机构都可以通过现代金融体系更方便的融资[5],P14,更是标志着伦敦成为英国乃至世界的金融中心。
政治中心、商业贸易中心与金融中心的地位带动了工业中心地位的形成。伴随着英国海外贸易自16世纪开始的扩张,对呢绒与船只的需求量都出现了上升,与此同时,圈地运动造成的大批失去土地的农民涌入伦敦城郊,为扩大的呢绒与造船工业提供了充足的廉价劳动力,将伦敦变成了工业革命前英国的工业中心。1700年,在伦敦大约有20万人从事制造业活动,他们大多集中在伦敦的东郊。
伴随着伦敦成为英国的政治中心、商业贸易中心、金融中心和工业中心,伦敦的人口在此时期也经历了迅速的扩张。1500年,伦敦的人口仅为5万左右,1550年增加到10万人左右,半个世纪翻了一番。1600年又增加到20万人左右,1650年达到40万人左右,1700年增加到57.5万人左右。在人口绝对数量上升的同时,伦敦占全国人口的比例也在持续上升,1650年伦敦占全英格兰人口的7%,到世纪末,这个比例上升到11%。[6],P44-45迅速的人口扩张使伦敦的人口数量从16世纪初的欧洲的第六位变成了17世纪末的第一位,其城市首位度也由16世纪初的3变为20。[7],P18-19而且此时伦敦也已初步形成了都市圈结构,威斯敏斯特是政治中心,伦敦城是金融中心,而伦敦西郊则主要发展商业以及面向王公贵族和上层商人的奢侈品工业,伦敦东郊与北郊则主要是造船及呢绒等工业。这种圈层格局虽历经变化,但是其基本结构并未出现重大改变。
18世纪中叶开始的工业革命使英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城市化国家,1851年,英国人口城市化率已经达到54%,1901年达到77%,此后城市化率稳定在76%~79%。伦敦虽然并非工业革命的中心,其城市首位度在工业革命中有所下降,但是凭借贸易与金融中心的地位,伦敦的人口仍然迅速增加,1801年,伦敦人口达到101万,此后平均每年以2.14%的速度增长,直至1939年达到历史峰值891万人。此后在逆城市化力的作用下,伦敦的人口出现了下降,在1981年降到历史最低值661万。此后,则又恢复了缓慢增长的态势,并于2011年重新达到817万人。[8]伴随着伦敦不断扩张的是其地域面积的不断增大,由古罗马时期一个不足一平方公里的城市变为今日以绿带环绕的面积1600平方公里的大都市区,并且有进一步蔓延的趋势。
从伦敦都市圈的发展与演化过程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伦敦的发展与其优越的地理位置以及很早就成为政治与经济中心密切相关,原始的优势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得到了不断强化,使伦敦围绕伦敦城及威斯敏斯特两个核心区域不断向外扩张,形成大都市的圈层结构。
二、伦敦都市圈管理体制的发展与演变
伦敦虽然是在逐渐向外扩张的,但是其治理在很长时间内是分散的。虽然自13世纪以后,伦敦的城区已经逐步扩展到伦敦城墙以外,但是伦敦城的居民并不愿意将城外的区域纳入自己的范围。直到1394年,城外的法灵顿区才作为一个独立的区被纳入伦敦城的管理,成为城内24区以外的第25区。又过了一百余年,1550年,才将泰晤士河南岸久已存在经济联系的大城区纳入管理作为第26个区。这使伦敦虽然在地理范围上不断扩张,但是其管理仍然是分散的,伦敦城与郊区之间互不干预,各地区实行充分的自治。这也体现了英国各地域自治的传统。
伦敦这种分散自治管理模式与前现代社会并不需要提供庞大的基础设施密切相关。但是随着城市的迅猛发展,一系列的城市病也暴露出来,大量涌入城市的人口缺乏基本的居住与生活条件,造成了犯罪率上升、传染病流行等一系列问题,城市成为了坟墓而不是生活的乐园。[9]这种局面要求政府转变自己的职能,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以改善城市的生活状况。但是这种要求与伦敦的自治传统形成了冲突,各个地区不愿意放弃自己的权力,结果只能是继续实行自治的模式,各地区提供本区域内的公共产品与服务。但是公共产品具有不可分性与规模经济的特点,如果各区域单独提供本区域内的公共产品,必然造成公共产品与服务的供给成本过高,因而这就从本质上要求必须产生一个覆盖全伦敦区域的政府协调公共物品的提供。由于各区域不愿意放弃权力,首先产生的并不一个政府但是却具有政府管理性质的机构,即1829年成立的伦敦警察局,在当时全伦敦范围内提供治安服务。随后,为了统筹规划全伦敦的污水处理问题,1848年成立了下水道委员会,由其全面负责伦敦范围内的污水处理问题。这个机构实际上已经具备了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的政府职能。此后,随着需要提供的公共产品与服务的日益增多,更多地职能与权力实际上已经归属于该机构。1855年,为了适应增长的公共服务的需要,下水道委员会变更为都市工作委员会也表明了在伦敦范围内权力机构出现的必要性。但伦敦都市工作委员会只是一个雏形,其权力仍然很小,不足以协调全伦敦范围内的事务。这促使了1888年《地方政府法案》的颁布,该法案废除了“都市工作委员会”,决定成立伦敦郡,由伦敦居民直接选举郡议会以处理本地区事务。但是作为实际权力机构,伦敦郡将极大削弱已有自治团体的权力与利益,因而遭到了他们的激烈反对。这场激烈的冲突直到1899年才以《伦敦政府法案》的出台而暂告一段落。1900年正式进行了改革,废除了教区,该为自治市,给予伦敦郡议会以更大的权力。在各自治市将一部分权力交给伦敦郡之后,伦敦地区的双层政府管理体制初步形成,奠定了伦敦都市圈的管理框架。
伦敦都市圈的管理体制虽然已经初步确立,但是双层政府间的分工与合作仍然存在着问题。各自治市仅仅是将部分权力交给伦敦郡,由伦敦郡对大伦敦地区的公共产品与服务进行协调,但是两级政府间并不存在隶属关系,如何划分相互之间的权限是两者矛盾的焦点。为此,伦敦郡成立了大量的委员会对此问题做出分析。结果是出台了法案,决定通过建立大伦敦议会及合并自治单位减少相互之间的摩擦。1965年,大伦敦议会成立,并且将原有的85个市镇减少为32个市镇。这项改革由于减少了自治市的数量,使每一个自治市提供公共物品与服务的范围得以扩大,在某种程度上解决了公共物品与服务提供范围过小的问题,但是也造成了扩大后的自治市权力增强,使大伦敦议会的权力受到抑制,不能够充分发挥其规划与协调作用。
1986年,在保守党执政期间,为了减少政府干预,实现经济自由化的目标,英国政府解散了大伦敦议会,由32个自治市各自处理本区域内的事务。这种变革虽然确实减少了管理层级,有利于各自治市根据自己的情况提供本区域内的公共产品与服务,而不必陷入到如何分配权力的无休止争论当中。但是对于此时已经连为一体的大伦敦地区来说,跨自治市的公共设施与服务要求各自治市之间必须相互协调与磋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自治市之间成立了很多联合组织,而且民间也成立了很多盈利与非盈利机构提供跨自治市的公共产品与服务。结果导致的是伦敦拥有数量众多的各种机构,竟然使伦敦市民无法弄清楚究竟是谁在提供公共服务。纷繁复杂的公共机构提供相互重叠的公共设施与服务效率低下,使伦敦作为一个国际城市的竞争力出现了下滑。[10]保守党执政时期伦敦混乱的管理也更加从反面证明了有实施统一管理的必要性。因而1997年工党重新执政后,便力图建立一个统一的伦敦市政管理当局。1999年,伦敦的全民公决也显示了伦敦居民对一个统一的管理机构的热切期盼。2000年伦敦大都市管理局成立,管理局包括市长和议会。其中市长的主要职责就是对伦敦进行总体上的规划,而各区级政府则主要执行伦敦市长规划的本区域内的事务。虽然大伦敦当局的权力相对于其他都市圈政府来说仍然是有限的,但是显然它已经超越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的伦敦政府,这本身也表明了现代都市圈需要一个与都市圈地域范围相适应的政府对都市圈统一做出发展规划并有权力执行它。
可见,伦敦都市圈的管理体制经历了由前现代的分散治理模式到现代的双层治理模式的转变,虽然各地域均不愿意放弃自己的权力,但是现代城市发展需要总体规划以及更大区域内公共产品与服务的提供也使各自治区域更多放弃自己手中的权力,将其交给大都市区一级的管理机构。
三、私人资本在伦敦都市圈发展中的作用演变
伦敦的发展过程中很长一段时间里是没有统一的政府管理组织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伦敦严重缺乏公共设施与服务。交通即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二战以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伦敦交通体系发展的模式都是由英国议会将某项交通服务的特许权颁布给某家公司或某几家公司,由他们来负责伦敦公共交通。这种模式促进了伦敦交通运输体系随着城市的扩张而不断扩张。18世纪中叶以后,伴随着与美洲、亚洲贸易的迅速扩张,伦敦的港口资源显得非常不足,在这样的背景下,1799-1823年兴起了私人资本投资于码头扩建工程的热潮,满足了伦敦日益增长的海外贸易的需求。随着国内贸易的扩张,与内地的联系加强了,私人又开始积极投资于泰晤士河上的运输服务,1830年在泰晤士河上就出现了私人运营的固定航班。在市内交通上,伦敦同样是由私人运营的出租马车承担的。在1807年,伦敦就已经拥有了大约1000辆领有牌照的出租马车。此后,由于公共马车的出现,对出租马车形成了挑战,伦敦又通过法案,允许公共马车的竞争。私人竞争提供了方便的市内交通。随着伦敦的进一步扩大以及地面交通的日益拥挤,1854年英国议会同意了伦敦铁路公司修建地铁的请求。1863年1月,世界上第一条地铁线在伦敦开通。此后,大量私人资本涌入这个领域,并将其线路连接在一起,至20世纪初就已经完全在私人资本投资下拥有了一个相对完善的城市地铁系统。[11]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伦敦对私人资本的投资运营是放任自由的,如果触动了了公共利益,英国中央政府与伦敦当局将会对私人资本做出限制。1841年,由于私人竞争日益将铁路线延伸至市中心破坏了市中心的古建筑,因而英国议会做出决议,禁止私人资本在市中心设立火车站。19世纪中期,为了满足日益增多的贫穷工人的出行要求,伦敦开行了廉价的工人列车。1883年英国议会通过了《廉价列车法案》,要求私人铁路公司必须经营工人列车。[11]随着城市的日益扩大,私人营运交通的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主要是完全以赢利为目的的私人运营的线路与城市交通日益增长的公共属性相矛盾,主要表现在(1)私人线路过多集中在人口密集地区,不能够满足城市边远地区的出行要求;(2)私人线路票价偏高,难以满足普通中下等居民的出行要求;(3)私人线路受到经济周期的影响较大,难以保障实现稳定的交通服务。这些矛盾迫使英国政府与伦敦政府日益增加伦敦交通的公共属性。早在19世纪中期,英国议会即通过了法令,要求伦敦的私人交通公司提供廉价车票给每天往返的工人。二战以后,伦敦又成立了伦敦乘客交通委员会负责制定伦敦交通规划,并且将私人交通公司收归该委员会,为市民提供廉价、便捷的公共交通。即使如此,伦敦并非将所有私人交通公司收归市政所有,相反,对一些赢利性的项目,仍由私人公司继续运营,这样一方面可以减少大规模投资公共交通所带来的财政压力,也可以防止公有企业运营中的低效率问题出现。
四、小结
伦敦都市圈的形成与发展呈现了典型的“结核扩张”模式,即首先形成作为扩张内核的政治中心威斯敏斯特与贸易、金融中心伦敦城,然后围绕核心不断向外呈圈层结构的扩张。虽然伦敦很早就向外扩张,但伦敦的管理体制直到19世纪之前一直是区域自治的模式,跨区域的公共产品与服务的提供主要依赖私人资本。随着城市对公共产品与服务需求的增加,伦敦也日益形成了“双层政府管理体制”,虽然几经起伏,但是大伦敦都市区政府的权力得到逐渐强化,从而保证了可以从整体上规划伦敦都市圈的发展。
从伦敦都市圈的发展过程中可以得出对我国首都经济圈的启示包括:(1)都市圈的形成与扩张必须具有内核;(2)现代都市圈在管理体制上应该由都市圈政府作出总体规划;(3)现代都市圈公共产品与服务的提供仍然需要发挥私人资本的作用。
[1][美]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M].宋俊岭,倪文彦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
[2]吴江艳.中世纪伦敦城市自治探析[D].河北大学硕士论文,2011.
[3]Ramsay.G.D. The English Woollen Industry,1500-1700.London,1982.
[4]Clay,C.A. Economic Expansion and Social Change:England,1500-1700,Cambridge,1990.
[5] [瑞士]尤瑟夫·凯西斯.资本之都——国际金融中心变迁史(1780-2009)[M].陈晗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6] Wrigley.A Simple Model of London;’s Importance in Changing English Society and Economy 1650-1750,Past and Present,No37.(Jul,1967).
[7]任传永.论16-17世纪伦敦的成长[D],天津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0.
[8]毛新雅,彭希哲.伦敦都市区与城市群人口城市化的空间路径及其启示[J].北京社会科学,2013(4).
[9]李冈原.英国城市病及其整治探析——兼谈英国城市化模式[J].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2003(6).
[10]马祖琦.伦敦大都市管理体制研究评述[J].城市问题,2006(8).
[11]张卫良.“交通革命”:伦敦现代城市交通体系的发展[J].史学月刊,20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