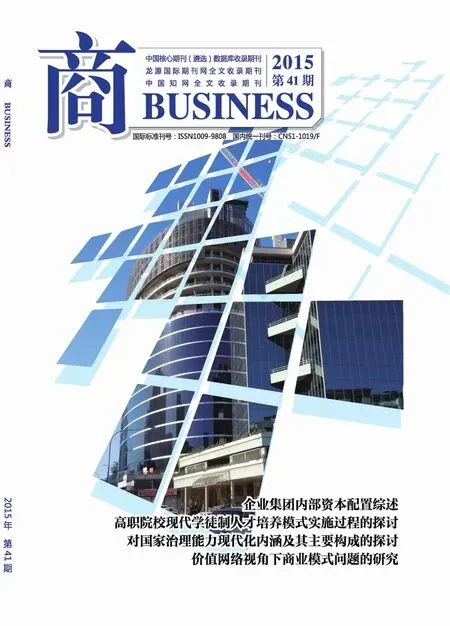对中国“法律信仰论”的思考
2014-03-26王高峰
王高峰
摘要:部分学者引用伯尔曼关于法律与宗教关系的论断,转向信仰领域解决法律的意义问题,虽然使法律权威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承认,但冷静思索近些年中国“法律信仰论”的指涉,可以发现其对“法律信仰”概念上理解的偏差及局限:对传统和历史的割裂、单一的建构路径及重新流入法律工具主义的潜流的倾向。
关键词:信仰;法律信仰
自梁治平将伯尔曼的系列演讲集《法律与宗教》翻译介绍之后,“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这句话便蜚声中国法学界,随着社会的进步、学者们对“法律信仰论”的命题也开始出现了极大的争论。
一、理解何谓“法律信仰”
反对“法律信仰论”的呼声如同在沸水中投入了冰块,一时间法律能不能信仰,值不值得信仰就成为了大家争论的话题。综合各方的意见,本文作者认为首先应当对“信仰”这一概念进行界定,在此基础上才能对法律信仰以综合性判断其可能。
宗教学学者史密斯在《宗教的意义与终结》一书中认为 “宗教”这一混杂的意指可以被分为“信仰”和“累积的传统”两种进路进行理解,它们分别代表了人宗教生活的内在和外在方面。信仰是一个个体,或者许多个个体,与神圣的超验者的关系;无论后者被看作是人格性的还是非人格性的,是宽厚的还是苛求的。这种意义上的信仰包括有宗教经验、对神圣既敬又畏的宗教情感、希望和恐惧、崇拜的意向以及愿意事奉于更高的实在与价值的意愿。
我国宪法规定中国人有信仰宗教的自由,即信仰作为宗教中“超然”的部分必然是自由的,而在信仰之外,被组织化的宗教组织因为其社会性所以应当受到法律的规定,这也为宗教界中呼吁为“宗教立法”的观点提供了根据。在理解了“信仰”的所指之后,“法律信仰”这一名词应当被理解为“个人对法律能够成为自身主宰的虔诚,在此,法律的作用能够是一种本体论,也可以是一种世界观,法律在此和宗教一样,是自身及他者的原因”。在社会现实中,法律因其“工具性”当然不能成为有效的“信仰”,但对个体而言,信仰何种事物都是“合法”,这也是人的有限和人的自由的题中之义,但涉及到社会群体,“信仰”因其个体性就丧失了“合法性”,因为此时的“信仰”就会成为“认同”而丧失其“合法性”,必然会受到社会团体,尤其是政治团体的规定。因此在谈“法律信仰”时,应当分析其意指“群体”还是“个体”,从中国法律信仰论者的现实情况而言,均指其群体性,这本身就是对概念适用的混淆。
二、中国法律信仰论的局限
1.罔顾伯尔曼对历史和传统的尊重,割断法律与历史和传统的联系
在中国的法律信仰论者看来,要在中国树立法律信仰,首要的就是必须拒斥历史和传统。中国法律信仰生成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对中国历史和文化传统的否弃①。制度和文化的“自我更新”往往需要一定程度的物质发展及“遥远又真切”的建构模板,因此自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对国家和制度的反思是被动而仓促的,在这个过程中,对国家和制度的设想基本是现实的参考,从英国到美国再到苏俄,急于寻找救世良方的知识分子将中国落后的原因统统归咎于“旧社会”,也即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传统,更有甚者,在中国部分学者看来,中国传统儒家意识形态支配下的传统法律文化与现代法治完全相互抵牾。随着改革开放后中国物质环境的发达,人民日益对“有尊严地活着”的需求越来越高,作为现代文明的代表“法治”越来越受到重视,但正是由于对中国传统的主流负面认识,中国的法律信仰论者开始向生产现代法治的“原产地”,寻找其精神和价值源头,法律信仰论由此转向了一种“文化移植论”,显然“文化移植论”在具有重大的缺陷的:一方面,“文化移植论”明显带有“唯意志论”的倾向,充满了理性的狂妄。另一方面,这种思维方式也超出了伯尔曼对法律的原有认识范畴。伯尔曼在《法律与宗教》一书中开头就申明自己是一种“综合的”观点,他试图重新建立法律与历史以及其他因素的外部联系,而“文化移植论”所假定的法律规则试图切割掉这一外部联系。法律信仰与传统的割裂,导致对法律信仰的讨论只能被人为地限定在一个狭小的话题内,仅仅局限在谈“法律如果能被信仰会有多大的功能性”的问题,从现实角度来看,这种尝试对于社会现实的反应是消极的,这也是为什么“法律信仰”没能形成系统理论的一个重要原因。
2.单一进路的“建构中”的法律观与伯尔曼“整体的”法律观的冲突
对于“法”而言,西方的“law”用一个字涵盖了自然法,人为法,宗教法等等,且“应然”和“实然”二者是相通或相近的。事实的现象和有价值判断的人创造出来的规则,都可称为“law”,法的生命在于社会现实而非理性,因此法律必定与其他的社会规范发生联系,这既可以是自由和人权,也可能是天理人情、更可能是市场经济秩序的要求等等,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所以法律能与宗教发生联系,因此伯尔曼才能强调其“整体的、演进的”法律观,在他那里,西方世界的法律与整个西方的文明传统联系在一起,这种西方文明发展出了独特的关于法律的制度、价值和概念。这些西方的法律制度、价值和概念被有意识地世代相传数个世纪,由此形成一种传统。中国古代的传统法律如果能被认为是法律,这种法律也一定与中国社会的道德、政治理想等规范联系在一起。反观中国的法律信仰论者的简单建构观,实质上低估了法律与其他中国当代社会规范之间的联系,尤其是中国社会的强组织力量——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理想,实质上,这种建构中的法律观的参考坐标仅仅对准了“中国人理想中的西方法律”,由于不能从文化和传统中汲取力量,只能借助于强化突出主体的建构,即表现出对打造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浓厚兴趣。
3.法律工具主义的抬头
在伯尔曼看来,一种法的社会理论依照它对法律定义的分析应当强调精神和物质、观念和经验之间的互动作用,反对当时盛行于西方社会中的实证主义法律观。实证主义法律观,按照伯尔曼的解读,正是西方法律危机的根源。中国的法律信仰论,其理论抱负使它必然采取一种国家主义策略,由国家来推动一种自上而下的普法模式走向法律信仰论与国家主义的结合,使得其在制度层面的设计、实施以及权力技术的推行。其次,二者的合流还体现在它们对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共同信奉上。法律职业共同体本质上源出于法律实证主义关于“法律自主性的主张”,在对一个封闭的自治的法律职业共同体所抱持的人为理性的强调下任何历史的、道德的和社会的因素都成了法律无须考虑的“局外因素”,中国法律信仰论者因其孤立的、建构中的法律观是完全接受封闭的法律职业共同体这一主张的,同时,它也能够借助这一法律职业共同体实现对共同体以外的“局外人”的普法。在很大程度上,不仅法律是一种工具,法律信仰也可以被理解为是一件用来贯彻特定政治、经济和社会政策的精心制作的工具。中国法律信仰论者主张法律信仰,首先的考虑不是因为有了法律信仰层面的东西会使得法治会变得更“好”而是法治会因此变得更为“有效”。从根本上而言,法律信仰论的着眼点正是工具主义的出发点,而这正与伯尔曼苦心思索的“综合的”法律观相左。(作者单位: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
参考文献:
[1]哈罗德·J·伯尔曼著,梁冶平译《法律与宗教》[M],中国政法出版社,2002。
[2]威尔弗雷德·坎特韦尔·史密斯著,董江阳译。《宗教的意义与终结》[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3]金观涛、刘青峰著,《开放中的变迁:再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系统》[M],法律出版社,2010.
[4]刘小平、杨金丹,中国法律信仰论的内在悖论及其超越[J],法商研究
注解:
①刘小平、杨金丹,中国法律信仰论的内在悖论及其超越[J],法商研究,p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