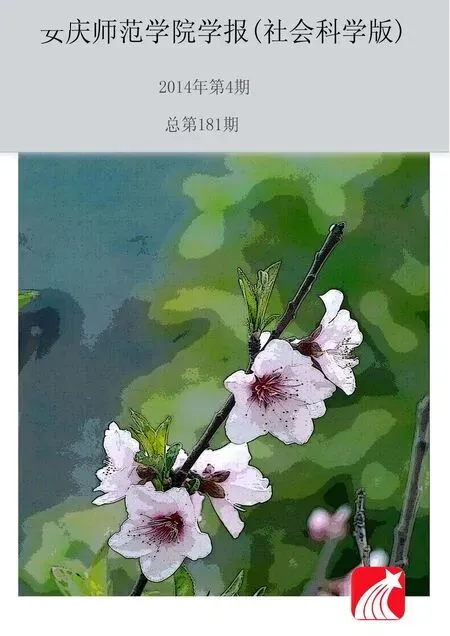德育有效性
——语义分析和语用阐释
2014-03-21胡心红
胡 心 红
(合肥职业技术学院, 安徽 巢湖 238000)
德育有效性
——语义分析和语用阐释
胡 心 红
(合肥职业技术学院, 安徽 巢湖 238000)
德育有效性本质上是一种对象之于人的价值关系,必须联系主体及其尺度来理解。语义分析由“效”的文字学溯源开始,“效”有三个名词性用法:效用、效率、效果。而在语用层面,德育决策者基于国家立场和阶级意志,追求德育的效用价值,要求德育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培养有用人才;德育教育者要秉持绩效主义观念,执着于德育的效率,以期快速、高效地培养人才;德育受教育者则从鲜活的个体感受、体验出发,对德育有效性有着独特的理解和阐释,吁求真正的德育效果的诞生。
德育有效性;语义分析;语用阐释;效用;效率;效果
有人说,天底下最难的事是“把自己的思想装进别人的脑袋”。道德教育被认为是“五育”中最难取得成效的“一育”,德育不是简单的“道德知识”灌输,而是一项关系学生作为“人”能否“立”得起来的伟大事业。现实中,学校道德教育的低效成为一个广受诟病、且难以破解的教育与社会难题[1]。德育有效性问题一直是德育领域研究的重要课题。通过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检索发现,2004年以来共发表论文1 283篇,近五年共发表论文937篇,近三年则每年都超过200篇,其中,2011年212篇,2012年217篇,2013年210篇。为增强德育的实效性,学者们纷纷“把脉开方”,分析低效(失效)原因,提出增效对策。
毫无疑问,无论是诠释德育有效性的研究者,还是处理德育有效性的实践者,“有效性”概念都是他们学术研究的逻辑起点和学理前提,尽管常常以“预设”的形式存在。研究者往往以下定义的方式来界说“有效性”。
毋庸讳言,德育有效性研究对“有效性”一词的使用是频繁而基始的,但其结果却是杂乱而粗浅的。一方面,学界对“有效性”的使用长期缺乏一个统一而恰当的界定。一些文献从德育决策者的角度来定义有效性,突出其意识形态性(党性)。一些文献从德育实施者(教育者)的角度定义有效性,突出其知识性(理性)。另一些文献则从受教育者的角度定义有效性,强调其可接受性。更多的文献则对“有效性”术语采取了缺乏分析的模糊使用。另一方面,学界对“有效性”范畴既有的分析建构又颇显滞后。多数情况中,人们看到的是未加辨析和定义下对“有效性”一词的直接使用。研究者对“有效性”有意无意地“模糊化”处理,直接影响有效性范畴的科学建构,强化了相关学术研究中的“对话障碍”和“认同危机”。
诚然,有效性作为人们试图把握的对象,并非如直观的物理现象那样,可以由我们在学理上作出非此即彼的严格判定[2]。迄今为止,学界对有效性的定义,存在语义阐释和对象指称的多种差异与分歧,蕴含了诸多源自语言方面的风险和纰漏。J.D.贝尔纳告诫我们,给一概念下“什么是什么”的定义是很“刻板的”事情,可能有使精神实质“被阉割”的危险[3]。语言学方法没有给我们提供一个“有效性”的确切定义,而是为德育有效性的理解和阐释增添一个新视角、新方法,为我们“接近”“有效性”提供一个新路径。
一、德育有效性的语义分析:何为“效”
诠释“有效性”( effectiveness或validity)的关键是抓住它的内核“效”字。“效”是一个会意兼形声的字。甲骨文写作“”,其左边是一个两腿相交,正面站立的人。右边是一只手,手里拿着一根木棍类的东西,正在扑打左边的人。右偏旁后来演变成“攴”(pū),“攴,小击也”。“效,象也,从攴交声”(汉·许慎:《说文解字·攴部》)。段玉裁注曰:“象当作像。像,似也”。(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所以,“效”是“模仿”、“学习”的意思,“效”字的本义是“效法”或“仿效”(动词性用法)。后来又引申为“效果”,也就是“效法”“仿效”的结果如何(名词性用法)。从词源上看,“效”字和“教”字还具有高度的“互文性”。“教”的甲骨文写法:,左下边是“子”(小孩),上边是两个叉,象征被鞭打的符号。古人还说过“教,效也。”(汉·刘熙:《释名·释言语》)“教,上所施下所效也”(《说文解字·攴部》)。[4]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初步看出,在古人那里,“效”和“教”是密不可分的,都和教育、学习相关;“效”或“教”既有动词性用法,也有名词性用法,必须联系行为后果来考察其完整的意义;从偏旁也可看出,教育需要适当的惩戒。
显然,所谓“有效”是相对的,有效是相对低效或无效而言的。与德育有效性相关,本文将重点考察“效”的名词性用法。在德育有效性的论域内,这个“效”字大致可归纳为三种解释:效用、效率、效果。
(一)效用(一般译作utility或usefulness)
效用主要是一个经济学概念,是指由客观资源的有用性而引起、获得的满足程度。效用的概念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客观资源的有用性,即资源的使用价值;二是指客观资源满足人类期望、需要的主观感受和评价。前义可称为客观主义解释,后义可称为主观主义解释。
(二)效率(一般译作efficiency)和效果(一般译作effectiveness)
“效率”和“效果”两词意义相近,人们甚至一些研究者也经常将其混用,包括一些词典,如《现代英汉综合大词典》“efficiency”词条解释为:效率;效能;实力,生产力;功率;产量;有效作用等。“effectiveness”词条解释为效率;效能;效果;有效性等。可以看出,它们之间存在“意义错综”,但是它们之间还是有意义差别的。
在组织行为学或管理学中,“effectiveness”又被译作“效能”。组织行为学家罗宾斯说过,效能是目标的达成,而效率是为达到目标的投入与实际产出之比值。[5]管理大师德鲁克曾简要指出:“效率是‘以正确的方式做事’,而效能则是‘做正确的事’”。[6]“正确地做事”与“做正确的事”有着本质的区别。“正确地做事”强调的是效率,突出“快”和“多”,以使我们更快地达至目标;“做正确的事”强调的则是效能或效果,突出“好”和“对”,确保我们坚定地朝向自己的目标迈进。两者的价值尺度也有根本区别,前者以“正确”为尺度,后者以“正当”为准星。“正确地做事”是以“做正确的事”为前提的,如果失去这个前提,“正确地做事”将发生“异化”,变成“不是它自己”,甚至导致“越正确就越错误”。首先要“做正确的事”,然后才存在“正确地做事”。[7]
总之,效率注重的是投入、产出或者输入、输出之间的关系,是经两点(起点和终点)对比得出的。而效能或效果则是动态的,注重过程及目标达成的。达到目标才是最终的追求,而高效只是通向目标的必要方式。也可以说,效率是达成效能或效果的手段。[8]
二、德育有效性的语用阐释:谁之“效”
一般来说,词语作为人的认识对象,可分为两个层次:一个是语义层次,即该概念本身的意义指向;另一个是语用层次,关联该概念的使用者、解释者。“前者揭示的是范畴的实际指称对象,后者则表达着范畴使用者的意图。”[9]有效性,就其本质而言指的不是对象本身的存在性状或事实关系,而是对象之于人的价值关系,性质上是一种关系范畴,指的是主客体之间一种需求与满足的关系。
德育有效性本质上是人们对德育属性及其对人的意义的感受、体验、认知和评判。对于同一客体对象,不同主体因其地位、需求甚至利益的差异而产生不同的感受和评判。德育主体是多元的,在德育领域,主要有三类主体,即德育决策者、德育教育者、德育受教育者。三类主体对于德育具有不同的“期待视野”,相应地,他们对德育的要求及自身所获得的满足程度就各有不同,因此,他们关于德育有效性的认知也就具有差异性。
(一)德育决策者的有效性——效用的追求
德育决策者是指德育方针政策的制定者、德育内容(教材)的提供者。维护阶级利益,表达阶级诉求,反映国家意志和意识形态导向,是决策者对德育认知的基本视角和立场。考察德育的两个范式及其转换可以看出它的脉络:
1.政治教育范式。新中国成立直至改革开放前,我国的德育总体上属于政治教育范式。德育方针政策、目标任务的制定遵循这样的信念和假设:德育在本质上属于上层建筑,德育是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工具,德育从根本上讲是政治教育。教学内容(教材)承载着过多的政治教育意义和隐喻。
更有甚者,政治教育功能“泛化”为整个教育的功能,或者说,德育的功能“窄化”为政治教育功能。
2.绩效主义范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结束了“政治挂帅”的政治化时代,进入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经济化(现代化)时代。随着社会转型,整个教育研究开始出现范式转换,这种转换首先表现在对教育本质属性的重新认识、教育功能的重新定位上。“教育属于社会生产力范畴,具有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功能”,“教育的功能在于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培养高素质的人才”[10]。随之在教育研究领域形成了绩效主义范式,教育领域也充斥着“教育GDP主义”。“教育研究的绩效主义范式确立了‘知识教育观’以及教育是通过知识传授来培养人才的前提假设。”一方面,德育研究范式无法逃离教育研究范式的规训,德育领域充斥着“知识化”倾向,教学论、课程论都是关于知识论的,注重学生在认知领域的发展。另一方面,德育领域也提出了“适应论”,以期主动适应大规模经济建设和市场化改革的需要,进行“道德转型”和“道德重建”[11]。
总之,无论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还是“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其理论基础都是政治决定论和经济决定论。德育的学术信念则变成“社会适应论”。德育在其中都是“不独立的”、“为他的”,人们关注的是德育的工具价值。在决策者那里,有效主要就是有“效用”,有效性就是有用性,是否有用以及用处多寡就是有效性的尺度。
(二)德育教育者的有效性——效率的执着
教育过程是教育政策的具体化过程。教育者作为教育政策意图的领会者和主要执行者,主导着德育有效性的生成过程。在这里,一方面是受教师绩效考核制度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找到了一个方便的偷懒办法, 教育者成了德育“绩效主义”的坚定实践者。教育者将“效率”(以考分作指标)当作主要价值目标来追求。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1.德育课程化。人们认为,德育应该有自己的专门课程、专门课堂和专门时间,以期像现代化工厂那样大规模地、高效地生产出统一规格的产品。“德育课程化”规定德育有自己专门的课堂、专门的时间,德育需在专门的时间(上课)、空间(课堂)内进行“专修”,以期单独完成德育任务。
诚然,德育课程的单独开设可以让学生系统地学习道德知识,发展道德认知能力。但这种“专修”偏重于对道德知识的介绍和传授,并非严格意义上的“道德教育”,只能算是“关于道德的教育”[12]。
2.课程知识化。为便于教师传授和学生学习,德育内容受到“知识化”、“科学化”改造。教材模拟科学技术知识教育的定理、公理、公式等认知图式,变成道德知识、行为规范的知识点教育。德育遵循“科学认知的逻辑”,丰富的道德内涵被缩略为定义概念、功能意义,“知识德育”将道德缩减为逻辑严密的知识体系,甚至进一步浓缩为知识点。
这样的教学内容虽然便于记诵,但却使最具“自由”品性的德育内容“被肢解、分裂为单向度的‘碎片化’课程现象,并将其绝对化、唯一化”[13]。
3.教学灌输化。“绩效主义”德育以追求德育的功利化、高效化为目标,这种情况下最为简便易行的教学方式莫过于灌输式教学。灌输教学走一条“纯粹理性”路线,仅在“纯粹理性”的意义上宣示道德文本和预设行为规则,使学生单纯接受“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的现成结论和“什么是可以做的”、“什么是不可以做的”的既定规范[14]。
当然,我们不能否认灌输所具有的教育意义,因为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讲,任何教育都不可避免地包含着大量的灌输因素,教育就是一种灌输,社会的存在和发展都有赖于此。我们所要克服的正是“宽泛意义上”“灌输”理论留下的障碍。泛泛的“灌输”论恰恰忽视了生活、体验、交往、表达的方法论意义,剥夺了对象的主体性。
4.测评考试化。为检验“灌输”之效果(效率),书面考试是最简便的测评方法,分数则是评判的唯一标尺(外在指标)。只要学生按照教材回答问题,即被认为合格,学习道德就是“道德应用题”的解答。背诵强记道德知识以应付考试,就成为学生的当然选择。学生学习道德的动力不是来自于主体的内在需要,而是来自于外在的考试压力,因而是强制性的。
考试固然是一个“相对公平”的“不坏”的评价方法,用之于德育,却可能使德育沦为“记诵之学”、“考试之学”。曾任清华校长的曹云祥指出:“所谓教育并非专事诵读记忆而已。是欲养成高尚完全之人格,为立足社会之准备。否则,教育失其本质。”南宋学者罗点曾说:“仁义之效迟,功利之效速;人情厌迟而喜速,所以舍彼而取此。然久而后成者,又不可以遽坏;旦暮可获者,不足以久安。”(南宋·袁燮:《絜斋集》卷一二《罗公行状》)
(三)德育受教育者的有效性——效果的吁求
受教育者是德育的对象,也是德育效果的最终承载者和体现者。作为德育目的的实现形式——德育效果,或者说是在受教育者身上“涌现”出来的有效性。“效果”作为德育目的,最初只是主观性的存在,即德育所要创造的未来对象只是一种观念性的、本身并非实存的东西。效果必须通过人的对象性活动——教育活动,才能扬弃自己的主观性,达到主观和客观的统一,从而实现由概念规定的“效果”。在目的的实现过程中,手段是把目的的主观性与客观性结合起来的桥梁和中介。如此看来,作为实现效果的手段、途径的效用、效率、效能等,只是通向效果之路的“桥”和“梯”。
朱熹说:“德者得之谓也,得之于心而守之不失”[15]。从受教育者角度来说,德育是“为己之学”,有效性是“为己之物”。受教育者才是有效性的真正主体。受教育者理解的德育有效性——“效果”大致有三个层次(或曰三个尺度):
1.表层次是悦纳,即对象乐意接受道德教育或者说在德育过程中体验到愉悦。这种愉悦不是简单的快乐,而是指向身心灵和谐发展的“完满”和“幸福”。人在德育活动中,与主体外的东西不再处于对立状态,外部世界没有了冷漠和陌生的面孔。主体获得了快乐的源泉,在德育活动中“享受”,从而摆脱了控制心灵的羁绊,使心灵发生新的变化,体验到一种新的自由感。[16]在德育过程中主体若被唤醒并自我生成、自我建构,德育效果才会被主体“理解”并“接受”。
德育应该经得起受教育者的追问:“我为什么要接受你的教育?”“你的教育对我有什么好处?”
2.中层次体现在德育过程中获得一个全新的“世界图景”和“自我观照”,即关于世界和自我的“双重建构”。主体一方面在德育活动中发现一个迥异于日常生活世界的全新世界,他不再遭受日常经验的束缚压迫,重新找到心灵解放——如释重负的感觉。另一方面,主体意识被唤醒,可独立地对道德事件作出自己的道德评判和道德选择,他在其中拥有道德价值的独立自主性,坚持自己在本质直观中所形成的本真解释。通过自我观照,实现自我确证,即主体的自我建构、自我实现。
3.高层次是指主体的超越和解放,是自由的“高峰体验”,是知识、生活、生命的“深刻共鸣”。道德的深层体验是对自己和世界重新审视和批判的感悟,是超越现实对自身存在价值的反思。可以说,这种道德经验是一种全新的感受方式和体验方式,它克服了精神世界的浮躁、迷茫、幽暗和荒芜,使人性从日常生活的麻痹萎靡和习惯偏见中解放出来。不仅解放了人的生活经验,而且解放了人的内在经验和对世界所抱持的价值信念,即臻于“至善”之境。
道德的自由感和超越性功能,对于人生具有“赋值”和“寓意”功能,正因为有道德,人才有“人之为人”的价值可言,这个世界才有意义可言。正是通过道德经验,使庸常生活发生净化,产生一种新质。道德是帮助每个人“成为他自己”,因而,在这个意义上,道德是“人的解放的车轮”。
总而言之,决策者的德育有效性,基于经济、社会发展,反映意识形态要求,本质上表达的是一种整合与凝聚全社会观念的意愿和意志。“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是德育的主要目标,有用性——效用是他的主要价值诉求。教育过程是教育政策的具体化过程。教育者作为教育政策的贯彻者和行动者,主导着德育有效性的生成过程。在应试教育的大环境下,受市场经济绩效主义影响,教育者将“效率”(以考分作为价值尺度)当作“心中的太阳”来追求。如何快速、高效地培养有用的知识型人才是教育者的追求。作为德育主体的教育对象——活生生的人,对于德育有效性必然有着自己的理解和诠释。德育除了具备上述社会适应性的特点,同时也具有个体适应性的特点,即适应个体追求社会生存及发展的需要,以及追求“自我实现的需要”。
道德追问的是“人应该如何生活”“人怎样活成他自己”的问题。道德就是主体对自身内在自觉及自为性的发现,德育的目标就在于催生受教育者生命的自我觉醒,并尊重其作为道德选择的主体地位。一方面,受教育者把被动的接受过程变为主动的探求过程,主动地探索和认识自己、他人、社会及其相互关系。另一方面,受教育者带着积极性、主动性,对既有道德价值体系、规范和道德现象进行独立的思考、理性的判断和选择,并将它们内化为自己的观念和情感。
从某种意义上说,受教育者才是有效性的真正主体,有效性在他那里才能达到与效果“同一”。只有在这个时候,被喻为“产品”的有效性才被真正生产出来。
关于德育有效性的思考和标准的确定,必须基于多主体的价值诉求。评价有效性,既要考察其达到教育者、社会所期望的教育目的的程度,也要考察其符合学生成长、成才内在需要的程度。有效性是效果、效益和效率的有机统一,它们是把握有效性内涵及其评价标准的三个维度。当对德育有效性的理解和评价真正建立于三重主体的有效整合的基础上,或者说,以“效果”为“校准”,整合“效用”和“效率”,德育将真正受到受教育者的普遍欢迎,也会取得更好的实效。
[1]蔡连玉.道德教育中的编码、解码与抵制:提升德育有效性的分析[J].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12(2):54-58.
[2]张正军.公共管理论阈中的公共性问题——语义分析基础上的哲学诠释[J].江海学刊,2009(3):104-111.
[3][英] J.D.贝尔纳.科学的社会功能[M].陈体芳,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1.
[4]左民安.细说汉字[M].北京:九州出版社,2005:316-320.
[5][美] 罗宾斯.组织行为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257.
[6][美]德鲁克.卓有成效的管理者[M].许是祥,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17.
[7][美]埃克·拉塞尔.麦肯锡卓越工作方法[M].金雨,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4:213.
[8]张喜军.教学效能研究综述[EB/OL].( 2009-7-21)[2014-05-06].http://www.xdxx.com.cn..
[9]张健,张新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语义分析和语用阐释[J].伦理学研究,2007(7):10-12.
[10]张应强.中国教育研究的范式和范式转换——兼谈教育研究的文化学范式[J].教育研究,2010(10):3-10.
[11]鲁洁.论教育之适应与超越[J].教育研究,1996(12):3-6.
[12]王艳.“缺效“失效”“反效”——道德教育“有效性”的三重境遇[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1):55-59.
[13]郝德永.从两极到中介:课程改革的路径选择[J].教育研究,2010(10):33-37.
[14]陈艳秋.现代高校德育的“知识化”困境[J].现代教育教学,2006(5):112-114.
[15]朱熹.四书集注(上)论语章句集注[M].北京:中国书店,1994:27.
[16]鲁洁.再议德育之享用功能——兼答刘尧同志的“商榷”[J].教育研究,1995(6):27-31.
责任编校:汪沛
SemanticAnalysisandPragmaticInterpretationofMoralEducationEffectiveness
HU Xin-hong
(Hefei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Chaohu 238000, Anhui, China)
Moral education effectiveness in essence is a value relation between subjects and objects, and should be understood with subjects and the yardstick. Semantic analysis begins with the origin of the word “effectiveness”, which has three meanings: utility, efficiency and effectiveness. As for the pragmatic aspect, firstly, decision makers of moral education are expected to pursue the effective value of moral education on the basis of state position and class will and require moral education to adapt to the needs of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so as to cultivate useful talents; secondly, moral educational workers should uphold performance assessment concept and hold on to moral education efficiency in order to cultivate talents with speed and high efficiency; thirdly, people who receive moral education ought to have unique understanding of moral education effectiveness out of fresh individual experience and call on real moral education effectiveness.
moral education effectiveness; semantic analysis; pragmatic interpretation; utility; efficiency; effectiveness
2014-03-27
合肥职业技术学院人文社科一般项目“主体及其尺度视角下的德育有效性研究”(rwyb201312)。
胡心红,男,安徽无为人,合肥职业技术学院高级讲师,硕士。
时间:2014-8-28 15:45 网络出版地址:http://www.cnki.net/kcms/detail/34.1045.C.20140828.1545.031.html
10.13757/j.cnki.cn34-1045/c.2014.04.031
G410
A
1003-4730(2014)04-0136-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