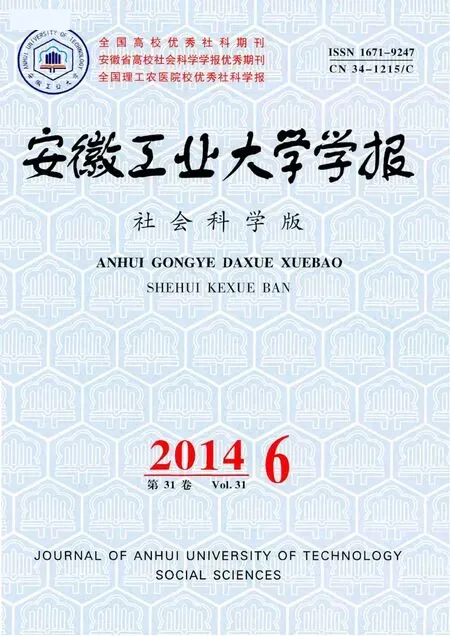《我知道笼中鸟为何歌唱》中黑人女性寻求自我话语权的心路历程
2014-03-20吕万英徐诚榕
吕万英,徐诚榕
(中南民族大学 外语学院,湖北 武汉430074)
玛雅·安吉洛是美国当代著名的黑人女诗人、畅销书作家及人权活动家。小说《我知道笼中鸟为何歌唱》是其撰写的六部自传作品中影响力最大的一部,记录了她童年和少年时代的生活。作品将自传与女性成长小说完美地结合起来,形成了一个带有独特叙事风格的文体,突破了传统自传与成长小说的叙事方式,细腻而深刻地展现了一个黑人女性所特有的成长经历。笔者拟从人格心理学的视角,针对人格面具的变换展开分析,来探究黑人女性寻求自我话语权的心路历程。
一、人格面具
“人格面具”一词源于演员所带的面具,是瑞士心理学家、当代分析心理学创始者卡尔·荣格集体无意识理论中原型的重要构成之一。人格由面具所构成,一个面具就是一个子人格,或人格的一个侧面,人格就是一个人所使用过的所有面具的总和,“实际上是我们所说的‘我’,我们所表现给别人看到的我们自己”。[1]荣格认为:“人格最外层的人格面具掩盖了真我,使人格成为一种假象,按着别人的期望行事,同他的真正人格并不一致。人可靠面具协调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决定一个人以什么形象在社会上露面……人格面具是原型的一种象征。”[2]人格面具是一种社会产物,它把人际交往的方式上升到了理论层面,是个人与社会关于人应该如何行事所达成的一种妥协。现实生活中,人格面具靠我们的服饰、谈吐、肢体语言等告诉外界“我”是谁,去表现理想化的“我”。此外,人格面具可以掩盖人们因面对未知的人、事物或环境所产生的怯懦与恐惧,有意无意间进行心理上的调整,从而产生了与真实人性不同的心境。人们无时无刻不戴着人格面具,在不同的时机、场合使用不同的面具来表达不同的心理活动。
二、玛雅人格面具的变换
在小说《我知道笼中鸟为何歌唱》中,玛雅3到16岁的成长过程是一个持续转换人格面具的过程:由幼年时期的幻想型人格面具,到少年时期的远离型人格面具,再到青年时期叛逆型人格面具以及对消极伪装性人格面具的摒弃,从迷惘、困惑、痛苦到自我意识的觉醒,玛雅迎难而上,逐渐获得了社会大众的认可。
(一)幼年玛雅的幻想型人格面具
在南北战争结束后半个多世纪的南方,白人仍然在心理上固执地捍卫着自己曾经的特权,这种偏执的心理甚至比以往更顽固、更疯狂,致使像斯坦普斯一样的南方小镇依然笼罩在种族歧视的阴霾之中。生活在这种氛围中,幼年玛雅很早就察觉到自己卑微的社会地位,过早地承受屈辱、悲惨的命运。同大多数黑人女性一样,玛雅的内心极度自卑,“我的腿上涂抹着蓝标凡士林,还扑上了阿肯色红土。经年累月,土的颜色渗入皮肤,让它看起来肮脏而恶心……”[3]2对于自己 “又黑又卷”的头发,“又宽又大”的脚板,有“间隙”的门牙都十分厌恶,阿妈精心为她缝制的复活节长裙也不过是“白人洗旧了不要的紫色长裙”。白人长期的偏见以及白人对黑人肆无忌惮的欺凌让玛雅对黑人身份产生了错位感。这种以白人即美、黑人即丑的错位感让玛雅极度压抑和痛苦,因而幻想有一天能彻底摆脱,成为有“一头金发”和“大而迷人”、“浅蓝色”眼睛的白人小姑娘。小玛雅甚至执着地幻想自己本有着白人的身份,只是遭邪恶的巫婆继母嫉妒才被其施魔法“变成一个丑陋的、大码子黑人”。这是一个生活在还带有严重种族歧视色彩的美国黑人少女发自内心的奇想。
在白人文化占主导地位的美国,玛雅从生活中直观地感觉到社会对黑人的厌恶和否定。毫无疑问,幼小的玛雅不可能深层次地去认识和剖析生活之所以痛苦、压抑的原因,她只能凭自己稚嫩的心灵去思考,并认定一切是由于自己容貌的丑陋所致,从而否定自己。幼年时期的玛雅将自己长时间隐藏在一个幻想型的人格面具之后,反映了身为黑人的小玛雅强烈的自卑感和错位感,同时也反映了她希望能像白人那样获得他人的尊重。
(二)少年玛雅的远离型人格面具
少年时期的玛雅从熟悉的南方小镇被接到圣路易斯外婆家,环境的突变使玛雅心理产生了很大的抗拒。门铃、火车、汽车、巴士、抽水马桶的噪音等各种喧嚣使她意识到自己不属于这里,因而将自己的内心深深隐藏起来。更不堪的是,年仅八岁的她在搬到妈妈家之后不久便遭到妈妈的男友弗里曼多次骚扰和强暴,并被弗里曼威胁不准说出去,否则就要杀了她最亲近的哥哥贝利。性骚扰和强暴以及对弗里曼的恐惧等令人心碎的事情几乎将玛雅推到了崩溃的边缘。这些痛苦的经历使少年时期的玛雅一度寡言少语,刻意疏远身边的人,包括亲近的阿妈和威利叔叔,以此掩盖痛苦的回忆,同时包裹自己,免受流言蜚语伤害。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玛雅沉默寡言,过着乏味的“像一块过期饼干、落满尘埃”的生活,除了哥哥贝利,玛雅不与任何人交流:“我走进一个房间,人们有说有笑,他们的声音如碎石一般撞击着墙壁。而我只要静静地站着,站在这喧嚣中,一两分钟后,宁静就会重归此处,因为我吞噬了所有的声音。”[3]91回到祖母身边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她认为自己满身罪恶与肮脏,变得敏感多疑,认为威利叔叔的眼睛“满是疏远的神色”,以至对自己的精神状态产生疑虑:“所有传到耳朵里的声音都变得沉闷……周围的颜色不再逼真……那完全不是我以往熟悉的斯坦普斯,人们的名字也逃离了我的记忆。”[3]91这些痛苦的经历使玛雅亲自为自己带上远离型人格面具,封闭自己,缩进了为自己织好的茧。
(三)玛雅消极伪装型人格面具的摒弃
对于少年的玛雅来说,与弗劳尔斯夫人的相识改变了她的一生,弗劳尔斯夫人抛给了困境中的玛雅一条救生索。弗劳尔斯夫人高贵优雅,独立自信,并善于开启玛雅因受伤而封闭的心灵。在玛雅情绪低沉时,弗劳尔斯夫人借给她诗集,鼓励她开口诵读,让她领略诗歌的魅力,认识语言的神奇力量。朗诵书籍让玛雅打开了封闭许久的心扉,当玛雅读到“我现在做的事,比从前要好得多得多”时终于释怀,愿意与人交流了,摒弃了远离型面具,这是她成长道路上的一个重要转折。
在弗劳尔斯夫人的帮助下,玛雅开始认同自己的黑人身份,逐渐意识到了自身的存在价值以及黑人尊严的重要性。这表现在,她不愿被白人为了称呼方便就随意简化自己的名字,在观看以黑人为笑料的电影时的不安和反思,同时,慨叹黑人对自己悲惨境遇麻木不仁。十岁的玛雅在卡利南夫人家做女佣时,被这位夫人随意更改了名字,便故意打碎了白人主人心爱的盘子以示抗议,赢得了保卫尊严的第一场战争。玛雅的反抗不仅是她个人身份意识的觉醒,也代表了全体黑人女性的抗争。几个世纪以来黑人总是被随意称呼,如“黑鬼、黑鸡,脏鬼”等,这些称呼是对黑人的侮辱,称呼的随意性折射出黑人作为一个种族的卑微和可有可无。玛雅的反击行为不仅让其萌生了自我意识,还使她走出了白人为黑人划定的狭小生存空间,为自己是“伟大而美丽的黑人种族的一份子”而无比自豪,并极力维护着黑人的尊严。最终玛雅卸下了自己幻想型人格面具,开始了独立人格的蜕变。
(四)青年玛雅充满理想的有效社会人格的形成
玛雅的青年时期除在洛杉矶停留半年,大部分时间是在旧金山度过的。玛雅来到旧金山恰逢二战刚开始不久,日本人大批逃离,大批黑人从乔治亚、密西西比等地涌进旧金山,原先的日本人聚集区很快变成“哈莱姆”区,黑人平生第一次成为生活的“主角”,他们可以付钱让别人为自己服务,这让黑人意识到自己也“有人需要甚至欣赏”。这时的玛雅渐渐产生了一种“归属感”,开始在心中塑造理想的自我,“希望自己长大成人后友善而矜持,冷静却不冷漠或拒人千里,高贵但不顽固”,并且变得勇敢无畏。此时旧金山流传着的关于黑人老兵在公汽上为尊严而不卑不亢地回击白人歧视的故事表明,黑人作为群体对白人的歧视不再忍耐而是奋起反击,这无疑是黑人开始身份认同的象征。
与爸爸一同跨越边境去墨西哥探险的旅程则让玛雅清楚地看到了爸爸面具后的另一面:自信且游刃有余。玛雅爸爸在墨西哥小酒吧中轻松自信的表现让玛雅再次找到归属感:“他是美国人,他是黑人”,这个身份足以让“他们(墨西哥人)崇拜敬仰”。
玛雅开始从各个方面证明自己:回家的路上,从没开过车的玛雅决定代替酒醉的爸爸驾驶,尽管知道稍有不慎,就会跌落山崖、车毁人亡,但这样的挑战却让玛雅兴奋:“我,玛格丽特,独自对抗着自然的伟力。”[3]243这是玛雅自立自信的突出表现。随后,从爸爸那出走,在废旧车场的经历让玛雅产生了归属感。玛雅和一群黑人、白人还有墨西哥人的流浪孩子生活了一个月,捡瓶子、修剪草坪、给店铺跑腿等等,她敞开心扉融合到一个多种族的氛围之中,产生了不分种族、不分彼此的观念,打破了种族的藩篱。
生活在一个备受歧视的年代,黑人女性要承受来自性别、种族与阶层的多重压迫,生活给予她们的从不是甜美,而是困惑、绝望和无休止的羞辱。受“南方黑人教育”的玛雅,和其他黑人女性一样,深刻感受到生活的不公平和沉重的压力。在遭受一系列不公之后的玛雅,在与生活和种族歧视抗争的过程中,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独立自强的重要。而母亲无所畏惧独立打拼的个性也无形中影响着玛雅。母亲“自助者,上帝助之”的箴言和“没有什么事人们做不成的”话语鼓舞着玛雅。南方之行结束后,玛雅自主的理念越发强烈,她立志成为旧金山电车上首位被雇的女性黑人。尽管遭受前所未有的质疑和冷漠,玛雅表现出了惊人的倔强和勇气,决心打破旧金山不让有色人种上有轨电车(工作)的限制。玛雅通过呼吁黑人组织支持,锲而不舍地争取,最终成为旧金山电车上首位女性职员,证明了自己的存价值。
三、人格面具变换下的自我话语权
19世纪40年代以前,美国黑人女性在文学作品中往往都被刻画成“单一的女佣形象:黝黑,肥胖,健壮,迷信,吃苦耐劳,毫无存在感且毫无话语权”。[4]19世纪后期,随着美国妇女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黑人女性勇于向传统社会挑战、寻求自我话语权。《我知道笼中鸟为何歌唱》中,作者通过细腻而深刻的笔触,展现了主人公人格面具变换下坎坷的成长道路和走出失语状态的心路历程,不仅为黑人女性争取了平等的话语权,也印证了福柯的论断:强势群体,即占据话语权的一方为了自己的主体地位,往往会施加一种压力,抹杀他者的声音。而被压迫的一方要么保持沉默,要么代表权力话语发言。[5]
(一)幻想型人格和远离型人格面具下的无语和失语
美国内战后,黑人的人权在法律上得到肯定,然而种族歧视并未随着黑奴的解放而消失,黑人的社会生存环境依然恶劣。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幼年的玛雅带着幻想型面具过得自卑且压抑,尽管她逃避现实,幻想自己白人小女孩的身份,现实却是痛苦的,当玛雅在教堂背不出颂歌,被牧师的妻子嘲笑且一脸怜悯地说“愿上帝保佑这个孩子”时,羞怯、屈辱的感觉在心里剧烈碰撞,玛雅想逃离却被绊了个趔趄,尽管她想说些什么却无法开口,屈辱的感觉使玛雅失去控制而便溺。在小玛雅眼中,阿妈的形象无疑是高大的,然而当那些不懂礼节的白人小混混成群结队地闯进店里胡闹,用奇怪的姿势模仿、侮辱阿妈时,小玛雅除了幻想自己“抓一把黑胡椒粉撒到她们脸上,再将碱水灌进她们的鼻子”,[3]32却也只能在一旁哭泣,她明白自己的身份和无能为力。稚嫩、脆弱、自卑且缺乏安全感致使玛雅逆来顺受,无法用言语来维护自己和家人的尊严,此时的玛雅毫无话语权可言。
以早期的小玛雅为代表,黑人女性在种族歧视和传统观念的双重枷锁束缚下,无法在社会生活中占有一席之地,大部分黑人女性甚至意识不到自己悲苦的命运,只是在沉重的枷锁下浑浑噩噩地活着,她们在种族与性别的压迫下,在白人文化的侵蚀下,更加不敢开口说话,长期处于失语的状态。
(二)叛逆型人格和有效社会人格面具下话语权的重建
回到斯坦普斯小镇一年多后,玛雅在弗劳尔斯夫人的开导下已渐渐走出难堪的过往。小说有这样的一个场景:一次阿妈带玛雅到镇上的诊所去看牙医却遭到白人医生的拒绝,而且还用刻薄的语言侮辱她们,不得已的阿妈只好将玛雅留在门外,自己去求医生。门外的玛雅却想象着阿妈昂首阔步地走进去揪住医生的衣领痛骂道:“你是我见过的最‘对不起观众’的医生了”、“我不想让你当着玛格丽特的面道歉,因为我不想让她知道我的力量,但是此时此刻我要命令你,太阳落山以前离开斯丹普斯。”[3]195尽管是想象,玛雅却觉得牙疼已经减轻。可以看出,当玛雅面对不公平待遇时,不再忍气吞声,虽是借由着想象中阿妈的言语,却是玛雅内心叛逆、抗争最有力的表现。
此外,当玛雅在爸爸家度假时,爸爸的情人多洛雷丝却对她心生不满,认为她妨碍了两人的关系,言语上极尽刻薄甚至出言侮辱玛雅的妈妈,玛雅被激怒道:“我的妈妈,她比你强一百倍……”“我要扇你这个又蠢又老的贱货”,[3]250说罢便同她打了起来。此时的玛雅走出了失语状态,重拾了自己的话语权,语言上不再是被压迫的一方。青少年时期的玛雅积极向上,充满理想。南方之行结束后,玛雅立志成为旧金山电车上的售票员,尽管压力重重,她依旧坚持着去证明自己的存在价值,“我会得到那份工作。我要成为一名售票员,挎上一个用我的皮带改成的鼓鼓囊囊的零钱袋。我说道做到。”[3]273最终玛雅成为了旧金山电车上首位被雇的女性黑人。青少年时期的经历也让玛雅学会认识自我、直面自我,唤起了自我作为主体的力量,恢复了自我话语权,不再是一名“需要黑人贫民窟这块盾牌呵护的”黑人女性。
四、结语
借助心理学中人格面具这一理论可以看到,在《我知道笼中鸟为何歌唱》这部自传体小说中,主人公玛雅的成长经历体现了一个在人格面具更替下自我话语权恢复的过程:从沉默失声到为话语权进行抗争,再到自我话语权的恢复,展现了黑人女性重获自我话语权的艰难曲折的心路历程。同时,我们也从该作品中看到了一种全新的黑人女性性格特点:坚韧、执着、自立,宛如真正冲破牢笼的鸟儿一般,自由歌唱。
[1]申荷永.荣格与分析心理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2]何静静.人格面具与自我迷失——探究长日入夜行的人物悲剧性格来源[J].绥化学院学报,2008(5):140-142.
[3]玛雅·安吉洛.我知道笼中鸟为何歌唱[M].于宵,王笑红,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3.
[4]朱振武.美国小说本土化的多元因素[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
[5]Foucault,M.TheArchaeologyofKnowledge[M].Sheridan Smith A M,trans.New York:Random House,19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