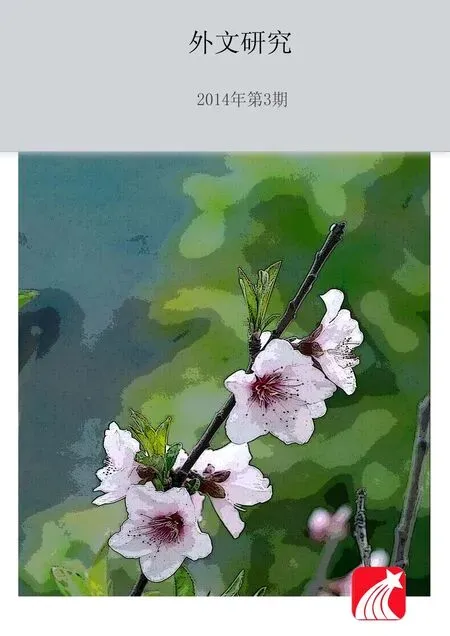狗先生眼中的美国社会
——保罗·奥斯特的《在地图结束的地方》评析
2014-03-20河南大学薛玉凤
河南大学 薛玉凤
当代美国著名作家保罗·奥斯特(Paul Auster, 1947-)的三十多部各类作品中,人们关注较多的是《纽约三部曲》、《孤独及其所创造的》、《幻影书》、《巨兽》(Barone 1995:1)等代表作,《在地图结束的地方》(Timbuktu, 1999)出版后虽被许多读者所迷恋,但似乎很快被中外批评家所遗忘。不多的几篇外文评论,大多讨论身份、自我、主体性、拟人化、二元对立、族裔散居等主题。在中国知网上,只有一篇相关文章:“存在的悬置——评保罗·奥斯特《在地图结束的地方》”,探讨了作品中的存在危机。然而半年内读奥斯特的七八部作品,印象最深的两部之一,就是《在地图结束的地方》。
读《在地图结束的地方》中小狗骨头先生的故事,自然会联想到杰克·伦敦(Jack London, 1876-1916)的经典名作《野性的呼唤》(TheCalloftheWild, 1903)中的狗王巴克和《白牙》(WhiteFang, 1906)中的混血狼狗白牙,尤其是前者。骨头先生和巴克都是小说的主人公,都是狗,都曾被主人宠爱,生活无忧无虑;失去老主人后,生活都变了样,食不果腹,朝不保夕,饱尝人间冷暖心酸。小说看似狗的遭遇故事,折射的却是社会中的人,或人与狗的世界,借此倡导真善美,抨击假恶丑,警醒人们关注精神世界。
骨头先生与狗王巴克相比,可谓既幸运,又不幸。幸运的是,骨头先生不像巴克那样被偷,被多次转卖,被迫在冰天雪地的阿拉斯加做苦力拉雪橇。四十五岁的老主人威利病逝后,骨头先生有幸遇到对“他”*原文如此,本文沿用这一称谓。宠爱有加的11岁华裔男孩亨利,后又邂逅视他如心腹的善良女主人波利,遍尝美味,阅尽人世,也算过了几个月富足的狗类中产阶级生活。不幸的是,从小与威利一起生活的骨头先生早已失去野性,既无法独自生存,又不能像强壮的巴克那样重返荒野,而两个新主人家的男主人又偏偏不喜欢狗,这就注定骨头先生的新生活坎坷多舛。几个月后,被寄存在狗旅馆的骨头先生病入膏肓,不想再被庸医折磨,毅然选择有尊严地死去,到另一个世界与威利团聚。
三个主人三种生活,骨头先生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饱尝生活的艰辛与世态炎凉。男性中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及消费社会的种种弊端,是我们通过骨头先生的眼睛所看到的美国当代社会的三个侧面。
一、男性中心主义的余孽
男性中心文化与专制的家长制作风,是骨头先生在两个新主人家所体验到的新知识,也是他不幸的源头。虽然早在19世纪,一些有识之士就为妇女解放做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后经过20世纪60年代轰轰烈烈的女权运动与民权运动,美国女性的地位普遍提高,但直到《在地图结束的地方》中的故事发生的1993年8月,妇女的从属地位仍无根本性改变。男积极,女消极;男主动,女被动;男主外,女主内;男性勇敢坚强,女性柔弱温顺(汪民安 2007: 210)等传统男性中心主义观念仍在兴风作浪。男人与女人、家长与孩子、人与狗,在这些显而易见的二元对立中,起主宰作用的无疑是前者,而后者无意中结成了同盟,却还只能是屈从,或做些无谓的默默反抗。
骨头先生的第一个新主人亨利与他的老主人威利一样,视他为知己,只可惜亨利只是个孩子,无力保护自己的新朋友,父母又坚决反对养宠物,因此他们的友谊注定短暂。亨利在中餐馆长大,父母忙于生计,无暇顾及儿子的精神需求。亨利与流浪的骨头先生邂逅,一见如故,视其为伙伴和知己,无奈他只能把骨头先生藏在后院的破纸箱里。但秘密还是很快被专制的父亲发现,他不顾儿子的苦苦哀求,用石块砸向骨头先生,亨利只能与新朋友生离死别,彼此的友谊就这样成了男性中心和专制家长制的牺牲品。
骨头先生在第二个新家的境遇要好得多,但男主人迪克的男性中心意识还是让骨头先生吃尽了苦头,并最终决定逃离。首先,迪克是家里名副其实的一家之主,一旦他做出决定,妻子儿女必须无条件服从,说什么都是白费口舌,三比一的民主制在这里几乎无任何意义。虽然在八岁爱女爱丽丝的极力游说下,迪克答应留下骨头先生,却提出了五个非常苛刻的条件,包括不得进入室内、去势等,使骨头先生觉得身心受到重创。不过,尽管付出了惨痛代价,骨头先生总算有了名正言顺的新家,住进不错的狗屋,获得应有尽有的食物。聪明的骨头先生很快成为两岁半小老虎的玩伴,小爱丽丝的交流对象,女主人波利的灵魂伴侣。骨头先生明白,最需要他的其实是女主人波利,因为波利和他一样,“都是命运的囚徒”(奥斯特 2012: 148)。*以下出自本书的引文,只在文中注明页码。
波利与迪克的婚姻可谓父权制与男性中心文化的双重牺牲品,是一个偶然导致的结果,波利完全处于被动地位。波利18岁认识大她八九岁的飞行员迪克,两个月后发现自己怀孕。气疯了的父母骂她“荡妇”,嫌她败坏门风,拒绝提供任何帮助,刚入校不久的波利走投无路,不得不从大学退学,与迪克结婚。如果父母稍稍替情窦初开、不谙世事的女儿考虑一下,和她一起面对眼前的问题,波利也不至于匆忙嫁人,后面的悲剧也许可以避免。婚后,体弱多病的女儿爱丽丝和儿子小老虎的相继诞生,一次次打碎波利重返校门的梦想,工作的念头又一再被丈夫迪克无情扼杀。在迪克眼里,妻子理应扮演贤妻良母、“家庭天使”(汪民安 2007: 212)的角色,依附于丈夫和家庭,她的事业就是相夫教子。
然而,波利毕竟是个受过高等教育的独立个体,婚后这种牢笼中的“天使”生活使波利对丈夫“阳奉阴违”,一直在做着小小的反抗。表面看来,波利对迪克唯命是从,小心翼翼地扮演着贤妻良母的角色,但迪克外出工作后,家里就是波利的天下,骨头先生就是她忠实的伴侣与倾诉对象。然而,纸包不住火。尽管波利小心翼翼地打扫骨头先生的痕迹,迪克还是在客厅和卧室里发现骨头先生的两三根毛发,夫妇俩的战争一触即发。与亨利的父亲一样,迪克是绝对的一家之长,在供应全家衣食住行基本需求的同时,也享有绝对的权威,很少考虑家人精神方面的需求。
迪克为修补急剧加速的婚姻危机,决定带全家外出休假两周,于是把病中的骨头先生寄养在一家狗旅馆,身心俱疲的骨头先生终于忍无可忍,决定再次逃离。不过这次逃离的目的不是寻找新主人,而是用狗们爱玩的“躲车”游戏自杀,到另一个世界与心爱的老主人团聚。骨头先生从两个新家的两次逃离,起因都是男主人,如果没有男主人霸道的男性中心意识作怪,已在亨利、波利与爱丽丝身上找到威利影子的骨头先生无疑会生活得很愉快,但亨利父亲和迪克的男性中心意识与家长制作风,不仅使家庭危机四伏,还直接导致骨头先生厌倦尘世生活,从而不惜放弃自己的生命,到地图结束的地方——汀泊图,那个被威利形容为“精神的绿洲”(46)的地方与老主人会合。
有评论家注意到,奥斯特在多部作品中通过父子关系形象展示父权制与自律这对相反相成的规训权力形式,小说中的亨利父子、迪克父子以及威利父子,莫不如此。父权制是主流社会意识形态的外化,它与个体自律意识的相互作用,犹如个体与社会霸权之间的关系:个体为获得自由,奋力在社会霸权中挣扎(Walker 2002: 389)。威利、亨利和波利,就是《在地图结束的地方》中为摆脱父权制与男性中心文化,反抗社会霸权而努力抗争的个体代表。
在平等与自由观念深入人心的当代美国社会,男性中心与父权制文化仍然余孽未除,妇女与儿童的权利得不到充分的保障。而当人们面对动物与自然,这些文化现象则表现为人类中心主义,它与男性中心主义一样,是一种歧视弱者的强权行为。
二、人类中心主义泛滥
亨利的父亲和迪克之所以对狗深恶痛绝,完全是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在作祟。人类中心主义的实质是,一切以人为中心,一切从人的利益出发(余谋昌 2000: 140),忽视其他物种的基本权益。骨头先生失去老主人威利的呵护,试图在这个自私自利的人类中心社会中寻找新主人,艰难坎坷不难想象。
离开垂死的威利后,骨头先生所接触的第一批人类,是巴尔的摩一个公园里的六个十二岁男孩,他们时而像天使,时而像恶魔,视骨头先生如玩物。一开始,他们给了骨头先生“一流的皇家待遇”(93),好吃好喝好玩,但他们的“小流氓”或“暴民”本性很快显露出来,相互之间发生激烈争执,甚至打架斗殴。骨头先生使尽浑身解数,讨好这群孩子,试图转移他们的注意力,却遭脚踢石砸,使他伤心不已,失望之极。他“告诉自己,不要再这么轻信别人,应该只想人的坏处,直到他们表现出好的意图来”,并给自己定下第一条行为准则:“不要靠近孩子”,因为“他们缺少同情心”,而“如果一个两腿生物缺乏了这种品质,他们就和疯狗差不多”。(95)这些孩子不只缺乏同情心,也缺乏人类起码的理性、思考与交流能力,因此只能与疯狗相比拟。他们歧视动物,对骨头先生的好意视而不见,完全从自己的意志出发利用骨头先生,难怪骨头先生会对代表人类希望的孩子如此失望。
骨头先生逃离亨利父亲的追杀,一路从马里兰州的巴尔的摩跑到弗吉尼亚北部,三天三夜几乎不吃不睡,路上还险遭枪杀。睡梦中,老主人威利再次力劝骨头先生找一个新主人,因为那是他活下去的唯一出路,但骨头先生已经不再相信人类,觉得世上唯一可信赖之人已死,这世界再无安全之处。就在前一天,骨头先生还被人开车追赶, 那家伙一边追一边大笑,后来突然拿枪朝他开火,幸好没打中。心有余悸的骨头先生认为,也许还会有几个亨利那样的傻瓜对狗有好心肠,但大多数人看到误闯他们地盘的四条腿生物,都会毫不迟疑地给手枪上膛,因此他宁愿死在荒郊野外,也不愿冲进枪林弹雨中去。人类的自私、残忍、无情与自以为是,再次让骨头先生绝望(115)。
亨利的父亲是小说中利己主义思想的又一代表,毫无根据地对狗深恶痛绝,只顾自己餐馆的利益,从不考虑动物及爱狗人士的需要。在他眼里,狗意味着美味,意味着中餐馆赚钱的免费食材。中餐馆的大厨,按照威利的说法,每周可能会捕杀几十只流浪狗,然后在菜单上“挂羊头,卖狗肉”,供圈里的美食家享用。尽管威利临终一再忧心忡忡、苦口婆心地告诫爱犬远离无处不在的中餐馆,骨头先生的第一个新家却还是鬼使神差地安在了这家中餐馆的后院,结局注定悲惨。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有华人食用狗肉,但并非所有中餐馆都卖狗肉,更非所有中餐馆都见狗就杀,作者这里对华人的描述显然夸张过分,有东方主义之嫌。
而迪克之所以严禁狗进入室内,只因怕狗毛弄脏家具。在他看来,无论骨头先生如何聪明,他都“不是人,只是一条狗,狗是不会问问题的。他们总能随遇而安”。(135)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对迪克的这条规定,骨头先生却是疑虑重重,问题丛生:如果一条狗不被允许进入房子里,怎能成为家庭一员?其实是迪克孤陋寡闻,自以为是,不愿设身处地地为狗着想而已。
“曾经沧海难为水”,骨头先生之所以对他后来的境遇不满意,是因为他从小就和威利一起生活在布鲁克林,七年来一起吃,一起睡,一起流浪,每天24小时形影不离。威利从不把他当低等动物看待,而把他当朋友,唯一的朋友和伴侣。正因如此,威利将其命名为“骨头先生”,以“他”相称,而非“它”,使骨头先生觉得自己生来就为和人类做朋友。加上威利是流浪诗人,还是个不折不扣的“恋语狂”(4),从早到晚,几乎一直不停地对骨头先生说话,因此骨头先生温柔、文明、会思想,懂得隐忍,明白威利所说的一切,会做出一些合适反应,只是不会说话而已。这次他们从二百多英里外的纽约来到巴尔的摩,是因为威利意识到自己时日不多,想把23年来创作的74本笔记手稿交给赏识自己诗作的高中英文老师(6),并为他心爱的骨头先生安排后路,但还未能如愿,他就在爱伦·坡故居门前倒下了,临终前一再警告骨头先生小心这个人类中心主义社会的种种危险。
威利之所以对骨头先生平等相待,大概与他独特的身世与生活经历有关。首先,他虽是家中独子,却与父母形同仇敌,内心孤独无助。威利出生于1947年,父母都是波兰犹太人。夫妇俩为躲避纳粹的迫害,曾在波兰和法国九死一生,后移居纽约布鲁克林。威利有幸成长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布鲁克林孩子,但他父母始终是在美国挣扎的波兰移民,亲子之间经常剑拔弩张。威利的父亲曾是波兰年轻有为的律师,在布鲁克林却只能在亲戚的纽扣厂做苦力,心中的苦闷可想而知。更不幸的是,他把这种苦闷转嫁到儿子身上。对威利来说,父亲就像一个炸药包,随时会为一点小事对他拳打脚踢,父爱似乎没了踪影。威利12岁时,父亲死于心脏病,威利没有太大痛苦,反而觉得是一种解脱,可见他与父亲的敌对程度。家里只剩下威利和母亲,母子俩本该相依为命,但截然不同的世界观使他们根本无法和平共处,吵架成了家常便饭。
其次,威利不只与父母无法和平相处,与身边的社会也格格不入。好不容易进入大学,威利却没交到一个同龄朋友,反而愤世嫉俗、离经叛道,成了逃亡诗人,最后因吸毒进入疯人院,大学生活戛然而止。从疯人院出来的威利无处可去,又回到母亲的住所,吸毒改为酗酒,直到有天受电视上圣诞老人的感召,决心做个圣徒,圣诞老人的使者,他甚至在右臂上文圣诞老人图案,却因此使他的犹太母亲伤心欲绝。威利不解,开始长达16年的半流浪生涯,冬天才猫在家里写诗,晚上往往一坐就是三四个小时。
救溺水女童,保护受暴徒攻击的81岁老人,挽救自杀者的生命,让悲伤者在他怀中痛哭,对倒霉者倾囊相助(23),流浪诗人威利像耶稣一样,勇敢、慷慨、善良,一心传达圣诞老人的信息,不求回报地将爱给予这个世界,却经常在流浪中被陌生人打得头昏眼花,身上枪伤刀伤不断,健康每况愈下。骨头先生就这样被威利抱出收容所,做他的贴身保镖。威利与这个世俗与势利的社会格格不入,为家里家外的社会成员所不容,因此把所有的爱与希望都寄托在自己唯一的朋友骨头先生身上,也就顺理成章。他和骨头先生亲密无间,很快建立起最热切、最真挚的感情。他觉得骨头先生是一条纯洁正直的好狗,有着优雅高贵的灵魂,是束缚在狗皮里的天使,“狗中之狗”(38),整个犬类的代表。他发现“狗”(dog)这个词反过来写就是“上帝”(God),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最低等的造物在其名字中却蕴含了最高造物、全能的造物主的力量(32-33)。
骨头先生虽只是一条其貌不扬的杂种狗,但与主人威利一样有思想、有理想,有自己的喜怒哀乐。与威利一起流浪的七年时间,使骨头先生觉得自己“是地球上最幸运的生物”(27)。最后几个月的冒险生活,看多了男性中心与人类中心的丑恶嘴脸,更使他明白威利的可贵之处,坚信自己所向往的,是与威利所过的那种虽然物质贫乏,精神却极其丰富的简单生活。威利是个富有生态思想的智者,身体力行地践行人与动物平等共处、互敬互爱的信条,摒弃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将大爱惠及自己的爱犬,可谓难能可贵。从威利对骨头先生的依恋、关心与忧虑,可以看出他对万物生灵的博爱情怀。
人类中心主义不但累及骨头先生这样的小动物,而且在物质极大丰富的消费社会,也助长了人类无限膨胀的消费欲望,导致物质资源的浪费,人类精神生活的匮乏。
三、消费社会的弊端
在消费社会中,消费不再是物质属性的消费,而是符号属性的消费,符号价值代替了使用价值;消费成为人通过商品符号展示自我存在价值的一种方式,“精神需求的无限空间开始由符号加以填补”;“人们的幸福意识完全表现在对符号的占有和操控上”(汪民安 2007: 397-398)。正因如此,尽管威利深爱他所生活的这个世界(65),但他“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对消费主义泛滥的社会现实深恶痛绝。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威利还在痛骂消费主义的弊端,历数无家可归的道德优势(63)。
威利对功名利禄漠不关心,对物质享受嗤之以鼻。对自己的诗作,威利从未想过出版,他不在乎“那些虚荣的玩意”,认为“有意义的是做的过程,而不是完成之后再去做的那些事”(64),他享受的是写诗的过程。二十年来,他大部分时间都在流浪,尤其是最后四年,他和骨头先生相依为命,无家可归,过着饥一顿饱一顿的生活,但威利总是毫不犹豫地拒绝物质文明的诱惑,总是攻击它们,用偏激、滑稽的方式抱怨这些东西。他认为,“圣诞节是个大骗局,是一个花钱如流水和收银机叮当响个不停的季节,而作为这个季节的象征,作为消费主义精神的核心,圣诞老人是这个季节里最假的一个”。(18)尽管后来威利成为圣诞老人的使徒,但这并不妨碍他对消费社会的抨击。
威利对物质享受无动于衷,猛烈抨击消费社会,他关注的是自己喜爱的诗歌创作,一心一意像上帝那样,奉献爱心,服务社会。每年圣诞节那天,是威利唯一一天按时工作的日子。无论多累多难受,他都会爬起来穿上圣诞老人的衣服,到大街上晃荡一整天,给人送去希望和欢乐。这是他表达对教父尊重的方式,以纪念他的自我牺牲。威利认为活着就意味着奉献和付出。然而每当看到威利毫不犹豫地把他们的晚餐钱送给比他们富裕得多的人们时,骨头先生就觉得心疼,但他明白威利有他疯狂的道理(156)。视钱财如粪土,威利一向如此。母亲去世后不到十天,威利就把母亲留下的一万美元保险费都捐了出去,而他和骨头先生,却仍然过着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流浪生活。
在美国,中餐馆意味着美味,意味着极大的味觉享受,还意味着流浪狗的地狱与坟墓。自从威利的母亲去世后,四年来骨头先生从未吃饱过,但亨利为他提供了无穷无尽的美味,使他很快爱上了中国美食,对美味的期盼一度占据他的心思,生活在“地狱门口”的中餐馆后院的恐惧似乎也不那么可怕了。骨头先生过惯了和威利一起的简朴生活,从不耽于物质享受,如今却很快被美食所俘获,暂时忘记了自己的危险处境与精神追求,由此可见美食的巨大魅力,物质文明的巨大诱惑,更反衬了威利坚信理想与信念的决心与意志。
飞行员迪克对物品的符号价值了然于心,并能充分利用这些符号价值为自己服务。迪克为证明自己对妻子的爱,几个月前给她买了一套漂亮的大房子,带两个车位,还有精心修剪的草坪,宽绰的后院。这些东西具有使用价值的同时,也具有明显的符号价值,明显地代表着人与人之间地位、身份和声望的差异(蒋道超 2006: 659)。一座大房子,两部汽车,一个娇妻,两个孩子,外加一两只宠物,这些都是美国中产阶级的典型特征,意味着幸福、安逸、富裕和令人羡慕的社会地位。不幸的是,在这座光鲜亮丽的大房子里,却充满着阴谋与仇恨,爱情濒临死亡,家庭面临解体。波利爱这套大房子,却不爱迪克,只是她还未意识到这一点,夫妇俩都被消费社会的符号价值蒙住了双眼,失去自我,失去主体性。骨头先生的到来像个导火索,加速了波利自我意识觉醒的进程。她无视迪克的规矩,把狗放进屋里,并视其为心腹和知己。这小小的举动是她对迪克背叛与挑衅的开始,怨气已经变为勇气,撒谎成了家常便饭,这些都必将导致更大的矛盾与隔阂(150)。
在波利这里,物质生活的诱惑甚至再次腐蚀骨头先生那纯真善良的心。波利夫妇把骨头先生带入了一个和威利截然不同的世界,每天的新经历新感受让他应接不暇。坐在副驾驶位上和波利兜风,有规律的饮食,后院的烧烤,上等牛排骨,湖中游泳,富有艺术气息的购物中心……骨头先生对这些新体验乐此不疲,甚至开始怀疑老主人威利哪里出了毛病,为何要费尽心力地抵制这些美好生活的诱惑。两个半月后,骨头先生已经完全适应这种新生活,甚至不再在意爱丽丝给他取的难听名字,戴着锁链的日子似乎也不再屈辱。但这些都是暂时的,迪克的男性中心作风与人类中心意识,最终还是使骨头先生猛醒,进而义无反顾地放弃优裕的物质生活,甚至不惜放弃自己的生命,象征性地重回威利的精神世界,因为他所向往的,仍是与威利所过的那七年虽物质贫乏,却精神丰富的简单生活。七年中,他们无拘无束、互尊互爱、相依为命。一条狗尚且如此,何况人乎?物质与精神,孰优孰劣,一目了然。
在六畜中,狗最通人性,也最忠实于主人,因此不少中外作家都曾以狗为主人公来撰写作品。卡夫卡的《一只狗的研究》,屠格涅夫的《狗》,康拉德·劳伦兹的《狗的家世》,斯坦利·科伦的《狗故事》等,都是精彩的狗故事。①著名作家和编剧张嘉佳的新作《让我留在你身边》,也不约而同地以自己爱犬梅茜的口气创作故事。而在奥斯特笔下,骨头先生像人一样会思考,有七情六欲,能感知痛苦、绝望、恐惧、希望等情感,忠于自己的主人,希望自己是主人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非可有可无的点缀。与杰克·伦敦笔下的巴克和白牙一样,骨头先生比他所遇见的大多数人类高贵而值得尊敬。“我见的人越多,就越喜欢我的狗。”②普鲁士大帝弗里德里克的这句话,应该使人类汗颜。
尽管有评论家把奥斯特归为后现代,甚至后后现代作家,但奥斯特认为,严格来说,自己是现实主义作家(Brooker 1996: 157)。在一次有关《在地图结束的地方》的访谈中,奥斯特高度评价《堂吉诃德》,认为它是“小说中的小说”③,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堂吉诃德的影子,而威利和骨头先生,就像堂吉诃德和桑丘一样,形影不离,活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
将动物的生活经历作为小说的核心,从动物的视角观察社会百态,《在地图结束的地方》形象地反映了作者的生态伦理意识。摒弃人类中心主义和男性中心主义观念,倡导建立和谐的人类与动物关系,批判人类残酷对待动物的行为及消费主义的种种弊端,奥斯特花五年时间创作的这部篇幅不长的小说,带给人们太多思索。
① 白牙[OL]. [2014-08-07]. http://www.baike.com/wiki/%E7%99%BD%E7%89%99.
② 狗故事[OL]. [2014-08-07]. http://baike.baidu.com/view/2025151.htm?fr=aladdin,2014/8/7.
③ Interviews & Essays [OL]. [2014-08-04]. http://www.barnesandnoble.com/w/timbuktu-paul-auster/1100336770?ean=9780312263997&itm=1&usri=9780312263997.
Auster, P. 1999.Timbuktu[M]. London: Faber & Faber.
Barone, D. (ed.). 1995.BeyondtheRedNotebook:EssaysonPaulAuster[C]. Philadelphia: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Brooker, P. 1996.NewYorkFictions:Modernity,Postmodernism,theNewModern[M]. New York: Longman Publishing.
Brown, M. 2007.PaulAuster[M]. Manchester, UK: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Ittner, J. 2006. Part spaniel, part canine puzzle: Anthropomorphism in Woolf’sFlushand Auster’sTimbuktu[J].Mosaic(Winnipeg), 39 (4). http://www.questia.com/library/journal/1G1-158838831/part-spaniel-part-canine-puzzle-anthropomorphism.
Walker, J. S. 2002. Criminality and (self) discipline: The case of Paul Auster[J].ModernFictionStudies48 (2): 389-421.
保罗·奥斯特. 2012. 在地图结束的地方[M]. 韦玮译.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蒋道超. 2006. 消费社会[A]. 赵一凡,张中载,李德恩主编. 西方文论关键词[C].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汪民安主编. 2007. 文化研究关键词[C].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余谋昌. 2000. 生态哲学[M]. 西安: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