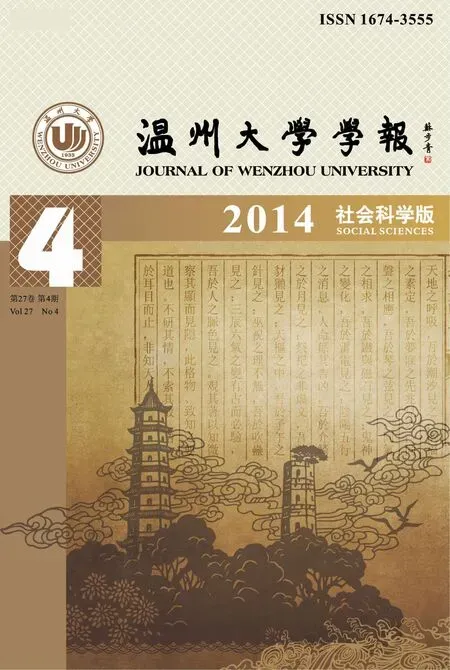论叶适对韩、欧碑志文的继承与新变
2014-03-20戎默
戎 默
(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上海 200241)
论叶适对韩、欧碑志文的继承与新变
戎 默
(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上海 200241)
叶适作为南宋前期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在文学方面的成就向来为人所称道,其碑志文更是散文中的一大特色。叶适碑志文不止继承了韩愈、欧阳修记录人物“随事赋形”“纪大略小”的特点,而且还呈现出一些新变化。叶适对人物事件的拣择详略,受其学术思想的影响很大。这种新变与南宋日趋深化的学术派别分野意识以及永嘉学派本身的思想特性有着莫大关系。而这也似乎暗示着一种南宋文学与学术关系的新形态的形成。
叶适;永嘉学派;韩愈;欧阳修;碑志文;学术思想
叶适,南宋大儒,政治家,不止在思想界、政坛声名卓著,而且在文学方面的成就也多为人称道,《四库总目提要》称“适文章雄赡,才气奔逸,在南渡卓然为一大家”[1],而其碑志文的写作更是特出于诸文之上,后世多有评价,如永嘉孙诒让称其“碑版之文,照耀一世,几与韩、欧诸家埒”[2]。其实,对叶适的碑志文,在南宋时期就为人交口推许,真德秀称“永嘉叶公之文于近世为最,铭墓之作于他文为最,……笔势雄拔如太史公,叹咏悠长为欧阳子”[3],黄震亦谓:“水心之见称于世者,独其铭志序跋,笔力横肆尔。”[4]而叶门弟子陈耆卿在叶适晚年代人上书求铭,书云:“今天下人子之欲显其亲,不以得三公九卿为荣,而以不得阁下之言为耻。”[5]可见叶适在当时作碑志文字方面的声誉。
一、叶适碑志文对韩、欧文的继承
叶适碑志文创作的一大特点,便是在突出人物形象特点方面颇具匠心。吴子良《荆溪林下偶谈》云“水心为诸人墓志,廊庙者赫奕,州县者艰勤,经行者粹醇,辞华者秀颖,驰骋者奇崛,隐遯者幽深,抑郁者悲怆,随其资质与之形貌,可以见文章之妙。”[6]在《毛积夫墓志铭》中,叶适刻画了一个不循俗常的奇杰之士,突出一个“奇”字,选取一系列与常人不同的“奇事”,展现了其不合时宜的个性,并对其终因“奇”而不得用于时的人生命运表示沉痛惋惜[7]408。《陈秀伯墓志铭》则将笔墨集中在陈尧英的几次上书之上,叙述他因上书而受高宗重视,却又因为上书得罪执政而被罢免,但其又屡上不止,抗言如故,不以升黜为意,将一个正直的骨鲠之臣的形象刻画得惟妙惟肖[7]347。
叶适碑志文创作的这种特点,显然继承于前代碑志文大家韩愈与欧阳修。韩、欧碑志,众人皆推,至有“古之作志、铭者,以韩、欧为准”的说法。两人碑志文的一大特点就是对人物形象刻画的重视,能展现出碑主与众不同的精神风貌,李耆卿《文章精义》认为柳宗元墓志“千篇一律”,而韩愈则“篇篇不同,盖相题而设施也”[8]。可见韩愈碑志迥出当时作手正体现在人物刻画的多样性上,所谓“人人殊面目”[9]“随事赋形,各肖其人”[10]等都表现了这一特点。欧阳修则将人物形象的突出与刻画视为碑志创作中的首要追求,并进一步提出记叙人物应当“止记大节”“纪小而略大”[11],即记录碑主生平事件应当有详有略,有取有舍,从而可以更加突出人物特点。
叶适十分推重二人,其云:“韩愈以来,相承以碑志、序记为文章家大典册。”[12]其门人赵汝谠也说:“昔欧阳公独擅碑铭,其于世道消长进退,与其当时贤卿大夫功行,以及闾巷山岩朴儒幽士隐晦未光者,皆述焉,辅史而行,其意深矣。此先生之志也。”[13]对欧阳修“纪大略小”的说法,叶适也有所申说,《陈同甫王道甫墓志铭》云:“志复君之仇,大义也;欲挈诸夏合南北,大虑也;必行其所知,不以得丧壮老二其守,大节也。”[7]482点出碑志文的人物刻画应该突出大义、大节。
不过,叶适的碑志文在人物形象的刻画方面除了对韩、欧碑志的继承外,也表现出了一定的发展与变化。细读叶适碑志作品可以发现,虽然叶碑对碑主生平事件的处理有着十分明确的通过详略变化“纪大略小”从而突出人物形象的意识,但这种详略的突出似乎并没有完全“随事赋形”,按照碑主本身的特点来撰写墓志,而是有着十分强烈的主观色彩,与韩愈的“谀墓”产生的主观情绪不同,叶适的这种主观色彩则是与其学术思想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叶适碑志文中表现出的这一特点是韩、欧碑志所没有,是新变化,这种变化与南宋学术思想的深化以及学术派别分野意识的加强这样一种学术背景有莫大的关系。
二、叶适碑志文对韩、欧文的新变
叶适有一篇比较有代表性的碑志文《司农卿湖广总领詹公墓志铭》[7]285,乃其为朱熹弟子、南宋理学家詹体仁所作。詹体仁的行状则是真德秀所作(《司农卿胡广总领詹公行状》)。行状这种文体作为一个人的传记资料,它主要注重的是对状主生前事迹尽可能详细的记录,《文体明辨序说》“行状”条说:“盖具死者世系、名字、爵里、行治、寿年之详,或牒考功太常使议谥,或牒史馆请编录,或上作者乞墓志碑表之类皆用之……而其文多出于门生故吏亲旧之手,以谓非此辈不能知也。”[14]需要事事皆详,与墓志铭这种文体稍有差异,而且还往往作为墓志铭拣择事迹的参考资料。因此,比对这两篇文章可以看出叶适对哪些事件详写、哪些事件略写、哪些事件略过不提,从而获取叶适在选取事件上的一些思路,也可发现学术思想对其碑志文创作的影响。
通过比对二文可以发现,叶将叙述的侧重点全部放在了詹体仁地方政绩这一方面,大书特书,甚至加以敷衍润色。他将碑主任职郡县一些琐碎的政事贯串记事,首尾加以评论点缀,以突出其“精神”[7]286:
“盖儒者之政,归于正己厚下而已。世吏所以便文自用者,虽善弗録也。为民利无不举,为民害无不去,以其下为当捐无不与,以其上为不当取无不革也。故公于浙西,开漕渠、浚练湖、置斗门,以备水旱。特散盐本钱数万,以业亭民。湖广币轻,出百万权其价,而放诸州积欠亦百余万。诸屯累重者,增劵给之。簸腐籴新,士食好米。又与鄂州运司同筑武昌万金堤。福州之僧坊以赂易,主者差其直,有常数,公一彻去。其在桂,则十县之税钱为阁一万四千,杂税朱胶为除八千。大凡州县之以用乏告,以赋重请,皆立应无留也。人或疑公且空有司之藏为百姓地矣。而公之财常源源暴暴,如泉涌山聚,此又世吏所难测也。”
而对詹体仁知静江府时改造农器一事,甚至较之行状更加详细和生动,加入人物语言,《行状》云[3]:
从图5可知,当电池组中某个电池单元出现热失控导致的起火冒烟时,电池预警防护系统界面中的火焰报警模块和烟雾报警模块分别以红色显示,并且信号值同时发生变化,说明设计的电池预警防护系统具备了及时预警的功能,在预警信号发生后,系统根据指令设计,将灭火动作下达至灭火模块,开启灭火剂管路向燃烧的电池喷射灭火剂,从图6可知首先是电池明火被扑灭,其次在电池明火扑灭后由于灭火剂的窒息冷却效果发挥作用,电池熄灭不在燃烧,表现为图5中的烟气探测值归零。
“复龙图,知静江府,春行视农见其田器薄小,不足以尽地力,乃为询访简易之法,物别为图授之。”
还是比较简略的,而《墓志铭》则说[7]286:
“复龙图,知静江府,始至,劳农观田器。公曰:‘是薄而小,不足尽地力,且无沟畎,何以行水?’乃更造农具,取水法,物别为图授之。”
而对其它大事件的处理,如定高孝二宗的谥号、以《周易》性理之说劝光宗过重华宫,预言皇甫斌必败等则叙述十分简略,笔墨能省则省。以说光宗过重华宫为例,《行状》云[3]:
“越岁召归班,至则除太常少卿。陛对,首陈父子至恩之说以感动上意,其略谓:《易》于《家人》之后次之以《睽》,《睽》之上九曰:‘见豕负涂,载鬼一车,先张之弧,后说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则吉。’夫疑极而惑,凡所见者皆以为寇而不知实其亲也。孔子释之,曰‘遇雨则吉,群疑亡也’,盖人伦天理有间隔而无断绝,方其未通也,堙郁烦愦,若不可以终日及其醒然而悟,泮然而释,如遇雨焉,何其和说而条畅也;伏惟陛下神心昭融,圣度恢豁,凡厥疑情,一朝涣然,若揭日月而开云雾,茂建皇极,丕叙彝伦,以承两宫之欢,以塞兆民之望,天下幸甚。”
详细记录了他劝导光宗的言论,而墓志铭则只用“(詹体仁)陈父子至恩,激发廷臣,使交疏迭谏,用意尤苦。”[7]286寥寥数语概括,不可谓不简略。
另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叶适在叙述詹体仁学术渊源以及学术特点的时候,也做了一个非常具有主观色彩的处理,即淡化其作为朱熹门人及其对性理之说的精通,而是着力突出他的百家杂学这一特点[7]287:
“公少从建安朱公学,得其指要。已而徧观诸书,博求百家,融会通浃,天文、地理、象数、异书,无不该极。”
与《行状》详细记录其朱学背景不同,《墓志铭》只用“得其指要”四字概括其朱学渊源以及学术修养,而对他学问的广博,不名一家倒着墨甚多。
显而易见,叶适对《司农卿湖广总领詹公墓志铭》的详略处理,似乎有意突出其在地方政治方面的功绩,从而刻画出一个非常善于治理地方实务的官员形象,这与一般历史上对詹体仁的印象有所出入,《宋史》称詹体仁“以存诚慎独为主”,俨然一副理学家模样。虽然《宋史》乃理学后学所编,有着夸大理学影响之嫌,但结合《行状》,亦可看出叶《墓志铭》乃刻意规避詹体仁的理学背景。可见,叶适的碑志文虽然继承了韩、欧碑志“纪大略小”即通过详略刻画人物形象的方法,然而,叶适所记之“大节”,所突出之重点,却没有那么“随事赋形,各肖其人”了。
三、产生变化的原因
叶适碑志在刻画人物大节方面展现出的主观色彩,首先来自当时学者中十分普遍的一种学术派别分野意识。这种意识发端于二程之理学建立之后,而正成于南宋中前期叶适所处的时代。这种意识的形成的影响因素则比较复杂,其一乃是传统文化中影响已久的“非此即彼”的线性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模式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已萌芽,《论语·卫灵公》篇云:“道不同,不相为谋。”[15]而这种思维在战国诸子百家争鸣时期极盛,《史记》卷六三《老子韩非列传》云:“世之学老子者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16]。不过,这样的思维模式在宋代之前仅仅停留在外部层面。所谓的此学派不合于彼学派也大多是党派之间的斗争。与之相对的是,先秦诸子对待各家之“道”,在内部的、精神层面之上,却显得异常“灵活”: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乃是道家,《老子》:“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17]即提倡最高的“道德”乃是没有固定界限之“不德”,《庄子·天下篇》则以诸家各自论道为失,认为自此“道术而为天下裂”[18]。而儒家方面,孔子也相对于不变之“经”提出可变之“权”与之相对①子曰: “可与共学, 未可与适道. 可与适道, 未可与立. 可与立, 未可与权.”,《礼记·中庸》篇则有“执其两端”[19]的说法。实际上,中国传统文化中,无论儒家道家,对于内部精神层面之“道”,一直采取一种十分圆通的态度。这种态度直到二程之理学建立之后才有所改变。而在二程之前的北宋学者,也依然如此,就以欧阳修为例,他有一篇文章《怪竹辩》,以竹之有灵无灵发端,证万物之道皆不尽相同,有不可知者,故当“治其可知者,置其不可知者”。其中说道:“万物生于天地之间,其理不可以一概。”[20]认为天下之“理”并不固定。而到了二程这里,这种对“道”圆通不定的态度就完全被打破了,程颐的观点十分明确,他说:“万物皆只是一个天理,已何与焉?”[21]主张当有一个统摄万事之“天理”,从而产生了一种“一定之理”的观念,这种观念对南宋学者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南宋学者无论是否被划定在理学学派之内,似乎都或多或少认为万物“理一”,尽管这种“理”之内涵各个学派都不一样。因此,各学派既然认自己之“理”为万物唯一之“理”,自然开始排斥其他与此“理”相悖之“理”,而南宋学派之分野意识之加强,关键便在于此处。对于这一点,叶适也概莫能外。他也认为道应该是“散在事物,而无不合于此”的,这样的表述和程颐所谓“一个天理”的表述可谓异曲同工。显然,“性理”之“理”与永嘉经制、事功之“理”有着一定的差异,并不是叶适认为的真正的“理”。叶适既然以永嘉学派之事功之理为真理,那必然排斥“性理”之“理”。因此,叶适在詹体仁墓志铭一笔带过讲论性理的朱学背景,乃有意为之。
那么,叶适学术思想中的哪些具体特性影响到了其文学创作?又是如何影响的?在一般对于叶适学术思想研究中,都会提到叶适作为永嘉经制学派的代表人物,他的学术在当时自出机轴,表现出与主流学术——理学相异的旨趣。这样的判断虽然似有过于夸大叶适学术与理学之间的相异性而忽略了其传承关系,但是,在论其学术自成一脉这一点上,还是值得肯定的。叶适的学术思想虽然承认了对自北宋以来理学家建立起来的对“理”的追求,其实也并不反对道德性命之说,但其在追求路径上还是有所不同,其外集《进卷》八卷有几篇文章透露出了其学术的关要所在,外集卷七《总述》篇开首即明其“道”之大意,其云[22]726:
“道不可见,而在唐、虞、三代之世者,上之治谓之皇极,下之教谓之大学,行之天下谓之中庸,此道之合而可名者也。其散在事物,而无不合于此,缘其名以考其实,即其事以达其义,岂有一不当哉!”
就十分符合理学建立起来的“理”所具有的“理一分殊”的特性。不过,他又强调说,要“即其事以达其义”,即要通过对具体事件的实践、考察来明了“道”,而不是通过“体认”“悟”来实现对道的理解,这也是他学术自成一派的关窍所在。
而在《皇极》篇中,他拈出《尚书》“皇极”二字,认为此乃“道德之本、众理之会”,不过圣贤认为其“微眇而难见”因此“特指其名而阙其义”,而“夫极非有物,而所以建极者则有物也。君子必将即其所以建者而言之,自有适无,而后皇极乃可得而论也”,认为要通过“建极”来达到微眇的“皇极”,那么,何谓“建极”,他解释说,“当尧舜之时,与其臣四岳、九官、十二牧建之。其最大者,禹以水土、稷以百谷,伯夷典礼,皋陶明刑,皆建极者也。”[22]728似乎,叶适认为,要达到“道德之本,众理之会”的“皇极”并不是去考察它究竟是个什么东西,而是通过具体治理百姓的手段来“建极”慢慢达到的。
叶适在《大学》篇还提到,“性命道德,未尝有超然遗物而独立者,”因此,君子应当“以物用而不为己用”“不须臾离物”,提出了一个人的“性命道德”的培养,是在与日常外物的接触中实现的,离开外物,便不可取[22]730。那么,叶适在墓志铭中突出詹体仁地方的政绩的原因也就明了了:显然,叶适认为一个人最重要的功绩便是“建极”,就是在治理人民上的实效,而墓志铭的文体特点便是突出个人的功绩。叶适在撰写墓铭时的这种倾向在其它作品中也得到展现,比如他为徐谊、蔡必胜写的墓志铭,二人都在孝、光两朝的朝堂之上有骨鲠直言之举,而且,二人都参与了立宁宗的事件。可以写的事情很多,但叶适还是对他们地方任上的实际功绩大书特书(如蔡必胜知楚州之平盗、知庐州之筑城;徐谊兴水利等事件)。
另外,我们还可以看到即使是一些没有作过官,无丝毫实绩可言而道德高尚的“处士”,叶适在撰写墓志铭之时也展示了其学术思想的特点,他并不是一味颂扬他品德的高尚,而是写出他在处理家庭、乡里关系的和睦融洽,如其《草庐先生墓志铭》云[7]376:
“草庐先生,姓林氏,名鼒,字叔和,黄岩县人。事父母兄无违志,朋友不倍其言,妻子裕如也,乡里欢如也,其行既修矣。……后生聚而谋曰:‘得无从草庐游乎?先生得无思见我乎?’邑大夫作而顾曰:‘某狱疑先生决之乎?某政谬草庐知之乎?’”
虽然这一段很明显有模仿韩愈之《送河阳温处士序》之嫌,但总体来说,对一名“处士”,叶适所记给人的感觉与传统“处士”有所不同——不是“高标一世,不与世俗同流”,而是与世俗和光同尘,其乐融融。这似乎也体现了叶适认为君子应当“以物用而不为己用”“不须臾离物”的学术思想特点对其文章创作的影响。
那么,叶适这一碑志文的新变又给予我们怎样的启示?自周敦颐提出“文以载道”的文学观念以来,文学与学术的关系日趋紧密。但是,文学与学术的结合通常只是表现在一种文学形态可以表达一种学术思想,也就是说,学术对文学所产生的影响仅仅停留于内容层面。而叶适碑志文的人物事件安排的详略却是文章创作方法上的问题,乃属于“文学形式”的问题,其学术思想又对此产生了影响。因此,叶适碑志文创作的这一例子似乎暗示,随着学术的日益发展,在南宋,学术思想对文学的影响已经从内容层面扩展到了“形式”层面。
四、结 语
注重人物形象的刻画乃韩、欧碑志文的一大特色,欧阳修更提出了通过记录生平事件的详略,“纪大略小”从而突出人物特点的创作理论,成为后世典范。而叶适作为南宋碑志文大家显然继承了韩、欧两人碑志文的这一特色,而且还呈现出了一些新的变化,即其对人物事件的拣择详略,受到了其学术思想很大的影响。叶适碑志文的这种新变与南宋日趋深化的学术派别分野以及永嘉学派本身的思想特性有着莫大关系。而这种新变似乎也暗示着一种南宋文学与学术关系的新形态的形成。
[1] 永瑢. 四库全书总目: 第2册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7: 2145.
[2] 孙诒让. 温州经籍志: 中[M]. 潘猛补, 校补.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5: 915.
[3] 真德秀.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 第35卷[M]. 四部丛刊景明正德刊本.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7.
[4] 黄震. 黄氏日抄·读文集[C] // 王水照. 历代文话: 第1册.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7: 870.
[5] 陈耆卿. 陈耆卿集[M]. 曹莉亚, 校点.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0: 51.
[6] 吴子良. 荆溪林下偶谈[C] // 王水照. 历代文话: 第1册.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7: 563.
[7] 叶适. 叶适集: 第2册[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1.
[8] 李耆卿. 文章精义[C] // 王水照. 历代文话: 第1册.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7: 1176.
[9] 陶宗仪. 南村辍耕录[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108.
[10] 钱基博. 韩愈志[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58: 134.
[11] 欧阳修. 欧阳修诗文集校笺: 下册[M]. 洪本健, 校笺.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 1842.
[12] 叶适. 习学记言序目: 下[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7: 733.
[13] 叶适. 叶适集: 第1册[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1: 1.
[14] 吴讷, 徐师曾. 文章辨体序说 文体明辨序说[M]. 罗根泽, 校点.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2: 147.
[15] 程树德. 论语集释: 第4册[M]. 程俊英, 蒋见元,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1990: 1126.
[16] 司马迁. 史记: 第7册[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2143.
[17] 朱谦之. 老子校释[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4: 150.
[18] 郭庆藩. 庄子集释: 第3册[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1: 1069.
[19] 朱熹. 四书章句集注: 第1册[M]. 影印本. 上海: 上海书店, 1987: 4.
[20] 欧阳修. 欧阳修诗文集校笺: 上册[M]. 洪本健, 校笺.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 565.
[21] 程颢, 程颐. 二程集: 第1册[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1: 30.
[22] 叶适. 叶适集: 第3册[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1.
Discussion on the Inheritance and New Change of Ye Shi to Han Yu’s and Ou Yang Xiu’s Epitaph
RONG Mo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China 200241)
As a famous thinker, statesman and writer of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Ye shi’s Achievements in literature has always been praiseworthy. The creation of epitaph in his prose writing is a major feature. His epitaph not only inherited the feature of Han Yu and Ou Yang Xiu about “shaped with the matter”, “through small, shown the large sections” on the record figure, But also show some new changes which Han’s and Ou’s epitaph have not expressed. His detailing and selecting about the character’s event has been greatly affected their academic thinking. This new change is related to the deepening awareness of the academic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factions in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and the ide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Yongjia school. This also seems to imply a kind of formation of new forms about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literature and of academic.
Ye Shi; Yongjia School; Han Yu; Ou Yang Xiu; Epitaph; Academic Thought
I206.2
A
1674-3555(2014)04-0045-06
10.3875/j.issn.1674-3555.2014.04.007 本文的PDF文件可以从xuebao.wzu.edu.cn获得
(编辑:刘慧青)
2013-10-17
戎默(1988-),男,江苏兴化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唐宋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