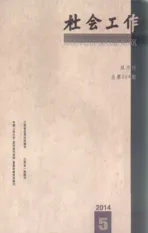医务社会工作在儿童临终关怀领域的实践
——以一位血液病患儿的临终关怀为例
2014-03-14刘潇雨
刘潇雨
医务社会工作在儿童临终关怀领域的实践
——以一位血液病患儿的临终关怀为例
刘潇雨
临终关怀是医务社会工作的一个重要领域,而儿童临终关怀是国内医务社会工作刚刚涉足的一个全新领域。本文以上海市某医院一个血液肿瘤科儿童临终关怀个案为例,探讨了儿童临终关怀中案主的需求、社会工作者的角色、服务的策略、介入的技术以及评估方式,并就儿童临终关怀服务中资源的链接、专业技能的运用、专业角色的定位和本土化的专业伦理提出了对策与建议。
临终关怀 儿童 医务社会工作
刘潇雨,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工作系社会福利专业博士生(香港 999077)。
一、问题的提出
临终关怀服务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英国,是帮助患者在临终前的几周或者几个月内,在生理上增强管理疼痛的能力,减轻痛苦,延缓病势发展;在心理上缓解对于死亡的焦虑,提升生活质量的服务。我国的临终关怀起步较晚,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目前,我国的临终关怀服务主要集中于成年人或老年人,甚少将关注点投向幼儿或儿童临终患者(安民兵、刘俊杰,2007)。
儿童临终患者较成人临终患者有其特殊性。在生理上,儿童对疾病和药物有着不同的反应,他们对乏力、恶心、呕吐、呼吸困难等不适症状以及抑郁和焦虑的情绪,有着不同于成人的表达,低龄患儿往往不能正确表达不适,需要家长协助制定个性化治疗的照顾方案;在心理上,儿童的心智发展尚未成熟,正处于情感、认知发展初期,往往无法理解死亡的真正含义,对于未知的死亡易产生恐惧和焦虑情绪;在社会关系上,孩子的死亡对其父母、兄弟姐妹、朋友、老师、医护工作人员而言,都是巨大创伤事件,会造成极大的痛苦和悲伤。特别是在临终的过程中,患儿和他们的家庭会经历生活质量下降、经济损失、无法选择临终场所等困扰,这些因素皆会使得患儿及其家庭陷入困境和压力之中。
为确保患儿临终过程中拥有高质量的医疗服务和心理疏导,需要医护人员和社会工作者的全程参与,并且需要临终关怀服务团队及服务体系的建立。在服务体系之下,服务提供者可以更加有效地评估患儿和家庭的需求,缓解患儿在生理和心理层面的痛苦,帮助家庭成员更好地处理患儿临终过程中的哀伤,明确照顾责任,以增进临终患儿及其家庭的福利。
儿童临终关怀是一个国内医务社会工作刚刚涉足的全新领域,有很多值得探讨的问题。本个案来源于在上海某医院血液肿瘤科的一次儿童临终关怀服务,希望能够通过本案例的研究和探讨为中国儿童临终关怀服务提供必要理论支持和临床经验。
二、文献检索
1948年,Nagy以儿童的死亡态度为研究基础,归纳出儿童对死亡理解的三个阶段(Kane,B,1979);皮亚杰认为儿童随着年龄增长,认知能力不断发展,对于死亡的概念具有更具体的认识,他将儿童对死亡的认知阶段划分为前运思期、具体运思期和形式运思期(Mark W.Speece and Sandor. B.Brent,1984);1999年,Faulkner也将儿童对死亡认知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结构性阶段、功能性阶段和抽象思考阶段(Frank,Viktor E.,2003:38)。中国学者张向葵(1988)对于学龄前儿童死亡认知的研究也认为,儿童对于死亡的认知从抽象模糊到具体清晰也有三个阶段。(见表1)。

表1 :儿童死亡概念发展表
除了有关对儿童死亡认知发展的探讨,存在主义中也有对于死亡问题的探讨。存在主义认为,死亡是有意义的,“向死而生”是存在主义理论中对于死亡的理解。人们对于死亡的认知既是生活经历的产物,同时也决定着生活经历。既可能使我们乐观地看待死亡,又可能给我们留下痛苦的经历(Corr,Charles A.,&Nabe,Chyde M.,&Corr,Donna M.,2011:15)。存在主义认为,首先需要解决的是对于死亡的焦虑和恐惧。存在主义治疗相信焦虑的意义,人在濒死时有焦虑是正常的现象,治疗师应该做的是如何减轻有害的焦虑。Yalom(2009)指出,对于死亡的焦虑越深,对于生活的满足感越少。临终的病人常常表现出冷漠,而这种情绪常常是对抗焦虑的消极手段。根据Frankl和Yalom的观点,死亡是一个孤独的过程,亲人、朋友以及有相同人生经历人的陪伴会减轻这种孤独感。
关于临终关怀,学者们认为时至今日,人们对它仍有很多误解,有的人甚至认为这个词就是“放弃”的意思,但实际上,临终关怀顺应了人们对自尊的渴望,满足的是宪法赋予他们的基本权力(Martin C.Granton,2012)。对于大多数癌症病人来说,晚期的疼痛会影响他们的睡眠和胃口,令他们情绪非常低落,因此临终关怀的一个重要意义就是减轻疾病带来的疼痛(Tutt B.,2012)。临终关怀服务将推动文化和医疗服务实践的改变(Stjersward J.,Foley KM,Ferris FD,2007)。
关于临终关怀社会工作服务,学者们也指出,建立和坚持临终关怀服务需要有四项措施:政策、可获得的药物、教育和执行。英国的临终关怀服务项目(National End of Life Care Programme)指出,社会工作在临终关怀中的作用在于帮助案主及其家庭,基于不同社区和文化背景,在临终关怀服务中帮助案主和家庭;在其中社会工作者要不断确认自己的角色和任务,增强案主和家庭对于死亡的认知并动员资源增强案主及家庭的承受能力(NEoLCP,2012)。其主要内容包括:(1)评估案主及其家庭需求,提供持续的照顾服务;(2)协调医疗团队,畅通沟通渠道,利用各种医疗或社会资源为案主和家庭服务;(3)以增能视角取代问题取向视角,使临终者与家人主动参与临终服务决策;(4)评估医疗资源和价值,有弹性及创造性地使案主可得资源最大化;(5)强调社会工作的专业伦理和心理承受能力(NEoLCP,2010)。
三、个案历程
(一)案主个人情况
案主W,10岁,2012年12月急性骨髓性白血病入院,治疗后好转,于2013年9月出院。10月白血病复发再次入院,骨髓涂片核细胞异常增生,说明其白血病复发,并伴睾丸、纵隔膜、头骨、眼眶、脑膜、肝肾,骨髓(少量)转移,抗肿瘤药物介入治疗无效,病情进行性加重。
案主在生理上表现为:(1)疼痛:左腿、口腔、小腿处以及右下肢肿块疼痛,加重时疼痛评估为6分(属于较重疼痛);(2)呼吸困难:纵隔膜肿块压迫呼吸道;(3)血液系统:血小板减少,骨髓抑制;(4)消化系统:案主消化道及口腔溃疡导致无法正常进食;(5)药物副作用干扰:使用吗啡介入治疗,患者大部分时间处于昏睡状态,每天的清醒时间不超过4小时。经常伴有头晕、头痛、恶心、呕吐,腿痛等。
案主在心理上,经由病患抑郁焦虑量表测量,结果为中度焦虑抑郁。案主对于自身即将临终的事实有一定了解,但家长对于其死亡的疑惑没有给出答案,而是含糊其辞,使得案主更加困惑,关于死亡和病情提问的频率不断增加,因得不到家长回复,心情抑郁低沉,沉默寡言。
患儿父亲37岁,货车司机,家中主要经济责任承担者,平日经常出车;母亲33岁,患儿主要照顾者,无业。患儿的外婆和爷爷跟随患儿一家生活,平日主要由母亲和外婆照顾,母亲自孩子出生之后就没有工作,医院日常照料由母亲一人承担。
(二)需求评估
在生理需求上,工作者通过疼痛量表、医院患者量表的测量和与案主的面谈,评估案主主要需求:(1)缓解疼痛:根据Oswestry功能障碍量表测得案主疼痛等级得分为40/45,说明案主的疼痛严重影响到案主的生活质量。需要对疼痛进行缓解,如利用注射吗啡帮助案主管理疼痛。(2)缓解呼吸困难:案主纵膈膜处长有肿瘤,压迫呼吸系统,需要通过雾化治疗缓解呼吸困难等症状。
在心理方面表现在:(1)缓解死亡焦虑:案主对于自己的病情有初步认识,预感到自己不久于人世,心中对于死亡存在疑惑,需要家长和社会工作者共同做出解答。(2)寻找生命意义:案主住院期间,生理上的疼痛让他情绪沮丧,丧失生存意志。社会工作者需要帮助案主寻找生命中的意义,丰富日常生活安排。
在社会关系方面:(1)家庭支持:案主需要从父母处获得情感上的支持,父母需在行动上表达对案主的关爱,在最后时刻陪伴案主,满足他的情感需求。(2)朋辈支持:案主长时间远离学校,希望得到同学的探望。朋辈群体的支持能够使案主感觉到被关怀和记住。(3)其他支持,包括志愿者服务和福利基金对于家庭经济的支持。
(三)干预目标
1.总目标
协助案主及其家庭平静面对死亡议题,缓解生理疼痛,发掘生命最后时刻的意义,由治愈目标转移到关注案主的日常生活,最终陪伴案主及其家庭直到案主生命终结。
2.分目标
(1)协调整合资源,为患儿及其父母提供信息支持,协助父母及患儿面对疾病做出理性决定;
(2)运用疼痛管理和姑息疗法缓解案主生理疼痛;
(3)协助案主处理死亡议题,使案主慢慢接纳身体的状况和死亡的现实,在生命最后时刻做想做的事;协助案主发掘兴趣,丰富日常生活安排;
(4)资源链接,增强朋辈群体、社会资源对案主的支持;
(5)协助家长从寻求治疗方法转移到案主生活中,平静地面对死亡议题并与孩子共同讨论死亡的话题,增强父母在案主临终关怀中的自主性,提升对案主的情感支持;
(6)在案主去世之后,对案主的家人进行哀伤辅导。
(四)干预策略
整个个案历时八周,具体安排如下:

会谈第一节目标及策略建立专业关系。第二节主要内容与案主家庭建立关系,签署个案协议。帮助案主了解疼痛管理和姑息服务的主要内容。帮助家长分析治疗过程的利弊,综合考虑案主意愿做出决定。信息提供,案主自决。第三节运用讲故事的方式帮助案主应对死亡焦虑。第四节用讲故事的方式帮助案主认识死亡,与案主讨论其对于死亡的疑惑和心中的焦虑。丰富案主日常生活安排,赋予生命意义;舒缓情绪。第五节“波动影响”,让案主感受到自己存在的意义。第六节第七节发现案主的兴趣,和案主一起制作作品集、相册集等,进行音乐冥想治疗。帮助案主回顾生命中感动的事和想要感谢的人,安排与老师同学的会面,和案主一起阅读老师同学的书信,协助案主写信表达情感。发现案主的愿望,在可能实现的愿望中帮他完成心愿。生命回顾法,与案主和家人共同回顾生命中的感动时刻。父母为案主准备了一封信,在情感交流中相互表达爱。第八节哀伤辅导。协助亲子沟通,表达情感,帮助案主父母接受案主即将离开的事实。进一步帮助案主家庭做好离别的准备。帮助案主家人处理案主死亡后的哀伤情绪。
具体的介入主要分了五个步骤:
1.协调临终关怀团队间的服务
临终关怀服务是一个团队协作合作的过程。团队成员包括患儿的主治医师、姑息治疗医师、社会工作者、护士。患儿主治医师负责患儿的诊断和用药,姑息医师负责减轻患儿生理疼痛,责任护士负责患儿的日常护理,社会工作者则是这个团队最重要的协调者和资源整合者。需要在医生、姑息治疗师、护士、志愿者间进行沟通,提供必要的信息(包括患儿心理、家庭及社会背景信息),保证团队在信息充分的情况下,做出适当的决定。
2.协调医生和患儿家属的分歧
当一个患儿由普通病房转至临终病房时,已经是给病患下了死亡判决书,对于患儿和家庭都会产生极大的消极影响。即使在得知患儿已经进入临终阶段,患者的家庭仍会不惜一切治疗手段在最后阶段给予患儿医疗救治(Chow,AYM,Chan,2006:513~520)。此时,社会工作者是医生和患者家庭之间重要的联系人。患儿每一步治疗方案的设计,都是在社会工作者协调医生与家长意见之后,由家长做决定。社会工作者先邀请医生作为专家向家长做专业解释,再帮助家庭分析各种治疗方案的利弊,最后由家长决定采取何种治疗,是继续坚持尝试不同疗法,还是以减轻痛苦为主的姑息治疗。社会工作者在此案例中协助解决的分歧有:是否进行骨髓移植、是否为案主插管治疗、是否送案主进入ICU病房以及患儿是否居家宁养。
3.整合社会支持资源
在临终关怀服务中,不仅要在家庭层面给予患儿支持,更要拓展支持层面,整合朋辈、志愿者服务及其他社会资源,为案主提供全面的服务。
在服务过程中,案主表达了两个心愿:一是希望在最后的时刻见一下老师和同学。社会工作者协助案主母亲联系了患儿的班主任和同学,并安排了会面。会面充分发挥案主的自主性,提前告知了案主,由案主自主决定会面时间、服装搭配、会面地点等。对学校老师和同学也做好防护措施,告知了患儿情况,帮助他们提前做好心理准备。二是希望在圣诞日见到米奇。社会工作者整合了志愿者资源,借助“香港迪士尼乐园米奇欢乐圣诞——关爱白血病患儿”的契机,在圣诞节安排米奇和米妮与案主见了面。
在政策和福利支持上,社会工作者向案主家庭提供了基金申请的各项渠道,为案主的治疗费用提供支持。
4.强调个别化的临终关怀服务
(1)增强案主的掌控感:疼痛管理
疼痛管理是病人通过药物手段对自身疼痛的控制,通过综合的、合理的治疗,缓解肿瘤造成的各种症状和疼痛,提高生活质量。相关研究评估疼痛表达和身体耐受力之间的联系,发现随着病人对痛苦报告数的增多,疼痛的强度有下降的趋势。也就是说,与他人表达和交流疼痛,有助于病人心境的改善和疼痛承受力的提高。在临终关怀阶段社会工作者能够进行在生理上介入,第一是增强案主对于自身疼痛的掌控感,如指导案主如何控制吗啡冲量;第二是给予案主自由表达身体疼痛的自由,如给案主疼痛等级的表情卡,每天在记录册上记录自己的疼痛状况,尽量让案主感觉能够知觉自己的身体状况,并主动去控制自己的疼痛。
(2)应对死亡焦虑:对死亡话题的探讨与生命回顾
死亡在中国人的价值观中是被禁忌的话题,“未知生,焉知死”的观念深入人心。在本案例中,与案主谈论死亡话题需要得到监护人许可。家长一方面没有完全接受孩子即将临终的事实,没有为孩子的离开做好准备;另一方面家长不知道如何与孩子探讨死亡的话题。因此死亡话题的探讨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社会工作者与案主探讨死亡议题。社会工作者征得家长同意后,与案主讨论死亡的话题,打消案主心中的困惑和疑虑。由于案主长时间呆在医院,其认知能力要略落后于其他10岁的孩子,因此他对于死亡的感觉,如死亡为什么会发生、自己为什么会死亡,以及人死亡之后何去何从等问题存在疑惑。社会工作者帮助案主认识到,死亡是人生必然要经历的事情,死亡并不只发生在老年人身上,小朋友、少年、成年人都会死亡,死亡了之后我们的身体不会感受到任何疼痛。案主十分喜欢小王子的故事,因此社会工作者选择了为案主构建一个《小王子》式的死亡过程,帮助消除案主对死亡的恐惧。
“每一个小朋友像小王子那样有一个星球,他们从星球来到爱他的爸爸妈妈身边。但是有的小朋友会生病,生很重的病,他们没有办法再呆在爸爸妈妈身边,要回到他来时的那个星球,那里也会有美丽的玫瑰花,有像小王子那样的小伙伴,很长时间的等待之后,爸爸妈妈也会到那个星球与他相聚。”
第二部分是家长与孩子共同回顾孩子生命中美好和感动的瞬间。死亡是一种孤独的过程,但是亲人和朋友与案主相伴会减轻这种孤独感。亲密关系表现在人际联结,用任何合适方式的安抚,说你想说的话,表明无论怎样都与你同在,不会抛弃你。这就是“在场的力量”(Frankl,Viktor E.,2003:38)。运用生命回顾的方式,利用家庭相册、日记等回忆方式,父母与案主共同回顾了案主10年生命中的许多美好瞬间。案主的父母与案主讨论了死亡的话题,并且做了形式上的告别。良好的亲密关系和家长的承诺会使案主降低对死亡的焦虑和恐惧,父母向案主承诺会一直爱他,陪伴他,并且他去到另一个世界之后不会有痛苦。案主也向父母表达了自己的心意,希望自己去世后父母不要难过。
(3)寻找生命意义:丰富案主日常生活安排
社会工作者在前期评估的过程中了解到患儿的兴趣爱好,知道案主喜欢手工剪纸和拼图模型。为丰富患儿的日常生活安排,让案主充分利用每天的清醒时间,社会工作者协助他制作了剪纸作品集和模型拼图图册,案主又将其分赠给其他病友。他的作品受到其他病友的喜爱,令患儿特别开心和有成就感。
(五)哀伤辅导:案主去世后对家属的抚慰工作
死亡虽然是人生必须经历的一部分,但是孩子的去世对于亲人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创伤事件。哀伤是对逝去的生命的正常反应。在儿童去世之后,临终关怀服务并没有结束,还需要为经历悲伤和丧亲之痛的人员提供心理、社会支持,以积极的心态和情绪状态来规划丧亲后的生活。
案主于第七次面谈之后去世,因此在第八次面谈中,社会工作者对案主的家长进行哀伤辅导。孩子的离开对于父母的打击是巨大的,尤其是母亲,由于母亲在孩子就医期间一直照料他,因此对于孩子的去世非常自责和后悔,认为自己没有满足孩子最后时光想要回家的愿望,心中充满了对孩子的愧疚和不舍。
首先,社会工作者帮助母亲平复情绪,探究她感觉到愧疚和自责的原因。自责、放大错误、寻找替罪羊,这是人遭遇创伤事件之后的自然反应。案主母亲所有的愧疚和自责、以及对父亲的愤怒都来源于无法接受孩子已经离去的事实。其次,社会工作者帮助父母亲梳理和回顾了在孩子临终阶段,他们为孩子做的所有事情,告知他们已经为孩子做了很多,他们在孩子最后时光的陪伴是对孩子最好的决定。第三,提升父母自我效能感,帮助母亲和父亲用替代补偿的方式与孩子告别,比如为孩子置办丧服、为孩子补办生日等,消除自责。最后,协调夫妻关系。强调夫妻虽然在孩子治疗过程中有分歧,但是他们都是基于对孩子的爱做出的决定,为了孩子,他们也要好好生活,因为他们是孩子生命的另一种延续。
四、总结与评估
通过量表和参与式观察,社会工作者进行了中期和后期评估(见表2),评估结果如下:首先,在生理疼痛上,案主能够根据社会工作者提供的信息,结合自己需要对疼痛进行管理;其次,在心理上,帮助案主和家庭共同应对死亡议题,最终阶段,案主与家人通过回顾相册的方式做形式上的告别,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案主对于死亡的焦虑以及对案主离去的遗憾;第三,在案主的家庭支持上,案主的家人给予了案主在生命最后时光的情感支持,尤其在最后阶段,父亲的陪伴对于案主情绪的缓解十分重要。

表2 :中期和后期评估
个案进行四次之后,社会工作者对案主情况进行了评估。由于案主口腔溃疡,语言表达不方便,主要通过访谈家人和医护人员进行评估。
在生理评估上,姑息医生使用疼痛量表对案主的疼痛情感作评估,等级下降到轻微疼痛;呼吸困难由于雾化治疗有所控制。案主在生理方面能够自主控制吗啡冲量管理疼痛,并且对自己每天的疼痛等级进行记录。
“感觉到他呼吸起来没有那么难受了,以前必须坐着睡,现在可以侧身躺着,我们每天都帮他贴表情卡,卡片上的表情也没有刚开始那么痛了”—案主母亲
“他最近状态还好的,我们根据他的情况帮他减少了吗啡冲量”—姑息医生W“他能够自己调控冲量,晚上喊我们也没有那么频繁了”—责任护士Z
在心理方面,虽然案主对于死亡的恐惧仍然存在,但是通过社会工作者和家人用故事的方法为案主构建了他即将要去的另外一个世界,他觉得将要死去的时光没有那么可怕了。
“这两天挺平静的,自从你给他讲了故事之后,他就没有再问过我死的事情,他以前一直痛,就不停的说,妈妈你让我死了吧,现在他不太这样讲了。”
在家庭和社会关系方面,案主表示,爸爸妈妈能在最后陪伴他一起看书、看动画片,妈妈爸爸为了他的心愿和想要的礼物四处奔波让他非常感动,学校同伴的探望陪伴让他最后的时刻减少了孤单和遗憾。
“我跟他妈妈最后跟他说的时候,刚开始真的很难开口,后来觉得说开了,每天陪着他看动画片,他笑我们也感觉好过了很多。”
“他拼了一个心形的图案送给老师和同学,他拿我手机给他老师发短信,他老师和同学这两天都发信息鼓励他,他聊天的时候特别开心。”——案主爸爸
“米奇来那天他特别开心的,很早就起床,穿好衣服,他已经很久没有这么开心了”——护士Z
结案之后,社会工作者又通过对医护人员和家属的访谈,进行了个案效果评估。在案主家人方面,他们表示目前已经能够接受案主离开的事实,也感谢社会工作者在案主生命最后给予的帮助。
“虽然有遗憾,但是最后满足了孩子的一些愿望,而且他也希望我们不要难过的。”——案主父亲
“最后跟他一起看相册,他说我爱你妈妈,那个时候我们一起哭……我还是感谢你能让我鼓起勇气跟他去说死的事情,说出来的感觉没有那么难了”——案主妈妈
“最后小孩走的蛮平静的,整个抢救过程也就十多分钟,后面他没有意识了,所以应该说走的不痛苦。”——护士Z
“这个小孩如果没有你们社会工作者跟进的话,肯定要多遭很多罪的,肯定到最后的结果就是过度医疗,很痛苦。你们介入支持效果是可以看得到的,每天查房的时候他也很配合,情绪也还可以。”——医生X
五、反思与对策研究
(一)构建跨学科的服务团队和督导体系
临终关怀服务的时间跨度长短不一,复杂程度不一,需要高效的、跨学科的团队协作,以保障案主及家庭能够得到有效的服务。在实际操作中,可运用个案管理模式,社会工作者作为独立第三方,对服务团队内各方资源进行有效整合。首先,社会工作者协调医疗服务与环境资源,并保证资源的取得富有弹性;其次,明确各部门间的责任,确保信息流的畅通和充分,保证案主及其家庭需求得到满足。
除了对于案主的支持,临终关怀可能会使社会工作者面临能力不济、情感耗竭的危险,在长达数周、甚至数月的关怀服务中,社会工作者随时需面对来自案主、案主家庭和医疗团队的诸多压力,此时,督导和同工的帮助和支持非常重要。在个案过程中和个案结案之后,需随时依需要获得督导,帮助社会工作者舒缓心理压力,提供专业支持。
(二)建立立足患儿和家庭整体需求的评估模式
儿童临终关怀的服务对象不仅限于患儿本身,还有患儿的家庭成员,是在评估患儿疾病种类、家庭背景、成员特质、过去经历以及心理、情绪、认知和行为的基础上提供的专业服务。系统的评估能够避免个案跟进过程中,因社会工作者缺乏对个案整体的掌控而出现被案主的问题牵制的现象,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过程。
儿童临终关怀服务的评估一般分成四个阶段:(1)接案评估:在生理上应评估患儿的身体状况、有无疼痛、清醒程度;在心理方面,应询问患儿和家人的情绪(焦虑、抑郁,悲伤、拒绝)、记忆、愿望等,了解患儿和家庭的心理期望和需求以及情绪状态、应对策略,以及任何存在的心理状况;在家庭方面需要尊重患儿的家庭文化、家庭价值观,以正确处理他们的焦虑、抑郁、愤怒、临终前期的悲伤和绝望等。(2)中期评估:社会工作者仍需对患儿的生理疼痛、心理状况以及需求的变化做密切的评估,这个阶段的评估涉及患儿和家庭的反应。(3)后期评估:在临终关怀后期患儿已经意识模糊,社会工作者无法完成社会工作者对其评估,此时一方面由社会工作者观察评估,另一方面由家长就患儿的需求和家庭的需求,通过家长的观察和自我陈述进行评估。(4)结案评估:患儿去世之后,对家庭跟踪回访,跟进评估个案效果。
(三)遵循儿童认知规律和中国文化特点对死亡议题进行讨论
死亡问题的讨论要符合案主年龄以及心智发展,并且需要根据家庭和案主对于死亡议题的承受能力,谨慎地探讨。本案例中,根据皮亚杰理论,在案主这个年龄段,“儿童认为死亡是不可逆的,每个人都会死,但是死亡只发生在老年的时候。这个时期儿童对于死亡的恐惧增加,对死亡的解释是具象或拟人化的(张淑美,1996)。”因此与案主讨论死亡议题需要根据其年龄以及心智发展特点,重点在于消除其对死亡的疑惑和恐惧,坦诚地谈论和面对死亡。
不同的文化塑造了人们不同的心理、行为方式,对人们的价值观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也即文化携带的内涵会在意义的层面上通过行为的方式清晰地表达出来。中国文化对于死亡的态度与西方社会不同,美国和德国从小学就开始对学生进行死亡教育,如模拟丧礼、遗体告别等,而死亡在中国文化中却是一种禁忌,父母对于死亡问题的回避源于他们自身的焦虑和恐惧。因此与案主谈论死亡议题时,应事先征得家长的同意,并和他们一起面对自身对死亡的疑虑和恐惧。在这个过程中,社会工作者始终扮演中介人的角色,当向孩子以故事方式呈现死亡议题的时候,由社会工作者向孩子直接表达,但一定要有家长的参与。
(四)强调社工的多元化角色
在临终关怀中,社会工作者的角色是多元化的。社会工作者不仅是链接医疗、福利救助资源的资源链接者,也是协助医务人员、家属沟通、交流信息的第三方支持者,更是带动案主整个系统趋向健康发展的使能者。社会工作者在临终关怀服务中的多元角色决定了社会工作者需要形成专业角色体系,在实践中的不同阶段对自己的角色重新认知、定位并进行角色整合。社会工作者在临终关怀服务中,还可以拓展的角色有:培训志愿者;为从事临终关怀的医护人员以及病人家属提供心理支持;在社区范围内宣传临终关怀,推动该事业的发展等。每个角色都很重要,而角色之间的协调和整合更重要。
(五)关注本土化的专业关系及价值冲突应对模式
在临终关怀服务之初,社会工作者一直强调单一专业关系的建立,但是随着介入的深入,面对这样一个巨大的哀伤,加之不断地与案主和家人的互动,社会工作者的情感投入也越来越明显,这种投入对于案主来说是一种有效的情感资源,但是对于社会工作者来说,需要警惕伦理困境及情感耗竭。这是在实务过程中,一定要非常谨慎的,如果有需要,一定要及时寻求督导的帮助。
在中国文化下,应对死亡议题并非易事。本案例中,患儿家长一直强调“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不会放弃我的孩子”,即使在患儿已经明确表示不想再做化疗时,医疗团队也明示化疗的意义不大时,妈妈仍然不肯“放弃”。此时,社会工作者虽不认同,但不能不尊重患儿家长的决定。这样的“忠于谁”的问题,在本案例中贯穿始终。与案主讨论死亡议题之初遭到家长的反对,社会工作者如果忠于案主,那么应当帮助案主解答死亡疑惑,但是由于案主未成年,因此必须要征得家长的同意,此时不仅要基于案主利益不断与家长沟通,更要让家长在做决定之时有足够的信息和资源支持,最终帮助家长做出更理性的选择;再如随着案主病情恶化,案主向社会工作者提出想要回家休养,社会工作者在帮助家长分析利弊之后,家长最终选择放弃回家休养。专业伦理要求社会工作者保证案主福祉的最大化,但是实践中案主家长又是事件最后的决定者。当案主和案主家长之间存在观点、利益的分歧时,社会工作者只能在提供足够信息的情况下,综合考虑案主的具体情况、家庭信念和社会文化背景,协助父母决定什么才是对孩子最好的选择。尊重案主自决,注意不要陷入专业操控,是一个非常难却很重要的过程。
(六)拓展临终关怀服务体系,以社区宁养作为补充服务
家的概念在中国文化中被赋予独特的意义,象征着安全和归属,临终患者重视家庭的温暖和舒适,家人的围绕对临终者的生活质量有积极的影响(李义庭、刘芳,2012)。在本案例中,案主在生命的最后时光希望回家休养,但是因为医护条件无法达到而搁浅,社会工作者选取替代补偿的方式,请家长从家中带来床单、被褥和居家摆设布置病房,让病房增添家的温馨。案主的需求折射出临终患者对于家庭温暖和社区宁养服务的需求。
美国以及台湾地区和香港地区已有完善的社区临终关怀服务体系,而内地的社区照顾尚未纳入医保体系。社区临终关怀服务作为院舍服务的补充和延伸,能够对病患和家属提供完整和全程的照顾服务。社区临终关怀服务需与医院临终关怀服务灵活变换,如果病患愿意,可以在家中走完生命的最后历程,但也允许病患在身体状况极度衰弱的情况下返回医院。应建立由主治医生、社区医护人员、病患、病人家属,社会工作者、家庭治疗师、志愿者等组成的服务团队,在居家宁养之前,由以上团队对病患生理、心理状况做全面评估,符合条件的,转入社区宁养,不符合条件的,进入医院临终病房。此举不仅能够充分尊重临终患者,满足其回归家庭的需求,还能够体现医疗服务的个别性和有效性。
儿童临终关怀是医务社会工作开展的一个重要领域,因相关照顾服务知识和实践的缺乏,在中国还是一个全新的领域,需要更多的探索与不断的实践。
[1]安民兵,刘俊杰,2007,《浅谈社会工作在临终关怀团队中的角色》,《卫生软科学》第4期。
[2]李义庭,刘芳,2012,《生命关怀的理论与实践》,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3]李幼稚,孙红梅,韩映红等,2004,《关于儿童死亡认知发展的研究》,《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期。
[4]刘翔平,1999,《寻找生命的意义一弗兰克尔的意义治疗学说》,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5]罗增让,2001,《社会性愿望对焦虑评定的影响》,《社会心理研究》第4期。
[6]张淑美,1996,《死亡学与死亡教育》,高雄:复丈书局。
[7]张向葵,1998,《3.5-6.5岁儿童对死亡认知的研究》,《心理发展与教育》第4期。
[8]Corr,Charles A.,&Nabe,Chyde M.,&Corr,Donna M.,2011,《死亡课:关于死亡、临终和丧亲之痛》,榕励(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9]Chow,AYM,2006,Qualitative study of Chinese widows in Hong Kong:Insights for psycho-social care in hospice settings,Palliative Medicinev.20 n.5,p.513—520
[10]Edvin S.Shneidman.,1984,Death:Current Perspectives.Mayfield Publishing Company.
[11]Frank,Viktor E.,2003,《追寻生命的意义》,何忠强、杨凤池(译),北京:新华出版社。
[12]Judy Oaks&Gene Ezell,1987,Dying and Death.GorsuchScarisbtick,Publisher.
[13]Kane,B.,1979,Child's concepts of death.Journal of Genetic Psychology.
[14]Martin C.Granton,2012,Rasouli case may help reduce misunderstanding about role of palliative care,the Globe and MAIL inc.
[15]Mark W.Speece and Sandor.B.Brent.,1984,Children's understanding of death:A review of three components of a death concept.Child Development.
[16]NEoLCP,2012,The Route to Success in End of Life Care:Achieving Quality for Social Work,National End of Life Care Programme(NEoLCP).
[17]NEoLCP,2010,Supporting People to Live and Die Well:A Framework for Social Care at the End of Life,National End of Life Care Programme(NEoLCP).
[18]Tutt B.,2012,Palliative Care may offer survival benefits,Oncolog 57:4-6
[19]Stjersward J.,Foley KM,Ferris FD,2007,The public health strategy for palliative care.J Pain symptom Manage33:486-493
[20]Yalom,Irvin,2003,《存在心理治疗》,易之新(译),台北:张老师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21]Yalom,Irvin,2009,《直视骄阳一一征服死亡恐惧》,张亚(译),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编辑/杨恪鉴
C916
A
1672-4828(2014)05-0039-09
10.3969/j.issn.1672-4828.2014.05.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