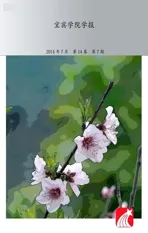钱大昕、钱大昭史学思想的异同
——以整理研究《后汉书》为例
2014-03-12杜高鹏
杜高鹏
(重庆三峡医药高等专科学校,重庆 万州 404100)
嘉定钱氏家族有“九钱”之称,以钱大昕、钱大昭为代表,为清代学术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成为史上“家学”传统的楷模。嘉定钱氏家族对《后汉书》的研究在所有《后汉书》的研究中具有一定地位和影响。钱大昕是钱嘉时期史学的代表人物,钱大昕的著作《廿二史考异》《三史拾遗》《十驾斋养新录》《潜研堂文集》《竹汀先生日记钞》等对《后汉书》有着精深的研究和独到的见解。钱大昭是钱大昕的胞弟,是乾嘉史学中颇具建树的一位学者,他尤精两汉史。钱大昭对《后汉书》整理研究的专著有《后汉书补表》《补续汉书艺文志》《后汉郡国令长考》《后汉书辨疑》《续汉书辨疑》等。钱大昕治《后汉书》涉及领域之广体现其知识面之“广博”,校勘精准、思维缜密可体现其“精”。钱大昭可谓治《后汉书》之专家,钱大昕兄弟研究《后汉书》成果突出,影响深远。钱氏兄弟有着相同的成长环境,钱大昭在思想方面受到其兄的影响比较大,所以他们的史学思想大体趋于相同,但是也有不同之处,具体反映在以下方面:
一 钱大昕、钱大昭史学思想的相同点
(一)经史并重
长期以来,史学一直是经学的附庸,学者们形成了一个共识——“经精史粗”,以至于“宋儒常言:读史易令人心粗”[1]。从宋代到清代这种思想还没有改变,包括一些从事史学的人也有这种“自卑”的心态。比如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小引》中言:“而资性粗钝,不能研究经学”[2]除了自谦的成分外,与当时的学术风气不无关系。钱大昕兄弟一直倡导经史并重,倡导“经史岂有二学哉”[3],这种思想对扭转当时的学术气氛有很大的作用。钱大昕不管是游学他方,还是在书院教学,他都倡导这一思想,受钱大昕启蒙从经学转向史学领域研究的学者不在少数,钱大昭就是其中的代表。钱大昭起初是以明义理而注经,后受到其兄的影响,遂“以达事为主”而考史。虽然钱大昭治学“经史并重”,但他一生中在史学领域的成就及其影响最大。
(二)语言规范,义例严谨
钱大昕认为作为史书,尤其是正史就要有一定的严谨性和规范性,不能随意写作,也不可用鄙俚俗语。如《后汉书·方术传下》:“而逢长房为谒府君。”钱大昕曰:“汉人称太守为府君,然叙事之文,当从其实。此传多采鄙俗小说,未及厘正,若东海君、葛坡君之称,岂可秽正史之乎?”并且强调:“流俗之称,不当用之正史。”[4]
在义例方面,钱大昕倡导规范,用通俗和常用的义例,以免造成误解。如《儒林传上》:“孔僖,世祖复封均子志为褒成侯。志卒,子损嗣。永元四年,徙封褒亭侯”[5]。钱大昕引“《孔龢碑》载:‘元嘉三年,司徒雄等奏称,褒成侯四时来祠。’又《韩敕碑》阴有褒成侯孔建寿名,碑立于永寿二年。又据《后汉书·安帝纪》,延光三年,赐褒成侯帛,及二碑俱称“褒成”,以证损未尝徙封,其说当矣”[4]。钱大昕引用了东汉时的两个石碑和《后汉书·安帝纪》,无“褒亭侯”之说,再考《续汉书·郡国志》无褒成侯国,于是他推出褒成之封,当是亭侯,非县侯。而按史例当书“褒成亭侯”,钱大昕推测,可能是脱“成”字,才使得范晔误以为徙封褒亭侯。
钱大昭在对待义例方面的态度也是一样,他倡导遵循通用义例,在《补后汉书年表》中对熊方义例不同于班固《汉书·表》之处作了大量的批驳,在其它著作中亦有表现。
如《后汉书·安帝纪》:“三年,东平陆上平言木连理”。章怀《注〈后汉书〉序例》曰:“凡瑞应自和帝以上,政事多美,近乎有实,故书见于某处,自安帝以下,王道衰缺,容或虚饰,故书某处上言也”[6]。钱大昭《后汉书辨疑》认为:“案《序例》之说亦未尽然,《桓帝纪》建和元年芝草生中藏府二年,嘉禾生大司农帑藏,永寿元年白鸟见齐国,延熹八年南宫嘉德署黄龙见,济阴东郡济北河水清,九年济阴东郡济北平原河水清。桓帝政事有何可美而不上书言?皆自乱其例。”[7]章怀《注》之《序例》所说值得商榷,言“自和帝以上,政事多美”,但钱大昭举出反例,“桓帝政事有何可美而不上书言?”并指出此是批评章怀义例不够严谨而“自乱其例”。
史书叙述应力求简要,而忌重复,“夫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而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8]。钱大昭对《后汉书》中的记载也是同样要求,他认为“《邓训传》:‘康以太后久临朝政’至‘遂免康官遣归国绝属籍’。案此事凡百三十余言,已见《邓后纪》,不必复载。”此处《纪》与《传》重复记载,这是不合义例,理应删除。
(三)广罗史料,博采慎取
钱大昕兄弟在校勘时,倡导广罗史料,包括山经、地志、金石、子集等。这是开始运用科学的实证方法为自己服务,尤其是钱大昕提出“金石之学可与经史相为表里”[9],其实在王国维提出“二重考证法”之前,钱大昕就开始实际运用了。清代方志学也兴盛起来,钱大昕倡导把研制地方志与考史结合起来,从而他的研究涉及到了历史地理学。他认为地方志是一方历史之征信,是考史最直接、基本、可考的文献。
钱大昭也是如此,他在作《续汉书艺文志》和《后汉书补表》时,就应用了许多前人未应用之文献,卢文弨称钱大昭著述“凡山经、地志、金石、子集之有于是书者,罔不网罗缀辑”[1]。他确实在著述过程中引用金石,如在《后汉郡国令长考》中引用《刘宽碑》《元宾碑》《鲁峻碑》《汉合阳令曹全碑》等材料,除此之外,谱牒家乘也使用,并兼采稗官野史,但他却不滥用,都是当作辅助证据。
(四)不掠人之美
在《后汉书》研究过程中,钱氏兄弟互相引证。钱大昕著述中多次采用其弟钱大昭的成果,所以说对于钱氏兄弟《后汉书》学之研究,不能截然将其分开。他们还经常引用同代人之成果,并一一标明,不将别人的成果占为己有。其实在历史上取别人之成果为己所有者也是屡见不鲜,而钱大昕兄弟能在那个稽查并不严格的年代,能保持这样的学术自律,这是没有崇高的学术道德作不到的。
《和帝纪》:“永元十五年,复置涿郡故盐铁官”。钱大昕言“晦之曰:‘盐’当作‘安’。《郡国志》:涿郡故安县。下刘昭注云:‘案本纪,永元十五年复置县铁官。’《前志》涿郡有铁官,无盐官,是其证也。”[9]
又如《续汉书·百官志》:“无虑有医无虑山。”钱大昕直接引钱大昭的论证:
晦之曰:“《安帝纪》元初二年,鲜卑围无虑县,又攻夫犁营。注云:‘无虑属辽东郡,有医无虑山,因此为名。’夫犁,县名,属辽东国。《鲜卑传》注亦同。然则章怀所见本,辽东属国有夫犁,无无虑也。无虑既属辽东,不应重出,窃意此“无虑”当是“夫犁”之讹,因声相近而耳误。此‘有医无虑山’句,当移于‘辽东无虑’之下。”[10]
钱大昕年较其弟长,学较其弟高,然引其弟之成果,并标明,令人感慨。
钱大昭也许在天文历算方面较之其兄略有不足,所以在《续汉书辨疑·律历志》中多处引用钱大昕之观点,如《律历志下》有“以周除日得三百六十五四分度之一”条,钱大昭言“詹事兄曰‘度’字疑衍。《律历》一篇,数理精微,非深于算学者不能考正,子兄校正本最精,今悉载之,其已刻在《考异》中者不列焉。”[11]但他还引用了钱大昕的观点数十条,说明钱大昕的许多考证成果在《廿二史考异》和《三史拾遗》中并没有体现,而钱大昭却引用,更能体现他不掠人之美和尊重兄长的一面。
钱大昭还引同代之说颇多,也可看出他并非厚古薄今和不掠人之美之德。又如《明帝纪》:“闲祀悉还更衣”。钱大昭引惠士奇曰:“东京庙制异室同堂。合祭于堂,是为正殿;闲祀于室,是为便殿,便殿为更衣。则闲祀非正祭矣。西京旧制,日祭于寝,月祭庙,时祭于便殿,寝日四上食,庙岁二十五祠,便殿岁四祠。则便殿乃时祭也,与东京不同,而闲祀皆于陵寝,诸儒以为非礼而罢之”[11]。他引惠士奇之说,为“闲祀”作注,说明闲祀非正祭,并阐明了西汉和东汉之不同。此外他也引用了卢文弨的观点和成果,但都一一标明了。
二 钱大昕、钱大昭对《后汉书》研究各具特色
钱大昕兄弟对《后汉书》的研究虽然不像王先谦的《后汉书集解》那样收集前人研究成果成为集大成者,但钱大昕兄弟在《后汉书》研究方面的成就和价值是极高的,并且具有自己的特色。
(一)钱大昕提倡直书,反对曲笔
刘知几引《左传》宣公二年“晋灵公不君”之故事:“如董狐之书法不隐,赵盾之为法受屈,彼我无忤,行之不疑,然后能成其良直,擅明古今”[12]以此来说明书法中直笔之重要性。钱大昕也提倡“史家以不虚美、不隐恶为良,美恶不掩,各从其实”[13]。他反对“春秋笔法”,“良史之职,主于善恶必书,但使纪事悉从其实,则万世之下,是非自不能拚,奚庸别为褒贬之词。”[14]认为史家应当把历史真实的一面反映出来,这也与干嘉学派还原古代经典原貌的思想是一致的。范晔在撰《后汉书》时许多资料取自《东观汉记》,而《东观汉记》溢美之词甚多,范晔有时不加分辨,而直接加以应用,对此钱大昕持反对意见。
比如《后汉书·崔骃传》:“贵启体之归全兮,庶不忝乎先子”[15],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引钱大昕言:“崔宗仕莽显贵,篆亦至二千石,已昧守贞之谊。汉室中兴,正当匡时以盖前愆,乃更辞归不仕,去就颠倒如此,而云‘无忝先子’,何颜之厚乎?”[15]以钱大昕之意崔骃祖父篆就不应在王莽当朝之时为官,而《崔骃传》就因崔篆辞官而对其大加赞赏,溢美之词过多,甚至颠倒事实。因此他指出:“此传叙述家世,词多溢美,盖由东观诸臣阿其所好,蔚宗承其旧文,不加芟削,未为有识也。”[15]
(二)钱大昭维护封建正统的思想
虽然钱大昭在史学领域的成就巨大,但其思想不可避免地存在局限。其中最突出的是,钱大昭在研究《后汉书》过程中体现出维护封建正统的思想。
例如《后汉书·李忠传》:“世祖会诸将,问所得财物,惟忠读无所掠”。对于光武皇帝问诸将所得财物之多少,只有李忠没有掠夺。其实一直以来,封建士大夫都在维护正统思想,王莽篡权而西汉亡,光武中兴以续刘汉,但是为什么汉光武帝的诸将们也会掠夺财物呢?钱大昭对此解释道:“是时兵少,势力虚弱,听任光之计,募发奔命,出功傍县,若不降者恣听掠之,人贪财物则兵可招而致。故‘问所得财物’,此权宜行之耳。忠无所掠,特优赐以宠异之,故能上合天心,下孚众望,非若更始居长乐宫,升前殿而问诸将后至者,更始虏掠得几何也”[16]。
依钱大昭之言,诸将掠夺财物之行为是为“权宜之计”,此言是在为刘秀之军辩解,很显然是其长期以来的正统思想在作祟,这与钱大昕提出的“不虚美,不隐恶”之思想,似有矛盾之处。
(三)两者对待古人不同的态度
钱大昕一生治学与为人谦虚,不苛求古人,在自己的著作中不指责和讥讽古人,即使对于古人著作中的错误也是平和地指出,就像柴德赓先生言:“西庄(王鸣盛)生活优越,性情骄傲,遇事一触即发,思想暴露无遗。竹汀(钱大昕)深沉,不多发议论,发必有深意,有时虽无议论,而字里行间,大有思索余地。随便看过,是捉摸不住的”[17]。柴德赓将王鸣盛与钱大昕做了一个比较,确实及其贴切,指出了钱大昕“不多议论”的特点。钱大昕在著述过程中遇到范晔、司马彪、李贤、刘昭、熊方等出现的错误时,指出即可,如言“此误”“注误”等,对熊方补《表》不依班固义例,也言“盖自出新意”,钱大昕所取得的成就与他一直抱着虚心向上的态度是密不可分的。
钱大昭与其兄相比,对于古人的错误和不足来说,则显得过于苛求。如钱大昭在着《后汉书补表》的过程中,对熊方《后汉书年表》中一些不依班《表》者或错漏之处一一予以批驳。如:“熊《表》脱漏甚多”[18]“熊氏不明此例”[18]“亦失史法,如此之类,不胜枚举”[18]“熊氏亦不注出,于史法亦疏”[18]“熊氏《表》又多谬误”[18]“熊表有不当载而妄载者”[18]等。而且对万斯同之补《历代年表》也进行了较为严厉的批评,如“近人鄞县万斯同补《历代年表》,于后汉有《云台功臣表》,但取二十八将,附以马援一人,疏漏浅率甚矣”[18]。更言“视熊《表》自郐无识矣”[18]。他指出除熊方以后的补表都不值得去评论了,其实万斯同《补历代年表》已经受到当时学术界的认可,也受到其兄钱大昕的推崇与尊敬,他主持修成《明史》更是被学人所称赞,其补表虽然有错误之处,但不能只视其缺点,而忽略其价值。
结语
钱氏兄弟治《后汉书》有着浓厚的家学色彩,重视小学、长于训诂,对《后汉书》的整理研究是从小学入手,进而拓展到其它方面,所谓“有文字而后有诂训,有诂训而后有义理,训诂者义理之所由出,非别有义理出乎训诂之外者也”[19]。钱大昕、大昭兄弟提倡经史并重、广罗材料、博采慎取、实事求是。此外他们继承了清初学者经世致用的思想,钱穆曾对乾嘉学术丧失了清初经世致用思想而痛惜不已。然而钱大昕却倡导经世致用,他说:“儒者之学,在乎明体以致用,《诗》《书》、执礼,皆经世之言也”[20]。钱大昭也是“以达事为主”而考史。钱氏兄弟的《后汉书》研究,是清代家学的一个缩影,反映出清代学术呈现的地域特色和家学特征,对后世影响深远。
参考文献:
[1] 卢文弨.后汉书三国志补表三十种[M].北京:中华书局,1985.
[2] 赵翼.廿二十札记小引[M].北京:中华书局,2001.
[3] 钱大昕.廿二史札记序[M].北京:中华书局,2001.
[4] 钱大昕.廿二史考异 [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
[5] 范晔,司马彪.后汉书·儒林传上[M].北京:中华书局,1965.
[6] 钱大昭.后汉书辨疑·安帝纪[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
[7] 刘知几.史学通义·叙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8] 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关中金石记序[M].卷二十五.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
[9] 钱大昕.三史拾遗[M].卷一.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
[10]钱大昕.廿二史考异·续汉书二[M].卷十四.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
[11]钱大昭.续汉书辨疑·祭祀志中[M].卷一.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
[12]刘知几.史学通义·直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13]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史记志疑序[M].卷二十四.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
[14]钱大昕.潜研堂文集·续通志列传总叙[M].卷十八.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
[15]钱大昕.廿二史考异[M].卷十二.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
[16]钱大昭.后汉书辨疑·李忠传[M].上海:商务印刷书局,1937.
[17]柴德赓.钱大昕研究[C].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1996.
[18]钱大昭.后汉书三国志补表三十种[M].北京:中华书局,1985.
[19]钱大昕.潜研堂文集·经籍纂诂序[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
[20]钱大昕.潜研堂文集·世纬序[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