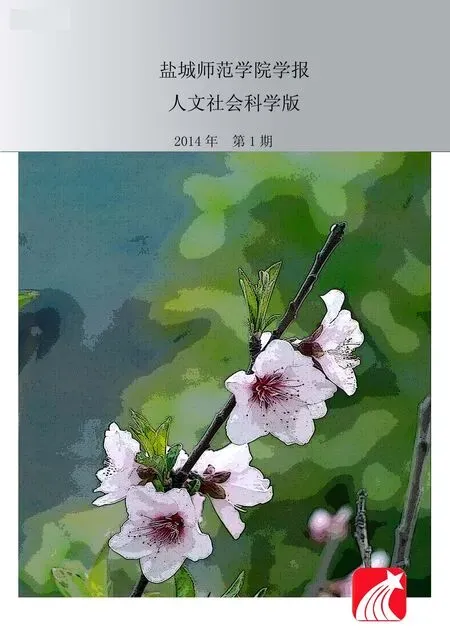明代宗臣的循吏思想及其实践*
2014-03-12顾国华
顾国华
(盐城师范学院 文学院,江苏 盐城 224002)
《明史·宗臣传》云:“宗臣,字子相,扬州兴化人。由刑部主事调考功,谢病归,筑室百花洲上,读书其中。起故官,移文选。进稽勋员外郎,严嵩恶之,出为福建参议。倭薄城,臣守西门,纳乡人避难者万人。或言贼且迫,曰:‘我在,不忧贼也。’与主者共击退之。寻迁提学副使,卒官,士民皆哭。”[1]7378宗臣既是一位爱国爱民的抗倭英雄,又是一名才华横溢的文坛才子,曾撰《报刘一丈书》揭露明代官场的黑暗,该文后被选入《古文观止》。对这位文武兼能的明代“后七子”干将,目前学界未有深入研究,关注点大多集中在《报刘一丈书》的单篇解读,笔者欲对宗臣循吏思想形成原因和实践活动进行深入观照,以便进一步考察嘉靖时期的官场生态环境、揭示宗臣循吏形象的意义和影响。
一、宗臣的循吏思想
“循吏”一词最早出现在《史记·循吏列传》中:“太史公曰:法令所以导民也,刑罚所以禁奸也。文武不备,良民惧然身修者,官未曾乱也。奉职循理,亦可以为治,何必威严哉?”《史记·太史公自序》则曰:“奉法循理之吏,不伐功矜能,百姓无称,亦无过行。作《循吏列传》第五十九。”相比之下,后者比前者表达得更为清晰——“循吏”即指那些奉法循理、不伐不矜、无称无过之吏。司马迁的“循吏观”与班固不尽相同。《汉书·循吏传》云:“及至孝宣,由仄陋而登至尊,兴于闾阎,知民事之艰难。自霍光薨后始躬万机,厉精为治,五日一听事,自丞相已下各奉职而进。及拜刺史守相,辄亲见问,观其所由,退而考察所行以质其言,有名实不相应,必知其所以然。常称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叹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讼理也。与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以为太守,吏民之本也。数变易则下不安,民知其将久,不可欺罔,乃服从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辄以玺书勉厉,增秩赐金,或爵至关内侯,公卿缺则选诸所表以次用之。是故汉世良吏,于是为盛,称中兴焉。若赵广汉、韩延寿、尹翁归、严延年、张敞之属,皆称其位,然任刑罚,或抵罪诛。王成、黄霸、朱邑、龚遂、郑弘、召信臣等,所居民富,所去见思,生有荣号,死见奉祀,此廪廪庶几德让君子之遗风矣。”[2]3624
班固特别强调循吏需仁爱百姓,富民教民,“所居民富,所去见思,生有荣号,死见奉祀,此廪廪庶几德让君子之遗风矣”。对比司马迁和班固的“循吏观”,余英时先生认为,“《史记》中的循吏和宣帝以下的循吏虽同名而异实,其中一个最显着的分别便在前者是道家的无为,而后者则是儒家的有为”[3]138。班固注重儒家积极进取的循吏观对后世有很大影响,明代宗臣得其沾溉,有比较浓厚的循吏思想。
明代宗臣在其诗文中四次提到“循吏”,其中三次提到了《汉书·循吏传》,分别见之于《赠曾公叙》、《赠陶先生之封川令叙》、《明瓯宁县令胡公德政碑》,充分证明了《汉书》循吏观对其影响之大。当然,《宗子相集》中所讴歌的循吏不限于此四篇,他还在《赠陈大夫之太平叙》、《赠查大夫报绩叙》、《武进白公集叙》、《赠巡台斗山樊公序》等文章中对那些具有循吏性质的官员进行了深情的礼赞。
综观以上作品,宗臣所称颂的循吏有以下特点:
1.心忧社稷,以民为本
宗臣《武进白公集叙》云白公忧愁天下,志在万里:“喜谈天下大事,每及兵戎,辄振缨髙论,勃勃英气逼人,人无不悚容而起者。至晚年更喜骑射,驰骋上下,志在万里。”宗臣《报郑侍卿》“明公深猷远策,下济民生,上培国脉,危言切论,尤足以感悟明主。”
宗臣在《明瓯宁县令胡公德政碑》中突出了民众的重要性:“夫天下之治系民,民系令,所从来长远矣。余读《汉书·循吏传》所称述咸守与令而卓、鲁诸君最着。迹其政,盖若慈母之于赤子,寒而絮,馁而哺,蹶而持,痛而抚,非夫文章之饬而礼乐之华也。”文中所称道的“卓、鲁”指汉代循吏卓茂和鲁恭。卓茂“性宽仁恭爱。乡党故旧,虽行能与茂不同,而皆爱慕欣欣焉……劳心谆谆,视人如子,举善而教,口无恶言,吏人亲爱而不忍欺之。”鲁恭认为“万民者,天之所生。天爱其所生,犹父母爱其子。一物有不得其所者,则天气为之舛错,况于人乎?所以他“每政事有益于人,恭辄言其便,无所隐讳”。范晔高度称赞他们的仁爱之心:“卓、鲁款款,情悫德满。仁感昆虫,爱及胎卵。”宗臣把胡公比作爱民如子的卓、鲁,胡公亦得到了民众的拥戴:“今公去瓯六十年,而父老悲思而祀之,则安知万世之下不以卓、鲁并公哉?”(宗臣《宗子相集》卷13《明瓯宁县令胡公德政碑》)
2.赈灾济民,抑制豪强
宗臣在《赠曾公叙》中感叹道:“余读《汉书》所称循吏传,未尝不投翰而叹也,曰:‘嗟乎!斯不负民哉!’以今睹于近事,则古今亦何殊焉!”他认为汉代循吏给他印象最深的就是以天下黎民苍生为念,为官一地,造福一方,即“不负民”。他亦以此古今无殊的标准来观照其笔下的官吏。灾荒是地方官常常遇到的难题,如何解决灾荒问题往往体现出地方官的仁心、智慧以及胆识。虽说有官仓储量,但朝廷管理甚严,且审批手续繁琐。地方官接到朝廷批文之时,可能早已饿殍遍野、死亡枕藉了。所以,有胆识且体恤民生的地方官往往采取比较灵活的措施,或开仓放粮,或截留漕粮,进行赈灾应急。如《明史·循吏传》中的徐九思曾担任嘉靖时句容知县,就是这种敢作敢为的好官:
岁侵,谷涌贵。巡抚发仓谷数百石,使平价粜而偿直于官。九思曰:“彼籴者,皆豪也。贫民虽平价不能籴。”乃以时价粜其半,还直于官,而以余谷煮粥食饿者。谷多,则使称力分负以去,其山谷远者,则就旁富人谷,而官为偿之,全活甚众。尝曰:“即天子布大惠,安能人人蠲租赐复,第在吾曹酌缓急而已。”
宗臣故乡兴化地势低洼,动辄发生水灾。“兴在扬,称困乃数十年,称大困。盖其地东亢西污,岁一值水旱,则耕者委耒,坐长蓬蒿”。当地老百姓日夜焚香渴望能有仁人君子来救民水火:“邑之父老子弟,日夜焚香告天,愿早得仁人君子来捄兹水火,乃曾君以名进士拜令兴”。曾公到后收治慓猾;赈济灾民;较射角矛以备岛夷;整冠束带,为民求雨。感动上苍,果降甘霖。曾公一系列举动深得百姓爱戴,“邑父老子弟,又輙日夜焚香告天,以为果得仁人君子来捄兹水火也”。(宗臣《宗子相集》卷12《赠曾公叙》)而另一位“以驾部郎左迁兴邑者”陈大夫同样仁爱子民,下车伊始“则顾怡貌恭容,日束带坐庭中视事,数数进父老子弟,问劳疾苦”。后又赈饥民,抑豪强,买卖公平,“于是邑之父老子弟家传巷诵,欢类更生。每朔则焚香膝行,望庭下拜曰:‘非明公,安有今日哉?’”(宗臣《宗子相集》卷12《赠陈大夫之太平叙》)除兴化外,浙江长兴也是水患频发,所以徐中行父亲认为“长兴至重至重者,不水利哉?岁水暴至,走数百里,田而山者立涸。其下者又坏堤决阜,无巳时也。胡不多其陂池而厚其堤?堤髙二丈,广十之,长百之,又多植桑、柘、桔、柚、竹、梧,阴阴丛丛其上也。岁且获木千章,桔千簏,笋万个,蚕万头,丝千两,鱼千石,何问暵潦哉?”(宗臣《宗子相集》卷13《明封承德郎刑部山东司主事东皋徐公墓志铭》)徐公除弊兴利,治本富民,颇有汉代循吏龚遂之遗风:
遂见齐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乃躬率以俭约,劝民务农桑,令口种一树榆,百本薤、五十本葱、一畦韭,家二母彘、五鸡。民有带持刀剑者,使卖剑买牛,卖刀买犊,曰:“何为带牛佩犊!”春夏不得不趋田亩,秋冬课收敛,益蓄果实菱芡。劳来循行,郡中皆有蓄积,吏民皆富实。
打击豪强,重绳盗贼,保障黎民百姓安居乐业也是循吏职责之一。福建巡台斗山樊公抑制豪强,伸张正义:“夫盗贼之起,莫不由于吏贪而豪肆,狱寃而市扰,事繁而财匮。今吏廉矣,豪绳矣,狱平矣,市理矣,传舍清矣,里甲节矣,则民又安肯以其父母妻子所仰赖之身而弃之于盗?则今日盗之所以渐弭者,非公之功而谁也?”(宗臣《宗子相集》卷13《赠巡台斗山樊公序》)“闽父老闲居,对其孥息诵公者,辄苏苏陨涕,恐公代。于是率其子弟数百人诣阙上书,固请留公。”(宗臣《赠巡台斗山樊公序》)査大夫“性简直不挠,即势族名家一罹于宪,则持之更急。人或言:‘大夫宜少徇时人情。’大夫谢不顾也。”(宗臣《宗子相集》卷12《赠查大夫报绩叙》)
3.重儒宣教,以德化民
汉代循吏非常注重教化,文翁、黄霸即为典型。文翁见蜀地辟陋有蛮夷风,即修学宫,重儒教,开一方文雅风气。“文翁,庐江舒人也。少好学,通《春秋》,以郡县吏察举。景帝末,为蜀郡守,仁爱好教化……修起学官于成都市中,招下县子弟以为学官弟子,为除更徭,高者以补郡县吏,次为孝弟力田。常选学官僮子,使在便坐受事。每出行县,益从学官诸生明经饬行者与俱,使传教令,出入闺阁。县邑吏民见而荣之,数年,争欲为学官弟子,富人至出钱以求之。由是大化,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2]3625黄霸任颍川太守时力行教化,天子下诏称扬曰:“颍川太守霸,宣布诏令,百姓向化,孝子弟弟贞妇顺孙日以众多,田者让畔,道不拾遣,养视鳏寡,赡助贫穷,狱或八年亡重罪囚,吏民向于教化,兴于行谊,可谓贤人君子矣。”
明代循吏也很重视教化之功。太祖时宁国知府陈灌:“天下初定,民弃《诗》《书》久。灌建学舍,延师,选俊秀子弟受业。”武间济宁知府方克勤:“社学数百区,葺孔子庙堂,教化兴起。”泰年间段坚初任福山知县“刊布小学,俾士民讲诵。俗素陋,至是一变,村落皆有弦诵声”,后擢南阳知府“创志学书院,聚秀民讲说《五经》要义,及濂、洛诸儒遗书。”[1]7029
宗臣笔下的地方官与汉、明循吏一样对教育相当重视。刑部山东司主事徐公“时时下帷授诸生经,诸生执经候门者,屦常满矣”(宗臣《宗子相集》卷13《明封承德郎刑部山东司主事东皋徐公墓志铭》)。瓯宁县令胡公“既以政而繋,瓯之父老之思督学君又以教而率瓯之子弟以趋于善。世有令德照于八闽,炳炳如日也。斯又汉臣所缺者。督学君则又具言,公之持身肃也。其俨而居,家人莫敢窥焉。遇乡之子弟辄教之,而公之门人由公之教以儒起家者如林矣。嗟夫,然则公之可纪独政哉?独政哉?”除教育门人子弟以外,胡公还针对当地陋俗,进行了移风易俗,乡民获益良多:“其革焚尸而示之孝;禁溺子而示之慈;法淫者而示之伦;察田尸而示之法;举释奠而示之礼。则何者非功哉!今瓯之民雍雍而纶纶,斤斤而井井,以惠于家而不坠其身者,是谁之遗也?”(宗臣《宗子相集》卷13《明瓯宁县令胡公德政碑》)
余英时在《汉代循吏与文化传播》中认为,大传统或精英文化是属于上层知识阶级的,而小传统或通俗文化则属于没有受过正式教育的一般人民。大传统的成长和发展必须靠学校和寺庙,因此比较集中于城市地区;小传统以农民为主体,基本上是在农村中传衍的。一般地说,大传统和小传统之间一方面固然相互独立,另一方面也不断地相互交流。所以大传统中的伟大思想或优美诗歌往往起于民间;而大传统既形成之后也通过种种管道再回到民间,并且在意义上发生种种始料不及的改变。而汉代循吏则成为大、小传统的沟通者,即他们扮演了文化传播者的角色。与酷吏相比较,循吏具有政治和文化两重功能。循吏首先是“吏”,自然也和一般的吏一样,必须遵奉汉廷的法令以保证地方行政的正常运作。但是循吏的最大特色则在他同时又扮演了大传统的“师”的角色。贾谊、董仲舒以来的大传统一直在强调郡守、县令必须发挥“师”的教化功能,而将执行“法令”的“吏”功能放在次要的位置。这是汉代循吏的思想渊源之所在。西汉中叶以后,循吏越来越以“师”自居,视“教化”为治民的首务,他们之终于成为大、小传统的中介人物,可以说是一种必然的归趋[3]171。
由此可见,无论是汉代的文翁、黄霸,还是明代的陈灌、段坚,以及宗臣笔下的徐公、胡公,他们不光是很好的“吏”,更是很好的“师”,他们成为大、小传统有力的沟通中介,富民教民,双管齐下,使老百姓雍雍纶纶,斤斤井井,而且后者的意义更大。多年前政治学者张纯明曾以英文发表了一篇研究循吏的专着,考察了中国史上自汉至清的循吏,指出循吏的成就表现出三个主要特征:1.改善人民的经济生活;2.教育;3.理讼。张氏特别注意到教育一项的重要性。他所说的教育则指两个方面:一是正式的学校教育,如文翁之立郡学;一是社会教育,即对于一般人民的礼乐教化。他并且强调说:循吏如果仅仅致力于改善人民的经济生活,而不同时对他们的文化和社会的生活也加以改进的话,那么他便不成其为第一流的循吏了[4]。如此看来,若只知使民众实仓廪,而不使其知礼仪,则不是“第一流的循吏”。倘以此为标准,宗臣突出徐公、胡公像汉代循吏一样,有重儒宣教,以德化民的教育之功,标志着他们确有第一流循吏的眼光,庶几达到荀子所说的“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荀况《效儒》)的境界。
4.所去见思,死见奉祀
宗臣笔下的许多地方官因以民为本,为民谋福,获得了民众的爱戴,当这些地方官调任或离任时,当地民众上书朝廷,希望他们继续留任。如挽留曾公:“邑之困赖公以苏,顾憔悴流离,尚充充然盈涂巷,是所望于公者更多也”(宗臣《宗子相集》卷12《赠曾公叙》);挽留陈大夫:“父老子弟闻大夫去,靡不顾妻子,感畴昔,靡不泪簌簌下也。”(宗臣《宗子相集》卷12《赠陈大夫之太平叙》)挽留兴化陈使君:“邑困甚矣,稍稍得保其父母妻子,而河伯又以一水鱼鳖之。天乎,天乎!我公其将谓何?姑孰之声藉甚,他日去之,则此地于公又何异兴也?以仆睹于当世之从事斯民者如公,难矣,难矣!”(宗臣《宗子相集》卷14《报陈使君》)循吏离任后,地方民众为了纪念其功绩,往往立祠祀之,如胡公即享有如此高的威望:“凡有功烈于民者,则祀之。古之道也。公之廉,之明,之勤,之惠……即不祠,何以解诸父老悲?思敢固以请,以附于古者有功而祀之义。”(宗臣《宗子相集》卷13《明瓯宁县令胡公德政碑》)
《汉书·循吏传》、《明史·循吏传》中有许多为循吏立祠祭祀的例子:
初,邑病且死,属其子曰:“我故为桐乡吏,其民爱我,必葬我桐乡。后世子孙奉尝我,不如桐乡民。”及死,其子葬之桐乡西郭外,民果共为邑起冢立祠,岁时祠祭,至今不绝。[2]3637
信臣年老以官卒。元始四年,诏书祀百辟卿士有益于民者,蜀郡以文翁,九江以召父应诏书。岁时郡二千石率官属行礼,奉祠信臣冢,而南阳亦为立祠。[2]3643
诚祖既得旌,益勤于治。土田增辟,户口繁滋,益编户十四里。成祖过汶上,欲徙其民数百家于胶州,诚祖奏免之。屡当迁职,辄为民奏留。阅二十九年,竟卒于任。士民哀号,留葬城南,岁时奉祀。[1]7191
庐山白鹿书院废,溥福倡众兴复,延师训其子弟,朔望躬诣讲授。考绩赴部,以年老乞归。侍郎赵新尝抚江西,大声曰:“翟君此邦第一贤守也,胡可听其去。”恳请累日,乃许之。辞郡之日,父老争赆金帛,悉不受。众挽舟涕泣,因建词湖堤祀之,又配享白鹿书院之三贤祠。三贤者,唐李渤,宋周敦颐、朱熹也。[1]7196
宗臣笔下的地方官秉承汉代、明代循吏的优良传统,克己奉公,廉政为民,跟黎民百姓休戚与共,赢得了广大民众的拥戴,在这些循吏离任后,民众或奏留,或立祠,以表达深深的敬意。
二、宗臣的循吏实践
宗臣不但熟悉《汉书·循吏传》,而且还饱蘸笔墨对那些为民造福的循吏进行了深情的讴歌,更重要的是,宗臣自己也是一个符合循吏标准的清官。
据史料介绍,宗臣1550年进士及第之后,曾有一段担任吏部考功郎的经历,对严嵩执政时期卖官鬻爵贪污腐化了解甚多,他不但没有随波逐流,而且还创作了名篇佳作《报刘一丈书》,借复信机会揭露了嘉靖官场行贿受贿的丑恶现状,表达了自己的一腔愤怒,同时也表现了自己高洁的操守。宗臣在被严嵩贬为福建参议之后,其时东南沿海倭寇猖獗。1558年四月,倭寇再犯福州,宗臣分守西门,活数万民众。王世贞《子相墓志》云:“君至而旋有倭难,当守西门。乡氓襁负求入者几万人。君戒门者内之。或谓:‘贼且近,奈何?’君曰:‘吾在,不虞贼也!’入甫毕,贼至……火具累百发洞中,贼死者无算,遂以溃去。”[5]1144嘉靖三十八年春(1559),宗臣由于战功卓著,迁福建提学副使。期间宗臣生活简朴,一省正气:“己未春,升按察副使,督闽学……行县试士则粝饭蔬食,时时披简啜茗,每吟哦,四顾萧然,立风日下。出则整衣拂屐,遇浊吏必怒目去之然后已。”[6]432宗臣“进按察副使,提督福建学政。闽,才薮也。臣所拔百不失一,惊以为神。条教数篇,士皆传诵。”[7]204其间作品有《福建己未贡士齿录序》、《移郡邑学官弟子文一首》、《总约八篇》等。其《总约八篇》包括遵帝、辨学、宏志、慎履、勤业、谈艺、端范、诫俗。他劝导诸生做孝子忠臣,重文武政教,以报效宗社朝廷:“以子则孝,以臣则忠,以士则修之家,以官则修之国,以庠序则教,以郡邑则政,以礼乐则文,以兵戎则武,以边疆则坐销敌人之气,不敢南向而牧马,以朝廷则目营四海之安危,而身负宗社之休戚。此学之正也,亦道之正也。”(宗臣《宗子相集》卷13《辨学》)他还针对福建地区的冠礼、婚礼、丧礼、祭礼陋习进行了抨击:
今夫冠而字之,圣人教天下以成人之道也。今髫而学者辄字矣,顷之号矣,未及胜衣,而已巍然大人长者之称矣。及其冠也,父既无以命子,甚至窃仕者之冠冠之,何谓乎?昏礼者,圣人教人以人道之始也。今也不择德,不论才,富则昏之,贵而富者亟昏之,鬻田聘妇,殚家遣女,佩环盈路,缯绨满车。不然者,夫厌其妻,而舅姑辄怒骂其妇。昏姻论财,古之君子夷之,而今乃甘心焉。丧礼者,圣人教人以厚终之孝也。今也苫块未视,布筵劳宾,饮食相藉,破涕为笑,召僧共佛,吹竽伐鼓,衰绖而居,展采姻聘。富有赀者,泥堪舆之说,而暴露其亲,以求利后人,贫者至以其亲骸而付之水火灭之,是仁人孝子之所惊悼而不忍言者也,而今之人何心哉!祭礼者,圣人教人以追远之孝也。今也大厦广室,高台曲池,少者千金,多者万金,而为之先者乃不得只尺之地而受享焉。贵人之临,供帐治具,烹羊炰羔,羞醑云缛,而为之先者则寻常羮豆之设,而无所加意焉。且岁时墓祭,又多男女之戏而耳目之观也,何视其先不若其身与客哉?(《宗子相集》卷13《诫俗》)
宗臣告诫诸生切不可随世从俗,表达了恢复古礼的愿望:“诸生内以谕其父兄,外以谕其乡之长老子弟,而稍稍习其说行之,雍雍磷磷,斐斐翼翼,而远近观则焉,则古礼虽不可尽复,其禁俗之不至于废礼也有余矣。是在二三子哉!是在二三子哉!”(《宗子相集》卷13《诫俗》)宗臣在福建提学副使的位置上,恪尽职守,简拔人才,教育民众,很好地沟通了大传统和小传统,具有强烈的循吏意识,成为“吏”和“师”二位一体的典型代表:“夫师儒者,士之范也,故曰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宗子相集》卷13《端范》)宗臣三十六岁逝于福建任上,远近恸哭,人人憾失良师。“庚申春,卒于官,越十余日,御史樊献科率诸司奉木主入祀‘名宦祠’。七闽之士远近恸哭,人人憾失良师。”[6]432
宗臣以自己的政绩和人格进入名宦祠,在当时确实是鹤立鸡群,因为明代到了世宗中叶官场生态环境非常恶劣。据《明史》卷七十二《职官志序》记载:“至世宗中叶,夏言、严嵩迭用事,遂赫然为真宰相,压制六卿矣。然内阁之拟票,不得不决于内监之批红,而相权转归之寺人。于是朝廷之纪纲,贤士大夫之进退,悉颠倒于其手。伴食者承意指之不暇,间有贤辅,卒蒿目而不能救。”朝廷乌烟瘴气,士大夫价值取向出现了严重背离:“今世所称士大夫,类抑外崇中,或以事外移,则负怨含恚,怏怏出。语盈道路,甚则高卧冀迁,不一至其地。即至其地,即又视其地如邮也,日对宾客,弄巵盂,投壶理局,吏人跽请视篆,辄怒目摄之,辄逡巡去矣。即去且不识其民,民何不忍哉?”(《宗子相集》卷12《赠陈大夫之太平叙》)可见士大夫多抑外崇中,一旦贬往郡县,则负怨含恚,怏怏而出。到任后,不少人整日盘算怎样鱼肉乡民,又怎能指望其像汉代循吏那样富民教民呢?“余读《汉书》所称《循吏传》至勤天子玺书赞诵,锡采章庸。当是时,天下之人,靡不瞿然惊已,洒然喜也。此其人必有英风殊略,表着耳目之外者,何至所状,卓、鲁诸臣汶汶闷闷哉?曰嗟乎!余于是知古道之所以兴隆也。世历弥降,学士大夫不谭隆古,一结绶临民,则壹志刑名期?而缓,厥民图其下,则更武遇其民,日鱼肉之。即家咨人吁,啖藻不给,乃其槖金,靡不巍然隆高也。斯何称吏治哉?”(《宗子相集》卷12《赠陶先生之封川令叙》)
事实上,宗臣生活的明世宗中后期,与明代前期吏治相比有很大差距。“自明兴至洪、宣、正统间,民淳俗富,吏易为治。而其时长吏亦多励长者行,以循良见称,其秩满奏留者,不可胜纪。”[1]7198而“嘉、隆以后,资格既重甲科,县令多以廉卓被征,梯取台省,而龚、黄之治,或未之觏焉。”[1]7185在如此恶劣的官场生态背景之下,老百姓对循吏的期待与呼唤是很急切的。“明中后期,朝政腐败,赋役繁重,加上官吏贪暴,豪强横行,冤狱遍地,百姓切望能有清官循吏出来‘为民作主’,凭借他们的道德良心和手中权力兴利除弊,减轻赋役,惩治贪污,搏击豪强,公正执法,平反冤狱,解救大众的苦难。但清官循吏却日见稀少,这就进一步增加百姓的期望值”[8]15。
宗臣正是百姓所期望的清官循吏,他刚正清廉,品行高洁,具有高度的责任感,上纾主忧,下除民瘼,内反权奸,外抗倭寇,重教诫俗,亲力亲为。最终积劳成疾,英年早逝。宗臣所作所为深得民心,士民为失去一位循吏而伤心恸哭,立祠纪念。宗臣被贬到福建后不是像同辈那样负怨含恚,消极沉沦,而是审时度势,积极进取,把贬所当作实现自己循吏梦的支点,远仰汉代循吏的风采,近绍明代清官的轨迹,将儒家的仁爱兼济思想和宣教化民的理念相结合,在短暂的仕宦经历中谱写了一曲人生的精彩乐章,与那些蝇营狗苟中饱私囊的贪官有霄壤之别。正因为难能可贵,所以才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才被人尊为一代伟人,士林伟范。
【参考文献】
[1] 张廷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2] 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3]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4] Chun-ming Chang. The Chinese Standards of Good Government:Being a study of “the Biographies of Model(Officials) in Dynastic Histories”[J].Nankai Social and Economic Quarterly, 1935,8(2).
[5] 宗臣.宗子相集[M].台湾:伟文图书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
[6] 欧大任.广陵十先生传·宗子相传[M]//四库禁毁书丛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7] 咸丰重修兴化县志[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
[8] 陈梧桐.论明前期的清官循吏[J].史学集刊,200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