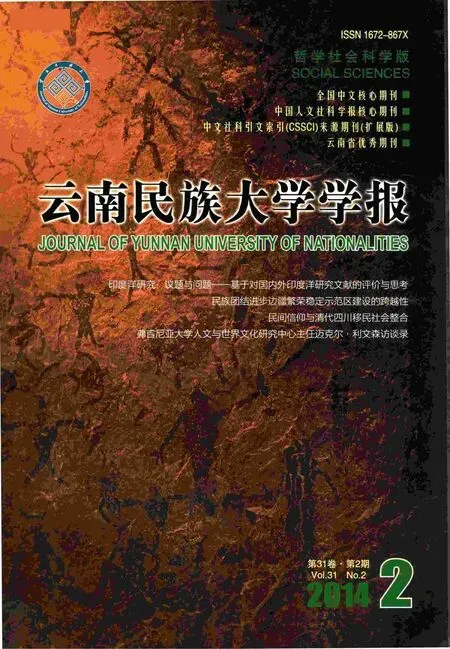宋代三教合一信仰格局对民间信仰的影响——以安岳、大足石窟造像为例
2014-03-06叶原
叶 原
(西南大学图书书馆,重庆 北碚 400715)
开凿于晚唐至北宋初期的安岳毗卢洞、园觉洞、华严洞、茗山寺等处石窟造像与开凿于南宋中晚期的大足宝顶山石窟造像同属柳本尊信仰所建道场。但后者除《华严三圣》、《柳本尊十炼图》等展示本信仰神祗、创始人等固有题材外,尚有《父母恩重经变》、《大方便佛报恩经变》等凸显孝亲观念的题材。两者间在造像题材上的差异与唐末五代至宋代国家权威、秩序由失衡转向稳定以及宋代三教合一思想格局的形成有关。
一、唐末国家权威、秩序的失衡与柳本尊信仰在四川地区的传播
柳本尊信仰的密宗色彩已被相关研究者多次论述,而安岳地区的石窟造像即为其早期道场。需要注意的是,在柳本尊之前,密宗已在四川地区得到广泛传播,其中僧人洪照为其中著名者。①参看黄阳兴:《中晚唐时期四川地区的密教信仰》,《宗教学研究》2008年第3期第107-112页。从有关洪照的史料记载来看,他传法乃是得到当时的东川节度使韦有翼之请,遂“居慧义般舟院,因得重新正观焉。常以真言祛邪逐崇,咒水治病救人,不可胜数”②黄阳兴:《中晚唐时期四川地区的密教信仰》,引全唐文卷806《东山观音院记》,《宗教学研究》2008年第3期。。又咸通年间:“蛮獠猖狂,将犯西蜀。有三藏僧洪照,召诸寺僧智海等,于旧基置降魔坛,号曰无能。节度使尚书独孤公因给牒,置院利人……”③黄阳兴:《中晚唐时期四川地区的密教信仰》,引全唐文卷806《东山观音院记》,《宗教学研究》2008年第3期。。再看《唐柳本尊传》碑的相关记载,其所言:“会广明离乱之后,饥馑相仍,民多疫疾,厉鬼肆其凶,居士悯焉。光启二年六月十五日盟于佛,持咒以灭之”、“时王建帅蜀,而妖鬼为祟,自称江渎神。天复元年正月十五日,持咒禁止之。妖性屏息,居士益自励。元间口口口救济,而秋毫无所受。蜀人德之”④陈明光:《唐柳本尊传》,《敦煌研究》,2006年第3期。。对照两人的史料记载,不难看出洪照与柳本尊的传法轨迹非常相似:首先是社会动荡导致国家权威、秩序失衡,如洪照记载中的“蛮獠猖狂”、柳本尊记载中的“饥馑相仍,民多疫疾,厉鬼肆其凶”;其次则是二人依靠密宗咒术传播信仰,如洪照“以真言祛邪逐崇,咒水治病救人”、柳本尊“持咒以灭之”、“持咒禁止之”。最后的结果是二人均得到四川地区官方、民众的认可、推崇。如洪照是“节度使尚书独孤公因给牒,置院利人”、柳本尊是“蜀人德之”。
从上述分析可以发现晚唐五代时期,四川地区社会的动荡,官方权威、秩序的失衡是推动柳本尊信仰传播的重要因素。值得注意的是柳本尊传法所用的咒术。《后汉书.皇甫嵩传》记载张角“奉事黄老,蓄养弟子,跪拜首过,符水咒说以疗病,病者颇愈合”①范晔 (南朝宋):《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299页。及《三国志.魏书.张鲁传》注引《典略》记载“师 (张鲁)持九节符咒,教病人叩头思过,因以符水饮之,得病或日浅而愈者,则云此人信道,或其不愈者,则为不信道”②陈寿 (晋):《三国志·魏书》,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64页。。从张角、张鲁的事例看,咒术是历代民间教团争取信徒,确立教主权威的重要手段,但这也会造成官方权威、秩序在民众心理上的瓦解,咒术之于柳本尊信仰也应有类似功能。此外,《唐柳本尊传》碑还有“然手指一节供诸佛”、“将香于左脚踝上烧炼,愿众生永不践邪摇之地”、“会嘉州四郎子神作孽,疫死甚众。居士割左耳,立盟以除之”等以自残方式表示信仰虔诚或展示神迹的行为③陈明光:重新校补宋刻《唐柳本尊传》碑,《敦煌研究》2006年第3期。,此种行为在安岳石窟、大足宝顶山石窟所凿《柳本尊行炼图》上均有表现,其功能与咒术大体相似。在晚唐五代的乱世,得益于官方权威削弱,像柳本尊信仰这样的民间教团能够凭借咒术、自残性宗教行为获得民众皈依,确立教主权威,甚至获得蜀主孟建推崇。④陈明光:重新校补宋刻《唐柳本尊传》碑,《敦煌研究》2006年第3期。但一旦社会由乱转治,教团也将丧失原先依恃的社会条件。
二、柳本尊信仰在宋代的处境
芮传明《论宋代江南之“吃菜事魔”信仰》一文分析宋代官方镇压“吃菜事魔”信仰的原因时认为,宋代官方对于“吃菜事魔”信仰的镇压出于两方面的顾虑:首先,“吃菜事魔”信仰具有的“烧香受戒,夜聚晓散,男女相杂”等宗教习俗有违官方所提倡的儒学道德;其次,也是最主要的还在于该信仰“倡自一人,其徒至千百成群,阴结死党”⑤芮传明:《论宋代江南之“吃菜事魔”信仰》转引廖刚《高峰文集》卷二,史林,1999第8期。、“夜聚晓散,相率成风,呼吸之间,千百响应”⑥芮传明:《论宋代江南之“吃菜事魔”信仰》转引宋会要缉稿166册刑法二,史林,1999年第8期。。这些“结党”、“聚众”都在事实上形成了独立于官方之外的权威,因此,官方会极力铲除这种潜在威胁。芮传明的分析可以作为探究柳本尊信仰在宋代处境的重要参考。首先,柳本尊信仰传法所依恃的咒术以及自残性宗教行为便有违宋代律法,如宋会要缉稿所言“诸色人燃顶、炼臂、刺血、断指,已降指挥,并行禁止,日来未见止绝,乞行立法”,其理由正是基于道德上的“毁伤人体、有害民教、况夷人之教,中华岂可效之”⑦葛兆光:《中国思想史》转引宋会要缉稿165册刑法二引政和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诏,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56~259页。。其次,参照张角、张鲁事例,咒术、自残性宗教行为还能够形成“结党”、“聚众”,从而威胁到宋代官方的权威、秩序。因此,宋代官方对此类行为是高度警惕的。《宋会要辑稿》即记载:“有以讲说烧香斋会为名,而私置佛堂道院,为聚众人之所者,尽行拆毁,明立赏典,揭示乡保”⑧葛兆光:《中国思想史》转引宋会要缉稿165册刑法二引政和四年二月五日诏,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58~259页。。文中的“私置佛堂道院,为聚众人之所”所指涉的正是像柳本尊信仰这样的民间教团。然而,即使赵智凤在大足宝顶重开柳本尊道场,依恃咒术、自残性宗教行为获取民众皈依的方式仍然被继承下来。其中的原因将在下文详为分析之。
揆之历史,柳本尊于正史与释史均无记载,这可能是该信仰为逃避官方打击,转入地下状态所致。此点亦可为后世史料所佐证,如清代道光年间所修《安岳县志》卷七《寺观·毗卢寺》在谈及柳本尊生平时仅云:‘《前志》,在治东八里,宋(实为唐末五代)方技柳本增 (为“尊”字误)置宝鼎于上’”⑨王家佑:《柳本尊与佛教信仰》,《佛教研究》2001年第2期。。县志虽修于清代,但所持观点可能有更久远的承袭。“方技”的称谓反映出柳本尊在安岳地区的传法活动并不为当地主流所认同,而时代与名字的讹误则进一步显示出柳本尊的传法活动并未在当地社会记忆中留下清晰印象,这与他生前所取得的名誉与地位形成巨大反差。而在柳本尊信仰湮没无闻近两百年后,赵智凤在大足宝顶兴建道场,使柳本尊信仰得到复兴,而这与儒释道三教合一思想格局的初步形成有很大关系。
三、宋代三教合一思想格局及佛、道在其中的作用
宋代是儒学复兴的时代,官方的礼仪典章、民众的生活习俗均由儒学主导,这一点乃是学术界的共识。或如杨庆堃在谈及中国宗教与社会的关系时所言“既不是佛教、也不是道教塑造了中国社会……。相反,中国社会是由不可知论的儒家传统通过士绅阶层来结构的”①庄孔韶:《人类学经典导读》,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405页。。而宋代官方对名山、五岳、渎川、神祗祭祀名单的调整、修正,以及广泛兴建学校,严禁民间巫觋、淫祀等举措,无疑也与儒学要求“一道德,同风俗”的文明宗旨有很大关系②参看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二卷第二编第三节“国家与士绅双重支持下的文明扩张:宋代中国生活伦理同一性的确立”,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53~279页。。
儒学无疑是主导宋代官方礼仪典章、民众生活习俗的正统思想,且它正统地位的确立也伴随着自身边界的清晰界定,士大夫对佛、道的激烈排斥。如道学家孙复在《儒辱》中申斥佛、道为“绝灭仁义、摒弃礼乐,以涂窒天下之耳目”③宋元《学案卷二“泰山学案”》,上海:世界书局,1936年,第58~59页。。但此种激进态度从未上升为官方的宗教政策。就官方而言,它更期望形成一种由儒学主导,三教合一的思想格局。或如宋真宗所言“:道、释二门,有助世教。人或偏见,往往毁訾,假使僧、道士时有不检,安可废其教耶?”④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419页。。文中所言的“偏见”、“毁訾”反映的即是儒学士大夫立场,而皇帝对此是不尽认可的。要言之,佛、道在宋代已渗透进官方礼仪典章与民众生活习俗的各个方面,因此官方不但不能将其废除,相反,从政权合法性的证明到民众的教化,官方对佛、道均有很大依赖。如宋代官方将道教的《斋醮式》和《金篆仪》等仪式纳入到国家祭祀体系⑤脱脱 (元):《宋史卷九十八》,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2422页。,皇室也追溯自己的道教祖先赵玄朗,以神话皇室。在某些情况下,道教甚至会与以正统自居的儒学在礼仪典章上发生争执。如元丰七年 (1084),宫中太史为当时还是皇子的哲宗皇帝选择好纳妃的吉日,恰好这一天被道教认为不宜婚嫁,并认为”违犯者必夭死”。于是“(皇太妃)持以为不可,上 (宋神宗)亦疑之。宣仁(宣仁皇太后)独以为此语 (道教观点)俗忌耳,非典礼所载,遂用之”⑥陆游 (南宋):《老学庵笔记》,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06页。。在这个事件中,尽管纳妃的吉日最终遵从儒学典礼,但道教的影响力也不容低估。
相比之下,佛教的影响更多地施于下层民众。如南宋理宗景定二年 (1261),吴县尉黄震从儒学孝亲观念出发,要求废除本地用于火化尸体的焚人亭。从黄震所言“案吏何人,敢受寺僧发觉陈状,行下本司,勒令监造”等语可知焚人亭实为僧人要求官吏修建的⑦张亮采,尚秉和:《中国风俗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129页。。火化尸体的习俗虽源于宋代人地关系紧张的事实,但该俗却滥觞于佛教。而从黄镇多少有些激愤的言辞中可以看出,尽管火葬违背儒学所倡孝亲观念,但本应服膺儒学的官吏在立场上却偏向佛教。由此可见佛教对民众风俗、乃至地方政府施政方针的影响。
从上述论述可知,儒学虽为思想正统,但佛、道渗透到从上层礼仪典章到下层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官方在制定政策时不得不顾及的因素。二者与儒学的关系也因此而显得复杂。一方面,官方把儒学视为正统,努力把佛、道吸纳入以儒学主导的三教合一的思想格局,共同维系政权稳定与合法性;另一方面,尽管向儒学观念靠拢是佛、道生存、传承的总趋势,但从以上两个事例可以看出在现实操作层面,儒学观念与佛、道间仍然存在不尽圆融的缝隙、有时也会相互抵触。既然佛、道并不因自身与儒学在礼仪典章、道德习俗上的抵触而被官方否定,那么柳本尊信也可以对所依托的佛教形式加以利用,使咒术、自残等带有违反官方权威、儒学道德嫌疑的行为得到一定程度的容忍,进而争取官方合法化承认。当然,容忍、承认的前提是表现出对官方权威、秩序的忠顺态度,避免官方将其视作“结党”、“聚众”的异端,具体而言即是为本信仰融入儒学孝亲观念。要言之,古代中国家国同构,忠孝一体的伦理治国理念,使得孝比忠更适合作为表述的语言。这不仅是因为家是国的根本,还在于以家族内的孝作为表述语言能够为统治披上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所谓在家为孝子,出门必为忠臣①参看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二卷第二编第三节“国家与士绅双重支持下的文明扩张:宋代中国生活伦理同一性的确立”》,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53~279页。。因此,在大足宝顶石窟造像中融入《父母恩重经变》、《大方便佛报恩经变》等孝亲观念题材便是赵智凤为柳本尊信仰争取合法化地位所采取的必要举措。这对民间教团而言并非难事,不过是在其本已杂糅的信仰内涵中融入新观念。
四、大足宝顶山石窟造像题材中凸显的孝亲观念及效果
大足宝顶山石窟第15号《父母恩重经变图》、第17号《大方便佛报恩经变图》是反映孝亲观念最为明显的题材。前者描绘怀胎、临产、生子忘忧、咽苦吐甜、洗濯、哺乳等父母抚育子女的辛苦场景;后者则描绘佛祖前生舍身饲虎、割肉供父母、亲探父王病、担棺葬父等事迹。据郭相颖考证,《父母恩重经》是唐人所撰伪经;《大方便佛报恩经》无撰写人名、年代,“系结集家之手草”,产生过程与《父母恩重经》类似,两者均为佛教迎合儒学孝亲观念的结果②郭相颖:《再谈宝顶山摩岩造像是密宗道场及研究断想》,《社会科学研究》1996年第1期。。事实上,自佛教传入中国始即有迎合孝亲观念的趋向。早在东晋时期,僧慧远在《答桓玄书》中便要求佛教“处俗弘教……忠孝之义,表于经文”,以使佛教“与王制同命,有若符契”③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93页。。但佛教内部宗派繁多,慧远的观点并不代表佛教界整体的认识,各宗派迎合孝亲观念的程度亦有深浅之别,某些宗派甚至持相反态度。如公元662年,唐高宗下令僧道必须致敬父母。为维护僧侣独立地位,当时作为“律宗”领袖的道宣率人到宫中争辩,终致使唐高宗废除原案④巫鸿:《礼仪中的美术——巫鸿中国古代美术史文编下卷“敦煌323窟与道宣”》,北京:生活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426页。。而就柳本尊信仰所渊源的密教而言,已有论者阐述宋代官方所明令严禁的“人祭”风俗与密教尸身法术的关系⑤刘黎明:《宋代民间的“人祭”之风与密宗的尸身法术》,《四川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北宋初期,官方亦因所谓“荤血之祀”、“厌诅之辞”的原因而中止翻译密教典籍⑥吕建福:《中国密教史第五章第一节“五代和宋朝的密教”》,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432页。。由此可见密教信仰与官方道德抵触之激烈。与之相佐证,在赵智凤之前,无论是《唐柳本尊传》、安岳石窟、抑或后世记载柳本尊的资料,均未在其信仰中发现孝亲观念存在的痕迹。据此可知,在造像题材中融入孝亲观念,于赵智凤而言固然是革新柳本尊信仰的创新,然若放置在三教合一的思想格局下考量,此举亦是佛教迎合儒学观念的必然趋势。
那么,赵智凤为造像题材融入孝亲观念的效果如何呢?根据最早的两则南宋时期有关宝顶山造像情况的文字镌刻大概可以推知。一则为宝顶大佛湾第5号造像龛底宇文屺《诗碑并序》 (据考证为1223年),其文曰“:剸云技巧欢群目,今贝周遭见化城,大孝不移神所与,笙钟麒甲四时鸣。宝顶赵智宗,刻石追孝,心可取焉,以成绝句,立诸山阿,笙钟麒甲。见坡诗,谓为神朸阿护之意也……南宋朝散郎知昌州军州事兼管内劝农事□□二江宇文屺书”⑦重庆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重庆市社会科学院大足石刻艺术研究所:《大足石刻铭文录》,重庆:重庆出版社,1999年,第233页。。一则为南宋嘉熙年间席存所著 (1237-1240年)铭刻残文:“赵本尊名智风,绍兴庚辰年 (1160年)出生于米粮之沙溪。五岁入山,持念经咒十有六年。西往弥牟,复回山,修建本尊殿,传授柳本尊法旨,遂名其山曰宝鼎。舍耳炼顶报亲,散施符法救民。尝垂戒曰:“热铁轮里翻筋斗,猛火炉里打倒悬。”嘉熙年间,承直郎昌州军事判官席存著为之铭⑧重庆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重庆市社会科学院大足石刻艺术研究所:《大足石刻铭文录》,重庆:重庆出版社,1999年,第211页。。
宇文屺为昌州 (大足)地方的军事、行政长官,席存的承直郎官阶虽为八品,但也属于官方体制内人员。两人的观点很能够代表官方对于赵智凤的态度。根据行文,两人对赵智凤的推崇均源于其“孝”。相比而言,席存对赵智凤的信仰情况描述得较为详细。更为关键的是,席存将舍耳、炼顶、咒术符法解释为“报亲”、“救民”的动机,这便为柳本尊信仰中的舍耳、炼顶、咒术符法等即违反儒学道德,又威胁官方权威、秩序的宗教行为进行了合法化解读。席存的解读尽管在逻辑上极为牵强,但所表现出的对儒学道德与官方权威、秩序的服从态度至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官方的安全顾虑,不将柳本尊信仰视作“结党”、“聚众”的潜在隐患。此外,在表现孝亲观念的造像题材外,宝顶山石窟尚有《释迦舍利宝塔禁中应现之图》,图附碑文曰: “上祝皇王隆睿算,须弥寿量愈崇高”①重庆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重庆市社会科学院大足石刻艺术研究所:《大足宝顶山小佛湾“释迦舍利宝塔禁中应现之图”碑》,《文物》1994年第2期。。正如前文所述,由于古代中国家国同构,孝亲观念乃是“忠”的投影。故直接向皇权表述忠心不过是《父母恩重经变》、《大方便佛报恩经变》等孝亲观念题材的题中应有之义。
依托佛、道形式,在造像题材中融入孝亲观念并以孝亲观念解读本信仰所含的异端成分 (无论其在逻辑上是否成立)即是赵智凤及其教团组织为柳本尊信仰争取官方合法化承认的主要思路。揆之历史,此种思路亦非孤例,乃是宋元间不被官方合法化承认的民间教团所普遍采用的。如宋元间最具影响力的白莲教在元初得到官方合法化承认,但由于白莲教也具有“夜聚晓散”、“男女杂处”等特点,还是被元代统治者视作扰乱道德,甚至聚众滋事的威胁,故又将其禁止。为恢复合法化地位,当时白莲教的领袖普度著《庐山莲宗宝鉴》、《万言》,极力向官方辩解。其所述要旨,一是将本信仰源头追溯到东晋慧远创制莲社,强调自己的佛教正统身份,而非“吃菜事魔”的邪教;二是将“夜聚晓散”、“男女杂处”归咎于白莲教在传播过程中的“叨滥者众”、“以伪乱真”;三是极力鼓吹本信仰“会三教 (儒释道)归一元”、“斋心念善,弥感圣朝之隆德”、“念佛之道有益于国化”,也即阐述白莲教对官方权威的忠顺态度以及帮助官方教化人心的功能②冯佐哲,李富华:《中国民间宗教史第七章第三节“白莲教在元朝的发展”》,台湾:文津出版社,1994年,第184~197页。。经过普度的力争,官方终于恢复白莲教的合法化地位。
即使那些在信仰上与佛、道边界相对清晰,异端色彩更重的民间教团,亦强调自身与儒学道德的契合。如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谈到在闽中地区流行的摩尼教 (明教),并称“至有士人宗子辈,众中自言道‘今日赴明教斋’”。陆游诘问那位士人:“此魔也,奈何与之游”,那位士人辩解称:“不然,男女无别者为魔,男女不授受者为明教”。“男女无别”正是前文官方指控“吃菜事魔”信仰的罪证,而“男女不授受”则是儒学观念的体现,却也为摩尼教所具备。正因为如此,陆游虽称摩尼教为“魔”,那位士人还是从儒学观念出发为摩尼教辩解。同篇还记载“又或指名族士大夫曰‘此亦明教也’不知信否”③陆游 (南宋):《老学庵笔记》,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25页。。可见摩尼教在当时应该吸纳了某些儒学观念,以致于连士人阶层也无法分辨,普通人更是将其与儒学士大夫名族混淆。
从上述分析中可知在宋代三教合一的思想格局中,儒学虽被尊为正统,但在现实层面,儒学与佛、道间实存在缝隙、且时有相互抵触。三教合一的格局虽已成形,但相互间的融合尚难称圆通。这些缝隙或抵触之处便可为柳本尊信仰这样的依托佛、道形式的民间教团所利用,并在孝亲观念的话语表述下,消除官方在道德,权威、秩序上的顾虑,进而获得官方合法化承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