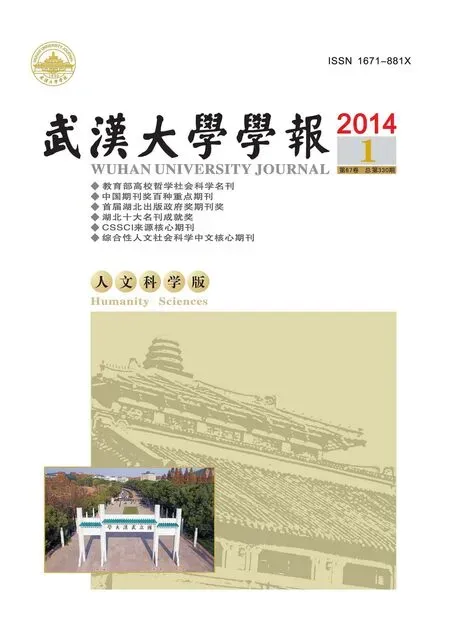神游鸟道贯中西
——萧师与佛学研究
2014-03-04龚隽
龚 隽
我的导师萧萐父教授是中国哲学史的大家,20个世纪80年代以来,他有关明清哲学史的论述蜚声海内外,而他所主编的《中国哲学史》(上下卷)也成为国内许多大学哲学教材的一时首选。我自己最初对中国哲学史的入门学习,除了冯友兰先生早年撰述的《中国哲学史》外,就是从先生主编的这部《哲学史》中去作解读与领会的。大体说来,佛家与儒、道两家共同构成中国传统思想与哲学的纲骨,这一点即使现在看来也不为过*陈寅恪先生在为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所撰“审查报告”中就说“自晋至今,可以儒释道三教代表之。此虽通俗之谈,然稽之旧史之事实,验以今世之人情,则三教之说,要为不易之论”。见冯著《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439~440页。。于是,佛学理所当然地应该成为理解中国哲学史中的一个重要面向。自近代中国哲学史的书写开创以来,大凡哲学史家无论对佛学的轻重存在着如何不同的意见,都对中国佛学的观念有所论评。佛学成为中国哲学史创作中一个不可绕过的环节。无论是对六朝或是隋唐哲学史的理解、书写,都不能回避佛学的议题,甚至对宋明理学乃至近代中国哲学史的论述,也无法抛开佛学的影响于不顾。而困难在于,作为中国哲学史重要一环的佛学本身又是一个相对独立与外来的思想系统,这需要我们对佛学的理解与研究不能仅局限在中国思想和哲学的脉络下来作论述,而是要贯通中印,即对印度佛学,甚至印度学具有一定的知识准备,才能够对佛学的思想获得恰当的理解。这是近代汤用彤、吕澂等一批佛学史大家所共持的见解。
自胡适截断众流地以现代知识史的方式首创中国哲学史的书写以来,就一直萦怀于佛学的问题而上下求索。胡适自己完成他的《中国哲学史》上卷后,处理到中古中国哲学史的议题时就碰到棘手的佛学问题,这使他放下原有哲学史的思考而转入到专门的禅学史研究。这一做法也表明,佛学问题之复杂而使他无法简单地在原有哲学史的脉络下来作论述了*关于胡适禅学研究与其中国哲学史研究关系,可以详见拙作《胡适与近代形态禅学史研究的诞生》,刘笑敢主编:《中国哲学与文化》第5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41~270页。。冯友兰先生续著《中国哲学史》,对现代中国哲学史的著述具有“典范”的效应,虽然其第二篇“经学时代”对六朝隋唐佛学的许多观念皆有述义,颇费周章,但中国佛学的论述仍然成为其哲学史论述中较为薄弱的部分。可以说一直到今天,中国哲学史上不少议题缺乏突破性的新见,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缘于中国哲学史界对佛学的论述,缺乏有系统与深度的研究。
先生对佛学素有兴趣,他治中国哲学史其中一环就是要“玄化通观”地把中国思想与印度所传佛教进行贯通。他在1996年纪念石头禅及曹洞宗学术讨论会中曾经占诗一首,表达了他学贯中印(即传统所谓西学)的思致*其诗云:“玄化通观涵渐顿,神游鸟道贯中西”,见其文《石头希迁禅风浅绎》,载《萧萐父文选(上)——思史纵横》,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94页。。虽然他仍然是在中国哲学史脉络下来解读和处理中国佛学的观念,在佛学的研究上不见其细密,但是他对中国佛学思想史上的一些重大问题和史观却经常能别出新见,开未发之覆。先生对中国佛学思想的问题是着重于从哲学意识去加以掘发,如他对中国佛教重要“证悟学说”的研究,就是从其“认识论问题”为中心来进行检视的*参考先生论文《佛家证悟学说中的认识论问题》,载《萧萐父文选(上)——思史纵横》,第183~188页。。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以和的观念来通观和爬梳中国佛学思想史上许多关键性概念的形成及其演化。有趣的是,他发现和合异流恰恰是佛教思想的一个殊胜之处,“显密各宗合一脉,如来欢喜百家鸣”*见先生《五台行吟稿》五,载《萧萐父文选(上)——思史纵横》,第189页。。在先生看来,和合诸家思想不仅是中国哲学的活水源头,也成为中国化佛学最重要的标志之一。他对中国佛教各宗思想之阐论,也就特别集中在对其和合观念的抉择与分析方面。如先生对六朝佛教思想的发展——这是中国化佛教重要的时期——提出了一个意味深长的洞见,他认为印度佛法作为一个理论体系为中国文化所吸收、消化,从其宏观大势看有几大段落,首先《肇论》的出现是一个标志,其把印度般若中观学与中国老庄玄学进行“格义互释而逐步融通”,从佛学本体论方面形成中国化佛学思想的关键;而《大乘起信论》则融摄南北朝地论、摄论、涅槃诸宗心性论问题的论争,作为“群诤之评主”而成为佛教心性论中国化的一个标志。对于隋唐佛教的论义,先生同样秉持了这样一种见地,特别是对禅学的讨论,他提出北禅南义两家都是沿承《肇论》《起信》以来和会诸家的宗义,对传统禅学旧义进行改造,而与中国的儒、道人生修养论“互相涵融”,到东山法门的出现,则完成了佛学人生观与价值观方面的中国化*见先生《略论弘忍与东山法门——1994年11月黄梅禅宗与中国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词》,载《萧萐父文选(上)——思史纵横》,第190~193页。。在先生关于中国化佛学的论述中,和合涵融的思想包容观成为其观察中国佛学思想的一大法眼。1996年先生撰述《石头希迁禅风浅绎》一文时,还是以“圆融思想”与“回互学风”为中心来加以讨论,认为石头一系的禅法精要就在于其“求同存异,观其会通”。先生甚至对中国哲学史上的文化史观,始从《易传》《中庸》《六家要旨》《庄子·天下篇》一直到唐代禅学史家宗密之《华严原人论》等,作了一番通观释论,认为其中一以贯之的一个要旨就是,各家皆主张“会通本末”、并行不悖的多元思想史观*均见《石头希迁禅风浅绎》一文。。
从现在学术史的立场来看,先生的中国佛学之论当然有不少可以再行商量之处,先生之佛学论述中的宏远疏阔或许失之不够精密。而我以为,论衡先生之学,不能仅就其佛学知识史的内涵来作判断,必须放到他所处的时代脉络中去作系谱学的观察,方能见其价值所在。先生之论究学思大都涵藏了以史论今、以古为鉴之笔法。从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先生的论学是与他对当下社会生活及文化处境的判断密切关联的,他试图以和合多元的开放心态来作中国文化的再思考。于是,他也努力以此观念来重新解读和组织对中国哲学,包括中国佛学思想在内的一些重要观念,从而有意识地掘发其中具有思想启蒙性质的思想元素。从他此时期所著有关易庸之学、道家隐者与思想异端以及道家风骨等论来看,都鲜明地贯彻了新的批判与启蒙的思想主题。先生的哲学史著作是史亦是论,是传统的亦是当代的。他同样赋予他的佛学史论以这样一种启蒙主义的思想性质,如果不明于此,我们就无法深刻领会先生哲学史论述背后的微言大义。
我与先生第一次深入谈论学问与人生问题是在1990年的夏天,记得先生当时的处境与身体都很不好,却仍然非常认真地要求我这个刚入师们的后学谨守“德业双修、学思并重、史论结合、中西对比、古今贯通”的二十字箴言。特别让我当时印象深刻的是,先生要求我不断努力扩充自己的知识视域,告诫我说,“一事不知,儒者之耻”。先生对弟子们的期许成为我调整自己治学方式的动力之一,虽然我们现在哪怕对治一个很小的问题都需要面对浩瀚的专业材料,很难竭泽而渔地穷尽一切。而取法其上,得乎其中,先生的教诲逐渐让我在治学中养成一种态度与习惯,即尽量在研究过程中去消化古今中外的相关成果,而不要闭门造车、鼠目寸光。
个人与佛学研究的结缘,是在我博士二年级时,先生要求我协助其完成点校注释《大乘起信论》。此前,我在硕士期间已经学习过吕澂先生关于中、印佛学史的讲义,对佛学初有接触与了解。先生对疏解经典的要求很高,希望我对所疏经典中的每个字义都不能够轻易放过,对原典中的每项重要概念都要皆知源流。在先生的督促下,我不仅对流传的《起信论》版本作了一些调查,对古来各家《起信论》疏也要有较为系统的解读,后来居然以此为主题完成了博士论文。现在看来,20多年前的那部博士论文限于当时的条件而在材料、方法上都颇显粗陋,但是一直到今天,我对中国佛学思想史的研究,还离不开当初跟随先生作经典疏解的那段训练。可以说,先生在佛学上的许多具体观点现在对我的治学影响不大,而其治学的开放态度与方式却让我终身受益。
诵业易成,风骨难得,先生不仅以其博大的胸怀来平章学术,也以此来教我们做人。先生对我学术事业影响最为深刻的方面在于,如何养成一种思想与学术上独立而又包容的心态。我自己的佛学研究很久以来都与国内主流颇有不同,这使我经常面对国内佛学界不同的声音与批判,我一直能够坚持独立走自己的路,精神上面与先生的教诲是分不开的。我毕业后每次有路过武汉的机会都会去看看先生,每次谈话中,他最关心的还是我的学问。让我感到非常温暖与感动的是,他身体不好,有时读书都成问题,却还一直关注甚至阅读弟子的研究成果。对我这样有些异类的学术方式,先生不仅没有责备,还给予了很大的肯定与鼓励。他经常用禅门中说的“见与师齐,减师半德,见过于师,方堪传授”来鞭策我走出自己的学术道路,不要拾人牙慧,人云亦云。我在先生身上看到了真正老一代学人的风范与修养。他自己在学术与文化的理想上追求殊途百虑,异以贞同,也同样在现实生活中以这样达观的生命原则来面对和欣赏弟子们各自不同的学术成长与发展。
先生不仅引领我走进佛学,更重要的是,他为学与为人的境界风范留给我永恒的精神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