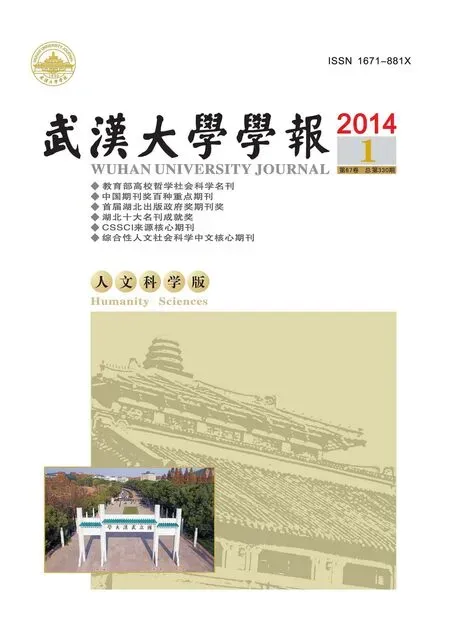伊拉克战争对伊拉克未来走向的影响
2014-03-04钮松张羽
钮 松 张 羽
美国大举入侵伊拉克迄今已整整十年,当前中东地区正处在“阿拉伯之春”的第三个年头。伊拉克战争首先是一个大国粗暴干涉别国内政、悍然入侵他国的行径,是对《联合国宪章》和国际关系准则的严重践踏。伊战带给伊拉克人民的是战争、动乱和一系列灾难,无数平民死于战火之中,同时国内政局持续动荡,直至今日仍未消停。虽然美国许诺的所谓民主局面和繁荣并未完全出现,但不可否认的是,伊拉克由于外力的作用而导致旧政权瞬间崩溃,并在美国的主导下确实较早开启了民主化进程。从2003年伊战爆发后的重建到2010年底“阿拉伯之春”爆发前,伊拉克的民主化在历经七年的阵痛之后,逐步臻于完善,其政权在“阿拉伯之春”中的相对平稳便是有力的例证。反思伊拉克战争中美国的预期目标与当前伊拉克民主成果以及伊斯兰极端主义复兴的真实关系,在当前就显得尤为必要。随着美军撤离伊拉克以及中东教派冲突的扩大,伊拉克的未来走向值得关注。
一、 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动机与效果
伊拉克战争对当代伊拉克政治发展影响巨大,它是伊拉克政治的历史性分水岭。美国主观的动机和客观的成效,对理解伊拉克战争之于“阿拉伯之春”时代伊拉克的意义至关重要。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动机自战争爆发之前直到现在,都是一个充满争议且众说纷纭的话题。十年来,国际社会关于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动机争议主要包括几大方面:
第一,石油说,认为美国发动战争的首要目的就是为了谋取其丰富的石油资源。这种观点看起来似乎有其相对严密的逻辑性并极具煽动性,并成为定性美国战争“不正义”的“证据”。但从十年的历程来看,这并不符合事实。美国不仅自身蕴藏丰富的油气资源,而且为了减低中东产油国对其能源安全的威胁和掣肘,近年已选择美洲而非中东为其首要的石油进口地。换言之,美国有着稳定的石油供应源且伊拉克萨达姆政权并未对美国石油安全及其石油卖家的原油出口造成威胁。伊拉克因入侵科威特而遭受联合国制裁,美国坚决支持该制裁而不与伊拉克进行石油交易,但伊拉克却有着出口石油的强烈意愿,在此情形下,美国没有发动战争夺取伊拉克石油的必要。最为关键且较少为世人所知的是,根据《海牙条约》的规定,占领他国后的私有化是被禁止的*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琳达·J·比尔米斯:《三万亿美元的战争:伊拉克战争的真实成本》,卢昌崇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92页。,这也包括伊拉克石油部门。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美国乃至西方石油公司并未成为伊拉克石油的最大获益者。
第二,宗教说,认为美国发动战争的首要目的是反击伊斯兰教对基督教的挑战。小布什被认为是美国历史上宗教使命感最强的总统,他深受美国基督教福音派领袖葛培理的影响*参见史蒂芬·曼斯菲尔德,《活出使命:布什总统的信仰》,林淑真译,中国档案出版社2006年。。他虽然有过“第十次十字军东征”和“伊斯兰法西斯主义”等“口误”,但这并不能代表美国政府的态度。值得注意的是,并非是伊拉克发动了针对美国的“9·11”恐怖袭击,而且萨达姆政权是阿拉伯复兴社会主义的世俗而非宗教政权。如果认为美国的首要动机是宗教对抗,那么它对敌人的选择及对其性质的定位皆存在偏差。但不可忽视的是,宗教对于国际关系的参与度与影响力正不断提升,宗教事实上在国际关系中扮演着“冲突根源”与“和平使者”的双重角色*参见徐以骅:《宗教与当代国际关系》,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
第三,民主说,认为美国发动战争的首要目的是推进其民主化。推进伊拉克民主化是美国并不回避的动机,小布什就认为中东恐怖主义的根源来自于两大赤字:经济赤字与民主赤字。美国政府将伊拉克作为其日后“大中东民主计划”的样板工程来看待。美国确实不遗余力地在伊拉克土地上移植美式民主模式,并为此消耗巨资。虽然美式民主有些水土不服,但伊拉克新政权在美国军事力量的保护下,缓慢地朝着美国所期望的角色迈进。美国希望通过塑造伊拉克这个民主样板,向中东盟友适量施压,向中东敌国趁势加大威慑力度,以促成这些国家的民主改革*参见汪波:《中东与大国关系》,时事出版社2013年。。事实也证明,美国并不准备在伊拉克战争之后再发动新的战争,其军事力量已长期被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局势所牵制。
时间已经证明,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官方理由,即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也纯属无稽之谈,且少有人相信。对于美国战争动机的三种争论也将持续下去,但有一点要明确,任何动机都不会是孤立存在且明显处于首要位置。从历史的发展来看,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有其建立冷战后国际新秩序的内在逻辑,即首先通过科索沃战争进一步铲除所谓共产主义残余势力,然后通过阿富汗战争打击伊斯兰激进和恐怖势力,最后通过伊拉克战争削弱世界世俗反美势力,这将有利于我们考量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复杂动机。考察美国的伊战得失与美国是否实现自身的战争预期目标密切相关。如前所述,美国事实上宣示的战争动机包括推进民主化和削弱反美主义,从这个角度考察较为妥当。
美国以武力为后盾的制度民主的输出虽然加速了萨达姆政权独裁统治的覆灭,但是毕竟依托于血腥的战争。同时,民众往往把新政权视为美国的代言人,一筹莫展的民生问题也削弱了民众对民主的热情。不容否认的是,伊拉克的政治生态发生重大改变,伊拉克政治权力格局与公民政治—宗教结构实现了吻合,少数族群和妇女权益得到提升。虽然美国酝酿伊战之时,欧洲版本的反美主义让美国产生了“新欧洲”与“老欧洲”的忧虑,但事实证明,美国的欧洲乃至亚洲盟友在美国的伊拉克战争与重建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欧洲并未分裂,美国利用伊战在欧洲的“后院”整合了其盟友,这些似乎达到了某些战略预期。
整体上说,美国的预期与目标相距甚远。美国最直接的失败在于付出巨额美元和大量人员伤亡的代价之后,仍未能最大限度消除反而激发了更多的反美主义活动,尤其是伊斯兰恐怖主义打着反美主义的旗号反而愈演愈烈。伊战以后,美国在世界范围内所遭遇的安全威胁不断涌现,这主要来自于以“基地”为代表的伊斯兰恐怖组织。强大的美国在保卫国土安全以及海外利益上耗费了巨资,过度安全化侵犯了个人自由和隐私,美国陷入了“越反越恐”的安全困境。由于十年来深陷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直到奥巴马第二个任期开始,美国重返亚太的东移战略仍未能完全实现,这极大影响了美国的全球战略调整;美国剪除伊朗东西两翼的敌人塔利班和萨达姆,伊朗及其代表的什叶派势力在海湾地区力量陡然上升,伊朗更是与朝鲜加强了在核武器和远程导弹上的互动,这是美国始料未及的*张琏瑰:《伊朗朝鲜,商业性核试验交易?》,载《世界知识》2013年第8期。。
二、 伊拉克教派主义主导下的民主化
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时遭遇到伊斯兰—阿拉伯世界的强烈反对,但伊拉克数年的民主化成果以及政治生态的相对良性发展在近年尤其是“阿拉伯之春”中,越来越多地被阿拉伯世界所反思。当前伊拉克的政治生态相较于十年前乃至1932年伊拉克独立后的数十年历史而言,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改变,这主要体现在三组关系上。
第一,两大教派权力格局逆转。伊拉克是奥斯曼帝国垮台后被英国人为制造出来的国家,英国罔顾伊斯兰什叶派人口占该国多数的事实,扶植逊尼派王室予以统治。1958年共和国建立之后,这种教派权力失衡的局面一直延续到2003年。虽然伊拉克长期奉行世俗的复兴社会主义原则,但由于伊斯兰教的强政治特性,教派政治仍然在伊拉克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发挥着独特的影响。尤其是海湾战争期间,“萨达姆从全世界大量的原教旨主义者和其他明显的穆斯林团体那里获得支持”,“他成功地在这些团体中将起自身形象转变为反伊斯兰的帝国主义的反对者。”*J.O.Voll.Islam.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the Modern World.New York: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1994,pp.335~336.伊战以后,占多数的什叶派人口毫无悬念地通过选举政治而获得主导权,教派身份日益成为更加难以跨越的政治鸿沟。
第二,中央地方权力格局消长。伊拉克长期以来是一个单一制国家,中央政府对地方进行着强有力的掌控,尤其那些散漫的部落群体被政府严密控制。伊战后,由于局势动荡和教派纷争不断,新政权一时间难以整合地方政治—军事势力,地方政府和部落领袖各自为政,甚至拥兵自重,伊拉克形成了“弱中央、强地方”的新格局;不仅如此,库尔德自治区获得了史无前例的高度自治权,“伊拉克战争结束之后,伊拉克库尔德人声称他们将保持自己作为伊拉克的一部分,即在联邦系统下的高度自治的库尔德斯坦”*Wang Bo.“The Political Perspective of the Iraqi Kurds after US Military Retreat”,Journal of Middle Eastern and Islamic Studies (in Asia),2010,(2),p.1.,这种高度自治事实上已使库尔德地区处于半独立状态,其丰富的油气资源更是成为其挟持中央的杀手锏。
第三,政党政治格局多元化。伊战后,复兴社会党的一党统治格局被打破,政党政治迈向多元化,虽有主张西方民主的自由派政党,但宗教政党尤其是什叶派政党在伊拉克政党政治中发挥着主导作用,而复兴社会党则在2003年即被强制解散。有学者指出:“总体而言,伊拉克的世俗政党,以及尤为突出的是,那些基于宗教的党和部族党,都缺乏在当今时代建立并运作一个民主系统的历史与经验。”*S.Aziz.“Kurdistan:Democracy and the Future of Iraq”,in A.Paya,J.Esposito,eds.Iraq,Democracy,and the Future of Muslim World.New York:Routledge,2011,p.63.
遭受萨达姆二十余年独裁统治,并因其入侵科威特而遭遇国际制裁的伊拉克民众虽有变革之心,却无变革之力。客观而言,伊拉克人民本着推翻独裁统治、改善生存条件的朴素愿望,在战争爆发之初并不十分排斥美国的作用,即便不爱,亦很少有恨。战争之初,美军在伊拉克极少遭遇民众的抵抗,甚至许多伊拉克部队成建制地丢盔弃甲并“人间蒸发”便是例证。即便如此,“大多数性格倔强的伊拉克人不买外国占领者的账。”*李荣建:《伊拉克战争与国际局势》,载《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3年第5期,第581页。随着时间的推移,伊拉克的局势稳定遥遥无期,恐怖主义和教派仇杀泛滥,许多民众又开始怀念战前那个“不幸福却很稳定”的时代。随着美国国内的伊战反思潮,伊拉克民众也开始反思美国基于完全错误的官方理由所发动的战争,并进一步质疑伊拉克到底应该是民主优先还是稳定优先。美国虽然推翻了萨达姆政权,但绝非伊拉克人民的“解放者”;即便没有那场伊拉克战争,萨达姆政权也难以躲过“阿拉伯之春”,这是许多伊拉克民众的真实想法。但历史不容假设与重来。两年前美国的撤军在许多伊拉克民众看来,是美国国力衰落之后在中东运用有限军力支援阿富汗的“拆东墙补西墙”的无奈之举。他们高兴的是美军的撤离将会使伊拉克的国家主权更加完整,忧虑的是伊拉克政府军能否独立应对复杂的国内安全形势。
2010年后,中东地区政治一直处于变动之中。北非的突尼斯、埃及等国首先爆发了以增强民主、改善民生为主要诉求,以推翻现专制政权为主要目标的社会运动,并逐渐席卷整个阿拉伯世界,导致了多个政府的倒台,建立新的民主政体,群众示威最终在利比亚升级为全国内战,这些严重破坏了伊拉克国家外部环境的稳定。而今,叙利亚问题的僵持,国内“基地组织”恐怖主义行为的升级,从某种意义上对伊拉克而言,中东变局并未结束。伊拉克本身仍然处于“阿拉伯之春”之中。
从国内政治看,大选直接决定了什叶派、逊尼派和库尔德人对伊拉克国家权力分配和经济资源(主要是石油财富)决策权力的争夺。然而,缺乏美国直接干预的大选结果,可能无法再平衡原来各方的力量,安抚在投票人数上处于相对劣势的逊尼派和库尔德人,从而加剧伊拉克各派别之间的矛盾。更令人担忧的是,这种政治斗争极有可能向更极端、冲突更激烈的教派矛盾转化,由此引发新一轮自上而下的大对抗。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2012年的一份报告指出,教派分歧和民族对立会使伊拉克出现严重冲突甚至国家分裂*A.H.Cordesman,S.Khazai.“Iraq after US Withdrawal:US Policy and the Iraqi Search for Security and Stability”,http://csis.org/publication/iraq-after-us-withdrawal-us-policy-and-iraqi-search-security-and-stability,July 2012.。大选在即,伊拉克国内安全局势却更为恶化,恐怖袭击次数和人员伤亡的增加,一定程度上反应了矛盾激化的趋势。尽管总理马利基极力强调全伊拉克人民利益的概念,并企图通过进一步放松前执政党成员参政限制等手段减少教派冲突,促进伊拉克内部和解,但仍无法规避伊拉克大选具有国内各种势力权力竞技的意味*张淑惠、梁有昶:《伊拉克政府拟进一步放松对前执政党成员的限制》,载http://news.xinhuanet.com/2013-04/08/c_124548769.htm,2013-04-08。。事实上,伊拉克乃至中东地区由于历史原因,部落、宗教、民族关系十分复杂,并非一个宪法或者自由选举就能有效调节。美国在重建伊拉克的过程中迫使各方势力妥协,以建立一个表面上的联合政府,并未实质解决伊拉克各派别的矛盾,也无法完成它们之间权力的分配,仅通过对各方势力的制衡,以维持在其控制下统一的伊拉克。因此,伊拉克的“民主”是美国看护下的“民主”,所谓的联合政府也不具有广泛意义上的民众合法性来源。2013年的选举在缺乏美国近距离干预条件时,必然会有更多波折。
在国际政治方面,各国的地缘考量首先决定了伊拉克国内政治对中东局势的重要性。根据美国“大中东计划”,伊拉克和阿富汗是中东民主化进程中的两个前哨,能够形成民主外溢和民主榜样的效果,同时两者位于伊朗左右,连同土耳其、沙特和以色列共同组成美国在中东战略的盟友国家,以对抗中东反美因素。因此,伊拉克是美国中东战略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同样,对于伊朗和叙利亚而言,伊拉克的中间位置在四周亲美国家环绕下变得十分关键。在伊斯兰教派斗争方面,2003年后伊拉克成为了什叶派和逊尼派斗争的新中心。萨达姆时期,伊拉克国内教派矛盾被强制压制,其政权被推翻后所推行的民主选举为两派提供了合法的政治斗争途径,同时由于库尔德问题关系到土耳其的统一,因此伊拉克已经成为中东局势的一个关键点,其政策倾向对整个中东局势有着巨大影响。
三、 “阿拉伯之春”对伊拉克未来走向的影响
“阿拉伯之春”为阿拉伯国家民主化发展与伊斯兰极端势力的发展提供了契机。
首先,从民主化发展的角度来看,“阿拉伯之春”最初被视为伊拉克民主化的外溢。因为与其它当时仍在实行威权统治的阿拉伯共和制国家所不同的是,伊拉克战争使得民众对政治改革的要求提前由美国完成,“阿拉伯之春”的民主浪潮在政权形式和政府层面并没有给伊拉克带来很大冲击。但伊拉克对阿拉伯世界的影响力仍然有限,伊拉克也难以完全超然于“阿拉伯之春”:在政府层面,由于其国内刚刚经历选举,正面临组建新政府、权力交替的困难时期,政府的当务之急在于稳定国内局势;在国内民众层面,民众对腐败肆虐、两极分化严重、青年人口比例较大与高失业率、高通胀率、高贫困率等经济和社会问题的强烈抗议并未随着“阿拉伯之春”的深入有明显改善,如巨大的贫富差距、高失业率、安全局势的紧张等使得伊拉克民众对所谓“阿拉伯之春”的暖意失去信心,纷纷反思2003年伊战的意义以及美国的动机,并对政府执政是否清廉和能力产生怀疑;在美国因素层面,美国在伊拉克的存在决定了伊拉克政府本身外交不具有完全决策能力,需要通过美国逐渐融入国际社会。因此,伊拉克政府公布的2007~2010年的长期国家战略,主要表述为“反恐怖主义”,这基本与美国保持一致*安国章:《伊拉克制定了国家发展新战略》,载http://world.people.com.cn/GB/1029/42361/6223066.html,2007-09-05。。同年,联合国解除了多年来对伊拉克的经济制裁,使其逐步恢复经济主权与对外经济交往。
其次,从伊斯兰极端势力挑战的角度来看,伊拉克战争和“阿拉伯之春”都为伊斯兰势力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美国撤军伊拉克后,在中东留下了大块的权力真空地带,伊拉克的局势受周边国家,尤其是伊朗和沙特在政治、外交、宗教等方面的影响,伊拉克战争与重建都为伊拉克国内的教派和民族冲突提供了土壤,这使得伊拉克国内外的环境更为复杂。伊拉克民众对新政府的诸多不满又可能把伊拉克推入激进意识形态的怀抱中。面临民生压力的伊拉克什叶派政府还面临着来自逊尼派和库尔德人的教派和民族的挑战,后两者与外部势力相结合,这使得什叶派不得不也转向国际盟友。共同教派信仰的伊朗立刻成为大多数什叶派的首选,并据此来说服民众以转嫁国内矛盾,如伊拉克在叙利亚问题上的态度便部分反映了政府的考量。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伊拉克已完全倒向伊朗,与美国等西方国家为敌。在国际层面,伊拉克作为独立国家将面临沙特和伊朗为首的中东国家复杂的宗教和权力斗争,同时在客观上受美国、欧洲国家的牵制,这些也使得政府更为谨慎地缓和激进的意识形态。
2011年,随着中东局势动荡的升级,利比亚爆发内战,联合国通过1970和1973号决议对其实施禁运和设立禁飞区,国际上以法英为首的北约国家对其发动空袭。利比亚战争引起中东局势的紧张,伊拉克开始显现出什叶派当权后逐渐有别于美国的国家战略,其最初主要通过阿盟对利比亚局势发挥作用。叙利亚问题上,伊拉克的外交政策则更为主动且更具独立的国家意识。2011年底,伊拉克开始介入调停叙利亚问题,关心其局势走向,明确表达反对国际社会对叙利亚实行制裁,并在阿盟2011年中止叙利亚成员国资格、对其实施制裁的投票表决中弃权,这显然与美国意见相左。在美军完全撤离后的近两年时间里,伊拉克在叙利亚问题上具有明显的什叶派倾向*王宏彬、张宁:《伊拉克愿意参与调解叙利亚危机》,载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1-12/09/c_122398734.htm,2011-12-09;杨元勇:《伊拉克外长强调须在阿拉伯框架内解决叙利亚问题》,载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1-11/22/c_111184544.htm,2011-11-22。。2012年迄今,美国与伊拉克双方多次关于叙利亚问题进行谈话,美国强烈要求伊拉克对叙利亚关闭领空并实施禁运,同时严格检查伊朗至叙利亚的飞机,以确保没有杀伤性武器的运输。尽管如此,伊拉克政府仅主要接受对叙武器禁运,并愿意接受调查以证实所放行飞机运载的皆属于人道主义援助物资。随着大选的临近,伊拉克又开始恢复了对叙运输的检查*梁有昶、张淑惠:《美国敦促伊拉克阻止伊朗经其领空向叙利亚输送武器》,载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3-03/25/c_124496962.htm,2013-03-25;梁有昶、张淑惠:《伊拉克突检一架飞赴叙利亚的伊朗过境货机》,载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3-04/08/c_124554006.htm,2013-04-08。。
伊拉克政府在“阿拉伯之春”中的总体政策,反应了总理马基利试图将伊拉克建构成为现代主权国家,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来制定国家战略、解决国内外问题的意图。伊拉克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只有在内部团结的情况下,以本国国家利益为出发点,自强自立,抓住机会尽快融入国际社会,展开全方位外交,推进经济层面的交流和发展,解决国内民生,缓和国内教派与民族矛盾,才有可能摆脱中东冲突点的命运。大选后新政府的组建,若无法达成此共识,恐怕伊拉克很难真正走出“阿拉伯之春”的乱局。除此之外,缺乏美国军队强力支撑下的伊拉克政权是否能够有效应对伊斯兰极端势力的挑战,也关系到伊拉克的未来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