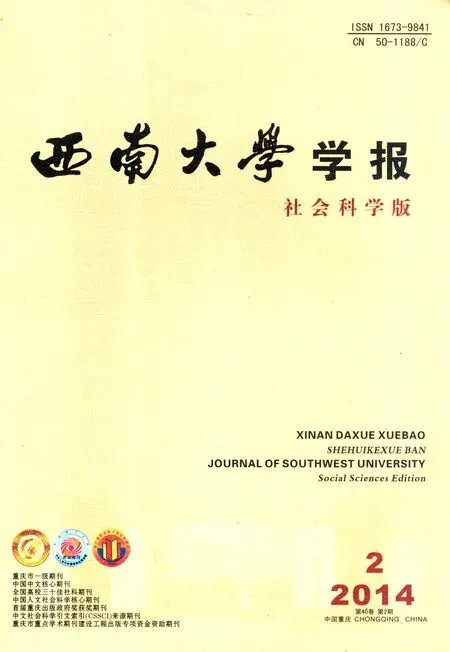转型时期伦敦的堂区仪典与社区认同
2014-03-04邓云清
邓 云 清
(西南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重庆市 400715)
转型时期伦敦的堂区仪典与社区认同
邓 云 清
(西南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重庆市 400715)
16、17世纪的英国之所以能在社会基本稳定的背景下成功实现社会转型,社区认同的巩固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从伦敦的经历来看,仪典在推进堂区认同、实现社会稳定方面起过大的作用。在人口规模快速膨胀、教堂仪典资源不足的情况下,伦敦堂区仪典仍能维持较高的参与水平。究其原因,除了宗教虔诚的基本因素之外,还有新富阶层对社会权力的追求、贫民阶层对慈善救济的需求等新因素的作用。
伦敦;堂区仪典;城市社区;社会转型;宗教改革
16世纪的英国开始步入社会转型时期,社会变迁日益加剧,社会的异质性日益突出。尽管社会变迁是英国社会转型的重要驱动力,但也引起一系列社会问题,对社会稳定起着巨大的消解作用。不过,英国安然渡过了这一时期,在社会基本稳定的基础上成功实现了社会转型。个中原因值得探讨。譬如世俗政府主导的济贫制度的建立,教会主导的仪典体系的巩固等。这些制度和方法将多元化的社会加以聚合并体系化,使同质性有所恢复,从而形成新的社区认同。在社会转型时期,社区认同是一个非常重要而复杂的主题。关于近代早期英国的社区认同,在国外学术界已有不少研究,如阿彻关于伦敦社区认同的研究[1]58-99,柏林关于伦敦堂区仪典的研究[2]47-66,斯内尔关于英国堂区认同的研究[3]1-504。在国内,相关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本文仅从仪典入手研究16、17世纪伦敦的堂区认同。
一、宗教改革对堂区仪典的冲击
在中世纪,堂区(parish)是天主教会的基层单元,仪典(ritual)是天主教会宗教活动的核心内容,堂区及其仪典具有浓厚的天主教属性。16世纪英国宗教改革是对天主教的改革,建立属于英国自己的民族教会圣公会。在圣公会体系下,教会和仪典的地位大幅下降,这势必影响到堂区仪典的生存和发展。伦敦堂区仪典亦不例外。下文介绍宗教改革前后伦敦堂区及其仪典的变化。
伦敦堂区归伦敦主教管辖,其数目大约有110个,在12世纪即已成形[4]126。堂区是天主教会的基层单元,主要执行宗教圣礼、道德说教功能,也执行与善功救赎直接相关的宗教慈善功能。在堂区内,堂区神父(parish priest)是首领,由他主持宗教仪典,救赎信徒的灵魂。16世纪宗教改革主张因信称义,反对善功称义,神父及其主持的仪典在因信称义的过程中不再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堂区神父也改称堂区牧师,在圣公会系统内称“parson”,亦称“incumbent”、“rector”或“vicar”,在非圣公会系统内称“parish minister”,其主要职责是向堂区内的平信徒讲经传道。14、15世纪的时候,伦敦堂区发展出治安、济贫等世俗功能,逐渐成为世俗政府的基层单元。1536年,国会法案要求堂区负责本堂区内贫民的救济与工作安置事宜[5]1028-1029,正式将堂区纳入都铎政府的框架之内[6]182,堂区成为教俗共用的基层社区。
仪典是天主教会宗教活动的核心内容。在天主教会看来,宗教仪典是基督精神的主要临在与表达,通过宗教仪典,基督之爱与兄弟情谊就内化在教民的心灵之中。天主教会的宗教仪典主要指七圣礼,包括洗礼、坚信礼、圣餐礼、婚礼、圣职礼、忏悔礼、临终礼。其中,圣餐礼通常每周举行一次,参与最为广泛。仪典与节日密不可分,宗教仪典通常在宗教节日和礼拜日举行。当时重要的宗教节日有圣诞节(Christmas)、复活节(Easter)、五朔节(May Day)、施洗约翰节(Midsummer Day)、元旦节(New Year’s Day)、主显节(Epiphany)等[7]216。此外,还有圣灵降临节(Pentecost,亦译五旬节)、圣母升天节(Assumption)、基督降临节(Advent)、耶稣升天节(Ascension)、万圣节(All Saints’ Day)、大斋节(Lent,亦译四旬斋节)、主显圣容节(Transfiguration)、棕枝主日(Palm Sunday)、基督圣体节(Corpus Christi)等。根据16世纪观察家威廉·哈里森的记述,英国宗教改革前的宗教节日有63天,非宗教节日有30天,未占用的礼拜日有27天,共计120天[8]36。大多数节日分布在从圣诞节(12月25日)到施洗约翰节(6月24日)的半年,有学者称之为“仪典的半年”[9]384。
宗教改革期间,英国宗教仪典的地位发生重大变化,教会的主要工作不再是主持圣礼,而是讲经布道。宗教改革反对天主教会的善功称义,圣礼特别是教会所建圣礼的地位大幅降低。在英国圣公会,洗礼和圣餐礼因由基督亲自建立而成为主要的圣礼,坚信礼、婚礼、圣职礼、忏悔礼、临终礼因由教会建立,其地位相对下降。即使作为主礼的圣餐礼,亦不再每周举行。在伦敦,圣餐礼每月举行一次[1]90。更激进的清教徒甚至不承认除洗礼和圣餐礼之外的其他五种圣礼的圣礼地位。宗教改革不仅是宗教和政治改革,也是社会和文化改革。节日不仅是宗教虔诚的一部分,也是大众狂欢的一部分,许多节日不仅遭到宗教改革者的批评,而且遭到传统文化改革者的抵制。他们指斥这些节日有严重的神学、道德等瑕疵,或带有非基督教甚至古代异端的痕迹,或纵容酗酒、暴食、性欲、暴力等罪恶,或浪费时间和金钱而使上帝不悦[7]253-258。1536年,都铎政府法令要求减少宗教节日及其庆典活动。1549年,一位评论家估计当时英国的宗教节日只有35天[9]385。16世纪60年代崛起的清教徒对大众娱乐的敌视态度更是众所周知,宗教节日的数量进一步压缩。五朔节、基督圣体节、耶稣升天节、施洗约翰节处于“仪典的半年”,充斥着性和暴力,是春夏狂欢的典型,在宗教改革前后很快走向衰落。譬如,五朔节就因其花柱具有色情色彩而备受争议,后又受到一次骚乱的牵连。根据16世纪历史学家斯托的记载,1517年五朔节期间伦敦发生骚乱。此后,堂区不得不加强对五朔节的约束,五朔节逐渐衰落下去[10]91。
以上可见,宗教改革对堂区及其仪典形成严重冲击。教会在堂区的力量大为削弱,世俗政府开始主导堂区体系。堂区的世俗职能大幅上升,如举办济贫事业、维持社会治安;其宗教职能显著下降,特别是主持仪典的传统职能大为削弱,而辅助圣经学习的讲经布道职能则有所加强。应该说,在中世纪,在善功救赎理论体系下,堂区凭借仪典的主持,在坚信基督信仰、彰显堂区价值的同时,也有意无意地加强了面对面的人际交往,形成了十分强烈的堂区认同。加上当时的社会变迁并不剧烈,故通过宗教维系的堂区纽带和教民意识十分强劲。不过,随着宗教改革的到来,堂区职能出现巨大变化。这势必要影响堂区及其仪典的前途,影响堂区及其仪典在聚合人心、形成新的社区认同方面的能力。下文通过伦敦堂区仪典的参与水平来探讨宗教改革后堂区认同的状况。
二、堂区仪典的参与和社区认同
教堂是堂区的主要公共空间。每逢重要节日,伦敦各个堂区均要在本堂区教堂举行仪典。其中最重要的是每月举行的圣餐礼。关于伦敦城堂区圣餐礼的参与水平,由于完备资料的缺失,无法给出反映全貌的统计数据,但个案统计并不缺乏。第一个例子是萨瑟克的圣萨维尔堂区(St Saviour Southward)。据统计,该堂区在17世纪20年代复活节圣餐礼的参与出席率高达80%~98%。第二个例子是阿尔德盖特的圣鲍托尔夫堂区(St Botolph Aldgate)。据统计,该堂区在16世纪90年代复活节圣餐礼的参与出席率为38%~56%。第三个例子是科尔曼街的圣斯蒂芬堂区(St Stephen Coleman Street)。据统计,该堂区在1602年复活节圣餐礼的参与出席率为75%[1]90。从这三个例子可以看出,复活节圣餐礼的参与出席率较高。需要说明的是,复活节圣餐礼并不能代表圣餐礼的全部,其参与出席率通常是最高的。
堂区仪典的参与出席率表现出较大的差异。这与堂区的规模有密切关系。通常而言,堂区规模越小,参与水平越高。小堂区主要集中在伦敦城墙之内,房主数一般在50~200户之间,其参与水平高一些。上述第三个例子圣斯蒂芬堂区就是墙内堂区,其户主数在200户左右。大堂区主要集中在伦敦城墙外沿地带,房主数大多超过1 000户,其参与水平低一些。上述前两个例子圣萨维尔堂区、圣鲍托尔夫堂区就是墙外堂区,其户主数均在1 000户以上。需要说明的是,圣萨维尔堂区如此高的参与水平相当难得,在墙外堂区中并不多见。墙外堂区参与水平普遍偏低的基本原因是堂区教堂无法容纳所有教民。虽然可以采用分组的方法领受圣餐,教民可以在某种意义上接触到堂区内的绝大多数教民,但并没有办法让他们在祈祷时完全真实地感觉到社区的存在。不过,墙内外堂区的这一差异似乎与时人的记录不相符。墙内堂区会的记录经常抱怨有人缺席,而墙外堂区的记录则在这个问题上保持沉默。有学者认为,这种情况正好反映了小堂区中定期参与是更广泛的[1]90。在墙内堂区,几乎所有房主都有座位,如果有人缺席,则一目了然;在墙外堂区,只有那些有头有脸的房主才拥有座位,即使有人缺席,其座位也会马上被人占据,所以很难知晓缺席的情况。
伦敦中上层人士大多是商人和作坊主,拥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对宗教改革和新教持支持态度,因而对堂区圣餐礼的参与水平较高。除了宗教虔诚的这层因素之外,他们的参与还有社会权力的因素。转型时期的伦敦充满经济活力,是一座生产新富阶层的城市,这些新富阶层迫切需要通过仪典来彰显并加强自身的社会地位。在这种背景下,堂区圣餐礼出现明显的等级化趋势。这体现在教堂座位的分配上。教堂座位越来越成为教民社会地位的象征符号,与宗教本身无甚关联。教堂座位的分配标准是:职位高低、财富多寡、年龄与性别。离圣坛越近,表示地位越高。前排中央座位由堂区的上层人士占据,包括在堂高级市政官及其他显贵、教会执事,以及“尊贵的”堂区委员。部分座位为那些愿意支付座位租金的富裕教民预留着,越靠近圣坛租金越高。这样,堂区教堂中最显要的座位由堂区官吏和富裕教民所占据。年龄与性别也是分配的重要标准,同年龄、同性别的群体往往安排在一起,宗教改革前即已如此。在教堂,强调的是社区,而不是家庭。不过,宗教改革后也出现了付租金的家庭座位,这可能与新教改革家对家庭宗教功能的强调有关,但同时必须以财富为基础。处于从属和依附地位的性别群体或年龄群体通常被安排在一起,包括未婚女子和女仆、贫困的寡妇,以及年少的男仆和学徒。部分教堂设有楼座,分配给本应出任公职但不愿担任而交纳罚金的富裕教民,以及接受堂区救济的穷人。穷人的集中,可以彰显他们对富有邻人的依附地位。正因为教堂座位越来越成为堂区教民身份与地位的象征,经过一段时间,教会执事就会根据情况的变化而调整教民的座位[2]54。
下层人士特别是贫民的参与是影响社区认同与社会稳定的关键。在对堂区圣餐礼参与进行考察的过程中,有必要特别注意贫民的参与情况。当时有不少资料提到,穷人不如富人虔诚,其宗教尊奉和仪典参与水平不高。尽管当时的很多富人这样认为,但就此认为穷人缺乏虔诚而不参与仪典是难以令人信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的穷人缺乏书写能力,知识阶层书写的文献资料缺乏属于穷人自己的声音。即使是在知识阶层书写的文献资料中,也可以找到为穷人的辩护词。一名叫特恩布尔(R. Turnbull)的堂区牧师就对富人蔑视穷人的态度提出警告,他认为穷人是“虔信、狂热、纯洁而诚实的”[1]91。定期参加教堂仪典还是穷人领受救济金的重要条件,出于领受救济金的目的,一些穷人可能是参加教堂仪典最勤的人员之一。一名叫史密斯(D. Smith)的穷人就希望他所在贫民所的室友们参加堂区教堂的仪典,因为缺席一次就扣掉2便士[1]91。要对穷人参加教堂仪典的动机进行深入考察是困难的。不管是出于宗教虔诚,还是出于领受救济金,仪典的参与无疑会提升堂区在贫民心目中的重要性,从而增强堂区的凝聚力。在社会分化加剧的时代,堂区仪典无疑为伦敦多元社会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社区认同工具。
作为堂区认同的工具,还有一种特别的堂区仪典值得一提。堂区巡界日(Rogation Days,又译祈祷节)是堂区一年一度最盛大的节庆之一,它也是历经宗教改革而幸存的唯一一种堂区巡行。具体日子是耶稣升天节之前的星期一、星期二和星期三。堂区巡界游行队伍由堂区牧师、两位教会执事与部分堂区委员领头,后面跟随着一大群堂区少年儿童。游行队伍从教堂出发,沿堂区边界巡游一周,中途会在堂区界标处停留。这时候,牧师带领众信徒歌唱圣歌,吟诵使徒书,感恩吾主上帝,也感恩国王的恩赐。堂区巡界实际上是对本堂区辖制区域的公开宣示,是对本堂区土地财产征税权以及本堂区教民救济责任的宣示。堂区征税范围的大小、救济人口的多少,直接关涉到本堂区所有教民的利益。对堂区边界的公开宣示,不仅为了防止堂区的土地与财产为别的堂区所侵占,而且为了凝聚本堂区居民的凝聚力,共同履行慈善救济责任。大量堂区少年儿童的参加,有助于堂区认同的从小培养。他们通常会在巡游过程中得到小点心和一种特制的小球。通过这种仪典,可以将堂区地界镶嵌在童年的记忆里。埃克斯钱基的圣巴多罗缪堂区(St Bartholomew Exchange)的官吏就称,赠送特制小球就是要孩童们记得巡游线路,等到他们长大时之后,他们就会自觉地维护和保卫堂区的财产权利,就会自觉地履行堂区的责任。参加仪典的孩童一般来自堂区定居有年的家庭,他们长大后一般仍留在堂区。在科希尔的圣彼得堂区(St Peter Cornhill),所有堂区委员的孩子都得参加。当遇到边界纠纷时,当年参加过巡界活动的教民就可以根据童年的记忆给出证据。无独有偶,特制小球的接受者都是男童,他们被指望在日后的边界纠纷中给出特制小球作为证物[2]57-58。
以上可见,宗教改革后伦敦堂区圣餐礼的参与是广泛的,社会中上层人士的参与水平很高,社会下层人士的参与水平也不低。圣餐礼参与的较高水平、堂区巡界日的长盛不衰无疑有效抑制了宗教改革以来仪典数量下降所带来的堂区认同消解的可能。历经宗教改革的冲击,为什么堂区仪典参与依然保持了较高水平?应该说,宗教虔诚是堂区仪典之所以存在的基本根据,在宗教改革前后并无本质变化。从个人内心的动机而言,宗教改革后伦敦人的宗教虔诚上升了,这不仅表现在富人中间,也表现在穷人中间。“对于许多人来说,堂区依然是宗教情感的重要归属所在。”[1]98堂区仪典参与之所以保持在较高水平,其原因不仅在于宗教虔诚,而且需要到社会变迁中去找寻。下文结合当时社会变迁的大背景,对影响仪典参与的因素加以简要分析。
三、社会变迁背景下的仪典与社区认同
16、17世纪的伦敦是一个快速城市化的社会,社会急遽变迁,多元性迅速成长。1500-1650年间,伦敦人口翻了三番,从5万[11]241增长到40万[12]316,人口增长之快,大大超过了12、13世纪,形成伦敦人口的第二个高增长期。紧随人口高增长而来的是人口结构失衡与社会分化加剧。一是外来人口畸重。据研究,16世纪晚期17世纪早期外来移民在伦敦人口中的比重高达70%以上[13]161。事实上,推动伦敦人口急剧膨胀的主要因素就是外来移民。二是年轻人口畸重。据研究,16世纪晚期17世纪早期伦敦的年轻人口(25岁以下)所占总人口的比重高达63%以上[14]74。三是贫困人口特别是流浪汉畸重。据研究,16世纪中晚期伦敦城贫困人口的比重是14%左右[1]153。1552年伦敦城“懒惰成性”的流浪汉有200户[15]21,所占总人口的比重达1%,此后还有上升。在伦敦城郊区,贫困和流浪的规模无疑更大。人口的高流动性、年轻化、贫困化,无疑大大加强了伦敦社会的异质性和不稳定性,从而对社区认同和社会稳定提出迫切要求。不过,即使在16世纪90年代的饥馑时期,以及17世纪40年代的内战时期,伦敦均未出现来自底层的大规模社会暴动,仅仅出现政治和宗教革命。伦敦如此,英国其他地方亦如此。英国基层社会基本稳定,基于贫富分化的社会暴动基本销声匿迹。从16、17世纪英国的经历来看,在社会转型时期,基层社会的社会分化是不可避免的,但基层社会的大规模动荡是可以避免的。社区认同可以部分消解人们之间的疏离感,是避免社会动荡、实现社会稳定的有效手段。
从16、17世纪伦敦的经历来看,仪典在推进社区认同、实现社会稳定方面起过很好的作用。在伦敦人口规模快速膨胀、教堂仪典资源的压力增大的情况下,堂区仪典仍能维持较高的参与出席率。究其原因,除了宗教虔诚与传统文化的魅力之外,还有两个新因素在持续发挥作用。一个新因素是新富阶层对社会权力的追求。古往今来,仪典都是彰显社会权力的有效手段。在宗教改革前,社会分化并不严重,富人不多且在宗教上的地位低于穷人,而神职人员的地位突出,仪典主要是彰显教会和神职人员权力的手段。在宗教改革期间及其后,神职人员的地位下降,富人在经济和宗教上的地位大幅上升,仪典成为富人彰显社会权力、提升社会地位的有效手段。另一个新因素是贫民阶层对慈善救济的需求。济贫本来是宗教慈善的一部分,是富人向穷人进贡进而获得灵魂救赎的基本途径之一。在宗教改革后,济贫成为世俗公益的一部分,堂区将参加仪典与接受济贫相联系,使仪典成为社会控制的有效手段。部分穷人对堂区仪典的参与热情,主要出于领受救济金的目的。总体看来,推进堂区仪典参与的因素主要有宗教虔诚、社会权力、慈善救济等。这些因素尽管在宗教改革前就存在,但其重要性明显有别。在宗教改革前,主要是教会权力与宗教虔诚。在宗教改革后,宗教虔诚仍然重要,但世俗权力的上升、社会救济的捆绑等新因素在提升堂区仪典参与水平、消解人口疏离和流动、重组社会秩序方面的作用不容小觑。堂区仪典用一条来自传统的宗教情感纽带,外加权力象征和利益捆绑的世俗链条,将社会中上层与下层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将新富阶层与贫民阶层联结为一体,从而成为推进转型时期伦敦社区认同的有力手段。
综上所述,16、17世纪的英国之所以能在社会基本稳定的背景下成功实现社会转型,社区认同的巩固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从伦敦的经历来看,仪典在推进堂区认同、实现社会稳定方面起过大的作用。在人口规模快速膨胀、教堂仪典资源不足的情况下,伦敦堂区仪典仍能维持较高的参与水平。究其原因,除了宗教虔诚的基本因素之外,还有新富阶层对社会权力的追求、贫民阶层对慈善救济的需求等新因素的作用。关于近代早期伦敦堂区仪典与社区认同的研究,可以加深对城市社会转型的认识。
[1] Ian W. Archer. The Pursuit of Stability: Social Relations in Elizabethan London[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2] Michael Berlin. Reordering Rituals: Ceremony and the Parish, 1520-1640[C]//Paul Griffiths, Mark S. R. Jenner, eds. Londinopolis: Essays in the Cultural and Social History of Early Modern London.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0.
[3] K. D. M. Snell. Parish and Belonging: Community, Identity and Welfare in England and Wales, 1700-1950[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4] N. J. G. Pounds. A History of the English Parish: The Culture of Religion from Augustine to Victoria[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5] Ken Powell, Chris Cook. English Historical Facts 1485-1603[M]. London: The Macmillan Press, 1977.
[6] C. H. Williams, ed. English Historical Documents, 1485-1558[M]. London: Routledge, 1999.
[7] 彼得·伯克.欧洲近代早期的大众文化[M].杨豫,王海良,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8] William Harrison. The Description of England[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68.
[9] 向荣.移风易俗与英国资本主义的兴起[J].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3):382-387.
[10] John Stow. The Survey of London[M]. London: J. M. Dent, 1929.
[11] Caroline M. Barron. London in the Later Middle Ages: Government and People 1200-1500[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12] Peter Clark, ed. The Cambridge Urban History of Britain, Volume II: 1540-1840[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13] 邓云清.转型期的伦敦移民问题与政府治理[J].理论月刊,2006(4):161-163.
[14] 邓云清.转型时期伦敦的移民文化及其建设——兼论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关系[J].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0(1):73-75,89.
[15] W. Lempriere, ed. John Howes’ MS., 1582[M]. London, 1904.
责任编辑 张颖超
2013-08-20
邓云清,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西部和边疆地区项目“转型时期英国城市公益体系的构建与结构城市化研究”(13XJA770001),项目负责人:邓云清;西南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盎格鲁-撒克逊法研究”(SWU1409122),项目负责人:邓云清。
K561
A
1673-9841(2014)02-017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