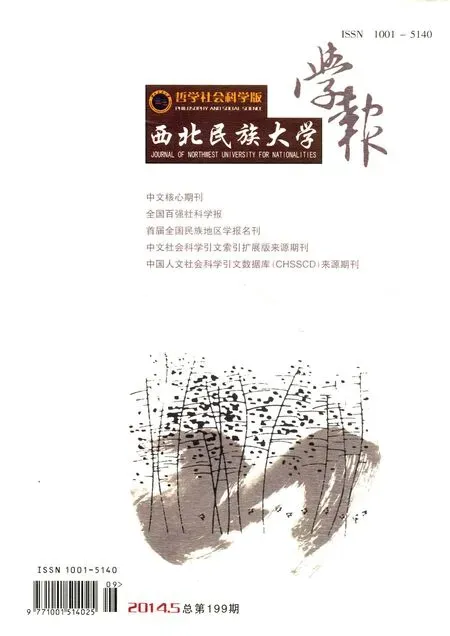文化人类学与“古史新辨”——以郑振铎《汤祷篇》为中心
2014-03-03苏永前
苏永前
(西安外国语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学院,陕西 西安710128)
一、从“疑古”到“释古”
提起20世纪前期的中国史学,许多人可能对冯友兰“信古”“疑古”与“释古”的划分耳熟能详。其实,这种划分的始作俑者并非冯友兰,在其之前,学界已有类似划分。比如1930年,时为南京中央大学史学系学生的张崟在《古史甄微质疑》一文中指出:“年来研究中国古史之风,一时颇盛,而要而言之,大抵不外:(一)旧史学派,(二)新史学派,(三)疑古派。”[1]这里所谓“旧史学派”,实即“信古”一派,因其“一遵往古代代相承之说,亦步亦趋,不稍更易”[2];而“新史学派”,指以王国维为代表的“释古”一派,他们“依地下掘得之新史料,以补旧史之偏而救其弊”[3];“疑古派”自然是以顾颉刚为代表、以《古史辨》为中心的一批史学同仁。
1935年,冯友兰在《中国近年研究史学之新趋势》一文中,首次对“信古”“疑古”与“释古”3派作出明确界说:“中国近年研究历史之趋势,依其研究之观点,可分为三个派别:(一)信古,(二)疑古,(三)释古。‘信古’一派以为凡古书上所说皆真,对之并无怀疑。‘疑古’一派,推翻信古一派对于古书之信念,以为古书所载,多非可信。‘信古’一派,现仍有之,如提倡读经诸人是。”[4]数日后,冯友兰在北平辅仁大学的演讲中对上述观点再次作了申述。所不同的是,他将此前“信古”“疑古”与“释古”3派概括为前后相续的3个阶段,“(一)信古——学者具有此种态度较早,是最缺乏批判精神的,所以后来研究史学的对于这种态度渐渐发生转变”[5];“(二)疑古——关于疑古,是发生于信古以后,是研究史的另外一种态度,此种自较盲目的信古态度进步些,可是立于研究的立场上说,仍是属于消极方面的,而于研究的效率方面,亦不能得到满意的进展”[6];“(三)释古——释古是研究史学的第三种态度,是与信古、疑古两者迥不相同的,同时也是研究史学的态度进步到第三个阶段”[7]。这种概括并不完全符合事实:王国维“释古”力作《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其《续篇》早在1917年发表,而作为“古史辨”派宣言的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则迟至1923年才问世。不过,这并未影响这一概括的风行。自冯友兰关于20世纪前期中国史学的“三派”或“三阶段”说提出之后,很快在学界引起共鸣。后来的学者如杨宽、柳存仁等,多在其基础上作进一步引申。值得一提的是,当时3派之中,影响最大的无疑是以顾颉刚为首的“疑古”一派:“近三十余年(大约自1917年蔡元培长北京大学时起至1949年全国解放时止)疑古学派几乎笼罩了全中国的历史界,可是它的大本营却在《古史辨》及其周围。”[8]其流风所及,以至《古史辨》第七册于抗战中期出版时,学界竟有千呼万唤、众目以待之势:“渴望已久之《古史辨》第七册由童书业君继续编纂现已完成,行将在上海开明书店出版,想士林必以先睹为快,故本刊特介绍其目录于左。”①见《责善半月刊》第1卷第8期(1940年6月30日)“学术消息”栏。
以顾颉刚为首的“古史辨”派,揭起“疑古辨伪”的大旗,推倒了两千年来唯经是尊、盲目崇古的治学风尚,其贡献无论从学术史,还是从思想史的层面来衡量均不可低估。不过,“古史辨”派也并非无可指摘,在致力于推倒“伪古史”的同时,他们回避了“古史重建”这一更为重要的问题。此外,“古史辨”派因疑古而否定全部上古史的真实性,甚至断言“东周以上无信史”[9],这种极端疑古的态度自然会招致许多人的反对。早在《古史辨》第一册出版后不久,陆懋德即为之撰文,在肯定其积极意义的同时,也指出顾颉刚诸人未能借助新材料而达成最终结论:“然吾披阅顾君之书一过,甚服其读书之细心,及其疑古之勇气,然亦惜其惟知作故纸堆中之推求,而未能举出考古学上之证据,故辩论数十万言而未得结果也。”②见《清华学报》第3卷第2期(1926年12月)“介绍与批评”栏。相形之下,前文提到的中央大学学生张崟,对“疑古”一派的批评分外尖刻:“其疑古一派,则稍闚皮毛,率尔立异,师心自用,如饮狂药,一切旧史,目为土饭;以现代之理论,决遂古之事实;深文周纳,惟意所欲,裂冕毁裳,靡所不至;如以尧舜为神非人,以伯禹共虫等眎,其著例也。”[10]这种近乎谩骂的批评当然不可取,不过得承认,它也体现了当时一些学人对于“古史辨”派的态度。
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郑振铎虽然主要以文学史家名世,不过他对史学界的情形也十分关注。在《汤祷篇》一文开篇,郑振铎便说:“古史的研究,于今为极盛;有完全捧着古书,无条件地屈服于往昔的记载之下的;也有凭着理智的辩解力,使用着考据的最有效的方法,对于古代的不近人情或不合理的史实,加以驳诘,加以辨正的。顾颉刚先生的《古史辨》便是属于后者的最有力的一部书。”[11]如果借用冯友兰的表述,这里所说的第一种研究,可称为“信古”;第二种研究,当属“疑古”。两者之中,郑振铎对后者表示肯定:“顾先生重新引起了人们对王充、郑樵、崔述、康有为诸人的怀疑的求真的精神。康氏往往有所蔽,好以己意强解古书,割裂古书;顾先生的态度,却是异常的恳挚的;他的‘为真理而求真理’的热忱,是为我们友人们所共佩的。”[12]尽管如此,郑振铎在古史问题上仍然与顾颉刚有着根本的分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顾颉刚认为“古书皆伪”,郑振择则以为“古人或不至像我们所相信的那末样地惯于作伪,惯于凭空捏造多多少少的故事出来;他们假使有什么附会,也必定有一个可以使他生出这种附会来的根据。愈是今人以为大不近人情,大不合理,却愈有其至深且厚,至真且确的根据在着”[13]。2.顾颉刚“疑古辨伪”主要凭借的是古代流传至今的书面典籍,方法上遵循的是乾嘉考据学传统;郑振铎却认为“老在旧书堆里翻筋斗,是绝对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以外的。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旧书堆里的纠纷,老是不会减少的”[14]。说到底,在郑振铎看来,顾颉刚等人所从事的“疑古辨伪”仅代表古史研究的一个阶段,因而他说:“但我以为,顾先生的《古史辨》,乃是最后一部的表现中国式的怀疑精神与求真理的热忱的书,她是结束,不是开创,他把郑崔诸人的路线,给了一个总结束。但如果从今以后,要想走上另一条更近真理的路,那只有别去开辟门户。”[15]所谓“别去开辟门户”,便是采用新的材料和新的眼光对古史进行解释。前文已述及,早在1917年,王国维已发表“释古”力作《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其续篇。不过,受过传统金石学训练的王国维,所采用的“新材料”主要是殷墟甲骨卜辞,所采用的“新方法”是“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相互参证的“二重证据法”。而曾经留学欧洲,又对俗文学长期保持兴趣的郑振铎,所倡导的“新材料”与“新方法”,主要是综合人类学、民俗学与考古学资料进行跨文化参证的“立体释古”方法:“自从人类学、人种志和民俗学的研究开始以来,我们对于古代的神话和传说,已不仅视之为原始人里的‘假语村言’了;自从萧莱曼在特洛伊城废址进行发掘以来,我们对于古代的神话和传说,也已不复仅仅把他们当作是诗人们的想象的创作了。”[16]郑振铎所推崇的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便是当时运用摩尔根的人类学理论解释中国古史的典范。基于上述认识,郑振铎才有了“古史新辨”的设想:“我对于古史并不曾用过什么苦功;对于新的学问,也不曾下过一番好好的研究的功夫。但我却有一个愚见,我以为《古史辨》的时代是应该告一个结束了!为了使今人明了古代社会的真实的情形,似有另找一条路走的必要。如果有了《古史新辨》一类的东西,较《古史辨》似更有用。也许更可以证明《古史辨》所辨正的一部分的事实,是确切不移的真实可靠的。这似乎较之单以直觉的理智,或以古书考证,为更近于真理,且似也更有趣些。”[17]
《汤祷篇》的写作,正是郑振铎对于上述设想的实践。这篇论文最初发表时,副标题便是“《古史新辨》之一”。
二、郑振铎与《金枝》
由于郑振铎“古史新辨”主要采用的是人类学跨文化比较方法,因而在讨论《汤祷篇》之前,有必要对郑振铎与文化人类学的关系作一梳理。与当时多数文史学者一样,郑振铎所受文化人类学的影响主要来自古典进化论学派。《汤祷篇》第四节的标题即为“蛮性的遗留”,作者对此虽未作任何说明,但对人类学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这一概念来自爱德华·泰勒的《原始文化》。在此前已出版的《文学大纲》中,郑振铎曾援引安德鲁·兰的话,从人类学角度追溯文学的发生:“安特留·兰说:‘在野蛮人看来,天空、太阳、海洋及风,不仅是人类,而且他们是野蛮人。’古代的人,具有这种观念在心里,于是他们所答复的宇宙的问题,便天然地取了故事或所谓神话的形式。当文学开始创造,人类开始著作之时,他们天然地要最先的把那些一代一代复述下来的熟知的故事,如关于生与死的神秘与人对于所住的世界的一般关系之类的,述写下来,这些神话便是文学的最初基石。……文学的开始大多数皆为神的行为的记述,而当宗教观念发达,人类建筑庙宇时,在世界的许多地方,庙宇又为书籍的最初的家。”[18]同一书中,在解释不同民族间神话传说等相同的原因时,郑振铎对“偶然说”“同源说”表示不满,而对古典进化论人类学派的“心理共通说”给予很高评价:“我们研究民歌与民间传说,有一件事实觉得极重要而且极有趣味。东方所歌咏的事物与西方所歌咏的事物都有很相同的,而许多同样的故事,也同为世界一切人民所传述。这种神话的广播的原因,曾有许多理论来解释过它。……最令人满意的解释是说,同样神话之所以有普遍性,是因为它们是普遍的经验与情感的结果。安特留·兰说:‘他们是初民心中的粗率产物,还没有印上种族与文化的歧异的特性的。’”[19]
不过,如果要在古典进化论人类学中选出一部对郑振铎影响最深的著作,恐怕非弗雷泽的《金枝》莫属。周予同在为《汤祷篇》一书所作的序言中写到:“什么时候,他读到佛累才(J.G.Frazer)的《金枝》(The Golden Bough),我不清楚,但他被这部书迷住了!他藏有原著本,又有节本。他曾经有这样的计划,为了扩大中国学术的部门,想着手翻译这部民俗学大著,设法接洽承印的书店;后来因为时间不够,书店也不易接受,又想改译节本,但都没有实现。”[20]查郑振铎早年日记,1928年2月4日写到:“今天购得J.G.Frazer的《Golden Bough》。”[21]此时郑振铎正在欧洲游学,所购《金枝》为何种版本虽然未作交待,但起码可以肯定,早在这个时候,他已经藏有《金枝》一书。此外,郑振铎1957年4月16日致刘哲民的信中说:“家晋兄的信已经收到了。《金枝》他愿续译下去,最好。惟英文本尚未找到,俟借到,即寄去。”[22]5月12日郑振铎致刘哲民的信中又说:“《金枝》的译文,我所已译的部分,归后,也即当寄上。”[23]5月20日郑振铎致刘哲民的信中再次说到:“《金枝》节本的原书,找了几天,还没有找到。一找到,当即行寄上。我只译了五万多字。”[24]可见,郑振铎已将《金枝》译出一部分。刘哲民此时在出版部门工作,两人信中所谈,当是《金枝》一书的翻译及出版事宜。遗憾的是,此书尚未译完,郑振铎次年便不幸罹难。直到30年后的1987年,《金枝》中译本才首度在国内面世。
从《汤祷篇》一文来看,所受《金枝》的影响也十分明显。作者不仅援引弗雷泽的“祭师王”理论对“汤祷”传说进行解释,第六部分更是以“金枝”为标题,对弗雷泽的这部大著作了介绍:“英国的一位渊博的老学者Sir James George Frazer尝著了一部硕大深邃的《金枝》(The Golden Bough,a Study in Magic and Religion)专门来解释这个问题。单是说起‘王的起源’(Origin of the King,《金枝》的第一部分)的一个题目,已有了两厚册。所以关于理论上的详细的探讨,只须参读那部书(当然还有别的同类的书)已可很明了的了。(《金枝》有节本,只一册,Mecmillan and Co.出版)本文不能也不必很详细地去译述它。”[25]
进一步比较会发现,《汤祷篇》不仅对《金枝》一书的理论多有借鉴,甚至在行文风格上也与《金枝》酷肖。熟悉《金枝》的人都知道,作为文学造诣极深的古典学者,弗雷泽在《金枝》一书开篇,便对内米湖畔的如画美景与其间上演的惨剧作了尽情渲染。而在《汤祷篇》第一部分,郑振铎同样用散文化的笔法,勾勒了一幅紧张不安的“人祭”场面。
三、《汤祷篇》的学理分析
1933年1月1日,郑振铎在上海《东方杂志》第三十卷一号发表《汤祷篇》。文章在正式讨论“汤祷”传说之前,还有一段用小号字体排版的序言,谈的正是上文反复引述过的对于古史的看法。今天出版的各种郑振铎文集,均将序言与正文用同一字号排版,序言的“总纲”性质反倒不大明显。
在《荀子》《尸子》《吕氏春秋》《淮南子》和《说苑》等典籍中,均载有商汤祈雨的传说,这些传说大体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商汤派人去祈雨,如《说苑》所载:“汤之时,大旱七年,雒坼川竭,煎沙烂石,于是使人持三足鼎祝山川,教之祝曰:政不节邪?使人疾邪?苞苴行邪?谗夫昌邪?宫室营邪?女谒盛邪?何不雨之极也!盖言未已而天大雨。”[26]
另一种则是商汤“以身为牺牲”,“剪发断爪”而祷于桑林。这种类型在古代典籍中占多数,如《吕氏春秋》所载:“昔者汤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汤乃以身祷于桑林,曰:‘余一人有罪,无及万夫。万夫有罪,在余一人。无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伤民之命。’于是剪其发,磨其手,以身为牺牲,用祈福于上帝。民乃甚悦,雨乃大至。”[27]这些记载至少会引发两方面疑问:第一,上述两种类型中,哪一种较少经过后世文人的改篡,因而更加接近传说的原初形态;第二,传说中所讲述的故事是否真的发生过?
对于第一个问题,郑振铎依据人类学派的观点,认为“在古代的社会里,也和今日的野蛮人的社会相同,常是要发生着许多不可理解的古怪事的。愈是野蛮粗鄙的似若不可信的,倒愈是近于真实”[28]。上述两种类型中,第二种讲述商汤“以身为牺牲”,显然与其作为王者的至尊地位有所不合,因而更加难以理解,却也因之更加“近于真实”[29]。
对于第二个问题,过去的学者如宋代张南轩、明代李九我、清代崔述等早已作过探讨。他们立论虽有所不同,在否认这件事的真实性上却态度一致,因而纷纷加以驳诘。比如,崔述在《商考信录》中引述张南轩的话说:“史载成汤祷雨,乃有剪发断爪,身为牺牲之说。夫以汤之圣,当极旱之时,反躬自责,祷于林野,此其为民吁天之诚,自能格天致雨,何必如史所云。且人祷之占,理所不通。圣人岂信其说而毁伤父母遗体哉!此野史谬谈,不可信者也!”[30]崔述本人更是运用考据学方法对“汤祷”传说进行辩驳。不过在郑振铎看来,这些学者的话实在幼稚得可笑,他们最根本的问题,是“以最浅率的直觉的见解,去解释古代的历史”[31]。进一步说,上述诸人的观点之所以不可取,就在于他们缺乏有关上古史的知识,而“站在汉,站在宋,乃至站在清,以他们当代的文化已高的社会的情况作标准去推测古代的社会的情况”[32]。此外,如果对中国学术史作一通观,会发现这种以后世的理性对古史妄加怀疑的现象并非孤例。自东汉王充至清代崔述,可以梳理出一条源远流长的“疑古”传统。其在当代的继承者,自然非“古史辨”派莫属。这些学者的“疑古”精神诚然可贵,但因为不了解上古文化的真相,所得结论难免会出现偏差。要走出这种误区,需要对人类早期文化有所了解,这样才有可能避免“以个人的理性来修改、来辨正古史”[33]。郑振铎的主要意图,正是借助古典进化论人类学所提供的上古文化图谱,对崔述等人的观点进行反驳,进而证明“汤祷”传说并非古人的“伪造”。当然,郑振铎也意识到,他与崔述等人的根本分歧,并不在于“汤祷”事件本身,而是古代是否真的曾经“以王为牺牲”。只要能证明这一事实为真,“汤祷”传说自然有了历史的依据。不过,对远古时代“以王为牺牲”这一事实的证明,需要分3个步骤进行。
第一,古代是否有过“人祷”行为。对于这一问题,郑振铎举中外典籍中的相关记载作为参证。《史记·六国年表》载:秦灵公八年,“初以君主妻河”[34];《史记·滑稽列传》也载有魏文侯时邺人为河伯娶妇的事。此外,古希腊悲剧作家欧里庇得斯(Euripides)的名剧《伊菲吉妮娅》(Iphigenia)中,也讲述希腊人将阿伽门农之女伊菲吉妮娅作为牺牲献给阿尔忒弥斯(Artemis)之事。从这些记载可知,“祈雨而以‘人’为牺牲的事,乃是古代所必有的”[35]。到了后世,才渐被发和爪,乃至牛和羊代替。对于“汤祷”传说而言,“虽然‘旱’未必是‘七年’,时代未必便是殷商的初期,活剧里主人公也许未必便真的是汤,然而中国古代之曾有这幕活剧的出现,却是无可置疑的事。——也许不止十次百次”[36]!如果从西方“原型批评”的角度来审视,“人祷”应当是一种“仪式原型”,商汤祈雨传说不过是这一仪式原型的“置换变形”。郑振铎的考察重点,正是这一原型本身,而非由该“原型”所衍生出的种种不同形态。
第二,古代是否曾经以王为牺牲。相对而言,在中国古代典籍中,对于以王为牺牲的记载较为少见。针对这一难题,郑振铎援引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的著名命题“蛮性的遗留”(survivals),通过《诗经》以降历代典籍中的蛛丝马迹来对上古历史进行“还原”。比如,《大雅·云汉》讲述天下大旱,周宣王忧思不已,作者据此推断:“在周的时代,为了一场旱灾的作祟,国王还是那末样的张皇失措,那末样的焦思苦虑,那末样的求神祷天,那末样的引咎自责;可见在商初的社会里,而发生了汤祷的那样的故事是并不足为怪的。”[37]由此出发,郑振铎进一步引申道:“不仅此也;从殷、周以来的三千余年间,类乎汤祷的故事,在我们的历史上,不知发生了多少。天下有什么‘风吹草动’的灾异,帝王们便须自起而负其责;甚至天空上发现了什么变异,例如彗星出现等的事,国王们也便都要引为自咎的下诏罪己,请求改过。”[38]显然,后世帝王的“下诏罪己”与周宣王的“引咎自责”一样,不过是更早时候“汤祷”一类故事的“蛮性遗留”。正因为此,作者不厌其烦地梳理了自西周直到明代的各种灾异现象以及帝王对此的反应,以作为商汤“以身为牺牲”的参证:“他们这些后代的帝王,虽然威权渐渐地重了,地位渐渐地崇高了,不至于再像汤那末地被迫的剪去发和爪,甚至卧在柴堆上,以身为牺牲,以祈祷于天;但这个远古的古老的习惯,仍然是保存在那里的。他们仍要担负了灾异或天变的责任;他们必须下诏罪己,必须避殿减膳,以及其他种种的‘花样’。”[39]在郑振铎看来,既然历史上每逢灾异帝王们仍要“下诏罪己”,那么以此逆推,在上古时代,商汤牺牲自身来祈雨便不足为怪。
第三,为何要以王为牺牲。解决了第二个问题,我们接着可能会问:为什么不选择某个地位低下者(比如奴隶或罪犯),而必须以国王自身作为牺牲?对于这一问题,郑振铎借助英国人类学家弗雷泽的“祭师王”理论来作答。在《金枝》中,弗雷泽用大量民族学资料表明,古代的王与祭师两种身份常常合二为一。比如在罗马及其他拉丁城市,总有一位被称为“祭王”或“祭仪之王”的祭师,他的妻子也被称为“祭仪之后”。在雅典共和国,第二位每年的主国事者,也被称为“王”,其妻则被称为“后”,两者的作用均属宗教性质。更值得注意的是,在“野蛮社会”里,身兼祭师职务的部落首领被认为具有神秘的魔力,或者干脆被视作能呼风唤雨、使谷物成熟的神灵。不过,这种集世俗与神圣权威于一身的职位看似显赫,其实却潜伏着危险。每逢灾祸发生,“野蛮人”在祈祷无效、极端失望之时,往往要迁怒于国王。中国民间祈雨时“打龙王”一类的民俗活动,正是这种现象的“遗留”。此外,根据古希腊传说,古代的Achai人在饥荒或瘟疫时,常要在Laphystius山的高处,把国王作为牺牲献给宙斯,因为祖先告诉他们,只有国王才能担负民众的罪过。古希腊悲剧《俄狄浦斯王》一开幕,讲述忒拜城遭受瘟疫,城里的民众集合于王宫前面,祈求国王的救护。中国的“汤祷”传说,与上述古希腊神话传说一样,正是“祭师王”原理的体现:“我们昔时的许多帝王们,他们实在不仅仅是行政的领袖,同时也还是宗教上的领袖;他们实在不仅仅是‘君’,且也还是‘师’;他们除了担负政治上的一切责任以外,还要担任一切宗教上的责任。汤祷的故事,便是表现出我们的原始社会里担负这两重大责任的‘祭师王’,或‘君师’所遇到的一个悲剧的最显然的例子。”[40]行文至此,原本迷雾重重的“汤祷”传说终于峰回路转,拨云见日。
四、余论
《汤祷篇》问世不久,曹松叶在《东方杂志》第三十卷十三号发表《读〈汤祷篇〉》一文作出回应。对于郑振铎“古史新辨”的设想,作者在文中表示赞同:“我对于郑先生主张研究古史,应别开门户,别走新路,完全同意。我的心里早有这种意思。今天读郑先生的文章,不禁起了共鸣的作用。我以为不但研究古史应别走新路,即研究中世史近世史,若专用理智去判断,足有不少的错误,不能知道当时的真面目。……但以民族学、民俗学、人类学的眼光去看,那又是另外一种样子了。”[41]不过,曹松叶此文的重点,则是针对《汤祷篇》一文的具体论证从5个方面提出质疑。1.“汤祷”为主动抑或被动;2.商汤“献身”的动机何在;3.“吃耶稣”“打龙”是否同于“汤祷”;4.祭师与王的出现孰先孰后;5.“活剧”的主人翁究竟是否是商汤?正如作者所言,以上5个问题中,后面4个“乃枝节问题”[42],第一个问题却“极关重要”[43],因而作者用了多达一半的篇幅,以表明“汤祷”一事为“自动而非被动”[44]。笔者以为,即便如曹松叶所言,“汤祷”乃主动而非被动,也不影响《汤祷篇》一文的结论。在郑振铎看来,“汤祷”是否为主动或被动,甚至“人祷”这幕“活剧”是否发生在殷商、主人公是否为商汤均不重要。说到底,作者只是力图表明:“中国古代之曾有这幕活剧的出现,却是无可置疑的事。”[45]——只有后一问题,才是郑振铎与历代“疑古家”的真正分歧所在。只要能证明“以王为牺牲”这一文化现象在中国上古时代确曾存在,则崔述诸人据后世理性以怀疑古史的做法会不攻自破。郑振铎之后,李宗侗在《中国古代社会新研》一书中,对于“汤祷”传说的解释与此如出一辙[46]。此外,对于渺茫难稽的古史传说而言,文献资料往往所得有限,考古发现又带有极大的偶然性。除非我们试图回避“古史重建”这一问题,否则,郑振铎在此文中所采用的借助异文化资料重构古史的方法,依然有其无可替代的价值。
需要一提的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国内兴起文学人类学研究的潮流,其主要方法之一,便是综合运用传世文献、出土文献与民族志资料的“三重证据法”。不难看出,这一方法与郑振铎的“古史新辨”设想一脉相承。从这个意义上说,《汤祷篇》不仅是“古史新辨”的典范之作,也是中国文学人类学史上的早期典范之作。
[1][2][3][10]张崟.古史甄微质疑[J].史学襍志,1930,(3).
[4]冯友兰.中国近年研究史学之新趋势[A].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十四卷[C].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255.
[5][6][7]冯友兰.近年史学界对于中国古史之看法[J].骨鲠,1935,(62).
[8]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26.
[9]胡适.“研究国故”的方法[A].胡适.胡适全集:第十三卷[C].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45.
[11][12][13][14][15][16][17][25][28][29][31][32][33][35][36][37][38][39][40][45]郑振铎.汤祷篇[J].东方杂志,1933,(1).
[18][19]郑振铎.文学大纲(上)[M].上海:商务印书馆,1927.15-16,17.
[20]周予同.汤祷篇序[A].郑振铎.郑振铎文集:第四卷[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466.
[21]郑振铎.郑振铎日记全编[C].陈福康整理.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6.86.
[22][23][24]郑振铎.致刘哲民[A].郑振铎.郑振铎全集:第十六卷[C].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8.431,435,436.
[26]向宗鲁.说苑校证[M].北京:中华书局,1987.20.
[27]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2009.200-201.
[30]崔述.考信录(二)[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217.
[34]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705.
[41][42][43][44]曹松叶.读《汤祷篇》[J].东方杂志,1933,(13).
[46]李宗侗.中国古代社会新研[M].北京:中华书局,2010.152-1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