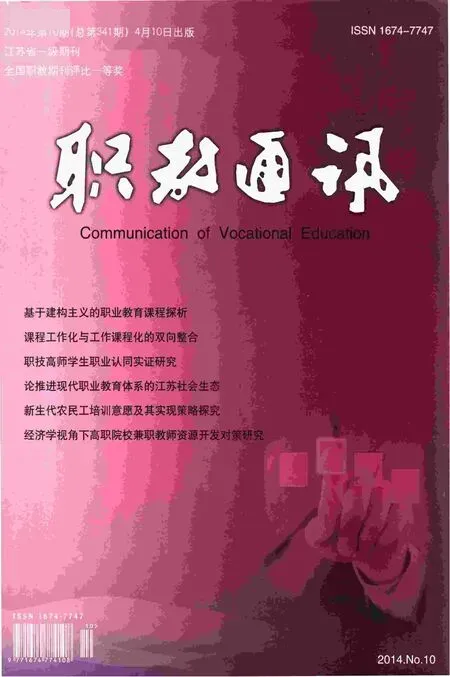性别视阈下民国女子职业教育
2014-02-05陈韦吉
陈韦吉
性别视阈下民国女子职业教育
陈韦吉
从社会性别视阈来分析民国初期的女子职业教育,其教育理念、教育方针主要由男性倡导和推动,目的在于实现女学和经济生产的“联姻”,完成实业发展和民族振兴。民国时期女子职业教育遭遇的诸多困境,则反映出女性生活需求的觉醒与男权中心为基础的社会存在之间的偏差。直至女子职业教育延伸进立法决策,也始终是在男权制定的标准下获得的有限教育机会和单薄的教育内容。
女子职业教育;偏差;民国时期;性别视阈下
女子职业教育进入到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关注视野,与源自戊戌变法时期的近代女学兴起密不可分。从维新派受到西方思想文化的熏陶、祈望女子教育发展能成为救国救民一条有效途径,到晚清政府兴办女子实业教育,为救亡图存做最后一丝努力,直至民国时期有关女子职业教育的一系列法令出台,号召妇女“经济独立”,积极投身社会服务。女子职业教育问题从来都不是单纯的女子自我意识觉醒及生活诉求问题,而是被作为一种有利于建构优势民族、振兴国家经济的重要渠道。
一、性别视野下的教育诉求
近代中国女子职业教育最大的瓶颈在于该种教育形式的发展并非掌握在妇女本身。女子职业教育从一开始就不是一种自发的以性别觉醒为前提的教育创新,妇女的职业教育是由近现代史上那些对民族历史有所反省的先觉者们提出的,后来又不断地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下来。
民国女子职业教育是在晚清倡导的女子实业教育上生发而来的。甲午战败后,以康梁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为减缓民族危机提出“物质救国、实业救国”的主张,有关于此的“上谕奏折”不下数十件。[1]康有为在上奏光绪皇帝的过程中力主广设“专门学”,即实业学校,并对“专门学”做出了详细解释,其中,除了偏重男性技艺的铁路、重工艺、矿学以外,也有偏女性技艺的茶务、桑蚕等学校。而梁启超则是明确提出了女子实业教育的重要性,他在1896年《时务报》上发表的《变法通议.论女学》中表示“女子二万万,全属分利”,中国之所以贫弱是因为“妇人无业,实为最初之起点”,并且举以美、英、法、德、日本等国之例分析“是故女学最盛者,其国最强”。这一时期的女子职业教育尚处在播种阶段,播种的目的还仅是面对积贫积弱的中国现状、围绕“救国”意图展开。
晚清政府层面的实业教育几乎没有涉及女子实业教育的倡导,政府改良派的作为也只是源于对先进西方围攻下的积极回应,洋务中的技艺学习重点在“练兵制器”“军用工业”等“制夷”的目的中。相反社会层面的实业教育由于更重视实业教育与民间经济生产的结合,因此,在不断的办学渗透中,开始出现了女子职业教育的萌芽。1897年,浙江道监察御史林启就“王政、浙省以及时局”三角度详述了筹款创设杭州养蚕学堂的理由,并于当年三月招生开学。当时的蚕学馆还没有招收女生,但是,蚕学馆毕业生之一史量才于1904年在上海创办了第一所女子蚕业学堂,开创了我国女子职业教育先河。[2]史量才建立女子蚕业学堂是基于当时农村推广的重要目的,女子是我国蚕桑生产活动的主力,尤其是在农村,女蚕校招收女生,更加便于传授蚕桑生产知识,能更直接地提高生产技术。[3]当时中国蚕丝业之所以为社会进步人士所关注,并且为民国女子职业教育的实现首先走出了一条具体的道路,是基于一个特殊的背景之下的。丝货长期以来是我国最重要的输出货物之一,遍布全球市场,在国际上享有至高无上的美誉。以生丝中的代表“辑里湖丝”为例,就曾在1851年的世博会上一举夺金,是我国第一个获得国际大奖的民族工业品牌。晚清末期,由于中国缫丝技艺现代化程度不高,引起西欧商人的极度抱怨。另一方面,国际舞台中出现它种丝的不断挑战,使得国内相关行业难以为继。史量才的上海女子蚕业学堂建校宗旨之一就是“挽回我国利权为宗旨”。最关键的是中国丝自身存在着不可忽视的问题——蚕子有病,世代相传,恐会灭绝。于是,以教育为中心的蚕丝业改良运动开始了。这一时期的女子职业教育已经开始萌芽,虽然着力考察女子和社会经济的关系,但是,落脚点仍然是为近代中国社会发展寻求出路。
民国初年教育思想家们相继提出了一系列女子职业教育的诉求,并形成了一定的影响,其中,以蔡元培、陆费逵、黄炎培等为主要代表。蔡元培的女子职业教育主张可以追溯到他的《学堂教科论》等著名书籍中的论述,蔡元培主要是从三个要害处——即男子、家庭以及国家等对象角度出发分析,指出“女子不学”带来的三大流弊:(1)倚重男子;(2)使一家受其累;(3)使国家蒙其害。其意图更多旨在表明女子受教育、有职业对他者的重要性,而不是着重在女子作为一个群体需要发展的角度。陆费逵表示两性有别,男女生理基础有异,女子的生理较弱,并且将来要为人妻、为人母、为家庭之主妇[4],因而,女子职业教育应“以妻之教育,母之教育,适宜职业之教育,为女子教育之主义”“当设女子裁缝、刺绣、蚕业等学校,期可以习一业为生活”“不可以接受政治家、军人等职业教育”。[5]陆费逵的女子职业教育思想紧密结合当时社会的实际情况以及女子本身的生理水平,其思想主张将女子实际情况纳入考量范围,但仅限于生理层面,女子精神层面的述求依然没有被提及。女子职业教育是黄炎培整个职业教育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6]早期,黄炎培的女子职业教育从提倡“生活教育”开始,即女子可以通过受到良好的生活教育就可以更好的服务家庭。显然,这个时候黄炎培的女子职业教育还比较注重“家中心”。在黄炎培看来,女子接受职业教育是一种手段,目的是获取女子在经济上的独立,进而可以“家庭幸福、国家稳固”,达到社会进化。在女子职业教育科类设置的探讨上,黄炎培则反复强调”家政和手工科”之于女子的重要性,甚至要求在各级女校中提倡“家事教育课程”。当然,黄炎培这样的女子职业教育选择也是为当时社会情况所牵绊。
上述女子职业教育的理论以男性层面的主张与倡导居多,其出发点紧紧围绕“家庭”“经济”“民族”“国家”“社会”等层面展开。当然,也有对女子生活需求及意识觉醒的关注,但是,这毕竟不是男性层面主张的根基所在。男子主张的女子职业教育似乎更多地是为了女子在社会转型的时期适当转型,然后再以更合适的姿态重新走进旧有社会家庭进化后再造的女子特定角色,尤其是家事科的不断被提及和设计。由男性出发的女子职业教育重在经济生产以及家庭、民族、国家利益。而女性眼里的职业教育,则是女性需求的觉醒以及生活再造的一个窗口,选择女子职业教育不仅只是为了回归家庭,更多的是企图能够在社会动乱变革之际抓住一线希望,寻求女性角色的突围与精神解放。一旦突围成功,将为女子群体造成另一个别样的世界来。
二、民国女子职业教育践行的困境
女子职业教育兴起在一定事实上谈不上是自发的妇女行动,与主流理论中的女子自我解放运动有着本质的区别:这种职业教育的实施针对的是女性,然而,男性却抓住大部分的话语权,女性只是被动地接受了由这些话语权引出的一系列措施,从而变成了决策时的旁观者、实施时的接受者。男子层面的女子职业教育兴起是“改良思潮”,以职业为途径救国于水火中。而女子层面的女子职业教育则企图遵循“启蒙思潮”,以职业为途径达到女子在传统生活中的彻底解放。这两者间的诉求在历史的巨型框架中,容易造成偏差,从而影响近代中国女子职业教育的发展历程。
由于以男子层面出发的女子职业教育思潮更多关注的是女子以职业教育提升地位的形式规定,而不是关注妇女生活的具体需要,因此,当时的女子职业教育并不为当时女子所积极推崇。纵观整个近代中国女子职业教育,其发展速度是十分缓慢的。据民国教育部1916年第五次统计,当时全国实业学校男生数为28 223人,女生占总学生数的6.2%,男生数大于女生数15倍强[7],可见当时的女子职业教育人数之少,势力之薄弱。直到1927年,中等职业学校男女学生总数为39 647人,女生 10 923人,女生百分比仅为27.55% 。[8]
值得一提的是,沈雁冰在《妇女经济独立讨论》中对农村妇女和城市妇女职业诉求做了区分。他认为,农村妇女并不能因职业的存在,而取得经济上的独立,因为旧礼教束缚下的女性是不可能有自由支配自己劳力所得的权利。而城市妇女的职业独立障碍则是社会经济组织。如果没有适宜的社会经济组织,这方面的女子职业教育定然不可能获得全面的成功。因此,如何打破礼教上的束缚以及改革社会经济组织是女子职业教育从女性视角出发得以发展的两个重大前提。近代中国是一个传统农业国家,就农村妇女而言,封建思想根深蒂固。女性对于礼教束缚甚至具有严重的依赖心理,懒于、羞于或者怕于争取自己在职业付出方面的所得。同时,又无法了解女子职业教育能给自身带来什么样切实的利益。因此,很多底层女性都不愿意接受女子职业教育。再者,女子职业学校一定程度上又都是为了传统妇女的发展而开设的,其中的职业课程设置也尽数与她们的现实生活结合。上世纪20年代,女职校的数量有所增加,但科目设置范围较狭窄,大多集中于刺绣、缝纫、卫生等科,如杨鄂联所言:“十校之中仿佛有九校是刺绣、缝纫,间或有育蚕、花边等科”。[9]而随着民生穷困,女子生计日蹙,很多平民女子都出现失学以及无力向学的情况,此时如果仍以学校形式的教育接受职业教育,恐难为大多数底层女子所难容纳。
对于城市妇女而言,在近代女子运动的历史上又必须将其分成两类:一类在女子运动中,乐于追求与男子政治、立法权力方面的平等,趋向去选择高深的学问学堂,这里不做相关阐述。另一类则是城市女性群体中的大多数——劳工妇女,她们更多的是在前类女子团体的帮助下追求职业平等权和职业环境权。杨鄂联认为,对于女子职业教育而言,最大的障碍来自于两难,首要问题就是无适当的职业。[10]其实,职业细化程度不高,适合女子的实业也不够多是当时社会、经济环境所限制的,短时间能不可能改变。因此,对当时的女子职业教育而言首要关注的问题是“无合理的职业环境”。劳工妇女在近代中国历史上不断出现的罢工潮,很多都是源自于女工职业环境的苛刻。近代中国女工所遭受的剥削和压迫十分残酷,工作时间长,一般每天达12—14小时,有时甚至午饭时间也不许休息;工资低,一般女工工资比男工低12%至25%左右;而且,女工们的劳动条件极其恶劣,还经常受到工头的蹂躏和毒打。[11]1922年8月,上海闸北丝厂女工罢工人数达到2万余人,罢工的原因是某女工中暑却不准假,最后间接导致该女工死亡。女工罢工的诉求无非就是要求社会经济组织的改革,比如增加工资、减少工时以及承认女子具有行会建设的权利以便保障劳工妇女享有宽松的职业环境。
女子职业教育的兴办虽然对当时女子技术能力的掌握以及职业渠道的拓宽有一定帮助,但是,男子层面的思潮却没有极力涉及女子职业教育成功与否的保障前提。例如女子职业教育作为一种教育形式有否发挥净化女子职业环境的功能,在这种教育类别的设计中有否建立相关保护女子职业教育果实的行业团体——要求同工同酬,要求行会保护,这些都应该是女子职业教育得以顺利发展必须要提前解决的问题。女子接受职业教育后的出口在哪里,女子职业选择后长期进入的环境应该如何。这些也都是基于女性主义视角必须合理思考的问题。
民国女子职业教育客观上具有启蒙女子意识、满足女子生活需求的意义,但从学者派的话语建构来看,主要并不是从妇女自身出发,而是出于救国家、民族于危亡之际的必然选择。按女性主义理解,女子有业是相对于男性同胞而言的性别比较基础之上的一种权利主张,妇女之所以要有职业、学职业技能是因为男女间的不平等造成的。民国女子职业教育事实上并不是基于两性比较的视角而产生的,而是基于男性单方视角的一种国家语境下的建构。近代中国,饱受列强蹂躏,这无疑是国家稚弱造成的。国家之所以弱,女子衰弱是其中原因之一。中国衰弱因此部分被投射到女子身上,进而扩大到到“女子职业”等一系列问题的辨析。因此,仅就性别视阈来看,女子职业教育更多的是社会精英基于“国家”前提的一种教育创新与建构。精英们的诉求是想以职业教育的形式来改造传统中国妇女。然而,知识从来就不是由对女性生活的提问产生出来的,而是一种基于男性生活的概括。[12]基于女性立场,近代女子职业教育本质上很大程度是蕴含了男性主体的国家民族主义以“女子进步”的名义将职业教育建设强加给了传统妇女。以男子为主的精英层考虑问题以及决策的目的主要在于国家命运的把握,女子是这种命运把握的一条特殊途径,因而,女子职业教育更多的是作为开垦这条途径的一种有效手段。
[1]吴洪成.中国近代职业教育制度史研究[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21.
[2]佚名.上海女子蚕业学堂章程[J].女子世界,1905:6.
[3]范虹珏,盛邦跃.近代太湖地区的蚕业教育与蚕种改良(1897—1937)[J].中国农史,2012(1):39.
[4]王巧玲,王明强.对民初女子职业教育的再反思[J].职业教育研究,2008(5):159-160.
[5]郭俊朝.陆费逵与职业教育[J].教育与职业,2003(7):59-60.
[6]孟凡萍,刘桂林.黄炎培女子职业教育[J].教育与职业,1994(3):12-13.
[7]中华教育改进社.中国教育统计概览[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
[8]民国教育部.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丙编教育统计[M].上海:开明书店,1934:437.
[9]杨鄂联.中国女子职业教育之经过及现况[J].教育与职业,1922(4).
[10]李仁.对于推广女子职业教育之意见[J].教育与职业,1921(6):59-60.
[11]刘巨才.中国近代妇女运动史[M].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89:273.
[12]柳士彬,何爱霞.成人女性性别课程开发初探——女性主义课程论的视角[J].教育研究,2012(3):88.
[责任编辑 金莲顺]
陈韦吉,女,浙江师范大学职业技术教育学院2012级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职业教育管理。
G719
A
1674-7747(2014)10-0058-03